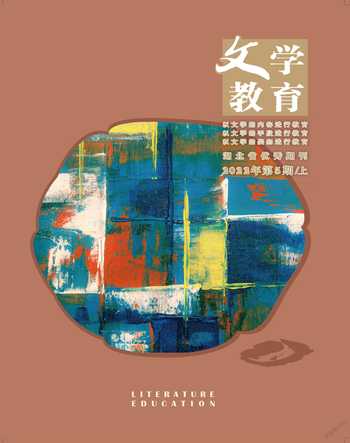叙事学视域下《伊芙琳》的女性意识困境
王天睿 张之俊
内容摘要:《伊芙琳》讲述了主人公伊芙琳为了逃离照料家庭的悲惨命运而选择和男友私奔,中间掺杂诸多纠结矛盾与回忆,临走之时她却突然改变了决定。本文借用叙事学视域下三个叙事学概念:叙述视角、双重认知叙事以及叙事模式,剖析伊芙琳所面临的重重困境。叙事学视域下,《伊芙琳》展现了都柏林社会中以伊芙琳为代表的女性面临的社会桎梏、家庭压迫、婚姻刻板印象束缚以及自我麻木这四重内外困境,突出了都柏林群众精神瘫痪与女性意识薄弱的主题。
关键词:乔伊斯 叙事学视域 《伊芙琳》 女性意识
《都柏林人》是乔伊斯所著的短篇小说集,小说背景为20世纪初期都柏林人中下层民众的生活,乔伊斯旨在揭示都柏林人精神瘫痪这一主题,其中《伊芙琳》是其中描绘女性压抑生活的重要篇目,讲述了作为都柏林男权社会的弱势女性,伊芙琳身受父亲的欺压,承担照料家庭的重责,为了逃避当下生活决定与伴侣弗兰克离开家乡,其中充满了她复杂挣扎的内心活动,临走时她却突然改变主意,呈现呆滞麻木之态,展现了都柏林社会瘫痪麻痹与女性缺乏自主意识之画面。
至今尚无学者从叙事视角、双重认知叙事以及叙事模式这三个叙事学概念对该小说进行具体分析。过往关于《伊芙琳》的研究中,学者主要探究伊芙琳的内心变化与特征。如吴其尧从蝉联法这一修辞学角度,指出“主人公伊芙琳身上的反应迟钝和精神上的麻木不仁”[1]。张丽娜从语言功能中的及物性系统着手分析该作品,指出从主人公的行为、存在和关系过程中足以看出伊芙琳在长期沉重状态下已失去对未来生活的憧憬[2]。段晓英通过比较《伊芙琳》与《比赛之后》得出结论:这两篇小说展现了“围绕成年人对待家庭责任的不同态度,刻画了关于人的心灵瘫痪的两个极端典型”[3]。也有诸多关于伊芙琳内心特性的探讨。如Pirnajmuddin与Teymoortash根据名字分析出伊芙琳身上蕴含的一种无力感[4]。Yang与Sun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分析伊芙琳的自我,本我和超我影响自己身体和精神的运作方式,并指明超我的压制导致自我不能自由满足本我欲望,使其最终成为陷入瘫痪深渊的活死人[5]。还有部分学者探索伊芙琳的悲剧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如Boysen将《伊芙琳》中这种爱情故事与对无情的社会与意识形态制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6]。Scholes运用符号学理论研究伊芙琳处于象征剥夺状态的原因[7]。Ingersoll指出伊芙琳在社会中历经被女性化的过程,揭示其脆弱性[8]。可见学者大多指出了伊芙琳的内心瘫痪与社会环境的压迫,却未运用叙事学视域中的叙述视角、双重認知叙事与叙事模式概念系统分析伊芙琳面临的社会、家庭、婚姻刻板印象以及自我的多重困境及其深陷的层层罗网。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叙事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且发展为研究小说的重要理论之一。申丹与王丽亚指出叙述视角是叙事研究采用的重要工具,多种观察故事的角度有不同功能,并将叙述视角分为四种“内视角”(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与五种“外视角”(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外)[9]。认知叙事学是叙事学与认知科学的交叉学科,意在探讨叙事与人物思维或心理的关系[9]。Alan Palmer提出双重认知叙事是该领域中研究人物思维的一种形式,指人物的思维中存在其他人物思维[10]。思想或话语表现方式是叙事模式的重要方面,也是修辞手段,是作家与作品的文体风格体现,不同的人物话语或思想表现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文体效果[11]。Leech和Short将思想表现分为以下五类:直接思想、间接思想、自由直接思想、自由间接思想以及心理行为引述,并且将言语行为分为以下五类: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以及言语行为的叙述体[12]。本文借用文体学概念对小说中的思想与话语加以解释。
因此,本文将采用叙事学视域下三个叙事学概念:叙述视角、双重认知叙事以及叙事模式,探讨造成伊芙琳女性悲剧的原因,指出社会、家庭、伴侣的多重外在力量与伊芙琳自身的软弱麻木共同导致了她的不幸,亦是都柏林社会女性意识缺乏的原因。
一.叙述视角:叙述者对伊芙琳困境的呈现
申丹与王丽亚指出,叙述视角是指叙述时以什么视角来观察故事,若视角不同则产生的叙事效果也会大相径庭,并在厘清定义的基础上将叙述视角分为四种内视角与五种外视角,内视角指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外视角指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外[9]。叙述者开篇使用全知视角这一外视角。全知的叙述者有权利窥探人物思想,并像上帝一样处于故事世界的上方看到并知道一切[13]。小说开篇,身处故事之外的叙述者对伊芙琳周围环境的变化以及童年记忆进行记录,用“以前”、“后来”、“那时”、“当时”、“现在”等词串连当下对过往的回忆,呈现出全知叙述者对故事来龙去脉、古今变迁了如指掌。叙述者在该段结尾写道“现在她也要走了”[14]。乔伊斯暗指她身处重重困境,引出下文她将离开的种种思量。
此后,叙述者转向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申丹与王丽亚将该内视角定义为叙述者“用故事内人物的感知取代了故事外全知叙述者的感知”[9],使读者通过这一有限视角来感悟故事。在此,乔伊斯通过人物有限视角,鼓励读者透过伊芙琳的视角来步步感知故事的发展。叙述者开始呈现伊芙琳的意识来感知事件,让读者跟着彼时的她衡量离开家乡的原因。首先她考虑离开后会造成的社会舆论,认为人们会说“她是个傻瓜”(34),可见伊芙琳担心外界看法,表明社群舆情会对她的决定有一定限制。从这一叙述角度来观察文本内容,可发现社会桎梏是伊芙琳深陷的第一重困境。随后乔伊斯仍聚焦于伊芙琳的心理活动,逐步描述父亲对伊芙琳的胁制榨取。
甚至现在,虽然她已经年逾十九,有时仍觉得自己还受着父亲暴力的威胁。她知道,正是那种威胁才使她胆战心惊。(35)
该句指明父亲对身处男权社会的她一直管束牵制,并产生悬念,让读者好奇父亲压榨她的原因。由此,读者跟着过去的伊芙琳一步步观察父亲对她造成欺压的多个事件,并时时感到惊诧同情,从叙述者的感知角度,深度体会到伊芙琳的可怜唯诺,以及发现男权压迫是她深陷的第二重困境。感受完父亲的压迫后,读者再次聚焦伊芙琳的内心活动,她开始寄希望于她的男友弗兰克:
她要和他一起乘夜船离开,做他的妻子,和他一起在布依诺斯艾利斯生活,他在那里有个家等着她。(36)
此处读者可充分从伊芙琳的视角中感受到她的真实想法,即她想跟弗兰克私奔并成为她的妻子以此来摆脱当下的苦难,但她却未意识到依附另一个男性来脱离身处已久的男权社会将再次重蹈覆辙,在叙述者透视伊芙琳内心世界的过程中,可发现女性一味想通过婚嫁而谋求幸福的刻板观念是绑缚她的第三重困境。当她下定决心离开这里后,她去了码头,叙述者依然透视伊芙琳的感知来让读者观察事件,此刻她的心理又发生了转变:
她觉得脸色苍白发冷,由于莫名其妙的悲伤,她祈求上帝指点迷津,告诉她该做什么。(38)
叙述者仿佛正在经历此事,而非从事件外部进行简单回顾。乔伊斯仍采用有限视角,与对任何事都非常清楚的全知视角不同,读者只得从伊芙琳有限的视角感受她的心境与事态变化。由于无明确提示,文中“莫名其妙的悲伤”的确切内涵读者无从得知,可见有限视角具有局限性,却增添悬念,吸引读者阅读兴趣并引领读者探究她突然悲伤的原因,以及她最终会不会离开。这呈现了她纠结挣扎的复杂心理,她在选择过安稳不变的生活与追求所谓的幸福之间无数次徘徊,可见软弱犹豫的性格是导致她悲剧的原因之一。小说结尾处,读者再次跟随她的有限视角来探究其心理:
她双眼望着他,没有显示出爱意,也没有显示出惜别之情,仿佛是路人似的。(39)
在临上船之前,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叙述者一直聚焦于伊芙琳的心理活动,而读者也一直跟着伊芙琳体验她身上发生的一切,从而推测出她突然又想起来了母亲的嘱托,以及她身上肩负的重责,她彻底失去了追求自由幸福的意念,呈现出麻木迟钝的状态。
以上分析发现,叙述者主要通过使用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来充分展现伊芙琳的心理活动,展现了她深陷的困境,即社会桎梏、父权压迫、刻板观念这三重外部压力以及她犹豫麻痹的内部矛盾心性,一同构成重重阻力导致了她的不幸结局。
二.双重认知叙事:外在迂腐思维在伊芙琳脑中的嵌套
1.社群思维潜隐:腐朽现实的束缚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天主教会成为英国统治的帮凶,爱尔兰人逐渐变得麻木,呈现扭曲异化以及精神瘫痪的内心世界[15]。伊芙琳多次考虑周围人对于她即将离去的看法与舆论,多次呈现双重认知叙事,展现出压抑的女性思想,即思想受社会文化影响,精神趋于愚笨与麻痹。如:
倘若他们知道她跟一个小伙子跑了,那些人在店里会说她什么呢?也许,说她是个傻瓜;(34)
“那些人”属于显性思想陈述。张之俊与刘世生指出,思想陈述 (thought report)是叙述者对人物思维的展现;显性思想陈述 (overt thought report)是叙述者通过显著性的语言标记表现出社会思维[16]。此处体现了伊芙琳思维中存在社群思维。当她同意出走后,开始反思决定的正确性,考虑到周围熟悉她的人对于她和男人私奔可能会传来风言风语。乔伊斯构建了伊芙琳的双重认知叙事,即猜测他人对她即将所做行为的看法。足以可见大部分爱尔兰人具有狭隘的爱情观,使得追求爱情的女性自由受到束缚,而这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已然内植于心,阻碍女性遵循内心想法并促使其本能生长。
盖文小姐会感到高兴。她总是显摆比她强,尤其是每当有人听着的时候。(34、35)
此時伊芙琳猜测盖文小姐对她即将出走所的反应,此处再次展现双重认知叙事。在当时的爱尔兰社会,女性普遍经济不独立且无社会经验,只得依附男性。而她在店里干活,本是突破男性限制的典型表现,而盖文小姐却对伊芙琳当店员之事表露轻蔑,可见女性也成为束缚女性提高社会地位的阻力。
那时,她就结了婚——她,伊芙琳。那时,人们会尊重她。(35)
“人们”也是显性思想陈述的重要体现,呈现在伊芙琳的双重认知叙事中,即对人们的想法进行推测,认为等自己结婚之后人们可以尊重她。尽管伊芙琳已萌生奔赴自由与追求独立生活的想法,但内心仍旧被残酷现实所绑缚。世俗标准限制女性追求真正的幸福,最终沦为精神瘫痪社会的最大牺牲品。
2.家庭思维潜隐:父权体系的桎梏
20世纪的爱尔兰,父权制居统治地位,女性毫无独立性,展现男尊女卑的等级状况。伊芙琳的脑海中多次出现父亲与母亲的思维,即双重认知叙事。她感受到父亲的压迫以及母亲让她照顾家庭的规劝,可见她早已被社会规则与文化所浸染,深陷其中,难以真正突破家庭对女性的禁锢。
他从未像喜欢哈利和厄尼斯特那样喜欢过她,因为她是个女孩。(35)
当她开始回忆成长期间父亲对她的态度,此处呈现双重认知叙事,她深知父亲因为性别缘由而对自己态度恶劣。该句展现当时爱尔兰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规训,女性在社会大背景下深受男性摆布与桎梏,无法自由生长。关于家庭的思想涌入她的脑海中,使她深感焦虑烦扰,受家庭牵制。
他会想念她的。(37)
她在离开之前的某天回忆过往,推断在她走后父亲会想念她,此处再次呈现双重认知叙事。父亲总是威吓和训斥她,她却认为父亲会想念她,可见伊芙琳已湮没在女性处境悲惨,一味依附男性的现实洪流中,难以挣脱父权制的影响。
她浑身颤抖,仿佛又听见母亲的声音愚顽不停地说着:
“我亲爱的孩子!我亲爱的孩子!”(38)
她开始对自己的决定进行重新审视时,母亲的话笼罩在伊芙琳的脑海中,乔伊斯再次构建伊芙琳的双重认知叙事。她本不想成为像母亲那种辛苦持家、无私忍让、做出无端牺牲的女性,但她的思绪中却掺杂着母亲愚顽的嘱托,此处表明以母亲为代表的女性也成为男权社会牢笼的帮凶,让更多女性无法消解男性中心,反而让她们丧失抗争斗志与觉醒意识。此处也彰显着男权社会的腐朽思想深入她的心中,让她无法挣脱。
3.伴侣思维潜隐:刻板印象的压迫
男友弗兰克的思维多次出现在伊芙琳脑海中,表明伊芙琳在推测弗兰克所想,暗指她内心仍无法摆脱男性而追求独立生活,反而依赖其他男性逃离当下社会,说明她早已被迫卷入男权压迫的世俗罗网,难以摆脱。
弗兰克会拥抱她,把她抱在怀里。他会救她的。(38)
她在思索中渐渐发现社会与家庭拖拽着她,将她拉进男性统治的沟堑,她想逃离这个只得压抑自己,自我牺牲的环境,她考虑弗兰克的想法,觉得他会带她逃离这个荒谬麻木的地方,此处再次呈现双重认知叙事。此处表明之前伊芙琳悄然觉醒的女性意识突然湮灭,她想依附于弗兰克,让他成为帮自己摆脱悲惨境遇的救主,她已掉进男性主宰的深沟,尚无自我独立的想法,仍依附于男性,可见男权社会已经牢牢把女性禁锢在自己的世界里。
全世界的海洋在她的心中翻腾激荡。他把她拖进了汪洋之中;他会把她淹死的。(38)
她在码头临走之际,象征自由的汹涌海洋在她心中不断泛起波浪,她仿佛看到了自己紊乱陌生的新生活,她考虑到他依然是主导者,无法满足她内心追求真正自由的渴求。她猜想他只会将她拖进一个依附于他的困顿的生存状态。此处再次展现双重认知叙事,表明伊芙琳自我顿悟,发现自己已深陷男权社会的泥沼中,无法逃离这令人窒息的陈旧规训,可见外在的压迫使她的悲剧成为必然。
三.叙事模式:伊芙琳自身的犹豫麻木
1.间接式思想呈现:伊芙琳的僵化沉闷
叙事者使用间接与自由间接这两种间接式思想,呈现出伊芙琳的思想僵化与性格犹疑。利奇(Leech)和肖特(Short)对其定义为:在间接思想这种形式中,叙述者会用自己的话来表达受述者思想,由引述句与被引述句构成[12]。叙述者用该形式转述伊芙琳的思想:
她曾许诺一定要尽力维持这个家。(37)
伊芙琳的思想出现在叙述层,实现了人物思想的叙述化。因为此处并非为直接形式,思想受到叙述者部分控制,使得叙述者介入角色与读者之间,该句出现在她的回忆里,她由于夷犹混乱的心境导致难以直接表达具体在想什么,只得由叙述者来处理她的思想,可见伊芙琳思绪纷飞,甚为纠结,正在思虑她对母亲的承诺,推测出她没有私奔的决绝果敢,而是处在瞻前顾后、彷徨无措的心理状态。相较于直接思想,自由间接思想时态后移,且第一人称向第三人称转换,而且没有引出思想的主句,疑问形式与问号[12]。该形式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叙述者与人物声音的重叠,并能听到叙述者对于人物的同情或者讽刺。
叙述者在这篇小说中多次使用自由间接思想来展现伊芙琳夷犹摇摆的心境,以此揭露伊芙琳悲剧的根本原因。如:
家!她环顾房间的四周,再看看房间里所有熟悉的物品;多年以来,她每周都把这些东西擦拭一次,不知道灰尘究竟是从哪儿来的。也许她再也看不见那些熟悉的物品了,她做梦也没想到会离开它们。(34)
在她已经决定要走之后,她立马提到“家!”这一感叹句体现了伊芙琳对家庭的依恋与不舍,预示后文她会多次产生决定私奔的犹疑矛盾心理。而灰尘象征着人心蒙上了无尽的灰尘,伊芙琳深受社会道德的精神桎梏[17]。叙述者暗指她已深陷精神瘫痪的泥沼,处于麻木迟钝、缺乏独立意识的状态。自由间接思想使用第三人称与过去时使得读者与人物的话语之间产生距离,无法直接代入,使读者客观分析角色心理。读者从“她做梦也没想到会离开它们”发现,她以前困于家庭生活,缺乏对自身境遇的思考,极易在做决定时产生进退維谷的心理困境,这亦是导致角色悲剧的内部原因。
她已经同意出走了,离开她的家。那样做明智吗?她尽力从每个方面权衡这个问题。(34)
此处呈现自由间接思想,表明她在做出决定后仍然怀疑自己的判断,体现了她持有举棋不定、优柔寡断的心理。尽管她此前对自己的生活非常不满,希望改善生活,但从她的潜意识里,读者可以窥探出她觉得自己的选择是与社会以及家庭要求相悖的。她不敢积极主动地做谋求改变的行动发出者[18]。即使她此前认识到自己的生活存在问题,已经做出想改变当下生活的决定,但由于禁锢社会民众的道德瘫痪长期困扰,促使她无尽地思考决定的正确性,只得进行自我内心对话,可见她当断不断、迟疑不决的思想限制她寻求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只会无休止地思考沉吟。通过自由间接思想,叙述者常常与人物声音融合起来。而在这句疑问句中,叙述者隐匿在人物言语后面与读者对话,引发读者加入伊芙琳的思考,深入感受伊芙琳的纠结心绪。
逃!她必须逃走!弗兰克会救她。他会给她新的生活,也许还会给她爱情。而她需要生活。为什么她不应该幸福?她有权利获得幸福。(38)
叙述者于此处运用自由间接思想,在伊芙琳仿佛听见母亲劝她留下来照料家人的话语时,她即刻转变想法。叙述者对人物声音进行部分加工,使得读者从前两句感叹句中极易推测出伊芙琳想要逃离当下压抑生活的决绝态度,最后两句话也体现了她想追求幸福生活的毅然坚定。叙述者对角色言语有一定控制,使其叙述的权威性误导读者,即让读者相信她决意重塑自我,跟随弗兰克离开家乡并奔向自由生活。但小说呈现的结果不同:伊芙琳最终没有选择和弗兰克一起走,使得读者读到最后会感觉小说具有讽刺意味,讥讽爱尔兰社会的精神瘫痪泯灭民众独立意识,并对像伊芙琳这样深处压抑社会环境的人表达同情。此处“而”一字表示转折,前文所提的“新的生活”、“爱情”与她想要的“生活”并不矛盾,故“而”字前省略了脑海中与她产生矛盾的辩论方的话语[19]。此处是叙述者故意为之,句子间的逻辑矛盾突显伊芙琳的冲突内心,揭示她的犹疑不定是造成她深陷悲剧的深层原因。
在他为她做了这一切之后,她还能后退么?(38)
此处再次呈现伊芙琳的自由间接思想,叙述者保持了角色的原有思想,可以窥视伊芙琳的内心:在她回忆时发现经常压迫她的父亲以及照顾兄弟的重责等诸多因素都使她的生活长期陷入不良境地后,她已然做出了要离开的决定,但当她到达码头之后,她再次陷入迷茫,开始考虑弗兰克的因素,此处再次展现她的复杂挣扎的痛苦内心。
正是自由间接思想的运用使读者可以与伊芙琳的文字保持距离,从理性角度做出判断,而叙述者干预的痕迹也频频出现在该形式中,让读者体会到乔伊斯对爱尔兰精神瘫痪的讽刺以及对伊芙琳的同情。
2.直接式引语对比:伊芙琳的被动软弱
乔伊斯采用自由直接引语与直接引语这两种直接式引语呈现弗兰克以及伊芙琳双亲的话语,以突出他们直截了当与振振有词的表达方式,而伊芙琳全篇无引语呈现,只有间接式思想用以表达自身心绪,二者对比下可见伊芙琳的怯懦麻痹。
叙述者使用自由直接引语引述弗兰克的话语。相较于同时拥有引号与引导句的直接引语,该形式在其基础上去除原有的一个或两个特征,使得角色直接与读者对话,因为此时叙述者不再是中间人[12]。
她用双手紧紧地抓住了铁栏。
“来呀!”
“来呀!”这句话是由弗兰克所言,由于缺乏引导句,此句为自由直接引语。这种形式因为摆脱引号与引导句,使其更加“自由”[9]。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叙述者的控制,可以直接从弗兰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弗兰克因为看出来了伊芙琳的徘徊踟蹰,用直接的方式来催她,而无引号与引导句使得句子长度变短,加快叙事速度,表明当时情况非常仓促。此处可以清晰窥视人物的真实想法:弗兰克想让伊芙琳赶紧跟他走的着急心理,且反衬出伊芙琳的猶疑动摇。
此外,叙述者多次使用直接引语如实地呈现伊芙琳双亲以及弗兰克的话语。叙述者报道某人的言辞时,他会逐字引用受述者所用的字词[12]。
“我知道这些当水手的小子们,”他说。(37)
叙述者一五一十地对父亲的话语进行记录,从此处看,父亲讲话方式直接,径直指出弗兰克的身份,表明父亲对他不屑轻蔑的态度,并禁止伊芙琳与其继续往来的想法。叙述者用该形式完全保留了父亲的个人语言特征,这源于男权社会赋予了统治阶级话语权,使其自身展现居高临下的姿态。而上文分析所呈现的内容表明,伊芙琳大多使用自由间接思想,因为她只在心里思索,而未曾向父亲直言,这是一种较为谦卑的间接形式,乔伊斯想用此方式对比突出她怯懦踌躇的心理,影射她最终会放弃与情人离开家乡。
而母亲的话语同样也由直接引语来呈现(关于该话语分析,请参见前面双重认知叙事部分)。叙述者用直接引语的形式呈现母亲的话语,且含有两个感叹号,蕴含了母亲关于家庭问题的态度,即女子应以操劳家庭为重。
伊芙琳双亲的直接引语彰显了理直气壮的态度,在伊芙琳周围形成一种压抑气氛,使得伊芙琳尽管与其意见相悖也不敢言,只得将诸多顾虑藏于心中,而乔伊斯选择由自由间接思想来暗含主体意识,整体呈现出一个意存观望、犹豫迟疑的人物形象。
在小说最后,叙述者写道:
不!不!不!这不可能。她双手疯狂地抓着铁栏。在汪洋之中,她发出一阵痛苦的叫喊。
“伊芙琳!爱薇!”
他冲出栅栏,喊叫她跟上。(39)
此处伊芙琳的言语是由自由间接思想呈现,而弗兰克的话由直接引语呈现。自由间接思想由于采用过去时态与第三人称使得读者处于一种间接的位置,并从中客观揣度伊芙琳所说的话。叙述者用了三个“不”而且加上用于加重语气的感叹号,表示她不想离开这里的强烈想法。在前文关于双重认知叙事的分析中,本文指出:伊芙琳在最后认识到了自己已经深处男权社会的漩涡里无法自拔,所以刚萌芽的女性意识被自己掐灭,只得选择继续留在这里。而即使她已经做出了决定,但叙述者仍在此处使用自由间接思想,而非言语,意在突显她自身性格的不果决,故难以向他人直说自身打算。而读者可以直观弗兰克的言语,因为男性的卓越地位,使得他可以采用直接引语的形式对伊芙琳直爽地表达自身想法,亦或许他惊于伊芙琳心意的突然转变,故在此处呈现直接引语。叙述者于此处突出直接引语的声音效果,即直接引语具有音响效果,小说家常用直接式与间接式的对比来呈现对话中的“明暗度”[9]。弗兰克的一句话单独占一个段落的篇幅,且采用直接引语,于伊芙琳与读者而言都具有引人注目的响亮效果。即便如此,伊芙琳还是无所作为,无助相望。这种呈现方式之间的对比,足以衬托出伊芙琳心中的想法较为黯然,整个人物呈现一种麻木呆滞且精神瘫痪的状态,揭示了其悲剧的内在原因。
李维屏在评价《伊芙琳》时说道:“她既没有胆量逃离‘可爱、肮脏的都柏林’,也没有勇气选择新的生活道路。[20]”正是伊芙琳自身长期浸染在爱尔兰这一道德瘫痪的社会,使她丧失逃离困顿生活的勇气,最终造成内外束缚式的悲剧。本文运用叙述视角、双重认知叙事以及叙事模式三个叙事学概念构成的叙事学视域分析《伊芙琳》,呈现其绑缚以伊芙琳为代表的女性的四重困境:呆滞麻痹的爱尔兰社会、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思想、迂腐陈旧的刻板印象以及踌躇怯懦的自身性格,有效展示了都柏林群众精神瘫痪中女性意识薄弱的画面。
参考文献
[1]吴其尧.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都柏林人》中语言的反复现象浅析[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6(04):53-58.
[2]张丽娜.从及物性分析浅谈《伊芙琳》的精神“瘫痪”主题——评《都柏林人》[J].领导科学,2020(17):129.
[3]段晓英.平凡的都市生活 深刻的精神剖析——浅谈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02):127-129.
[4]Pirnajmuddin,H.&Teymoortash,S.S.On James Joyce’s EVELINE[J].The Explicator,2012(1):36-38.
[5]Yang Xinwei&Sun Yu.Analysis of Emotional Paralysis in Dubliners in terms of Personality Structur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s,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2017,3(4): 213-
218.
[6]Boysen,B.The Necropolis of Love:James Joyce's Dubliners[J].Neohelicon,2008,35(1): 157-169.
[7]Scholes,R.Semiotic Approaches to a Fictional Text: Joyce’s "Eveline"[J].James Joyce Quarterly,1978 (1/2):65-80.
[8]Ingersoll,G,E.The Stigma of Femininity in James Joyce’s "Eveline" and "The Boarding House"[J].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1993,30(4):501-510.
[9]申丹,王麗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8,95,96,147,158,222.
[10]Palmer,A.Social Minds in the Novel[M].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12.
[11]王林.思想或话语表现方式变更对原作风格的扭曲[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1):110-116+160.
[12]Leech,G.&Short,M.Style in Fiction: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Prose[M].London: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7:255,258,260,271.
[13]Fludernik,M.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ology[M].London:Routledge,2009:92.
[14]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M].王逢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34.下文对该作品的引用只标注页码.
[15]吴庆军.城市书写视野下的乔伊斯小说解读[J].广西社会科学,2013(01):126-129.
[16]张之俊,刘世生.群体精神瘫痪:叙述声音中的都柏林人群体思维[J].外语研究,2021,38(03):101-105+111.
[17]吴素梅.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语言重塑——女性主义文体学视野下的《伊芙琳》[J].外国语文,2018,34(04):23-29.
[18]刘娟.道德与情感的交融——从语料库文体学视角探讨伊芙琳的精神逃亡[J].外国语文,2013,29(04):48-52.
[19]胡秋冉.乔伊斯《伊芙琳》中的叙事空白新解[J].外国文学研究,2019,41(04):64-74.
[20]李维屏.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98.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叙事学视域下二十世纪英语小说中女性主义特征研究:以英国、美国、爱尔兰三部作品为例”(项目序号:A353)。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张之俊为本文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