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的诗性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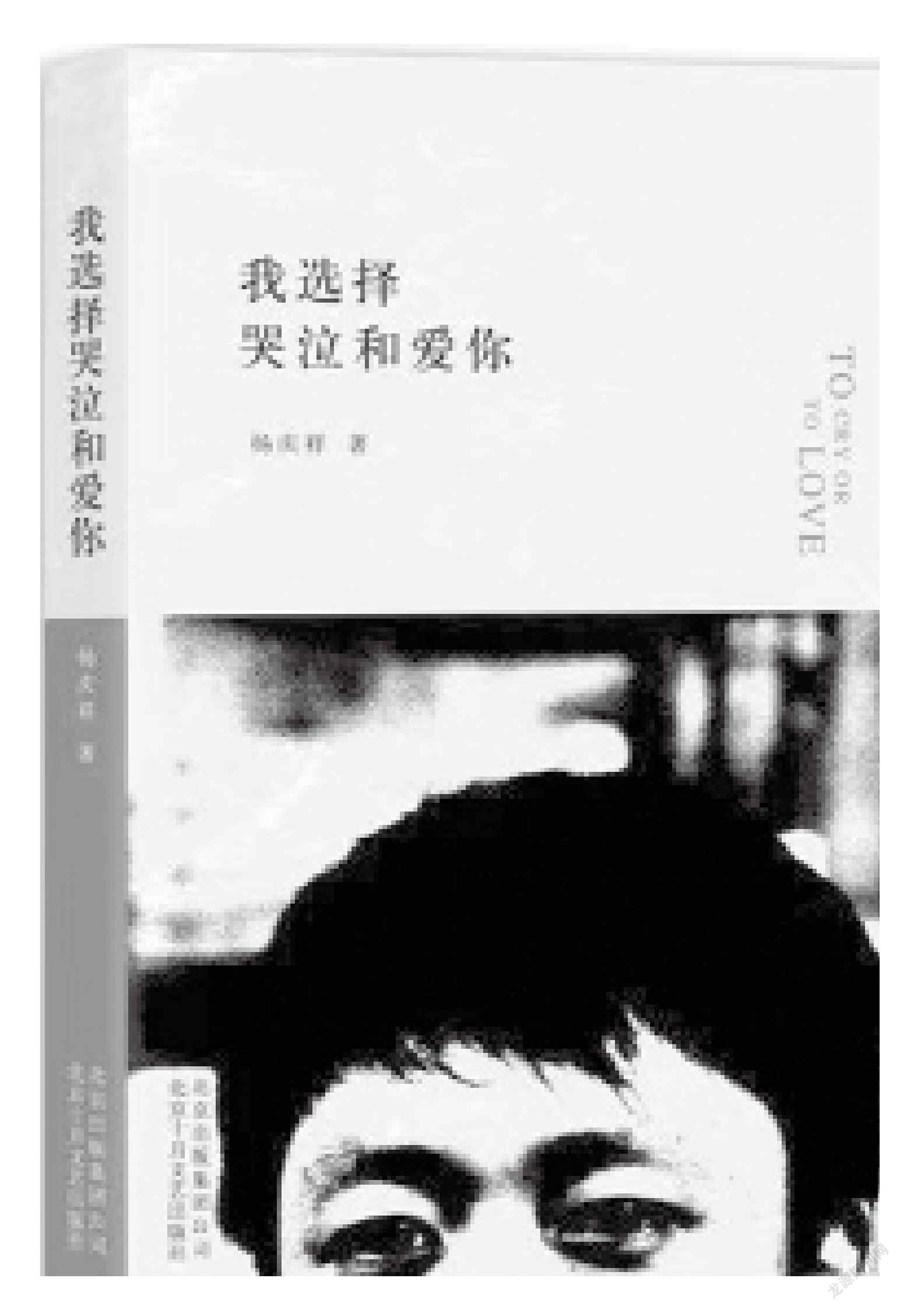
1
读完杨庆祥最新的诗集《世界等于零》,轻轻地放在案上。封面上的那两行诗句:“我来过又走了/世界等于零”,还紧紧地盯着我,凝视着我。我也死死地盯着它,凝视着这本诗集的封面。封面上,那片淡蓝得有些发绿的天空中,与一朵大白云所对峙的右上方,大大的,黄色的,竖排的,五个紧紧连挨的字,“世界等于零”。我知道,这是这本诗集的名字。但是,我总是在怀疑,犹疑不定,后来质疑,世界能等于零吗?
好多了不起的人,包括那些智者、高僧和大德者,都喜欢告诉世人说,要学会清零,要一切从零开始,抱着虚无、空静的心灵去读书念经,去阅世阅人,去面对世界、面对生活与现实。这可能吗?我来过了,我见过的一切,我读过的一切,能清零吗?我觉得是很难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除非我的精神生命或者物质生命结束或新开始一次,“我来过又走了/世界等于零”。
这样看来,“世界等于零”,可能是一句箴言,也可能是一句召唤,还可能是一句描述。
但是,我觉得,“世界等于零”,首先是一种描述。真如杨庆祥所说:“零不是无,零是无限的可能,在某一个看似‘无的地方滋生出无穷尽的可能,这个可能里包括自我、世界、色相和观念。”由此,进一步他又谈到了文学和诗歌,说:“我个人的看法,文学和诗歌,是在原始巫术仪式丧失后,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零。或者说,当‘零被具体化为一个阿拉伯数字序号,而丧失了其哲学内涵后,‘零的重新仪式化被落实到了诗歌里面。所有的诗歌写作都可以说是‘从零到零。从零起始,意思是指诗歌的起源不可确定,到零结束,意思是指诗歌的意义永远无法穷尽。真正的诗歌就在这两个零之间划出一道无法测量的曲线,这个曲线的长度与诗歌的生命力成正比。” (《从零到零的诗歌曲线》,《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版,第170页)由此可见,这可能就是我们去阅读和理解杨庆祥诗歌的一把独特而“私人化”的钥匙。
这样看来,“世界等于零”,仿佛就是一句箴言了,是否在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诗歌写作的“秘要”:“道是什么?道就是零。”“零是一个更重要的概念,零既是开始,又是倍加,又是无限地大——乃至于无穷。”(同上)
2
但是,我读完这本诗集后,还是觉得,《世界等于零》,首先是一种描述,是对现在世界生活的一种个人化的描述,是一种极端“私人化”的描述,是对“包括自我、世界、色相和观念”的描述。和他的上一本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一样,都是对他的现存现实生活的一种主观化下的客观描述。从这116首诗中,或者说从这116块时光碎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大学青年教授、青年评论家的另一副面孔:感性、敏感、细腻,或者说,多情、感伤、颓废、多愁善感、郁郁寡欢。这可能就是他作为当代青年诗人的一种面孔。我喜欢他这种诗人的面孔。他不像那些更多的当代诗人,总是在仰起面孔,叙述着那些遥远的历史、民族与古老的不生动的故事,抒发着关于世界、宇宙与国家的那些大而无当的情怀。从他们的这些虚无缥缈的诗意中,读不到当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的人间烟火的具体生活,感觉不到当下人们世俗生活中具体的喜怒哀乐。正如杨庆祥以耳语的私密形式,偷偷告诉我们的真话:“我珍爱三种人:/吻我的,陪我哭的,给我买马卡龙的//我厌弃三种人:/撒谎且不脸红的,假笑的,和所有人打成一片的”(《我珍爱三种人》,同上,第009页)。是的,我们不喜欢那些“撒谎且不脸红,假笑的,和所有人打成一片的”人,我们也不喜欢那些“撒谎且不脸红,假笑的,和所有人打成一片的”诗歌。
我喜欢杨庆祥的诗歌,他总是平视着我们,以自己的心触摸着人心。他“一边以诗歌为利刃”,刺破自己坚硬的生活表层,刺破自己善良但却冷漠的内在心理,剖出自己的赤子之心,“黑暗选择遮蔽一切/黑暗己经遮蔽了一切啊/我正在黑暗之心/亲爱的,我选择哭泣和爱你”(《我选择哭泣和爱你》)。“如果命运禁止我们去爱/我们还活着是为了什么”(《四月,早安》)。“我发现我永远都离不开一些东西/旧情/故人/和伤心”(《截句三十五首》),尽管“伤城伤心”,但是,他又“一边捡拾人间碎片”,并且“穿越时代的残骸与碎片,拥抱完整”,“以被不断剥离的人类只有借助不同的方式”,以爱情的方式,以诗歌的方式,来“一次次重返那种‘完整”。杨庆祥的诗歌,总是通过自己实实在在的涉世经历、身体经验、自我抒情、精神漫游、智性深度,来书写这个世界,来记录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感觉与感悟,告诉我们,“不浪费生命/不试验人性/爱自己/也爱自己”(《截句三十五首》)。我喜欢这种用自己的赤子之心去“吻你的”,让人能有一种被“陪你哭的”感觉的诗歌。它真切感人,暧昧朦胧,热烈伤心,汁液饱满,细节丰富,生机葳蕤,充满不确定性,不可定义,“它逃避一切的阐释,因此也拥有无穷的阐释”(《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版,第172页)。
杨庆祥在《思无邪》中写道:“很多人饱/我用饿爱你//很多人瘦/我用胖爱你//很多人沉睡/我用失眠爱你//很多人笑/我用忧愁爱你//你有一张多么好看的脸/我用一张不好看的脸爱你//很多人成功了/我用失败爱你//夜晚的榴莲清晨的芒果耳旁的清风/枝头的春花秋月碎碎念念//我因为爱你而太过失败我用所有事物的反面求证/我爱的深寒孤绝亲爱的晚上一起吃点好吃的吧”(同上,第009页)。这是当代青年的爱情之一种。一种认真的爱情,一种刻骨的爱情,一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爱情,当然,也是一种再日常不过的爱情,“晚上一起吃点好吃的吧”。他在《夏天来了,你要抱一抱我》中寫道:“夏天来了,你要抱一抱我/我兜里的硬币,正好够买一大杯啤酒/我们可以一起喝酒,醉了就躺在地上//有很多东西可以享受/天空,虽然没有星星/天桥,虽然贴满了小广告/很久以前这里有一个小提琴手/面带菜色神情落寞/他在夜晚反复拉一首梁祝//如今我人到中年,坐在地上喝酒/用艾草洗头发,唱歌,抱一抱/所有不要钱的东西/抱一抱夏天,空气,水中的鱼/天上的鸟,消失的小提琴手/如果还有多余的硬币,就去买一盒避孕套/放在包里,虽然永远都用不着”(同上,第056,057页)。这是当代中年人的爱情之两种。一种是“抱一抱/所有不要钱的东西”;一种是“面带菜色神情落寞/他在夜晚反复拉一首梁祝”。这可能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常见的一种爱情。爱得如此执著如此深入,但爱的却是无物之阵,或者飘渺的过往,都是那么遥远而不可及。尽管如此,这种爱情却是如此的日常而痴迷,祖国的大地上,无论在何处,都可以偶遇到这种令人忧郁的场景。面对这样的城市景观,你忍心说“世界等于零”吗?这不正是世界表象之一种吗?或者说世界的形象呈现之一种,还可以说是世界之反映与作用之一种。杨庆祥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不仅是敏感的、深情的、细致的,而且也是冷峻的、客观的、真实的。他不仅热眼观人,多愁善感,而且更是冷眼旁观,洞若观火。他在那首《假装有很多人在想念你》中写道:“假装有很多人在想念你/假装有很多人不睡/等雪花,把冰之心带给你/还有一副枫叶的手套//假装那是晚上,夜话围炉/森林温柔地呢喃/有很多人假装迷路/为了找到你//假装很多人相遇相爱/很多人找到很多个你/假装他们都哭了/他们许诺不会离开你”(同上,第033页)。你会相信吗?你肯定不会相信的。因为这是现代社会无处不在、无时没有的“假装爱情”。“雪花”是有,但是哪里有“冰之心”?“枫叶”是有,但是哪里有“枫叶的手套”?“一片冰心在玉壶”,玉壶,有钱人的贵族家庭里是有,但是,真的没有“一片冰心”。过去,倒是有过一个笔名叫“冰心”的女作家,可惜已经不在人世间了。纯真的,纯情的,纯结的,以及神圣的、圣洁的,或许都可能是空洞无物,化名虚物。正如“很多人不睡”,不可能都在“想念你”。是“有很多人假装迷路”,但不都是“为了找到你”。你要是如此理解这个世界和“认识你自己”,那你就是自作多情,假装“万人迷”。其实,“万人迷”,也是“迷倒一个人”,不可能有“很多人在想念你”,尽管他们看见你在舞台中央的表演,呼嘘嚎叫吹口哨了,手舞足蹈摇打塑料拍拍了,但是“他们许诺不会离开你”肯定是假的,肯定是一时一霎的。因为你知道,你在台上的这一切都是“表演”的,自然,“他们都哭了”,也百分之八九十是在“假装”。
3
我总觉得,杨庆祥的诗歌有一种强烈的“同时代性”。也就是他和金理等青年文学评论家一直在强调的,要去写同时代的人,要去写与时代同步的文学。阿甘本说:“真正同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杨庆祥正是这种极具“同时代性”的诗人。他身处这个时代之中,他深知这个“世界”不会“等于零”,所以,他才清醒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凝视着世界的表象,却郑重地对此做出批判的审视。他既没有为了所谓的永恒性,而脱离了时代与当下,也没有为了追求“同时代性”,而被世界表象所淹没与裹挟。在他的诗歌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一直在认真而郑重地处理着诗歌的所指与能指、意义与诗性之间的平衡。他知道,无论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的景象有多么壮观,但是,作家和诗人绝不应该在拥有全景视角的大海景房里写作,而应该是在自己的陋室中独立写作。他应该转过身背对着这个世界,从而就当作这个“世界等于零”,然后进行自己批判式审视的写作。因为写作是对精神的观照,“世界是我的表象”。因为最高级最好的文学,都存在于它的虚构之中。虚构之美,才是文学的最高境界。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大作家和大诗人都想把世界的表象转变为他自已作品中的形象的原因。
但是,杨庆祥用自己的诗告诉我们,唯一不能说谎的工作就是诗歌。你不能在诗歌中撒谎。如果你是一个文学上的骗子,诗歌中的谎言者,你终究会被揭穿。或许明天,或许十年二十年,或许在你离开这个世界后,世界也不会等于零,但如果你说谎,你终究会被揭穿。诗歌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因此,你必须写出这个时代和世界表象之后最真实的精神面貌和心灵画像。只有这样的诗,才能与成千上万的读者的心灵发生关系。正如他所说:“真正的优秀艺术品,包括诗歌在内,作品本身之中应该存在一个空间一个层次感,这个空间或者这个层次感里面,应该有一种召唤的结构,召唤的结构会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向他发出一种信息,接受这个信息以后,这个他者就能够进入到这个空间里,并与创作者完成一次心灵的对话。”其实,他所说的“一种信息”,就是世界上最恒久、最感动人的东西,即真实性和诚实感。他还说:“这个空间,包括但不仅指作品的共情力,但要更高级一点,因为共情可能只是一种情感的煽动,但这个是心灵的对话。”(名家专访丨杨庆祥:诗歌的另一个变量是它所具有的人间情怀,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微信公众号2021年10月28日)
诗歌应该去温暖人。诗歌作品应该具有这样的一个“人间情怀”,一个这样的“空间”,一个这样的“层次感”。因为一首优秀的诗歌,一部伟大的经典作品,最终流传给世界的绝对不等于零,而是杨庆祥所理解的那个“零”的真正的意义,即“两个零之间划出的一道无法测量的曲线”。而就是这道无法测量的曲线,会慢慢变成“一种心灵上的对话”。而这种对话,既是对人的精神结构的提高,也是对人心最有效的安慰。
正因为这样,很多读者把他的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世界等于零》中的很多诗,当作是“爱情诗”来读。杨庆祥却说:他想“通过一种极端的个人化表达出极开阔的历史感”,“我其实是想用一种醉生梦死的爱情,来表达虚无绝望的‘政治抑郁症。”(“80”后作家对话录丨杨庆祥:叩击无物之阵,中国作家网微信公众号2020年10月15日)
4
在诗集《世界等于零》的好多诗歌中,我们能够读到好多的“你”。杨庆祥在《我们各有所属》中写道:“你和那么多的人喝酒。我在路上。/你和那么多的人喝酒、吃烧烤、说好玩的笑话。/我还在路上。//那么多的人越来越多。星辰稀少了。/我在路上和野花说说话。//所以归根结底,我看不到你醉酒的欢颜。/你也不知道那些长路多么喜欢我。//所以我们只能各有所需。”(《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版,第118页)他在《我在我们的血里》写道:“今夜,我穿过春风去领一枚勋章/橘色的灯光长出一层细绒毛/你在窗户伺弄盛世花//你的手划过一道弧形如闪电,仅仅是/一瞬间的觉醒/然后是黑暗猛吻你的唇直至春天的雌兽/将你整个香躯吞噬//这一刻我们必须重逢。亲爱的,/头盖骨伴着青瓷呜咽冲锋,/‘我在我们的血里纯净如处子/——班玛斯德”(同上,第128页)。在他的“饮冰”系列中,更能看到好多的“你”:“你有你的软玉小耳/我有我的含金媚眼”(《饮冰第一》,同上,第137页)“所以/左边是风,右边是长髦发/中间种着一颗乳牙//……/你呀你呀,一枚小小的洁白乳牙”(《饮冰第二》,同上,第138页)还有好多好多的“你”,不再举例了。这么多的“你”,可能是爱人,或者情人,或者朋友,或者是自我,那个内在的我。总之,是和诗人亲密对话的那个对方。对了,就是对话。其实,在这本诗集中的好多诗,尽管没有“你”,但是,都是写与人的对话,“当我不能爱/我就坐在菩萨的法眼里/我问自己//是不妩媚了吗?/还是风尘磨损了深情?”(同上,第019页)“妈妈,为什么人的脸如此愁苦?”“妈妈,为什么人的脸哭泣悲恸?”“妈妈,多少真理啊!多少张脸!”(同上,第104页)
诗中出现的人称代词“我”和“你”,这种杂糅交混,自然形成对峙或对话,被吸纳在作品的空间之内,在语词的意义世界里,或有具体的所指,或是不确定的能指,自然,会让读者的内心里产生无尽的遨游。“我”,是诗中的一个持有主体视角,一个发起叙述并参与对话的线索人物。而那个“你”呢?可能是具体的故事情境中的那个和自己十分亲密的人,也可能是一种“内我”的另一种称呼,那是为“内我”设置的对话者,或者说是“内我”的隐形叙述和声音。这些都构成了多重自我之间在诗性空间里的对话和声音的重叠。诗人运用这样的方法,不仅仅是为了诗歌内在張力与结构的亲密,更多的是用对话进行貌似亲密的质疑、质问,或者是对自我的逼问、拷问。诗人觉得,一首诗就应该像一把斧子,劈开我们那善良却冷漠、沉静却坚硬的心灵,逼问出所写故事的真相与人性的真实。就像卡夫卡所说,“一本书应该像一把斧子,劈开人们心中冰封的大海。”当然,他说的是小说。
这可能就是杨庆祥一直在强调的“对话式诗学”。他说:“我所有的诗歌都在维系一种最虚无的个人性和最暴力的总体性之间的一种对峙和对话,这让我的诗歌在美学上呈现为一种暧昧、反讽和哀告。我用这种方式挑战我们这个时代的‘假大空以及一切精神奴役。在通往真理和自由的道路上,诗歌是我的利刃,伤心伤城,伤人伤己。”(同上,第176页)
5
的确,《世界等于零》中的诗歌,大多数是“伤心伤城,伤人伤心”的。“每一句话说出你,舌头卷起告别的秘密”,都是当代人的灵魂在尘埃微微颤抖之后的秘密,是这些尘埃上颤抖的细微光影变化的记录,是这些光影里那些稀薄的看不见的气息里发出的呻呤与叹息。诗人无论是在倾诉心怀,还是叙写情事,都是想尽最大可能地捕捉当代人灵魂的微小颤动,追寻世界正大的人间情怀。诗人以自己敏锐而不屈的个人心性,将自已的生命经验不时地化为极具个人私密化的“伤城伤心”的诗句,把关切民生之多艰的现实书写,不时地化为贴己的日常生活的极端真实,以及内心的痛苦与挣扎,还有反思的智性深度,让读这些诗的人,也感到“伤人伤己”。
杨庆祥是“80”后的诗人,自然,诗中写的也是当下青年一代的复杂爱情、复杂情事和复杂情感。我在读完这本《世界等于零》后,心中涌起的感觉,仿佛叶芝在他的诗歌中所写的情感:“多少人爱你愉悦丰采的时光,爱你的美,以或真或假之情。只有一个人爱着你朝圣者的心灵。爱你变化的容颜里所蕴藏的忧伤。”
这本诗集中的每一首诗,不可能都好,都优秀,但是,他这种非常强调个人,强调个体独特的审美和对世界的独特经验的“秘密花园式”的创造性行为,这种将诗情、诗境、诗思三者完美给合的“当下经验与情感”书写的尽心努力,的确是很令人敬佩和仰慕的。
2021年11月21日写于山西省孝义市
【作者简介】马明高,山西省孝义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在文学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文学评论等七百万字,编创的五部电视剧在央视和各省卫视播放,出版著作二十多部,获央视全国优秀电视剧奖、中国文联全国优秀评论文章,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文艺评论奖、人民文学观音山杯游记散文奖、中华读书报散文奖和浙江作协非虚构散文奖等十余项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