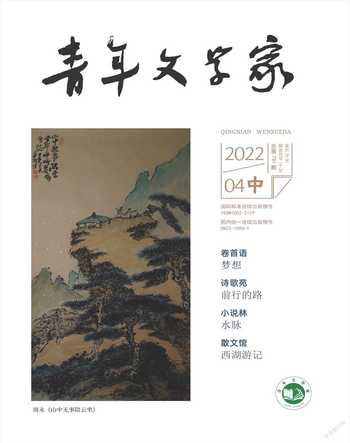论曾巩女性墓志铭中的妻子形象
杨纯

曾巩的作品集中一共收录了六十余篇墓志铭,其中关于女性的墓志铭共有二十五篇。墓志铭是一种具有特定的模式以及内容的应用型文章,但曾巩的墓志铭中除了撰写人物的一生事迹,还融入了自己的思想观念。通过阅读曾巩所撰写的墓志铭,我们不难了解曾巩对古代女性的观点,以及他所认为的理想妻子形象。从曾巩的视角来看,他认为一个符合他思想的妻子应该具有孝顺、仁爱、有礼以及顺从等各种妇道品格,同时还应该兼具一定的学识才华,能很好地完成相夫教子的工作。但是,对于女性形象的确定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且单一的问题,这与当时社会的道德伦理、主流思想、政治因素都密切相关,曾巩对女性墓志铭的撰写自然也受到其影响。本文将从为妇之道、相夫教子、富有才华三个方面来论述曾巩女性墓志铭中的妻子形象。
一、为妇之道
曾巩受到治学思路和家族世儒的影响,所以他是一名纯正的儒家学者。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他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与此同时,曾巩的作品充斥着“文以载道”的优良传统,较为显著的特点是遵守并且发扬儒家的思想和观点。因此,在他的墓志铭中,自然有着同样的思想,那就是宣扬传统的儒家观点,称赞其中女性的为妇之道。妇道指的是当时妇女一定要遵循的礼仪规矩,《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以顺为本者,妾妇之道也。”妻子对丈夫和公公婆婆是必须绝对顺从的。曾巩在《夫人周氏墓志铭》中写到一位叫琬的夫人,字东玉,在出嫁之后,没有公婆,顺从丈夫,疼爱儿子,严格遵循祭祀礼仪,她平时的学习行为,都应礼仪规矩。此外,《永安县君李氏墓志铭》一文是由曾巩为其姑岳母所作,在文中曾巩这样介绍她:夫人姓李,本来是燕人,后来夫人嫁给了骆氏,骆家也是家许州的长葛。她的丈夫名叫与京,夫人仁孝慈恕,一言一行一定要遵从义理。侍奉父母不违背他们的教诲,侍奉公婆不违背他们的意愿,侍奉丈夫顺从而能认识到丈夫的优点,做到内外兼备,不违背礼节。
曾巩对女性的表彰在每一篇墓志铭中都透露着对“礼”的强调,如果女性能够做到“治家以礼”,那么曾巩会对其尤为赞颂,这体现的是曾巩在行文中对家庭伦常秩序的重视。从儒家的观点来看,礼不仅是当时人们行为举止的外在规范,还是社会秩序得以整饬的保证。曾巩在《礼阁新仪目录序》中说:“夫礼者,其本在于养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动视听之间。使人之言动视听一于礼,则安有放其邪心而穷于外物哉?”所以曾巩认为礼对整个家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女性如果要得到赞扬,那么做到“言动有礼”和“治家以礼”是不可或缺的。曾巩在《夫人周氏墓志铭》中说:“昔先王之教,非独行于士大夫也盖亦有妇教焉。故女子必有师父,言动必以《礼》,养其德必以《乐》。”他曾用“一切悻礼,相趋于骄骜淫僻而已,求其所以辅佐夫可乎”来表达他对当时女性不遵守礼的行为的深切厌恶以及强烈批评。
妻子除了做到孝敬、顺从、守礼之外,还要做到勤俭持家、操持家务。曾巩除了称赞女性的作品外,也有指责当时女性的言论。如他在《说内治》一文中对女性的行为进行批评:“自居室家,已相与矜车服,耀首饰,辈聚欢言以侈靡。”女性追逐衣服首饰的华丽,家族聚会只讨论奢侈的生活,在他看来是不遵守妇道的。曾巩赞扬那些能够勤俭持家的女性,尤其是在家庭充满困难时尤为可贵,如《金华县君曾氏墓志铭》中提到的曾氏,其丈夫是一名侍御史,但在曾氏出嫁之后丈夫家庭贫穷,她奉养婆婆尽妇道,辅佐丈夫尽妻子道。在丈夫死后,她艰难地生活,以勤劳节俭逐渐壮大家庭,诱教不倦使她的儿子成才,可以说又尽了全部母亲的职责。又如《天长县君黄氏墓志铭》中:“夫人能尽其力,治饮食、衣服以进,及丧,能尽其哀,皆如其夫之志。”黄氏在家中能够尽其所能,负责饮食、衣服,她不仅能够勤俭持家,还可以将家庭关系处理得很好,以维持家庭内部的稳定和平。《周易·家人·彖辞》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意思就是女性对大家族、小家庭中内部的稳定至关重要,而每个家族和家庭内部具有稳定的关系,那么天下才能做到真正的稳定。《寿安县太君张氏墓志铭》中的张氏就是一位能够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女性,对内外关系、尊卑、长辈小辈以及亲近疏远的关系,她都能秉持礼节,安排妥当。
因此可以看出,曾巩认为一个守妇道的妻子,首先要做到孝顺,对父母、公婆孝敬,对丈夫顺从。其次,妻子还需要做到勤俭持家,保持家庭成员的和谐,维护家庭内部关系的稳定。
二、相夫教子
前文中提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可以知道对于古代女性来说,其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室内,女性的日常与义务在主中馈、奉祭祀、侍舅姑、相夫教子等方面,因此女性的价值直接体现于对“家”的贡献。一个妻子如果做到恪守妇道、管理家务、相夫教子,扮演“贤内助”的角色,那么她的丈夫才能够专心读书、获取功名、治国平天下。《江都县主簿王君夫人曾氏墓志》中写到试校书郎、扬州江都县主簿王无咎的妻子曾氏:“以归王氏。王氏家故贫,曾氏为冢妇,而其姑蚤世,独任家政,能精力,躬劳苦,理细微,随先后缓急为樽节,各有条序。有事于时节,朝夕共宾祭奉养,抚其门内,皆不失所时,将以恭严诚顺,能得其属人。”曾氏是一个能力出众的贤良妻子形象,她能够将家里家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那么她的丈夫自然可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地治国平天下了,所以曾氏的丈夫发出这样的感叹:“不以私累其志,曾氏助我也。”又如曾巩在《福昌县君傅氏墓志铭》中记载福昌君在家中时,为父母所器重,出嫁后跟着丈夫没有任何退却,穿着麻布衣服、吃着粗粮,做事却细致入微。她教导儿子仁慈、严肃。关公在池、台两州当官,八十岁才回来,说:“我年轻时致力于做官,而年老时休息在家,没有因家事拖累我的志向,因为我有夫人。”关公之所以能够安心做官,老得其所,是因为没有家事困扰自己,全倚仗妻子。
可见,曾巩墓志铭中的女性与丈夫之间的关系是顺从、辅助丈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曾巩的女性观,他对那些“既嫁则悖于行而胜于色,使男事女,夫屈于妇,不顾舅姑之养,不相悦则犯而相直”的女性是十分厌恶的,直接指出“吾未见其可也”。曾巩指出:“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阃内。岂非风俗之厚薄,人道之邪正,寿夭之原系于此欤?”由此不难看出,常年接受儒学思想熏陶的曾巩,也将推崇道德、维护封建家庭的人伦关系渗透在了他所写的女性墓志铭中。
在另一方面,曾巩认为妻子也不仅是丈夫维护家庭的工具。他在《祭亡妻晁氏文》中有这样的一段叙述:“子有仁孝之行,勤俭之德。宏裕端庄,聪明静默。穷达能安,死生不惑。可以齐古淑人,为世常则……呜呼哀哉!父失贤女,姑亡孝妇,子丧严师,吾亏益友。”曾巩提倡妻子在做到顺从丈夫、帮助丈夫的基础上,应更进一步成为丈夫的“益友”。如果仔细阅读曾巩的这篇祭文,可以发现在他的描述中,妻子在道德层面的表率作用十分显著。在曾巩的记忆中,晁氏让他最难以忘怀的是她在贫困交加的条件下依旧能够做到勤劳持家,是“言无疵悔,动应衡规”。曾巩的悼亡诗《秋夜》里也有对妻子的深切怀念,他将妻子形容为“肺腑友”,即“平生肺腑友,一诀余空床”,他把妻子放在了自己心灵的最深处,认为妻子是一个能肝胆相照的好友。由此看来,曾巩的夫妻关系不仅充满了夫为妻纲的传统儒学思想,还有“益友”的夫妻标准。夫妻能够成为“益友”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既能够促进双方在道德上有所提升,又能够在学识涵养上给予双方启迪,使两人获益。
三、富有才华
前文中提到的两个方面,我们提到的是曾巩遵循传统、恪守典型的儒家思想的一面。但是曾巩的女性墓志铭中,还十分常见又与众不同的就是他对女性充满才华的赞美,这是他的墓志铭作品中独树一帜的特点。
例如,在《寿昌县太君许氏墓志铭》里提到:“夫人许氏,苏州吴县人。考仲容,太子洗马。兄洞名能文,见国史。夫人读书知大意,其兄所为文,辄能成诵。”许氏的理解能力极强,任何书一读便能知道大意,同时还有着超群的记忆力。曾巩在《亡妻宜兴县君文柔晁氏墓志铭》中也写到他的妻子晁氏在十八岁时嫁给他,为人聪明伶俐,遇到事情可以迎刃而解,没有做的不合理的事情,因此在他的妻子去世之后,曾巩“余不知其所以,而又不自知其哭之之恸也”。一位富有才能智慧的贤妻,能够更好地协助丈夫,治理好家庭。又如《夫人周氏墓志铭》又记载了这样一位女性—周氏,她名叫琬,字东玉,父亲和兄长都推举明经。唯独她喜欢图史和做文章,日日夜夜都不懈怠,好比学士大夫,跟从她的舅舅邢起做文章,共有诗七百篇,她文静而正,柔和而不屈服,谨守礼节,言行遵守法度,是一位贤人。周氏是古代知识女性的典型代表,她不仅喜欢书籍和创作,甚至还有作品留存于世,她的诗歌娴静而纯净、柔和而谦卑,语言简洁而不超出法度。
曾巩为其妹妹也作过墓志铭,他在《江都县主簿王君夫人曾氏墓志》中这样描述其妹:“孝爱聪明,能读书言古今,知妇人法度之事,巧针缕刀尺,经手皆绝伦。”曾巩称她的妹妹孝顺聪明,对读书十分精通,知晓古今世事。这些聪慧、富有才智的女子,不但能胜任其“贤妻”的角色,当然还能担当起其“良母”的职责。曾巩认为母亲作为子女的第一任启蒙者,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在女性的墓志铭中多次提到了女性应该具有教育子女的基本能力。正如司马光所说“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宋代社会非常强调母亲的这一责任,如曾巩《寿安县君钱氏墓志铭》中叙写道:“夫人姓钱氏……夫人色庄气仁,言动不失绳墨,居族人长幼亲疏间尽其宜,事夫能成其忠,教子能成其孝,是皆可传者也。”
其他如“子曰披,国子博士,有吏材;曰括,扬州司理参军、馆阁校勘,有文学。其幼皆夫人所自教”的王氏(《试秘书省校书郎李君妻太原王氏墓志铭》),以及前文提到的《寿昌县太君许氏墓志铭》中,称赞“有益于夫,有迪于子”的沈括的母亲许氏等。曾巩撰写的二十五篇有关女性的墓志铭中,有许多女性因为教导子女有方、培养子女成才而受到他及众人的赞美。曾巩多次主张女性识字读书、充满智慧,是因为女性承担了教育孩子的重要责任,这对于当时孩子的成长大有裨益。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了解,曾巩在他关于女性的墓志铭中,记载了许多古代智慧女性的细节和逸事,同时曾巩的作品又遵循儒家思想带有一定的男尊女卑色彩,但是文學性和应用性依旧充斥在他的二十五篇女性墓志铭中。透过这二十五篇墓志铭,曾巩心目中的一个理想妻子的形象似乎已经跃然纸上:首先,要成为一个精明的管家,处理好大家庭中的各项事务,安排妥当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第二,要保持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和谐,做到遵守妇道、勤谨贤惠,顺从丈夫、帮助丈夫的事业以及孝敬公婆等;最后,还要充满学识与智慧,很好地完成教育下一代的职责。但是曾巩毕竟是当时儒家思想主流群体中的一员,他对女性形象的描写不可避免地受到宋代士大夫们为女性塑造的规范和话语模式的影响,他是不可能从这种影响中脱离而出的,很难做到像刘义庆在《世说新语·贤媛》中称赞具有独立个性的“谢道韫”们那样的女性,完全地反传统和反礼教。从曾巩的墓志铭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宣扬儒家思想的同时,试图对传统的女性观进行些许有益的变革,在此基础上,他对当时的许多典型女性进行了赞扬。他认为女性多读书识字且充满智慧,能在日常生活中尽到作为妻子、儿媳、母亲角色的职责是值得欣赏并赞颂的,但是他对女性的描述大多都限于室内,他不可能也不愿意表达女性参与“门户之外”的活动,这一点是有所缺乏的。最后,曾巩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并没有关注或者是赞颂,他选择了忽视或是遗忘对女性情感欲望的需求,他不愿意肯定,让其保持空白。总之,曾巩通过他的二十五篇女性墓志铭,将当时大众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