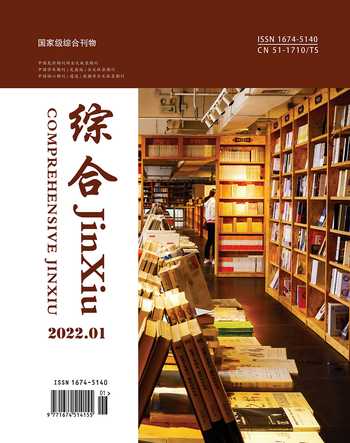“真”的探寻
杨脂媛
摘要:19世纪以来存在主义哲学占据思想的主导风潮,探讨人之为何而存在,而非简单存在(动物性),存在不是活着。艺术家在此哲学思潮影响下,作品不再是古典的故事性叙述,而是历史悲剧下人的苦难再现,试图唤起集体的潜在共识。埃因霍夫作为德国当代艺术家,其作品立足于观照人本身,试图通过作品显现历史伤痛,在观照个体自身存在的同时,同时观照集体的存在。其作品以“失真”人像为主,消除了个体的个性化特质,呈现人的共性外在形式,永恒的真便逐步显现。
关键词:真;脆弱性;集体共性;痕迹语言
一、人的集体共性特质
依叔本華而言,人类与生俱来的盲目性,脆弱性,是意志欲望的表象世界。存在者对存在的虚无感知,对肉体的非永恒性及悲剧性的逃避,而表现出的消极麻木,是非尼采式与生命无意义性的积极对抗。作为通道的艺术家,代替宗教的“神职”,呈现出艺术作品,为观者提供自我存在的沉思,反观自身,找寻个体存在价值,启迪自觉性,对抗盲目性。埃因霍夫认为人这个物种是一个脆弱的、永恒的杂交体,其中的自我矛盾是固有的,是事件的预告,让陈述凝结在寓言中。没有高潮或结局:“被永久地剥夺了解释的钥匙,然而,个体真的曾经存在过吗?演戏角色导致了假扮角色的存在(就像旧照片中那样)。”其作品五官多数空缺而只留得外形的勾勒,保留外在“形式”的共性,消减个体“质料”的差异,似禅宗的内观,面对悬而未置的面部,观者不得不驻足凝视,凝视片刻便是向内寻的观照,注视着熟悉的同类,看到的却是全然不同的样貌。形象的残缺为不可见的神秘打开一扇窗,悠悠透其而入,冲击了固化的视觉,呈现出真的可贵。艺术家自述:“我的人物被安置在空间里,好像他们同时被庇护和监禁。”无疑是在刻意的疏离观者。
埃因霍夫人物作品面貌区别于杜马斯和培根人物作品中的“直视”,后者更趋于内心的阴暗,将恐惧直接的、无蔽的呈现。埃因霍夫的人物作品消解了五官,比“直视”更委婉的传达了人类集体的脆弱性。
二、痕迹语言袒露“真”
绘制作品的过程,耗费的是时间,呈现了痕迹语言,是不断建构自己存在的过程,即为“真”的再现。作者通过作品试图复盘前意识下自己存在的意象。作品中的痕迹语言是制作过程的体现,过程即艺术家意象的逐步显现,是其(存在者)之存在,即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埃因霍夫的作品语言痕迹不同于贾科梅蒂的环绕式线性语言形式,而是制作过程的非预构性生成结果,根据艺术家自述:“在过程中形成的绘画,一幅作品的最终状态并不存在,是一种不断改变作品的欲望,对自己的想法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把我的一些作品比喻成痕迹,这也暗示了碎片概念,即一种让观众从非静止的图像中感受到转瞬既逝的画面。他们是零时人物和人物痕迹”。因此,埃因霍夫作品中的痕迹语言呈现的不只是绘制的过程,也是存在者之存在的痕迹显现。
架上绘画的物质性呈现,由塔皮埃斯推至极致,物质性承载观念性,丰富了视觉呈现的多样性,增强的观念呈现的力度和广度,有强化作者意图的助推效力。埃因霍夫作品中运用大量的非传统媒介材料进行创作,制作过程中有泥沙、水性涂料、胶质等,因此,画面在反复调整的过程中无意识增加了作品的形式厚度,非完全覆盖的修改使得画面保留调整后的痕迹,作品中的时间性随机流露,作者个体的存在性得以留存。痕迹语言是20世纪以来不新鲜的画面呈现样式,但区别于一般的简单化绘画语言的花拳绣腿,埃因霍夫的痕迹语言是独一的,个人的,通过反复的画面调整不断接近个体性意象,作品中个体性意象袒露了集体部分的普遍共性,人类普遍的共有特质(集体脆弱性的显现),同样是永恒的共通的。
三、“失真”后“真”的再现
埃因霍夫的作品是直面苦难的艺术作品,人的脆弱性,虚无性直逼眼前。简化的头部,模糊的五官,冲击观者所熟知的自身的视知觉样态;遗失的肢体,二维的背景,将人的集体普遍共性赤裸裸的呈现,直逼眼帘,或痛苦沉思,或碑式而立。作品凝固的是人类集体存在的自觉意识,即一种共性。击中痛点的作品无疑是深刻的。用无关自身的图像,通过审视,想象背后的不可见的神秘,改造图像,得出其存在的模糊意象,并将其复盘,成作品而显现。历经战争的存在者是苦难的,同时也是真正存在过的,存在的价值无非是还可以继续呼吸的生命延续,埃因霍夫及为此类存在者。战后,无此威胁,人的集体虚无感油然而生,产生对存在价值的否定,回归叔本华式的钟摆,部分人开始消极的应对,荒诞派诞生是对此虚无的直接对抗,将日常生活抽象的视觉呈现,进行怪诞的讽刺,驳人一笑的同时,激发人之存在的价值思索。
埃因霍夫作品通过“失真”后的人像,逐步显现“真”的永恒意义。艺术家曾在档案馆工作,使其每日面对大量的证件照及档案图,使本就关照人本身的他,从最初的观照个别特殊群体(精神病院),至后来观照人本身的集体共性(盲目性、脆弱性),作者自述“对照片的强烈亲和力,将其融入到作品中,以重新创作和异化的形式。”埃因霍夫的作品显现的是对集体共性的关照。与此同时作者认为作品也“描绘了来自周围空虚世界的神秘感”。笔者认为该神秘感区别于东方神秘主义的个体修行而得的神性显现,而是画家所处时代大环境的集体虚无,集体对文明进程和信仰的质疑,而被笼罩在对存在未知的神秘感之中。埃因霍夫试图永担历史罪恶,通过作品中人物“失真”的样态,唤醒集体内在“真”的再现。
四、结语
“真”即为永恒,在西方哲学史上探讨了进乎几千年,每个个体或群体对其的界定范围都是各有所向,以康德为界点,系统权威的质疑了以理智统领的哲学史观,提出感性意志高于形式化的理智。
笔者文中的“真”即为消弱个体的质料特质,呈现集体的普遍性特征。可阐释为个体自觉性的反抗的一种真,自我意识觉醒,通过作品为载体,呈现永恒真实的不可见之神秘,唤起集体刻意回避的无意识。埃因霍夫作品敲击人内心沉睡已久的痛点,使观者生发的思考是除个体外更广的延展,对视知觉固化的冲击,观照人的普遍存在价值,为倍感虚无的存在者生成提供精神依托。
参考文献
[1]孙蛮:《敞开之地的召集—塞尚〈圣维克多山〉系列作品形式结构的生成》,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10月第一版
[2]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的世界—论哲学、文学与艺术》王士盛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
[3]康拉德·G·米勒,梅·鲁道夫:《光和视觉》,刁云程等译,科学出版社1980年
[4]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4
[5]《林中路》,德,海德格尔,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20.06
[6]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林夕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