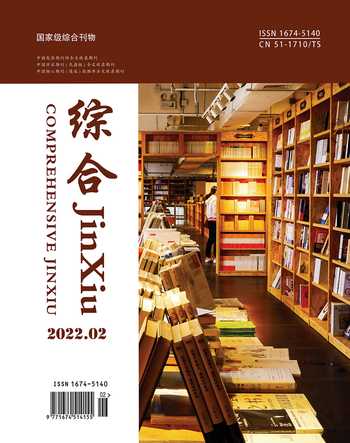网络流行语“打工人”的传播动因分析及文化阐释
黄可可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不断井喷的流行语也成为社交媒体信息交流中的重要图景,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反映着时代社会心态的变迁。因此,本文将以网络流行语“打工人”的风靡传播作为个例,结合狂欢理论、风险社会和身份认同理论来分析此类网络流行语背后的传播动因,在此基础上试图探讨“打工人”背后隐含的社会心态和主体诉求,对“打工人”的风靡传播进行内在的文化阐释,进而厘清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社会结构性困境。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打工人”;传播动因;丧文化
一、网络流行语“打工人”的风靡传播
随着移动端设备的普及,人人都是麦克风,平等开放的互联网环境推动了以用户为核心的信息生产和传播,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网络流行语诞生,网络流行语一般与社会热点紧密结合,具有较强的多样性、趣味性、恶搞性以及传播性,受到网民的青睐,成为人们沟通交流的重要载体。网络流行语“打工人”的风靡传播正是一次网民情绪的集中爆发。打工人,原本多指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通常为外来务工人员。2020年9月末,某名网友发布了一条短视频,结尾他说了一句“早安,打工人”引来大量关注和模仿,“打工人”瞬间成为年度最热的自嘲用语。
二、网络流行语“打工人”的传播动因
(一)社交情境下的印象管理和自我表达
欧文 · 戈夫曼曾提出“印象管理”的概念:个人会试图影响他人对自己的印象,为达到“预期印象”,人们会在社会互动中对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进行选择。网络流行语已成为青年人用来进行自我建构、身份识别的符号资本,通过一句“早安,打工人”就能迅速彰显自我的个性,甚至获得别人的赞赏、认同等正面回馈,以此进行自我外在形象的建构,因为个体在选择加入这场传播潮流的同时,就表示了自身對于流行语背后文化的认同,也即是对于自身个性的呈现,在互动、复制、仿真的信息世界中,群体成员在群体内部的自我调侃和戏谑中悄然完成了自我指认,进行着自我印象的管理。另外一方面,这也是青年人集体情绪的一次自我表达,通过“打工人”这种幽默诙谐的自我反讽,当代青年表达着自身对于现实处境的和阶层上升通道不断变窄的绝望,不论怎样都是“打工人”罢了,无奈的同时还含有一丝自我激励的情绪意味。
(二)全民狂欢,娱乐至上的氛围导向
尼尔·波兹曼笔下娱乐至死的年代已成为现实,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1]。由此,我们便可发现,网络流行语也其实是一种隐喻,创造着特定的文化内容。人们在网络上追求个人情感的宣泄,在情绪化的时代,娱乐至上的氛围环境之下,“打工人”这类自嘲话语很快很容易发生病毒式的传播,人们用笑声代替思考,用娱乐取代权威,那么此时“狂欢”也就成为了现代人闲暇之时最佳的放松方式。网民们将网络平台当作狂欢的广场,在场中通过生产、交流和使用网络流行语来进行自我表达和情感宣泄。在这样一场全民的传播运动中,“打工人”以其自身文本的幽默诙谐精准地把握了集体情绪,迅速吸引了网络大众的传播,面对着狭窄的阶级上升通道,当代年轻人通过戏谑自己是“打工人”,来缓解现实生活的无意义感。
(三)风险社会中的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之中,为了不让自己处于孤立状态之中,个体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群体共鸣和身份认同[2]。个体通过把群体特征与自我特征进行反复比较,从中挑选出与自己相似度最大的个体,由此组成一个文化圈子,人们从该文化圈子中获得语言素材,基于情感、情绪的自我认同生产出专属于圈内成员的词语,再以此进行交际,并因之而获得认同感。网民们对“打工人”进行各种各样的戏仿、改造和拼贴,通过“打工人”背后的文化符号在社交平台上进行对话交流,许多打工人相关的表情包以及诸多含有”打工人“的流行语不断被创造传播,诸如“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晚安,打工人”等等,这些文本和图像的表征都是个体建立身份认同和自我表达的载体,通过对于“打工人”的再创作和传播,个体进入与群体相同的话语体系,构建与群体相似的身份标签,最终获得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感,归根结底,网络流行语的风靡传播其实是一次个体在风险社会中的抱团取暖。
三、丧文化内核下的抵抗叙事
网络流行语是特定时代文化、心态与集体记忆的载体,呈现了某个时期大众的社会情绪和生活心态,反映出特定社会时期的亚文化思潮。“打工人”一词的传播看似是青年人积极的自我调侃,实际上是一次蕴含着丧文化内核的抵抗叙事。“丧文化”是一种新兴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带有负面、消极和颓废等色彩。丧文化的外在呈现形式一般通过对主流“鸡汤”话语进行着“消解”与“解构”实现[3]。“打工人”一词的流行,本质上是丧文化的再现,相比于“社畜”、“佛系青年”等词语,更显得诙谐轻松,带有积极主义的乐观色彩,这种玩梗式的自我调侃本质是青年群体向世界提出的温和抗议,“打工人”背后,是年轻人对于生活重担的调侃,是对于高压环境的不满,也是对于平凡人生的不甘,是属于成年人的一种黑色幽默。在内卷越来越严重的当代,社会结构性压力逐渐加大,阶层流动的通道不断收窄,加剧了青年人的意义危机。“打工人”的集体传播折射出当代青年人的社会境遇和情绪心态,也表达着他们对于解除现代社会症结的美好憧憬。对于青年的意义危机也许是短时间无法根除的,但对于导致青年社会处境恶化和内心焦虑不安的结构僵化,则是必须予以面对和解决的社会问题[4]。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中信出版社, 2015:17.
[2]张康之.论风险社会生成中的社会加速化[J].社会科学研究,2020(04):22-30.
[3]杜骏飞.丧文化:从习得性无助到“自我反讽”[J].编辑之友,2017(09):109-112.
[4]王佳鹏.从政治嘲讽到生活调侃——从近十年网络流行语看中国青年社会心态变迁[J].中国青年研究,2019(02):80-8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