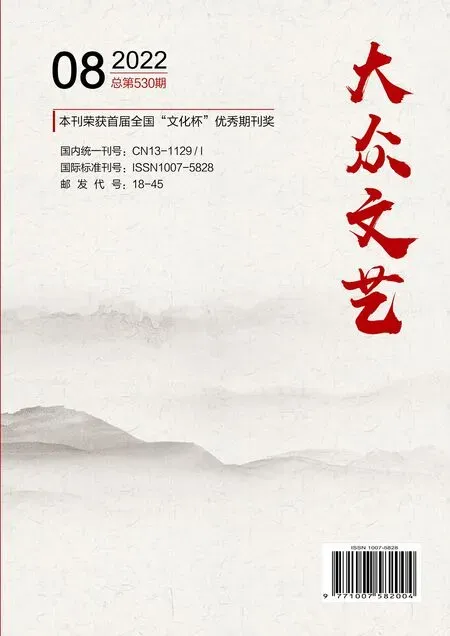从《娱乐至死》反思当代艺术的媒介文化形态
林芷含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000)
《娱乐至死》撰写于1985年,一个的电视文化广泛流行的年代。在书中,波茨曼对影视声像技术逐步替代传统文字语言的新媒体发展潮流作出了批评。
波兹曼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了论述:第一,信息媒介形态如何塑造文化特征;第二,对新闻、法律、政治等严肃行业的泛娱乐化进行批判;第三,身处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泛娱乐化。
而我们看到,波兹曼这一系列超前性的观点在当今时代仍然适用。因此,笔者将运用其理论,对于“如何认识和面对当代艺术的媒介文化形态”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辨。
一、文本解读——“娱乐至死”
1.“泛娱乐化”的滥觞
首先来看,《娱乐至死》全书的主旨在于:“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里的“娱乐至死”,指的是新闻、教育、政治等严肃公共行业的“娱乐泛化”,也就是娱乐媒介形态的性质或行为超出了娱乐范畴,向其他领域渗透,如文化、教育、新闻、商业、宗教甚至政治意识形态。
“泛娱乐化”即人类全方位地附庸于娱乐。例如信息爆炸社会中,我们离不开电视文化传播、互联网,离不开手机等智能产品,这就是人类屈服于欲望的文化表征。
时至当今,网络发展已到达准Web3.0时代,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当代社会在思想、行为、交往方式甚至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方面的变革。在被“泛娱乐化”时代所娱乐的同时,人类也在追求着效率。关系网不再需要面对面地建立,而是通过互联网便可以实现——一切均可通过光缆来重塑。然而,效率的过度追求直接导致需要慢速构建的文化、知识体系这类要素被逐渐架空。
大众文化对于感觉,对于感官刺激的无止境追随,使人性弱点暴露出来,社会成为庸众化的社会。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资本:“追求利润是资本的本能,为了获得更多利润,资本家会不择手段地展开竞争。”
因而,当近年来兴起的新媒体行业意识到其服务的对象是追求欲望的“庸众”之时,逐利性使它不得不利用过盛的欲望进行服务:如视频平台的劣质信息泛滥、电商平台的异化消费等,都在潜移默化中显示着文化产业屈服于娱乐、屈服于欲望的起点和趋势。
2.“泛娱乐化”对于艺术形态、文化形态的影响
当前,各领域的庸众化都正在使娱乐和非娱乐之间的界限消失,甚至影响着我们的艺术形态、文化形态,娱乐属性逐渐参与到当代艺术的领域中,我们发现,媒介产品的泛娱乐化倾向正在一点点显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艺术展览测评、网红展览打卡现象火爆,“小红书”等平台的营销和宣传使人们更多地抱着“打卡”和“彰显个性品位”的目的去观展。然而,在欣喜艺术的普及度的提升的同时,我们是否应当更多地去反思过度娱乐化的弊端呢?
一些网红博主仅将与展品合影的“出片量”作为评价整场展览的评判指标,评价寥寥数语,就武断地概括、界定了某些展览的好与坏,这种单一的审美倾向的过度泛滥势必会导致大众审美的庸俗化。
这种泛娱乐化的根源,源自在早自印刷时代过后就存在的人性弱点:我们人类获取外界信息过程中的基本导向是趋于感性的、寻求最短路径的。电视传播媒介中,感性的视觉刺激是最快速直接、成本低廉的信息获取渠道,而诉诸纯粹理性结构的方式成本更高,因而大众趋向于选择感性而一步步导致了“泛娱乐化”。
有行为科学的实证研究表明,交谈时,只有20%获取的信息是来自文字本身。例如我们在看书时,比起直接阅读文本,更愿意通过诸如“一分钟带你读xxx”的短视频来学习;又例如,大学课堂里,往往会讲段子的老师更受学生喜爱。纯粹的理性世界对大众来说太沉重,而诉诸感性是更便捷的接近理性的路径,人们得以获得“理性般的快乐”,由此更加乐意进入“亚理性”的世界而缺乏一种严肃深刻的思考。图像、音视频的视觉刺激制造了宏富的幻觉,却使人忽视了文字本身的逻辑性、理性、深度。相较而言,接收电视文本一定比印刷文本更使人轻松,但它也同时是一个虚幻的陷阱,使信息本身被简化、异化。由此,可以延伸到波普艺术对流行文化的反思和杜尚“艺术已死”的现代主义批判,说明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当代文化的浮躁性。
3.“印第安人的烟雾”——异化的媒介符号引发的信息肤浅化
波兹曼提出了“印第安人的烟雾”的理论观点,他认为,许多时候我们使用的媒介符号本身的局限性限制了我们获得的信息,我们不能指望电视文化里蕴含着深刻。
例如电视里的载歌载舞;广告中的虚张声势;名人带货直播的晕轮效应;典礼仪式的妄自尊大;各类媒体当中的八股一般的空泛套话……这些其实都是“印第安人的烟雾”,它们一直环绕着我们,并且在电视时代达到巅峰。
它们呈现出欢乐的、泡沫般使人沉醉的东西,用福柯的话来说,这是“异托邦”,即人们用这些不存在的文化时空来规训你,让你误认为这是真的,是合法的、有价值的,用琐碎的生活细节慢慢塑造整个社会。在媒介中,这一点显示得更为宏大:它们让你觉得,媒介从广播电视时代开始到互联网时代,始终在向我们提供的东西都是应然,然而它们其实只是实然范畴的价值。
二、当代艺术的媒介文化形态思辨
1.文化、艺术领域的“娱乐至死”
《娱乐至死》对于媒介形态的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收束:“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其理论核心在于面对时代的不幸而愤世嫉俗;波兹曼不断哀叹娱乐带来的后果——人们离理性而去。也就是说,当人们都会从影像中获得欢乐,从而依赖影像的时候,人们正在离理性而去。
波兹曼由此进行了批判:在观看影像媒介的过程中,知识性的思考能力被压制了,而大部分有深度的理论思考、哲学思考,其实更加需要在专注安静的环境下,通过阅读文本诞生。奥多•阿多诺及马克斯•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描述了资本操控传媒,文化卷入商业化浪潮的时代景观。文化、艺术工业在现当代产生了一个巨大代偿性的损失——影像对人的“文化带宽”占据太重,以至于人们被低质量的娱乐所裹挟,从而放弃了思考的责任。
《娱乐至死》中还形象深入地描绘了媒介与事物的关系:“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
也就是说,当有了钟表,人们开始将注意力放置到媒介本身之上,却漠视了现实中的日出和日落;人们与时间和大自然相互感应的过程被取代。
人们心中壮阔的时间感、对季节的感知和面向宇宙的追问,往往只有在观看日出之时才会沉浸进去;然而有了钟表,你会开始忽视这一切——在感知万物的层面,钟表实际上是失效的。而正如我们不能用只钟表来定义时间一样,我们不能单纯用一段媒介文本来测量艺术的价值;即“媒介即隐喻”指媒介反映了隐喻(思考方向)、反映了一定的信息但不能代替信息本身,这一点跟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论构成一定的对立关系。
波兹曼认为,那些媒介娱乐塑造了一部分大众文化和生活形态,带来了欢乐和迷恋,但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只是人们被卷入了,且与同类互相相信了这一景观。这些欢乐本身的泡沫,使人们逐渐放弃了深度的思考和对周遭环境的自然感知,而是在千篇一律的娱乐化刺激中沉沦,最终远离了自己的人生本质,
2.新形势下当代艺术的媒介文化形态
由于一定程度上的时代局限性,波兹曼认为,最终的语言表达和理论思想沉淀的符号是文字。其实,波兹曼这种过于绝对的论断否定了艺术和影像传播的价值,而过度宣扬了文字信息的力量。
然而实际上,随着当今的数字技术应用的不断成熟和“互联网+”产业形态的高速发展,全新的媒介传播方式逐渐形成,在互联网时代中,五感的记录和传播的力量绝不次于文字,音像和影像具有另一个层面的、文字无法到达的多位面感性输出和效率呈现。在许多当代艺术作品中,数字艺术、电视影像的适度参与是被广泛认可的时代趋势——多媒体的媒介形态在艺术形式上的普及不是个例,而是时代的大趋势,我们必须接受它,并积极改良它。当代艺术普遍借助各类线上及线下相结合的新媒介、新平台进行内容的传播,实现了海量信息的广泛共享,这也极大改变了当代的艺术生态。
3.新形势下当代艺术媒介的传播效能、传播效果问题
艺术领域媒介形态更新与变革展现了当前全媒体整合性的力量,但审视当代艺术的媒介文化生产及传播的具体状态,其艺术观看的“在场性”的缺失以及传播过程的泛娱乐化趋势等现象,造成了媒介的传播效能、传播效果上的问题。
第一,当代艺术的创作过程和叙事手法更加多元化,但当这些创作进入互联网等线上媒介的传播路径时,虽然传播范围更广、传播机会更多了,但许多原文本的内容在慢慢变味。屏幕上,艺术形态变得扁平,受众往往由于线上的信息过于便捷而放弃了线下观赏的“在场性”,或许只是浏览一张图片、一篇推文,观者对于艺术本身的思考就结束了,这使艺术欣赏变得“快餐化”。这种快餐化、大众化的艺术传播模式使艺术的传播效果大打折扣,且在不同传播主体的解构中,原文本的内容逐渐异化。这当然有利也有弊,即艺术作品在被解构的过程中往往失去其严肃性,原作者的意图被消解,但同时也得以获取更为新鲜的艺术欣赏视角。
第二,我们要警惕艺术媒介传播的异化,防止“泛娱乐化”的越界,抵制那些千篇一律、质量低劣,影响大众审美正常运作的艺术传播。一些网红、营销号,借用艺术之名哗众取宠,将艺术作品的本质曲解以增加播放量和曝光度,冲击着艺术领域的生态平衡。这些泛娱乐化的传播方式实际上是在“羞辱”观众,消磨审美意趣,而时代进步中的我们更加需要更加高雅的内容传播引导,艺术审美的提升和媒介形态的优化,需要我们共同的助力和推动。
三、如何面对艺术领域的“泛娱乐化”
1.面对“泛娱乐化”的内容传播主体
传播方式的变革为我国当前的艺术生产提供着新的驱动力,而面对新媒体的时代场景中全新的传播方式,内容传播主体应把握好媒介本身的优势,利用“泛娱乐化”的趋势,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去创造和传播艺术内容;不断创新传播理念,以“观看”为基础的表达途径,以视觉语言为核心媒介范式,进行各主体间的互动交流,充分挖掘艺术作品蕴含的美学理念与创作内涵;不断提出新问题,为有效地解读新的艺术现象,阐释当代艺术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同时,要警惕“泛娱乐化”带来的威胁,主动担当新媒介时代的社会责任。艺术内容的传播主体应在建构和分析艺术现象的过程中结合主流价值观,充分考量其传播的历史文化语境,不为博关注而歪曲或粗制滥造艺术评论等内容创作,而要通过对当代艺术理论进行深刻的解读,使观者对艺术本身形成全面的认识。
此外,既需要汲取与西方可供借鉴的普遍智慧,也需要从我国地域文化实际出发,探索本土化的独特经验。
综合以上几点,只有传播主体审慎对待其媒介形态的各方面特征,才能真正实现艺术追求与价值情感兼得,达到引领艺术领域的发展的效果。
2.面对“泛娱乐化”的个人
那么,面对过度“泛娱乐化”的威胁,个人应当怎么做呢?
首先,要与“被构建”的虚幻保持适当的距离,警惕那些即时性的快乐,学会在踏实、严谨的审美学习中寻找乐趣;其次,要多花心思去做那些看起来“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努力沉淀自身的艺术素养,在艺术创作或艺术欣赏中多阅读、多发现多积累,使艺术创作、艺术欣赏不失扎实的文化底蕴的支撑;最后,在庞杂、浮躁的海量信息面前,要“坐得住”,多思考、多钻研,深入在某一方面剖析问题,多角度去探寻当代艺术的底层逻辑,不能放弃媒介文本本身的深度。
结语
在“娱乐至死”的大环境下,当代艺术的媒介文化形态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泛娱乐化的媒介传播趋势在迎合大众文化、提升传播效率的同时,也消解着人们的理性。
而人类社会的进步之处在于理性、在于深度的思考,如果一味地沉沦于即时的、浮于表面的快乐,我们最终只会成为一个“吸食鸦片的人”,从而拉低自身的审美层次。当我们享受着当代媒介传播的便利之时,也应警惕“娱乐至死”的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