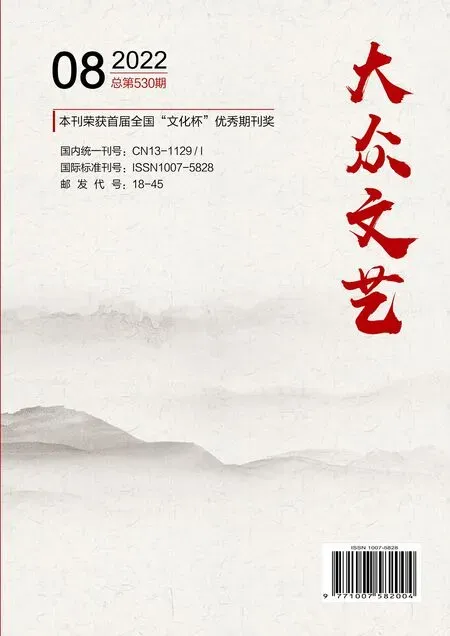论《欲望号街车》中的空间书写
匡荣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四川眉山 620860)
田纳西·威廉斯1947年在纽约上演了他的剧作《欲望号街车》,这部作品囊括了美国三项戏剧大奖:普利策奖,纽约戏剧奖和唐纳德森奖。作品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侧重于以下方面的研究:布兰琪悲剧命运的成因;表现主义及隐喻在作品中的运用;中外作品中女性主义的形象对比研究;及从景观视角出发的研究等。本文运用“空间批评”理论,分析了剧作《欲望号街车》中女主人公布兰琪,在空间实践与空间体验中的逃离与幻景,救赎与疏离,以及被驱逐的悲剧。而布兰琪的悲惨遭遇,也展现了现代社会中普通人在寻找空间归属中的无奈与彷徨。
一、逃离与幻景
剧中,布兰琪生活空间的多次转移向读者陈述了故事的主线,“空间实践可创造大量的叙事地图”。布兰琪空间实践的“叙事地图”有两次大的转向:一是由庄园、家庭、劳伦尔镇转向新奥尔良都市公寓;二是由梦想的公寓转向折叠床、浴缸。这个过程体现了权力与空间的关系。当时,随着美国南方种植园的没落,加上资本大量地涌入北方,北方工业的急速发展和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使得南方没落成为一种宿命。作者虽然没有花费大量笔墨去书写南方庄园,但字里行间透露着南方社会行将就木,资本对社会空间的侵蚀,使整个社会卷入了商品的洪流,加快了南方种植园的崩塌。南方种植园的家是布兰琪的精神寄托,除了资本的步伐加速了它的毁灭,还有家族内部的腐败使庄园日渐萧条,资不抵债。剧作第二场中,斯坦利一直觊觎庄园财产,趁着布兰琪洗澡,打开她的衣箱,翻抖衣物和饰品,寻找财产单据,却得知种植园因为父辈、兄长们丑陋的通奸丑行,把祖产一块块抵押了出去,大部分就这样被败光了。布兰琪再也回不去她的美梦庄园了,布兰琪仅有的一点精神价值和对精神家园的渴望也日渐消失了。
出于家族和自身的原因,她不得不背井离乡,一出场时就身处新奥尔良了。20世纪上半叶,严重的经济萧条的将新奥尔良推向了边缘。从新奥尔良可以看到整个南方经济的演变史,从种植园经济的衰落到工业的兴起,资本涌入创造新财富的同时,也在毫不犹豫地破坏了原来的城市生态平衡,贫民窟就是田纳西.威廉斯一开场就展现了一处城市景观。“这部分虽属穷人区,却不像美国其他城市的穷人区那么惨淡,自有一种俗艳魅力”。这里的房屋建筑破落又有点俗套、诡异。面对颓败的景象,布兰琪异常震惊,揶揄并讽刺道:“我想房子外头是食尸鬼常出没的威尔森林吧”。穿过街区的铁路、灰白色的房屋、摇摇晃晃的楼梯、褐色的河流,到处充斥着工业文明的喧嚣、废弃和鄙夷。资本的巨大力量建造了一座城,同时又在以惊人的速度废弃着一座城。金钱是城市空间关系中的核心价值,资本权力渗透到城市空间中,富人区、黑人区、逼仄而破落的公寓划分了城市的不同阶层,同样也赋予了他们不同的空间价值和归属感。对于布兰琪而言,这里是陌生之地,初次的体验是格格不入的。她貌似锦衣华服地出现在妹妹面前,期望有一个不错的前程,能重新开启生活,但事实上她来到了一个贫民窟。她那廉价的衣服饰品好像是与这里有某种不谋而合的归属,本想作为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掩饰,但资本将都市生活空间分成三六九等,现实直白又惨淡。
这种凄凉似乎没有停止,寄宿者的身份又将她推向崖底。在抵达妹妹斯黛拉的一室一厅的公寓之后,布兰琪被分配了一张折叠床,不由得问妹妹:“两个房间都没有门,而斯坦利(妹夫)—这样得体吗”?“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边界被描绘成了渗透性”。资本的渗透使得空间成为稀缺品。城市空间的不同区域建构着都市人不同的日常生活感受,布兰琪在冰冷的城市公共空间生活中感到无奈又乏力,“在社会空间和社会与空间的每一种关系中,这种结合的连续性和程度在空间实践中得到了加强”。这种逼仄的空间更加激发了她的物质主义,如果说在种植园她还有对爱情的渴望,对自我价值捍卫、尊崇,那么回到奥尔良,已经无法回到从前,生活的焦虑、落魄和对于金钱的崇拜使她无心无力再建筑自己的精神世界。都市美好生活的假象在剧中第七场得到更深一步的验证和推进。此时,布兰琪正在洗澡,斯坦利嘲弄道她是一只金丝雀!布兰琪还沉浸在甜美的歌声里,泡着澡,在小小的浴缸里她吟唱自己的幻景。同处贫民窟,不应该是同病相怜吗?但令人讽刺的是,他不放过这个无产又可怜的女人,似乎更有践踏的权利,相煎何太急啊。拥挤在城市阁楼里都市人麻木了,不想相互同情,亦不会相互抚慰;相反来蹂躏和侮辱。因为前者还有工作、收入和一丁点的社会地位,有一些发言的权力,金钱决定了他们不平等的空间关系。
二、救赎与疏离
离开故土,成为走进都市的陌生人和城市生活中寄宿者,布兰琪对这些物质空间的感知逐渐建构了她的情感脉络和精神世界:陌生、孤独和压抑。“物质空间完全就是可以触知的,在感觉上与物质交互作用的世界,它是体验的空间”。在体验的空间里,女主人公无法实现救赎,在众人的目送中走向崩溃。
爱情,是布兰琪永恒的日常生活空间的主题,也是她精神世界的支柱。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幸福的渴望,源于她对南方家园的挚爱。曾经,她热爱她的生活,期待并忠于她向往的、纯真的爱情,南方的一瓦一木是她心中的伊甸园,滋养了她对美好生活的情感。她爱上了艾伦,欣赏他的才华,在这段恋情里,她专一、真挚,纯洁高雅,但曝光艾伦同性恋的事实后,她对丈夫的自杀身怀愧疚,十分自责。同性恋是不被接受的,甚至是遭鄙视和厌弃的,这与当时南方生活的传统价值和种植园的没落是同向的。种植园里,黑人奴隶受到的盘剥、压榨和欺侮,白人庄园主的肆意妄为、不劳而获,在这个空间里是缺乏平等和民主的,社会传统价值观对于同性恋是持有敌意的,甚至会遭唾弃。艾伦通过自杀想来救赎自己,与艾伦不同的是,布兰琪选择沉浸在纵欲中,妄图在堕落中获得良心的暂时安宁和自我救赎。“跟陌生人缠绵悱恻对我而言是唯一能将我空洞的心填满的途径”。最后在自己就职的学校,开始了和一个十七岁男生的恋情。威廉斯在1973年接受《花花公子》的采访中也非常明确地说:“布兰琪在丈夫死后内心痛不欲生,她必须为杀死自己的丈夫赎罪,她希望通过不断的纵欲得到宽慰”。艾伦选择结束生命来找到生命的起点和尊严,而布兰琪则缠斗和浸染在现实生活的泥泞中、不堪中来寻找生机。遗憾的是,殊途同归,相似的体验空间和南方传统的价值观念促成了他们的悲剧。种植园的生活体验使人压抑又绝望,物质空间的改变造成了精神无所寄托,在布兰琪的亲戚们偷偷抵押庄园财产,变卖祖产,为了获得金钱时,他们就早已放弃了家园,那时家已经分崩离析了,精神家园变成了海市蜃楼,尊重、理解和谅解的家园价值不复存在。
尽管如此,来到在新奥尔良的公寓,布兰琪和米奇开始了新恋情,再次寻找新的生活契机。虽然,她之前行为不检,但遇上米奇,她确实想走进新的爱情。在一次次的空间转移和体验中,她遭受严酷的打击和绝望,仍期望从深渊中被救赎,每一次的不幸,让人愈发同情布兰琪。但都市的贫民窟,并不能容纳她的幻景。在这个生存空间孕育下的一分子斯坦利,缺乏对布兰琪的基本同情心和尊重;这个在凋敝环境中的生活的都市人,内心是干枯的,无生命的,冷酷的,甚至是卑劣的。斯坦利不仅暗中调查布兰琪的风流韵事,还如数地抖落在米奇面前,更无耻的是强暴了内心不堪一击的布兰琪。
空间不但会表现为具体的物质形式,由一定具体的物质空间构成,人们在这个空间生活、交流,对空间有具体的认知;同时,“又是精神在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从南方庄园到都市生活,布兰琪难以逃脱空间体验中的压抑、不平等。无论是亲戚们还是斯坦利,他们崇尚物质,舍弃亲情,无法构建共同的精神家园,布兰琪被一步步逼退在角落里,在对城市的幻景里,被驱逐和排斥,失去了主动和选择的权力,在边缘化的进程中逐渐丧失了自我;生活的意义逐渐在消失,在空间生活的冲突中展示了现代人生存的真相,在空间体验的感知中渐渐沦为被控制和疏离的对象。
三、屈从与被驱逐
布兰琪遭遇了两次驱逐,一次是被赶出劳雷尔镇,一次是被送进精神病院。无论在种植园还是都市,她都没有被认可,甚至受到排挤、非议、打压和驱逐。在“经历过的、被合并到我们日复一日生活中的感觉、想象、情感和意义的空间”中,主人公的精神家园面临一次次的危机,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不得不屈从于现实与精神的牢笼,受制于空间的压迫。
“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空间结构隐射着权力秩序。权力的运作和秩序在布兰琪的空间体验中也显露,她的生活轨迹似乎被笼罩在某种权力的暗示和引导中。布兰琪的悲剧命运始于她在庄园的生活,虽然从小家境不错,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家族的腐败,加之劳雷尔镇淫乱的生活,声名狼藉,无法安身,被迫离开。布兰琪因为家族没落失去了强大的经济来源,到新奥尔良寄居在妹妹的公寓里,又不得已成为睡在折叠床上的寄宿者。她处境尴尬,小心谨慎,过度掩饰:初访中得知家中无人,小心翼翼地给自己倒了半杯威士忌,迅速喝完后,“仔细地把酒瓶放回去,在水槽里把平底杯洗干净。然后重新在餐桌前的椅子上坐好”。当被斯坦利问起喝酒的事,她否认自己极少喝酒。学会伪装,意味着权力的妥协。布兰琪意识到在空间生活中的弱势,让位给斯坦利,这和妹妹相处时的高调和强势是不同的。在窄小的房子里,斯坦利是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在他的各种刁难,鄙视面前,布兰琪示弱才有一点可怜的生存空间。
另外,被驱逐除了经济因素,布兰琪触犯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认知和接纳的红线。女性的成长历来是规训的过程,贤良淑德是标配。家族中有通奸丑行,大肆挥霍,无人问津,而对于她的堕落是被厌弃的、不齿的。金丝雀是供人来欣赏的,玩弄的,是依赖他人而活的。这里社会伦理道德所形成的合力对布兰琪来讲,是毁灭性的。
在医院,布兰琪哀求道:“不管你是谁—我总是指望陌生人的慈悲”。在都市空间体验中,“人类身体的概念,即身份价值和社会存在取决于时间和空间的定义”。[她的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任由医生领着她向前走。她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陌生人,任由他摆布,放弃了抵抗,放弃了幻景,放弃了逃离,放弃了救赎,“仿佛她就是个瞎子”。布兰琪的结局令人深深叹息,精神上受到的压迫,无奈地屈服,可以感受到她和世界的妥协,让步,但在物质、欲望弥漫的现代社会,布兰琪努力挣扎、疯狂逃脱,结果是徒劳的。她的价值和社会存在的意义是卑微的、渺小的、甚至是虚无的,好像南方种植园的遗迹会有人谈起,但终会被渐渐遗忘,还会引来对旧世界的批判;也似美国都市的贫民窟,令人厌恶、窒息,凌乱又肮脏,遭人鄙视。空间的意义决定了布兰琪微不足道的价值,她的生活无人深深关照,她的痛苦无人与她真正分享,她的骄傲和幻景只是被嘲笑和践踏。令人讽刺却又荒谬的是,她的离世却又被众人共谋。她的存在仿佛深深陷入无意义的深渊中,难以自拔,在被驱逐中,终将被推向了渊底。在欲望号街车里没有灵魂地游荡在大都市里,寻找栖身之所,寻找陪伴之侣,寻找属于她的人群。在一个被统治的、屈从的空间中,缺乏平等、友善价值观念的认同,缺乏精神共同体的陪伴和支持,在精神的荒原里使得现代美国人无法找到栖息之所,追寻空间生活的意义,分享共同的精神价值似乎是一种奢望和幻景。
结语
田纳西.威廉姆斯虽然是在二十世纪中叶将此剧搬上舞台,但布兰琪这个孤独的旅行者,在空间的迁徙中被疏离,痛苦地屈从于困境,直至被驱逐。布兰琪的空间体验,呈现了她的生存状态,也戏剧化地映射了普通美国人在现代社会所经历的种种局促,禁闭乃至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