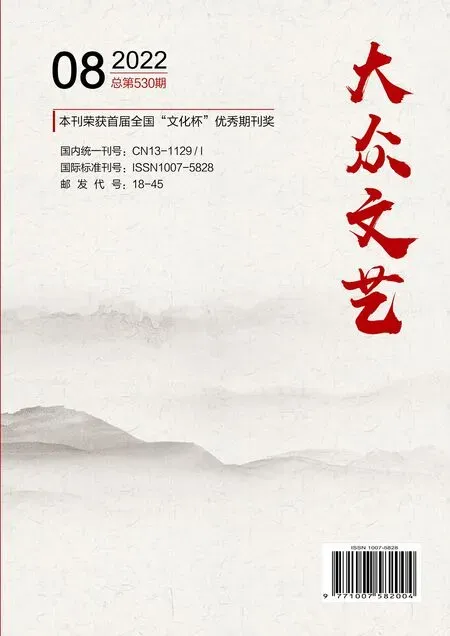规训、抵抗、爱的共同体
——《无声告白》中的越界书写
高树娟
(广州华商学院,广东广州 511300)
新生代华裔美国作家伍绮诗的著名小说《无声告白》讲述了华裔二代移民詹姆斯•陈一家在白人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被边缘为“局外人”,女儿甚至因此而自杀的故事。詹姆斯及其子女由于东方人面孔遭遇了来自主流社会的他者化凝视,无法融入白人社区,并由此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与身份危机。在白人父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主人公一家是游离在社会边缘的他者,格格不入的‘异类’,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纽约时报书评》指出:“这部小说写的是成为‘异类’的那种负担与压力。”主人公无声、窒息的家庭氛围交织着对种族、性别、身份认同的不满和克制。本文分析了白人文化至上主义对边缘群体的文化规训是为了构建以白人为中心的权力话语和社会秩序,充斥了曲解和排斥。詹姆斯•陈和子女们因此无法融入白人社区,女儿的死亡敲醒了边缘文化失声的警钟,促使詹姆斯对文化身份的探寻,打破边界,构建有别于主流文化审美观和价值观的主体意识,最后,主人公夫妇的和解以及白人社区的关爱诠释了以爱为出发点和归宿,抵抗主流文化专制,构建边界开放的、爱的共同体的憧憬。
一、边界与规训
美国“二战”结束后的同化政策强调少数族裔应融入“WASP”主流,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但是华人移民却由于肤色遭受主流社会的排斥。詹姆斯的父亲借用他人姓名蒙混入境,时刻担忧被遣返和驱逐,忐忑不安、东躲西藏地讨生活,极力掩饰外貌的与众不同,拼命融入美国社会。由于或明或暗的排华政策,华人移民的艰辛并非个案,事实上由于肤色遭遇主流社会的排斥是早期华裔真实的生活写照,也成了华裔的集体记忆,促成了主人公詹姆斯•陈一生渴望融入主流社会。然而,种族特征成了白人和华裔受到不平等对待的依据,肤色成了华人难以逾越的界限,在白人文化为中心的社会历史语境下,詹姆斯•陈和子女难以逾越基于种族建构的文化边界,作为被看者承受着白人他者化的凝视,被视为异类,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融入当地的白人社区。
詹姆斯的子女们即使出生在美国,也难逃被凝视的宿命。莉迪亚有着蓝色的眼睛,外表上最像白人了,但是她依然不能逃脱被注视的目光。遗传了华裔父亲的黑头发使她行走时处处被观望,使她“意识到自己在他们眼中的形象,格格不入。”詹姆斯一家如同身处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建筑,白人行使着监督者的特权,注视使詹姆斯一家受到压制而惶恐不安。福柯认为全景敞视建筑的成功在于无处不在的“层级监视”,注视取代酷刑等身体惩罚时刻提醒囚犯不可肆无忌惮,最终养成自觉,实现被规训的目的。来自白人的凝视确立了其作为主体的权力,詹姆斯及其子女们在凝视中被客体化,正如福柯尖锐地指出凝视促成了“他们总是处于受支配地位”。詹姆斯在白人的凝视中受尽屈辱,入读劳埃德学院的第一天,同学因为他的眼睛而诧异,老师也因此惊恐,在哈佛做助教时,由于外貌,第一节课时,学生投射出鄙夷的目光纷纷离开教室,在米德伍德任教时,同事把他错认为了日本外外交官,了解到他是美国历史教授时,难以置信地眨眼睛。无论詹姆斯如何自我辩护其是美国人的事实,在白人的注视下,詹姆斯及其子女无疑是异类和他者,由此促成了白人中心-华裔边缘的分界。
詹姆斯如置身于全景敞视建筑中的囚犯,时刻接受来自白人群体的监督,最终目的便是实现自我规训。詹姆斯主动接受白人主流社会的文化规训,他为自己制定美国文化学习计划,不和父母在学校里讲话,不讲中文,大学选择研究代表美国文化的课题--牛仔,工作中讲授美国历史,詹姆斯为融入主流社会,一切像典型的美国人看齐,甚至因为娶到玛丽琳,一个白人女孩,而激动不已,白皙的肤色是他选择玛丽琳的原因,因为“她能够完美地融入人群”,他把全家福摆在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自豪地介绍妻子不是中国人。詹姆斯内化了白人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并作为子女教育的标准。儿子内斯在游戏时被伙伴们羞辱戏弄时,詹姆斯想象着用暴力使儿子改变。他以白人女孩的穿着打扮、行事风格为标准要求女莉迪亚,最期待看到莉迪亚交到白人朋友,把社交列为她的首要任务,鼓励女儿参加白人伙伴的聚会,挑选最受白人女孩欢迎的项链作为礼物送给女儿,显然,詹姆斯以白人价值观为主导,不仅丧失了自我身份和主导地位意识,而且内化了白人至上思维,无形中增加了子女的心理负担。他默认了主流社会对华裔的曲解和错误表征,并把此当作弗洛伊德所说的缺失,在自己无法获得的情况下,施加到了子女身上,期待子女弥补自身无法融入的缺失。
詹姆斯坚定的美国文化认同被根深蒂固的种族界限所挫败。玛丽琳认为女儿是华裔,所以警察没有对女儿的死因进行彻查,她愤怒指出女儿是白人的话,警察就会继续调查,这刺痛了詹姆斯,他意识到即使在最爱的白人妻子眼中,他也无法逃脱种族凝视的目光,自责地认为自己的血统害死了女儿。这种凝视使“东方不是在场的、言说的主体,而是被看、被理解、被表述的客体”,即为赛义德笔下东方主义话语的再现,是主流社会对边缘人群的控制机制。贝尔•胡克斯认为对于少数族裔边缘群体,肤色决定了他们不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她一针见血地指出“种族才是决定他们的命运休戚与共的因素”。在白人至上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围绕种族而建构的文化边界根深蒂固,在被他者话和客体化的权力体系中,詹姆斯即使主动接受与实践白人社会的文化规训,也无法使自己的身份由客体转换为主体。
二、越界与抵抗
贝尔•胡克斯在《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中坚定地表达了抵抗专制文化的立场,她认为对专制文化持有抵抗姿态是走向解放的第一步,如果没有“对这种统治文化说‘不’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得到解放?”。胡克斯认为边缘文化不应放弃自我表征的权力,在从边缘到中心,从被曲解到自我表征的过程中,不应为了“融入”而牺牲复杂性与个性,要通过差异来显现事物的真正意义。詹姆斯为了融入而摒弃一切差异性的文化表达,并未实现被主流文化所接纳,反而逐渐逐渐丧失了主体意识。为重新确立主体地位,詹姆斯从族裔文化差异中寻求自我表征,从族裔文化定义美国人属性,从而实现文化身份的越界。
华裔路易莎•陈是詹姆斯在米德伍德教书时见到的第一个东方学生,他和路易莎有着莫名的默契,詹姆斯从路易莎身上看到了其族裔性的投影。斯图亚特•霍尔指出在建构文化身份时,差异构成了“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因素,这是一种“迫使我们将自身视作和体验为‘他者’”的差异。认识到差异性唤醒了詹姆斯的主体意识,他试图在自己的族裔文化中去寻找同一性,从而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路易莎如同一面镜子,詹姆斯面对她时,萌生了主体意识。路易莎一方面是东方文化的象征,作为文化的他者,唤起了詹姆斯的美国人主体身份意识,同时作为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人,詹姆斯从路易莎所代表的族裔文化中获得认同。在与路易莎交往中,詹姆斯感觉轻松自在,“他想,这就是他应该爱上的那种女人,一个长得像这样的女人,和他相像的女人。”对路易莎的爱恋也意味着他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寻求自我表征,被压制的主体意识获得解放,由客体逐渐转变为主体。
小说中对詹姆斯多年后吃中国食物进行了细致的描述,“里面是三块雪白地小点心,表层地褶皱就像含苞待放地牡丹花球,露出一点里面的红褐色地馅料,烤猪肉地香甜味道飘进他的鼻孔。食物是一种文化联系,回忆起母亲做点心的画面,以及父亲最爱的点心,“这种点心是他父亲的最爱,叫作‘叉烧包’”。詹姆斯脱口而出讲中文有着深刻的寓意,他由食物联想到了父母,食物是亲情的寄托、族裔文化维系的纽带。食物意象频繁出现在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食物是文化符号,重新确立了主体与族裔文化的联系,是族裔文化的社会表达。在这里,食物是詹姆斯建构主体地位、宣示自我的重要表达途径。食物也是表达爱意的语言和媒介,露易莎的家是他被主流社会边缘化、驱赶孤独的避难所,是他跨越种族边界、抵抗白人至上主义后的慰藉。食物是他精神和文化的滋养:“它的味道就像一个吻,充斥着甜咸交织的温暖。”食物是族裔文化的表征,是詹姆斯被放逐到了社会边缘后,争取主体地位的呼声,标志着他自我意识的觉醒,他认识到自身族裔文化的属性,通过族裔文化这一差异获得自我表征。
三、构建爱的共同体
伍绮诗在谈道《无声告白》的创作初衷时,提到除探寻族裔差异外,她希望作品可以用爱触动人心,她书写的“是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家庭,爱和失去。”在詹姆斯家庭内部,爱开启了沟通的大门。玛丽琳和詹姆斯的跨种族婚姻一开始就存在误解,詹姆斯娶白人妻子是为了避免与众不同,玛丽琳嫁给华裔认为是可以标新立异。胡克斯指出在跨种族婚姻中,只有爱还不足以超越差异,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也需要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理解和接受代表边缘文化的伴侣,“相互奉献和索取能使他们的关系得以保持下去—不是什么罗曼蒂克的幻想”由此,爱和理解的过程是一个互动和双向的过程,共同作用才能超越种族的界限。詹姆斯和玛丽琳最后的争吵开启了有声沟通,玛丽琳了解了种族歧视对丈夫的伤害,而詹姆斯也理解了性别歧视对妻子的压迫。爱的实践包含了理解和越界,从而实现“建构一个能够容许越界的文化发声和自我表征的空间”。由于爱,这个家开始了有声的沟通。
莉迪亚的死亡不仅是家庭悲剧,而且触发了整个白人社区对死亡和生命的本质的思索。人们自发地参加了葬礼,莉迪亚和内斯的学校在葬礼当天停课一天,莉迪亚和内斯的很多同学也参加了葬礼,“一些邻居围住了李家人,抱紧他们的胳膊,说着安慰的话。”内斯去在一家卖酒的商店,店员得知内斯是莉迪亚的哥哥的时候,破例同情地递给内斯两瓶威士忌,并且免费。内斯将车开到最安静地县界,大口喝酒,烂醉如泥地倒在车里。菲克斯警官默默地给予他父亲般关爱与照看,以至于内斯误以为是父亲对他的照料。人们对詹姆斯一家的不幸给予同情、关爱和帮助,这超越了围绕种族的分解以及围绕种族所建构的文化分界,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贝尔•胡克斯构想的爱的共同体。胡克斯在《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一书中也强调边缘人群在反对专制文化的斗争中要以爱为出发点和归宿,“既要爱自己,也要爱自己的敌人或对手……要在差异的基础上构建爱的共同体。”爱的共同体超越了种族边界,可以包容差异,消解了中心与边缘的界限,独一无二的主体性得以确立。胡克斯认为爱是颠覆主流文化的实践,可以通过改善集体来改造社会,由此这种爱包含着关怀、认同和接受,是一种变革社会的力量,爱的共同体超越差异和文化分界,消解了白人与华裔、主体与他者的边界。
结语
借助跨种族婚姻家庭被排斥和边缘化的故事主体,《无声告白》讲述了华裔男主人被主流文化规训和排斥,但从族裔文化中得到精神的滋养,并定义了自身的多重文化身份属性。主人公重塑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主体地位消解了白人盎格鲁-萨克森文化中心论,打破白人霸权话语中主体-客体的分界,实现了文化的越界,同时小说用死亡敲响边缘文化失声的警钟,凸显了爱可以架起沟通的桥梁,超越主流话语中中心-边缘的分界,爱的共同体是抵制主流文化的专制的强大力量,契合了贝尔•胡克斯爱的变革力量的表述,构建了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