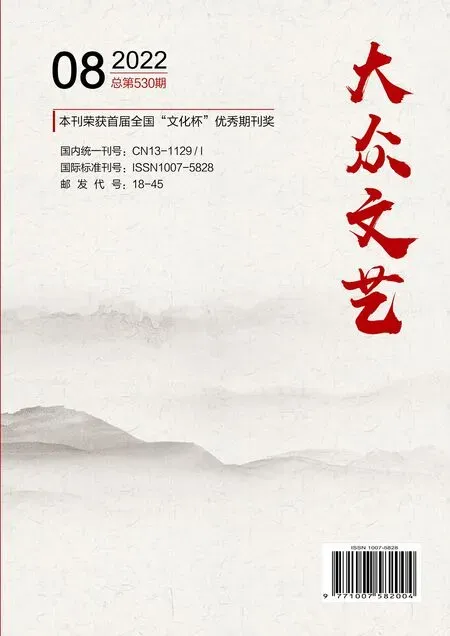加速社会的“无聊”抵抗: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视域下的电影《帕特森》
程梦菲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长沙 410000)
吉姆•贾木许是当代美国少有的长期坚持在电影作品的艺术风格与工业生产层面均保持高度独立性的著名导演代表。受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安迪•沃霍尔、“地下丝绒”乐队等前卫艺术家所树立的纽约地下艺术精神的深刻影响,首先,贾木许的影片表现出了显著的极简主义美学与反主流特征。在剧本创作上,贾木许背离了好莱坞主流商业电影的叙事成规与类型片逻辑套路:例如少有悬念、反转等叙事噱头,主要以生活流或是模块叙事组织故事情节;不关心精英生活、英雄事迹或是大人物的发家史与罗曼史,而注重对他乡异域、异质性文化符号以及边缘人物生活状态的指涉等。在视听语言表达上,诸如长镜头、简洁的标题与不自然的黑屏转场等都是贾木许的作者性标签,制造出其影片独特的疏离气质与割裂感。同时,贾木许电影的制作模式也依然体现着纽约地下艺术所确立的传统,不愿“牵手”大型电影制片厂,坚持有限成本投入与独立工作室制作,在确立导演个人对作品主导权的基础上,发动所处文化艺术小圈子内熟识的好友及业界人士共同参与到作品的生成过程中去。对于贾木许而言,电影是他同他所信赖的伙伴“集体合作的结果”。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面临着流媒体、社交网络以及资本浪潮更为剧烈的冲击与裹挟,贾木许依然坚守着独立不移的影人品格。在其新近作品中,不同于围绕角色非人化的吸血鬼与僵尸身份设定做文章的《唯爱永生》(Only Lovers Left Alive,2013)与《丧尸未逝》(The Dead Don’t Die,2019),于2016年在戛纳电影节首映的《帕特森》(Paterson,2016)延续了贾木许此前作品中对在生活方式和状态上表现出游离与边缘属性的普通人的刻画,聚焦新泽西州帕特森市一位叫帕特森的公交司机和他的伴侣劳拉一周七天的日常生活情境,既完成了一次对其前期作品中反复探讨的重要母题的推进,又温和而坚决地对于当下的一种时代症候作出了不合作的表态。
一、贾木许影像中的“无聊”母题
“无聊”是贾木许早期电影所偏爱的核心母题之一。在其不少电影作品中,充斥着人物有效信息贫乏、营养与深层内涵欠缺的枯燥对话。此外,主人公懒散怠惰的表情、肢体与动作以及目的不完全明晰的行走与浪费时间的娱乐等行为亦是人物无所事事、无聊透顶状态的直接反映。当然,面对着当下沉闷而闭塞的生活,体验着无聊情绪的恼人侵袭,贾木许电影中的人物也并非都无动于衷、毫无作为。此时此地的无聊感受往往唤醒了他们内心深处的逃离冲动,催促他们离开此地、踏上旅途,企图在新的地方获得一种新的人生体验,改善无聊的生活境况。这种逃离冲动作为贾木许前期作品中支撑人物行动的关键内在驱力,在贾木许的导演处女作《长假漫漫》(Permanent Vacation,1980)开头男主角的独白中便已经得到了表达:“有些声音告诉你,到此为止吧,是时候离开了,去别的地方看看……”于是,在直觉与感觉的驱使下,年轻的主人公开启了漂泊游荡的“漫长假期”。那么,人物出走后如何呢?这一问题在贾木许的成名作《天堂陌影》(Stranger Than Paradise,1984)中得到了更清晰地展现。在终日和威利一起荒废人生而倍感厌倦的埃迪赞同威利提议和他一道去往克利夫兰探望他的表妹艾娃后不久,依旧空虚的埃迪在克利夫兰寒冷的雪地里对威利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你来到了一个新地方,而一切看上去似乎都一样。”在贾木许前期的电影作品中,他已有意或无意识地揭示出,在不动摇持续生产无聊的日常生活形式结构的情形下,远方仍会导向虚无。
在《不法之徒》(Down by Law,1986)中,意外入狱、在监狱里穷极无聊的倒霉“罪犯”扎克和杰克同由意大利著名演员罗伯托•贝尼尼饰演的杀人犯鲍勃成功越狱,在与鲍勃分别后,二人最终又在岔路口踏上了充满未知的前路。此后,贾木许剧情长片中的主人公仍旧时常在异乡、在路上,而贾木许在电影中对于无聊、空虚之情绪与境况的表现似乎又融合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元素:诸如《神秘列车》(Mystery Train,1989)中的摇滚巨星“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离魂异客》(Dead Man,1995)中的印第安文明等。而关于“无聊”议题所遗留的“建设性的”问题——普通人的一种抵御无聊的日常生活状态应该是怎样的,似乎直到在电影《帕特森》中,贾木许才通过展现由亚当•德赖弗饰演的公交司机帕特森的生活给出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范式。亚当•德赖弗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贾木许影片主演惯常的表演风格,男主人公帕特森如同此前很多贾木许电影当中的角色一样,表情变化、肢体动作不灵敏,在应对外界发生的事情时总是表现出些微的局促与笨拙。但在《帕特森》中,这些迟钝的身体反应并非主角百无聊赖之心理状态的外化。帕特森爱好诗歌,在他并不忙碌的工作之余,他习惯于观察和倾听,从身边事物及日常见闻中汲取灵感,投入到诗歌的构思与写作中去。在这里,帕特森所显现出的观众习见的贾木许电影典型人物情态,是主人公专注于内心与自我、沉浸在个人丰盈的精神世界这一生活状态的写照。与此同时,帕特森的“不远行”亦是他满足于当下生活的佐证。在贾木许此前的作品中,导演注重捕捉旅人们在异地街巷、机场、旅馆等供人途经、中转或暂时休憩的这类地方的言行举止与神态,对于这些旅人们而言,这些地方可以被认作“非场所”或带有着“非场所”属性。所谓“非场所”,依据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热的观点,即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不能被定义为关系性的、历史性的或与身份相关的空间”。在类似的旅人们短暂停留的城市地带,他们的职业与家庭身份在很多情况下处于隐匿或无关紧要的状态,他们既无法在这里找到自己过往存在的证明,也难以发展出新的人际关系。这些地方无关个人历史也不提供创造未来的环境空间,对于贾木许影片中本就游离于主流社会外围、缺乏归属感的边缘人来说,他们在同当中陌生的人与事物应接不暇的相遇中不断遇到新的问题或是陷入新的无聊与错愕,更激发出了他们内在的孤独与空虚。于是他们继续奔赴他处,也似乎在比喻意义上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移动的“非场所”。而在《帕特森》中,主人公并未萌生出走的意图,从家庭到工作岗位再到夜晚消磨时光的酒吧,帕特森的生活主要围绕着一些固定的场景运行。作为一名沉迷于写诗的公交车司机,帕特森依然以特定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但享受着同诗歌和爱人相伴的充实而平和的生活,帕特森不再具备逃离的内在需求或动机。贾木许电影中的普通人不多见地拥有了内心沉静的品格、达成了安定的生活状态。而在贾木许的影像世界中,这样一个显著的超越“无聊”的普通人角色的诞生,也带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性。在人们的精神生态因现实生活压力的催逼而普遍趋向荒芜、“无聊”持续作为一种整体的消极情绪氛围而存在的当前社会,帕特森异于时代主潮的生活模式是值得关注与进一步分析的。
二、加速时代的“无聊”症候与《帕特森》的“表态”
如果能够稍微留心周边人的生活状态或者偶尔反思自己的日常行为方式,我们或许能够体察到当代人所经验到的“无聊”产生及作用的吊诡形式。贾木许早期电影中所主要呈现的游手好闲或是无所作为的“无聊”已不能反映当今社会无聊症候的全貌,相比于闲得无聊,忙得无聊悄然间成为我们生活中占据主导的无聊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与经济总量的稳步提升,普通民众的生活便利程度较以往而言得到了极大地增加,然而,人们却普遍感受到生活的便捷并未让我们个人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在很多社会场景中,人们的办事效率都得到了有效提高,但时间却似乎反而越来越不够用了。为了获取现今加速丰富且表现形式不断更新迭代的经济、文化等各类资本,将自己打造为世俗意义上出类拔萃的“人物”,人们拼命学习、工作与赚钱,生怕被他人超越、被时代落下。可以说,现代人不止不休、疲于奔命的追赶如同滚轮里的仓鼠一样——这一比喻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霍耐特的学生、以对加速社会的批判性分析及理论体系构建确立学界地位的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曾提及的,用以形容加速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典型生活状态。在这样的情形下,受世俗评价体系的影响,不少人潜意识中就会认为,做无关个人资本积累的“无用”之事是对于时间与生命的浪费,从而激发我们内心的焦虑与罪恶感——即便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可能带给我们精神上的滋养与满足。因而人们最终陷入了罗萨所讲的“所做的事(即便是我们自愿做的事)并不是我们真的想做的事”这样的一种“异化”状态。为了成绩刷题、为了绩效应酬、加班……并且还要竭尽所能开发时间,提高效率,超出平均速度。被这些重复、持续而低幸福感的事情绑架让人感到劳累与厌倦,而为了缓解忙于加速所带来的疲惫与无聊情绪,人们沉迷于电子设备中算法设计的、缺乏内容深度的各种社交媒体信息与短视频,以无聊的娱乐方式调节非意愿工作与学习的无聊,从而能再投入到忙碌的无聊中去。这便是加速时代以悖论的形式存在并不断循环生产的典型无聊症候。以“无聊病”为代表,在罗萨看来,加速社会所带来的危机之一便在于其对人的诸如此类的精神异化。贾木许同样排斥现实社会加速体系对于人之精神世界的倾轧与损害,在电影《帕特森》中,贾木许对于现时代“无聊”症候的反思性指涉,也能够在贾木许对其产生机制渊源——加速社会的影像“修正”中显露出端倪。
也许是出于对影像在美学上的独立感或纯粹性的追求,贾木许不太热衷于在影片中探讨真实世界当下直接现实的热点话题,对时代症候发表议论与见解,而更偏好意义模糊、价值判断冷淡的话语表达。而在《帕特森》中,贾木许还是通过帕特森拒绝使用智能手机这一情况,在作品中融入了其对于当今现实问题相对清晰的观点与立场。例如面对劳拉在得知帕特森工作路上发生意外后让他再度考虑使用智能手机以方便平日遇到突发事件时联络的建议,帕特森态度明确地表示了回绝:“在智能手机诞生之前,世界也正常运转着”。帕特森对于智能手机的抗拒情绪背后,可能便寄寓着贾木许对于由电子产品发挥重要控制作用的现代加速体系进步性的质疑与不信任。自然,《帕特森》完全不会因为这有限的现实表态便成了承载发声需要的社会批判工具式的影片,但这一表态作为贾木许影像世界中的少有事件,标志了《帕特森》影像世界的建构所可能具备的显著的现实背景基础。在电影《帕特森》中,贾木许围绕着帕特森的日常生活行动轨迹,构造了一个理想化的、独立于当今加速社会风暴之外的人物生活空间,或许可从罗萨所讲的加速社会“加速”的三个方面的范畴——科技进步、社会变迁以及生活步调尝试予以体察:
在科技进步方面,落实到人物具体的生活情境中,相比于科技加速进步浪潮下人们的私人或社会生活均被云服务与电子设备绑架的现实,在电影里,如无意外事件发生,无论镜头对准家庭内部还是城市公共空间,我们在排斥进入互联网体系的帕特森的个人日常生活中都难以捕捉到信息技术直接介入的痕迹。在社会变迁层面,不同于人们的工作、兴趣和习性跟随社会需求、热点与风尚的加速变迁而不断更新与转移的时代景观,在电影《帕特森》中,主人公所生活的城市“帕特森”与主人公“帕特森”都未完全跟上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对于城市“帕特森”而言,贾木许关注到了其在加速时代中的“落伍”属性。相比于热闹又吸睛的大都会,新泽西州帕特森市整体氛围相对平静、安宁,并非充满浮躁气息的引领时代潮流的最焦点地域。位于美国东北部瀑布线,帕特森曾经依靠水能资源成了美国历史上重要的工业城市。伴随着工业的繁荣,这里曾涌入大批移民,也曾兴起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影片中女主人公劳拉的伊朗血统以及公交车上两位自认为或许是“这座城市最后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大学生的谈话均可能带有对相关城市历史的暗示。然而,属于这座工业城市的曾经的激荡与喧嚣终在信息技术时代归于历史遗留,并铸就了其发展出陈旧与衰败美学的基底。在电影中,我们能够看到贾木许对于帕特森城市景观中的商业化、时代性元素的表现是有限的、侧面的。而对于主人公“帕特森”而言,身兼司机与诗人的角色,其终日重复着主要在家中、工作岗位上与酒吧里活动的规律而单调的生活,但由于他将空余时间留给了自己所钟情的伴侣与诗歌而非电子产品,所以他从不感到生活的乏味。只要生活中不发生大的变故,似乎他能够恒久地做这份悠闲又无压力的公交司机的工作,恒久地写诗,也恒久地同加速浪潮隔离。实际上,影片片名的双关指向便或许已经泄露出了贾木许谋求表现主人公同其所处环境在神韵上的契合这一心思,而这一构思也同样借助影片的拍摄手法得以体现。依然通过其作品中对准主人公的跟拍镜头“对于移动和人物周围变化景物做最纯粹的视觉还原”,贾木许着力捕捉人与城市的同频共振。此外,摄影师拍摄出了带有胶片质感的城市景观与人物影像,更强颗粒感、昏黄感与朦胧感的画面又为人与城市的“不变”赋魅,更衬托出老派且安于现状的司机兼诗人帕特森同他所在的城市新泽西州帕特森彼此统一的内在气质。最后,在生活步调层面,在加速时代的日常中,个体开展学习与工作、娱乐以及休息的时间分配时常呈现出相互侵犯、界限模糊的粗糙状态,工作时间挤占维系个人身心健康所必要的休闲娱乐时间,使个体的生活节奏片面地加快。而由于后者得不到充分保障,主体也时常驱使后者“报复性地”干扰前者,致使个体的生活节奏杂乱无章。人们对于事物的深度注意力也被“超注意力”取代,“这种涣散的注意力体现为不断地在多个任务、信息来源和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但对于帕特森而言,他在自己相对固定的活动空间中能够游刃有余地捋顺生活的时间线。通过对其日常生活空间的“窥探”,我们发现其“工作时间”与“爱好时间”之间的关系不存在分毫当代社会习见的冲突与紧张。二者有规律地交替运行,使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帕特森享有着充足的时间,也享有着平稳、从容的生活节奏。
总之,通过展现帕特森所置身的与加速时代日常有违的生活空间及其中发生的生活事件,贾木许表达了其对于加速的现实社会的疏远与抵触。而关于个体怎样摆脱加速思维,有效地开展生活“降速”,从而对抗加速社会所催生的以无聊为代表的消极集体情绪产物这一问题,贾木许也借助帕特森的具体生活方式提出了一种生活理想,或许能够为加速时代迷茫且被动的个体克服精神危机、追求美好生活带来抚慰与灵感。
三、作为抵抗策略的亲密关系与诗歌
在罗萨对于如何抵御加速社会症候、实现理想生活状态这一问题的回应中,其注意到了“共鸣”(Resonance)这一带有隐喻意味的说法在阐释人与世界关系的层面上所具有的理论表述潜质,并围绕这一概念勾勒了应对加速社会及其引发的新异化形式的理论蓝图。所谓“共鸣”,指向的是主体同他人或各种抽象与具体事物间源于心理认同而建立起的精神层面长效、稳固且深厚的情感联结,这种情感联结是同基于功利目的的复杂外界社会关系相剥离的。“共鸣不是一种回声,而是一种回应关系”,“共鸣关系要求主体和世界都充分地‘封闭’或自我一致,以便各自发声,同时也保持足够的开放以便彼此影响或接触”。由主体视角观之,无论对象是否有生命,此端都能感受到彼端对于主体意识活动的激活与呼应。而在《帕特森》中,男主人公帕特森同自己伴侣关系的经营及其在诗歌爱好上的艺术追求便分别从人与人以及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两个向度上提供了个人抵抗精神世界的无聊与空虚的共鸣形式示范:
对于现代人的生活而言,在立场先行、个人至上、交往理性凋敝的社会舆论大环境下,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上的龃龉、人际关系处理上的摩擦已经构成了人们常态化烦闷与无力情绪的重要来源之一。加速社会追求“短平快”的实用交际,因而当麻烦、误事的沟通障碍或观念分歧出现时,人们为了“更要紧的任务”或是必要的休闲状态时的“耳根清净”而习惯搁置或逃避沟通,对人际关系经营冷处理、不作为。背后的重要原因在于,付出达成理解的努力相较于付出赚取金钱、名望、学分等“实际的东西”的努力而言,在当今社会的价值评估体系中不具备更高的性价比。因此人们便更加懒得沟通、没时间沟通,认为沟通无用且无聊。在交际对象上,亲友作为个体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同他们关系的处理丝毫不比同一般同事或是陌生人关系的处理来得轻松。由于亲友同个体私人生活及情感更为紧密的牵连与羁绊,同他们之间关系的良性与否也更容易左右到主体的精神状态变化。省去了一般关系中的试探与客套,亲友关系中的个体在不少情形下可能更容易丧失交往耐性,一旦一方的意见不被另一方认同或接纳,便极易触动消极情绪的爆发。长此以往,个体可能面对的精神困境或许就不再仅仅只是无聊、空虚与无力情绪这么简单,甚至可能走向崩溃与绝望。在《帕特森》中,帕特森与劳拉之间建立起的伴侣与知己关系是值得重视的。像他们这样在性格与观念上存在着明显差异与分歧的一对伴侣能够维持感情的长久稳定,这在当下的现实中是不太能够轻易实现的。帕特森为人相对古板、木讷与内敛,而劳拉则有着自由、活泼、浪漫的性情;相比于帕特森专一的诗歌爱好以及一成不变的规律生活,劳拉则有着发散的兴趣点,追求变化,每日忙着窗帘涂鸦、纸杯蛋糕制作、学弹吉他等不同事项,乐于尝试新鲜事物;帕特森生性淡泊,写诗只为单纯的自我抒发,并未考虑借由诗歌实现些什么,而劳拉则怀揣着成名的愿望,梦想成为乡村歌手,也一直劝告帕特森将他写在小本子里的美妙诗歌打印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她谈不上急功近利,但她拥有且并不回避与掩饰自我的欲望与雄心……然而,在两人的相处模式中,他们都并未陷入自我强硬的执念而灼伤他人,都懂得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认真且耐心地回应彼此的诉求,给予了对方充分的关心、认同与尊重。例如当劳拉提议希望自己将诗作打印出来后,帕特森愿意顺从爱人的心意,约定在周末完成这一事项;而在得知帕特森在上班途中驾驶的车发生了故障后,出于担心她建议爱人考虑买部智能手机以便发生意外事件时联络,但当帕特森表达了不情愿后,劳拉也无意强求……考虑到帕特森和劳拉性格上的诸多不同,很难说二人之间关系的调和是出于同类人的志趣相投与脾性相近,在人际交往中拿捏好分寸,不为得失斤斤计较,放下一己偏执而愿意花费时间倾听与沟通才是两人在相异中达成契合、实现情感共鸣与爱情保鲜的秘诀。而有了和谐美满的亲密关系做支撑,排除掉一地鸡毛的家庭琐事干扰,个人生活的幸福感也有了基本的保障。
同加速时代的人际关系处理类似,对于不少普通人的生活而言,追求工作之外的艺术爱好既不足够“有用”,又不足够“放松”,“两头不到岸”。而对于“地下艺术家”出身的贾木许而言,对艺术的亲近无疑应当是相对独立与封闭的个体敞开自我并同世界保持联络的重要凭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贾木许曾跟随“纽约诗派”重要人物肯尼斯•科赫以及戴维•沙波里学习诗歌,与音乐和电影一道,诗歌这一艺术形式深刻地影响了贾木许的精神生活——这也能够体现在贾木许的电影创作上。贾木许影片中习见的分模块这一影像材料组织方式以及模块间叙事上的重复与押韵,便显著地反映出了诗歌艺术的属性。而除了一以贯之的结构形式上的诗性特征之外,诗歌艺术作为内容元素则一般仅以零星的符号化的方式存在于贾木许此前的作品里,但在《帕特森》中,诗既作为文化符号发挥作用,又是贯穿影片始终的情节连接线索与主题,并被赋予了现代人可以依靠的精神解放之门这一功能。在暂且不论个人难以撼动的加速社会强大的规训与整合体制的情形下,与亲密关系的经营相仿,主体要想通过同诗歌或其他艺术形式建立“共鸣”的方式通往真正的诗意生活,其介入的心境与姿态是至关重要的。以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为偶像,帕特森的诗歌写作也承袭了前者的宗旨,不关注华丽、宏大的意象,而注重观察自然与生活,复活对于周边人、事、物的感知觉,挖掘日常生活意象的意义潜能:早餐时手边的“俄亥俄蓝标火柴”、瀑布、偶遇的写诗少女、当然也包括劳拉……都可以是他创作的灵感源泉。能够真正沉下心去、有感而发,帕特森的写作实践是赤诚而纯粹的,区别于借助诗歌逃避现实,无病呻吟还自我陶醉的“文艺病”,亦不流于利用艺术装点门面或是算计利害得失的庸俗做派,其对诗歌无所企图的非功利心态铸就了他强大的内心,使他同诗歌的情感联结难以被斩断。出于热爱,一方面,他能够很好地消化来自社会主流的、带有成见或刻板印象的声音。在帕特森偶遇的同样爱好诗歌的少女对他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却喜欢艾米莉•狄金森表示惊讶时,尽管这只是孩子在有限认知水平下的一时口快且并不带有主观恶意,但她所表达出的下意识的关于社会身份及其对应习性的固化思维在真实的社交场景下其实很可能对于听者构成一种心理上的冲击乃至伤害。而在电影中,镜头给到的帕特森此时的反应非常值得玩味——在女孩说完那句话并离去后,他短暂地愣了一下,随后若有所思地念出了少女刚刚念给他的诗句。帕特森愣住的一瞬反映出他可能在这一次通过他人观点确认自己“异类”属性的事件中感受到了一丝愕然,而他也可能只是还没有从女孩的言语中回过神来。但无论他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活动,最终他将注意力锁定在了女孩优美的诗句上,甚至于后来回到家中,还念念不忘地同劳拉分享。对帕特森而言,关于诗歌的感受与灵感终究是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当生活给他开了小玩笑,对诗歌的依恋也是推动他心理重建的根本因素,使他能够较快地从生活中不十分重大却足以让人倍感灰心和沮丧的打击中走出。在同劳拉约定好的打印诗歌的日子到来之际,意外发生了。在帕特森外出同劳拉看电影的这段时间里,两人留在家中的狗马文把记录帕特森诗作的笔记本撕咬成了碎片——这让帕特森和劳拉都很受伤。有趣的是,贾木许既“狠心”地宁愿毁掉帕特森最珍爱的事物也不愿让他迈出可能的通往功利性的一步,又体贴地给他安排了提供慰藉与疗愈的同道人。第二天,难过的帕特森独自外出散心,在他停下脚步呆坐在瀑布旁沉默时,一个拿着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作品的日本人坐到了他的身边——他也是一位诗人,如他所说,为了看看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所生活过的城市是怎样的,他来到了帕特森。两人随后聊起了诗歌,言谈分外投机。当日本人将要离开时,他送了帕特森一个空白笔记本作为礼物,并说出了“有时候空白页代表了更多的可能性”这句话作为临别赠言,完全照应到了刚刚发生在帕特森生活中的糟糕事情。他似乎看穿了帕特森独坐瀑布旁的忧郁,没走几步还回过头对着帕特森说了一声“啊哈”。在这位“天降神兵”般的日本诗人的感染下,帕特森也念了一声“啊哈”,之后打开本子并拿起了笔——这标志着他情绪的恢复,也暗示了其创作欲的重燃。在这里,日本诗人的助力这看似过于巧合的设计之所以不显得突兀,原因之一便是基于帕特森自己同诗歌长久、纯粹且深厚的依恋,这是不会那么轻易地由于偶然的外界变故而转移的。通过聆听日本诗人对其诗歌情结的讲述,帕特森再度发现并确认了自身。在影片结尾,帕特森再次从劳拉身边醒来,一如既往地准备开始新一周的工作。在那段小插曲后,他将继续回归自己规律而充实的生活,继续和爱人相爱,继续写诗。
结语
前文已经提到,帕特森的个人生活空间与一般人身处的加速推进的个人生活空间之间存在着区分。这一设定所指示出的贾木许对加速社会现实症候坚定而克制的排斥态度在延伸贾木许电影的“无聊”母题表达、指示电影思想内涵的同时,或许也体现了导演排除对于影像而言带有杂质与噪音属性可能的激进现实表态的影像美学坚持。此外,迥异于针对公交车司机帕特森工薪阶层的阶级身份同其文艺的生活习性间在社会惯例评价准则下存在的不对等与不匹配制造冲突性事件,以炮制更具有话题性的、引人感慨与议论的爆款叙事的做法,贾木许并不围绕存在于帕特森身上的二者间的错位设计突出的戏剧矛盾。除去借偶遇少女的无心之言道出帕特森作为一名公交司机却懂诗歌按照社会惯常认知确实不太寻常的荒谬却是事实的情况本身以外,贾木许并未立足于这一情况将之进一步“文化现象化”,走向对特定群体可能的动机可疑的、冒犯性的阶级凝视,而只是聚焦帕特森个人的生活形式本身,为加速时代普通人从个体出发克服精神世界的“无聊”,追寻理想生活状态提供范例。贾木许对加速社会现状的有限表态与达成“慢生活”的个案举例不无理想化成分,但事实是,如果个体被困在对强大的加速社会体制控制下的生活无能为力的思维中而无法摆脱,更多地只能是同自己过不去。《帕特森》让我们看到,相信主体的能动性并改变一种日常生活形式,我们每个人仍然具备从加速社会的无聊困境中超脱、突围的潜能。
注释:
①参考贾木许访谈自述转述。参见吉姆•贾木许.艾米•陶宾.常识——美国独立电影导演阿克西姆•吉姆•贾木许谈《帕特森》的常规艺术表现及拍摄《给我危险》的困难处理[J].赵悦婧译.世界电影,2017(4):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