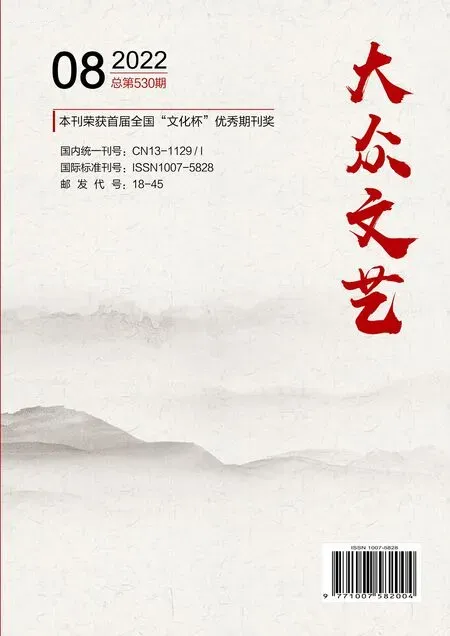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文化自觉的树立
——浅析中国民族民间舞当代创作的四条路径
林康馨
(北京舞蹈学院,北京 100081)
中国民族民间舞创作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走来,迎着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正昂首阔步走向新时代。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民族民间舞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舞蹈艺术,而成为一种具有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中国传统文化活体。当我们将目光从戴爱莲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和新秧歌运动慢慢追溯到当下,中国民族民间舞以其独有的文化性和艺术风格成为舞台表演和广场娱乐中喜闻乐见的舞蹈样式。当我们将目光进一步聚焦于舞台创作,我们会发现,从50年代的质朴与古拙,到80年代的自由与昂扬,从90年代的寻根与乡土气息,到20世纪初的时髦与雅化,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当代创作异彩纷呈,呈现出多元并行的局面。
当历史的指针转向2010年至2020这一时期,此时的中国民族民间舞创作正进行着四种不同路径的实践尝试:一是,在“非遗热”火爆大江南北时,2014年北京舞蹈学院推出《沉香》系列为民族民间舞创作带来新的发展可能;二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拉开文艺界“深扎”序幕;三是,十九大的召开强调现实题材创作,指引民族民间舞创作新的发展道路;四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动文旅产业地发展,“民族地方歌舞秀”不断兴起,进行商业化探索。虽然路径有所不同,但他们共同体现出民族的意识觉醒与文化自觉的树立,以新的方式延续民间舞传统,丰富民间舞内涵,成为解析当下审美旨趣的文化载体。
一、非遗视阈下的民间舞创作
昆曲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无疑是2001年中国文化界最激动人心的大事件之一,或许连申报团队都无法预料,一场非遗保护热潮自此慢慢席卷中华大地,成为当下最为热门的文化保护项目。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单“传统舞蹈”一项就有324个保护项目(截止2021年7月)。这无疑为民族民间舞创作提供了丰富而又多元的创作素材,也为艺术工作者和非遗传承人搭建有效的沟通桥梁。当非遗照进舞蹈界,“传统舞蹈”以丰富的文化性激起北京舞蹈学院民族民间舞系师生传承与保护各民族传统乐舞的自觉与责任感。在2014年,作为北京舞蹈学院建校60周年系列演出之一,《沉香》系列的第一台专场晚会一经推出便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注。这台晚会所展现的舞蹈形态,在地域上涵盖了黑龙江、青海、新疆、贵州、湖北、云南6个省区,在民族分布上囊括了汉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苗族、土家族、普米族、哈萨克族、彝族9个民族。从2014年至2019年,民族传统乐舞集《沉香》,一共推出了五个系列晚会,累计61支民族传统乐舞。《沉香》系列作品的出现,冲破人们对学院派民间舞以元素教学法为基础,以编导为中心的固有认知,带来了一种以传承为核心,淡化编创技法的新面貌。以一种久违的乡土之气,回归田间地头的怀抱,也一表对文化传承的决心与魄力。
纵然《沉香》系列只是一个教学实践项目,是民族传统舞蹈的教学模式探索,但它在象征着中国舞蹈风向标的舞台上演出,也再度引发关于传承与创作之间“度”的把握的探讨。从选材来看,《沉香》系列的素材都来源于非遗保护项目,与非遗传承人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它不同于以往学院派民间舞那般选取部分民族素材为编创元素再不断生发动作,而是要求在舞台上尽力呈现一种完整的,仪式化的,“原汁原味”的民俗舞蹈形态。这种关系的转变得益于传承人“话语权”的确立,曾经用审视的目光下田间“采风”的艺术工作者们,转变心态,虚心向传承人学习,对传统文化充满敬畏之心。从立意上看,它不突出编导个体意识,而是从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挖掘,牢牢把握民族精神、民族风格和民族特征,将中国大地上斑斓的民间舞蹈艺术呈现在舞台上,唤起深藏观众内心的民族意识。从编创角度看,它减掉大量调度、灯光舞美设计和编创技法的运用,力求最大限度“复刻”民间原初形态,很多作品甚至去掉音乐,采用演员边歌边舞的形式进行展现,这与当年《云南印象》的“原生态”追求有异曲同工之处,可谓民间舞人的又一次“文化寻根”。
让我们把目光锁定在近年来的“爆款IP”,无论是央视综艺《国家宝藏》的火爆还是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抑或是《唐宫夜宴》《只此青绿》的出圈,都预示着当下大众审美早已不满足于表面的浮华,而是追求更加精致的制作和更深厚的文化内涵。《沉香》系列之所以轰动,在于它与众多炫技、煽情的民族民间舞蹈作品相比显得太过与众不同,却又以一种形式上的极简与内容上的厚重,完美契合当下审美需要。由此可见,在民族意识再次觉醒的当代,要重视对文化价值的挖掘和延续,才能让中国民族民间舞教育和创作走向新时代。
二、“深扎”后的舞台民间舞创作
如果说《沉香》系列作品是从教学模式的探索出发,辐射到民族民间舞当代创作,那么中国舞蹈家协会于2015年开启的一系列“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下简称“深扎”)的舞蹈实践活动则是在民族意识觉醒下对舞台民间舞编创的一次主动尝试。“深扎”活动来源于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文艺创作方法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个座谈会引发广大文艺工作者对“深入生活”艺术创作路线的重新关注。基于这样的背景,王玫、田露、王舸、吕梓民等著名编导响应号召,在中国舞蹈家协会的组织下深入西藏、海南、河北、内蒙古等地区感受民族民间风情,全面了解当地民族舞蹈文化,在“扎根人民”中吸取养料,编创出《老雁》《转山》《独树》《玄音鼓舞》《我们看见了鸿雁》等舞蹈作品。这些作品因编导身份的不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质:以田露、袁媛为代表的民族民间舞人对于民族风格特征的坚守和以王枚、王舸为代表的职业编导对民族民间舞素材的择取。
第一类作品在保留地域和民族属性的同时体现对个体生命的思考。比如作品《老雁》作为非典型性双人舞,限定在一条长板凳上以及一束舞台定点光内完成表演,在有限的时空内诠释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孤寂之美。老人悠长、苍老的低吟声配合舞台黑、棕两大色调,迅速将观众带入寂寥的大草原,就这样一位老人开始了他的回忆之旅。一明一暗,一虚一实,两位舞者的身体在板凳上交错起伏,眼神直直向前望去却又无法相交,想要尽力去拥抱却什么也抓不到。他们或许拥有过比翼双飞的美好过去,却终究落入“更与何人说”的无力之境。当装饰达到极简,当语汇极度浓缩,舞者脸上的表情跃然成为一种有力的动作表达,摆脱传统舞台龇牙咧嘴的夸张表情,带来一种极具戏剧张力的镜头感,淡淡地陈说着过去的故事。作品选取蒙古族“柔臂”动作,在限定的条件内,捕捉到了人性,触及了真情,巧妙将原有的限定变成了表现作品主题的助力,在不破坏民族属性的基调上,探索对个体生命的敬畏和对族群认同的拿捏。如果说第一类作品还保留着对民族传统的坚守,那么第二类作品在编创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了。它更多是以“为我所用”的心态进行创作。同样以蒙古族舞蹈《我们看见了鸿雁》为例,作品直接将贾作光先生作为“IP”进行打造,运用陌生化的处理方式,将“老的”和“新的”区别开来,突出当下和过去的对话。蒙古族“碎抖肩”“柔臂”等动作本身就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有了传承、保护的含义。当笔者看完该作品,油然而生一种敬畏、责任、传承之心,不仅看到传承的血脉正慢慢流淌在一代代学子的身上,也看到文艺工作者的文化自觉正在慢慢树立。
正如我们常说,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在广大文艺工作者深扎的实践中,有太多精彩故事等待着文艺工作者去发掘、去绽放、去讴歌。从根本上说,“深扎”不是一项政治任务,而是一种艺术态度。这个艺术态度里包含内容选择、情感方式和技术手法。在进行民族民间舞蹈编创之时,不要执着于讲多么复杂的故事,抒发多么大的壮志,要深入体会和捕捉人生百态,探寻那些真实、平凡却又触动人的东西。唯有沉下心去,紧跟时代的足迹,去聆听追梦者的心声,才能把中国故事讲得更加精彩。
三、现实题材影响下的当代创作
舞蹈界轰轰烈烈的“深扎”实践,无形中影响了民族民间舞当代创作的另一条路径——现实题材在民间舞领域的探索。所谓现实题材是指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它往往需要从现实生活和社会变革中选取素材,与历史题材是两个相对的题材概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于是,我们欣喜地发现在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2019年)比赛上,参与终评的51个作品里有10个现实题材作品,现实题材的民族民间舞蹈创作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民族民间舞本身就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它创作于民间,流传于民间,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征。民间舞蹈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直接反映了人民的生活、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这与现实题材创作要义相似,也为现实题材创作与民族民间舞融合提供了更多的契合点和更大的可能性。脱贫攻坚、抗击疫情、乡村支教等等,回顾党的百年风华,有太多太多值得歌颂,值得挖掘的人物、事迹、情怀,有太多太多精神和担当有待表现。
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舞台化创作不能摆脱民族民间舞蹈活态传承,更不能缺失民族意识,这里的“民族意识”即包括族群、地区更包括民族国家和民族大众。新时代为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艺术家要敏锐发现中国人民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只有立足当下,立足人民才能更好地“为我所用”,从而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艺术、新文化。在笔者看来,一方面,在舞蹈语汇上,要研究如何运用那些或来自生活,或来自传统民间舞的语汇,创作独一无二的形象;另一方面,在编创上,在艺术手段上的运用要有巧思,摆脱千篇一律的重复和挪用;最重要的是,从选材上,要聆听时代的呼唤,抓住当代生活、当代审美,挖掘人性共通的共情点和时代特质,与当代活生生的人产生情感共鸣,才能将其外化为舞台上动人心弦的作品。
四、乡村振兴战略下山水实景演出的兴起
2004年,《印象刘三姐》在桂林阳朔公演,虽然在前期营销惨淡,但最终凭借“7000万元的投入,8亿元的产出”一炮而红,拉开了中国“山水狂想式”实景演出序幕。此后,以“印象”系列为代表的实景演出在2010年后呈现井喷之态:云南丽江出品《印象丽江》、杭州西湖出品《印象西湖》、福建武夷山出品《印象大红袍》。在尝到实景演出“红利”之后,各地政府纷纷出手,山水实景演出多点开花,杭州宋城《宋城千古情》、陕西西安的《长恨歌》、山东威海《华夏传奇》、贵州省《西江盛典》……中国民间艺术走了一条与美国好莱坞歌舞片以及欧洲踢踏舞秀完全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化道路。以大自然为布景,配上豪华的舞美装置,这些山水实景演出不仅带给观众视觉美感,还能生动反映地方的文化和民俗,带来了沉浸式文化体验和感受,给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效益和文化自信,也开辟了中国民族民间舞商业化道路的新探索。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到2017年,我国旅游演艺观众人次从2789万人次增加到6821万人次,增长了145%;旅游演艺票房收入从22.6亿元增长到51.5亿元,增长了128%。在地域风格浓厚的地区推进山水实景演出,可以成为辅助脱贫攻坚的手段,给村民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提高地方政府税收。然而,在繁荣的背后个别实景演出惨淡收尾的现象也引发新的忧思。随着越来越多山水实景演出的诞生,大多数作品都流于“大晚会”浮华娱乐之风,大凡承载的是以原生态“聚名”、用原生态“说事”的现象和案例。当艺术和资本碰撞,在资本的逐利性带动下,民族民间舞市场化容易进行复制山寨,艺术性消失的同时游客也会减少,商业化盈利固然就难以维系,这就会陷入文化产业发展的恶性循环,因此不能简单理解为“娱乐化”“旅游舞蹈”和景区舞蹈。正如《印象刘三姐》经过5年零5个月的打磨,由中外著名艺术家参与创作,修改方案109次最终上演。“把最好的文化放在最美丽的山水之间去展现”,山水实景演出中的民族民间舞创作要挖掘地方特色,讲的是这个地方的故事,用的是这个地方的山水,这个地方的人,要以民族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去追寻一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价值,表现出潜藏在游客心中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家园意识。不忘初心,方能长盛不衰。
结语
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促使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华民族”用来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开始逐渐位全国各族人民所接受,并得到了广泛使用。迈克尔•弗里登曾指出“民族主义只有在短暂的时段内变得极为重要,即在民族建构、征服、外部威胁、领土争议、或内部受到敌对族群或文化群体的主宰等危机时,民族主义才显得极为重要。”忆往昔峥嵘岁月,今天的中华民族正以一派欣欣向荣的面貌,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赶考之路。面对新的发展时期,中国面临的社会局势是纷繁多变的。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文化自觉的树立便在无形之中弥漫开来。潜在于普通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感情是巨大的,而民族信仰、民族认同、民族文化等就成为民族民间舞蹈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面对传统的坚守和时代的发展之时,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民族民间舞在新时代呈现出多元的发展路径,中国民族民间舞正积极参与当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重构,积极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形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续写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