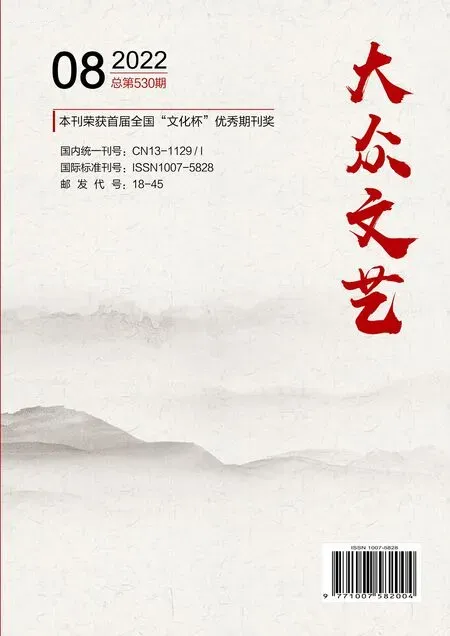南朝石刻的写意性特征
刘松
(中国艺术研究院雕塑院,北京 100029)
具体而言,中国古代雕塑未能如绘画、书法般发展出统一而完善的艺术体系。先秦三代到秦汉,乃至魏晋、隋唐、明清,中国的雕塑可以说四面开花,在材质上出现了陶质、玉质、铜质、石质等多种样式,在功能上分为实用性雕塑、纪念性雕塑、宗教性雕塑等,在思想上又往往因地域、民族等因素,差异性极强,如三星堆、中山国铜像,红山、良渚玉器,以及分布在山东、南京、四川等地的石刻艺术,可谓形态多样,趣味横生,换而言之,虽然中国古代雕塑体系不够完善,但于历史及社会中反映的丰富性及广泛性的背后又具有一定的统一性——雕塑精神。
在美学领域,自顾恺之“传神论”问世后,“传神写照”成为中国艺术最重要的美学范畴之一。鲁迅就曾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因此,所谓的“传神”一定不仅仅在绘画中,更不唯顾恺之独有,而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审美思潮。至少就其后的南朝短暂各个时代而言,它们之间的连贯性、继承性更胜于其他历史阶段。其中,六朝石刻艺术可以为我们洞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精神提供一个历史的、有效的通道。
一、南朝石刻的历史维度
这里讨论的南朝石刻,主要是指分布在今天南京、丹阳等一带的南朝石刻雕像。具体而言,尤指陵墓前的石兽雕像。南朝帝王等陵墓前往往由石兽、石碑、神道石柱等组成地上建筑,它们既是陵墓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个国家政权、思想的象征。被称为“六朝古都”的南京,经历了孙吴、东晋、(刘)宋、(萧)齐、(萧)梁和陈代六代王朝,在此期间及之后,留下了大量记载和传颂这段历史的诗词歌赋。据《南齐书•豫章文献王嶷传》记载,南朝宋文帝长宁陵:“麒麟及阕,形势甚巧,宋孝武(帝)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
由此可以粗略得知,南朝陵墓前安置麒麟等石刻雕像始于(刘)宋。而且还透露,这种陵墓雕像的样式来源于河南襄阳。如果我们把河南洛阳等地出土的辟邪等雕像与现存南京的最早一处麒麟雕像相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关系。如1992年出土于孟津先老城乡油坊街村和洛阳孙旗屯村的辟邪,它们在题材、造型、形式等方面都与南京现存的南朝石刻雕像存在极高的相似度。更重要的是,(刘)宋的这一石刻“传统”得到了(萧)齐、(萧)梁和陈代的继承和发展。
(萧)齐与(刘)宋一样,这些石刻雕像只限于帝王陵,这些墓主有的是生前为帝,有的死后被尊称为帝。也即是说,有过或有着帝王身份的陵墓前往往会有如此罕见的陵墓建造。到了(萧)梁,不仅数量上超过了前朝,而且使用范围得到扩大。除了帝王墓,一些诸侯墓也出现了类似前朝和当朝帝王墓的形制。从现存(萧)梁陵墓石刻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的变化。可惜的是,陈代虽然继之,却没有能走向更大的繁荣。而且,陈代之的这一石刻艺术“传统”,甚至很快在中国大地上逐渐消退。在林树中看来,“陈代石刻已是南朝的尾声”。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陈寅恪的历史文化观中找到缘由。他认为,“陈代是由北来的下等阶级(经土断后亦列为南人)与南方土著掌握政权的时代”。因此,他把南朝分为东晋,宋、齐、梁以及陈三个阶段。由此可以揣测,陈代没能成功地继承前朝的石刻艺术大观,可能是由于存在文化上的隔阂,而后来地隋朝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尤其是推崇朴素的价值观,使得南朝时期追求宏达、繁复的石刻雕像日渐边缘化,最终走下历史舞台。
因此,如果从历史的维度看南朝石刻,南朝石刻艺术有两个文化特征:
其一是有始有终。从相关文献到现存实物可知,南京地区的南朝石刻有它的历史性,尤其是它与河南承接关系,这一观点得到李零的支持。他认为河南洛阳以及南阳地区出土的汉代天禄、辟邪雕像“是魏晋南北朝这类石刻的前身(形体不如后来巨大,但基本特征相同)。魏晋时期,这类石刻未见,南北朝时期才重新流行(但北朝以后衰落)。北朝所刻不精,制作精美者多是南朝的作品(集中于南京、丹徒一带)。它们的共同源头还是河南”。南朝石刻的来源,不仅在形式上直接继承了河南石刻艺术,推而广之,它的历史维度可以延伸到中国整个图像史,李零的相关文章为我们提供了相对系统的论述。但是,从历史角度看,南朝石刻形式如何承接到南京尚需要更为详细的历史考证。这一疑难应该与它的“终结”同样值得思考,即盛极一时的艺术形式为何在极短的时间之后又潜藏到中国历史文化中?这就是它的第二个特点:昙花一现。
南朝石刻的“昙花一现”在历史、空间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载。在南朝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不仅政权、社会、版图出现了剧烈变化,这一变化也显现在它的石刻艺术发展上。(刘)宋到陈代,南朝石刻艺术的有效发展时间要更短。从另一层面来说,虽然石兽雕塑“传统”没有得到再大发展,但无可置疑,正是在如此短暂和动乱的时代环境中它达到了历史和艺术高度。仅就此而言,南朝石刻的“昙花一现”其实没有消失。
二、传神写意正在文化中
南朝石刻艺术给人的最初感受,正是来自它所散发出来的精神特征。金琦认为“六朝石刻艺术作品,是无声的音乐,无论是一般石刻还是陵墓石刻,都是以丰富多彩的形象和永恒的生命力,迷恋着中外专家学者”。金琦用带有散文性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六朝石刻艺术的看法。而且,如果我们不论石刻艺术的历史性,甚至可以断言金琦对石刻艺术的大部分感受及观点正是来自南京的六朝石刻艺术。
南朝的石刻艺术通过高超的技艺在刚与柔、静与动、粗与细的冲突之间达到近乎完美的视觉境界,尤显作者的创作魄力。还有就是南朝石刻的传神性。南朝石刻艺术的传神性,与南京城市以及石刻的历史性尤为相关。也就是说,如果前两个方面还是从艺术的表现的角度来看,那么在此就有必要将它还原到原境(巫鸿语)中。只有还原才能体现出美学背后的人文神韵。
这种必要性在经历了多次实地考察之后得到了确切验证。正如喜仁龙在评价中国佛教雕塑艺术是所言,“世人所以崇拜这些雕塑,是因为与它们代表着自然界与人世间具有指引作用的强大力量。这些造像不是某个艺术家创造的,它们出自特定的宗教传统,而非艺术传统,因此不会为了迎合某些审美偏好而任意改变”。虽然喜仁龙表述的对象是佛教艺术,但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这一观点也适用于南朝时期的石刻艺术;不仅因为时间上具有一定的重叠,更值得关注的是南朝石刻艺术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性和社会性。因此,喜仁龙所用的“宗教传统”就显示出了同样作为精神载体的陵墓雕像的价值和内涵,我们甚至可以用“石刻传统”来指称。那么,在山东嘉祥武梁祠有关石狮雕像和河南洛阳辟邪铭文(“缑氏蒿长成奴作”)上的作者信息就显得较为次要,因为个人的文化观和审美趣味必然服从于时代和这个大的文化传统。
因此,不管是艺术、文学的传统,还是生活、风俗的传统,都是文化在历史中的外在表现。南朝石刻艺术体现了艺术图式和题材上的发展传统,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比于西方的写实主义雕塑、绘画等艺术,中国艺术则更加注重写意精神的表达。吴为山就将“传统”形象地比喻为文化的“脉搏”,他说:“传统是源流,它在承传嬗变过程中不断拓展原本的系统;美术是人类精神之产品,其发展轨迹正反映了新与旧、情与理、美与丑,以及保守与进步的交锋”。南朝石刻艺术的出现、发展与消隐,恰可称之为中国文化的一次“脉搏”的跳动,它的“永恒的生命力”(金琦语)不在于某一次无限的高涨或低落,而在于起伏的过程,是“修正”“创新”“交锋”的辩证的发展轨迹。
既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显示,南朝石刻艺术中的麒麟、辟邪、天禄等都与狮子形象密切相关。在李零的研究中,认为狮子在艺术中的出现开始于东汉,是随着佛教艺术传入中国的。在佛教的发展中,狮子的形象逐渐融入了中国文化中,并成为民间传说“龙生九子”之一,可见它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到了南朝陈代,麒麟等石刻艺术的造型已经开始走向了写实道路,这一点到了隋唐时期更加明显。由此可以看出,石刻艺术中形象首先来源于现实中的狮子形象,在加入神秘化的文化思想之后,突出了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其次,以石象生,则意在突出艺术之外石刻雕像的社会功能。这种社会功能,必然要与中国文化产生相一致。具体来说,就是要与中国写意雕塑精神进行对话。
因此,写意雕塑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写意不是为了写意而写意,更不是为了追求表现颤动、诗意、变形,而是要融化、渗透、弘扬精神。有了精神,作品才有了构架,才有了灵魂及内在的‘气’,才有了那一目了然而又意蕴无穷的艺术形式”。因此,不管是神化之后的写意,还是走向真实之后的写意,其最终指向都是生命,一方面表现物象之生命精神,另一方面是要突显出文化的生命精神。
注释:
①林树中编著.南朝陵墓雕刻[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8月,第52页.
②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129页.
③李零 著.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6月,第106页.
④见金琦在全国古都学会第二届年会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六朝石刻之我见》,1984年11月,第1页.
⑤[瑞典] 喜仁龙著.《5-14世纪中国雕塑》.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第2页.
⑥吴为山著.《雕塑的诗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279页.
⑦吴为山著.《雕塑的诗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