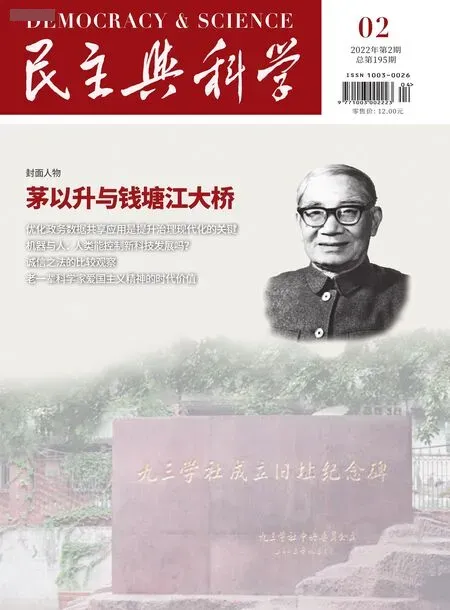老一辈科学家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价值
李婧铢 董贵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要大力弘扬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主义精神。[1]以吴文俊、吴良镛等35位科学家为代表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简称“最高奖获奖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既具有独特的典型性,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作为一种优秀的民族基因,爱国主义精神穿越时空,在当代以及未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价值。
老一辈科学家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基因传承的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2]老一辈科学家特别是最高奖获奖者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基因传承的典型代表。
我国历代知识分子都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内圣外王”的士大夫情结和“以身许国”的救世情怀伴随他们的人生追求,他们自觉地将个人追求和家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司马迁“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无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高贵的人格和崇高的价值追求已内化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成为支撑中华民族不断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财富,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最高奖获奖者作为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大多出生成长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求学的青少年时期,亲历外敌入侵、颠沛流离带来的痛苦。2019年最高奖获奖者、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小学毕业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辍学半年后,与长兄背着书籍行囊,步行跋涉,抵达了因日寇侵略而迁入揭西山区的聿怀中学。由于战事吃紧,聿怀中学很难保障正常学习,黄旭华不得不踏上了去往桂林的求学之路。1941年夏,黄旭华经兴宁、越韶关、奔坪石、掠湘南,经过整整两个月的晓行夜宿,终于抵达桂林,考入桂林中学。1944年,日寇的铁蹄逼近桂林,黄旭华在匆匆结束高中学习后,再度开启了求学之旅。出广西、越贵州,走走停停、历经艰险,两个月后终抵达重庆,但错过了各大学的招考,只好再过一年后,才进入了国立交通大学造船专业学习。[3]严酷的现实和国家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使最高奖获奖者们切身感受到,没有国,哪有家?“学以致用”“救国图存”成了那个时期青年学生思想的主旋律。
2011年最高奖获奖者、中国粒子加速器之父谢家麟,当年在燕京大学就读,每次从海淀往返城里必经日本兵的岗哨,日本兵荷枪实弹对行人搜身、殴打等行为让他倍感屈辱。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日本军队占领燕京大学。在物理系只差半年就要毕业的谢家麟不愿在日本统治下的燕京大学读书,秉持着“航空救国”的思想选择了在乐山复校的武汉大学航空系从头念起。[4]
在战乱频仍的时代背景下,从中学到大学都纷纷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肩负起爱国主义教育的使命。学校长期开展传统爱国思想教育,实行“读书救国”办学理念,激励最高奖获奖者中的一批青年人,最后成长为传承和赓续中华民族精神基因中最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代表性科学家。
老一辈科学家爱国主义精神是爱国奉献与人生价值的高度统一
最高奖获奖者群体历经了当时国家积弱积贫、外敌入侵、民不聊生的痛苦,深深地明白一个国家独立富强的可贵,把“富国强民”融入个人的发展中,并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1950年前后,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海外学人的“归国潮”,最高奖获奖者中的一批科学家义无反顾回到祖国。他们不顾危险,冲破种种阻力,抛弃发达国家重金与富裕生活的诱惑,为的就是报效祖国。首届最高奖获奖者、中国拓扑学奠基人吴文俊,谈到回国的原因时说:“每个人都有爱国之心,我们这些留洋的,盼望着学成回国为祖国做些事。”[5] 1951年回国后,吴文俊一心扑在科研和培养人才事业上,在数学众多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是新中国数学发展的重要开拓者。2013年最高奖获奖者、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程开甲曾说,在国外继续待下去,學术上也许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没有幸福感,只有把自己所学与祖国紧密联系才是最大的幸福。
在新中国建设中,老一辈科学家自觉自愿把祖国的需要、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最高奖获奖者群体把国家需要作为强大的科研动力,把他们一生的精力无私奉献给科技兴国事业。在“两弹一星”研制工作中,2009、2013、2014年最高奖获奖者孙家栋、程开甲、于敏等一批科学家长年隐姓埋名,甚至在学术界销声匿迹;2008年最高奖获奖者、中国稀土之父徐光宪为了适应祖国的需要,从量子化学、络合物化学到核燃料萃取方向再到稀土化学等,横跨多个领域,为了国家需求多次转变研究方向;2017年最高奖获奖者王泽山带着“强军兴国”的使命,选择火炸药领域作为主攻方向,常常在戈壁滩现场“风沙拌饭”,用“一甲子”的时间书写了我国火炸药实力进入世界前列的传奇。
老一辈科学家们,有的在戈壁滩上隐姓埋名,有的在漫漫长夜苦心演算或建模,有的在实验基地熬红双眼,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凝聚形成了“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爱国主义精神的丰碑,在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进程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老一辈科学家以“小我为大我,为大我忘小我”的胸怀和实际作为,深刻诠释了爱国主义精神,是爱国奉献和人生价值的高度统一。
老一辈科学家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与作用
第一,弘扬老一辈科学家爱国主义精神,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6]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发展,需要持续的自主科技创新,更需要持续的爱国主义精神滋养和武装我们新一代的科学家队伍。纵观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只有那些有民族气节、有爱国主义精神、有坚定信念支撑的科学家才能走得正、走得远,才能攻克一个个科技难关、干成一件件大事、完成一项项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老一辈科学家,面对国内科研“一穷二白”、国外技术严密封锁的困境,将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转化为独立自主的创新勇气,转换为探求新发现新发明的持久动力,立足国情,靠智慧和毅力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科技发展之路。
当前,我国还有许多基础领域、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工艺等还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高端芯片、农作物种子等在内的一些“卡脖子”难题依然阻挠和困扰着我们的发展。新一代科技工作者要全面继承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肯在难度大、周期长的基础研究及应用领域上下功夫,“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苦功夫”,勇闯科学技术“无人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第二,以老一辈科学家为榜样标杆,树立青少年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当今,在多元价值文化影响下,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渐渐蔓延到学术界、科技界和其他领域。一些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出现严重偏差,“精致的利己主义”等价值观影响着他们的成长,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和现代化强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7]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具象性、生动性、典型性和代表性,以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为范例,在全体公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可以有效地塑造我们民族崇高的价值观。2014年最高奖获奖者、中国氢弹之父于敏曾说:“青年人选择职业和专业方向,首先要选择国家急需的。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都与国家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会有所作为,才会是一个无愧于祖国和民族的人。”[8]发扬老一辈科学家将“小我”融入“大我”的奉献精神,以老一辈科学家爱国主义言行为榜样,将国家长期重大需求、迫切需要与个人专长和志趣相统一,将爱国奉献、人民利益与个人价值和利益相统一,建树全民正确的社会主义人生价值观。
第三,发挥老一辈科学家精神引领作用,进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
老一辈科学家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熱爱祖国忠诚国家的感情、思想、信念和行为的综合。培养受教育者特别是青少年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和为国家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的精神,应该是各行各业开展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由于金钱至上、享受主义和娱乐主义的流行,再加上一些网络自媒体的炒作发酵,社会上崇拜影星、歌星、球星和成功商人的风气远远超过了对科学家的敬慕,这种现象在一些青少年中尤其普遍。产生这种现象,除了社会转型的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主流媒体宣传的不到位,在文化教育界的普及性差,而对老一辈科学家爱国主义事迹的宣传与普及常流于表面,特别是未能对青少年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老一辈科学家爱国主义精神的言行是那样的生动鲜活和可歌可泣,这种言行本身就是活典范,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特别是网络多媒体等新颖的宣传形式,才会更加有效地发挥老一辈科学家爱国主义精神对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的引领作用和示范作用。
注释:
[1]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09-12(002)。
[2]张启华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会议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594页。
[3]王艳明:《誓言无声铸重器 黄旭华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30-47页。
[4]谢家麟:《没有终点的旅程 谢家麟自传》,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4页。
[5]黄祖宾,吴文俊:《走近吴文俊院士——科学史家访谈录之四》,《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4期。
[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4页。
[8]解放军总装备部政治部编:《两弹一星——共和国丰碑》,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页。
(李婧铢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董贵成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科学社团资料的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ZDA214〕部分成果,本研究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专项资助)
责任编辑:尚国敏
——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