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读常新的“轻”与“重”
杨苗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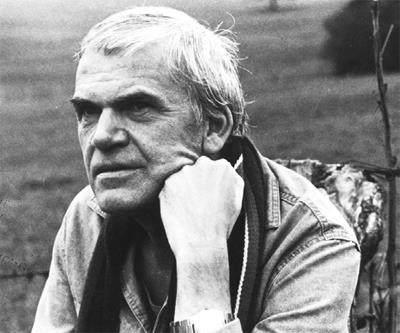
米兰·昆德拉
时隔二十多年后再去读米兰·昆德拉这本公认的经典名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我惊讶地发现,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除了对几个人物的名字和那个孰轻孰重的问题还有点印象,具体的情节完全模糊。也许当年根本就没能完全理解这本书。重读一遍,会在记忆深处泛起什么样的涟漪?
这本出版于一九八四年的小说,通过两对人物的情爱故事,探讨了“轻与重”“空虚与意义”“灵与肉”“真实与媚俗”等一系列哲学问题。我甚至觉得,米兰·昆德拉就是思想先行,他将小说定义为“通过虚构人物的媒介对存在的思考”,他创造出来的人物“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就像艾略特用《米德尔马契》探讨人与社会的反抗或迎合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罪与罚》隐喻人与宗教、理性与虚无的关系一样,《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以昆德拉的风格,将爱情故事、政治评论、美学探索和对人类生存悖论的沉思结合在一起,引发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人类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存在意义、人类命运和欲望的挑衅性冥想。
之所以说它具有挑衅性,是因为今天的社会似乎比五十多年前更加撕裂,存在的意义和人类的欲望更加强烈也更加无序,如何在这种日益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寻求出路,这部解构了人类存在的基本辩证法:爱与性、真诚与背叛、艺术与媚俗,还有人生意义的轻与重的小说,应该是一面镜子,值得我们认真凝视。
轻与重:托马斯与特丽莎
托马斯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捷克医生,在与妻子离婚之后,他变得放荡不羁。他认为性爱双方都不要有感情投入。
特丽莎是一个小镇姑娘,生活在一个粗鄙的家庭,从小就时常被母亲羞辱,她想要逃离这个环境,对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与理想主义的爱情十分向往,所以她的腋下总是夹着一本书,因为在她看来,这本书可以把她跟周遭粗俗的世界区别开来。
特丽莎与托马斯的第一次相遇是在她所在小镇旅馆的餐厅里,特丽莎是这家餐厅的服务生。由于托马斯与镇上的酒鬼有完全不同的气质,加上他的桌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对于极想摆脱粗俗的特丽莎来说,书本的隐喻似乎在昭示着她所向往的世界,具有无与伦比的诱惑力。之后托马斯便和特丽莎开始了约会。最初,托马斯只是把特丽莎当成他众多情人中的一个,但是后来,他觉得自己爱上了特丽莎。特丽莎的出现,让他感受到了“爱”的存在。当特丽莎在睡梦中依然紧紧握住托马斯的手时,他的灵魂深处出现了震荡—这个女人与他以往交往的女人不一样,就像一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篮里顺水漂来的孩子,纯洁、天真、完整,沒有受到媚俗世界的玷污,就像上帝的使者一样,要帮助托马斯一起完成灵魂的救赎。至此之后,托马斯开始被爱套牢,一步步丧失自己之前订下的原则与生活方式。米兰·昆德拉这样评论:“人脑中看样子具有一块我们可以称为诗情记忆的区域。那里记下来诱人而动人的一切,使我们的生命具有美感。从他遇到特丽莎起,再没有女人有权利在他大脑的那一区域中留下一丝印痕。”特丽莎就是那个诗意的存在,既然已经出现,便再也抹杀不掉。尽管如此,在这段关系中,特丽莎一直都是弱势的一方,她深爱着托马斯,却又无法改变他的性观念,在这种沉重的精神负担下,她感到非常痛苦。为了减轻她的痛苦,托马斯与她结了婚,并送给她一条叫卡列宁的狗。然而,婚后的托马斯仍然无法保持忠诚,他的一次次出轨让特蕾莎的痛苦变得越来越沉重,托马斯自己也陷入了一种心理怪圈,每次一出门去见情妇,马上又因为内疚而失去了欲望;可只要一天不见情人,他的心里又会痒痒得立即打电话约会。因为托马斯在婚后仍然情人不断,每次回家,头发上都能闻到其他女人的味道。这使得特丽莎十分忌妒与不安。由于局势的恶化,也出于不让特丽莎再如此焦躁不安,他们搬出了捷克,逃到了瑞士苏黎世。但是在苏黎世时,特丽莎依然孤独与痛苦,于是他们又先后回到了布拉格。在短暂的小别胜新婚之后,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托马斯回去之后开始任职于原本的医院,但由于之前发表过对当局不利的言论,又拒绝签署撤回声明,最后沦为一名玻璃擦洗工。
两人都感觉到身心疲惫。终于有一天,他们达成了共识,移居乡下,这是他们逃避现实的唯一途径。在那里,托马斯当了一名卡车司机,特丽莎当了一名牧牛女。他们从此远离了过去的一切,过上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然而,当幸福的牧歌刚刚奏响没多久,他们便走向了生命的最后一站。在一次回家的途中,托马斯的卡车因为刹车失灵而坠入深谷,他们在车祸中不幸身亡。意外比明天更早到来了。
托马斯和特丽莎分别是作者笔下“轻”和“重”的化身。昆德拉为什么会认为生命或者存在的本质是“轻”呢? 这要从尼采的“永恒回归”说起。假设我们做决策的每一个瞬间,都会无限次的重复,那我们便可以尝试不同的方向,把所有可能的选择都试过一遍,最后找出对我们最好的那个未来。但是由于这样的永恒回归是不存在的,任何决策的瞬间都只会发生一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选择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的生命只能是“轻”,正如德国谚语所说“偶然只发生一次的事,算不得数”。
与之相对,“重”是我们对于意义的追求,毕竟对于生命来说,有意义的东西必定是有重量的,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可以说,意义本身所带来的感受便是沉重。这便构成了本书的第一个主题:生命因为永恒回归的不存在,所以是轻的;但是由于生命又需要意义,才能对抗“轻”所带来的失重感,所以又同时是沉重而难以承受的,最后生命便成了“不能承受之轻”。
尽管我们的生命依然可以在它辉煌灿烂的轻盈之中展现出来,可“重”真的是残酷?而“轻”真的是美丽?其实,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最激越的生命实现的形象。相反的,完全没有负担会让人的存在变得比空气还轻,远离地面,一切动作都自由自在,却又无足轻重。
所以,无论是“重”还是“轻”,都无法让人满意,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生命的困境之中。当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你会发现,昆德拉所提出的一系列哲理性问题都是无法解答的问题,他的目的可能就是要让读者在不能把握的生存困境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
虚无与意义:萨宾娜和弗兰茨
萨宾娜是一位画家,她本身是反对“媚俗”的代表。她和托马斯是情人关系,她很喜欢托马斯那毫不媚俗的态度。由于祖国捷克被入侵,萨宾娜搬到了瑞士,在那里,她认识了大学教授弗兰茨。弗兰茨生活在安逸太平的瑞士,对于捷克那些激情式的苦难与爱国主义充满着向往,萨宾娜的到来刚好填满了他心灵的这个空缺。他对萨宾娜的爱充满着神圣感,夹杂某种革命情怀;虽然他跟萨宾娜也是情人关系,但是他跟托马斯完全不同,他对萨宾娜近乎顺从,简直就是把她当成捷克人民所受的苦难孕育出来的女神般来崇拜,但这恰恰让厌恶媚俗的萨宾娜感到不小的负担。
在萨宾娜察觉到弗兰茨会向她求婚时,她果断地消失了。萨宾娜的“轻”是不停地背叛,背叛父母、背叛丈夫、背叛故国、背叛弗兰茨,她同托马斯一样轻视世俗传统的价值观,将媚俗看作一生中最大的敌人。但她并不清楚自己的背叛究竟有什么目的,她也未想过要给自己的举动寻找意义。背叛时她激动不已,背叛后却陷入忧伤。因此,萨宾娜对责任、承诺、媚俗的拒绝使她走进了虚无主义的胡同:“她的背叛让她充满了兴奋和快乐,因为他们为背叛的冒险开辟了新的道路。但是,如果这条路走到尽头了呢?一个人可以背叛自己的国家、父母、丈夫、爱,当国家、父母、丈夫、爱都消失了—还剩下什么可以背叛?”萨宾娜看似一生没有压力、没有责任,甚至让人略有些羡慕,其实她是不幸的,甚至是可怜的。她的悲剧不是因为“重”,而是在于“轻”。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弗兰茨跟特丽莎一样,是有重量和责任感的人物,他深深地被萨宾娜吸引。在萨宾娜看来,他聪明、懂她的画、善良、正直、英俊。弗兰茨有着安稳的生活和自己的小家庭,他生命中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就是被一位哲学家写信嘲讽;但弗兰茨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想要追寻历史伟大进军的脚步,追求轰轰烈烈的冒险人生,结识萨宾娜使他得以背叛自己原来的生活。弗兰茨的“重”是对历史的崇尚,对内心政治理想的固守。在他决定离开妻子与萨宾娜在一起的时候,却发现萨宾娜不辞而别。但这并没有阻挡弗兰茨对意义的狂热追求,他认为萨宾娜曾经像女神般的存在,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他开始陷入了“自己感动自己”的模式,他觉得应该为他心目中的女神,为这个苦难的世界做点什么,所以他像许多左派分子一样,志愿去了那个时候被苏联控制的越南。最后他因被一帮柬埔寨的土匪打伤,送回国医治无效而死亡。弗兰茨死后,他“终于属于了他的妻子”。昆德拉用这种令人窒息的叙述,既否定了萨宾娜的虚无,也反讽了弗兰茨的意义。
相比之下,小说以托马斯和特丽莎相互和解而结束。托马斯承认:他在乡下忠于特丽莎的生活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昆德拉以相互承认和接受对方的吸引力作为结尾,让轻松穿越重量;但又以他们的悲剧,进一步揭示轻与重、虚无与意义的相生相克:苦难的意思是,我们走到最后了;幸福的含义是,我们在一起。苦难是形式,幸福是内容。快乐填满了苦难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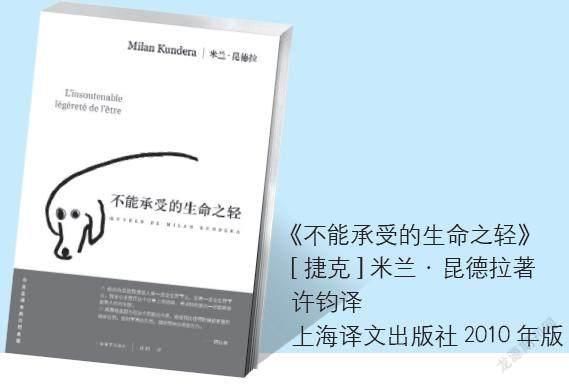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所有的情节都看似偶然,却又是必然发生的。在第一章第一节中,作者就评价生命:“即使它是残酷、美丽或是绚烂的,这份残酷、美丽和绚烂也都没有任何意义。”托马斯认为,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没有活过一样,因为我们无法判断抉择是好或坏,一切都是初次经历。我们既没有足够的经验,也没有客观的角度去评价究竟什么是客观价值。托马斯的想法颇具虚无主义的真谛。在这部作品中,昆德拉常常从叙述背景中跳出来,夹叙夹议,但我们依然觉得这个文本非常立体,它有足够的丰富性和让人思考的空间。它的情节无足轻重,只是哲理表达的一种辅助工具。我们甚至并不关注故事本身的结局,而是想找到故事下面那个宝藏—生命哲学的意义。
常读常新:生命的本质
二十多岁和五十多岁读同一本书,感受真是不同。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当然觉得生命应该为有价值的东西而付出,而承担。但什么是有价值的,不同的时代会有各种不同的回答。书中所言的生命之轻,是在认识到生命相关的一切本身的无意义之后,对世俗生活采取的一种超然态度。生命之重,则是从当下世俗道德与价值观的角度出发,对社会普遍认知中的意义的固守。萨宾娜代表了生命之轻式的人物,特丽莎和弗兰茨代表了生命之重式的人物,托马斯则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那一端,逐渐走向世俗意义的爱与责任,在田园牧歌的归宿中,回到了生命沉重的状态。
年轻时的阅读是将价值的天平放在重的一方,以为世俗意义的责任应当固守。并为那轻的一端留下轻视的目光。时过境迁,今天再读,感受特别深的是书中这一句: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同前世相比,也不能将它在来世修正。小说从“一次不算数,一次就是从来没有。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没有活过一样”这个德国谚语出发,通过小说的几个人物,指向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双重性。在昆德拉的作品里,爱情、信仰、政治、友谊……种种美好的所在,全都是靠不住的。他曾经说过:“人所拥有的、惟一可以确定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智慧。”(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这种不确定性,本该包括好与坏、积极与消极、希望与绝望或是多种状态的复合。然而,读昆德拉的小说,你总会觉得叙事者最后总是“很确定”地告诉你,没什么是值得信赖的。昆德拉意义上的“不确定的智慧”,是跟怀疑与解构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依然相信他的内心是有某种意义的确定性的,比如,书的最后,托马斯做出了让步,同特丽莎一起移居乡下,颇有些长相厮守的意味。两个人终于确信了自己的爱情,达到了一种牧歌式的幸福。比如,特丽莎、托马斯与卡列宁之间的爱,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爱是最美好的,它完全出于自愿,不依赖于荷尔蒙,不依赖于社会关系,是无私的爱。这种互不要求、不存疑问、相互接受的爱,是本质的爱。昆德拉的人物与故事毫无疑问地透露了:幸福与苦难就像世界的两极,看似遥远,却是相互转换,甚至两极相触。“轻”与“重”虽然代表了生命的两极,但它們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无论我们选择轻还是重,其实都是我们对生命的热爱,这种热爱不能变成对生命的苛求,不能去要求生命必须是美好的干净的,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设计生命。生命是它本来的样子,有生老病死,有快乐和不堪,有鲜花和青草,也有垃圾和粪便。无论是那个年代的捷克人民,还是当代人,生命中的难以承受之轻,其实就是生命的本质所在。一个人生命的重量,意义是合成的,当他认识到这种意义的人为性质时,他从精神到肉体就都自由了。
未来很多年里或许《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都会萦绕在我心头。它抓住了人性的核心,并广泛地涉猎了性、欲望和人体的日常现实,可以算得上是一本“人性启示录”,我甚至陶醉于昆德拉对叙事的哲学性打断。但是,昆德拉终究还是个小说家,当我们站在小说家的视角,就会发现:美和爱一直在那里,在托马斯接住草篮里的特丽莎的那一瞬间,在特丽莎睡梦中紧紧拉着托马斯的手那一瞬间,在特丽莎拯救乌鸦的那一瞬间,在弗兰茨对萨宾娜说“你是个女人”那一瞬间,也在萨宾娜凝望墓地想起弗兰茨的那一瞬间……书中最后一部分,也是最美的一部分,特丽莎和托马斯在乡下农场,他们一起埋葬卡列宁,一起饮酒,一起跳舞,然后一同赴死—那是无边的快乐,那是无尽的悲伤,那是生命的美好,那是岁月的沧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