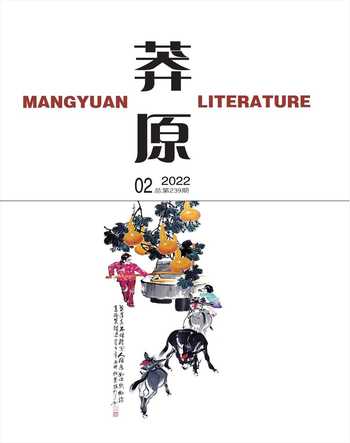风惊
墨安
1
那颗牙是三月八日黎明前突然发难的。张一东从睡梦中疼醒,弯着舌尖去探,如同舔到一颗热炭渣子,烫!舌头受惊回弹,裹进一团火焰,燎肿了牙龈,灼伤了脸腮。再睡已无可能了,苦逼的是,他不敢乱动,也不敢呻唤。
张一东怕吵醒郭燕。
老夫老妻同床共枕19年,按说比翼连枝,惺惺相惜,她应该体恤他的痛,为他找药递水,暖语相慰。这种温存是有过的。新婚那阵儿,她拱在他怀里,和他拉钩上吊,发誓要相亲相爱到永遠。然而,永远并不远,等她生了儿子当了妈,好像对他也长了辈分,温柔少了,严厉多了,甚至无遮无掩地嫌弃。
惹不起,他就忍。忍,已经习惯成自然。
这时,他听到了乌鸫的叫声。
惊蛰过后,乌鸫的瞌睡也少了,凌晨四五点钟就开始闹腾,除了原声聒噪,还模仿斑鸠、八哥、灰喜鹊等多种鸟儿叫。
儿子读高中后,郭燕一改睡懒觉的习惯,五点半,闹钟一响,她就弹出被窝,穿衣下床,匆匆洗漱,奔向厨房,一天一个花样给儿子做早餐——好的早饭,会催生好的心情;好的心情,能激发无穷的拼搏精神。这是郭燕的理论。张一东却担心她鸡血打多了,会适得其反,让儿子压力山大,最后落个鸡飞蛋打,一地鸡毛。不过,也只能在心里鼓泡,绝不发半点杂音。儿子中午和晚上两顿都在学校吃食堂,郭燕愿意淋漓尽致地表现伟大的母爱。他也跟着沾儿子的光,自然不好指手画脚。
“你操过儿子的心吗?尽过做父亲的责吗……”
时不时郭燕就这么训斥他。张一东盯她的嘴皮,不禁心生怀疑,她的前生是一只乌鸫。
见郭燕起床,张一东也跟着起了。她奇怪地问:“你起这么早干吗?”
张一东脱口而出:“尿涨了。”
“懒牛懒马屎尿多。”骂着,郭燕已经穿好衣服出了卧室。
洗漱间被郭燕抢先占了,张一东只好去阳台点了一支烟。他期望烟气一熏,那颗牙便昏昏沉沉麻醉下去。哪晓得他吸了一口,病牙却亢奋了,把牙龈当舞台,蹦嚓嚓跳了起来。他抖着指间的香烟不知所措,吸吧,疼;扔吧,可惜。
郭燕从洗漱间出来,张一东赶紧冲进去,挤了一大坨牙膏糊在病牙上,试图快速败火降温。那颗牙闹得正欢,突然被牙膏一浸,顿时惊慌失措,疼痛直往牙龈里钻。他接连几个干呕,泪花直滚。
张一东捂着腮帮,唏唏嘘嘘哈着气走出洗漱间。
郭燕的眼风扫过来,眉毛一挑,张嘴就损:“哟,你那泡尿彪悍呐,把牙都胀疼了?”
张一东没理她,恨不得把那颗作怪的牙咬碎,吞进肚里。
“喊你戒烟戒酒,你就是不听,自作孽,活该!”郭燕不依不饶。
“拜托,不要都往烟酒上扯。”他赶紧辩解,“昨天我去乡下,呛了冷风,牙受惊了。”
“呛风?没得赖的了……”
“信不信由你,反正就是呛了风,牙才开始疼的。”
呛风是真,但张一东说得没底气。三月的春风,已然温润柔和,说春风惊了牙,春风不喊冤,郭燕也不会信。可他还有个理由,只是不好说出口——若不是你装怪,我就不会心烦气躁,就不会去看油菜花,不去看油菜花,就不会见到李晓梅,见不到李晓梅,就不会……
沾上李晓梅那个女人,谁的运气好过?
2
三月四日下午,吕少明打来电话,说要和几个高中同学搞一次小范围聚会,约张一东去广汉市西高镇看油菜花。张一东眉头打结,说吃茶喝酒还行,看油菜花,没兴趣。
张一东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大学毕业先在畜牧局,后与农业局合并,组成新的农业农村局,每个月都要跑几趟乡镇。用郭燕埋汰他的话说,身上的鸭骚猪臭没断过,还稀罕看油菜花?
吕少明在县委办当过秘书,随后下去当副镇长,镇长,镇党委书记,最近回城当了统计局局长,仕途通畅,自然说话就带了官腔:“我给你强调一遍,我们是去广汉市西高镇,那里上万亩的高科技培育出来的五彩油菜花,可不是你平常看到的那种老油菜,那规模,那色彩,想想就如入仙境……”
张一东被逗笑了:“你大局长亲自召唤,我这小老百姓自是受宠若惊,哪还敢装怪?实在是你们定的日子不对,七号那天我已另有安排,实在抽不开身。”
一段时间里,张一东总感到他和郭燕的关系成了一堵漏风的墙。他没错,但问题肯定出在他身上。或者扩展点说,这样的问题好多中年男人都无法避免:收入平平,又没在单位混个体面的职位,兜没肥,人先油腻了;人没老,头先秃顶了——在女人眼里,尤其是在自家女人眼里,男人的平凡就是平庸。稍有不顺,随口就来:“当初我咋就瞎了眼,嫁给你这个窝囊废!”每每想到这些,张一东的心就像生了虫子,如咬如噬。郭燕对他的嫌弃已然理直,哪天她气壮了,会不会和他挥挥手,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为此,他曾诚恳地对郭燕说:“老话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我可能是命里不带官运,就这么随遇而安,佛系人生吧……”
他尚未把话说完,郭燕差点啐他一脸:
“不求上进叫上善?自甘堕落叫佛系?别冒充文化人了!”
郭燕在文化馆工作,主编《邡江文艺》,单位和职务都很文化。并且,去年出版了一本诗集,晚报上有人为她写书评,大赞她的诗“如若江南水乡的温婉,小桥流水的轻慢,简约而不失精巧,有妩媚而拨动人心的魅力……”他翻过她的诗集,既没有感到摄人心魄的冲击和震撼,也没有被哪一句诗感动得泪眼婆娑。当然,这可能与他不文艺、不懂诗之玄妙有关,但郭燕的话更扎心:“懒得理你,一个和畜生打交道的。”
张一东是经常跟畜生打交道,但朝夕相处的还是郭燕。所以他要化危机为契机,把握好即将到来的女神节,在特别的日子给郭燕特别的爱。翻了日历,三月八号是星期一,他和郭燕都得上班。那就六号和七号吧,连续两天为她庆节,让她感受到更充足的浪漫。
晚上,等到郭燕下班回家,张一东给她说了自己的计划。
郭燕说:“三月六号星期六,文化馆请了个省城作家来讲课,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文学的魅力?”
很长时间了,郭燕都不愿带他参加她单位的活动,这是怎么了?莫非是他的计划让她感动了?他有点小激动:“好呀,增添了文学细胞,我也跟着你写诗。”
他刚飘起来,郭燕就当头一棒:“写诗?算了吧。我只是不想你趁我不在家,跑出去和你那些狐朋狗友喝烂酒。”
心一下子凉了,他哼了一声:“我不去会我的狐朋狗友,也不高攀你那些文人雅士,在家做卫生总行了吧?”
“唉,我知道你不会去,只是随便说说。”
张一东计划好的特别的日子特别的爱,被郭燕硬生生拦腰砍掉一半,他犹豫了,是听天由命,继续过他的佛系人生?还是委曲求全,为她筹备一个浪漫的女神节?
想了一会儿,张一东立马重新规划过节的流程,三月七号那天,先去花店给郭燕买一束鲜花,再牵着她的手去逛商场,让她开开心心买买买,接着由她选饭店,只管快快乐乐吃吃吃,然后去看一场电影,若意犹未尽,还可以去红峡谷的泡泡屋住上一夜,望星空,说情话……她就是铁石心肠,他也要努力把她哄得甜蜜蜜暖酥酥。
3
如此这般,张一东怎么能让油菜花误了他精心策划的浪漫?
吕少明见虚晃无效,突然耍起狠招:“喊你看花,又不是找你借钱,磨磨唧唧。实话告诉你,若不是李晓梅非叫上你,我才懒得和你说这么多废话!”
李晓梅的名字像三粒橡皮子弹,精准命中张一东。好在他皮厚肉糙,痛了个趔趄,不至于晕倒。
李晓梅是张一东和吕少明在邡江中学的同学。那时,她的身边总有男生围着打转,但她分寸拿捏到位,从不讨厌谁,又不对谁真好。男生们为她发痴犯傻,她却不迷不惑,玩耍学习两不误,后来,她顺利考上了师范大学。围着她打转的男生,除了吕少明去重庆读了大学,其余的都在高考中折戟。大学毕业,李晓梅留在省城当了老师,不久,嫁入豪门。据说,她夫家是做轮胎生意的,在西南几省市都有公司和门店。去年,她离婚了,有说她婚后一直没有生育,遭到夫家嫌弃;有传她丈夫出轨,她忍无可忍,慧剑斩情丝;还有说她不甘铜臭染身,向往文艺清新的自由。前头两条张一东都信,唯独不信后一条。明摆着,她若真文艺清高,当初又咋会嫁了富家公子哥?
李晓梅离婚不久,回到邡江,组织了一次同学会,并预先打了招呼,她请客,不需要任何人出钱,吃喝玩乐,全程包圆。席间,出来上厕所,吕少明对张一东说:“我敢打赌,李晓梅是花钱买热闹,掩藏她心中的落寞。”张一东也这么想,不然,谁会在离婚后,欢天喜地搞派对?他大赞吕少明看问题深入透彻,乘机鼓动说:“机不可失,乘虚而入。”
现在回想起来,张一东已辨不清当时他是怂恿,还是讥讽。似乎哪一种情形,对吕少明都合适。毕竟吕少明在高中时追求过李晓梅,如今又和她联系紧密。但吕少明却摇摇头,喘了一口长气:“李晓梅通透洒脱,一般人驾驭不了。”
“你是局座,不是一般人。”张一东坏笑着说:“你就是有心无胆,怕你家那位上房揭瓦嘛。”
“我倒不怕她上房揭瓦,就怕她耍起泼来,把我乱刀剁成肉酱包饺子。”
吕少明的老婆原来是化机厂的检验员,后来单位改制,她买断工龄摆了个小摊,专门卖手工抄手、饺子。同学们都想不通,吕少明大小也是个正科级干部,又在官场混这么多年,关系网宽广,随便给老婆找个单位,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张一东把这事说给郭燕,郭燕却说得玄乎:“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张一东不解,问:“吕少明贵为一局之长,老婆沦落去摆摊,还能乐得起来?”郭燕哼一声:“所以说,你当不了官。”细细咀嚼她的话,总算品出了点味:吕少明是在标榜公正清廉,挣口碑捞官声,还想往上升。
“一有聚会,李晓梅就要拖上你。我就不明白了,她为啥对你那么好,你为啥又总是扭扭捏捏……” 吕少明说。
张一东心里一动,但毕竟人到中年,耳闻目睹了太多事,知晓一旦牵扯到女人,男人就言不由衷。有些人明明想精想怪想和谁整出点你是风儿我是沙的故事,偏偏口是心非,拖一个不相干的人做靶子,转移冷枪冷弹。他不好妄断吕少明对李晓梅有没有猫心肠,只知自己没有亮点可以吸引李晓梅。以前,他还有帅气的相貌做资本——郭燕不止一次说,她之所以愿意嫁给他,看中的就是他长得还不错,可以给下一代遗传好的基因——这些年,抽烟把脸熏黄了,喝酒把肚子泡大了,整个人都变得油腻邋遢。那次同學聚会,他和吕少明走一路,李晓梅指着他圆鼓鼓的肚皮笑得前仰后合:“我的天啦,腐败局长带着猥琐小秘书进村啦。”
上高中那会儿,李晓梅倒是对他刮目相看,为他写过几首诗,夸他学习刻苦,长得高大帅气,还说想去他家那个山村玩耍。高考落榜后,李晓梅笑着对他说:“你只是发挥失常,千万别气馁,一定要复读。”她说话的语气,辨不清是同学间的劝慰和勉励,还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谆谆教诲。
就为李晓梅这句话,张一东苦苦哀求他爸,好话说尽,胸脯拍烂,坚决要去复读。他爸卖了一车谷子,还卖了两头一百多斤的架子猪,让张一东重新走进了课堂。为此,他总觉得自己有罪。复读那一年,几乎在拼命,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考上了大学。参加工作后,他每个月都往家里送钱,买东西,以实际行动向爸妈赎罪。有时候想想,还真得感谢李晓梅,若没有当年她那句话,张一东也许就放弃了。
吕少明说:“你不给我面子无所谓,让李晓梅失望伤心,你自己去哄。”
张一东心里暗自发笑,李晓梅又不是他的谁,他为何要去哄?再说了,她有他的微信和电话,若真想见他,为何不亲自约他?吕少明这般阴阳怪气,是嫉妒李晓梅在意他,还是打着李晓梅的幌子戏谑他?
他总算松了口:“如果不是七号那天我真有事,你大局长即便放个屁,我都得扑爬跟斗撵过去。这样吧,我尽量调整一下,若挪得出时间,就去和你们碰头。”
这显然是在搪塞,已经计划好给郭燕过一个浪漫的女神节,他不会因一个李晓梅改变计划。同学关系再好,毕竟不是在一个锅里搲饭吃,不是在一个窝里抱着睡。
4
三月六号那天,郭燕出门后,张一东就忙开了,拖地,擦窗户,洗衣服……想让郭燕回家后眼前一亮,为接下来的故事作一个好的铺垫。
晚上十一点半,郭燕才回家。她显得有些疲累,竟没有留意到家里的变化,直接去洗漱了。张一东帮她把扔在沙发上的挎包挂好,又把她带回来的书摆到书房的架子上,走进卧室,把灯光调成暖柔色调……做这些时,他思绪奔腾,好像回到了恋爱的年龄。
等郭燕洗漱好上了床,张一东伸手去抱,她却打开他的手:“都半夜了,快睡。”
张一东把手从郭燕的肩滑到她的腰上,探寻着点爆她的引线。郭燕皱紧了眉头:“还有三个月儿子就高考了,你还有心思东想西想,真是动物!”他的手再次被她甩开。他还是不甘心,把嘴凑到她耳朵边,改用糖衣炮弹去软攻:“女神节就要到了,我想好好爱爱你,你想要什么礼物,想去哪里玩……”
果然引爆了:“张一东,你究竟长没长
心?儿子在紧张备考,你却想着怎么玩,像个当爸的人吗?”
看着郭燕翻身裹紧了被子,张一东懵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夫妻俩亲热和儿子高考有什么关系。莫非接下来的三个月,他只能清心寡欲,碰她一下就成了动物?就不是儿子的爸爸了?
他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啪嗒一声关了灯,往床边一滚,把后背甩给她。然而,闷气在肚子里不断膨胀,撑得他没有半点睡意。熬到乌鸫啼叫,他索性穿衣起床,到阳台上抽烟。天空像一张厚实的网,望不到一点亮光。他劳累了一天,郭燕没给半点奖励,他又何必拿热脸去贴她的冷屁股?去她的女神节吧,不如去看五彩油菜花——他想起了李晓梅。
没等郭燕的闹铃响起,张一东便出门了。开车到西高镇,天才大亮。他找了一家小吃店,喊了一碗米粉,摸出手机给郭燕发了一条短信:“临时接到通知,我去单位加班了。” 愣了几秒,他又给吕少明发了一条短信:“我已到西高镇,等你们。”
那时候,张一东还没有想到会被风呛了大牙。
5
西高镇离邡江县也就五六十公里,一帮同学会合,很快就到了。
张一东受了郭燕一肚子气,又一夜没睡,面对斑斓多彩的油菜花,一点也打不起精神。他心不在焉地跟大家走,只盼着时间过得快一些,中午好去吃乡村柴火鸡,酒杯一端,烦忧全无。
突然,他的小腿像抽筋了,腰一闪,差点摔倒——
张一东看到了他的顶头上司宋局长。
宋局长也看到了他。
出于礼貌,张一东快步过去打招呼。没想到李晓梅竟然跟着他追了过来,这让他有些担心,生怕宋局长误会他和李晓梅有啥关系。宋局长是从妇联出来的女干部,她来到局里以后,对男女关系异常敏感,以前开惯了玩笑的男女同事,都变得小心谨慎,一本正经。张一东下意识地想摆脱李晓梅,可已经来不及了。
李晓梅蹦蹦跳跳抢在了他前面,冲宋局长身边的男子喊道:“哇,柳老师,真的是你呐!”
原来她也遇到了熟人。
张一东终于松了一口气。
被叫柳老师的男人愣了一下,好像没有认出李晓梅。
“柳老师,我是十七中的李晓梅啊。前年你来我们学校讲写作课,我还请你签过名呢。”李晓梅满脸开花,又激动地蹦了一下。
柳老师马上挤出笑容,伸出手:“你好。”
李晓梅握着柳老师的手不松,像极了花痴,把张一东和宋局长当了空气,说了一大堆恭维仰慕的话。
张一东呆呆地站在宋局长面前,忘了问好。宋局长没有招呼张一东,只是盯着李晓梅似笑非笑。
李晓梅把手机往张一东手里一塞:“别傻愣着啊,快,帮我和柳老师照几张合影。”
张一东给他们拍了照,才想起跟宋局长打招呼:“宋局,真巧啊,你们也来看油菜花啊。”
“是呀,巧。”宋局长微微点了点头,表情怪怪的,似乎对张一东和李晓梅的贸然打扰很不满。
张一东心里七拱八翘,努力往脸上挤着笑容:“宋局,你们慢慢看花,那边还有几个同学在等着,我们过去了。”
然后,对李晓梅使眼色。
李晓梅只顾拗着和柳老师说话,根本不看张一东。他想去拽她,手还没伸拢,又缩了回来。敏感时期,他绝不能在宋局长眼皮底下和别的女人拉拉扯扯。
“老同学,我们该过去了。”无奈,张一东只好开口明说。
“急什么?急了你先过去吧。”李晓梅很是不满,朝他嘟了一下嘴。
赖着不走,惹宋局长讨厌;催促闪人,惹李晓梅讨厌。张一东尴尬极了,只好讪讪离去。
李晓梅见张一东真的转身了,才慌着抱了一下柳老师,恋恋不舍地挥手告别。但自始至终,她都没有礼貌性地和宋局长打声招呼,甚至没有看宋局长一眼。
“你呀,还是老师,当着人家老婆的面,和那个柳老师拉拉扯扯,抱来抱去,一点矜持和斯文都没有。”
其实,他并不确定那个柳老师是不是宋局长的丈夫,他只是想用这种关系呛李晓梅。
“那女人会是柳老师的老婆?”李晓梅眼睛鼓得溜圆,“她那么老,那么土,给柳老师当保姆都不配。”
“你见到过谁带保姆出来看花?”张一东揶揄说,“告诉你,她是我们宋局,今年还不到四十岁,比你还小几岁呐,配那个柳老师绰绰有余!”
“原來是你的老大呀,难怪你紧张得屁滚尿流。”李晓梅笑得花枝乱颤,“还别说,她那么土气,做农业农村局的局长还真是合适。”
“见了男人就又搂又抱,叫洋气?”
“咦,说你土老帽,你还不安逸了。嘻嘻,你不会对你老大有想法吧?”李晓梅往张一东肩上一拍,继续嘻嘻哈哈。
眼看就要走到吕少明那帮同学身边了,张一东懒得理她。
“老实招来,你是吃柳老师的醋,还是吃我的醋?”李晓梅又拍了一下他。
“我喝酒吃酱油,从不吃醋,不像你那么花痴!”
“谁花痴啊?”吕少明插嘴了。
一口风呛来,带着浓郁的花香,张一东鼻子一痒,还来不及用肘去挡,一个响亮的喷嚏就打了出来。李晓梅一只手挥扇着空气,一只手掏出纸巾捂着口鼻,嫌弃的眼神和郭燕一模一样。
“李晓梅现在单着,看到帅哥口水就流出来了,想啃嫩草呗。”吕少明坏笑。
李晓梅居然一点没有不好意思:“懂我
者,吕少明也。”
吕少明摇头晃脑:“嫩草不够味,还是中年男人好。”
几个同学都跟着起哄:“数中年男人,还看吕局好。”
“非也,非也,你们没看到,李晓梅和张一东一路打情骂俏,唱天仙配呢。”
一伙人哄笑不止。
张一东心里又起泡了。李晓梅的话虽然尖酸刻薄,但那个柳老师确实年轻帅气,和宋局长在一起,怎么看都没有夫妻相。若不是夫妻,一个是省城的老师,一个是小县的局长,又怎么会相约到西高来看油菜花呢?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想向吕少明询问,毕竟都在一个县当局长,吕少明肯定认识宋局长的老公。但奇怪的是,吕少明和宋局长相距并不远,两人却都装作没看见,连声招呼也没打,莫非心照不宣也是当官的艺术?
6
过了一天,牙似乎更疼了。张一东嘶嘶吁吁的抽气声,总算引起了郭燕的重视,她翻开他的嘴皮,用电筒往嘴里照了照,说:“牙龈有些红肿,像是要长溃疡。”然后,她从药箱里抓出几袋牛黄解毒片,“管住你那嘴,别再沾烟酒。”
张一东声音小如蚊蝇,答应得并不干脆。
抽烟喝酒是他的软肋,一戳就疼。刚认识那会儿,郭燕就要他戒烟戒酒,他也表了决心,奈何恒心不够,半途而废。她骂他屁大的毅力都没有,不像个男人。有了儿子以后,她骂过多少次,他总是耍赖敷衍,痴心不改,大不了她嫌他口气臭,不和他亲嘴打啵啵。
张一东吃了牛黄解毒丸,牙火依然不退。郭燕就尝试给他用偏方——咬姜片,无效;牙缝填蒜泥,不抵事;醋泡花椒水漱口,也没用;芦荟,蜂蜜,丁香花,统统没用……他被她折腾得眼泪花花直冒,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啥叫痛并快乐着。到底还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相爱相惜啊。以至于他暗自愧疚,不该在三月六号晚上和她怄气,更不该七号那天撇下她,跑到西高镇去看油菜花。
吃了几天清汤稀饭,又喝了郭燕为他熬的中草药,张一东牙龈红肿渐渐消退,那颗牙也安分多了,不遇冷热酸甜,不碰坚硬和粘糍的食物,基本上感觉不到疼。他悄悄准备着,等郭燕心情好的机会,拉她去吃一顿火锅,弥补一下女神节对她的亏欠。
哪料到,局里的一纸人事任命又让张一东呛了一口冷风——规划股的李刚强被任命为畜牧兽医股股长,张一东扶正的愿望又落空了。
张一东这个副股长已经当了五年了。八个月前,股长调走,虽说组织并没有找张一东谈过话,但股里的同事都在说,不管是论资排辈,还是看功劳苦劳,他都该扶正了。那时宋局长还没上任,局里让张一东暂时负责股里的工作。这让张一东看到了扶正的希望。谁知,风云突变,张一东的“暂时”变成终止,“扶正”化为泡影,他以后在股里还有脸面吗?想不通,于公他没有犯错,于私他跟宋局长没有个人恩怨,就算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也不该烧到他身上啊。
更气人的是,宋局长还留他谈话:“你是科里的老人,经验丰富,要多支持和帮助李刚强的工作。”
“必须的。”
张一东想表现得自然些,反而把话说得咬牙切齿,疼痛如木螺钉一样往牙龈里拧,连嘴角都扯得抽搐不止。
“你咋啦?”宋局长很诧异。
“牙疼。好些天了……”
张一东好气恼。他本来很真诚,那颗牙却把他折磨得面目狰狞,宋局长肯定认为在闹情绪。他捏紧了拳头,只想一拳把它击落。
“少抽点烟,最好戒了。”宋局和郭燕一样,把牙疼和抽烟联系到一块。
张一东条件反射地辩解:“我这牙是遭风呛惊的。”
“呛风?”宋局长明显不信,“你这说法倒是怪。”
“是有点怪。”张一东咧了下嘴,“我经常跑乡下,啥样的风都吹过,偏偏那天和同学去看油菜花,呛了一口风,牙就疼了。”
“看油菜花……”宋局长笑了笑,“算下来,好几天了,还是赶紧去看医生吧。”
张一东捂着右腮:“就怕遇到庸医,直接给我拔了。”
“牙真要坏了,留着也是遭罪。带病上岗,隐患无穷。”
张一东的神经突突地跳,感觉宋局长话里有话,在敲打他。好吧,牙作怪,就抽牙的怪筋。
7
李刚强上任才三天,郭燕就知晓了,免不了对张一东又是讽刺又是打击。
张一东心里感到窝囊,但嘴巴很硬:“一个小小的股长有啥稀罕的?”
“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蚂蚱腿也是肉!”郭燕说。“你若当上了,工资就会跟着上调,以后退休了,养老金也要高一截。”
“我到退休还早,说不定过两年我的运气来了,能升一个更好的职位哩。”张一东辩解。
“升?我看你生疮差不多!”郭燕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满了四十五岁,还有提干的可能吗?老得无望了,还不自知。”
张一东刚想说,我才四十四岁,一切皆有可能,但突然想起宋局长的话,“你是股里的老人”,一个酸嗝打出来,话就变味了:“是,你说对了。老局长喜欢年轻美女,现在宋局喜欢年轻帅哥。我老了,没戏了。”
“你咋变成这样了?自己莫得出息,还满脑子的男盗女娼。”
“不是我满脑子男盗女娼,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张一东忽然想起宋局长和那个来自省城的柳老师一起看油菜花的事,便一股脑全说给郭燕听。
郭燕撇了下嘴:“张一东,你咋比八婆还喜欢捕风捉影?真是没救了……”
张一东抓狂了。他明明是就事論事,咋就和郭燕有理说不清呢?她为什么总喜欢站在他的对立面,板着一副面孔教训人?
张一东没能去副转正,说意外也意外,说不意外也不意外。人事上的事,千变万化,充满玄机,只是他心里那道坎过不去,尤其是被郭燕打击一番后,他更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笑话。看到同事们在一起说笑,他就怀疑人家是在戳他的背脊骨,谁不经意轻叹一声,他也觉得是对他的惋惜和怜悯。他像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丑事,心里充满了压抑。那颗牙像桀骜不驯的猛兽撕咬钢丝笼一样,生拉活扯着他的牙龈。莫非,它也看不起他,想甩开他?
他管不住别人,自己嘴里的牙,他做得了主。
下午下班后,张一东绕道去了鼓楼街,找到一家牙科诊所。
诊所并不大,临街的三间铺面,开着大灯,亮亮堂堂,只见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围着一张矮桌吃饭。他发现都是些年轻女人,不免有些担心——常言道,看医生还得找老的。
“大叔,看牙?”
一個女人放下碗筷,站起身问。
“你叫我大叔?”张一东的脸瞬间拉了下来。
“哎哟,小哥哥,对不起,刚有菜汤溅到眼里,看模糊了。”女人扯了一张纸巾,却没有去擦眼,而是抹着嘴,好像在掩饰偷笑。
另外几个女人都嗤嗤笑起来,丝毫不怕口中的食物呛到气管里。
从进了这家诊所,张一东就没有好感,疑心起了一次又一次,可邪门的是,他就是没有想到拔腿离开。
女牙医从塑料瓶中挤了几滴免洗消毒液,双手揉搓了几下,戴上口罩,走到张一东面前,问:“小哥哥,洁牙还是补牙?”
张一东感觉浑身都在起鸡皮疙瘩,但他没有纠正。被叫小哥哥,总比被喊大叔舒服些。他没有去看她的胸牌,目光被麻辣干香的味道牵走了。矮桌上放着一盆毛血旺烧肥肠,那颗牙馋了,像是要从牙龈里跳出,蹦到红亮的油汤里去。他用手指了下嘴说:“有颗大牙……疼得要命。”
女牙医随口问道:“哪天开始疼的?”
“三月八号凌晨……”张一东想了想,又改口说,“也可能是七号夜里……”
他再次回忆了一遍——本来要给郭燕过“三八”节,但六号夜里郭燕装怪,给了他一闷棍;七号一大早,他负气出走,与吕少明和李晓梅等同学去西高镇看了五彩油菜花,呛了一口风,牙受了惊,但当晚回家直至睡下并没觉异样;疼醒时,他听到了乌鸫的啼叫,应该是八号的黎明……这很重要,他必须把话说清楚。
“我确定是八号黎明前开始疼的。”
“哦。”
张一东有点恼怒,他严肃认真的回答居然只换来她漫不经心地“哦”了一声。他盯着她搓得白嫩透红的手指,真想咬上一口。
女牙医似乎并不在意时间是否准确。她抽出一次性医用手套戴上,说:“躺下,我给你检查一下。”
她打开治疗床上方的灯,从盘子里取了口镜,要他张嘴。靠得太近,没有闻到消毒水味,却闻到了如兰的香水味。他想看看她的脸,可惜她戴着口罩,只看到她的眼睛大而清亮,很好看。
口镜在他的痛牙上碰个不停。他满嘴口水,含混地喊叫:“疼,就是那颗大牙。唔,好疼。”
“它不叫大牙,叫第三磨牙。”
张一东头皮一紧,好似听到了郭燕的声音。恍惚中,好像在一个教室里,郭燕站在讲台上,把口镜当教鞭,把黑板敲得砰砰响:大牙?没文化,真可怕,硬是要笑掉大牙呐!划重点,它叫第三磨牙,这是考点!
“第三磨牙太靠里面,平常刷牙清洁不彻底,引发了牙髓炎。牙已经坏了,得拔。”
张一东紧张地问:“拔牙?痛不痛?”
“大男人还怕痛?”女牙医的话硬邦邦的,和郭燕一个调门,一点没有医者仁心。“不过今天不能拔,牙龈发炎这么凶,拔不得。”
“可是,不拔了它,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钻个孔,把脓水放出来就不会疼了。”
女牙医拿着的电钻很小,纤细如针,然而,那亮晃晃的钻子带着水雾一触到牙齿,一种酸痛麻痒的感觉立即让张一东神经绷紧,身体僵硬,心脏似乎也被一点一点拽出。就在他快要崩溃瘫痪时,女牙医总算停手了。他吐了几口黄褐色带血丝的口水,气还没有喘匀净,女牙医又让他张大嘴,将一小块药棉球塞进刚钻的小孔里。一股凉丝丝的苦味迅速在口腔里漫开,刺激得口水澎湃。
惊喜的是,那颗牙真的就不那么疼了。
女牙医示意张一东坐起来,接了一杯水让他漱口。然后,她去了写字桌,像是在写处方。等张一东漱了口过去时,她已经停止了书写,但没将写好的单子给张一东看,直接交给另一个更年轻的女人。
很快,药拿了过来。女牙医让张一东三天后过来检查,如果炎症消了,就可以拔牙了。
8
回到家里,张一东对着镜子,用手指去摸那颗坏牙,果真松松垮垮;再移到别的牙齿上轻轻一掰,骇出一身冷汗,一摇都动!莫非真的衰老了,就要掉光牙?他有点纠结。毕竟朝夕相处了几十年,这颗牙一拔掉可就长不出来了。就算安装一颗假牙填补牙龈上的缺口,唇齿间还会有那种相依的默契吗?
郭燕回家后,他突然想把手指伸到她嘴里,去试试她的牙松不松。他当然没那样做,她连和他亲嘴都嫌臭,他把手指伸进她嘴里,她不一口咬断才怪。
牙疼的那些日子,郭燕虽然厌烦,动不动就拿抽烟喝酒说事,但还是想方设法替他打听治牙偏方,给他熬粥煲汤,虽不耐烦还是表现出温暖和体贴;牙不疼了,又看他不顺眼,懒得理睬了;加上儿子高考日益临近,她也愈发焦躁,一言不合,就暴跳如雷。
张一东怀疑郭燕到了更年期。他劝她从容淡定,要顺其自然,今年考不好,明年再考……话没说完,她就直接怼了过来:你别给儿子灌输这消极思想。你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可丢不起那脸!
网络上有个说法,两口子揭伤疤翻老账,就算感情尚未完全破裂,基本上也没救了。说很多中年夫妻明明已经不爱了,但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学习,还貌合神离地硬撑到高考结束。因为孩子高中毕业基本上已年满18岁,心智也比较成熟了,且上大学一般是离家住校,父母离婚对孩子影响相对最小。张一东细思极恐。他担心儿子高考后的某一个日子,郭燕会突然弄一桌子酒菜,冲他举杯:来,干了这杯酒,我们就各奔东西……
郭燕对他不满意,绝对不是因为他不文艺,和她没有共同爱好,主要是嫌弃他庸庸碌碌没出息。可是,没钱了,逼急了还可以去偷去抢,可职位这玩意,领导不提拔,你啥法也没用啊。
正当张一东山穷水尽脑壳皮都要抠破时,一个消息传来:农机的钟所长即将退休。如果他能抢到那个位置,郭燕肯定会对他刮目相看。对,不能再听天由命,该主动时就得主动。毕竟,他的资历摆在那,往上升一级合情合理。可这事一把手说了算,怎么能过了宋局长那一关呢?
这么一想就想起了李晓梅——李晓梅认识那个柳老师,能不能通过李晓梅,找到柳老师,让他帮忙打通宋局长的关卡呢?但张一东马上就否定了这个想法。看李晓梅与柳老师的关系,也就是泛泛的一面之交,未必能搬动柳老师,再说,柳老师也不一定是宋局长的老公啊。
想到这里,张一东给吕少明打了个电话,问起宋局长的婚姻状况,果然,宋局长的丈夫叫姚雄飞,供职于省文联。他心里一动,既然宋局长的丈夫并不姓柳,那她跟省城来的青年才俊双栖双飞去看油菜花算怎么回事?那次不期而遇是不是可以成为他手里可打的惊天王炸?
张一东敲开了宋局长的办公室。
宋局长问他有啥事。张一东突然心虚冒汗了。参加工作以来,他从来没有拍过领导的马屁,没有给领导送过礼,也没有在领导面前表过功,现在,他捏着领导的把柄搞要挟,这是人干的事吗?
“没事,没事。我就是来看看领导有没有事……”他避开了宋局长的目光。
“真没事?”宋局长好像不相信,起身取了一只纸杯,给他倒了一杯水。“是不是工作上有啥问题?”
“没问题。”张一东捧着纸杯,如捧着沉重的铅块,双手抖得直抽筋。“对了,我那颗牙不疼了,真的要谢谢你。”
“我又不是止疼药,你谢我干吗?”
“若不是你叫我去看医生,我肯定还在受罪。”
“有病拖不得,呵,有事也闷不得哟。”
“没事,我真的没事……”张一东感觉双手不听使唤了,赶紧举起杯子喝水,喝得太猛,呛了一口,剧烈地咳嗽起来。
“没事就回去好好工作吧。”宋局长笑了一下,又好像没笑。“有些事组织会考虑的,个人多想没用,也没好处。”
“是的,是的,谢谢宋局。”
张一东放下纸杯,看都不敢看宋局长一眼,就脚板抹油,溜了。
9
五·四青年节那天晚上,县团委和文化馆共同举办诗歌朗诵大赛,郭燕作为评委,自然不能缺席。张一东一个人倒在客厅的沙发看电视,可频道换来换去,就是没找到一个节目可以看进去。他脑子里装的事太多,想不通自己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为什么几任领导都不肯重用他,想不通文化馆为何总在晚上搞活动,也想不通郭燕一个杂志主编为何每次活动都要到场,更想不通她已人到中年为何要去凑青年人的热闹……
无聊。他关了电视,一边抽烟,一边拿起手机——他看到了李晓梅发在朋友圈的自拍照和诗作。
他晕乎乎点开了聊天窗口,晕乎乎地打了一行字:“突然怀念高中时期,你给我写诗的日子……”
一支烟抽完了,他端着茶杯去阳台站了一会儿,又端着茶杯回到客厅,重新倒在沙发上,捏着遥控板不停换台。
一声脆响,李晓梅终于回信息了:“可惜时光不能倒流。”
他更加犯晕了:“今天是青年节,我突然生出一种年轻的期盼,想收到你的诗。”
“可惜我已不写诗好多年了。”
“好遗憾啊……”他又点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两口,把这句话发送了过去。
“嗬,你什么时候对文学感兴趣了?”李晓梅发了个捂嘴的笑脸。
他似乎找不到话说了,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突然脑筋急转弯:“我一直喜欢读文学作品啊。不信你看——”
他跑进郭燕的书房,对着书架拍了好几张照片发过去,“瞧瞧,我买的文学书籍不比你少吧?”
“哇,你还有柳老师的《寻梦记》!”
张一东心里一惊。一本一本搜寻,抽出了那本《寻梦记》。他记起来了,这本书是三月六号晚上郭燕参加完文学讨论带回家的,是一本诗集,封面红与黑的对比好强烈,像长夜里一个热烈的梦。他翻开封面,看到了作者简介:柳摇风,本名姚雄飞……他早就打听清楚了,宋局长的丈夫叫姚雄飞,那么,柳摇风应该是姚雄飞的笔名了!
他当即呛了一口风,已经不疼的那颗牙又有点酸疼。
书房的窗关着的,哪来的风呢?肯定是接连抽了几支烟,给熏的。他真是笨到极点,幸好,他只是磨牙坏了,没有再去宋局長那里乱磨牙。
六月七日,闹钟比以往提早了一个小时。
郭燕一边穿那件大红旗袍,一边催张一东快起床。头天夜里,她给他找了一件绿色的T恤,给儿子新买了黄色运动衣裤,这样一家三口进考场,就寓意“旗开得胜”“开门红”,“一路绿灯”,“走向辉煌”……
把儿子送进考场,张一东松了一口气,催郭燕去上班了,她却充耳不闻,像掉了魂一样,在学校门口走来走去。突然,她过来挽住他的胳膊,温柔地说:“等儿子高考结束后,我们就一起休假,好好出去旅游一圈,放松放松……”
一股风拂来,携夹着浓浓的栀子花香。张一东的鼻子一痒,打出一个响亮的喷嚏,一粒坚硬的东西如子弹般贴着嘴皮射出,打在水泥路面上,又弹跳了几下。他捡起来一看,是一颗黄中发黑的牙。慌忙弯着舌尖去探,舌尖卡在凹槽里,却没有痛感;往纸巾上吐口水,口水清亮,有淡淡的血丝——没有拔掉的牙,就这样戏剧性地落了。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张一东接通电话,耳边响起李刚强的声音:“恭喜啊老兄,你的调令来了,接任钟所长主政农机所工作!”
这个消息,比起春天那场乍暖还寒的风,更让张一东受宠若惊了。
责任编辑 申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