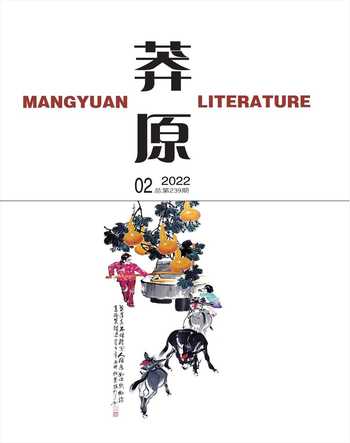小说讲堂:主题
言 说:
小说讲堂:主题 张炜
古人云:“文以载道”,无论如何,小说是有主题的。只在,读者在阅读之后,才会触摸到主题的脉搏;作者在创作一部小说时,却并非主题先行,而是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有了表达。
著名作家张炜先生以他半生的创作经验,给予了很好的解答。
首先,小说的“主题”是以各种方式存在的,它无论是潜隐在深处还是流露在外部,都源自作者的世界观——作者对这个世界的总的看法,一定要在作品里展现出来。其次,是作品的主题如何表达。杰出的作家往往是一些奋不顾身的人,这里的“身”也包括了小说本身。在激烈的情感中、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也许会忘掉“小说”作法,忘掉自己在世俗生活中的安危,但不会忘记责任和使命。他们的道德判断不仅清楚,而且简明锐利,或者通过人物,或者直接就是他自己,做出一些尖锐深刻的表述。其三,小说的“主题”,不能像论文那样去论证一种思想、说明一种观念,甚至不能通过人物和场景、也不能通过故事去直接阐明某个道理,它是一个作家对个人、对自己置身的这个世界永不疲惫的探寻过程,是世界观的形成轨迹。只要这个轨迹存在,他的作品就不会像一摊烂泥一样萎泄在地。
总之,作家以个人的思维方式、个人的语言方式讲述故事,这才是主要的。这一切都是不可代替的。它所表达的主题,渗透在语言、故事和人物之中——语言、人物和故事也都是“主题”,因为“主题”就溶解在这些里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主题在哪里
读者看过了一本书,掩卷之后常常要想一个问题:这部书表达了怎样的思想?主题是什么?他们往往是要这样琢磨一番的。
而作者们却未必如此。他们在创作一部小说时,是否想过这个问题还不一定——有的开始构思时想的尽是人物和故事,想如何讲述,“主题思想”或许从来都没有想过;也有的为此所苦恼,围绕作品所要体现的理念动了不少脑筋;另有不少作者可能会直接否认小说的“主题”,认为那是写论文才要考虑的东西。
教科书上说,作家通过小说表达的思想,要蕴含在作品之中,作者的思想倾向会通过人物的性格和情节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它一般不会把主观意念直截了当地说出,就是说,“主题”不能是裸露在外的。
不过,当我们具体分析时,情况可能要稍稍复杂一些。因为如果简单化地理解“主题”与作品的关系,难免要误导创作,最终把小说这个文体与其他写作的界线弄得模糊起来。
众所周知,如果要写一篇论文,那肯定要有主题,有逻辑推理,最后得出一个比较完整和清晰的结论,通篇要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如果是一篇散文,它的思想逻辑关系也会相对清楚一些,读者可以分析和提炼出文章的“主题”。
唯独到了小说这里,好像一切都变得不太一样了。我们知道,小说一点儿也不比论文、散文和戏曲等其他文体的说服力小。它的说服力也许更强大、更深入和更长远——所以它需要作家调动全部的艺术手段,比如语言的魅力,人物的感召力,意境的深邃,情感的饱满等等,深深地打动读者、进而“说服”读者。
我们读文学作品与其他的文章有一点儿不同,就是除了信服和赞同,还会有更多的期待,即获得审美上的满足。其实这种满足感的获得,从头至尾下来,也是我们被“说服”的过程。想想看,我们阅读一部小说,“人物”的所思所行,一举一动都是活生生的,让我们感到了可敬、可信或者憎恶,就好像看到了生活中的一个真实人物似的。小说营造的情境笼罩了我们,这时候所有的文字都变成了活的,变成我们置身其中的一个生命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在打动人、改变人,它以综合的因素作用于我们,一次次造成心灵的冲击。一些倾向和意绪就在这期间渗透出来,被我们慢慢接受下来。
小说没有论证,也不需要论证,所以它的思想观念的部分,就不能简单地用“主题”二字去概括了。这里谈到“主题”,完全是借用了一个比较通俗的讲法,用以说明小说的思想因素是怎样存在的、它的存在形态是怎样的。
读者读一篇论文,很容易就捕捉到作者的思想脉络,并最终弄懂他要向我们证明的一种思想或一个观点。读小说就有点麻烦,不仅很难一下子弄明白作者想要强调的意思,而且有时候还越读越糊涂——作者表述的很多想法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还有时本来渐渐趋向了明朗,但不久又进入了另一种模糊和隐晦。就像雾里看花,隔山打炮,让人始终抓不住要领。可是我们又分明知道,作家还是要通过人物和情节等等,渗透和表现出一些倾向,用来影响读者。
实际上,大家对怎样看小说确有不同的认识。一部分人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主题”的一场费力搜寻;另一些人读起来倒是放松得很,他们不管那么多,只是看得愉快和过瘾,看得有意思就行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感动,尽管这感动也许难免糊糊涂涂的。
前一种阅读显然是边看边研究,而后一种阅读大概只是一般的欣赏。
对于小说和它的作者来说,究竟是前一种好还是后一种好?或者问:作者希望更多地遇到哪一种读者?
这有点不好回答。有人可能觉得前一种讀者水准更高,得到这部分人的认可或许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后一种读者只是看个热闹,是平常的所谓“文学爱好者”。可是果真如此吗?放眼望去,报纸杂志上有数不清的文学理论,其中的一大部分仍然在做“思想分析”,对待小说如同论文,仍然要在“通过什么说明了什么”这个大框子里解读。对他们来说,“主题”是绝对存在的。小说没有“主题”吗?那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能否挖掘出来。他们就是这样看待小说的。
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世界,里面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只要愿意寻找,似乎什么都可以找到。问题是他们真的找到了小说的“主题”吗?
也许小说会有许多“主题”,他们找到的只是其中之一。这就有了另一个麻烦——究竟哪一个“主题”才是最重要的?的确,到了现代小说这里,人们越来越赞同这样的观点:一部作品中可以容纳不同的“主题”。这一来事情就难办了,研究者要格外耐心地寻找所有的“主题”。
最难办也是最令人尴尬的,是我们常常给作品误植一个“主题”——它根本就没有研究者费力推导出的那些东西。看来作品是一个复杂而又完整的生命系统,硬是用一把逻辑的解剖刀来肢解,很容易割伤它的神经。
说到“主题”,我想到了契诃夫的一部短篇小说——因为读得太早,已经不记得题目了,只记得小说的主人公有一段时间非常苦恼,老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问他为什么?说因为“找不到主题思想……”原来他在为这个苦恼。这个人似乎有点可笑;但我们也会因此而尊敬他,因为生活中真的有人为“主题思想”的缺失而痛苦!
假如我们把这个人想象成一个作家,即以写作为生的那种人,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他的创作一定遇到了大麻烦。虽然小说不一定将“主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作者失去了生活的信仰还是成问题。这样,伏到案子上心里就会没底。看来一个作家总得有个“主题思想”才行。当然,它可以不必集中在一部作品里,不须如数表达,不必和盘托出——那样就会直白和概念化,当然要不得;但是作为作者,他的一生、他在生活中,总要有真理的追求,这大概是我们所希望的。
说到这里似乎可以明白了,契诃夫笔下那个苦恼的人,病根在于没有自己的“世界观”——这就是他的人生“主题”,它没有了,丢失了,他也就坐卧不安了。这个人多么可爱。
一个人因为找不到“主题思想”而苦闷,乍一看有点不好理解。如果问某个人为什么苦恼,回答是穷困等等现实问题,那倒好理解。但是这个俄罗斯人牵挂的偏偏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这就相当晦涩了。这种痛苦可能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当然契诃夫这里只是一个暗喻,表示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俄罗斯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没有了精神坐标,没有了方向感——就如同这个人一样,一位作家具体进入了写作,心里空荡荡一片茫然,是很成问题的。
原来“主题”对于小说来说不是没有,而是真实存在的,是作为最可宝贵的东西藏在了作者那儿。但它大多数时候并非直接放在一部小说的字面上,而是由创作者随时携带、一直装在心里的。这样,如果我们总是把目光凝聚在具体的作品上,当然就很难找到了。
“主题”藏在作者心里,有时也可能藏在意识深处——那是连作者本人都难以察觉的一个角落。
对世界总的看法
如果回头看一下大陆的那一段文学史,从“文革”前后包括1949年之后的很多作品,“主题”之类往往显得过分直接和明确。社会功利性让作家把“主题”推到了第一线。这是为社会服务的一种需要、一种方式。这种服务本身就要求简洁明快,因为大多数人看不懂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思想,这思想太复杂,作品就没用了。当时强调作品的实用性。所以真正的艺术品在这种情形下是难以产生的。
所以,为了“服务”,为了一种切近的社会功利性,“主题”也就变得非常浅显,一下推到了小说的表面。这样,小说的多种可能性、它的多种诠释空间,都被简化和省略了。那时的小说只能写得浮浅,文学作品应有的那种含蓄性和立体感,都谈不上了。这种伤害对于小说艺术是致命的。
希望小说的思想观念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其实等于承认了作家主观指导思想的存在、以及它的重要性。事实上越是好的作家越是固執的人,他们总要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表达出来,一有机会就会顽强地表达。他们不会是理念世界中的缺席者,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言。不过他们的发言方式不会是简单化的,不会做传声筒——他们的思想是相当深入和阔大的,而不是浮浅和狭隘的。由于长期的不倦的探索,他们走过的是一条相当曲折的道路,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可能一度呈现游离和矛盾、或者某些不确定性;但它存在于作品中的仍然是完美与和谐,是一个生命的真实和自然完整。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概括:比起论文和某些散文,小说的“主题”是以各种方式存在的,它无论是潜隐在深处还是流露在外部,都源自作者的世界观——作者对这个世界的总的看法,一定要在作品里展现出来。也就是说,作家的全部作品会有一个总的主题;同时,他不能停止的写作活动,比如契诃夫笔下的那个人的苦恼,也是在寻找自己的“主题思想”。可见这个工作是长期的、不能间断的,所以他要写个不停。
为了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对自己所生存的这个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的总的认识,他要思索不止。他的看法或者是清晰的,或者是模糊的,但探索是执着的、无休无止的。他的认识会有阶段性的变化,但这改变一定有着自身的轨迹,并非是任意的和突兀的。在这方面,他是质朴和诚实的。他怎样拥抱或拒斥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的全部紧张关系,都表现和概括在所有的文字中了。
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是极其认真的,他在顽强地探索着人生的道路,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
人在不同的生活空间里会有不同的看法,譬如说一个人从大陆来到了香港,面对新的环境就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形成自己的见解。他对社会架构、民主制度、城市建设、自然环境、教育体系等等,都要有一些了解,做出很多具体的判断。这属于空间上的变化。
人在时间里的变化更为显著。比如一个人在前二十年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看法是一个样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又会有新的发现和理解。他甚至会对以前的判断作出相当严厉的否定和批判。这就是不断探索的结果,是对世界总体看法的又一次修正。
一个杰出的作家必然有自己的世界观,有关于人类生存的形而上的思考。这是他整个创作的恒久的主题。具体到某一部作品,可能只是诠释这个主题的一个局部或一个侧面。所以他的每本书常常有所不同,既以新的面貌出现,又不会使我们在阅读中产生巨大的陌生感。我们会发现,他的所有思绪都像小溪一样汇入了大河——这条河流弯弯曲曲,没有中断,没有干涸,一直流淌到人生的终点。
所以中外的作家研究,常常要用很大的篇幅来讨论作家的人生道路、生活经历。这有助于理解作家和作品。一个真实质朴的作家才会是有意义的,因为他的探索是切实有力的、不会中断的、不曾跟着风尚流转的。坚持独立思考是他的本能,是生命的性质。如果反过来跟风追时,那就无足轻重了——这样的作品“主题”裸露,单薄浅近,而且总是变化突兀。因为作者没有什么世界观,对所处的时代也不会较真,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机灵的混世者,哪里会有什么真痛苦,更不会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种顽强的探索力。作家既然无力思想,却要表达自己的“见解”,那就只好跟从潮流,跟从时尚的需要——作品的所谓“主题”在这儿肯定是不难找到的,这是一种概念化的表达,是对于一个时期的强势的附和,是一些时髦的“思想”。在诸种强势当中,市场是最大的强势,潮流是最大的强势。
总而言之,作品的“主题”受制于作家对世界的总的看法。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个杰出的作家往往具有不可思议的顽固性格,这正是生命的品质所决定的。看风使舵的人可以当一个政客或商人,但不会是一个有价值的作家——就具体的作品而言,其表达可能有所不同;但所有的作品,大致都会具有跟风趋时的统一性。
要理解一位杰出的作家,最后只能着眼于他的整个人生——一生都保持了对社会生活、对人性的顽强探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见解、自己的生命轨迹。
他的“大主题”包括了社会的、生命的、美学的、哲学的、历史的……无数个方面,由此保证了每一部作品的思想深度,拥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他面对的是复杂的生命状况,他把一个生命在某个场景里的所有可能都如实地再现,并始终保持了一种诚实和诚恳。这样的表达怎么会像一篇论文那样,推导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它常常是笼罩整个世界的困惑和不安,还有巨大的喜悦——要表述的一切是这么深邃和繁复,所以很难用简单的话语去概括和归纳了。这就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越是杰出的作家作品,其“主题”就越是难以把握——一百个读者会读出一百个“主题”;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会读出不同的“主题”。
奋不顾身的人
研究一下文学史,那些杰出的作家往往是一些奋不顾身的人。这里的“身”包括了小说本身,即写作规范之类,而不仅仅是指身体的“身”。在一种激烈的情感中、在一种大是大非面前,他们也许要忘掉“小说”作法之类,同时也忘掉自己在世俗生活中的安危,站在了“斗争”的第一线,战斗中连个掩体都不挖。
那时候他们的道德判断不仅清楚,而且简明锐利。他们忘记一切地辩论和争执,把自己的见解悉数说出来。这时候作家或者通过人物,或者直接就是他自己,做出一些尖锐深刻的表述。他的思想是裸露无遗的——按一般的“小说作法”来讲,作品的倾向是越隐蔽越好的,只有这样才会留下足够的空间,让读者有多方诠释的余地。从这个角度看,作家的这种忘情言说多少有点犯忌。可奇怪的是他好像把这一切全都忘了,并不忌讳什么。他们凭借更强大的自信力和执着力,从头说起,旁若无人,不受技术以及其他种种约束,甩开所有的羁绊,纵情言说。
这是一些特别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丰富而强大。他们那种忘情的诉说和表述,会形成一种客观的张力、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奇怪的是这非但没有使作品的思想变得浅近和简单,反而更为深刻——深不见底。强烈的主观性走到了一个极端,又化为一种令人惊愕的“客观”——作家忘我言说的同时,已经变成了一尊可以独立欣赏的、无处不在的特殊“人物”,他和小说中的其他情致风物浑然一体,可以任人诠释任人评论了。
可惜这大半是十九世纪以前的事情了,二十世纪以后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中,几乎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文学冒险者了。实际上对于一般的写作者来说,那真的是一种冒险,是不可模仿的。因为说到底这并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不同的生命特质。换句话说,如果不具有那种极其独特的灵魂,不具有那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道德激情和生命自信,最好连试也不要试。那會让人担心,担心变成简单的说教,空洞苍白,最后令人厌倦。看来“说教”要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生命现象,要么就是一种惯于卖弄的恶习。
有人会指出一些现代结构主义作品——他们的作品中有大段作家自己的“言论”,那么这和前边说过的那一类作品有什么区别?它们至少是相类似的吧?其实二者之间的差异很大,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后者仅仅是、或者更多是在形式方面做出的探索,突出的是那种现代的“结构意义”,而不是其他。这种言说表现了一种“复调”和“多声部”,正好用来表达他们对现代世界的怀疑、充满矛盾的心绪,而不是十九世纪的那种孤声决绝——当年那样质朴和冲动的、坚毅的笔调,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时过境迁了。
即便是现代小说中能够纵横捭阖的思想家,他的言说透露出更多的也还是苦涩的自嘲。那大多是闲谈式的、讨论式的,显得冷言细语。作家不是站在辩论席上的人,不是诉讼人和指证者。那种置身旷阔厅堂满脸激动、不顾一切大声言说的人,早就离去了——时代过去了,那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文学创作具有怎样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它在许多时候是很难用“小说作法”一类去概括的,因为这些“作法”讲的只是常规,而最优秀的写作者往往是要突破常规的。我们能够用语言来加以表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道理,更多的内容、它的一些特殊规律,就需要每个写作者在漫长的实践中去把握和感悟了。“文无定法”,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所谈的只是一般的规律性的东西,是从前人的工作中概括出来的,是普遍创作现象的总结。可是所有这些经验都是僵固的,正在进行的劳动才是活鲜的,它会因为不同的写作而不断地发生变化。
说到那些文学史上的“奋不顾身”者,他们当然是极少数,可以称为文学的“异类”。我们不是从技法层面学习他们,而是心灵。可是我们又知道,灵魂和生命特质是无法传授的,它们的确不可以当成技艺来讲解。文学的世界像生命的世界一样广阔,这其中发生什么都是可能的。如果在写作中简单地模仿某一类,绝对地肯定或否定某一类,都有可能是武断和莽撞的。
在小说写作的历史中,有人不太顾忌常规,从所谓的艺术法则来看,似乎是一些逆行者。章法对他们不太管用。我们可以在名著中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奇怪的是这一类作品不仅让读者感到有趣,还令职业作家、那些声名显赫的现代小说家也极为推崇。不同的是一般的读者只会觉得好玩和吸引人,而专业人士看取的则是更内在的东西,表现出职业式的费解和好奇。比如中国传统小说《老残游记》《镜花缘》等,其中的作者所宣示的理念部分,在今天看来不仅裸露,而且还有些粗浅和絮叨;从结构上讲,也常常在不合时宜的地方出现这一类文字——往往是为了引出一段情节,作者就提前宣讲起来,然后举出一些事例来加以说明,证明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小说的骨干部分、一些故事和人物情节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多少有点笨拙,是写论说文的方法。这些例子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十分常见,使人觉得中国过去的作家是极为看重“主题”的,他们不但不忌讳不害怕“主题先行”、不担心作品为某种理念服务,反而还极乐意做一个思想宣示者,时不时地提醒读者注意他的“见解”,唯恐自己发现的那些大道理被人物和情节埋没——这和现代小说理念相去太远了。
按理说这些传统小说一定是失败的,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我们常常被其中的人物和场景所吸引,到最后完全忽略了作者的宣讲。这些宣讲也许只有某些分析小说的人、那些评论者才会注意,而大多数赏读者是不太在乎的。作家一再强调的“思想”和“发现”,他们的见地,在我们今天的读者看来大多是不重要的。更有趣的是,他们的这些理论阐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小说人物以及生活描述脱节的、没有什么紧密关联的。
用现在的文学眼光来看,这些传统小说的写作技法是相当业余的——没有结构方面的匀称感,没有叙述的娴熟和圆通。读中国传统小说,的确会时不时地有这样的感觉。
然而,这些感受并不完全是时代的隔膜造成的,因为同时代的另一些作品,在“小说套路”上就显得更专业一些——可惜这其中的一大部分是通俗作品,在文学价值上反而要低廉许多。比如当时的一些言情武侠小说,单讲结构和叙述就显得匀称多了。由此看来,那些不太在乎小说技法的人、一些似乎是小说行当之外的社会劝喻者,反而能够写出更具文学价值的上乘之作——这些人不是通常的“写手”,不太注重结构情节之类的调度,也没有太多的机心和匠心,反而具有了朴拙敦厚的气息——这恰恰是最为可贵的一种艺术品质。
中国传统是这样,外国的也不例外。比如被现代西方作家越来越推崇的一部长篇小说《白鲸》,就值得后人好好研究。它被后来的专业写作者反复诠释和琢磨——整部书格外有生气,但却不顾章法大写一通,显然不是行家里手做的事情。作者的议论有时很莽撞很冒失,再加上一章章一节节多余的、笨拙的描述,看上去稚嫩得可爱,也单纯得可爱。这种气质不是伪装出来的,而是一种本色。麦尔维尔当过捕鲸手,真的在海上挣扎过困顿过,是海上生活的行家里手——他不是职业作家,没有通常那些职业气。比如他为了显示自己海上生活的博学,就不厌其烦地、细细地写起了网具、帆、桨,写海浪、各种鲸,写熬制鱼油的方法和过程。他的笔下太多捕鲸专业教科书才有的东西,这在专业作家看来是可笑的,大可不必写进小说中。可是麦尔维尔并不这样看。他觉得这也是“海上传奇”的组成部分——既是“传奇”,就要记录,这正是闹市里的人最爱看的。
他的目的既单纯又简单,这在专业作家们看来也很有趣。就是这种泥沙俱下的、不管不顾的野路子,形成了《白鲸》独特的艺术景观。这部书今天看粗粝而又大气,浑然天成,有一股陌生气,是超越一般文学意义之上的罕见杰作。如果仅仅从写作学的意义上看、看它的局部,书中的“败笔”可算太多了。
类似的书还有《堂吉诃德》,这也是一本没有职业气和匠气的小说。作者的书写十分自由,它所赢得的独特气质,使后来在技法上处心积虑的现代作家们心生羡慕。
图解和游戏
作为写作教科书,它告诉我们的往往是一些最基本的原理,即规律性的东西:小说要让主题隐匿起来,一直隐匿到作家自己的心里去;它起码不要像论文那样去论证一种思想、说明一种观念,不能通过人物和场景、也不能通过故事去直接阐明某个道理。不然作品就会变得浅近、概念。的确,作家为了图解一种思想,不遗余力地去做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是很不值得的。
在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小说就曾经这样做过。那时的小说家们忙着图解一种思想,而且这些思想并不是作家自己的。我们知道,世界上即便再伟大的思想,只要不是自己的,那也不能当成个人发现去诠释;而且就算是自己的,也不能在小说中用来图解——无论这种思想多么时髦和多么重要,小说家都不能用来做一部作品的“主题”。小说是一门艺术,它有自己的规律,硬是让小说做一部社会机器上的零部件,是十分短视和浅薄的做法。
可是直到今天,我们要完全避开这条可笑的荒谬之路,也不是那么容易。有人以为今天完全放开了,作家们简直是愿怎么写就怎么写,什么爱啊性啊千奇百怪,上天入地,想象大胆五花八门——一句话,现在的作家自由多了,再也不必为“图解”和“服务”而苦恼了。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也不一定。真实的情况是,小说在这方面一点都不乐观——自觉或不自觉地重蹈覆辙的人仍然很多,他们不过是从图解和服务于一种思想转向了另一种思想。如果说过去的图解和服务是因为受到强调和利诱这雙重力量的话,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强大的物质利诱。这对于小说的危害其实是一样大或者更大的。
表面上看文学的世界潮流走到了今天,早已经远离了强势和权力。小说从二十世纪初就开始写虚无、写荒诞和嬉戏,它嘲弄的就是秩序和权力、虚伪的道德。它不断强化自己的自娱性,无责任无传统无顾忌更无“主题”,什么都可以游戏,已是从未有过的恣意和放松。
可是细细地拆解“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些过程和关节,我们又会心生疑窦,发现它并非那么简单。
现在它仍然在为这个时期的强势服务,仍然是附和与跟从,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法而已——它依旧在“图解”,只是换上了这个时期所需要的“思想”和“主题”。在这个时期,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要通过文学艺术作出表达——一部分写作也正是这样响应的。
人的郁闷、心灵的荒芜,只是时代的一些副产品。打乱一切文化秩序,嘲弄一切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挑战一切宗教精神,最后将所有的意义都归结为物欲。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再没有其他了。作家和其他人一起恍然大悟:这个世界上所谓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正义”是不需要的,“公平”也是扯淡;原来自古至今,对人类的一切道德要求都是精神鸦片,是障眼法,只有利益和物欲等现世享乐才是真正的目的和意义——简单来说,现代商业社会的某些“文学写作”正在走向这样的认知,汇成了这样的一股浊流。
不久前,大约二三十年前,就在同一块地方,还图解和强调着“阶级斗争”的主题——今天只一转身,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换上了另一个主题。
在西方,现代主义将资产阶级典雅的艺术厅堂弄脏了,所以那些利益集团最初并不喜欢它。当年的一些现代绘画想到沙龙里展出都不行,被认为是伤风败俗。大多数民众对一些现代画也看不懂,觉得它们一味胡来而没有什么正经,没有思想,也不健康,是些颓废的玩意儿。这是现代主义最为艰难的时期:两边不讨好。但不久情况就改变了,利益阶层终于发现这种虚无和荒诞颓废可以“为我所用”。尽管虚无和荒诞是源于对物欲主义的绝望和批判,但这些完全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将其轻而易举地导向相反的方向。因为两极相通,二者相距并不遥远。后来最早收购这些荒芜怪诞、确立它们神圣地位的,还是一些大资产者。
这些荒诞和游戏,原本只是反抗资本主义的规则和现存秩序,它的创作者是绝望的、底层的——可惜仅仅是止于绝望,是嘲弄和推倒;再往前走,就走到了思想的对立面、严肃与坚持的对立面,恰恰最宜于投进资产者的天地大玩场,成为物欲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精神指标。
因为大家都在胡闹,都在疯狂地娱乐,谁还有时间心情绷紧。这种放弃和涣散当然是权势阶层乐观其成的。而一旦社会气氛走向严肃的探索,直接的后果就是求诉和反抗。任何一个时代,无论是极权专制还是财阀统治,他们都同样厌恶精神力量的培育。
所以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些权势利益集团一度那么喜欢“解构”。原来那些貌似大胆、疯狂和肮脏的“艺术”,与强势掠夺者在深层上本是一家——一种狼狈为奸的关系、主仆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有时甚至是在不自觉中完成的。在物欲的诱惑下,小说家们开始琢磨怎样改弦易辙,靠近一个时期的主题——这个时期不需要思想,只需要跟从,跟从大的潮流和方向。一场大规模的“图解”就这样形成了,“主题先行”的习惯做法再次风行起来。从表面上看作家们只是在游戏,不拘小节和顽皮荒唐,实际上却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审时度势地加入了物质主义者的大合唱。
任何跟随都是有利可图的。而今与阶级斗争时期的那种思潮从方向上看并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但其内在道理和本质意义却是相同的——它造成的效果、对人的生存和艺术的损伤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写作者放弃自己的探索,其作品的“主题”真的是隐晦了——压根儿就没有;可是他们的风格与内容又融入了整个潮流,水乳交融。这样做并不难,因为他们对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探究之心,一切都无所谓,一切都为了市场、为了卖出。
至此,“主题”到底是什么就慢慢清楚了——它是一个作家对个人、对自己置身的这个世界永不疲惫的探寻过程,是世界观的形成轨迹。
只要这个轨迹存在,他的作品就不会像一摊烂泥一样萎泄在地。
它原来无处不在
如果我们看的是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如《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这样的书,它们从头到尾讲的只是爱、思念、痛苦,似乎只是两个人的世界,一切都很简单——书里并没有什么复杂的、高深的思想啊。是的,它真的只是一个朴素的故事。但我们前面说过,小说的主题不应该是理论推导,不宜装入“通过什么说明了什么”那样的框子里——它的主题和思想是通过语言和形象、通过故事的講述,于默默无察中抵达的。思想不需要如数摆在桌面上,不能堆在那里让我们参观。
我们的阅读,最好还是放松下来,享受作家娓娓动听的讲述。小说家使用的是个人的语言,有一种特别的语调,我们只需要跟住它往前走就好了,去经历一次陶醉。这个过程我们也会在心底生发出一些人生的感慨,一些联想。小说和我们以往听到的那些爱得死去活来的故事不同,传达出的意蕴、表达出的强度和深度都有不同。
如果仅仅是一个故事,那么这样的故事随便让一个人去讲,我们还会同样感动和入迷吗?显然不会。
我们在沉入忘我的境地险些走不出来,对作家强调的意念和思想反而不太觉察。比如男主人公为什么自杀,我们可能只想到强烈的爱恋让他无法忍受——再追究下去,还有对朋友的道德承诺、对所爱一方的诸多顾及……好像还有许多,远远不止如此——作家对如此一个优秀生命的悲恸和惋惜、对他最后选择的思考、选择的全部理由,显然还有无尽深意蕴含着。我们作为读者,如果是更细心的读者,就会从文字中、从一个个场景中,感受这些潜隐的存在——只是我们无法清楚地说个明白,无法把这一切全部条理化。
比如作家书中对一个长工与女东家的深爱,对那两棵菩提树的浓笔重墨,对山河风物极尽情感的描绘,都蕴藏了意义和思想。其中大多是难以直接说出的,而只能在阅读中意会和体味。一般的书评者总是对这部作品给予社会意义上的过分解读,比如什么反封建之类——因为当时的德国是从所谓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于是这种高论就十分盛行。其实我们平心静气地读书、自然而然地欣赏,哪里会有这么尖利和及时的政治发现?这些“思想”不仅不太显著,而且也可以说简直就没有——起码作家没有这样的喻示,没有这样的想法。全书写的就是我们人人都熟悉的人性,是青年男女的爱与被爱;美女遇到少年,少年又遇到无法克服的难题……全部的痛苦、无法解决的矛盾就在这里。这种情形带来的痛苦,不光是封建社会,即便奴隶社会也有,人在这时候的内心反应都是大致相似的。
不同的是本书向我们讲述的故事、男女主人公,完全是歌德式的。一些特别的意味、思绪和倾向,都渗透在一行行文字和词汇中,一切既解释不尽,也没法分离出来。我们所讲的“主题”,如果真的存在,那也绝不是用逻辑思维即能加以概括。它没有那么便捷,比如不可能用一句“反封建”就算了事。要“反封建”也是我们在反,不是歌德和维特所为。
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反封建”的结论,可以做出各种联想和感想——作品一旦问世就开始了独立生长,它可以让每个阅读者从不同的方向欣赏、总结、推敲。如果是一个格外多愁善感的人,一个对大自然充满柔情的人,又会对少年维特最后的归宿——长眠在两棵大菩提树下生发出无限悲伤的同时,产生一种回返自然的神秘和敬畏。每个人由于心情不同,阅历不同,性格不同,各自都会得出自己的一些结论、发出一些慨叹。可见“主题”有无数个,它就散布在字里行间,随处都是;它溶解于整个篇章,化掉了,但是却没有蒸发。
谈到这里,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没有溶解在全部文字中的所谓“主题”,倒有可能是不祥之物,它在许多时候都是可疑的和有害的。
就一部作品而言,作家以个人的思维方式、个人的语言方式讲述故事,这才是主要的。这一切都是不可代替的。它所表达的思想,也正是包含在这其中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是这样,那些看上去饱含妙悟与哲思睿智的书、复杂之极的书也是这样。比如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又是另一个绝好的标本。在这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中,一个犹太知识分子正在经历婚姻的尴尬、朋友的贫穷潦倒和嫉妒、黑社会的敲诈,好多东西搅成了一团。因为它是一个学者写的,主人公又是知识分子,所以字里行间到处都是“思想”。思想的火花在噼噼啪啪爆响,闪烁得频繁刺眼。我们打开书,随便看几页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高深的思想家在讲故事,随处都有深邃的洞察。一个多么复杂的思想的世界,这么纠缠,这么多悖论和辨析!它的质地,和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单纯的爱情小说差距何等巨大。
即便如此,从道理上讲,类似的写法就一定比那些单纯的作品在思想的层面上更为深刻吗?当然未必。这只是两种不同的写法而已。后者局部的思想的闪光,其实也等同于形象,我们甚至可以当故事去读。这一切的背后隐藏和交织的,才是更加复杂的“主题思想”——那是作家整个的人、整个的世界观。
一切都是通过语言抵达的。作家饱满的表述过程,随处都渗透着“主题”的因子。如果我们硬要把它从中提炼出来,哪怕像酿酒那样,一点一点蒸馏的话,大概都很难做到。它蕴含在里面,既不能蒸馏也不能过滤,它就是物质(文字)本身。
我们特别强调作家在生活中的个人探索,强调这种探索要贯彻到底,贯彻到人生的最后一刻——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作家无论在思想的探求上多么曲折,只要是真诚质朴地坚持下来,就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谈写作,谈技术层面的东西,谈到后来会发现,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难以独立存在的——它最终还是要退到后面;而精神和灵魂,它们却会慢慢凸显出来。
所以说,一个道德激情特别强大的作家,一个思想上积极不倦的探索者,终究不太可能是技术上的低能儿;相反,那些嬉戏生活、没有精神追求的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倒是很难拥有出色的艺术表达。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与艺术有关的一切方面,都需要作家的勇气、意志和恒心。
严格讲来,我们今天谈的不是某个技术的单项,而是触及了创作的核心。为什么把它放在这里来讲?因为它其实渗透在语言、故事和人物之中——语言、人物、故事也都是“主题”,因为“主题”就溶解在这些里面。
我们如果这样理解小说的写作,将这些元素能够作统一观,也就有了浑然一体的理解,算是跨到了门槛之内。
一开始讲的时候我们要分开,把语言、人物、故事作为不同的单元,但是到了“主题”这儿,我们就得将它们合在一块儿说了。只有这样,“语言”才算有了生命,“人物”才算有了气息,“情节”也才成为人的行动。
责任编辑 丁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