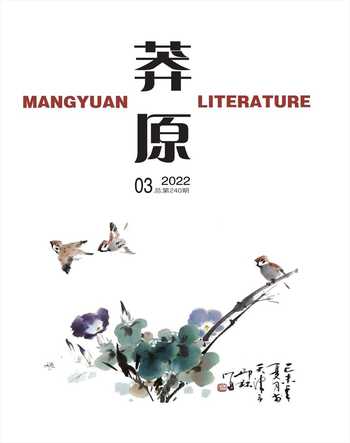乡村絮事
赵成媚
人像一只风筝飘向了城里,心里却有一根线,牢牢地系在故乡的土地上,那从来不曾消失的脚步声,和乡间的方言俚语,沿着这根线激荡过来,在风筝上弹出经久不绝的回音。
喊 話
伯母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心地善良也是满村公认的。
早些年,有乞丐上门乞讨,伯母宁可自家七个孩子嘴里欠点,也会毫不吝啬地盛一碗米饭给乞丐吃,好多次,惹得大孩子叫、小孩子哭。伯母便厉声呵斥:人不是没有活路能出门讨饭?你们一人少吃一口也饿不死!后来,儿女们都长大了,五个儿子个个有出息,两个女儿亭亭玉立,也各自找到了好婆家,这让她和伯父无比自豪,在村里也出了风头。
印象最深的是伯母那种乡村直白式的喊话,还有我三叔的喊话方式也很特别。
喊话,在江淮间的乡村,是寻找丢失东西的一种方式。那次,村里有两家都丢了东西,用不同的喊话去寻找。
初夏的傍晚,暮色熟练地漫进村庄,劳累一天的人们,有的坐在门口乘凉,有的坐在树下抽烟聊天,牲畜家禽们也像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各自入圈钻笼,村庄渐渐安静下来。忽然,就有了伯母喊话的声音:
“给我听好了——谁偷了我家的芦花鸡,现在放出来还不迟!”
伯母那时四十岁左右,她的圆发髻有一撮尾发留在发网外面,向上翘着,如一尾光滑油亮的鸰毛。声音像喇叭,站在村东头讲话,村西头的人都能听到。
当时,伯母刚从田间回来,草帽锄头还没放稳,就开始清点鸡数,却发现少了一只鸡,又数了一遍,还是少一只,再数一遍,发现丢的是一只芦花鸡。她找遍了角角落落也没有发现那只芦花鸡的踪影。在20世纪70年代,物资极度匮乏,农户每家养鸡也有数量限制,一只芦花鸡,差不多是家里的小半个盐罐子呢。
连续喊了两个晚上,芦花鸡还是没有踪影。伯母忍无可忍,吃过晚饭,又一次走出家门开始了喊话——不再是简单的喊话,而是带上喊话道具,她一手拿着菜板,一手拿着菜刀,斩一下菜板,跺一下脚,咬牙切齿地亮开了大嗓门:“你个馋嘴猫啊,你吃我的鸡,我剁了你的头!”
伯母每喊一句,就会有一个急停,随之在地上跺一脚,又斩一下菜板,接着再喊道:“你吃我一块鸡肉,嘴上生一个疔疮——”
村上的孩子们,一个个顾不得咽下嘴里的饭,伸着头看着伯母这奇特的动作,迫切地期待她喊下一句。
伯母又喊道:“你给老娘记着,疔疮没得医,十天放不出一个屁……”
孩子们嘻嘻哈哈地大笑起来。
伯母的脚步跺得通天响,一踩地上一个窝,声音高亢有力,音调抑扬顿挫,前两句甩着长长的尾音,后面一句,喊得满腔怒火义愤填膺,好似深仇大恨一般。
听着伯母喊话,我心里很害怕,倒不是我吃了芦花鸡,而是两天前那只芦花鸡被我撵急了掉进一方藕塘里。原因是它经常吃我家菜园里的菜,那天我撵着它不放,它慌不择路,想飞过池塘逃跑。可是它高估了自己,在飞越池塘的空中失事了。我眼见着它掉进池塘,落在荷叶中间,不断扇动翅膀发出咕咕嘎嘎的求救声……看着芦花鸡在池塘里失魂落魄的样子,我没有理它,很解气地走开了……
我悄悄对母亲说:“叫伯母别喊了,我害怕。”
母亲说:“你又没吃她的鸡,怕什么?”
我说:“我怕黑灯瞎火的,菜刀万一斩到伯母的手指头怎么办?”
母亲忍不住笑了,说:“你个傻丫头,伯母整天剁菜切面,她才不会斩到手指呢。”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起得比哪天都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伯母家后院的池塘边,想看看那只芦花鸡怎么样了。两个堂姐比我起得还早,她们正在用竹竿打捞芦花鸡的尸体。鸡腿脚上缠着很多藕叶草梗,我一时犯了难,犹豫着要不要向两个堂姐坦白我的罪行……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不想这一咽竟是数年。
我们村子很大,三天两头就会有人喊话,但像伯母这种带着道具气急败坏式的喊话,并不多见。
三叔喊话就是另一种风格。
有一次,三叔家丢了一根扁担绳,到了傍晚,他双手背到屁股上,迈着八字步,眼睛顺着街道两边看,像是在自言自语,不急不慢地说:“呔,哪个捡到我家扁担绳喽?噢,旺叔吃饭啊?您吃,您吃。您说扁担绳又没长腿,咋就不见了呢?”
看到沿街有一人吃饭,三叔就同人家打着招呼。
所谓扁担绳,是两条结实的绳子,两米多长,绳子的一头有树杈做的钩子,可以捆扎稻草、棉柴等长禾类东西,是乡下不可或缺的劳动工具,每家都有一两副。
“我那扁担绳好认,两只钩子两个样,一只是枣木做的,一只是榆木做的,绳子呢,是用尼龙绳搓的……噢,五魁婶带孙子啊?这娃长得,虎头虎脑的真可爱。”三叔摸了下小孩的脑袋,继续往前走,边走边说。
“做这副扁担绳可费我大劲了,砍木钩子,差点砍掉我手指头,搓绳子手掌都起泡了……呀,二嫂,白菜炖豆腐啊?好吃,也好看,一清二白的,跟二嫂为人一样。这做人啊,就应该一清二白的,不是自家的东西,就不该昧起,一根扁担绳不值钱,昧下了也发不了财。”三叔一边夸着一边走路,一边还说着自己的事。
“谁捡到了就撂出来哈,不然烧成灰,我也能认出来……”
三叔就这么一边说,一边走,从村东走到村西,又从村西走到村东。
第二天早上,三叔开门时,一眼就看见扁担绳挂在他家门环上。
我家也丢过东西,是一只秃尾巴小黑猪。父母鼓励我用喊话的方式寻找,还答应若找回小黑猪,就为我买个新书包。
有奖品犒赏,我鼓足了勇气,学着三叔慢条斯理又很风趣的风格,也来一次喊话:“老少爷们都听着哈,我家有一只尖嘴秃尾巴小黑猪丢了!捡到的放出来哈,不然养成大牯牛我也能认出来哈……”
当天晚上,我们正准备睡觉,听到有猪拱门的声音,母亲就去开了门——小黑猪果然被我喊回来了。
喊话不知道是从哪个年代开始的,庄户人家经常丢三落四,哪家丢了东西,就会派一个人从村子的一头喊到另一头;喊话的内容各具特色,第一遍,主要告知丢了什么东西、何时何地丢的;喊过了,如果没有找到,还会喊第二遍,主要描述丢失物品的相貌特征;两遍喊过了,还没有找到的话,就会喊一些气愤的话,大多是发泄一下怨气,很少有真正骂人的话。捡到东西的人一般不会据为己有,他们习惯放在家里等人喊话,听到喊话,就会对号入座,然后不声不响地把捡到的东西还回去,从不要失主答谢。当然,也有少数贪财者拒不交出,这时候喊话者就会加上威胁,诅咒和谩骂。喊话能起到相互督促的作用,也有警示效果,所以,失物往往都能找回来。
当然,也有少数失物没有找回,其中无非有几个原因,要么是被邻村路过的人捡走了,要么就是毁损而无法还回了——像伯母家那只芦花鸡,被我撵到池塘里淹死了,也就无法挽回了。
喊冤与赎名誉
中国的乡村分布看似四零五散,其实很有规律,为了便于各种农副产品贸易,方圆十里之内,必会有一个集市——大到农具耕牛,小到针头线脑,基本上应有尽有。
集市,也是收集和传播各种信息的场所。
我们那个村离集市不远,农历逢“四”逢“九”的日子,就是集日,乡下人称为“逢集”。一个月里有六天是集日,我们买卖东西不用跑远路,确实比从乡下来赶集的便利很多。上小学的时候,我还被同学们称之为“半个街上人”,心里有过短暂的优越感。
那时还不兴外出打工,逢集很热闹,赶集的热情也高涨。逢集时,乡亲们会把家里多余的蔬菜、水果、粮食挑到集上卖掉;还有牲畜家禽,泥鳅虾子等等,统统可以到集市上交易;一些手艺人像裁缝、木匠、铁匠、补锅匠、补鞋匠、剃头匠等也都赶热闹挑着担子赶集揽生意。即使没有手艺、也没有买卖要做,人们也喜欢背着双手去赶集,东瞅瞅,西看看,把行情收进心里,或者以赶集为借口到亲戚家吃个饭,喝顿小酒,交流着大道、小道消息,也交流着乡村的情感。
我家住在村子边缘,一大早梳头时,从窗格子里就能看到路上赶集的大人孩子,肩背车拉,潮水一样来赶集。
有一次逢集,二翠妈咣啷咣啷敲打着破脸盆,嘴里在高声喊着什么。我们这些好事的孩子一窝蜂地挤到她跟前,大眼瞪小眼,不知深浅地叽叽喳喳。二翠妈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声音沙哑,平日白皙的脸皮气得发紫,唾沫星子到处乱溅。
二翠悄悄告诉我,她妈前天受了她舅舅和舅妈的委屈。这种亲人之间的纠葛,是没地方讲理的,何况,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二翠妈气极了,就是想乘着逢集日子,凭着“人多正义在,心有公平秤”的想法,把自己的委屈诉给赶集的人听,让大家评评理,解决一时的心头之气。
这种方法在乡村叫喊冤。喊冤一定要有凭有据,如果被对方抓住漏洞,对方会反咬一口,说你坏他名誉,会叫你为他赎名誉。赎名誉,同样也是乘着逢集人多,你敲打着旧脸盆大声喊话,说明事情原委,还得向人家赔礼道歉。所以,喊冤好喊,赎名誉在乡村却是件尴尬的事。
邻村有老两口,开着一个卖针头线脑的乡村小店,店铺在正房,用橱柜隔开,与厨房通着,厨房靠近灶口的墙上掏了一个小洞,一来方便烧灶的人透风凉快,二来方便自家的猫狗在晚间关门后从小洞自行出入。
乡下人把这个洞叫猫洞或狗洞。
有个年轻人打起了小店的坏主意,某天夜里,乘着月黑风高,钻过猫洞潜到店里偷盗。凑巧小店老太太起来夜解,发现家里进贼了,吓得大声惊叫。儿子听见了,顾不得穿鞋,就朝着夺门逃跑的小偷奋力追去。一个跑一个追,追过几条田埂,又追过两个村庄,天色已蒙蒙亮了,小偷眼见要被抓住了,突然转过身子,用手电筒狠狠砸向店家儿子的面部。店家儿子在倒下的瞬间,认出小偷是本村某某的儿子。
小店老太太就去小偷家里质问,说你家儿子偷了我家东西还打伤了我家儿子。没承想,小偷的父亲看到躺在床上装睡的儿子,说,你已经看到了,我儿子在家睡觉,你说他偷你家东西,那他偷了你家什么?捉贼要捉赃,你人赃都没有,凭什么坏了我儿名誉?
小偷父亲反咬一口,要店家为他家儿子赎名誉。
那天也是逢集,店家老太太先是燃放了一串爆竹,引来赶集人的围观,又敲着旧脸盆喊,我对不起某某家儿子!他没偷我家东西!也没打伤我家儿子,是我家儿子看花了眼,让鬼打了,我今天来给他赎名誉……
赶集的人都心知肚明,却也不能说破,只是一味地摇头叹息离开。
诸如此类乡村琐事,眼下差不多都绝迹了——寻物喊话变成了一张纸写的寻物启事;喊冤与赎名誉也已多年不见,乡镇有法庭,专为那些有冤情的人伸张正义,喊冤在乡村只是一种释放内心委屈的方式。
修补茅屋和支锅搭灶
严格来说,修补茅屋、支锅搭灶都属于泥瓦工的手艺,但在乡间,却不像张木匠、李瓦匠、王裁缝这些正规的手艺人,有个响当当的名头;就连补锅匠、补鞋匠、剃头匠这些走村串户的匠人,似乎也比修补茅屋、支锅搭灶这类民间手艺人地位要高一些。
父亲有两件宝贝——木扑和木泥刀。他用这两件宝贝,修着我们家的日子,也修补着左邻右舍乡亲们的清苦岁月。
早年间,乡下人都住草屋,土坯垒墙,屋顶由麦筒、香莆铺成。但时间长了这些草本植物容易腐烂,加上风雨侵袭,如果不及时修补,遇到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漏久了甚至有墙倒屋塌的危险。村里有几户人家,每逢雨季,不是屋檐被拽掉几块草,就是屋脊被掀个精光,好端端的屋子瞬间弄得面目全非。
到这时,父亲就会接到邀请去给人家修房子。
补屋的人家早就和好泥浆,单等父亲到来。父亲腰间束着绳子,把木扑、木泥刀插进背后腰间,裤角处也用细绳扎紧,踩着梯子步步高升,动作麻利又果断。登到屋顶,地面上的人会把一捆捆麦筒梳理好抛给父亲——从地面到屋顶差不多有七八米,父亲竟然能一一接住。偶尔有一捆因用力过度,抛得高了,偏了,眼看就要坠往别处,父亲直起身子,手往空中一捞,还是稳稳地接住了……
看着父亲修好的房子,想着屋里的人再不会经受风雨侵扰,我常常觉得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本领最大的人。
父亲还有一项本领,就是给人支锅搭灶。
20世纪80年代以前,乡村每家都有一大一小两台土灶,用土坯或砖块砌成,烧的是柴草。柴草锅灶最大的好处,就是煮饭能有香脆的锅巴,大灶可以架锅梁,上面蒸几盆菜,下面煮米饭,所谓饭菜一锅熟,既能省时间,又能保温。
锅好支,灶难搭,支锅灶就特别讲究技术。能否出烟顺畅通常是考量匠人的技术指标。烟道不畅,就容易憋烟窝火,更有甚者,火龙就从烟道蹿出烟囱口,屋顶一旦被卷入火舌,一场火灾就在所难免。
父亲每年都要帮村里人家支锅灶,技术也是一流,走东家,到西家,虽是无数次,但一次也没有收过工钱。
到了90年代,草房基本上从乡村消失了,家家都住上了瓦屋,继而又翻建成一座座小楼。锅灶也被煤气灶、电磁炉代替,没有人再来请父亲修补草屋、支锅搭灶了。父亲的木扑和木泥刀、还有那用来支锅搭灶的特制卷尺,都徹底退居二线,成了乡村的民俗文物。
“你们这代人太了啦!”父亲感慨地说。这里的“了”字,应该是“了不起”“了不得”的意思。话外音里,既有感慨,也有无奈。
但每每看到木扑、木泥刀和卷尺,我的脑海中还能浮现出父亲登高补屋、支锅搭灶的情景。
责任编辑 吴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