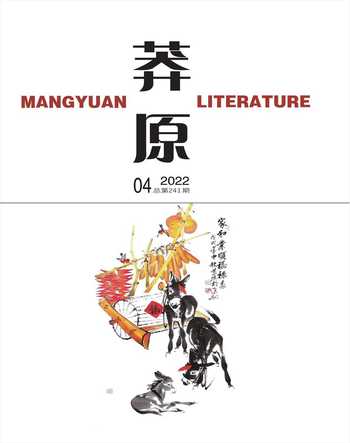东南西北
许攀蕾
最先知道秋天到来的是城北人民公园里那棵梧桐树顶端的一片叶子。它刚睡醒,一个惊心动魄的梦还没来得及回味,就看到秋天赶着一群鸟破空而来。它揉着惺忪的眼,身上的露水汇成一个圆球,沿着它的脊椎欢呼着滑到另一片叶子上,终于确定了这不是另一个惊心动魄的梦,它的脸骤然黄了。秋天金灿灿的鞭子抽到了它的头上,它第一次感觉到疼,不敢相信自己竟能喊出声来,便喊得更大声了。
我正开着三蹦子在人民路上飞驰,我的员工,我唯一的一员大将坐在我的左手边,交警的两辆摩托车紧随其后。我坚信只要跑到人民路尽头的第一中学向右拐,钻进那片民房的小巷子里就能甩掉他们。我循着那个凄厉的喊声看到了那片正在下落的叶子。叶子在从楼房缝隙透过来的阳光里翻转,楼房也跟着翻转。站在早餐摊旁边的巴黎理发店的老板娘穿着睡衣也凑热闹一样横了过来。绿化带出现在我的头顶上,里面的老鼠抱着半根烤肠,惊恐地看着我。以后天空就在脚下了吗?我想着碰撞白云应该不算是违章吧,不自觉笑了起来。大将咧开的大嘴辜负了我的笑容。伴随着一个沉闷的响声,世界又正了回来。一群鸟从我的正上方飞过去,我把脸偏向一边,以防不怀好意者从空中投掷炸弹。
我的运气向来不好。别人让我吃瓜子,我要是半推半就拿一个塞进嘴里,它必定是苦的。平时走路我绝不踩窨井盖。别人踩没事儿,我踩上去,它就有可能张开大嘴把我吞下去,并且极有可能是淤塞了很久的最脏的那一个……
所以,当我的大将背着包裹来到我刚刚开业的快递站点面试时,我在黑板上写下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运气好吗?
他笑嘻嘻地说,我从旅馆出来就捡了五块钱,买的包子还没吃完就看到了你的招工广告,我的运气还不错。
我又接连写下了几个关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团队精神的问题,他在回答的过程中意识到了我的缺陷,说话的嗓门提高了一格,连比画带说,生怕我不明白。我在黑板上告诉他我能听到,他才恢复到了正常音调。
当这个小城的官员学着大城市颁发禁摩限电令时,我才知道他没有驾照。自此以后就成了我们两个一起去取件送件儿,往往是我忙着打包称重,他跟客户谈笑风生,他倒比我还像老板。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比我机灵,我想要是他开车兴许很快就能甩掉后面的交警。
世界没有倒过来,它只是颠了一下屁股又稳稳当当地坐在了那里。颠一下屁股要不了我们的小命,它只压断了两条腿,我的右腿,大将的左腿。
他躺在床上没完没了地哭闹,我正是相亲的年纪,这要是瘸了怎么办?
我给他发信息说,你不会残废,我的断了三节,医生都说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你的才断两节。
他没有看手机,也不看我,他的脑袋在枕头上扭来扭去,双手拍著床板,做戏给我看。
我这可是工伤,你可不能坑我呀。他连老板都不叫了。
我继续给他发信息:放心吧兄弟,我不会坑你的,就算我不治,也要给你治好。
他依然没有看手机。
我也拍着床板,想让他看看我。我在手机上给他发信息:你看手机呀,兄弟,你别喊,你看看你的手机。
他继续喊,你不坑我,我也不会坑你,反正钱你是要赔的,至于多少我们好商量。
赔,你放心吧,砸锅卖铁,我也不会让你白受一场罪的。我把信息发过去,却没听到铃声。我想也许他没带手机,最好是没带,要是在事故中坏掉了,我还要赔他一部手机。
输液管上的苍蝇躁动不安,它们胆小,总是受到惊吓,大呼小叫:护士来了,护士来了,护士成群结队地来了。我向外看,一个护士端着托盘走了过去。
我在大将和苍蝇的吵闹声中昏昏欲睡。
你爸来了,你爸来了,你爸成群结队地来了。我闻到一股烟味,我爸从门外走了进来。
妈妈离开之后,烟成了爸爸的命,成了他的灵魂。以至于我走在大街上看到抽烟的人就像看到爸爸一样嫌弃、亲切、畏惧,一样想上去把他的烟掐掉,在他的脸上亲一口,或者朝他鼻子上来一拳。
大将看到有人进来止住了声音,他咧着嘴看着我爸爸像要哭了。爸爸看了我一眼径直走到大将的床边,低声问,他出声了没有?
2001年夏,妈妈走亲戚的第三天,坐在门槛上刮胡子的爸爸像被蝎子蜇了一样跳起来,手里的镜子掉到地上摔成了几瓣。他骑上自行车直奔十三里路之外的我姥姥家。爸爸后来回忆说,等了三根烟的时间才有人开门。
她人呢,我来接她回家。
谁?她没来,你们吵架了吗?爸爸说老头子的眼神躲躲闪闪。
没有吵架。
爸爸说他在路上的时候就觉得鼻腔里痒痒的,像是有一群细小的虫子在往外爬。爸爸屏住呼吸以为这样就能阻挡它们爬出来,就能把已成事实的事摁回到混沌里。
他绕过挡在面前的老头子往屋里走。老头子跟着他进屋,重新站在我爸的面前。爸爸跟我们说,他盯着我的鼻子看,上嘴唇翘着似笑非笑,奸贼!爸爸总是这么称呼他。爸爸一直都后悔当天没能把他的老巢翻个底朝天。
当爸爸骑着自行车去我二姨家的时候,那撮茸毛已经冒出了头,爸爸转动着眼珠向下看,能看到脸上的这批新居民闪烁着淡金色光泽。
妈妈也不在我二姨家。中午留下吃饭吧。我二姨盯着爸爸的脸说。
他们还有心情吃饭,他妈的,谁都脱不了干系。爸爸对我们说。
那天,爸爸直到天黑才回来,我和妹妹放学后坐在大门的两边,看着阴影顺着邻居家的山墙缓缓往上爬,直到爬过屋顶淹没树梢,颜色一层层地加深。
你妈走了。爸爸说。他身上飘散出一股轻盈的带有淡淡甜味儿的羊臊气。我和妹妹低着头,谁都没说话。
她不要你们了,爸爸又说。我和妹妹交换着眼神,都希望对方能说点什么,或者哭出来,把这件事情翻过去。直到要上床睡觉时,我才透过昏黄的灯光看到妹妹的眼睛里噙着两颗黄豆大小的泪花,无法分辨是因为妈妈不要我们还是因为饥饿,总之这是爸爸渴望看到的两朵泪花。他露出了笑容,开始安慰我们,你们一天没吃饭了吧,他说,别哭了,快,让你哥哥去买点方便面,再买一盒罐头,好不好?我买了东西回来时,妹妹已经不哭了。她正拿着剪刀给爸爸剪耳朵上的毛。那些细密的闪着绸缎光泽的银白色毛发被风扇吹得到处都是,爸爸歪着脑袋生怕被剪到耳朵。
我和妹妹每人吃了一包北京方便面,用筷子剜着分食了一盒牛肉罐头。我觉得妹妹跟我一样没吃饱。这时我们对奶奶的思念多于对妈妈的思念,一直以来都是奶奶照顾我们一家人的起居,她从不会让我们挨饿。奶奶在去世当天还为我们蒸了一锅馒头,她在水井台边清洗面盆时摔了一跤,还没能送到医院就去世了。
爸爸耳朵上的茸毛除之不尽,一夜之间又长了出来,更长,更浓密,顺服地贴在皮肤上。他在院子里打转,不停地用手抹着脸,他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出门,他还幻想把妈妈找回来,这样脸上的毛就会消失。
他躲避着路上的人,人们一看到他的脸就什么都明白了,有些人为了避免尴尬,也躲避着他。到下午我妈妈走了的消息像杨絮一样漫天飞舞,学校里的学生也都知道了,老师站在讲台上,不时地瞟我。
在镇上读初中的姐姐回来之后,对着闷头抽烟的爸爸说,走就走了,有啥大不了的,没女人你还活不了了?爸爸抬起头盯着她,不知道在想什么。姐姐说,要不,找电视台来吧,上电视还有可能找回来。爸爸说,找电视台?那还让不让我活了?还嫌我不够丢人吗?就算我不要脸你弟弟还要成家呢。家里的事一句都不能往外面说,你们都听到没有!爸爸就是这样,他觉得脸面大于一切。
长一层白毛还挺好看的,姐姐看着爸爸说。一只拖鞋飞过来,姐姐跳着脚躲开了。
爸爸问遍了所有亲戚,看谁都可疑。他觉得妈妈的娘家人肯定知道点什么,说不定就是他们合伙窜捣妈妈离开的。
在同一年,住在村子另一头的我大伯关掉了他家的养猪厂。我的大娘得到了某种启示,做起了大仙儿。她烧香拜佛,性情也跟着变了,说话时轻声细语,和蔼可亲,带着一股唱戏的腔调。她有时有烟瘾,每天要抽掉两包烟,跟我爸不相上下;有时又一根烟都不抽。她说她抽烟的时候是土地爷上身,不抽烟的时候则是观音娘娘。我大伯对此深信不疑,全力支持她的事业。我们两家向来没有多少来往。当年兄弟两个分家之后,似乎就再也没有了瓜葛。他们分家从锅碗瓢盆一直分到了老头儿老太太的葬礼。奶奶去世之后,关系就更淡漠了,甚至相互之间还生出了某种敌意。
那天晚上爸爸却拿了一条烟两瓶酒去了大伯家。大娘看到他之后说,没进门的时候就知道是你,你早就应该来了。还能找回来吗?爸爸问。她让爸爸上了香,朝着我爸爸的脸洒了水、喷了烟雾。没走远,她说,在东南。我姥姥家就在我家的东南方。我就知道是老东西搞的鬼,爸爸说,我去要人。大娘说,要是要不回来的,还可能出人命。得让她自己回来。爸爸从她那里领了一道秘法。
爸爸在院子的东南角点燃妈妈的衣服。跪下,他对我们说。他让我们边哭边喊妈妈,要出声又不能被外人听到。那时已经过了十二点,四下里只有衣服和衣服下面的杂草燃烧的声音,火光照亮了邻居的后墙和我们一家四口的脸,妹妹首先哭了出来,喃喃地喊着妈妈。接着是姐姐,我不敢相信她竟然也哭了,脸上挂着两颗琥珀一样的泪珠。爸爸在我后脑勺上拍了一下,哭,他说。我看着皮影一样随着火光抖动的妹妹,流出了泪水。喊,他说。我张张嘴,没发出任何声音。喊妈!爸爸压低声音瞪着我。我还是张着嘴巴,没有发声。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大娘说她的秘法之所以没有灵验就是因为我没有喊。爸爸半信半疑。我觉得就算我没发声,但是姐姐和妹妹出声了呀,就连爸爸也喊了几声妈妈的名字,一定还有别的原因。也许是我们的仪式被墙外的某个人听去了,或者是那些鸟,那些整天站在树上歪着脑袋的贼兮兮的鸟,它们截获了我们发给妈妈的信号。
丢掉语言的包袱,我的世界顿时轻便了很多。我再也不用跟人说话了,就算有人骂我,我也可以默不作声。课堂上也不再提心吊胆怕老师提问,可以肆无忌惮地走神。代价仅仅是忍受一段时间姐姐妹妹与几个同学的白眼和嘲讽。但无论怎样总是会有人嘲笑我的。
爸爸用尽了所有办法,打骂,恐吓,吃药,针灸,都没能让我开口。后来就没再强迫我,但我知道,他像无法接受妈妈离开一样无法接受我成了个哑巴。
在我看电视或者写作业时,他会冷不防地喊我的名字,或者抛出一个问题。我盯着他的脸看,他露出歉疚的笑脸,表示自己忘记了。在我睡着时,他会像壁虎一样贴在墙上,希望能捕捉到我的梦话。某天我发出了一连串的咳嗽,他突然转过头来,哈!他说。他的眼睛里闪着光,似乎终于抓住了我的把柄。
爸爸一直觉得我是装的。他坚信我会背着他讲话唱歌,或者发出其他正常人会发出的声音。他看到我骨折的信息之后,首先想到的是我会不会喊出声来,并借此打破沉默的魔咒。
大将咧着嘴看着我爸爸,不知是被他古怪的相貌吓到了,还是因为疼痛,一时也成了个哑巴。张口结舌,什么也没能说出来。
妈妈离开那年姐姐十四岁,初一没读完就回来接管了整个家,洗衣,做饭,跟爸爸一起或者一个人去田里干活。爸爸说家里只要出我一个大学生就行了。
有人说我妈妈跟隔壁村的一个光棍汉一起去了南方。光棍的哥哥在广东发了财,曾让光棍在老家招过人。他们说妈妈和爸爸都是贪图享受的人早晚会有这一天,他们还说之前就看到过我妈妈坐着光棍汉的面包车到处跑。
爸爸整天待在家里不愿出门,他说村子里没一个好东西,都在看笑话。他浑身都长满了跟脸上一样的白毛,穿不住衣服,每次不得不外出时他都会焦躁不安,回来时又会带着一股怒火,一进门就胡乱扯掉身上的衣服,团成一团丢到床上。他再也没有出去打过牌、喝过酒。让妹妹给他搔痒成了他的新癖好。妹妹也乐意梳理他的毛发,要不然就得帮姐姐干活。
爸爸不停地抽烟,嗑瓜子,每天都要喝下两暖壶开水,嘴唇上常年都长着燎泡。眼药膏的气味儿从他嘴上飘散到每一个角落,若有若无,冷不防就钻进人的鼻子里。整个家都在发炎,在欢笑声中发炎。爸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逗我们发笑,妹妹抚弄着他像在抚弄一只巨大的玩具或者宠物。他发出满足的哼哼声。左右上下轻重快慢,妹妹不耐烦时,就会在他腰上掐一把,别哼!她训斥他。爸爸安静不了一会儿就又哼起来,并抱怨自己是家里最没有地位的人。姐姐在厨房把锅碗瓢盆弄得叮当乱响。姐姐脾气暴躁,像炸雷。我们都怕她。
爸爸只敢使唤我和妹妹给他跑腿,我们身上沾着烟草羊臊消炎药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儿,上学,放学,去小卖部买东西,我们跑得飞快,带着风,到家时心脏像鼓点一样乱跳。我们也怕见人。像两只小羊羔,人们总是这样说。越是这样说我们跑得越快,也就越像小羊羔。
后来我就不愿出门帮他买烟、买瓜子、买饮料,买他突然想到的任何东西了。妹妹看我啥都不干就闹脾气,也不帮他跑腿。爸爸说军令如山倒,妹妹说倒就让它倒。他没办法只能承诺妹妹每跑一次腿就给她五毛钱。
当军令和跑路费都失效时,爸爸就放低姿态,他精于此道,就没人可怜我吗?我还没老就使唤不动你们了吗?他声音柔和,情真意切,没完没了。每当这时妹妹就会狡黠地看着他笑,一块!她说着就扑上去翻爸爸的口袋,两个人扭打成一团。
姐姐看到他们打闹就忍不住要发作。我就是你们的奴隶,她说。她叫爸爸老太爷,叫我大少爷,叫妹妹大小姐。她说,吃饭了大少爷大小姐。她说,更衣了大少爷大小姐。老太爷还有什么需要呀?这时爸爸就会一本正经地说,你姐姐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以后你们都要像孝敬亲娘一样孝敬姐姐。哎哟,我可当不起,我上辈子欠你们的。她说话的神态真像我们的亲娘。
日子就这样过着,直到有一天姐姐说她要去南方打工。她说,你看看街上还有人吗?谁还守着一个穷家呀。爸爸说他考虑考虑。考虑的结果是同意姐姐去打工,但不是去南方,而是去镇上的纺织厂。那里都是老太婆!姐姐不乐意。老太婆又不咬人。爸爸说。
那是2005年,我读初三,成绩不好也不坏,爸爸对我的期望却越来越高。你只有上大学这一条路。他对我说。我有时点点头,有时把书摔到一边,躺到床上用被子蒙住头。
妹妹隔三岔五就从学校跑回家,不是头痛就是肚子痛,她不喜欢学校。爸爸说,不想去就不去,咱们家出一个大学生就行了。
清明节爸爸带我们去坟上烧纸。太阳白白的,像块癣,一会儿就又敷上了黑色的药,开始下雨。蹲在坟前点火的爸爸嘴里念念有词,祈求鬼魂保佑。在纸钱烧尽时他却突然伏在地上,发出了凄厉的哭喊声。另一个世界的爷爷奶奶拿着纸钱,不知如何是好。妹妹被突然的变故吓到了,脸色煞白,冰凉的手指把我的胳膊抓得生疼。我回过神来想去把爸爸拉起来,却被他一把推开。我怔怔地看着他顺着河道向远处跑去。
我和妹妹到家没一会儿,他湿漉漉地回来了,一身泥水,像个疯子。他的耳朵向上长了一倍,尖尖的。额角的头发下面鼓起了两个圆圆的包。
她也走了,一样的贱货。爸爸边脱衣服边说,你们谁要是再来这一出儿,我就杀了你们!他面目狰狞,用皮带抽打着桌子。
爸爸躺在水池里,妹妹拿着刷子给他刷洗,他怒火未消像风箱一样喘气,在三米之外我都能听到咚咚的心跳声,好像一个愤怒的拳头在向外冲击。妹妹把手放在他的胸口上,安抚了好一会儿他才平静下来,缓缓合上眼睛。他背上的毛很厚,已不似原来那么白,微微泛黄。
纺织厂里的人说姐姐是跟一个货车司机一起走的。爸爸没有像找妈妈一样去找姐姐,甚至再也没有提起过她。
我继续上学,妹妹接管了这个家。阴天下雨,他就躺在屋里,抽烟,看电视。天气晴好时,他躺在院子里晒暖,散发出类似厚重棉被的气味。他时不时抖动一下耳朵,驱赶停在上面的苍蝇、牛虻、花大姐。他额头上的犄角也只是漏了一个尖,没有继续生长。
尽管如此,大将还是被我爸的样子吓到了。爸爸对他嘘寒问暖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来。大将不确定我有没有发声,一会儿说我说话了并承诺要赔偿他,一会儿又说我一声都没吭。爸爸看着我,我把脸转向一边,看着门外的走廊。
我感觉到疼时,大将也疼了起来。他对我爸说,我告诉他那里有警察他非要从那里过,我告诉他不要跑,他也不听,非要跑。你说说,三轮车怎么能跑得过摩托车!疼痛占领了我的身体,我的脑子成了没有信号的破旧电视,每一个频道都布满了辛辣的雪花。我不确定大将是否提醒过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开口说了话。
大将一开口便没完没了,他的疼痛通过声音排出体外,闪着金属光泽的音节像庆祝节日的字母气球一样堆积在病房洁白的天花板上。我昏昏沉沉的,直到手术过后才逐渐清醒过来。大将偷偷摸摸拿出手机,我意识到在康复之前他的家人是不会露面了。
爸爸说想跟他父母商量一下出院的事,他说他没有父母。我想幸亏我的腿断了,要不然爸爸会亲自把我的腿打断。他原来就不同意我办什么快递站点。现在他只能把断腿的儿子和断腿的陌生人一起拉到家里去。
别指望我伺候你们,他对我说。这时我想到了妹妹。这些年她在美容院上班,我似乎已经看到她那张堆满笑容和化妆品的脸。
2008年爸爸破天荒主动提出让妹妹跟姑姑一起去广东打工。妹妹不想去广东,她哪都不想去,只想在家梳理爸爸的毛发,给他洗澡,抓虱子。爸爸说他自己也要出去打工,去西北。妹妹噘着嘴,用白眼看我。
她恨我。无论我能否考上大学都需要一大笔钱,用来交学费,或者建房子。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房子却越建越大,看着让人胆怯,过年的时候街上停满了各种款式的汽车,旁边站着从全国各地回来的人。好在我不用说话,不用跟任何人打招呼。
爸爸当真跟着架电线的队伍去了西北,后来他一直把那个地方挂在嘴上,他喜欢那里,那里的风沙雨雪让他感到亲切。妹妹说爸爸偏心,在去广东的车上暗暗发誓再也不回来了。不久之后,跟她在同一个工厂上班的姑姑发现她偷偷谈起了恋爱。
我没有,是他们总缠着我。她说。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姑姑说。妹妹安静了,她说她是被姑姑这句话敲裂的,她说,如今在睡梦中依然能够听到自己开片的声音。我看到了她抿着嘴唇一动不动的画面,好像她一不小心就会有蛋液流出来。她的脸红了,姑姑的脸也跟着红了。她们同时想到了那两个消失的女人。紧接着便想到了遗传,骚,不要脸。她们持续很多天都没说话,直到一天姑姑看到她拿着一件男生的外套,站在路边的台球桌边像拉拉队一样欢呼,姑姑把她揪了出来并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我管不了她,也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姑姑在电话里对我爸说。姑姑在我的脑子里弯了,像个电话,像个翻盖手机,像棵被雪压弯了的纤弱的树苗。
爸爸立刻就买了去广东的车票。被带回家的妹妹情绪只低落了三天,便重新振作起来,以家里唯一见过世面的人自居,对爸爸和偶尔回家的我指指点点,嫌弃一切。
妹妹第二次出去打工时,我已经上了省里的一所专科学校。没有姑姑监护,妹妹很快就给自己找了个隔山隔水隔着方言和肚皮的外地老公。爸爸不開心,但也无可奈何,他只有一个要求——回家里补办一次婚礼。男方的家人也不开心,直到妹妹生下第一个孩子,才让他们一家三口回来。婚礼是爸爸出的钱。妹妹觉得丢人,憋着和男人吵架,酒席过后她连家都没回就和男人一起坐上了返程的车。透过玻璃我看到她噙着泪,咬着牙,定是再次发誓就算死在外面,也不会来了。她恨我呀!那恨在她困苦的心里茁壮生长。她恨我们所有人。那恨是有形的,从她身体里像狼烟一样奔突出来。
三年后她拉着行李箱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虽然一眼就认出来是她,但越看越觉得陌生。她丰满,漂亮,言行举止完全是一个成熟妇人。她长得像妈妈,又像姐姐,只有在她给爸爸梳理毛发时,我才能看到一些妹妹的影子。外地方言的腔调像铁锈一样附着在她的声音上,她不是原来的妹妹了,她是一个由妈妈、姐姐和一个陌生妇女的碎片拼接成的布偶。
妹妹断断续续在镇里的纺织厂上了两年班。之后便学起了美容,她说总有一天要开一家自己的美容院。我和大将的断腿让她的梦想再次延期。爸爸说我们的医药费一大半都是妹妹付的。我想现在她更恨我了,所以在我住院的这些天里她一次都没露面。
村里的柏油路破烂不堪,两个断腿的人,被颠褪了色。大将龇牙咧嘴,大呼小叫,每过一个坑脸色就白一分。我的后背也湿了,额头上的血管突突直跳。
我们到家时妹妹已经把房间收拾好,敞开大门等着我们。可算回来了,她像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一样迎接我们。爸爸把我们背回屋里,妹妹忙着端茶倒水,整理床铺,她进进出出一会儿问大将需不需要调整位置,一会又问我们想吃什么。妹妹身上的香水味在我们头顶打转。大将像是打了鸡血,脸跟猪肝一样红。
妹妹傍晚就回了城里,大将的兴奋却迟迟没有退去。妹妹真漂亮,他看着我笑,不愧是在美容院上班的,妹妹是在美容院上班吧?大将扒着窗户往外看,他嘴里的妹妹比他大八岁。我看着他的黄牙,想扑上去掐死他。
接下来的日子沉闷压抑,大将没日没夜刷视频。我把耳机丢给他,他看都没看一眼。他是货真价实的债主。手机里发出的尖锐的配乐和哄笑,不停地往我耳朵里钻,我的脑袋随时都会像西瓜一样爆炸。
我转让了快递站点,把钱交给大将。希望他能早点离开。他嫌少,我答应他在他能上班之前仍会每月给他发工资。他才勉强把钱收下。他说他也不想待在我家,但他无处可去。
只有妹妹回来时,家里的气氛才会缓和一点。大将不再刷手机,爸爸也不用为做饭发愁。妹妹依然喜欢帮爸爸梳理毛发。爸爸说,十个儿子也抵不上一个女儿。大将躺在床上吃醋。真恶心,他小声嘀咕。
我实在无法忍受每天跟大将待在同一个房间里,就搬进了厨房旁边的杂物间。也许爸爸也不胜其烦。中秋节过后妹妹就没再去上班了,她似乎很享受照顾几个男人,并迷恋上了和大将一起刷手机拍视频。我不知道大将哪一点吸引了她,总之他们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
妹妹换着不同的衣服让大将给她拍视频。大将说她会成为网红,他跟着妹妹改口喊我哥哥,语气里充满戏谑、挑衅的意味。
嬉闹声化作成群结队的蛾子,从被大将霸占了的我的屋子里飞出来。我和爸爸躺在院子里晒暖。你不管管?我用眼神向爸爸传递信息。爸爸抖动着耳朵假装没看见。只有他们闹腾得太过火时,爸爸才喊妹妹出来帮他抓虱子。
断裂的骨头逐渐愈合,大将的父母跟冰冻一起出现了。他们带着媒人和礼物来提亲。以爸爸平静的神态猜测,妹妹应该提前给他透露了消息。大将拄着拐杖迎接他们,好像他是这座房子的主人。
妹妹的第二段婚姻就这样被确定下来。大将当天跟他的父母一起回了家,我顿觉轻松,终于吐出了那团压在胸口的浊气。
腊月初六,一辆花车后面跟着一辆拉着礼炮的小货车把妹妹接走了。妹妹上车前说,好歹这次有个花车。我想总有一天妹妹也会像妈妈和姐姐一样悄无声息地离开。想着大将像爸爸一样长出一身白毛,我险些笑出声来。爸爸跟往常一样坐在那里抽烟,覆满白毛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当天晚上我又听到了大将的声音。我恍恍惚惚的还以为是做梦,他的喊叫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愤怒,他用拳头砸着铁门。
我欠起身子,等爸爸去给他开门。我屏息凝神,爸爸的房间里没有一点动静,他睡着之后,像个死人。我起床,打开院子里的灯,听到大将在门口喊,都死了吗,还是不敢开门?
我打开门,妹妹被大将推了进来。大将的后面还跟着两个脸色阴沉的人,其中一个跟他很像,应该是他的亲戚。妹妹只穿着红色内衣,她披散着头发,眼眶淤青,手掌和裤子都磨破了。我把妹妹拉到身后。
大将指着我的鼻子叫骂,说我们把一个破烂货丢给他。
让白毛老怪出来,让他来认认自己的女儿怀的是谁的种。大将声音洪亮,底气十足,半个村子的人都被他吵醒了。在美容院上班,我看是在妓院上班吧。
我推着妹妹想让她进屋叫爸爸起来,她却蹲在那里哭了起来。
白毛老怪,白毛老怪!大将跳着喊。我想让他冷静下来,他把我的手打到一边,别以为你是哑巴我就不敢打你,他说。
爸爸的房间里有了响动,磕磕碰碰板凳倒地的声音,伴随着玻璃破碎的声音,一头写字台一样壮硕的山羊从窗户里跳出来。它的两支角像两把弯刀,肚子一侧的皮毛上挂着几滴血,它被玻璃划伤了。它直直地注视着大将,白睫毛掩映下的眼球泛着青色的光。大将后退两步愣在了那里,旋即又兴奋起来,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都看到了吧,都看到了吧!
这时我才发现大门外面围满了人。
妹妹蹲坐在地上神态茫然。我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大将在好似呜咽一样的羊叫声中飞了起来。山羊回头看了一眼我和妹妹,没有停留,它踩着井台,奋力一跃跳出了围墙。
大将再次被救护车拉走。三天之后妹妹也走了,她说无论如何孩子都要生下来。我没问她孩子是谁的,也没问她要去哪。紧跟着疫情在全国蔓延开来,妹妹发来了一条信息——把他找回来。
我拿着一条烟两瓶酒去了大娘家。大娘说,没进门的时候我就知道是你来了。我上了香,跪在她的面前,她对我洒了水、喷了烟。还活着,她说,在西北。
从大娘家出来的时候,空中飘着灰烬一样的雪花。拐杖点击路面的声音像水泡隐没在空寂的夜色里。天高地阔,西北的风雪应该会更凛冽,更壮观吧。
责任编辑 丁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