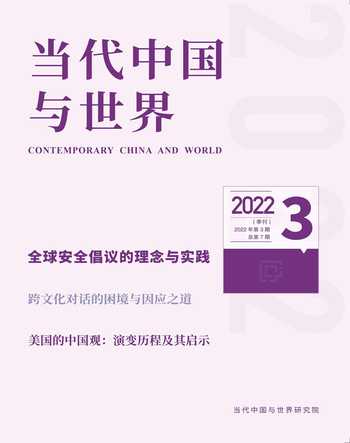跨文化对话的困境与因应之道
【关键词】不平衡性;自我遮蔽;不可避免的误解;理解他人的不理解;范式转换
跨文化交流是全球时代的一个必要话题。以新经济为基础的第一波全球化的退潮与跨文化交流信心的失落有着某种相应性的关联。因此,反思跨文化对话的困境、重新思量因应之道再度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跨文化对话的困境正显示出以普世主义为特征的第一波全球化的巨大局限,重提跨文化对话问题因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方向。跨文化对话较之一般的对话理论有着根本性差异,其呈现出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面向:对于普遍性的悬置,对话的不平衡性,他者他异性的框架性,等等,只有分析清楚其内在的理论层次,才能明白困境产生的缘由以及有效的解决之道。一般而言,在西方语境下提出的跨文化对话理论主要着眼于如何理解他者,如何包容他者;本文试图提出另一种视角,无意建立一种普遍的跨文化对话理论,而是聚焦于特定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自觉地从中国文化角度去展开讨论,并侧重在如何让自己被他者(西方)所理解。事实上,“让他者能理解”已经蕴含了对于他者(西方)的理解,是理解他者的深化。只有让自己能被他者(西方)理解才能形成一种真正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并有可能达成跨文化的思想共识,由此也才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作出实质性贡献。
跨文化对话的困境之一:交流的不平衡性
在理论上,谈起跨文化对话,人们总是倡导跨文化对话之间的平等性、互惠性,无论国家大小,无论文化差异,跨文化对话理论总是以平等为前提,以互惠为结局。作为一种应然原则,这无疑是正确的,得到普遍认可。但在现实中,文化间的对话却存在着某种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不一定直接涉及权力,而是在现代性条件下,各种文化之间的势能有所不同。如果我们着眼于一种有效的跨文化对话,那么就必须充分认识文化间的不平衡性。
在哲学上, 倡导对话的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提出“我与你”的对话哲学,这个“你”有很强的神学意味,布伯强调对话者间的相互性。采取现实主义立场的是黑格尔哲学,在黑格尔式的“主奴辩证法”中,起点上就有着主人与奴隶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主奴”关系可以宽泛地理解为生活中普遍不平衡的一种隐喻。在黑格尔式主奴辩证法中这种不平等在现实中会发生翻转,弱势的一方因为付出更多的劳作而成为优势一方。采取伦理主义立场的则是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在他的“面对他者”的逻辑中,他强调我与他人之间的“非对称性”,他者具有绝对的他异性、不可理解性,而我对于他者负有绝对的伦理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我有着低于他者的伦理姿态。在理论上,任何两个主体之间的对话,在人格上追求一种完全的平等地位。但在现实中,我们对于对话者之间在实力上、在先进性上、在文明程度上、在阶位上、在气质上的不平衡性应该有充分认识。因而在具体分析中,我们将采取一种现实主义态度,充分理解对话中的不平衡性并制定有效的因应策略,只有这样才可能进行有效对话。一种有效的对话,意味着对于他者的敞开,以及对于异质要素的吸纳;否则,看似对话,实则鸡对鸭讲,完全丧失了对话意义。就对话的姿态而言,我们采取一种反向的列维纳斯式立场,不是以自我立场强调他者的绝对他异性,而是以他者立场,强调如何让强势文化理解自己。因此对于跨文化对话的分析就不能简单教条地以对话的平等性为出发点,而是要充分重视对话中那种内在的不平衡性,并制定具体的路线图来加以认真克服。
在中外的跨文化对话中,事实上存在着文化间的差异,存在着实力上的差距,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对话方案,与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有着很大不同。与非洲地区、东亚地区、中东地区、拉丁美洲地区,以及与欧美世界,任何一种跨文化交流在这些地区的展开都是不同的。
在这里我们没有充分的空间来一一展开,本文主要着眼于对中西之间跨文化对话的思考,看看在这一方向上跨文化对话有哪些特点?有哪些目标?以及如何展开相应的思考与应对。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现代化的历程也是一段与西方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历史。这中间远远不止是对话,而是充满了冲突、暴力、斗争甚至是战争。这里不可能全面展开对中西之间关系的分析,仅限于文化层面的对话做一些思考与论述,并且明确只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展开。就与西方的跨文化对话而言,存在着“双重不平衡性”。其一,文化上强势与弱势的不平衡性。西方文化传统自近现代以来有着某种突破性的发展,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军事、技术等各个方面都建立起了世界性的“优势”,借着全球化扩张,西方文化在历史上在世界各地都曾确立起强势地位。因而在与其他文明的跨文化对话中,西方文化内在地具有某种“优越感”,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来说,这是一个具有优势地位的“他者”。这是第一重不平衡。在与西方的跨文化对话时,貌似平等的对话地位并不能掩盖在实际上的这种不平衡性,无视这一点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其二,现代性上普遍与特殊的不平衡性。源自西方文化传统的现代性文化,以理性的面目宰制着现代世界,因而具有很强的普世效应。关于现代世界的普世理论大多由西方社会提出,并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是,在这普世面目的背后依然有着西方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因此在现代世界的环境中,与西方展开文化间的对话,西方世界有着“天然”优势。现代世界之“理”主要源于西方文化传统。于是,我们总以普世理论来理解来自西方的理论,以具体实践和特殊国情来理解自身的传统与现实,这是一个代表着某种“普遍性”的西方文化,这是第二重不平衡。凡此种种在当代对话理论中西方文化都享有一种“话语霸权”。
要建立有效对话,首先就要对这种不平衡性保持敏锐与警惕。在对话的地位、对话的意愿、对话的设置上,毫无疑问要维护相互的平等性。但在现实性上,如果想要寻求一种有效的交流与对话,想真正地拓展现代性的边界,那么就要正视这种不平衡性,努力应因这种不平衡性,找出它的盲点和弱点,使西方文化有可能在这种对话中吸纳“他者”(非西方)的文化要素,从而展现人类文化的丰富性。事实上,居于强势的文化往往会形成诸多盲点,使其看不清对话者的实际状况。要克服这一状况,事实上主要靠弱势一方来完成。就像中国的太极拳,一直强调在力量上要弱于对方一分,只有弱于对方一分才能有效地“听劲”,也就是有效地了解对方的力量,从而把握整体局面。当然在对话中,并不是像太极拳那样是要去打击对方,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一种反向的列维纳斯立场。列维纳斯强调对于强势自我,他者有着绝对的他异性与不可理解性;在这里,他者是一种强势文化,在对话中如何让他者(强势文化)能够理解自己成为首要的任务。面对这种不平衡性,需要通过对强势文化深入探究,才能以有效方式呈现自己,从而让强势文化能够开放自我,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不平衡,削弱强势文化的“优势感”,达成一种真正有效的对话,从而为人类实现一种互惠性。
跨文化对话的困境之二:双重的自我遮蔽
跨文化对话的不平衡性会给弱势文化带来认识上的自我遮蔽。在对话中,外在的平等性反倒会掩盖实质上的不平衡性。对于跨文化对话的深入研究,就是要突破“对话”的应然要求,而进入其实质的状态。当我们无视对话中的不平衡性就容易在既定框架中来进行相互认识,而这样的认识一定是有所遮蔽的。由于与西方跨文化对话的不平衡具有双重性,于是在文化传统与现代性叙事两个层面上都会带来认识上的“遮蔽”,这是跨文化对话的又一重困境。
首先是显性的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自我遮蔽。“对话”常常预设了双方差异。认识到相互差异,因而有动力去寻求一种促进相互认识的对话。对于“对话”而言,“差异”是在先性的。那么如何去认知这种差异呢?最自然的就是一种“比较”。“对话”是双方主体的交流,“比较”可以是单方面的“客观”认识,真正的“对话”就是要防止单方面认知所造成的偏差。但现实中“对话”里的自我遮蔽也常常是由这种“比较”所造成。“第一重遮蔽”就来自于这种“比较”,“比较”本身会是一种陷阱。比如,中西绘画的比较,一般人们总会说,在绘画上,西方绘画传统强调焦点透视,中国绘画传统则是一种散点透视。“散点透视”概念本身是德国学者的发明,用以凸显中西绘画的差异。在这种论述中,看似强调中西文化间的“差异”。其实,只要用“透视”去理解中国绘画就已经是一种遮蔽。西方艺术传统追求“模仿”,“透视法”可说是模仿艺术的最高境界。中国绘画传统从一开始就讲究“气韵生动”,追求以形写神,重在绘画神韵。中西绘画完全是在不同“框架”中展开的,中国绘画从来就不用“透视法”来衡量。由此可见,用“透视法”作为衡量标准,看似可以作出鲜明区分,实质上只是强势文化的一种表达。当我们不能彻底反思这种“比较”方法时,由于对话的不平衡性就会造成自己在理解上的自我遮蔽。
其次是隐形上现代性叙事所导致的自我遮蔽。根据韦伯的理论,现代性叙事在西方有一个“祛魅化”和“理性化”的过程,因而现代性理论具有普世性特征。西方社会也有一个古今变迁的过程。就哲学而言,从17世纪西方近代哲学到当代哲学理论,在叙事上,西方文化传统越来越隐藏到“现代性”面目背后,越来越抹掉西方文化传统的痕迹,而显示其理性论述的特点。从历史上看,现代世界毫无疑问首先是在西方社会中确立的,以致西方社会自身在坚持某种“现代”理念时,也常常“遗忘”了这种理念有着“西方”的根源;因而许多“现代”理念在西方社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一现代性前提下,貌似跨文化的对话,其实有一层在先的自我遮蔽。比如自由主义有很强的基督教新教传统的渊源,但人们一般更多地会以现代“普世”眼光来看待自由主义,没有意识到这种“普世价值”背后很可能需要一种“西方”文化传统的支撑。以这种“现代性”眼光来推进跨文化对话时,就会形成认知上的另一种自我遮蔽,看不清自身传统与现代世界的结构性张力。
由双方对话不平衡性带来西方在对话框架上的优势地位,这种框架性优势在文化差异与现代性叙事两个层面上都会造成(中国文化)自我认识上的遮蔽。这种“自我遮蔽”势必影响跨文化对话的有效展开。基于这种框架性遮蔽的对话并非一种真正对话,而是一种假借“对话”形式的“独白”。当我们不能认识到“框架性差别”时,任何一种文化上“厘清”差别的工作,都只是一种更深层的自我遮蔽。
跨文化对话的困境之三:“误解”的必然性基于与西方跨文化对话的“双重不平衡性”,以及由此造成认知上的“自我遮蔽”,跨文化对话之间必然存在着“误解”现象。也就是说,尽管有貌似对话的举措,本质上却是一种相互“误解”,尤其是自己被他者(西方)所误解。与西方的跨文化对话并不是从纯粹陌生者开始的,一如当年利玛窦来到中国,东西方首次在思想层面展开对话,那时是完全的陌生,即便如此还是建立起了相互理解的基础。
今天再谈“对话”并非凭空而起,而是在已有基础上的推进。这既是“对话”的基础,但也有可能是“误解”的原因。在跨文化对话中,如何防止“误解”,让他者理解自己成为“对话”的首要任务。
在这种“不平衡”且有可能“自我遮蔽”的对话中,要使对方理解自己,首先需要了解他人产生“误解”的原因。就一般状况而言,弗朗西斯·培根曾分析过人们在认识中会出现理解偏差的原因:就人类而言,人总是有自己的自然偏向,偏好自己能够接受的,偏好自己的感觉,偏好自己的意志等,他称之为“种族假象”;就每个人而言,人都会受制于自己教育背景,受制于家庭状况以及认知的水平,他称之为“洞穴假象”;就人们相互交流而言,人会受制于语言的模糊性以及理解中的模棱两可,他称之为“市场假象”;就人的世界观而言,人们会身陷各自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并从这种理论出发去理解其他人,他称之为“剧场假象”。当然,培根并没有提出“跨文化”理解,会出现哪些“假象”,会有哪种误解?对培根来说,只有消除“假象”才能真正被理解,但对于伽达默尔来说,也许在“理解”中的“误解”是必然的。当然,伽达默尔是在生存论意义上来讲的,任何理解都是在“先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于两位哲学家的思想,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跨文化对话中“误解”是如何产生的。
相比一般的理解理论而言,跨文化对话中的“理解”有着更大的难度与挑战性。就一般的相互关系而言,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中人们常说“己所欲而施于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则强调“将心比心”,事实上这样的论述都预设了相同的文化环境。在相同的世界观和相似的价值观中,“己所欲而施于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能够成立的,“将心比心”也是有效的。但是,在不同文化传统中,世界观之间的差异就会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己所欲而施于人”就可能是一种“压迫”,而“将心比心”也会造成一种巨大误解。
在跨文化背景下,对于他者的理解,不是就事论事的简单化理解,首要的是理解对方文化的世界观。较之同一文化内部的对话,跨文化对话的最大困难就在于要彻底理解对方的世界观,理解对方的“框架性理念”。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世界观,有自身理解社会、历史与世界的“整体性框架”。跨文化对话不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对话,而是两种理解世界方式之间的对话,明白这一点尤为重要。
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理解这一点,那么“误解”就会是必然的。基于培根所讲的种种假象,在真正完成有效的对话之前,对话者一定会基于他的“洞穴”对你有一种“先见”。比如就哲学而言,在西方语境下,对于“哲学”有其固定模式,甚至专指源起古希腊的哲学。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就透露出这样一种“先见”。在黑格尔看来:“在孔子与他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只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能找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能找到,可能还要更好些,这是些毫无出色之处的东西。”对于黑格尔的这种评价首先不是表示一种“义愤”,而是需要了解基于什么样的“先见”,黑格尔会作出这种的“评价”。
尽管有伽达默尔对于“误解”的辩解,基于黑格尔对于哲学的总体性看法,基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预设,孔子在《论语》中的形象不被理解为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家是很正常的。但黑格尔对于孔子的评价仍反映出西方哲学对于中国思想传统的“误解”。今天充满赤裸裸文化偏见的话也许不会再说出来,但就具体问题而言,在西方学术框架下,一旦形成某种认识论、方法论,这些范式本身常常成为某种非反思前提,成为天经地义的坐标。在这个前提下,任何非西方的思想、方法、路径要闯进来,在他们原有的框架下也会被“接纳”,但这不是一种真正的“接纳”,而是一种基于“误解”的接纳。对于真正有效的对话来说,我们需要了解这种“误解”产生的缘由,纠正这种“误解”无疑是跨文化对话的目的所在。
还是举哲学这个例子,为什么对非西方哲学的“误解”那么深入骨髓?怀特海曾说过:西方2000多年的哲学就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注解。尽管前苏格拉底哲学中有各种流派,毕达哥拉斯派、元素派、原子论派、赫拉克利特哲学等等,就像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但并不是每一种哲学都在西方思想传统中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只是“巴门尼德- 柏拉图”的哲学框架,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儒家与道家”框架。与西方进行对话时,相比语言上的流利,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他们的思想框架。各自框架不同,对话中又有强势弱势的不平衡性,那么黑格尔就很难去理解孔子。而要纠正黑格尔就必须了解其自身所处的框架,以及孔子所处的框架。在现代社会,与西方的跨文化对话因双重的不平衡性导致了双重自我遮蔽,因此在理解上就会叠加相互的“误解”。跨文化对话首先意味着我们之间的框架性理念是不同的,对话的不平衡性,会强化优势方以自己框架来理解他人,同时又使弱势方加重自我遮蔽;凡此种种注定了在与西方的跨文化对话中“误解”的必然性。
破解之道一:以“去蔽”的方式认识自己
面对与西方跨文化对话的三大困境,如何因应成为推进一种有效对话的首要条件。破解对话的不平衡性首先需要“认识自我”。一般人们认为,对话的目标正在于去理解他者,为什么首先要认识自己呢?事实上,在这种不平衡的对话中,如果对作为对话者的自己不能有正确认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对话。因此推进对话的过程也是一个超越自我遮蔽的过程,是一个“去蔽”的过程。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才有可能避免对方的“误解”,才有可能使他者理解自己。
认识自己并不容易。任何一种自我理解都需要某种理论框架来做支撑。还是拿中国哲学来做例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常会在“中国哲学”论述中,看到“朴素的什么主义”“自发的什么精神”“直观的什么观念”等——总之,给人“低一等”的印象。即便是以推进中国哲学发展的新儒家,当冯友兰以新实在主义来构建中国哲学框架时,当牟宗三以主体论来推进心性儒家的思想时,这样的一种中国哲学依然是“自我遮蔽”的。无论实在论还是主体论都是西方哲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哲学框架。在这里,西方哲学不是以“他者”而是以某种“普遍面目”出现的,这严重制约了我们对于“中国哲学”的自我认知。
近代以来,如何来认识中国哲学呢?学界称之为“反向格义”。i 这是由胡适、冯友兰等开创的路径,主要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认识、理解与解说中国哲学,比如用西方哲学中的共相殊相问题来理解“理一分殊”的说法。事实上,冯友兰曾明确地说“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这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把中国思想“选而述之”的做法正是现代中国人不能正确自我认识的原因。
认识自己的关键是要有符合自身状态的“整体性框架”。就西方哲学而言,他们的哲学2000 多年尽管千变万化,但始终以“巴门尼德- 柏拉图”的哲学为主轴,以“存在”为起点,以“范畴”展开为其发展方式。根据他们对“存在”的界定,“存在”是永恒的、不变的,西方哲学传统就从这个“不变”的存在为起点来理解“变化”的可感世界。若同样以这种方式来理解中国思想传统就会形成自我认识的各种遮蔽,同时也会造成他人的各种“误解”。对话中的“误解”首先来自弱势一方的自我遮蔽。
正确的自我认知是对话的首要条件。就中国思想传统而言,不能以西方的存在论为框架,而是要以周易的“生生之谓易”为理解世界的整体性框架。需要从根本上了解哪些哲学思想为这个文明提供了框架性思想,而哪些哲学家只是提供了某些具体思想的可能性。只有真正懂得一种自己思想的“框架性结构”,才算是真正认识自己。
因此,对话的有效性,正来自于对自己有正确认知,这种认知来自对自我的整体性框架有清醒意识。笔者在德国教书时,曾有个来自希伯来大学的学生,主修哲学+ 物理专业,他有非常标准的科学思维框架,以这种方式,他一方面对于周易的演绎性有极大兴趣,另一方面同样以物理学标准对周易系统提出质疑。从现代科学思维框架去理解周易自然会产生许多疑问,“周易”系统也“经不住”科学的拷问,但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的思维方式与生存经验,它揭示了中国人思考世界的某些特点。对于这种“框架性差异”的敏感在帮助我们形成正确的自我认识的同时,也更能与他者形成有效的对话。
这似乎是一种“以中释中”的方式,比如中国人读《中庸》一定会觉得很有道理,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成长起来。汉语中很多说法都来自于《中庸》,《中庸》中的成语、习语渗透在汉语之中,它们会以语言方式规范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深陷其中却不知其所以然。如果我们的解释只是重复孔子讲过什么或孟子讲过什么,那么就不能完成对于传统思想的一种自我证成,我们只是发现我们日常思维的来源而已。真正的自我认识需要在现代世界中,以理性的方式完成一种自我证成,这是跨文化对话中面对他者的一种伦理责任。使自己不仅知道其来源,还在理论上理解其所以然。只有这样,才能让他者真正理解自己。他人理解自己首先在于正确的自我认识。
破解之道二:努力理解他人的不理解
在跨文化对话不平衡的前提下,处于弱势方的对话者,若希望对方能够完全理解自己,首先需要对自己有正确认识,其次需要努力去理解对方,理解他者(西方)。这种理解不是在自己框架中去理解他人,而是需要在他人思想框架中去理解他者,理解的标志正在于能理解他人的不理解。
就理解他者而言有两个层次:一是在具体语境中理解他者,这尚是一种浅层次的理解;二是不仅理解对方的具体语境,更理解对方说出这话背后的框架性理念。只有在这两个层面都理解对方,也即在对方的思想脉络与思想框架中都理解他者,才算是一种真正的理解而非“误解”。只要有同情心,有共情能力,理解他者的具体处境似乎还比较容易,但要理解他者的总体性框架就非常艰难;但这对处于跨文化对话的对话者来说又是必须的。伽德默尔曾说,对他者开放就意味着要接受反对我自己的某些东西。其实在跨文化对话中,要接受的还不仅仅是反对我的“某些东西”,而是要接受反对我的“某种框架”,所以接受他者并不那么容易,对于强势文化来说,弱势文化的框架性理念正是他的盲点。
对于弱势文化来说,这一盲点正是他的突破点。由于“去蔽”而正确认识自我的弱势文化,在“去蔽”中恰恰也完成了对于他者(西方)的真正理解,完成了对于他者(西方)所以产生“误解”的分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他者(西方)进一步的理解还意味着理解他的不理解。正因为你懂得他的思想框架,所以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你的思想在他的思想框架中会走形,会扭曲;理解为什么你的思想会被他所“误解”。只有理解了他者的框架性思想,才能理解他们的不理解,否则永远处于一种相互的隔阂。
在理解他者的不理解中,还要警惕一种貌似接纳的不理解。在现代世界,“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态度,让更多声音进入西方社会的公共平台似乎也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做法,这看上去颇有些“百花齐放”的感觉。但很多时候所谓“多元化”态度并不在意如何去真正理解不同的声音。不同声音只是以不同的声音存在在那里而已,至于这种“不同声音”究竟是什么,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究竟与主流声音如何相协调,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因此“多元”在这里常常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符号,在貌似接纳中依然是不理解,依然是一种拒斥。
当你最终理解了他人的不理解时,也可以说,你在跨文化对话中建立起了自己的认知“优势”。从而完成了某种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翻转”。从弱势的一方变成优势的一方。这是因为你不仅要认识自己,还要理解他者;不仅理解他者,而且理解他者对于自己的不理解;甚至是在所谓的接纳中辨识出其中的不理解。只有完成对话中的这些关键步骤,在接下去的跨文化对话中,你才有可能使对方真正地理解自己。
破解之道三:因应他者(西方)的框架来进行自我叙述
在跨文化对话中,人们往往急于讲出自己的故事。但讲好自己故事是远远不够的,让人听懂才是最关键的。在这个意义上,要讲好中国哲学,乃至讲好中国故事,前提是要让听故事的人听得懂;只有理解对话者的视域,你才有可能在他的理解视野中讲好你的故事。故事成功与否并不在于你的故事是否精彩,重要的是因应他的框架,你讲解的故事是否有效。
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跨文化对话的双方都各有其主体性,因此跨文化对话需要对中西文化的根本性框架有“双重”敏感性。一个讲解成功的故事并不是要把自己故事塞进对方的框架。如果是这样,得到的依然是一种“误解”。比如在讲授中国哲学的西方课堂上,要让西方学生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概念有深切体会,就需要把他们从自身框架中拉出来,同时借助这种思想框架来做某种“相应性的对比”,一种基于“框架性理念”的对比工作。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却是跨文化对话中比较有效的举措。举例来说,“亲亲”在中国哲学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仁者,人也,亲亲为大”。j 在中国哲学中如此重要的概念,在西方哲学中却付之阙如。如何让西方学者理解“亲亲”的概念,不是将“亲亲”置于西方哲学的框架之中,但需要“迂回”西方哲学。古希腊哲学中有Eros,是关于男女之间情爱的概念,有Philia,是关于“友爱”的概念,还有基督教中关于“圣爱”的Agape。无论是把“亲亲”之爱直接置于与“Eros”的比较,还是把“ 亲亲” 置于“Philia” 之中或“Agape” 之中,“亲亲”都显得无足轻重而不被理解。但如果理解了Eros、Philia 以及Agape 在它们各自理论框架中的枢纽地位,那么虽然在西方哲学中没有对应的“亲亲”概念,但借助于或者“迂回于”西方的哲学框架,理解这些情感性概念在西方哲学框架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还是完全可以把“亲亲”在中国哲学框架中的地位与作用讲清楚的。
在这个案例中,“亲亲”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概念,要让西方人能理解这样一个概念,就必须“迂回”到他们自己的思想传统中,在他们自己的框架结构中找到相应概念。这些表达情感性的词都是一种根基性的概念,在各自文化中都是“爱”的原型。虽然渊源不同,特点不同,是以“情爱”为原型,以“友爱”为原型,以“圣爱”为原型,还是以“亲亲”之爱为原型,但在整体性结构中所起作用却是类似的,在这个结构中起到凝聚的作用,对于切近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都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源初力量。基于这些不同的源初概念,中西哲学会发展出不同的思想体系,但它们的基础性的地位却是相似的。在这种对话关系中,需要“迂回”西方自己的思想框架,在相应框架中找到对应点。虽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西方哲学中也没有“亲亲”概念,但是借助于这种结构性的对应关系,还是可以把“亲亲”的故事讲明白。这里的难度在于借助于或者说是迂回于西方的立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前提是熟悉西方的框架,这样才能让对方理解自己的观点。
破解之道四:实现理解框架的“范式转换”
在跨文化对话中具有挑战性的,不是让他者仅仅听到你的声音,重要的是要理解这种声音,而理解这种声音就意味着要懂得其背后的框架性理念。因此,对话的关键并不在于建构某种“多元”的体系,让他者声音有存在空间,重要的是要充分意识到他者有自身主体性,有自身逻辑,有自身的整体性框架。
在跨文化对话中,最终要实现的是如何帮助他者超越自己框架来理解另一种文化存在的合理性。理解问题的框架常常是潜在的、隐性的,甚至是潜意识的,在自以为放下时依然会起着重重的阻碍作用。只有当对话的每一方都深切地理解自身的根基性内容,并保持空间去努力理解对话方的框架性理念时,才会迎来一个真正的对话时代。
真正的对话与虚假的对话的区别就在于对“他者”的“合理性”是否有充分的把握。虚假的对话往往也显示出对来自“他者”概念的欢迎,但“他者”常常被淹没在陌生性下,只是作为他异性被欣赏。对话者需要真正跳出自己的框架,有能力去理解另一种思想框架。一如赵汀阳教授对于“天下”概念所作的论证k,这种论证成功与否并不在于是否能将其纳入西方的概念系统,而在于借着这个概念能否牵引出理解“天下”的另一种思想框架。让他者(西方)不仅能面对这个概念本身,而且理解支撑起这个概念的框架性结构。这意味着自己不仅知道对于他者而言什么是新概念,还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说明这个概念所在的整体性思想框架。事实上,就中国文化传统本身而言,完全有这种重新阐释的能力。郑玄与朱熹对于儒家经典的诠释完全不同,但各有其整体的合理性。这说明中国思想传统从来不墨守成规,而是敢于面对时代的诉求,给予传统命题以新的“合理性”。在现代社会,一种文明如果依然葆有生命力,就一定有能力让生活在另一种文明中的人得以理解。跨文化对话并不是纯粹的双向并进,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我们是有能力突破自身边界,在不懂得中国文化传统的人面前,把中国思想的道理讲明白,把其背后的逻辑讲清楚,把承载其思想的框架展现出来。因此,就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而言,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对话者负有更重、更大的责任,其既需要懂得西方的方式,又能以现代方式阐释自身传统,从而在跨文化对话中推动那种不平衡性实现转化。
中国文化传统讲究“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只有以一种“诚恳”态度面对跨文化对话,才能“明了”对话的复杂性;只有对复杂世界有透彻“明了”,才能以“诚恳”态度面对对话者的疑惑与质疑。在他人的疑惑与质疑中,才更清楚自身的所长与所短。
在跨文化对话中,需要言说“中国故事”。看似言说,更重要的是一种倾听;也是一种理解,理解他人的不理解。只有理解他者的不理解,才能客观评价自己,才能更好地言说自己。在跨文化对话中,需要展示自己的“所长”。但只有理解他人长处,才更懂得自己的宝贵之处。自己“所长”并不是通过贬低他人获得的;自己“所短”,也只有在“对话”中才更加清晰。在人类文明中,并不存在某家独“长”,某家独“优”,而是各擅所“长”,各苦其“短”,这才是跨文化对话的真义与动力所在。真正的交流与对话,不是自炫“高明”,不是价值输出,不是形象宣传,而是在相互尊重与欣赏中,在互惠互利中推进人类的共同福祉。
作者简介 孙向晨,复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