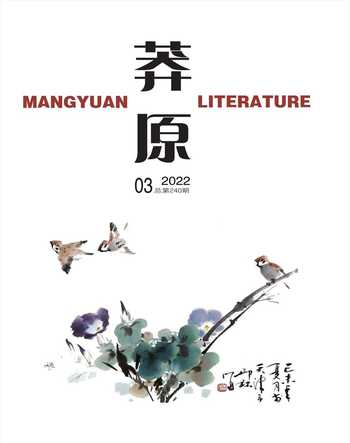遗嘱
侯发山
林平匆匆回到老家,父亲已躺在了草铺上,直挺挺的,没了气息。
其实,三叔在电话里就告诉他父亲已经不在了。当时,他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心说父亲终于不受罪了。想到此,心头一个激灵,自己怎么会有这种念头?难道父亲在世时过得并不如意?难道自己是个不孝之子?林平摇摇头。
院子里有不少人,认识的,不认识的,脸色一律凝重,肃穆。看到林平,有的点点头,有的对一下眼神,算是打了招呼。林平知道,他们是来帮忙的。在乡下,无论哪家有红白事,不用主家叫,乡亲们都会主动前来帮忙。什么是乡情?这就是乡情。林平感到一丝温暖,同时也感到不安和歉疚,平时乡亲们有事,父亲给他打电话,他总说忙,从没有回来过,都是父亲去应酬。难道说自己真的忙?想想,也不全是,有时候也是能够回来的。
三叔紧走两步迎上前来,抖抖索索摸出烟包,掏一支给林平,林平摆摆手谢绝了。三叔便自己叼在嘴里,拿出火机点上了。林平搓搓手,感到很不好意思,应该自己给三叔掏烟,给大伙儿掏烟,这是最起码的礼节。
三叔使劲吸了一口,缓缓吐出,看看林平身后,问,就你一个人回来了?三叔的口气里,有责备的意思。
林平赶忙解释,说儿子上午考试,下午老婆带儿子一起回来。
人已经没气了,不差这一时半会儿。三叔的表情漠然。
林平不知该怎么接三叔的话,他扭头看到父亲身上盖着一条褪了色的旧床单,下意识地皱了下眉头。
三叔歉疚地说,家里找遍了,能拿出来的就这条床单了。
三叔并不是林平的亲叔,老邻居,赶着辈分叫的。人家跑前跑后,感激还来不及,咋会怪罪人家呢?要怪只能怪自己。这么多年,他从未关心过父亲的穿衣打扮、铺的盖的。印象中,记得只给父亲买过一顶帽子,一件棉衣。林平走上前去,抖着手缓缓揭开了父亲身上的床单。尽管他有心理准备,心里还是颤了一下。他从未认真端详过父亲。不是没时间,是从未真正关心过父亲。此刻,他仔细打量着父亲,觉得那张脸熟悉而又陌生。父亲已经被人净了面,一改往日胡子拉碴的形象,颧骨高耸,眼睛紧闭,嘴巴微微张着,似乎还有话要说。
林平用手抚了一下父亲的嘴唇,试图把嘴合上,但父亲的嘴巴依然固执地张着。乡下有个说法,人死之后,如果嘴巴合不拢,就是有事要交代,且是很重要的事。爹,您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哦,我能猜测到您想说的话,好好工作,公家的便宜不能占;别打乐乐,他还是个孩子;对待玉梅要好,一日夫妻百日恩,要相互体谅;别太俭省,身体要紧……其实,这都是父亲平时絮叨的话。每次父亲絮叨时,林平就会打断父亲,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爹,您絮不絮啊?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父亲会嘿嘿一笑,讪讪地闭上嘴巴。
爹,您为什么不写点只言片语留给我呢?刚有这想法,林平马上觉得有点苛责父亲了。在城里,也只有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才会写遗嘱,乡下人,哪个写过遗嘱?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常年不捏笔,字写得歪歪扭扭像蚯蚓,哪好意思丢人现眼?
林平收回心思,看到父亲身上穿着簇新的送老衣,用手捻了捻,回头看了三叔一眼。
三叔叹口气,说,你爹早就置下了,都放在床头的箱子里……他去赶集,隔山岔五就捎回来一件,说是哪天突然走了,省得你忙不过來。
三婶捅了捅林平,悄声说,小平,哭啊。
办丧事,要的就是哭声,如果没有哭声,不是子嗣不旺,就是儿孙不孝,这会让外人笑话的。林平没有兄弟姊妹,他不哭没人会哭的。他腿一软跪在地上,张了张嘴,却怎么也哭不出来。
三叔似乎猜到了林平的心思,蹲下来,说,你爹没受一点罪,头天晚上睡下第二天就没醒过来……积德行善了,才会有这样的福分。唉,也活了七十多岁,是喜丧,不用哭。
三叔说不用哭,反倒勾起了林平的伤心事,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母亲死得早,是父亲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拉扯大的。为了供林平上学,农忙时,父亲黑天白日在地里劳作,农闲时,父亲走村串巷捡破烂。好在林平学习刻苦,成绩也好,从小学到中学,一直读到大学;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接下来,结婚,生子,买房子……他本想接父亲进城跟自己住在一起,让老人家安度晚年,可父亲说在城里住不惯。其实,林平知道,父亲是舍不得离开老家,舍不得几十年的东邻西舍,舍不得那几亩土地,更怕年老毛病多,怕乡下人不会说话,不懂规矩,惹得媳妇和邻居不待见。林平也就没再勉强,平时打个电话问候一下,逢年过节回家看望一下。父亲身体很好,是个种庄稼的好手,春种秋收、犁地扬场样样精通。上个月父亲还打电话,说豆角、茄子都长成了;鸡蛋也攒了一罐,让他回去拿……怎么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说走就走了呢?
父亲在村里口碑很好,每次赶集,自己舍不得买口水喝,却要捎一些水果糖,进村见人就分,不管大人小孩,不管你爱吃不爱吃,每人两颗……谁家有个大小事,不用来请,他就跑去了。时间一长,村里的红白事,都是父亲主持——主家有多少客,该买多少菜,啥季节有啥菜,啥菜该买啥菜不该买,哪一样买多少斤,父亲心里一琢磨就有了。不管你是有钱人家,还是没钱人家,都能给你铺排圆满,滴水不漏,既让客人满意,也给主家撑足了面子……
林平每次回家,父亲又是让他捎菜又是让他带面,说都是自己种的,也没上化肥,干净;林平给父亲零花钱,父亲也不要,说他在家种着粮食,有吃有喝,花不着……想起父亲的点点滴滴,林平眼里的泪越聚越多,哭声也越来越大。
没有人去拉林平,任由林平哭泣。这时候就该哭,不哭反而说不过去。
在林平哭的时候,三叔安排前来帮忙的人,谁去挖坟墓,谁去请阴阳先生,谁去借桌椅板凳,谁去垒灶台,谁去采购菜……办一场丧事需要很多细节,一点安排不到就要出纰漏。
等把一切安排停当,三叔才从灵前拉起林平,说,入土为安,还是议议咋办后事吧。
林平怔了一下,说,三叔,我没经过这事,您做主办吧。
哦,我倒忘了。三叔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说,你爹都铺排好了,你再看看,有啥补充的没有。
林平接过一看,字迹写得歪歪扭扭,但一笔一画都很认真:
小平,我的饭量越来越少了,我不敢去上医院,到了医院,钱就不当钱用了。再说,我的病我知道,花钱也治不好。知道你忙,也没给你打电话。
我感觉日子不多了,还是把丧事考虑一下吧,省得到时你着急。你又没办过这事,不知道咋弄。白布,孙男弟女远亲近邻都算上,每人一身孝衣,得80米,去镇东街老张的布店里买,那里最便宜;茔地我请人看好了,西凹咱家那块簸箕地,柿树正下方;响器用靠山屯的,记住,他们要价高,你得跟他们还还价,1000块就中,咱村都用这家响器,都是这个价钱;豆腐100斤,不能少,用石门沟老刘家的豆腐,吃着好吃,价钱不高,斤数也够;大肉80斤,要肥的……小平,按我说的办,不能俭省,不能小气,不然乡亲们会捣你的脊梁筋。
对了,还有一件事得给你说明,咱不欠人家的账,人家也不欠咱的账……
父亲在走前就把丧事的一切事宜安排好了。在父亲眼里,林平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啥事都得父亲操心……想到这里,林平又流泪了。
他暗自算了算,父亲这个丧礼下来,需要两万多。可是,这笔钱从哪里来呢?林平的工资每月4200块,玉梅在超市打工,每月1200块,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六千块。房子的月供,还有水电费,燃气费,物业费,一家三口的花销,礼尚往来的应酬……不到六千块的收入,平时花钱都是一分一厘算着花的。
可是,在农村,不管穷富,丧事一定要办得体体面面,排排场场,因为这是死者最后一件事了。换言之,既是对死者的尊重,也是给活人长面子。况且,父亲在遗嘱里写得清清楚楚——“不能俭省,不能小气,不然乡亲们会捣你的脊梁筋”!
林平掏出手机,开始给老板打电话,问能不能先预支半年工资。
话没说完,三叔就夺了林平的电话,随手甩给他一个鼓囊囊的方便面袋子。那袋子原本是有图案的,现在图案都看不清了,看来已经有些年头了。
林平狐疑地接过来,打开一看,都是皱巴巴的钱,各种面值都有,除了百元、五十元的大钞,还有十块、二十的零钱,最小的竟有几毛的硬币。
三叔说,已经数过了,两万八千七百六
十五元四角。
林平的手在颤抖,方便面袋子在颤抖,他的声音也在颤抖,三叔,这……
三叔嘆了口气,说,在你爹枕头下发现的,跟这张条子在一起。
“啪嗒”一声,袋子掉到地上,如同砸在林平的心上,好疼,好疼。他咧开嘴呜嗬呜嗬地哭开了,越哭声音越响亮,越哭声音越悲痛。
责任编辑 申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