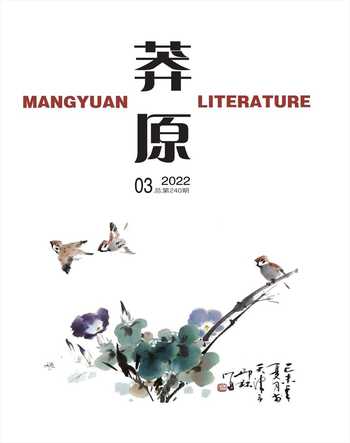失踪在1947
胡炎
1947年一个阒寂的秋夜,大耳朵踩着霜白的月光向村外走去。在村头的老槐树下,他回过头望了望家的方向。
望不到家,那三间瓦房同所有的村舍都淹没在了诡谲的月光里。邻居赵来顺家的疤瘌狗用特有的破锣音梦呓似的叫了两声,丝毫没有惊扰每一扇窗里酣沉的呼吸。大耳朵靠着树干站了一会儿,月光把他的两个耳朵剪影出硕大的轮廓。他似乎陷入了短暂的恍惚,甚至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叹息。
树枝上夜宿的麻雀从梦中醒来,不安地抖了抖翅子。大耳朵激灵了一下,便接着向前走去,越过田垄,穿过丛密的小树林,爬上了斗折蛇行的山道。月光冰凉,照着他脸上缓缓淌下的泪水……
多年后,大耳朵秋夜出走的情景依旧萦回在柳眉儿的梦幻里。她确信那天晚上大耳朵是含泪离开的,他在无边无际的夜色中不停地回头,就像一场身不由己的梦游。他被月光裹胁,走向了未知的远方。柳眉儿想,如果不是中了邪,他怎么舍得抛下年迈的父亲和刚刚半岁的儿子,当然,还有柳眉儿——四邻八乡的人都说:“大耳朵可真是好福气,娶了个比花还好看的女子哟!”
然而,大耳朵终究还是走了,在那个秋月高悬的深夜,无声无息地远去,然后彻底消失了。
在此后的时光中,柳眉儿常想:我的大耳朵到底去哪儿了呢?
这个疑问贯穿了她的一生,成为她后来三十余年苦苦寻找的谜底。她问过赵来顺,可赵来顺蜷缩在破烂的黑袄里,揉着惺忪的醉眼说,那晚他喝了半瓶苞谷烧,睡得死沉。她又向全村的人打听,同样没有一个人知道大耳朵的下落。她甚至在恍惚中问过赵来顺家的疤瘌狗,她说狗啊,大耳朵平日里待你多好,怕你饿着,省下半块馍都尽着你吃。你和大耳朵最亲,一定知道他去哪儿了对吧?听不懂人话的疤瘌狗只是无精打采地吠了两声,便趴在墙根下打盹去了。后来,她几乎把能走到的地方全部走过了一遍,这样就几乎走完了她的一生。
当柳眉儿再也迈不动双腿的时候,儿子盼归就成了她唯一的希望。她在熹微的晨光中对儿子说:“盼归,你该去找你的爸爸了。”她在石榴树摇下的碎月中对儿子说:“盼归,打听到你爸爸的消息了吗?”然而,盼归用一成不变的沉默和摇头,让她的失望在星移斗转中成为绝望。
柳眉儿佝偻着腰,虚弱地对着一个雾霭沉沉的黄昏说:
“大耳朵,你这个浑货,你是被旋风刮走了吗?”
其实,我多次试图告诉柳眉儿关于大耳朵的下落。除了我,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大耳朵的下落。在漫长的黑夜里,我悄悄地对柳眉儿说,跟我走吧,我带你去找大耳朵。但她毫无反应,只有眼角微微晃动的泪水倏地滑入暗夜。我叹了口气,觉得她日渐增多的白发和皱纹刺痛了我,甚至连她纤弱的呼吸都像刀刃抹过我的脖颈。我说,你这是何苦呢?大耳朵走得那么决绝,他没有回过一次头,没有流过一滴眼泪,这么绝情的男人值得你一生寻他、等他、盼他吗?
柳眉儿似乎听到了,猛地坐起来,看着我,尖叫了一声:
“大耳朵!”
她当然没听到,她只是无数次地在梦中遇见了她的大耳朵。即使在她老态龙钟的时候,梦里的大耳朵依旧是年轻时的样子。嚯,他可真帅,高挑个,宽肩细腰,鼻直口阔,尤其那两只威风凛凛的大耳朵,被日光映得赤红剔透。她捣着碎步追上去,嘴里叫着:“大耳
朵,你这个冤家啊……”但是,辽阔的夜色铺天盖地降下来,大耳朵在冰凉的月光中转眼便不见了,只有那条骨瘦如柴的疤瘌狗匍匐在老槐树下,吐着暗红色的舌头,可怜巴巴地望着她。
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人,就是大耳朵。作为柳眉儿的亲人,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像一朵花儿一天天褪色,慢慢枯萎,寂然凋零,我怎能不心痛?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不是大耳朵,又是谁呢?
我说,大耳朵,你怎么那么狠心呢?
大耳朵坐在一块石头上,傻愣愣地看着天,不说话。
我说,那么漂亮的小媳妇,你就没有一点怜香惜玉?
大耳朵瞧了我一眼,低下头,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大耳朵。
我说,你拍拍屁股走了,让柳眉儿苦了一辈子,你心里怎么过得去?
大耳朵叹息了一声,开始发狠地揪自己的耳垂。他应该自惭形秽,他欠柳眉儿太多了,他拿什么去偿还这个女人的一生呢?
我说,你好好想想,当年你走时,你的儿子还在襁褓里。他连你的样子都没有记住,就失去了父亲。你可真是铁石心肠,好好一个女人,辛辛苦苦拉扯着孩子,还给儿子起名叫“盼归”。一辈子没有改嫁,一辈子孤苦无依,一辈子受尽磨难,一辈子就这么毁了……
大耳朵把耳垂掐出了血痕,两行泪无声滑落。半晌,他向着遥远的天际喃喃道:
“我对不住柳眉儿,她是个好女人,好女人……”
柳眉儿和盼歸出现在潘教授的家中,是在1992年的夏天。那时潘教授正坐在阳台上,翻阅着一叠厚厚的资料。他没有想到家里会突然出现两个不速之客。67岁的柳眉儿看上去像一个极度衰弱的耄耋老人,被盼归搀扶着,颤颤巍巍地来到了潘教授的面前。还没等潘教授开口,柳眉儿就双手合十说:
“教授,求你帮我找个人吧!”
在这个燠热的夏日,党史专家潘教授和柳眉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到了后来,潘教授竟然落泪了。当然,年逾八旬的潘教授本身就是一个爱动感情的人。
“大耳朵当年出走前有没有什么迹象?”潘教授问,他试图从遥远的岁月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那或许是通向谜底的线索。
柳眉儿想了想,说,在大耳朵失踪的三天前,他对她说,家里地里也没有多少活了,你和孩子回娘家耍耍吧,不少日子没有回去了。他还说,别急着回来,在那儿住上一宿两宿的,好好和娘家人热呵热呵。
“我怎么没有想到,他这是有意把我支开呀!”柳眉儿老泪纵横,似乎为自己当初的愚钝懊悔不已。
潘教授说:“还有吗?”
柳眉儿用枯黄的手抹了抹眼窝,眼神倏忽空洞下来,茫然地摇着头说:“没有了,等我回来,就再也见不着他了,一辈子也见不着他了……”
潘教授沉吟了一刻,他总觉得有什么细节被忽略了:“把你找过的地方都给我说一
说,越详细越好。”
柳眉儿如数家珍,县里、市里、省里的民政部门都去过了,亲戚邻居、田间地头、荒村古道、陵园墓地……能找的地方全找了,哪里也没有大耳朵的踪迹,倒是有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言,在大耳朵出走后的几年里沸沸扬扬。
“都是些什么传言?”潘教授扶了下老花镜,问。
柳眉儿突然陷入了沉默,仿佛那些传言还像毒蜂一样在她的生命里飞舞。
一直低头不语的盼归搓了搓手,终于说话了。潘教授注意到,这个木讷汉子的手有些发抖。
盼归说,当年父亲失踪后不久,有关他的传言就在村里传播开了。有人说他当了土匪;有人说他八成是到蒋介石的队伍里当了兵,后来逃到了台湾;还有人言之凿凿地说,他并未去臺湾,而是在一次战斗中成了俘虏……至于是死是活,没人能说得清。
“这不是没可能。”潘教授拧着眉头,沉思一会儿说。
“不!”柳眉儿突然愤怒了,她站起来,枯瘪的两腮剧烈地痉挛着。“大耳朵是个好人,他怎么会去当土匪?他怎么可能跟老蒋?他一定是冲撞了不干净的东西,鬼迷心窍,把自己给弄丢了……”
潘教授对柳眉儿如此激烈的反应始料未及,他有些尴尬,一时不知所措。呆愣了一刻,赔着笑说:“别激动,大妹子,坐下慢慢说。”
柳眉儿不坐,全身都在战栗。她瞪着潘教授,好像这个她费尽千辛万苦打听到的“活菩萨”突然间成了她的敌人。他怎么可以随口胡说呢?他不老是宣称“不能让烈士的鲜血白流”吗?大耳朵就算当兵,那也一定是共产党的兵,一定是的。
“你放心,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寻找大耳朵。”潘教授说。
柳眉儿扬起拐棍,坚决地截断了潘教授的话:“不用你费心了,他死了!”
潘教授哑口无言,他看着柳眉儿转过身,狠狠地捣着拐棍,穿过卧室、客厅,拉开门走了出去,下台阶的时候,她脚下一绊,差点跌倒在地。盼归急忙扶住她,回头歉疚地看了一眼潘教授,嘴唇翕动着,却没有说出一个字来。
“他死了!”柳眉儿又厉声说,声音像折断的兵刃,在回旋的楼梯间猛烈跳荡。
我知道,这绝对不是柳眉儿的真心话。她希望大耳朵活着,她一辈子都相信大耳朵活着。很多时候,她坐在山脚下的河边,痴痴地望着水波里晃动的太阳和白云,仿佛大耳朵会突然从里边跳出来。
在大耳朵没有离去的日子里,他们曾经多次来到这里。她在青石板上洗衣,手中的棒槌击打出清脆的回声,五彩的泡沫顺流而下。大耳朵呢,忽然从水里一个猛子钻出来,身边溅起巨大的水花,手里举着一条活蹦乱跳的白鲢鱼,晶亮的水珠从他硕大的耳廓上一串串滴落……对呀,大耳朵一定是在河里捉鱼呢,没准还能抓到一条“火头”,他说过,这鱼最补身子了。
在秋天的玉米田里,站着一个个用来吓唬麻雀的草人。柳眉儿坐在田埂上,呼吸着玉米的清香,眼里的草人忽然就走过来了,在她愣神的时候,那草人摘下头上的草帘子,冲她憨憨地笑起来。大耳朵,你这个坏家伙,你装作草人故意吓我呢,把我的魂都吓掉了……在后来的岁月里,大耳朵会从羊群里跑出来,从山崖下飞上来,从树上的老鸹窝里跳下来,从麦秸垛里钻出来,身上、头上挂满了淡黄色的秸秆……他就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躲在岁月的某一处和她捉迷藏呢。
大耳朵呀,我等着你哩。春天,柳眉儿对着柳树说。柳丝在春风中摇曳,多像自己年轻时那一头乌亮的秀发啊。可是,柳树一年年绿着,自己的头发却白了。
大耳朵呀,回来吧,我不怪你。夏天,柳眉儿对着远处的大山说。大山在蒸腾的烟岚里像是迷迷糊糊睡着了,大耳朵想必也睡着了吧。她得把他唤醒,他睡得实在太久了。
大耳朵呀,看看咱的盼归吧,你瞧瞧,他长得多像你呀。秋天,柳眉儿对着村头的老槐树说。老槐树一声不吭,可它当年一定看到大耳朵往哪儿去了,它怎么就不托个梦呢?
大耳朵呀,就算你嫌弃我了,和别的女人过上日子了,我也不恨你,你就给我捎个信,说你活得好好的,我就知足了。冬天,柳眉儿对着雪花说。她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似乎看到大耳朵立了功,成了大英雄,那身军装穿在身上,要多英武有多英武。这是她最想看到的,我的大耳朵有出息,是全家的荣光呢,爹要是知道你成了大英雄,九泉之下也要大笑着喝上几碗苞谷烧吧。自然,大英雄就该有更好的女人,我知道配不上你,我就指望盼归有个好父亲,也能跟着你光光彩彩的……
对于柳眉儿来说,大耳朵是她此生唯一的念想,或者说,大耳朵就是她的一生。
多年来,我骂过多少次大耳朵,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每一次疼痛的时候,我就会把大耳朵叫到跟前,恨不得揪着他的耳朵扇几个大耳刮子。
我说,大耳朵,你真该给柳眉儿下跪。
大耳朵不语,他摸摸自己的膝盖,那两个膝盖好像生了锈,不会弯曲了。
我说,你只顾一个人东游西逛,逍遥自在,可柳眉儿为了你差点把命都丢了,你算个什么玩意!
大耳朵说,我不是玩意。
我说,回去吧,陪陪柳眉儿。
大耳朵说,我没脸回去了。
我说,你当然没脸,不光没脸,你还没种,否则当年赵来顺欺负柳眉儿的时候,你就该上去一拳头把那个家伙砸个满脸开花!
大耳朵叹息了一声,无地自容,默默地离开了。
赵来顺企图霸占柳眉儿,是大耳朵出走后不久的事。这个弱柳扶风般的女子,脸白得像嫩藕,眼美得像弯月,额前的刘海齐整整的,一笑俩酒窝,天上的仙女也没她好看吧。柳眉儿曾经多次出现在赵来顺的梦里,过去除了多偷看那么几眼,别的事连想都不敢想,那绝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如今不同了,柳眉儿再不是从前的柳眉儿了,男人失踪了;她公爹老货郎大雪天摔了一跤,头磕在石头上,也一命呜呼了——这世上,再没人护着柳眉儿了。
赵来顺打着酒嗝,趔趔趄趄来到柳眉儿家,说:“妹子,跟我过吧。”
柳眉儿不买他的账:“做梦。”
赵来顺冷笑着:“大耳朵投了老蒋,你还挑剔个啥?臭婆娘!”
柳眉儿青着脸,从地上抓起一块砖头:
“你滚!”
赵来顺贼心不死,在盼归的啼哭声中压在了柳眉儿的身上,用满是酒臭的嘴没鼻子没眼地亲着这个天仙般的女人。他扒开了柳眉儿的红肚兜,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荡魂摄魄的乳房。这让他发疯,他拼命撕扯柳眉儿的裤子,就在他要得逞的时候,他的小腿肚却突然被什么狠狠地咬了一口……
后来,柳眉儿才知道救她的是那条疤瘌狗。然而,她知道的时候,疤瘌狗已经躺在了血泊里,赵来顺用一把锄头敲碎了它的天灵盖。柳眉儿泪如泉涌,这狗到底是通人性的,它记着大耳朵的好,它是舍了命来报恩呢。
柳眉儿多次想到过死,她在河边想过,在山崖上想过,在老槐树下也想过。可她放不下盼归,更放不下大耳朵。她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找到大耳朵的,或者,大耳朵终有一天会回来的。他活着,一定活着。她又一遍遍地对盼归说:
“你爸爸是个好人,咱们一定要活着找到你爸爸!”
其实我知道,柳眉儿也诅咒过大耳朵。当那些传言甚嚣尘上的时候,她有过濒临崩溃的时候,她几乎相信了,此时,她就会在心里发狠地说:“他死了,他早就死了!”可转眼之间,她就推翻了自己:“不,大耳朵活着,肯定活着,坏人才该死,大耳朵那么好一个人,他怎么会死呢?”
这样的纠结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那边有人回到附近的村子省亲了。柳眉儿踩着脆薄的月光,就像踩着脆薄的希望在夜色里寻过去,一遍遍地向那人描绘着大耳朵的形象,一遍遍地问:“你见过我家大耳朵吗?”
那人努力想了一会儿,摇摇头。
“回去帮我打听打听吧,说不定他就在台湾呢。”
那人说,好的好的,一定一定。
可是,一去便杳无音讯。柳眉儿无数次遥望着想象中的台湾岛,好像看到大耳朵正站在海边,海浪撞击着他脚下的礁石。他一点都不嫌老,浓密的黑发在风中飘扬,耳朵还是那么浑圆舒展,两只眼睛含着泪花,忧伤的眼神穿过茫茫烟波,望着家乡,望着她,望着儿子盼归……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柳眉儿才意识到,她已不在乎大耳朵当年的去向了,她在乎的只有一个:大耳朵活着,他要活着,必须活着。
潘教授在1997年开始了生命中最后一次远行。尽管在此前的五年里,他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大耳朵的消息。但是1997年秋季的一天,他从一些零零星星的史料和语焉不详的传闻中捕捉到了几次不大有名的战役,确有部分烈士的遗骨至今没有找到。如果大耳朵果真是烈士,他就不能让他永远沉默在历史里,这是他的良心和天职;即便大耳朵什么都不是,他还是想试一试,柳眉儿的愤怒一直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他希望给柳眉儿一个交代,给扑朔迷离的历史一个交代……
潘教授沿着若隐若现的线索,在多个烈士陵园搜索,最终还是一无所获,因为这些陵园柳眉儿和盼归早就去过了。潘教授站在一座山头上极目四望,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惆怅。他一辈子都在历史中游走,解开了一个又一个谜团,而此时,他发现还有那么多的谜在岁月中雾一般飘荡。
在接下去的搜寻中,潘教授恍然觉得自己正走在1947年的秋夜里,月光滔滔,四野溟濛。他甚至听到了大耳朵的脚步声,听到了远方隐约传来的枪炮声……他下意识地紧追了几步,在一阵强烈的眩晕中倏然跌倒在了历史深处,再也回不去了。
柳眉儿是在潘教授去世后的第二天死的。她并不知道潘教授倒在了寻找大耳朵的路上。死前的头一晚,柳眉儿做了一个很长的梦。这个梦颇为奇怪,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各种萦绕不绝的声音——疤瘌狗虚弱的叫声,老槐树的枝叶在风中巨大的沙沙声,草叶在脚下扑倒的窸窣声,山路上的砾石滚下山崖的嗒嗒声,河流的呜咽和秋虫的嘶鸣,甚至听到了流星划过天际的尖啸声……到了后来,她听到一个女人忽柔忽怒的争吵声:“他活着——他死了——他活着——他死了——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柳眉儿觉得,这声音就是她的一生。她用双脚走完了生命里的白昼和黑夜,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有那种声音带着她的灵魂继续前行……
现在,我可以告诉柳眉儿所有的真相了,因为我们已经处于同一个世界。
当年,大耳朵出走的原因其实只有三个字:“干大事!”老货郎总觉得这个儿子眼高手低,好高骛远,骂他是个“不成器的东西”。而大耳朵对老货郎这个一身风尘走街串巷的行当颇为不屑,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干一件大事给这个鼠目寸光的老货郎瞧瞧。但他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他只知道那件大事绝对不会在这个古旧的村落,它应该在外面,在远方,在一个很大的地方……
这个念头一俟滋生便势不可挡,终于让大耳朵血脉偾张,义无反顾。在那个岑寂的秋夜,他奔向了省城的方向。
后来,像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大耳朵在半路上遇到了战争,遇到了部队。他确定了自己要干一件比天还大的事,尽管有些道理他还不能完全懂得,但他知道,这件事远远超越了他的家、他的村子,事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新的天下……还有什么比这事更大呢?
柳眉儿可以安心了,大耳朵加入的是共产党的部队。他在战斗中牺牲,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喋血疆场。但他参军完全是个意外,既没有告诉村里,也没有通过区上,县里自然更不可能有他的档案。历史,总有一些人不会留下名字。大耳朵对此并不在意,让他无法释怀的,只有柳眉儿和在屈辱中长大的盼归。幼时阴差阳错的遭遇,注定了盼归卑微而怯懦的一生。好在,盼归的儿子与盼归性格迥异,颇有些大耳朵当年的风采。他和赵来顺的孙子在同一年入伍,一个做了海军,一个做了空军。当然,这是后话。
但我最终还是沉默了,柳眉儿太累了,真的太累了,还是让她好好睡去吧,忘掉一切,包括大耳朵,也包括赵来顺。
多年后的一天,赵来顺提着礼品,瘦骨嶙峋地出现在了柳眉儿的门口。柳眉儿当时惊呆了。赵来顺说,他早就想来了,只是没有勇气。柳眉儿的牙咬出了咯咯的响声:“你来干啥?”赵来顺焦黄着脸,说:“我来认罪。”柳眉儿拿拐棍指着他:“你给我滚!”赵来顺把礼品放在地上,两腿开始慢慢弯下去,说:“我就想给你下个跪,死的时候也好落个心安。”但柳眉儿没给他这个机会,狠狠地把门撞上了。她不知道赵来顺究竟有没有跪下,就是跪了她也不可能原谅他,当年这个可怜的光棍汉为何一夜间变成了恶鬼,她百思不得其解。她断然不会接受他的道歉,她要让他带着罪孽下地狱,为自己的良心还债。后来,被酒精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赵来顺是跪着死去的。不用问,这个跪是送给柳眉儿的。
人死了,所有的恩怨都该随之了结。我希望柳眉儿醒来的时候,灵魂澄澈得像一泓白云游弋的清水。那样,她就又是当年未嫁时山花般的模样。我会一直默默守着她,就像这么多年,我无数次悄悄地潜入她的梦境。她当然认不出我,因为我早已在炮弹的轰鸣中化为云烟,再也没有了那两只让她刻骨铭心的大耳朵。
在那片荒芜的土地上,我们的手臂伸展成树,须发长成蒿草,葳蕤繁盛。其实,潘教授曾经踩到了我的发梢。他不遗憾,因为他最终找到了我。有时,我们会促膝长谈。我说,如果当年我的名字出现在了烈士花名册上,柳眉儿又会是什么样子?我的盼归又会是什么样子?
潘教授望着远方,凝思不语。
我说,如果你早一点找到我,柳眉儿和盼归是不是就能看到烈士纪念碑上有我的名字?
潘教授意味深长地点点头,不管有没有名字,你们都在碑上。
他的泪水潸然而下,打湿了土地下那堆沉默的骨骸。
我听到了这个时代的马达声。也许不久以后,这里将是宽阔的马路、繁闹的市场抑或飘着油烟味的住宅小区。这足以让我欣慰,因为这片土地上有我——一个失踪在1947年的无名烈士,以及我的战友们用鲜血浇灌的花朵。而更令我欣慰的是,我的兒子、孙子,他们都长着和我极其相似的大耳朵。
责任编辑 申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