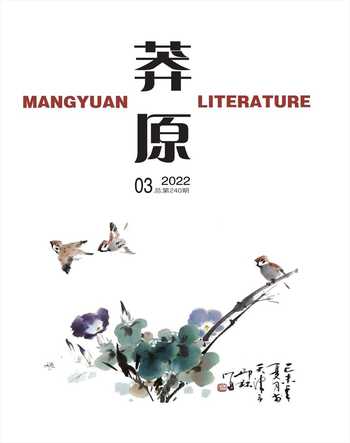蝴蝶飞
非鱼
太阳快要落尽了。
烟烧到了我的手指头。
轰隆隆飞逝而过的,是每天忙个不停的火车。
对了,霍亚军就是乘着火车走的。那天,我去送他,他抱着我,死命地抱着我,把我的肋骨都勒疼了,我没有说疼,但是真疼。我的肋骨似乎也硌疼了他。他咧了咧嘴,把厚厚的嘴唇向我压过来。我放开他的腰,双臂攀上他的脖子,递上自己的嘴唇。这样舒服多了。
他走了,说要出去闯一闯。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穷家富路。他要去的地方很遥远,远到像在另一个世界的天各一方。
爱上霍亚军的时候,我十七岁,他二十三岁。
他在巷子里堵住我,说,我喜欢你,我们交朋友吧。
我要上学去,如果再晚就迟到了。我居然点点头,他就让我过去了。我知道他是霍亚军,这个县城里,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烫着一头卷发,喇叭裤紧紧地兜着屁股,皮夹克很短,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看起来很酷。
那天下午有三节课,老师讲的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脑子里全是霍亚军摇摇晃晃的大长腿,和那张黑瘦的脸。放学的时候,我故意磨磨蹭蹭,没有和其他同学一起走,我知道,他肯定在校门口等我。他就是故意要让所有人知道,我是他的女朋友。
果然,霍亚军跨在自行车上,单脚点地,领子上挂着墨镜,冲放学的女生吹口哨。看见我,他从自行车上下来,单手握着自行车把的正中,跟了几步,就与我并排了。
我说,离我远点,别人都看着呢。
他俩眼一瞪,大声喊,怕什么,谁看见了?谁看见让谁看去。
大家自然地让出一条道。我紧紧地抓着书包带,低着头,匆忙穿过那排柳树,走过那片菜地,拐进了一条小巷子。
一进巷子口,我就后悔了。霍亚军把自行车靠在墙上,一把拉住我,你跑什么?
我没跑。
还没跑?你回家是这条路?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是哪里,我真不知道。
他松开我的胳膊,说,走吧,我送你回去。
不用,不用,你赶紧走吧。
傻样。这条巷子你要能转出去天都黑了,走吧。
我不能看他,一看他,他说什么我都会听。这个县城里有名的小流氓,好像真的有魔力,我既害怕,又无法抗拒。
从那以后,霍亚军经常在我上晚自习的时候出现。他好像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换座位,什么时候会换到靠窗的位置,他就出现了。
想起那扇窗,我就想哭。
红色的木格子窗,天稍微一热就会打开,窗外是校医景医生种的一大片菊花。白色的小菊花一开,满教室都是菊花的香味。霍亚军会在我上晚自习时突然出现,躲在木格窗扇的后面,掐一枝花扔在我的书上,等我扭头,就看见他咧着嘴,露出几颗大白牙,招手让我出去。我当然不能出去,于是,他就在窗外吹口哨,他一吹,我就把头埋在高高的书垛后面。
这样的口哨声,很快就被班主任和教导主任知道了,当然,我爸妈也就知道了。一脸严肃的教导主任大会小会不点名地批评我,说我结交小流氓,败坏班级风气,是高三一班的害群之马。
教导主任的批评没能阻止霍亚军在校园里出现,却让我变成了学校的“名人”,走到哪儿都有人指指点点,我爸打我、我妈骂我,我不是非要和霍亚军谈恋爱,可我也不想学习了,学不进去。高考前两个月,我正式离开了学校。我把所有的书本全留在学校,天天窝在家里,变成了待业青年,除了看电视,就是看三毛的书。
書看多了,我就希望霍亚军能带我去撒哈拉一样的地方,没人认识我们,我们好好地谈恋爱。他肯定知道我退学了,也能找到我家,但他一直没来找我。后来,我才听说,他因为打架,被抓进去了,打架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我问过他,他说没这回事。反正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脸上多了一道伤疤。
七月份以后,高考结束了,我从家里出来,无所事事,就每天坐在他的自行车前杠上,在大街小巷穿梭,一部接一部看录像片。录像厅里又脏又闷,黑咕隆咚的,经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醒来接着再看。那段日子,我和所有的同学都断绝了来往,不想听到他们任何人考上大学的消息。
半年以后,我爸托人给我找了个工作,在县化肥厂上班。
走开,你们这些坏孩子。
我拿起身边的石子砸他们。他们也拿石子砸我,拿树枝打我。一块石头砸中了我的头,流血了。他们跑了。
他们总是这样,我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我就坐这儿看会儿火车,他们也要来打扰我。不过,除了他们,还有黄阿姨、李大军,也没人关心我在哪儿。
我爸死了,人们都说是我气死的。也可能真是我气死的吧。霍亚军要跟我结婚,他不同意。霍亚军在我家门口跪了三天,他还是不同意,说他是小流氓,我要嫁给他,我们家祖宗十八代的脸就都让我丢光了。后来,霍亚军看软的不行,来硬的,跟我爸动手了,他们俩在院子里打成一团。那件事在整个县城影响还是挺大的,警察都来了。
我在化肥厂也成了名人,几个走后门进厂的子弟天天围着我转,他们说崇拜霍亚军,他是他们大哥,我是他们大嫂,他们要保护我。厂长说我们是一窝老鼠不嫌臊,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带坏了厂里的风气,要我写检查。我写了,在车间大会上念了。我觉得我写得很认真,很深刻,可车间的工友一直在笑,车间主任不得不让我下去,我说,还没念完呢。
第二天,厂门口贴出了开除我的布告。我撕了那张大白纸,去找厂长理论。我什么也没干,他们喊我大嫂,又不是我让他们喊的;我每天按时上班,按时下班,按时完成车间的任务,凭什么开除我?我在厂长办公室又哭又闹,最后,他不得不收回开除命令,说下不为例。
霍亚军看我爸实在不同意我们结婚,就在外面租了一间房,要我跟他一起住,我没同意。没结婚,我肯定不能跟他住在一起,这是底线。但我会去他的出租屋里,帮他收拾一下屋子,洗洗衣服。他也不勉强我,顶多抱一下,亲一下。
这个破县城实在太小了,我和霍亚军同居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我爸耳朵里了。他用皮带抽我,我说没有,他不信,瞪着血红的眼睛,疯了一样不停打我。那天晚上,如果不是我妈拦着,他可能就把我打死了。我的脸上、背上、腿上、胳膊上,几乎没有一块好地方,全是一片一片的血紫,哪儿都疼,睡觉只能趴着睡。
也就是那天晚上后半夜,我爸进了医院,再没有回来。安葬完我爸,我妈把户口本放在我床上,让我想干吗干吗,想跟谁结婚跟谁结婚,结完婚再也不要回这个家,权当她从来没生过我。
我爸死的时候我没哭,我恨他,恨他不相信我,恨他下死手打我;面对我妈,我哭了,哭得撕心裂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告诉我妈,我真的没有和霍亚军上过床,我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霍亚军也从没有强迫过我,我就是去给他洗衣服,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我妈说,你爸已经死了,有没有都不重要了。她的眼神和语气,冷得跟冰块一样。
我没有和霍亚军结婚,我害怕,害怕再也回不了家,害怕我妈不要我,不理我。
后来,霍亚军说他要去南方闯一闯,闯出个样了再回来娶我。我把我挣的工资、他给我的钱,全给了他。他就坐上这个轰轰隆隆的火车,走了。
霍亚军走了,他说要去赚大钱,证明他不是个小流氓,不是个混混,是真想跟我结婚,是真喜欢我,爱我。
我相信他,等着他。他给我写信,说南方遍地是钱,到处是机会,天天就跟捡钱一样。他还寄回过一张照片,背景是一棵椰子树,人更黑更瘦了,头发剃得很短,但很精神。
后来,他的信越来越少。然后,就消失了,我再也找不到他了。
我妈离开家那天,没有一点征兆。
我早上起来,在桌子上看到一张纸,是我妈给我写的信。她说别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是转业军人,老婆得病死了,对她很满意,她要跟他走了。我妈只说了他在山东工作,哪个城市,什么单位,都没说。她肯定是早有预谋的,就是不想让我知道。
我一路狂奔,跑到火车站,问去山东的车几点开。车站工作人员告诉我,往山东去的火车一天就一趟,已经开走了。
火车站广场上人来人往,我找来找去,撞来撞去,都不是我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已经没有爸了,再没有妈,就成孤儿了。他们都嫌弃我,都扔下我不管了,包括霍亚军,也不要我了。
呸,呸,该死的火车,就是它把他们都带走的。
化肥厂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干,厂长说没钱发工资了,厂里让我们车间先停产,主任说大家先回家歇几天,等通知,有好轉再开工。开始还发着工资,发着发着,就越来越少,直到劳资处通知,我下岗了,每个月只发一点生活费。
我妈一直没有给我写过信,她嫁那么远,就是为了不想跟我有任何联系吧。她说过,县城太小了,她受不了别人的指指点点。我名声不好,还气死了我爸。都是我罪有应得,罪该万死。
就剩霍亚军了,我给他写信,一星期一封,有时候一星期两封,他都没有回。
我想,如果十七岁那年,他没有在学校门口截住我,我爸也不会死,我妈也不会再嫁人,我也不会退学,眼看着别人考上大学,我成了待业青年。
霍亚军,这个混蛋,王八蛋,呸,呸,呸。但我不恨他,我爱他,喜欢他。我爸妈那会儿老是问我喜欢他啥,我哪能说清楚,他也没有给我机会让我想清楚啊。我妈说我鬼迷心窍,可能就是。他是真好啊,哪儿哪儿都好,他们不懂。
一个人的日子说好过也好过。饿了煮点面条,吃完了就睡觉,睡醒了去大街上逛。碰到霍亚军之前的朋友了,他们请我吃一顿。那天晚上,和霍亚军的朋友一起吃饭,他们也想他了,但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问我,我也没有。我说给他写了几十封信了,都石沉大海了。我们喝了很多酒,我大概喝了半瓶白酒吧。如果霍亚军在,他肯定不会让我喝那么多,他会瞪着我,夺走我的酒杯。他不在,就没人管我了。我喝多了,所有人都喝多了,我们像树上掉下来的叶子,晃晃悠悠,各自飘着,飘回县城的角角落落。
我家住在万花巷的尽头,是一个死胡同。我爸说这是我爷爷当年来县城做小生意置办的,独门独院,现在更是空空荡荡,除了那棵杏树和石榴树,院里的花都让我养死了,那只叫虎子的大黑狗在我妈走后,也不见了。我连我自己都养不好,哪有闲心养它们。
那天的事我实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我打开了院门,打开了屋门,没有开灯,直接躺床上睡了。天快亮的时候,我醒了,发现了身边的那个男人。我没有穿衣服,身上疼得要命,就像那天我爸打我一样疼。我大叫起来,那个男人也吓坏了,我不认识他。
他捂我的嘴,我咬他的手。他不停地说,别喊,别喊!我更拼命地喊。霍亚军都没有敢这样对我,他凭什么?他想跑,我拉着他,掐他,打他,咬他,直到隔壁的黄阿姨过来,抱住我,用被子把我裹住。
床单上有很多血。黄阿姨一直抱着我,轻轻拍着我。我小时候,被人欺负了,被我爸打了,害怕了,我妈就这样抱着我。黄阿姨让我别哭,说警察已经把那人抓走了,说我受委屈了。
这件事又在县城传遍了,尽管大家知道之前传说的我跟霍亚军同居、我爸被气死,不是真的,如今都已经不重要了。在他们看来,结果是一样的,只是换了个男人,说不定那个男人还是我领回去的。
那天我喝醉了,回家没有锁院门,也没有锁屋门,那个尾随我的男人不费一点力气,就躺在了我的床上,夺去我最美好的预留给霍亚军的东西。从此,我真的成了一个贱人,一个坏女人,一只烂鞋。
黄阿姨劝我,别理他们,以后日子还长着呢,要好好的。她怕我寻死。我才不会死,我还没等到霍亚军,没给他说清楚呢。
烂桃子一样的太阳,怎么这么快就没了?
天又黑了,那些坏孩子都回家吃饭了,这会儿火车也不跑了,除了我手上的烟头,就剩下草窝里那些虫子了。
有点冷了,走吧。哪儿暖和?除了桥底下、汽车站,也没有啥好地方。对,火车站售票大厅,就去那儿。
售票大厅一晚上都有人,找个角落,老老实实待着,如果遇到李大军值班就好了。他是霍亚军的小兄弟,后来接他爸班来火车站上班了。就是他带我到售票大厅睡觉的,告诉我不要喊不要闹,他还会给我带吃的,夹了咸菜的馒头或者烧饼,有时候还有鸡蛋、苹果。他是好人,大好人。还有黄阿姨,也是好人,我身上的衣服都是她给的,她也给我吃的,还给我洗头、洗澡、剪头发。
没看到李大军,今天晚上得饿着了。以前我常坐的那个角落里有人,再换个地方,只要能靠着墙就行,就能睡着。
霍亚军死了。是他哥霍冠军和他爸告诉我的。
那天晚上出事后,我一直等着他回来,得给他解释清楚,说我真的是无辜的,还要问问他怎么就不给我回信,不理我了,他到底干吗去了,赚到钱没有,啥时候回来跟我结婚。不结婚也行,话得说清楚,那个男人真不是我领回去的,我喝多了,真喝多了。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去玩,也再不喝酒了,但我学会了抽烟。我看到我爸生气的时候就不停抽烟,他死了以后,柜子里还有好几条烟,我开始抽,呛得不停咳嗽也抽,慢慢就学会了。
霍冠军和他爸进院的时候,我还躺在床上。他们说,起来,起来,跟你说点事。我认识他们,赶紧起来坐好。
霍冠军说,亚军死了。都是你害的,你这个女人真是个丧门星,气死了你爸不说,还害死了我弟。
什么?谁死了?
亚军,霍亚军,为了你跑南方挣大钱的霍亚军。
他怎么会死?他怎么能死?他怎么敢死?我还没有死,还等着他跟我结婚、生孩子呢。我不信,他们骗我。
他爸说,是真的,冠军没骗你。是半个月前的事,我们去了南方,已经处理了后事。
我号啕大哭。哭完了,问他们详细情况。
霍冠军说,霍亚军去了南方以后,先是在广州,后来又去了深圳、海南,跑了好多地方,也给家里寄过钱。具体做什么,他们也不知道。等他们接到通知,让去一趟,才知道他出事了,是在汕头。接待他们的人说霍亚军是突发疾病,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具体什么病,医生也没查出来。他们要求看尸体,对方说南方太热,尸体留不住,已经火化了。一直有两三个男人陪着他们,人生地不熟,说话又听不懂,他们也不知道该去找谁,反正人已经死了,就听从他们的安排吧。
我不相信事情就这么简单,我说他们隐瞒实情,你们得报警,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要弄清楚他到底怎么死的。
霍冠军说,也想过。可人都走了,后来商量了一下,就算了。
怎么能算了?那可是一条人命,是你弟弟。
他爸說,好了,我们今天不是跟你说这个的。冠军,你说吧。
是这样,亚军的事处理完了,我们收拾东西的时候,在他的包里翻到了这个,你看看。
结婚证。大红色的,带着塑料壳的两本结婚证。我打开,看到了我和霍亚军的合影。我不记得什么时候照过这张照片,一点都不记得。仔细看,确实是我们两个人的结婚证,日期是他和我爸打架之后,我爸还没死以前。我从来没跟他领过结婚证,他也从来没告诉过我有这回事,提都没提过。
我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死了,真的死了,世上再也没有这个人了。我却已经和他结婚了,两本盖着钢印的大红结婚证书,证明我们俩是一家人。天呐,太乱了,捋不清楚了,头要炸了。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直在想霍亚军,想我和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他对我是真好啊,他怎么能死呢?
黄阿姨告诉我,让我小心点他们。说大家都在传霍亚军死没死还不一定,公司出了事,他跑了,然后公司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他头上,还说他在逃跑的路上被车撞死了。霍冠军和他爸之所以不报警,是他们和对方达成了协议,人家给了他们一大笔钱。既然人家给了钱,他们也没打算再追究,干吗还要来跟我说,还爷俩一起来,这里一定有鬼。黄阿姨说,霍冠军和亚军不一样,面上看着老实,一肚子坏水,他爸听他的,你可千万小心。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他们又来了。这次来,他们开门见山,说要我家的院子和房子,起码得分一半。
这是我爸我妈的,是我爷爷留下来的,为什么要分给他们一半?我不理解。
霍冠军说,你和亚军是领了结婚证的,是一家人,你的就是他的。你爸死了,你妈也嫁人不回来了,这个院子和房子是你的,也就是我们亚军的。亚军死了,我们要属于他的一半。
我还是没有搞清楚,平白无故多出来一本结婚证也就罢了,怎么房子还要丢一半。不行,肯定不行。看来黄阿姨说的有道理,他们太坏了。
这帮坏人临走时撂下一句话,这事不是你同意不同意的问题,是法律决定的,我们还会再来的。
从那以后,他们隔三岔五就来,有时候是霍冠军一个人,有时候是他们爷俩,有时候是三五个我不认识的男人。黄阿姨也很气愤,她说,坚决不能给他们,凭什么,这是你爸留给你的唯一念想了。
肯定不能给,霍亚军要活着,全都给他我都愿意,可他死了,死了。
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没有了。
售票大厅吵吵嚷嚷,两个买票的人打起来了。一个人说另一个人偷了他的钱,另一个说没有,吵着吵着就动手了。
天已经亮了,我可以走了。
去哪儿?大街小巷,田野沟渠,哪儿都能去,都可以去。人们说我是疯子,既然是疯子,就不用管那么多,想去哪儿去哪儿,爱去哪儿去哪儿,想说就说,想唱就唱。但我最喜欢去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铁路边,去看火车;一个是以前学校旁边的麦地、菜地。
火车站广场上还没有什么人,空荡荡的,卖早点的刘叔喊我,递给我两个包子,让我趁热吃了。我冲他笑,他也冲我笑。我边走边吃,刘叔也是好人。
扫大街的开始干活了,竹扫帚哗啦哗啦扫着头一天的垃圾。大部分人应该都还没睡醒,他们太懒了。走到涧河桥,才看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匆匆忙忙;桥头有三四个老头老太太在打太极拳,比比画画;再走,人就多了,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一晃一晃,去上学。
火车昨天看过了,那就去城外吧,等太阳出来了,去麦田里再躺一会。
菜地不能坐不能躺,麦田能。麦子已经长成绿毯子了,旁边的油菜花也快开了,等油菜花一开,那个香哩,还有嗡嗡叫的蜜蜂,飞来飞去的蝴蝶。躺在麦田里,晒着太阳,仰脸看天上的云朵飞过来飞过去,听着蜜蜂嗡嗡蝴蝶扇翅膀,小蚂蚁、小瓢虫在我脸上、胳膊上爬上爬下,一会儿就睡着了。
睡着的时候,我还是会想霍亚军。
他那么好一个人,怎么会有那么混账的哥哥?
霍冠军一直来找我要房子,我不同意,后来就跟他翻脸了,不让他进门。他可能早就等着这一天,我关了门不让他进,他就撬锁,直接带人搬了家具堆在院子里,大喊着,这是他弟弟的,谁也不能剥夺他弟弟的权利。
就这样,他一点一点把柜子、床、沙发、乱七八糟的东西搬进院子,搬到我爸妈之前住的屋里,放进堂屋,把我家的东西堆在廊道下。我阻挡不住,报警也没用,霍冠军拿出了结婚证,说他弟弟有遗言,这是家务事。
最后,他彻底占领了三间房中的两间,只有我住的那间他们没有进来。他让他爸常住在这里,我撵也不能撵,骂也不能骂。
我只有不停地用拳头捶墙,拿头撞墙。刚开始,他爸听见了还过来劝我,让我想开点,慢慢地,他就不来了,看见我,也当没看见。他是真的把我家当成他的家了,每天进出自如,没事就搬个躺椅在树底下喝茶,晒太阳,听收音机。
快烦死了。看着廊道下我爸妈的东西,听着院子里收音机里哇啦啦播放的秦腔、眉户戏,想到霍亚军已经死了,他还有心听戏,我一脚踢翻了他的收音机,冲着他大叫,让他滚。我把他们的东西从屋里扔出来,扔得到处都是。
霍冠军来了,几个人把我摁在地上,让我住嘴。
黄阿姨替我找过他们,但也被他们骂回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被撵出来了,他们不让我回去。大门锁换了,我房间的锁也换了,我彻底没地方可去了,开始到处游荡。被人喊疯子,女疯子,漂亮的女疯子,没人要的疯子。
爱喊什么喊什么,爱叫什么叫什么,霍亚军都死了,我还管那么多。
起风了。这个时候的风,就像小孩子的手,在脸上摸来摸去,舒服极了。睡了一觉,浑身上下暖暖的,还有点出汗。
我坐起来,拔了几棵麦苗,拽出麦苗的嫩茎,我喜欢吃下面那一段,甜丝丝的,很好吃。油菜叶也好吃,但都没有油菜花好吃,还有梨花、桃花、杏花、苹果花。哪个花开了,我就吃哪个,然后等他们结果。小桃子不好吃,小李子和小杏好吃,酸酸的,涩涩的。
两只蝴蝶老在我眼前飞,我走到哪儿,它们跟到哪儿。一只黑色翅膀上带黄色圆点,一只棕咖色翅膀上带黄色圆点,它们俩你追我赶,上下翻飞,一会儿在我头上站一下,一会儿在我肩膀上停一下。太好玩了。
顾不上去找即将开放的油菜花,我想跟它们玩。
那会儿,大街上的喇叭里到处在唱,亲爱的你跟我飞,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亲爱的来跳个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跃这红尘永相随……
如果霍亚军没死,我们也会经常这样打闹、追赶。他会带我去河滩捡石头,打水花,打出一连串的水花;去杨树林里找鸟窝。他那么大个人,玩起来完全就是个孩子。我们跑啊,疯啊,喊啊,叫啊。
对啊,这俩蝴蝶是不是霍亞军变的,他让它们来陪我的?
肯定是。我就知道,霍亚军他放心不下,他不会不管我,他总有办法的。
妮妮,妮妮。是黄阿姨在喊我。她总是叫我妮妮,我记得我叫宁嘉惠,在家我爸我妈都叫我妮妮。
我追着蝴蝶跑,黄阿姨追着我跑,她身边还有一个人,也在跑。
黄阿姨喊,妮妮,回来,回来,你看这是谁。
管他是谁呢,跟我都没有关系了。
黄阿姨追上我了,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我冲她笑。她身边的那个人好熟悉啊,怎么那么像霍亚军,他刚才变成蝴蝶,这会儿蝴蝶又变成他了?
头又开始疼了。
他抱着我,就像霍亚军走的时候那样死命地抱着我。
他说,嘉惠,咱回家。嘉惠,回家。
责任编辑 丁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