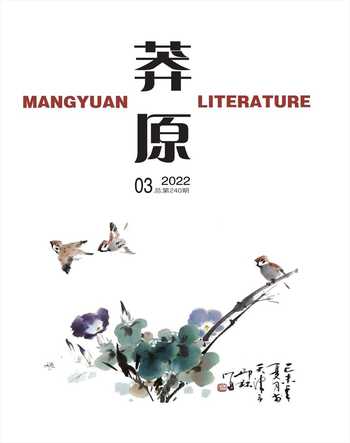西城楼
王俊义
西峡口有四个城楼。
东城楼和西城楼,是一模一样的——青砖砌起来十几米高的碉楼一样的建筑,分了两层。第一层中间是一个城门,并排能过两辆骡马大车,城门两边是橡树楼梯,通向第一层,樓板也是橡树的,木纹花朵一样绽开,两个窗户面向一条铺着青石板的道路。总有马车和牛车,从城门里出来,去老鹳河的码头,桐油和生漆卸下来,再缓慢地从石板路上原路折回。
老河口是汉江边的老商埠,帆船能到汉口甚至上海;西峡口老鹳河里的帆船要小很多,就只能到老河口。这几条帆船从湖北老河口拉回来的南货,以江南丝绸为多,杂有花膏和胭脂一类的奢侈品。西峡口大商铺有二十多家,生活自然讲究,上海有留声机之后没几年,西峡口大商铺的老板们也有了。西峡口的所有时髦都和上海的时髦连接在一起。只不过比上海晚三两年而已。
夜半之时,山西、陕西的马帮和驼队来了,驮着秦晋物产,经过西城楼到老鹳河码头,红铜铃铛响得很脆。听到铃铛的声音,不用叫喊,守城楼的两个兵丁,就抽出橡木大门上的巨大插闩,打开城门,让马帮和驼队经过。赶骆驼的顺手扔给两个兵丁半袋运城大枣或是一串洛川腊肠。这样,他们两个虽在西峡口守卫一个西城楼,倒也吃遍秦晋。
守城门的两个兵丁,穿黑衣服,胸前留下一个很圆的白,上边写着一个很黑的字:皂;和胸前相对的脊背上,也留了一个很圆的白,也是一个很黑的字:皂。他们隶属于西峡口巡检司捕房,捕头是他们的顶头上司。马帮和驼队留下的秦晋物产,都会留下一份给捕头。
西峡口的老日子,都从西城楼溜走了。
西城楼面向码头那边,是正门。一层和二层结合部,是一根四四方方的橡木,横放着。一层的砖墙举着橡木,橡木又举着二层的砖墙。整个西城楼是青砖灰瓦,中间这根橡木却染着一层赭红。那个颜色,和皇宫墙壁的颜色很是相似。
橡木和两个窗户中线对应的地方,伸出来两个鸡蛋粗的铁钩。过年过节,巡检司的巡检就到西城楼外边喊叫:“把红灯笼挂出来。”
两个穿着黑衣服的兵丁就喏然一声,各自举着一根木杆,杆顶举着一个灯笼。灯笼上有个铁钩,恰好和城楼上的铁钩吻合。入夜,巡检过来,顺着橡木楼梯走上二楼,从窗户里伸出手,把灯笼里的蜡烛点着。
瞬时,西城楼的两盏灯笼红了,落在石板路上的灯光也红了。有人从码头上过来,身影印在石板路上,也是淡然的红。
在清朝以前的国家序列里,西峡口隶属于内乡县。相当于这几年的口子镇和省界边的镇子,一把手都是副县级。西峡口巡检司的巡检,在清朝相当于县丞,也是个副县级。巡检司事情不多,逢年过节点燃四个城楼的红灯笼,这样象征时间意义的事情,巡检做得有滋有味。
西城楼还有两个特殊的橡木笼子,是其他三个城楼没有的。平日里放在西城楼二层的一个角落,有时候闲摆两三年,一次也用不上。忽然巡检司剿灭了西峡口某座山寨上的刀客,守城门的才把其中一个木笼拎出来,随便擦擦,深红色的木纹就显露出来。在不远处老鹳河的河滩上,巡检司的刀斧手砍了刀客头儿,守城门的就把刀客头儿的脑袋装进橡木笼子里,挂在西城楼年节挂灯笼的钩子上。刀客头儿的脑袋挂在二层,一层的砖柱上贴着巡检司师爷狼毫书写的告示,把刀客头儿的罪过列举十几条,然后在刀客头儿画像下边的名字上,打了一个类似老师改作业打的对号。人们看见这个符号,就知道一个刀客被斩杀了。
挂了半个月之后,在深夜里,守城楼的把木笼取下来。刀客头儿的脑袋是如何处置的,并无人知晓。也有好事者去问守城楼的,穿黑衣服的兵丁就反问:“是你爹?”
问者说:“不是。”
兵丁说:“不是你爹,你就不要问。”
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西城楼被拆除,也无人知晓那些脑袋的下落。
西峡口的南北大街,也是一条石板路。北大街第七家有一个不大的门楼,夹在林立的商铺中间,很不显眼,这就是蓝秀才的院子。大门两边过年贴的对联,是蓝秀才自己写的。上联是:满壁云烟杜甫诗;下联是:一篇风雨王维画;横批是:春风夏荷。
字很瘦,蓝秀才人也很瘦。秀才姓蓝,也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长褂子。一年到头,没人见到过他的鞋或靴,因为褂子太长太长,把蓝秀才的一双脚都装进了长摆里。何况,蓝秀才走路,是一步挪四指的小步子。
有人问蓝秀才:“你咋不把脚步迈大一点?”
蓝秀才说:“我又不急着去找死。”
是的,蓝秀才活得乐哉游哉,肯定不是急着去死的人。
蓝秀才有祖上留下的二十多间商铺,分布在西峡口南北大街,一半租给了山西人,一半租给了湖北人。租金不是很多,却足够养活蓝秀才。西峡口人把走路很慢,叫作蹲福。蓝秀才慢腾腾的样子,是在蹲福呢。
他早上喝一碗稀粥,就着一小碟豆腐乳和一小碟黄豆芽,吃两个老婆蒸的包子,擦擦有些尖的嘴巴和下巴,就出门了。他慢腾腾走向南大街的鹳鸟茶屋,要一壶粗糙的老树普洱,煮得很浓很浓,倒入乳白色茶碗里,两扇嘴唇嘬起来,吹吹茶碗里浮起来的水沫,优雅地喝一口,对茶屋的桑老板说:“好
茶,好茶。”
鹳鸟茶屋,原来叫桑树茶馆。蓝秀才来过几次之后,对桑老板说:“叫桑树茶馆,俗了。”
桑老板说:“我姓桑名树,茶馆叫桑树茶馆,怎么就俗了?”
蓝秀才说:“桑者,丧也,不宜作字号。”
桑老板就让蓝秀才帮忙另起一个。
茶馆门口有棵巨大的枫杨树,招惹来一群鹳鸟。蓝秀才灵机一动,说:“叫鹳鸟茶屋吧。”
桑老板说:“好。”
过一日,蓝秀才又来喝他一辈子都喝不够的老树普洱,手里拎着一块枫杨树木板,上边写着“鹳鸟茶屋”,说:“招牌我替你写好了,瘦金体,你看可好?”
桑老板连声说好,就把原来的“桑树茶馆”取下来,换了蓝秀才的“鹳鸟茶屋”。
蓝秀才到鹳鸟茶屋喝老树普洱,是不花银子的。他有一把三弦,一年四季都放在鹳鸟茶屋里。上午喝过三碗老树普洱,取下三弦,脱掉三弦的紫色琴袍,坐到一个绛红色的椅子上,右腿搭到左腿上,三弦放在腿弯里,轻轻拨拉一下,三根弦就流出很清冽的琴声。
一边弹着三弦,一边唱着陈年古旧的三弦书,是蓝秀才的日常生活。蓝秀才只有一个嗓子,却能唱出一群人的声调。《武松打虎》,是蓝秀才最拿手的。武大郎出场,是武大郎的懦弱之声;潘金莲出场,是潘金莲的靡靡之音;阎婆惜出场,是阎婆惜的扭捏之腔;武松出场,是武松的阳刚之气;小酒馆老板出场,是酒馆老板的嗫喏之调;老虎出场,是老虎的镇山之吼;阳谷县令出场,是县令的威严之态……鹳鸟茶屋喝茶的人,听蓝秀才的三弦书,如同在戏园子里听了一场大戏。
三弦书给鹳鸟茶屋聚拢了人气,唱三弦书的蓝秀才就免费喝茶。蓝秀才肚子里装了几百部三弦书,一年唱到头都不相同。西峡口上鹳鸟茶屋喝茶听三弦书的,都是不种地也能吃饱饭的主儿,不做生意穿得起绸缎褂子的主儿,他们听蓝秀才的三弦书,也会跟着哼哼几句。蓝秀才成了西峡口的范儿,他的一举一动,一腔一调,都是西峡口的圭臬。
蓝秀才还有个绝活,是唱南阳的鼓儿哼。
清末民初,鼓儿哼在南阳很流行,就叫南阳鼓儿哼。蓝秀才中了秀才,去开封乡试三次,都没有中举,却跟着南阳的另一个秀才,学会了南阳的鼓儿哼。三弦书唱的腻歪了,就唱唱鼓儿哼,让鹳鸟茶屋的茶客们换换口味。
一个牛皮小鼓,摆在架子上;两个犁铧片子,夹在左手里;一手敲鼓,一手摇晃两个犁铧片子,鼓声和犁铧片子的声音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蓝秀才就唱起了粗糙的鼓儿哼。起腔是鼻音哼出来的,落腔也是鼻音哼出来的,加上鼓声的伴奏,就叫了鼓儿哼。
鼓儿哼的开场白,听了让人难忘。蓝秀才唱得最多的,是《大实话》。简单直白,句句说到人心里,听过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说天亲,
天也不算亲,
天有日月和星辰,
日月穿梭使人老,
带走世上多少人。
说地亲,
地也不算亲,
地长万物似黄金,
争名夺利多少载,
看罢旧坟看新坟。
说爹娘亲,
爹娘也不算亲,
爹娘不能永生存,
满堂儿女留不住,
一捧黄土泪纷纷……
蓝秀才唱罢,茶客们都寂然无声了。
忽一日,蓝秀才刚刚唱罢开场白,正要开唱正本书时,一个老茶客走进鹳鸟茶屋,说:“西城门又挂了一个脑袋。”
蓝秀才問:“谁的?”
老茶客说:“刀客商之恩的。”
蓝秀才接着问:“会写五绝和七绝的那个刀客?”
老茶客说:“是的。”
蓝秀才说:“他的脑袋挂到城墙上,西峡口最好的五绝和七绝就没人写了。”
老茶客说:“一个烧杀掳掠的刀客,还写五绝七绝,那不是糟蹋李杜吗?”
蓝秀才说:“五绝七绝,李杜写得,刀客也写得。”
老茶客说:“刀客就是耍刀的,一写五绝和七绝,命就该绝了。”
蓝秀才说:“唉,当年商之恩和我一起到内乡考童生,三次都没考中,这才落草为寇了。”
鹳鸟茶屋喝茶的,都问蓝秀才:“那你呢?”
蓝秀才说:“我第一回就中了童生,第二回中了秀才。跟我一起中秀才的,还有巡检司的穆巡检。”
茶客们说:“蓝秀才,你咋没中举人呢?”
蓝秀才脸蛋子垮塌下来,黑沉沉地说:
“我就是个秀才的命。”
一个老茶客上鼻子蹬脸地说:“穆秀才还能当个巡检,你这个秀才不当吃不当喝,顶多就是个穆巡检的夜壶。”
鹳鸟茶屋的桑老板说:“说蓝秀才是穆巡检的夜壶,是糟蹋人。我看是穆巡检的花瓶,过节了摆摆,显得几分排场。”
蓝秀才说:“夜壶也罢,花瓶也罢,秀才自有秀才的好处。”
茶客们问:“蓝秀才啊,我们没有见你得过一点好处。”
蓝秀才说:“秀才的好处有三个。一是不服徭役,二是见了知县知府的八抬大轿不下跪,三是受审不受刑。”
这样的话,蓝秀才说了无数次,茶客们听了无数次,也都是笑笑罢了。
老茶客说:“蓝秀才啊,那你就去送送商之恩吧?”
蓝秀才放下三弦,伸伸懒腰说:“送送吧,谁也不敢说谁的脑袋不会挂到西城楼的城门上。”
桑老板说:“你蓝秀才走路连蚂蚁都害怕踩死,放屁都怕惊着蚊子,你的脑袋是挂不到西城楼上去的。”
蓝秀才抻抻长褂子说:“是的,是的,蚂蚁蚊子都是一条命啊。”
那天很晴朗,枫杨树的叶子把过滤了的阳光洒在通往西城楼的石板路上,如滚动一地银圆。蓝秀才和几个茶客踏上去,脚步却很虚很虚。不但阳光虚了,石板路也虚了。
穿过一条长长的石板路,就到了西城楼下的空阔地带。扭过身,西城楼和道路两边的老枫杨树,构成了一个剪影。
商之恩的脑袋装在橡木笼子里,挂在西城楼左边巨大的钉子上,应该才挂上去不久,还沥沥拉拉滴着血水。从老鹳河码头过来的人,和要到码头坐船的人,都在西城门外散落着。人们仰脸看了一眼,就匆匆离去。
鹳鸟茶屋的桑老板说:“刀客脑袋的血
水,滴到谁身上,谁的儿子就是一个大刀客,脑袋也会挂到西城楼上的。”
蓝秀才晃晃脑袋说:“刀客都是一锤子买卖,脑袋挂上去就挂上去了,谁还能管得了下个刀客是谁?”
桑老板说:“挂在西城楼上的大刀客,一人一姓。上一个姓巫,上上一个姓骞,再上上一个姓米,再上上上一个……忘记他姓啥名谁了。”
蓝秀才说:“姓庹。”
桑老板说:“还是秀才好记性。”
蓝秀才说:“这个刀客的脑袋挂上去,下一个刀客的脑袋已经开始晃荡了。一个一个又一个,就把西城楼挂老了。”
回到鹳鸟茶屋,蓝秀才喝下几杯很浓的老树普洱,展展深蓝色的长褂子,顺着南大街的石板路走向北大街的石板路,过了枫杨木板老吊桥,径直走向西峡口巡检司衙门。沿街商行的伙计们,从来没有见过蓝秀才这么快走路,长褂下摆扫过石板路,飞起很多灰尘。
巡检司门口有两个巨大的铁狮子,每个铁狮子跟前站着一个穿黑色衣服的衙皂。蓝秀才经过两个铁狮子的时候,两个衙皂把他拦住了,问:“找谁?”
蓝秀才说:“穆巡检。”
衙皂说:“巡检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说找他就找他?”
蓝秀才说:“我是蓝秀才,在西峡口可以随意找穆巡检。”
衙皂说:“别说蓝秀才,你就是黑秀才也不行。”
蓝秀才说:“穆巡检说过的。”
衙皂说:“穆巡检对你说过,我们没有听见,就等于没有说过。”
蓝秀才就站在两个铁狮子中间,扯开嗓子喊叫:“穆巡检,穆巡检……”
衙皂说:“你再大声喊叫,就是咆哮公堂,我们把你抓起来。”
蓝秀才又大喊了两声:“穆巡检,穆巡检。”
穆巡检从大堂前边的一条甬路上走过来,亲热地拍拍蓝秀才的肩膀,说:“蓝秀才啊蓝秀才,在西峡口巡检司,还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大声喊叫呢。”
蓝秀才说:“不喊叫,巡检大人听不见啊。”
穆巡检说:“巡检司掉根针,我也能听见。”
穆巡检和蓝秀才走到巡检司大堂边的厅房里坐下,就有衙皂端过来两碗茶,茶是新茶,香味四溢,足见穆巡检对蓝秀才的敬重。
蓝秀才说:“穆巡检,刚才我去西城楼,看到了商之恩的脑袋。”
穆巡检问:“难道说巡检司不该杀这个大刀客?”
蓝秀才说:“该。”
穆巡检问:“那是不该把商之恩的脑袋挂在西城楼?”
蓝秀才说:“该。”
穆巡检说:“好,有了蓝秀才的两个该字,我就放心了。“
蓝秀才说:“穆巡检啊,就是有一点,有点太骇人了。”
穆巡检问:“怎么讲?”
蓝秀才说:“商之恩的脑袋挂在西城楼,血水顺着橡木笼子滴下来,城楼下的地砖上,留下了一层血痂子。”
穆巡检说:“蓝秀才啊,只要杀商之恩是对的,至于橡木笼子还在滴血,地上留下一点血痂子,都是小事。”
蓝秀才说:“人死了,就如灯灭了。商之恩是个大刀客,也是个人,死了也就灭了。把他脑袋挂在西城楼,等于让他在西峡口多活了十几天。橡木笼子滴着血水,恐吓的不是死掉的刀客,而是西峡口活着的人们。”
穆巡檢说:“这就叫杀一儆百。”
蓝秀才说:“西峡口杀鸡,还不许剁掉鸡脑袋,何况人乎?”
穆巡检说:“商之恩自当了刀客,已经不是人了。”
蓝秀才说:“刀客也是人当的。”
穆巡检说:“喝茶,喝茶。”
蓝秀才咂了两口新茶,说:“好茶,好茶。”
穆巡检说:“蓝秀才啊,商之恩脑袋上的血水,流上三两个时辰,就不流了。你还是去鹳鸟茶屋唱你的鼓儿哼吧。”
蓝秀才说:“穆巡检,要是捉了下一个刀客,砍了脑袋,让血水干了再挂到西城楼吧。”
穆巡检说:“好的,好的,听蓝秀才的。”
蓝秀才走了以后,穆巡检说:“哪个大刀客掉脑袋的时候,脖子上不流血?这个蓝秀才,真是嘴里吃条鱼,手里拿条鱼,胳肢窝里夹条鱼,多余啊。”
穆巡检卸任,接任的是虎巡检。巡检司的巫捕头按照往常惯例,叫了西峡口的士绅和各个商铺的老板,在鹳鸟茶屋设宴为新来的虎巡检洗尘;为洗尘宴会助兴的,是西峡口几个说唱艺人。蓝秀才不是艺人,但他喜欢热闹,自然也算一个。
虎巡检是江南人,听惯了苏州评弹和江南小调,这让鹳鸟茶屋的桑老板很为难。西峡口没有人会唱苏州评弹,也很少有人唱江南小调。
桑老板问蓝秀才:“唱啥?”
蓝秀才说:“就是凑个热闹,唱啥都行吧。”
虎巡检坐在一把太师椅上,前边摆着一张枫杨木茶几,茶几上摆着一壶花茶。虎巡检喝着茶水,面无表情地听着老掉牙的南阳大调曲。桑老板唱《隐士词》的时候,虎巡检倒是听懂了几句:
看破红尘,一片浮云。
名利二字莫在心,总不如归山乐天真。
闲来时独对蒿窗把诗吟,闷来散步出柴门。
但只见青山淡淡,绿水滔滔柳垂金。
落花万点红相衬,茅庵一带净无尘……
虎巡检问身边的巫捕头:“还有可听的没有?
巫捕头说:“蓝秀才的南阳鼓儿哼,还是能听的。”
虎巡检说:“那就来个鼓儿哼吧。”
巫捕头走到蓝秀才身边,弯下身段对蓝秀才说:“虎巡检想听你的鼓儿哼。”
蓝秀才一手敲打着羊皮鼓,一手将两个很薄的犁铧片子碰撞出响亮的声音,唱了他最拿手的《大实话》:
说天亲,
天也不算亲,
天有日月和星辰,
日月穿梭使人老,
带走世上多少人。
说地亲,
地也不算亲,
地长万物似黄金,
争名夺利多少载,
看罢旧坟看新坟……
蓝秀才吐字清楚,声音响亮。虎巡检听了蓝秀才的南阳鼓儿哼,满脸还是没有表情。
巫捕头问:“蓝秀才的鼓儿哼,唱得不错吧?”
虎巡检说:“声音倒是不错,只是这词,有点和欢宴不搭配。”
巫捕头平日也来鹳鸟茶屋,听到的南阳鼓儿哼,都是这样的玩意儿。虎巡检说和欢宴不搭配,巫捕头仔细品味,觉得是有点不搭配。人家千里迢迢来当巡检,是个从七品的官员,相当于内乡的县丞,欢迎宴会上唱的却是“争名夺利多少载,看罢旧坟看新坟”,真的是不搭配。
虎巡检不高兴,巫捕头也就不高兴了。他走过去拍拍蓝秀才的羊皮鼓,说:“蓝秀才,这么高兴的欢宴,不要唱争名夺利的,也不要唱新坟旧坟的。”
蓝秀才说:“这是《大实话》,也是鼓儿哼的老词,不是我编的。”
巫捕头说:“你编个新词,让虎巡检高兴高兴。”
蓝秀才说:“虎巡检是个秀才,我也是个秀才,哪有一个秀才为了让另一个秀才高兴,就把唱了几辈子的老词给改了?那还叫大实话吗?”
巫捕头说:“你这个秀才没进衙门弄个一官半职,那就应该编个新词,伺候伺候虎巡检。”
蓝秀才说:“当巡检和不当巡检,秀才是一样大的。”
巫捕头说:“蓝秀才啊,一百个秀才,也没有一个巡检大啊。”
蓝秀才拎起羊皮鼓,对巫捕头说:“他当他的巡检,我当我的秀才,就此别过。”
竟没跟虎巡检打一声招呼,就走了。
巫捕头对虎巡检说:“西峡口是个小地方,秀才很少,就把蓝秀才惯得没大没小了……”
虎巡检说:“蓝秀才唱得不错,但是这个词一定要改改,换个日子,让蓝秀才来巡检司,亮亮嗓子再唱一回。”
过了十几天,虎巡检把几页米黄的宣纸递给了巫捕头,说:“这是巡检司马师爷改的南阳鼓儿哼,新词,送给蓝秀才,让他琢磨琢磨,来巡检司唱唱吧。”
巫捕头拿着宣纸,从南大街的石板路走到北大街的石板路,找到了蓝秀才的院子,把新词递给蓝秀才,说:“这是巡检司马师爷改出来的新词,好好练练,后天就去巡检司唱给虎巡检听。”
蓝秀才没有接那米黄色的宣纸,说:“我要是不去唱呢?”
巫捕頭说:“蓝秀才啊,那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把宣纸扔在蓝秀才院子中间的枫杨木小桌子上,噗嗒噗嗒消失在石板路的尽头了。
蓝秀才喝下一碗老茶,抻开宣纸,见马师爷的蝇头小楷很规整,一群大雁一样,飞翔在宣纸上:
说天亲,
天也不算亲,
巡检司内天地新。
来了一个虎巡检,
明镜高悬比天亲……
蓝秀才把宣纸扔到地上,踩了两脚,说:“这是在糟蹋鼓儿哼啊!”
过了两天,巫捕头敲敲蓝秀才的门,大声说:“蓝秀才,巡检司的八抬大轿来了。”
蓝秀才从门缝里挤出脑袋,说:“八抬大轿从巡检司抬来,还抬回巡检司吧。我不坐八抬大轿,我也不唱鼓儿哼。”
巫捕头把脑袋凑到蓝秀才跟前说:“你唱也得唱,不唱还得唱。”
蓝秀才把脑袋缩回去,关上大门说:“我不唱就是不唱。”
巫捕头没有请到蓝秀才,自己坐上虎巡检的八抬大轿走了。
很快,巡检司的马师爷来了。跟在马师爷后边的,还是那个八抬大轿;八抬大轿之后,是巡检司衙门的八个衙皂,穿着通身的黑衣服,腰上都挎着长刀。
马师爷是跟着虎巡检从南方来的,也是个秀才。他拍拍蓝秀才生着铜锈的门环,轻声说:“蓝秀才,我是巡检司的马师爷啊。”
蓝秀才隔着门缝说:“我不认得九爷十
爷,我只有一个大爷,早就死了。”
马师爷又拍拍门环说:“蓝秀才啊蓝秀
才,你的南阳鼓儿哼很好听,虎巡检很爱听。”
蓝秀才说:“他爱听我不爱唱。”
马师爷说:“较这个真干啥哩?”
蓝秀才说:“那天欢宴上,我唱过了。”
马师爷说:“你那天唱的是老词,今天要唱新词。”
蓝秀才说:“谁想唱这个新词,就让谁唱吧。”
马师爷说:“蓝秀才啊,你今天不去巡检司唱鼓儿哼,这个八抬大轿就横在你门口,把南北大街堵住了。”
蓝秀才说:“堵住就堵住吧。”
马师爷摆摆手,八抬大轿就横在西峡口大街上,不但堵住了蓝秀才的大门,也把南北大街堵住了。不一会,八抬大轿南边拥了一群人,北边也拥了一群人。马师爷站在八抬大轿前说:“八抬大轿是接蓝秀才去巡检司唱鼓儿哼的,他出来坐上八抬大轿,南北大街就不堵了。”
当时,商铺的伙计正在搬运一台德国摇把子唱机,这唱机从上海运到汉口,又从汉口运到老河口,好不容易从老河口运到西峡口码头,却被堵在了蓝秀才的门前。伙计拍拍蓝秀才的门说:“蓝秀才,巡检司的八抬大轿可不是谁想坐就能坐的。”
蓝秀才说:“我不想坐。”
商铺的伙计说:“我给北关穆之冠送唱
机,堵在你大门口了,你坐上八抬大轿,南北大街就通了。”
蓝秀才不得已开了大门。
马师爷随着商铺伙计,走进了蓝秀才的院子,说:“蓝秀才啊,巡检司的巡检是内乡县派出的,内乡的知县是南阳府派出的,南阳府的知府是开封都督府派出的,开封都督府的都督,是大清朝的皇帝派出的,你蓝秀才蔑视巡检司,就是蔑视内乡县,就是蔑视南阳府,就是蔑视河南,也就是蔑视大清朝;你蓝秀才蔑视西峡口的巡检,就是蔑视内乡的知县,就是蔑视南阳的知府,就是蔑视河南的都督,也就是蔑视大清朝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
蓝秀才说:“马师爷啊,大清律里规定,秀才不给官员下跪,秀才不上刑法。虎巡检还敢把我捆到巡检司去?”
马师爷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一百个秀才也没有一个巡检大。”
蓝秀才漠然看看马师爷,说:“那我要就是不去呢?”
马师爷说:“巫捕头手里的衙皂还不敢把你捆去?大清朝的律条是死的,巡检是活的,捕头是活的,活人能叫死的律条变活,也能规制住一个秀才。再说,我也是江南的秀才,还不是跟着虎巡检来西峡口讨碗饭吃?你是一个江北的秀才,和我是一样的。巡检司抬举你,你是个秀才;不抬举你,你就啥也不是。”
马师爷来自江南,把长江以北到黑龙江这么大一块地方,都叫江北。西峡口在河南南部,在马师爷的眼里,也叫江北。
蓝秀才咂吧咂吧马师爷的话,软里带硬,笑里藏刀,很无奈地说:“去吧。”
揽起蓝色长衫,坐上八抬大轿,蓝秀才去了巡检司。马师爷俨然是一个跟班,一只手扶着轿子,一只手随着轿夫的步伐甩动着。他隔着轿帘子对蓝秀才说:“你唱一辈子鼓儿哼,唱一辈子河南大调曲,也没有坐八抬大轿风光吧?”
八抬大轿经过了南北大街,西峡口的人都知道了蓝秀才坐了巡检的八抬大轿,商铺伙计们都惊羡不已,说:“蓝秀才这个鳖娃子,坐在巡检的八抬大轿里了。”
这是蓝秀才没有想到的。没坐八抬大轿之前,他没把巡检当回事,也没把八抬大轿当回事,现在坐在八抬大轿里,看到一街两行人们的眼神,蓝秀才忽然明白巡检就是巡检,秀才就是秀才,巡检和秀才是两个不同的物品,价格是不一样的,价值也是不一样的。
巡检司门口那两个巨大的铁狮子,平日里蓝秀才需要仰视,才能看到铁狮子的头顶,坐上八抬大轿,不用仰视,就能看到铁狮子头顶上那九个铁疙瘩。平日里看巡检司的各色人等,个子高高的,坐在八抬大轿上,再看巡检司里的人,包括师爷马秀才,也矮小了许多。蓝秀才终于知道了,人啊,一旦坐上了八抬大轿,对西峡口的一切就都有了居高临下的感觉。巡检每天都坐八抬大轿,每天都居高临下,所以蓝秀才在虎巡检的眼睛里,也是矮小的。
巡检司大院子里,三棵巨大的枫杨树树荫浓密,坐在树下,身上浓荫笼罩,竟没有点滴阳光。虎巡检躺在一张竹编的睡椅里,看见师爷领着蓝秀才来了,缓慢坐起来说:“蓝秀才啊,还是想听你唱唱南阳的鼓儿哼啊。”
蓝秀才说:“那天欢宴上,唱过了。”
虎巡检说:“那是老词,我想听听巫捕头给你的新词。”
蓝秀才说:“新词,我是唱不出来的。”
虎巡檢说:“蓝秀才啊,还是你的嗓子,还是那个调调,新词老词都是一样能唱出来的。”
蓝秀才说:“我是个秀才,你是个拔贡,哪有秀才唱拔贡比天地爹娘还亲的?”
马师爷说:“拔贡比秀才高了一点点,但是拔贡当了巡检,就比秀才高了很多。”
虎巡检说:“蓝秀才啊,马师爷也是个秀才,能写出来南阳鼓儿哼的新词,你也是秀才,就应该也能唱出来。”
马师爷把羊皮鼓架子搬到蓝秀才身边,把两个铁片递给蓝秀才说:“我听了你唱的南阳鼓儿哼,就学了个七八分。”
马师爷就把自己写的新词哼唱了一遍,说:“蓝秀才,我唱了一遍新词,我还是我马师爷,我还是我马秀才;你也唱吧,小不了你的身份。”
蓝秀才一手敲敲羊皮鼓,一手打着两个铁片子,清了清嗓子,唱出了马师爷新编的南阳鼓儿哼:
说天亲,
天也不算亲,
巡检司内天地新。
来了一个虎巡检,
明镜高悬比天亲。
说地亲,
地也不算亲,
巡检司内四季春。
来了一个虎巡检,
五谷丰登比地亲。
说爹娘亲,
爹娘也不算亲,
巡检司内恩德深。
来了一个虎巡检,
你比爹娘还要亲……
放下鼓棒,丢下两个铁片子,蓝秀才如释重负地坐到了虎巡检身边的椅子上,喝了一口茶,乜斜了虎巡检一眼。
虎巡检说:“蓝秀才啊,唱得好,唱得好
啊。你是西峡口的秀才,你这样唱,就给西峡口人做出了个榜样。不论是虎巡检还是穆巡检,都是西峡口的父母官,对待西峡口的百姓,都比爹娘还要亲啊。”
马师爷说:“蓝秀才啊,秀才就要有个秀才的样子。你刚刚唱新编鼓儿哼的样子,就是秀才的样子啊。”
蓝秀才无语。
虎巡检拎着一个深蓝色的布袋子走过来,对蓝秀才说:“布袋子里有云南老树普洱二斤,福建武夷山大红袍二斤,都是上好的茶叶,蓝秀才,你好好润润嗓子,巡检司需要你来唱一段鼓儿哼的时候,你可不要推辞啊。”
蓝秀才依然无语。
虎巡检接着说:“蓝秀才,这还有苏州丝绸二丈六尺,足够你缝制一件体面的长衫了;还有银圆三十块,算是对你唱鼓儿哼的犒劳。”
虎巡检出手如此阔绰,是蓝秀才想不到的。他坐上八抬大轿穿过南北大街回家的时候,阳光灿烂。蓝秀才掀开轿帘,沿街看过去,西峡口似乎一瞬间变了个模样,自己也似乎一瞬间变了个模样。
南大街的石板路上落满阳光,北大街的石板路上也落满阳光,在南北大街上行走的人,身上都落满阳光。蓝秀才恍如隔世地说:“每个人都在世上走来走去,看似是各走各的,其实每个人走的步子都是一样的,道路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世道吧?”
蓝秀才去巡检司给虎巡检唱了新编的南阳鼓儿哼之后,去鹳鸟茶屋的次数就日渐少了,茶客们也慢慢生疏了蓝秀才的弦音和鼓声。偶尔,鹳鸟茶屋的桑老板遇到了蓝秀才,也只是诺诺几句,并没有请蓝秀才去茶屋喝茶唱曲的意思。
慢慢地,蓝秀才寂寞了。
后来,虎巡检走了,苏巡检来了。巡检司的师爷也换了,他和巫捕头一起跟着巡检司的八抬大轿,去请蓝秀才参加巡检司的欢宴。
一群说唱艺人,还都是陈词滥调,让新来的苏巡检很是不耐烦,说:“来个压轴的。”
压轴的是蓝秀才。他问巡检司新来的师爷:“唱啥?”
师爷说:“苏巡检听虎巡检说,你的新编南阳鼓儿哼很好。把虎巡检换成苏巡检就是了。”
蓝秀才说:“我就像是烟花院的头牌,跟谁睡觉都是一样的。”
师爷说:“蓝秀才是个明白人。”
蓝秀才一只手敲响了羊皮鼓,一只手敲响了两个犁铧片子,清了清嗓子,鼓儿哼就从蓝秀才的口鼻里流淌出来:
说天亲,
天也不算亲,
巡检司内天地新。
来了一个苏巡检,
明镜高悬比天亲……
唱罢,蓝秀才收了苏巡检的犒劳,怡然自得地坐上了巡检司的八抬大轿,怡然自得地回到了北大街他那个院子里。
辛亥革命来了,西峡口的最后一个巡检颜仕璜响应革命之后,又当了一个多月民国的巡检,西峡口巡检司就撤销了。蓝秀才走过巡检司门口,那两个铁狮子还在,他摸摸铁狮子的底座说:“我这南阳鼓儿哼唱给谁听呢?”
很快,镇嵩军司令刘镇华手下的伍旅长开进了西峡口,驻扎到了巡检司的老院子里。伍旅长说:“听听南阳的鼓儿哼。”
就有五个马弁背着盒子炮,敲开了蓝秀才的大门说:“走,去给我们伍旅长唱唱南阳的鼓儿哼。”
蓝秀才说:“我是个秀才,不是个唱鼓儿哼的。”
马弁说:“在我们伍旅长眼里,秀才连根?毛都不如。”
蓝秀才说:“镇嵩军,不就是一群刀客和土匪吗?”
马弁把盒子炮在蓝秀才的额头上点点,说:“我们镇嵩军的司令刘镇华,任命状是袁大总统签署的,你一个秀才,说我们镇嵩军是刀客土匪,那就是说袁大总统也是刀客土匪。”
蓝秀才说:“我不知道袁大总统,我就知道宣统皇帝。”
马弁说:“宣统早他妈滚蛋了,现在的天下,远的说是袁世凯大总统,近的说就是我们伍旅长。”
五个马弁把羊皮鼓和蓝秀才装到一辆汽车上,说:“蓝秀才,识相一点,唱得让伍旅长高兴了,抓一把银圆给你,就够你花个年儿半载的了。”
伍旅长和巡检司的巡检一样,躺在枫杨树下的竹椅子上,一顶宽边礼帽盖着半个脸膛,两把盒子炮摆在随手能够得着的地方——左手伸出来,能摸着左边的盒子炮;右手伸出来,能摸着右边的盒子炮。见蓝秀才来了,伍旅长取下盖在脸膛上的宽边礼帽,说:“蓝秀才啊,到了西峡口,就听说你的鼓儿哼唱得不错。唱一个,让老子听听。”
蓝秀才说:“旅长,你比我小好多岁呢,咋能是我的老子?”
伍旅长说:“我有一千人马,我双手都能打盒子炮,在豫西地界,我走到哪儿,就是哪儿的老子。”
蓝秀才咽下了一口唾沫,觉得嗓子里堵得慌。
伍旅长说:“过去,你给巡检唱什么,就给老子唱什么?”
蓝秀才敲起羊皮鼓,打响铁犁铧片子,唱起了南阳鼓儿哼:
说天亲,
天也不算亲,
西峡口里天地新。
来了一个伍旅长,
明镜高悬比天亲……
伍旅长大喊一声:“拿一百块银圆。”
军需主任捧着一摞草紙裹着的一百块银圆,递给伍旅长。
伍旅长在手里撂了三下,递给了蓝秀才,说:“蓝秀才,唱得不错。你这么一唱,我这个刀客出身的旅长,就有了一个秀才儿子。”
蓝秀才愕然。
伍旅长说:“你说我比爹娘还要亲,那我不就是你的亲爹了?”
摆摆手又说:“送蓝秀才。”
蓝秀才把一百块银圆装进长衫的口袋里,坐上了伍旅长的汽车。
伍旅长对一个马弁说:“拉到老鹳河滩
上,敲了。”
马弁很疑惑地问:“敲了?”
伍旅长说:“是,敲了。”
马弁问:“为何?”
伍旅长说:“日他祖奶奶,一个秀才,能唱我比他爹娘还亲,我要这样舔屁股沟子的秀才弄啥哩?人一个亲爹一个亲娘,是谁也不能代替的。蓝秀才连这个路数都不懂,就不配活着,敲了。”
马弁说:“旅长,既然敲了,还给他一百块银圆干啥?”
伍旅长说:“老子向来赏罚分明,一码归一码,就用那银圆埋葬蓝秀才吧。”
大清国没了,刑不上秀才这一条也就废了,马弁的盒子炮响过,蓝秀才就倒在了河滩上。然后,蓝秀才的脑袋装进橡木笼子里,挂到了西城楼上。
血红的晚霞从老鹳河边的枫杨树上流淌下来,把西城楼染得血红血红。
那个橡木笼子也染红了。
责任编辑 丁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