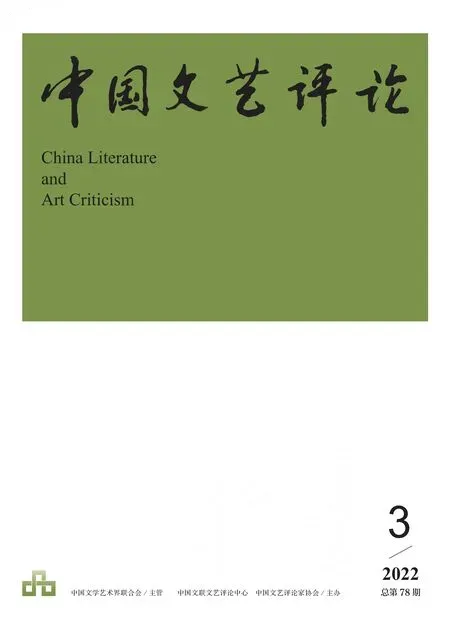传记电影的诗品与哲思
——访影视导演丁荫楠
■ 采访人:张 成
一、“学门手艺,吃碗干净饭”
您曾在多个场合提及朴素的家训:“谁家没有本难念的经”“夜晚千条路,早起卖豆腐”“学门手艺,吃碗干净饭”,家训与您从事电影事业有着怎样的关系?您是怎样走上导演之路的?
1938年10月16日,我出生在天津王庄子,父亲临终时留下遗言:“让孩子们念书。”后来母亲始终坚持让我考大学。少年时期,家道中落,虽然日子穷苦,但我受母亲呵护、影响,反而有了争气的动力。母亲教导我:“要儿自养,要财自挣,要有骨气。”从小学到初中,每当我早晨离家上学时,母亲总追着念一句:“好好念书。”我虽然答应着,但心中总幻想着别的事情,从未专心听课,总被许多课业以外的事情吸引着,比如参加红领巾话剧团节目演出,演出自创剧本《铁道游击队》《中队的荣誉》等等。我幻想长大后做话剧演员,常常放了学和同学合伙凑钱去电影院或剧场看戏。因为心思不在学业上,考不上好高中,我16岁便去天津钢铁厂当工人,我自尊心强,知道自己对不起母亲。母亲后来让表姐托关系给我在北京找工作,进京后,我打开了视野,内心产生了彻底改变命运的动力。
17岁的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后来在北京医学院生化学系做教学辅助人员,1958年下放当了两年农民。从1956年至1961年,我感到自己的生活没有主动权,没有专业技能就只能随波逐流。但我也遇到不少好心人:一位熊教授让我搬出四人宿舍与他同住,这让我有了安心学习的环境;老红军胡姐非常照顾我,给了我挣脱困境的动力;同时我还参加北京西城区的业余文化活动,后来又参加了北京市工人业余话剧团,和北京人艺、青艺的专业艺术家来往,吴雪、白凌、刁光覃、于是之、舒绣文、朱琳、童弟、童超经常到话剧团教我们。看北京人艺、青艺、实验话剧院的演员们排练,让我十分着迷而不能自拔,正因为受到艺术的陶冶与艺术家人格魅力的感染,我后来走上了艺术之路。
工作之余,我会在实验室大声朗诵戏剧里的大段台词,模仿名演员表演的话剧片段,我曾在北京医学院晚会活动中表演《风暴》中施洋的演讲、勾践在《胆剑篇》里的独白、《胡笳十八拍》里蔡文姬的诗,唱京剧等等,活跃的艺术实践使我性格变得开朗,变得乐观积极。当时每月37元工资,除了12块5毛的伙食费,剩下的我都买了戏票。在北京医学院的五年生活工作经历,释放了我潜在的力量,激发了我的艺术潜质。后来,一些青年教授支持我考北京电影学院,院领导也特准我以调干的身份考大学。
参加工人业余话剧团后,我迷上了表演,立志做话剧演员。原总政话剧团的李维新导演认为我做演员的条件不足,便建议我考导演系。1961年9月,我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报到,录取我的周伟老师说我的成绩并非是最好的,可我的天赋让老师们感到是个可造就之才。现在想来非常感谢周老师,其实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在哪里。

图1 丁荫楠在执导电影《邓小平》
1969年我被分配到广东话剧团,心想从此拍不了电影了,当时的失望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剧团领导王志华看出了我的心思,并向她爱人——珠影厂的革委会主任孙再昭推荐了我,1972年落实知识分子“归口”政策,我来到珠影厂,从此开始了电影导演生涯。
二、拍第一流的人物来展现中华民族史
戏曲评论家靳飞评价您是“史记式导演”,是指您执导的系列传记电影是新中国难得的有着鲜活而真实的情感的历史纪录,请问您为何对传记电影情有独钟?您的传记影视作品涉及周恩来、邓小平、孙中山、鲁迅等,有伟人、有传奇性的角色、有艺术家、革命家和政治家,请问您是如何选材的?
我曾思考过中华民族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是靠什么支撑下来的。众所周知,人民创造历史,历史造就人民英雄。因此我特别关注历史中的英雄、英雄的历史地位和在历史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尽管有兴衰,却始终没有消亡,我对其中的历史规律很感兴趣。拍《孙中山》时,我读了不少文献,了解到近代以来中国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奴役。同时,中华民族的精英领导了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直到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民族精英与人民群众一道,推动中华民族在历史的发展中螺旋式上升,中华民族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是靠一系列英雄人物大无畏的牺牲和创造来实现的。
对我而言,拍戏就是学习历史,学习历史中的英雄人物是怎样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奋斗的。《孙中山》拍的是民国史,《周恩来》拍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邓小平》拍的是改革开放的历史,《鲁迅》拍的是“左联”的历史,每部电影都通过一个核心人物来串起历史,以此为前景,进而延展到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所形成的巨大力量。在北京电影学院求学期间,我观看了大量的苏联电影,学习的艺术理论以马克思、恩格斯美学为主,审美是在苏联文艺熏陶下形成的。苏联电影的特点是格局宏大,富有史诗品格。个性、个人经历以及自身的努力方向决定了每个导演的专注方向,有的导演擅长讲故事,而我热爱传记电影,爱用史诗的叙事方法来拍人物,这是我从学生时代就确立下来的。
选材时,我会从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精英中选第一流的人物来拍。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流的人物,而我电影的主题一定是歌颂中国发展史、胜利史的,即历史是中国人民创造的。
《周恩来》等电影在豆瓣上评分很高,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您执导的主旋律电影是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精品,受到各个时代的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喜爱和推崇,这和您创作上独特的诗化、散文化的艺术特点分不开,请问您是如何确立自己艺术创作的美学品格的?
传记电影能表达对生活的理解,即每个个体都是与大时代脉搏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电影一定要把时代氛围表现出来。哪怕写小人物的感受,也不能只局限于描写小人物,而是要通过小人物把时代氛围映射出来。比如我执导的《春雨潇潇》中雨蒙蒙的感觉,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环境万马齐喑的隐喻,我借此在片中寻求一种压抑的感觉,运用“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意象,营造“四·五”事件前后中国人心境的状貌。《逆光》则表现了朝气蓬勃的感觉,我在片头设计“雨中的上海”,暗示一种诗意的开端:春雨的清晨,大都会的人们从各个角落出发,汇聚于车上、路上,奔向自己的工作岗位。这表现了一种流动的生活,当时有一位纺织女工看后告诉我,这就像她每天的早晨一样,给她一种亲切感。《周恩来》表现了周总理“支撑大厦”的感觉,《孙中山》表现了孙中山独树一帜、愈战愈勇的感觉。

图2 丁荫楠在执导电影《周恩来》
《孙中山》拍的是我心中艺术化了的孙中山,而拍周恩来,拍的是人民心中的周恩来。《周恩来》表现了周总理的担心、无奈以及他的劳累,他支撑住了“大厦”,电影契合人民对周总理的理解,符合普通老百姓对总理的认识。这些电影的表现方法都是诗化的、散文化的。我认为艺术的基础就是个手艺活儿,手艺做到位,才能有美的升华。拍传记电影表达了我观察历史、观察生活的方法,电影中的细节是为描述宏大历史和广阔世界服务的,而不是鸡零狗碎式的个人恩怨。
《周恩来》的主演王铁成曾向我表示信任地说:“你画圈,我往里面跳,保证严丝合缝。”周恩来总理在生活中平易近人,却又气质高贵。因此周恩来总理的形象只靠表演是无法完全呈现的。电影是综合艺术,要靠环境、气氛把戏渲染出来,周恩来总理这一角色要真正在电影中实现,必须依靠整体氛围,依靠其他演员配合,诸如警卫员等人物的配合,才能将周恩来“这一个”特定时代的形象展现出来。同时我也跟王铁成说,特写镜头完全由你表现,需要你表现准确,其他的由我组织。拍《周恩来》时,张玉凤等人在旁指导,片中周总理喊着“薛明”(贺龙夫人)来到贺龙元帅的灵堂,这是根据真实历史拍摄的。此外,拍周恩来总理视察乐队的情形时,我们特别想表现总理的艺术修养,因此我设计了总理离开时,突然放慢了脚步,一边听乐队的演奏一边打拍子,以此来表现周总理喜欢音乐,也为角色赋予了人性的色彩。
您是如何用具体手法实现电影真实性的呢?
我认为,时代和国家的大氛围应该充盈在影片中,哪怕电影讲的是小故事,也应该具有这种表现意识。比如《逆光》拍的是工人的故事,它聚焦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对国内的冲击,国门打开后,有的人经受不住各种诱惑,有的人则顶得住,以此来展现民族自信和民族自尊。《逆光》虽然是生活流,但我希望拍出史诗的感觉,通过影像、造型、细节、描写等诸多方面去呈现我的哲学观。所谓造型,无论是声音造型还是画面造型,都要体现导演对影片的全部创作意念,同时隐藏情节于生活图景中,让观众自己去发现、去辨认,从而增加生活实感,加强情节魅力和人物的心理刻画。
电影不能仅诉诸感官刺激,必须注重电影的真实性,真实的电影离观众才近。电影是影像的艺术,但凡细节有一点不真实,观众就会走神儿。像《逆光》给人的感觉是写实的,其实那些场景都是营造出来的,不是到实景中拍的。《逆光》中的大光明影院前的行人都是被组织的,只有个别过场镜头、大全景是抢拍的真实街景。《孙中山》中的场景也是造出来的。《周恩来》的环境是真实的,其中周恩来总理在北海公园怀念老舍先生时,回忆起看《茶馆》的场景,这一场景用的是于是之演出《茶馆》的实景拍摄。《邓小平》中,邓小平在天安门的场景也是组织的。对于这些电影中的重要场景,我尽量用纪实性的拍法,使之看起来更像纪录片。
您觉得其他比较好的传记电影有哪些?其艺术亮点是什么?
大学时代,我看了很多苏联电影,当时国产电影和苏联电影大都是现实主义风格的,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新中国成立后的《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都是现实主义作品。新时期以来,西方电影一下子涌了进来,当时北京各大机关、院校都在放映内部参考片,这些片子大都是西方电影。我当时天天赶场看电影,像《战争启示录》《猎鹿人》《教父》《日瓦戈医生》《孤星泪》《雾都孤儿》都是在这一时期看的。卓别林的电影、《出水芙蓉》《走出非洲》《莫扎特》这些电影更让我坚定了自己的叙事方法。我还看了日本战争片,影片中再现了壮丽的历史画卷,这些让我颇受启发,其在气魄、格局上与我大学时代看的苏联电影是吻合的。因此,当我有了执导故事片的机会时,我就将自己的所学所思都放到影片里了。
三、理想的文艺评论是巨人的肩膀
作为创作者,您怎么看待创作和评论之间的关系?请问您理想中的电影评论是怎样的?在您的从艺生涯中,有没有遇到过印象深刻的评论家,或受过其帮助,或受其评论的启发?
钟惦棐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电影评论家。钟老看了《孙中山》后,尤其是片中孙中山消失在人海的镜头,颇受触动,他认为这一场景有千古绝唱之感。我认为,钟老的称赞不是给我的,而是给孙中山的,因为电影拍的人物是伟大的人物,而我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来看历史和拍历史的。同时,我的创作深受钟惦棐先生的电影理论评论的影响,比如《逆光》就是响应他的理论倡议,即电影要摆脱戏剧化,要通过造型等来叙事,突出影片的诗化风格。《逆光》等没有被戏剧束缚住,也未严格按照起承转合的方法叙事,而是散点式地呈现,更多地按照散文来叙事。拍完诗化的《春雨潇潇》后,我又拍了《逆光》,钟惦棐先生看后非常兴奋,认为《逆光》是划时代的。2021年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致敬”单元展映了《逆光》等电影;2020年,我的《电影人》是第14届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的闭幕影片。这两部电影在这两个影展上放映后,年轻人很喜欢,在他们的印象里,我是拍主旋律电影的,没想到我还会拍先锋的艺术电影。我认为,红色的主旋律电影就是艺术电影,二者的创作逻辑是相似的。黄宗江说我的电影是“艺术的主旋律电影”,我认为这个概括比较准确。
此外,仲呈祥是杰出的评论家,倪震的电影评论也极富见地。比我年轻的一辈人中,我很欣赏戴锦华,戴锦华的理论工具比较西方化、现代化,但她关注的是中国本土问题,对现实具有关切性和批判性。

图3 丁荫楠在给饰演鲁迅的濮存昕说戏
您提到散文性和文学对您创作的重要影响,能具体谈谈这方面的创作心得吗?
除了从苏联电影中受益良多,我还受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非常善于白描,比如“三言二拍”的特点就是白描。我偏爱将大的国家环境和局部细节结合起来表现人物心理,从对局部细节的表现中提炼出整体情形。我的电影不太注重面面俱到式的讲述方法,而是从模式中跳脱出来,注重用细节、人物动作、造型来体现宏观。在第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中,我凭借《孙中山》获得了“最佳导演奖”,一同提名的影片还有谢晋导演的杰作《芙蓉镇》。评委们最终把这个奖授予了我,就在于他们认为影片是深厚的历史感与抒情诗意的有机结合,影片再现了历史,又传达了艺术家的人生感受和对世界的思考,实现了伟人与历史、导演主体意识与历史真实的统一。评委们可能觉得《孙中山》的亮点在于手法“新”,《孙中山》的色调就是尽量还原我心中的历史色调。

图4 丁荫楠在执导电影《邓小平》
我的电影不按照常规故事片起承转合的拍法来拍,而是用诗化的拍法,重在以造型叙事来再现历史真实,对历史有哲学层面的概括。拍电影不能只拍事件,只拍人物的“小”,不能“掉”在情节里,而要拍人物关系和性格,用写意的镜头描写人物的心理。以《孙中山》为例,孙中山为什么被推举成国父,成为民主革命第一人?我觉得是因为他个人的悲剧是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影片展现了他的四次起义,每次起义的展现各有不同。《鲁迅》则用鲁迅的七个梦展示鲁迅晚年的遗憾,如果用起承转合的线性叙事则很难实现,尤其是在短短两个小时内是很难做到的,把影片照本宣科地拍成影像教材非我本意。因此我聚焦鲁迅的人生大爱,通过造型的诗化语言,提炼出鲁迅心理的发展线索。拍《邓小平》时,我们无法面面俱到地在两个小时内全面展现伟人邓小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形象,邓小平光辉伟大的形象是不可能在两小时内被穷尽的。因此我们当时设想的是,让观众看到感性的、活灵活现的、鲜明而能触摸得到的、富有性格魅力的邓小平。为了避免堆砌事件,我们选择将邓小平一系列的伟大革命创举转变成情感的冲击波,把理性的事件转化为感性的情绪,对具体事件的呈现点到为止,放至后景乃至远景,前景呈现的则是邓小平的行为、思想和情感。
通过拍摄《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我得出的有效经验是:塑造伟人,决不能空凭艺术家的主观想象。艺术家仅凭个人经历是无法想象伟人的生活和性格的,必须充分采访伟人的家属以及共事过的同事、秘书、警卫人员等,利用他们所提供的细节来塑造人物。台词也是如此,要根据回忆、记录来创作,不能随意胡编,只能在真实历史素材中进行选择。
您提到京剧对您影响很深,有评论说您拍的是“老生戏”,有电影的程式美,戏曲艺术对您创作的影响有哪些?
我从小酷爱京剧。2009年,我拍了戏曲电影《响九霄》,这圆了我的戏曲电影梦。恩师陈怀皑曾想把大武生裴艳玲的《钟馗嫁妹》搬上银幕,有意让我做执行导演,没承想陈怀皑导演去世后,这个项目就搁置了。之后在中国文联党组的关心下,裴艳玲的《响九霄》被我搬上银幕。这是一部歌颂京剧艺术家响九霄替康有为、梁启超等志士传递变法论给光绪皇帝,为推动维新变法而牺牲的豪杰义举的主旋律现代新编历史京剧。这部影片贯穿了爱国豪情、热恋感情、艺术激情,这“三情”便是《响九霄》的气质,因此在剪辑时,除了按照锣鼓经的原则来剪辑外,尤其注重长镜头的抒情段落,即《响九霄》核心唱段的完整与连贯。
在剪辑故事片时,我同样在心里“打着”锣鼓点,我的电影节奏都是按照京剧的锣鼓点剪的,《孙中山》中几个牺牲的镜头,都是按照锣鼓点剪的。重要场景的剪辑就像一个重锤,角色的心理转折变化要鲜明呈现,而锣鼓点能体现鲜明的节奏感,成为心理节奏的外化。
中国传统戏曲注重表现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助人为乐和牺牲精神,这些阳光向上的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结合构成了我的文化养料。我是穷孩子出身,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很感恩。求学期间,我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定有序的环境中,适合做学问、研究艺术。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以及对我们进行的限制和制裁。为此我们奋发图强,在充满爱国热情的环境中成长,我的创作就是为了歌颂党的政策、歌颂祖国、宣传优秀杰出的人物。我的作品都是追求宏大叙事的,展现大人物,讲求大情怀,主题都是鲜明的爱国主义。
四、一直拍下去,拍年轻人爱看的主旋律
您怎么看待当下文艺界的一些不良现象,尤其是一些艺术工作者违反职业道德和法律的行为?
当代电影已经是一种“用形象来表达的文本”,就像过去的书信,只不过大众语言变成了影像而已。尽管影像已经全民普及,大家用手机就可以拍自己心中的影像,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层次高低之分。所谓“高”,就是要拍阳光向上的、能体现很好教养的、有感染力的影像;要敬畏这个职业,拍电影是很高尚的,其价值在于凝神聚气、化育人心,这些巨大的社会作用是无法只用金钱来衡量的;此外,电影创作的格局应该更宏大,不能只是个人想法情感的宣泄,或成为情绪的“抚慰奶嘴儿”。
您怎么看待主旋律影视作品的未来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等作品受到了年轻人的广泛好评,您怎么看待当代年轻人热追主旋律影视作品的这一现象?
好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就该让年轻人喜欢,比如《觉醒年代》备受年轻人推崇,其中陈延年、陈乔年牺牲的场景就让观众深受感动。我觉得只要做到艺术真实,主旋律电影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在新时代,我们要注重主旋律影视作品的表现手法,比如《觉醒年代》中更多的是写人,写朋友、父子、母子关系,写人物的离别、牺牲,这些场景的艺术冲击力是很大的。
我不太认可“商业主旋律电影”这一说法。为什么呢?因为主旋律重在真实,重在如其所是地反映历史与生活。而商业电影注重感官刺激,注重对人性的批判。这二者单独拍,都能拍出好电影,但这二者的艺术逻辑是不兼容的。主旋律电影在情感上追求真实、感动,商业电影则追求娱乐、宣泄,二者的诉求也不同。强行将主旋律电影按照商业电影的逻辑去操作,既有可能伤害了主旋律电影的感染力,在商业上也可能不讨好。电视剧《觉醒年代》没有商业化的元素,但年轻人很爱看;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中的基层干部、连长、团长表现得都非常好,有血性,这部剧在年轻人关注的网站上打分也很高,这都说明主旋律影视作品按照主旋律的艺术规律去拍是完全能征服观众的。
在数字时代,虚拟技术极大地改变了电影摄制实践。这其中给观众直观感受的就是电脑特效,我也在思考观众在观看电脑特效制作的电影时,与观看传统的“手工”电影时心理会有什么不同。比如在制作主旋律电影时,过往的一些宏大场面是需要调动“千军万马”来实现的,在拍摄过程中需要克服非常多的现实困难。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主创人员在创作这些场面时,需要切实地与现实发生关系,动用想象力,调动一切真实性元素来达到艺术目的。但今天,再复杂的场景也可以通过电影特效做出来,哪怕做得再仿真,观众也知道这是电脑特效做的、是假的,包括那些做的像电脑游戏似的电影。换句话说,传统的电影制作是创作者与导演达成的心理默契,即导演在创作过程中动用一切现实的艺术手段来营造现实,而今天的电脑特效则将创作过程虚拟化了,把这一默契改变了,这尤其值得主旋律影视创作者的关注。主旋律影视作品和《权力的游戏》《指环王》这样的假定性作品不同,其核心诉求是“真实”,其时代感乃至现实主义的风格都要求真实,它关系到主旋律电影能否抵达观众内心和抵达的途径是什么的问题。
我儿子丁震也是导演,他会根据我的偏好带我看当下的新电影,给我介绍外国先进、优秀的电影,像《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这些电影都是他带我看的。我觉得这些电影还留存着电影艺术的优秀传统。比如,电影中好的人物能让观众感动,拍得好的人物一定是拍出人物在两难选择中的选择。好多经典电影中的英雄在两难时会选择牺牲自我,为什么他会选择牺牲自我?这是由信仰所致,这样的人物才伟大。你看那些为了新中国前赴后继的革命者们,在当时肯定不知道革命能不能成功,但他们坚信会成功,并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英雄遇到了非人的境遇,能坚持下来的,都是靠理想和信仰在支撑,他们具有超人的情怀。因此,在电影中歌颂这些人,就要歌颂这些人的本质,即他们的信仰。还是《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对老百姓苦难的心疼是发自内心的,他由此出发梳理了自己的信仰,也更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我拍电影,在外头拍了二十多年,顾不上家里,也是靠信仰支撑着,对儿子和太太都亏欠很多。我太太为了不让我分心,也不跟我说她自己的病情。好多朋友跟我合作拍电影,因为这些电影,国家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每当想起他们,我经常感到不安,因为为了达到艺术效果,有时候我的脾气很不好,现在想来,也想对伙伴们有个交代,我最近要出一本书《莫思量自难忘》,便是对他们的怀念。
我个人比较幸运,在工作中遇到的领导都非常支持我,使我远离一些无谓的干扰,像原珠影厂厂长孙长城、八一厂原厂长明振江、原北影厂厂长汪洋、原上影厂厂长徐桑楚、原西安厂厂长田伟,他们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广电部门的主管领导、中国文联党组及有关部门负责人都非常关心、呵护我的工作。这些领导见了我都问,你想拍什么?他们关心我拍的作品是不是符合国家需要,而不是能赚多少钱。即使在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后,我很幸运,没有遇到过经费方面的问题,我是在各级部门和领导支持下完成这些工作的。现在我还有创作的热情,会坚持一直拍下去,这是我这辈子树立的目标。
2021年9月8日,这是十年间笔者第四次来到丁荫楠导演家里,之前的三次曾随中国文联党组领导来看望丁荫楠导演,听他讲述筹划拍摄《启功》,到后来《启功》杀青、公映。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在童年时期,笔者便看过丁荫楠导演的《周恩来》,那时候对历史并不熟悉,只知道主人公是人民敬爱的周总理。令人过目不忘的,还有丁荫楠导演对影片氛围的考究铺陈。30年后,为了此次采访,重看《周恩来》等影片,《周恩来》中红色的窗帘、绿色的台灯瞬间将陈年记忆召唤出来。

图5 影视导演丁荫楠
丁荫楠导演对党、对国家、对电影的爱是三位一体的,其人如其影。这也决定了他的电影具有宏大的格局、雄伟的气魄和无言的大爱。同时,丁荫楠导演的作品又具有细腻白描、真实毕肖、形散神不散的美学特征。拍伟人传记电影,将情思与诗性置于前景,将事件置于后景,二者结合,是丁荫楠导演开创的艺术手法。丁荫楠导演总强调电影是门手艺,在采访过程中,其语言质朴无华,辞约而旨丰。丁荫楠拍的《周恩来》等传记电影,在笔者看来,是不可复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丁荫楠导演极其注重氛围的真实感,当真实环境就绪后,自然升腾出精神层面的真实感。这种特殊的创作方法,决定了时光流逝、物换星移后,影片中环境与精神层面都具有历久弥坚的宝贵写实价值。
丁荫楠导演作品独特的美学品格,尤其是其散文诗化的叙事特征,其反对常规起承转合线性叙事的美学观念,在今天看来,愈发显示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卓然的先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