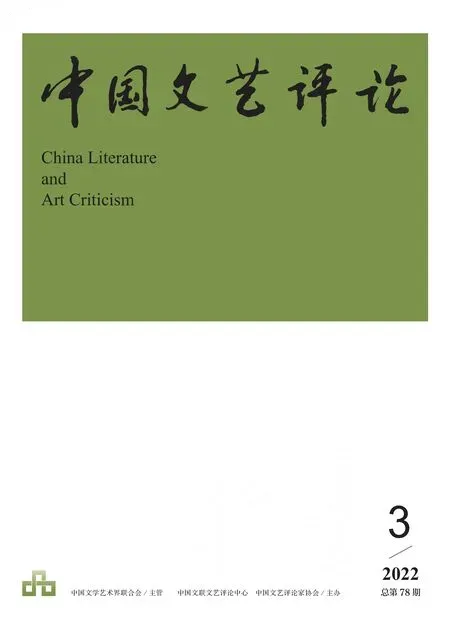现代诗:功能的“弱化”与“转型”
■ 陈仲义
一、 有用与无用的“混用”
古代中国,诗歌之用集中在“教化”上。早在2500年前,《论语·阳货》就庄重宣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继续展开为 “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真乃荦荦大端。接着有南朝裴子野之说“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雕虫论》),及至白居易起劲“追加”:上可以“补察时政”、下可以“泄导人情”,“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虽然平添了“家国为要”“匡时济世”的内容,但骨子里依然维持早期“兴观群怨”的框架。南宋杨万里曰:“诗也者,矫天下之具也”(《诗论》),清代徐宝善道:“人心正而诗教昌,诗教昌而世运泰”(《养一斋诗话·序》),大体也与“思无邪”的正教一脉相承,一直以来都作为培育世道人心的工具,同时彰显“温柔敦厚”的相貌。总之,诗歌充任正心的“法度”(符合韩愈在《原道》中所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承担着方方面面致知格物的利器功能。其间虽偶尔出现“无所匡正”“无益时用”的轻薄噪声,但毕竟是一边倒的言志载道,总领了中国庞大的教化体系。
当人们愈来愈看重物的价值,被物所左右,从而产生精神虚空,诗歌能否再次挺身而出,充任疗伤的救护?当欲火膨胀,灵性缺失,工具理性风行,人心变得脆弱麻木,诗歌是否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相信多数人还是持肯定态度,诗之于人心净化、人性安立、人情和解、人格塑造的作用,是其他事物难以替代的。
二、从“介入”到“取暖”
完全摈弃诗歌的社会功用,既违背历史事实,也扭曲诗歌属性,属于血本无归,得不偿失。诗歌曾长期居于中心庙堂,其能耐获得超级护航。四书五经的首经明摆着是《诗经》,经历几度沧桑后,现今虽多让位于数理化、高科技,只在特定的场合偶露峥嵘,更多时候则是默默蛰伏在个体心灵的深处,但“诗经”强大的基因仍通过特殊管道,传递到少数精英的神经末梢,再转换为清晰可辨的精神脉动。
与之相似,五年之后发生雅安地震,臧棣在第一时间写出《雅安,一个巨大的倾听》,与所有呼告的“直接诗”不同,他将诗歌直击的行动功能,处处置于艺术的“监察”之下,摒弃表面呐喊而抵达人心:
该诗没有表面的鼓动助威,而是充满反思性关怀,且更侧重内心的灾难竣通,这是一种介入性的深在之用。虽然有人不屑于“载道”“言志”的立场维度,但所谓的担待、承诺、公共性言说,都逃离不了作为时代良知的基本出发点——关键还在于看你如何“取用”。
由是,诗歌又可能会转化为一种温和的“栽培”方式。“70后”的梁雪波,保留着对日常的审视。简单的《流水》作业,不过是扶正歪歪斜斜的书、抹去封面上的灰尘,一切是那样琐碎,但因此可以享受划过琴弦那样的美妙,因为纸上的词在暗暗擦拭内心。“在书架和书架之间,一把遗失的伞,从手中坠下的雨滴”——有如知识海洋浸淫灵魂,共渡精神之旅的依恋与温馨。同样,《修灯的人》也写了日常简单重复的劳作:攀梯、旋转、拧紧,上上下下、小心翼翼,毫无诗意;但在明暗下展开的情书、鞋底掉落的小泥,让初春的书店松软起来——也叫“诗生活”生机起来,最后引入“内心的开关”,完成黑暗与光明的意义指涉——诗歌的直接性介入得到了多侧面的展示。
近20年来,诗歌界还普遍流行“梦想”论与“取暖”论。受巴什拉“梦想诗学”影响,不少人一直加持“做梦”理念。做梦总是伴随着寄托、向往、愿景;做梦难免拖曳着一条长长的浪漫主义尾巴。但为修复当下精神与物欲的严重割裂以及人际关系的冷漠,多数写作者和爱好者宁可更实际地把天堂的诗歌降格为“围炉”的诗歌。当然,“围炉”不是指那种大年三十才有的年夜饭,而是指天天浸润在公号、雅集、沙龙、微博里的团聚。取自“围炉”的“取暖”,非常形象地概括了现时代——诗歌从神到人、从高雅到平实、从纯正到杂芜、从尊贵到习俗的变化过程。
全面客观地说,诗歌的功能本应是饱满多元的:审美教化、社会认知、精神滋养、表情达志、人际协调、自救自娱,等等。抬升一些的,可进阶到宗教、准宗教、信仰、准信仰的殿堂;降格一些的,权当抚慰安顿的容留;更低一点的,无非宣泄游戏。当年诗歌在海涅那里,诗人死了可上天堂,上帝请吃苹果。现在诗歌呈现信息化、娱乐化、肉身化趋势。诗歌的兴趣让渡于自媒体的迷恋;诗歌的审美冲动转移到“砸”“踢”“晒”的嬉戏,“高于生活”的信条换作了日常账务的记录。
权宜之计?无奈之举?反讽之语?还是走到底线的最后一声叹息?在利益充塞交换、真情匆匆擦肩而过的时下,蒙塔莱的伟大诗句,还能起作用吗?
跟着你,臂挽着臂,
我走下了至少一百万级台阶。
——《赠礼之二》
一百万级台阶肯定夸大其词,但诗歌从神坛走下来,在日常生活事务中,在你我他之中流转,作为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顶草帽、甚或是打喷嚏的一条手帕、垫在屁股下的一张旧报纸、一个火炉、一杯清茶,一次相互搀扶的同步,或半夜醒来、微信里的悄声问候,想想,不也就够了吗?
三、在“下滑”中走向“习俗”
网络大大扩张诗歌疆域,结果一部分诗歌在随意、即兴、率性的感召下涌向流行、习俗,既部分挽回不食人间烟火的趋势,又带来泥沙俱下的混乱。诗歌开始与经济搭台、旅游联手,受文化依托、品牌推举,诗歌的嘉年华在政绩催化下演变为轮番的庆典。各路人马,皆大欢喜。
在笔者看来,现代诗意的蜕变改写了传统诗美规范。那些古典的宁静淡远、款款情怀,那些农耕文明的镜像,反映在文本中的对举结构、骈体格调已被挤兑得“格格不入”。倘若说古代觥筹交错的酒兴,尚能在当下生日快乐的祝辞中,溶解可口可乐和鸡尾酒,那么明月松间照的笔触,是否还可以进入人体胸腔,清除那些日积月累的PM2.5颗粒?吃喝拉撒中的蜂窝煤、缝纫机、搓衣板、马桶早已被钢化玻璃、塑料镀金、远红外、光纤、纳米所取代,天才如李白、集大成者如杜工部活到现在,恐也会大惊失色,束手无措。不被当作诗意的新兴的习俗诗意,夹带着后现代的瓦解性,正在筹谋一次次造反,不断把传统审美引入非诗边缘、去诗意边缘,从前大部分人认可的那些高雅、优美、动人的东西,可能面临转岗择业。
当诗歌不再把重心对准灵魂(灵魂是什么?聚散不定的“物流”?精神的虚拟图景?夸大的乌托邦净地?),而是转移到习俗的层面、语词的层面,那么它面对的,必然是要处理更多日常的锅瓢盆碗。扑面而来的是一大把鸡毛蒜皮的标题:《踢着一只空空的易拉罐》《玩具狗趴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我喝过的橘子汽水》《自行车轮的转动方式》《顺着枯草中的马粪》《用一根香杵敲你的额头》《果盘里有一种腐烂香气》《与自己的长裙拉扯》……诸如此类,铺天盖地。透过题旨,我们可以感知诗歌在生活与存在层面,业已进入毛孔与褶皱,从而进行更具私我化的“抚摸”,更具流俗化的演绎。
经典案例是2017年,中国诗歌破天荒地出现了第一部专治腰间盘突出的广告诗集《狗皮膏药》,接着是《千岁帖》扑克牌诗集,再接着是《狗皮膏药续集》,作者正是营销自个儿产品的诗人梅老邪。全部目录简直就是一部保健指南:《腰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早晨》《一般在卫生间久久不出来有四个原因》《酸困麻胀痛热凉痒八部曲》《好了我一个,解放全家人》等等,内容涉及病因分析、治疗过程、药物疗效等。(无独有偶,2018年10月,署名“屈太郎”的作者,也创作出广告诗12集,总共一百多首)。进一步分析,梅氏广告诗集不单在追逐利润,更融进作者大量日常生活体验:《老爸使用说明书》借助应用文格式,皈依生活实用,夹带着下辈对家严、高堂的关爱;《医缘》通过全球化角度,纾解了一直以来僵硬的医患关系。与其说它们参与了产品营销、文案制作,毋宁说在某种层面上复归了古代诗歌的人际关系——进入互赠酬答、生老病死、人伦贴近的日常作息循环。
就是这个“篡改”诗歌功能的生意人,不久前还把一首很普通的《我在卖花粉》卖得惊天动地,一夜间,引发网络数万人围观,各种“买卖诗”像炸响的蜂窝:《我在卖烤串》《我在卖神皂》《我在卖阉鸡》……共同推动新冠名的“邪体诗”一路蹿红。大众狂欢的流俗诗意或诗意的流俗,符合市民阶层心理,投合老百姓情趣,在亲和、嬉笑的呼唤中,平添了许多调侃、揶揄以及对生活的拥抱。
从艺术上考察,该诗乏善可陈,只提供一个信息:我起早摸黑、无休无止地做买卖,但却道出一个基本事实:华夏古国,全民皆商。一个完全出自私人的动机——叫卖赚钱的动机——怎么能扯上时代、扯上功能论呢?当下自由自在的地摊经济、眼花缭乱的网络交易,这一巨大变迁,为诗歌注入了“与时俱进”的内驱力。该诗结尾写道:现在世界最让人感动的三个字,不是“我爱你”,而是“要花粉”——从浪漫主义的常规主题完全跌落到日常运作。一个极为简单、见惯不怪的兜售行为,竟被作者敏锐捕捉、充分利用,穿过精神情感层面,贴近普通大众心理。前头所有铺垫都为着结尾的三句话服务——无意中揭示了社会场域的风向标——从情感伦理到物质资本的转向。诗歌功能,也在庞杂的时代精神的召唤下,悄悄发生了变化。
这个机灵而狡黠的大脑,一方面用包装的小本生意对付来自养生丛林的残酷法则,另一方面也不无真诚地应答来自精神方面的提问。比如《我死之日》,就用白描的民俗化手法写下非商业化的遗嘱,而遗嘱背后却站立着华夏民族的“风水仪式”。 在同一个人身上,奇妙地完成利润挂靠与重大主题交换:
当下的情况,不是个体能力想改变就能改变,想流行就能流行。崛起的广告诗集为何不可能集中出现在10年或20年前?当整个社会加速进入全民工商的趋势下,广告以其无比强大的资本逻辑收编诗歌,展开全方位的轰炸式“洗脑”。被“裹挟”的诗歌,无论自觉或被迫,其实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自然,笔者不敢说诗歌全部,但至少部分的“言志”转向了日常实用,部分的“载道”瞟向了商业利润,部分的“群观”打造出新的“取暖”景观,部分的“清音雅韵”落入原生粗鄙,部分失缺敬畏虔信的灵魂内核成了漂浮物。集结起来的泛广告诗、类广告诗迅速流通,吐露出政治经济深刻转型的信息,且外化为文化症候的生动表情。宽泛意义上说,广告诗还包括贺年卡上的诗、嵌入饰物上的金句、各种周转的题词、日历上的“每天必读”、图文并茂的影像、屏幕上的分行,以及流行歌词,等等。它们悄然暗示:既然功能转型的趋势不可扭转,文化变迁的潮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对各种“刻舟求剑”的观念行为,该不该作出告别?
现在,人们一边兀立在“真善美”的制高点,一览众山小;一边对功能下滑开始习以为常,且露出一种见惯不怪的“平常心”。诗歌从教化与审美两大重头戏流散为地方小节目,分摊为多功能的“平均值”。诗歌总体性力量削弱了,但诗歌“分流”与各种行当、各类需求——经济、文旅、娱乐的连结则增强了。这一“黯然”结果,让少数精英与部分受众看了十分不遂心,总是抱怨流失了什么,甚至作出诗歌完全“堕落”的判断。
在诗意缺失或“蜕变”的境况下,诗歌委实很难再赢回昔日的荣耀,因为习俗与取暖拉大与主流教化、传统审美的差距。欲想履平这一“鸿沟”,何妨先行一步对观念进行洗礼。原来的载道与审美充满“诗性正治”的教诲,全然拒斥世俗、肉身和游戏,现在却充溢着“异质混成”的味儿:不单单是崇高、尊严、统一的真善美的“后撤”,也不止于纯度、浓度、洁度的“稀释”,它全然放开了主体性负面(包括虚无、黑暗、龌龊),也大面积收编了混沌。从传统诗意丧失的代价中交换出的“筹码”,转化为另一种“崇低”“崇下”“崇俗”的能耐。那些推心置腹的耳语、惺惺相惜的依偎,那些嬉笑怒骂、家常便饭,皆于流俗与取暖背后,卸下表演妆容,复归本色,流淌着更为接近人性真实的点点滴滴,由点滴真实传递着更为接近灵魂深部的痉挛与缓解。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更接近琐屑、凡庸的事物;也比革命时代的危急“介入”更讲究策略;它至少放下高贵身段,以乐此不疲的平民化碎步穿梭于刷屏间,这一切,算得上古老功能转换的“新常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