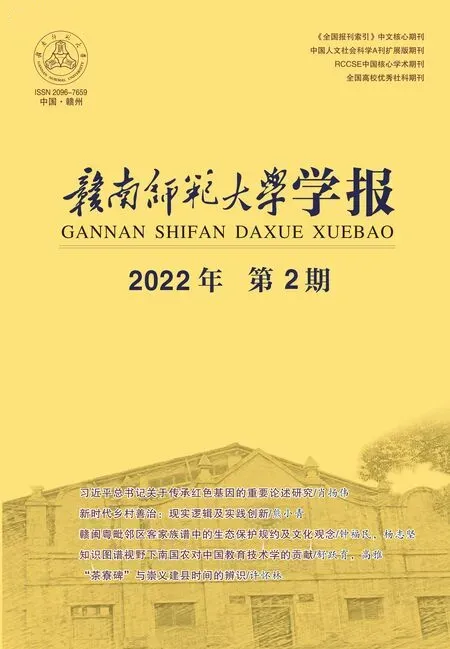一本万殊 :《明儒学案》学术史观考论*
赵文会
(铜仁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
《明儒学案》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的学术史意义。自康熙十五年成书以来不断有学者从编纂体例、资料选编、学术方法等维度对其展开了持续性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对于统领这些史料、史例、史法的史观之研究则有进一步的探讨空间,因为《明儒学案》的学术史观、学术史资料选编、学术史编纂体例、学术史方法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史意义系统。在中国传统学术史编纂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明儒学案》“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
一、 《明儒学案》学术史观诸家之说
所谓“学术史观”,即如何“观”学术史,它不同于具体的学术史方法,而是各种学术史方法能够展开在思想上总的依据,是一种稳定的思想宗旨和原则,也最能代表编撰者的学术意图,《明儒学案》的“学术史观”和“学术史方法论”有着内涵属性的根本不同,不能混淆。前人对于《明儒学案》学术史观的探讨主要从理学、哲学、史学的维度展开,大体有六种说法。
吴光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从学术史的角度提出《明儒学案》的学术史观是“一本而万殊,会众以合一”。他说:“《明儒学案》建立了以‘一本而万殊’的真理论为指导,以‘会众以合一’为方法去把握和整理学术演变史的学术史观。”[1]1002这是学界较早明确地提出《明儒学案》的学术史观问题。余金华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学术史的角度提出《明儒学案》的学术史观是“一本万殊,万派归宗”。他认为:“《明儒学案》以师承关系为基本线索,以‘学案’为基本单位,将个人与学派联系起来,通过把握宗旨来清理学脉,分源别派;而各个学派又统领于、贯串于心学之产生、发展、流变这一整个明代学术发展的主流之下,构成一个‘一本万殊’‘万派归宗’的发展中的系统。”[2]此说的特点是着眼于《明儒学案》的体例结构和功能发生。李明友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以《明儒学案》为主要材料提出黄宗羲的学术史观是“一本而万殊”。他认为:“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是黄氏学术思想之纲,而他的《明儒学案》,就是运用这一学术史观编纂的一部明代儒学史。”[3]此说的特色在于运用哲学的方法分析理学的问题。侯外庐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宋明理学的角度考察《明儒学案》的学术史观问题提出“和会学术异同”说。他说:“所谓和会学术异同,是指其对于理学内部不同学派采取居中持平的态度,力戒门户之见。”[4]此说是以宋明时期理学思潮范围内朱王异同为线索概括《明儒学案》的学术史观,“和会学术异同”说的思想史背景是理学。张圆圆在20世纪10年代初期从学术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提出《明儒学案》的学术史观是“一本万殊,万殊总归一致”。他认为:“‘一本’是指以儒学为天下学术之‘正宗’‘大本’;‘万殊’是指以儒学领域内不同形态的学说思想为‘万殊’之学。黄宗羲同时注重儒学范围内不同学说思想的融合与汇通。”[5]此说的特点在于提出了“学术史规律”的论阈。吴海兰在21世纪10年代中期从中国史学史的角度出发提出《明儒学案》的学术史观是“殊途百虑”。他认为:“黄宗羲倡导‘殊途百虑之学’,承认儒学存在多元发展的可能与必要,但仍然秉承道统传承的信念。”[6]并从《明儒学案》的书名设置、著述旨趣、编纂体例、资料选编四个方面论述,此说的着眼点是史学立场。
前人对《明儒学案》学术史观的探究角度不同,如中国史学史的角度、宋明理学的角度;方法各异,如哲学的方法,学术史的方法,皆鲜明有据。而如果综合地、整体性地观察《明儒学案》的学术史观,则会发现“和会学术异同”说、“一本而万殊,会众以合一”说、“一本万殊”说、“一本万殊,万派归宗”说、“殊途百虑”说、“一本万殊,万殊总归一致”说实际上均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指向:一本万殊。具体来说,“学术异同、会众、万派、殊途百虑”讲“万殊”,“和会、归宗、合一”讲“一本”。可见,“一本万殊”的思想大体上是前人关于《明儒学案》学术史观的基本共识。
二、“一本万殊”是《明儒学案》的学术史观
不同于前人将“一本万殊”作为《明儒学案》的理学史观、哲学史观,这里探讨的是作为“学术史观”的“一本万殊”,而实际上即使作为“学术史观”意义上的“一本万殊”,也是前人提出的。继续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前人虽提出却未论证,包括“一本万殊”内涵的定义、概念的起源与发生、黄宗羲运用并展开的思路与纲目等。故这里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作为学术史观意义上的“一本万殊”继续探讨,根本目的在于探究“一本万殊”与中国传统学术史编纂理论的关系。
(一)“一本万殊”思想的起源
“一本万殊”思想的起源与孔子有关,《易·系辞下》:“《易》曰:‘憧憧往来,朋从而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7]87“憧憧往来,朋从而思”是咸卦九四爻辞,孔子小象传的解释是“憧憧往来,未光大也。”[7]47为何没有光大?(唐)孔颖达进一步疏解道:“非感之极,不能无思无欲,故未光大也。”[7]47这种局面是由九四阳爻处阴位之不当位的处境决定的,孔子据咸卦九四之爻象进一步发挥,引申到了他对“天下”,即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认知: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孔子具有强烈社会现实关注感和历史忧患意识,“殊途同归、一致百虑”思想的提出与春秋时期动荡分裂的社会局面密切相关,其所指隐暗又真实,对后世影响较大。魏晋时期韩康伯注《易》解释道“途虽殊其归则同,虑虽百其致不二。”[7]87(唐)孔颖达说“‘天下同归而殊途’者,言天下万事终则同归于一;‘一致而百虑’者,言致虽一虑必有百。”[7]87孔子在《易传》中提出的“殊途同归、一致百虑”是“一本万殊”思想的在先秦时期最早的起源。另外,《大戴礼记·本命》篇提出“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8]“性命”是儒家伦理学说的基础性问题,而这必始于对“人的本质”这一问题的探讨,在《大戴礼记》看来,每一种“命”的样态是个别的、具体的、特殊的,而每一种不同的“命”所具有的共同的属性即是“性”,由此可见,“性”与“命”是一体之两面,断不可截然而分,但更不能混淆,因为二者的转化是有明确客观条件的,即“分于道”的过程和“形于一”的过程。《大戴礼记》的这种提法是后来儒家“一本万殊”思想的早期样态。由此可见,“一本万殊”思想起源于儒家,孔子从形上的维度在《易传》中提出的“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和《大戴礼记》从伦理的角度提出的“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均是后人从学术史角度提出“一本万殊”的重要思想来源。
(二)“一本万殊”在宋明理学思想体系中的衍变
宋明理学在对先秦儒学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建构,关于儒家天道性命学说,理学派大体上主张“理一分殊”,心学派大体上主张“一本万殊”。“理一分殊”出自程颐,是他对张载《西铭》进行主旨提炼时的用语。《西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9]程颐为了说明《西铭》的本旨与墨子“兼爱”思想之不同,对弟子杨时说:“《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10]609可见程子提“理一分殊”最初是从批评墨家思想而来的,“兼”有“二”义,言“用”可以,言“体”则断不可,因为“体”的属性只能是“一”,所以程子批评墨氏“二本而无分”,进而提出“理一而分殊”。后来朱熹充分吸收了程颐的这种思想并特别强调“《西铭》通体是一个‘理一分殊’,一句是一个‘理一分殊’;《西铭》要句句见‘理一分殊’。”[11]2522“《西铭》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11]2523“《西铭》大纲是理一而分自尔殊。”[11]2524朱子论“理一分殊”不仅与张载、程颐直接有关,也与周敦颐“一实万分”的思想紧密相连。《通书·理性命》:“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12]32朱熹解释说:“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之中,各有一小太极,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12]32实际上朱子论“理一分殊”与张载、程颐、周敦颐有区别,朱子之“理一分殊”的着眼点是整个理学思想体系。朱子为了解释建构理学,用“理一分殊”,也用“一本万殊”,二者既是理学观点,更是一种理学方法。《论语·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3]朱子注曰:“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14]朱子通过对忠恕之道的解释将“理一分殊”推向“一本万殊”。朱子曾明确提出“万殊便是这一本,一本便是那万殊。”[11]677到了明代,学者论儒家的天道性命问题则多取“一本万殊”。如薛瑄讲“统体一太极,即万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极,即一本之万殊。”[15]122明初崇仁学派的胡居仁讲“一本而万殊,万殊而一本,学者须从万殊上一一穷究,然后会于一本。若不从万殊上体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异端者。”[15]32明弘治年间江西学者汪俊讲“道一本而万殊,夫子之一贯是矣。”[1]459明成化年间福建学者周瑛讲“求诸万殊而后有一本可得。”[1]392明嘉靖年间徽州府人甘泉学派洪垣讲“万殊一本是理,理一分殊是功,分殊即在理一中。”[1]202罗钦顺讲“云《易》有太极,明万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为万殊也。”[1]413可见,与“理一分殊”比,明儒多从“一本万殊”的角度阐释理学思想。
(三)“一本万殊”在黄宗羲学术史思想中的核心位置
黄宗羲最初将“一本万殊”作为一种理学观点。关于本体,江右王门刘元卿认为“天地之间,无往非神。神凝则生,虽形质藐然,而其所以生者已具;神尽则死,虽形体如故,而其所以生者已亡。然而统体之神,则万古长存,原不断灭,各具之残魂旧魄,竟归乌有。”[15]576黄宗羲评价说“其生生不息,自一本而万殊,宁有聚散之可言?”[15]576黄宗羲反对将“统体之神”与“各具之神”分割开认识,他主张两者是一体,只是阐说角度不同,“各具之神”是重要的,基础性的,也是各不相同的,而所谓一本的统体的“理”只能是在万殊的各具的“理”之中,舍万殊何谈一本?这是黄宗羲哲学重工夫的一种基本倾向。关于工夫,黄宗羲评论诸儒学案庄昶“以无言为宗,略见源头,打成一片,而于所谓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功。盖功未入细,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后,流传多是此种学问。其时虽与白沙相合,而白沙一本万殊之间,煞是仔细。”[1]375庄昶有天资,故偏本体一路,为学多从“一本”出发,似有所成,然而实际上这也正是其缺点,即平常日用功夫的“万殊”之学未能踏实去做。陈献章担忧庄昶有见于一本而不见万殊,重本体却忽视功夫,结果就是庄昶为学境界似高却浮。故黄宗羲赞陈献章于“一本万殊”之间煞是仔细。黄宗羲又用理学的“一本万殊”思想来区分儒释,他认为:“佛氏之流行,一往不返,有一本而无万殊,怀山襄陵之水也。儒者之流行,盈科而行,脉络分明,一本而万殊,先河后海之水也。”[15]694儒家能够通过“万殊”而达至“一本”并由“一本”所统领的进路与佛氏“有一本而无万殊”的进路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还认为:“夫儒释之辨,真在毫厘。今观流行之中,何以不散漫无纪?何以万殊而一本?主宰历然。”[1]4黄宗羲认为儒者之所以能够“万殊而一本”是因为有天理之主宰,他认为能否“一本”而”万殊”是区分儒释的一个重要标志。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本体、工夫还是从区分儒释的角度看,黄宗羲都将“一本万殊”视为一种基本的理学观点,从其对“各具之神”“文理细密之加功”的评论看,其基本的倾向是重视“万殊”。
黄宗羲哲学重“万殊”、重“工夫”有其深厚的哲学本体论基础。黄宗羲认为“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16]77他将“心”的特点概括为变化不测,所以在外部形态呈现上就不能不万殊。具体来说:“心无本体,功力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16]77只有做切实的穷此心之“万殊”的功夫才能达至心之“一本”。落实到具体的为学方面,黄宗羲说:“某为《明儒学案》,上下诸先生,浅深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16]78竭其心之“万殊”,定会有醇疵深浅,但这本来就是心之“一本”的外在样态,所以黄宗羲极其重视这种“万殊”之学。在他看来,“一本”也只能从“万殊”中来。(明)正德三年春,王阳明在贵州龙场驿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17]这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明代学术特质凸显的起点,即由“理本”向“心本”转化,黄宗羲显然继承了阳明心本论的思想,他说:“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故穷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后之学者错会前贤之意,以为此理悬空于天地万物之间,吾从而穷之,不几于义外乎?此处一差,则万殊不能归一,夫苟工夫著到,不离此心,则万殊总归一致。”[18]7黄宗羲继承了王阳明批评程朱悬理于外的说法,力主理在各人的自性之内。求理于外有支离的危险,越求越细,越烦琐,越复杂,却始终没法有一个总的统领,这样的“万殊”是不能归于“一本”的。而若以“心”为统领,在心体上下工夫,这样的“万殊”有把柄,易于总为一致,归于“一本”。
黄宗羲倡“万殊之学”有其深层次的哲学意识驱动,这种不自觉的深层次的哲学意识是黄宗羲从几百年来宋明理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明末清初自己数十年抗清斗争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这种稳定的、深层次的、内化了的意识大体上可理解为黄宗羲对哲学本体的认知,而哲学是会外化的,即在黄宗羲各种生活实践和学术活动中都会显现,如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认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19]充分肯定了万殊之“民”的作用,有强烈的近代民主意识。在经济思想方面,主张“工商皆本”、肯定合理的“私利”,这与传统价值观中的抑商思想、轻利重义思想均有不同。文化思想方面,不仅编撰《明文案》,还编撰《明史案》《明学案》,从多个途径总结和反思明代文化,而不是单一的途径。学术史的编纂方面,《明儒学案》处处体现了其重“万殊”之学。黄宗羲总能看出人生、社会、国家、民族、学术等整体结构中“万殊”部分的重要性,这一点从本质上讲即是其重“万殊”哲学的外化。质言之,黄宗羲编纂《明儒学案》是其内在“一本万殊”哲学思想在编纂学术史时的外在体现,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内在的深层次的哲学意识在主体活动时自觉地外在地发生作用的过程,是内化哲学的外化,自然而然。
(四)“一本万殊”学术史观的正式提出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中正式明确地提出其“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他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15]6这段话的关键在“所谓”二字,“所谓‘一本而万殊’也”说明“一本而万殊”本来属于理学概念范畴,而黄宗羲却将这个理学概念范畴引申为自己编纂学术史的一种指导思想,这就彻底地实现了“一本万殊”由一种理学观点向一种学术史观的转化,而这种跨越式的转化是由黄宗羲自己完成的,源动力就是黄宗羲“一本万殊”的哲学。黄宗羲对“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进行了多方面的具体阐述。
第一,从“道原”的角度。黄宗羲在《钱清谿墓志铭》中提出“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虽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为无与于道也者。”[16]351黄宗羲极其强调儒家的“道”散殊于百家的现实,虽然人们的体会有深有浅,有偏有正,但都是对“道”之“一本”的体会,是探寻真理的过程,因此都是有价值的,即强调“万殊”之学的基础性和重要性。黄宗羲对“道”的这种特点做了形象的比喻,他说:“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涔,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也。”[18]7水之“一本”只能体现在“江、淮、河、汉、泾、渭、蹄、涔”这些“万殊”之水的样态中。
第二,从“道体”的角度。黄宗羲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即如圣门师、商之论交,游、夏之论教,何曾归一?终不可谓此是而彼非也。”[18]7商、师、游、夏皆从各自的特性出发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学术,取得了本领域内明显的成就。从这个角度看,各人学术不同之“万殊”正是各人对道体之“一本”的体会,不能是此非彼。黄宗羲进而批评道“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谓离经叛道。”[18]7这种做法是无益于对道体的体认的。因为“儒者之学,不同于释氏之五宗,必要贯串到青原、南岳,夫子既焉不学,濂溪无待而兴,象山不闻所受。”[15]6儒学的特点之一也正是强调对“道体”认知的多途与多维。
第三,从“道术”的角度。黄宗羲说“诸先生学不一途,师门宗旨,或析之为数家,终身学术,每久之而一变。诸先生不肯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虽或深浅详略之不同,要不可谓无见于道者也。”[18]7-8道术是体会道的方法,即体道之术。黄宗羲认为明代学者对儒家圣贤之道的体会是多途的,一派学术或分化为数家,即使每个人的学术也是经历了数次变化,绝不是一成不变或突然形成的。虽然各人的体会深浅不同,但都是对儒家圣贤之道的摸索,都有其特殊的价值,这种对师门学术变化和自身学术变化的“万殊”正是对儒家圣贤“一本”之道的体认。
由上可见,“一本万殊”是黄宗羲学术史思想的核心要义。明儒沿着宋儒“理一分殊”的思路讲“一本万殊”,黄宗羲在本体和工夫方面最初也是将“一本万殊”视为一种基本的理学观点,并充分主张“万殊”的一面。他重“万殊”的思想源于他对“心”处于本体地位的确立和对“心之本体”之“万殊”属性的规定。这种“万殊”的思想内化为黄宗羲的哲学,是他对宇宙人生社会等一切现象的本相认知。很自然地,这种内化的哲学一旦形成会外现于黄宗羲的各种社会实践和学术活动中,而编纂学术史时只是其“万殊”哲学在这一领域的外化。经过“内化哲学之外化”这一范式,“一本万殊”正式由一种理学观点转换为黄宗羲的学术史观。
三、“一本万殊”学术史观在《明儒学案》中具体展开的思路与纲目
史料、史例、史法三位一体的有机融合是“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在黄宗羲编纂《明儒学案》过程中具体展开的思路与纲目。学术史资料选编、学术史编纂体例、学术史方法论三者由“一本万殊”统领,在充分发挥各部分特有功能的基础上有效融合,达到了整体与部分的协调,从而使得《明儒学案》成为一部高质量的学术史专著。
(一)史料
黄宗羲在搜辑整理明代儒者的学术史史料时很注重史料内容的丰富、类型的多样以及收录传主时间跨度的长远、地域分布的广泛、科举出身的多途、理学思想的多元,这种思路充分体现了其重“万殊”的史料观。 第一,黄宗羲欲编纂一代学术史,首先要尽可能充分地、详尽地、可靠地占有明代学术思想的史料,资料不足则无法勾勒和表达明代学术的价值,他经过数十年的辛勤搜求积累了比较丰富而可靠的史料。二老阁刻本《明儒学案》近100万字,其中绝大部分文字是传主的学术资料选编,这些资料很珍贵,杨向奎先生认为《明儒学案》起到了“学术思想史和学术思想史料选编的双重作用。”[20]“万殊”的传主资料才能较客观和较有说服力地反映传主的学术。
第二,收录传主时间跨度之长远、地域分布之广泛、举业出身之多样、理学思想之多元均如实而准确地贯彻了黄宗羲重视“万殊”之学的学术史思想。时间上从明初的薛瑄、吴与弼直至明末的顾宪成、高攀龙。地域上自北向南从辽东、京师、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南直隶、浙江、广东、四川、福建均有传主的分布。从科举出身方面看,不仅有143名进士、33名举人,还有41名无举业功名却也卓然成家者。从理学思想方面看,不仅有持心本论的诸多阳明学者,也有持理本论的薛瑄、王恕等,还有持气本论的罗钦顺、王廷相等,心本、气本、理本虽各殊异,却都是对儒家圣贤道之一本的体认。最早刊刻《明儒学案》全本的贾润曾评价《明儒学案》“凡明世理学诸儒,咸在焉。”[18]9
第三,《明儒学案》大量传主的资料类型极其丰富,包括语(笔语、会语、录语、日语)、录(语录、漫录、传习录、日省录、求心录、困辨录、日录)、记、说、论学书、论学诗、文集、题跋、著撰、讲义、杂述、问答、论、诫、图、法(调息法、省身法)、札记、学则、随笔等,“万殊”的史料类型也说明了传主体道方式的多元。(详见表1)

表1 《明儒学案》53种学术资料选编类型分布表
(二)史例
学术史的编纂体例决定了学术史史料应用能力的下限,恰当合适的体例可以充分挖掘出史料的价值,二者有一个适配度的问题。黄宗羲用“学案体”很好地解决了《明儒学案》中史料与体例的适配问题。何为“学案体”?陈祖武先生认为:“学案体史籍以学者论学资料的辑录为主体,合其生平传略及学术总评为一堂,据以反映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21]沿着这个思路去观察《明儒学案》的编纂体例。首先,传主的学术资料是“万殊”的,有各种类型,语、录、记、说、书、诗、集、跋、著、撰、述、诫等,这些“万殊”的学术资料是传主学术思想在不同侧面、不同时间段的反映,但黄宗羲并不只是限于简单的罗列,而是选择那些能够集中反映该传主学术宗旨的资料进行有序的编排,这是“纂要勾玄”的过程,传主的学术宗旨是“一本”,传主的学术资料是“万殊”,但资料是基础,只有在“万殊”的资料中才可能见到传主学术宗旨之“一本”。其次,传主的生平是“万殊”的,如举业、仕宦、功业、师承、学友、游学、论辩、论学往来、正误得失、修德实迹等,但黄宗羲记载传主这些“万殊”的生平有一个根本的集中指向,即传主的学术宗旨,而传主“一本”的学术宗旨也只能反映在“万殊”的生平之中。最后,学派的小序的论述是“万殊”的,17篇学派小序提纲挈领,特色鲜明,如其论白沙学派“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15]78论河东学派“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15]117论姚江学派“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断矣。”[15]197论泰州学派“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15]820论东林学派“忠义之盛,度越前代。”[1]727这些“万殊”的学派概括正是从总体上把握明代学术之“一本”的依据,也只有从这些“万殊”的对学派特质的提炼中才能见到整体上明代学术之“一本”。黄宗羲重“万殊”的学术史思想以“序传录”的形式为载体,较好地解决了史料与体例的适配度问题,从而使得作为学术史的《明儒学案》趋向完善。
(三)史法
在学术史的叙述方法上,黄宗羲主要从学派分衍过程中的“正传”与“别派”、传主师承传授过程中的“墨守”与“转手”、传主个人为学过程中的“次第”与“衍变”三个层面贯彻其“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而尤其重视“别派”“转手”“次第”这些“万殊”层面的意涵。
首先,在学派的分衍方面,黄宗羲着重把握“别派”的出现,如论白沙学派与崇仁学派的关系:“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15]1陈献章之学虽出自吴与弼,宗旨却不同,自为“别派”。论三原学派与河东学派的关系:“关学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别派也。”[15]172论止修学派“见罗从学于邹东廓,固亦王门以下一人也,然别立宗旨,不得不别为一案。”[15]777阳明宗旨“致良知”,李材宗旨“止修”,虽有师承二传系统,却不得不归为别派。论泰州学派“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15]820泰州之学虽出于姚江,却是姚江之“别派”。这种区别于“正传”的“别派”之分化正是学派之“一本”在发展过程中“万殊”衍化之体现。
其次,在传主师承传授过程中,黄宗羲特别留意学生的“转手”,即为学路径的转变。黄宗羲所说“诸先生学不一途,师门宗旨,或析之为数家。”[18]7即指此状况而言。如《崇仁学案·序》“其相传一脉,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矱。”[18]14娄谅、魏校虽师承吴与弼,却在为学路径上稍有变化。《江右王门学案·邹德涵》“以悟为入门,于家学又一转手矣。”[18]333邹德涵是邹善之子,邹守益之孙,他虽出自家学,却以“悟”为入门,于家学的路径已经有明显的变化。《江右王门学案·罗大纮》“于江右先正之脉,又一转矣。”[18]548罗大纮对于江右王门学派邹元标的学术有所变化。《东林学案·陈龙正》“然师门之旨又一转矣。”[18]1502陈龙正于其师高攀龙的学术路径有变化。差异、变化是黄宗羲着重留意的,这体现了传主传授过程中的“万殊”之学。
最后,黄宗羲注重传主个人为学过程中的“次第”与“衍变”,他说“诸先生学不一途,终身学术,每久之而一变”[18]7即指此而言。如论王阳明学术形成前后经历了6次变化“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18]180“自此以后,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居越以后,开口即得本心;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18]180可见,黄宗羲是极其重视记录、描述、分析传主为学的次第和衍变这种“万殊”的学术现象的,另外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钱德洪、罗洪先、罗钦顺、罗汝芳、万廷言、邹元标、王时槐、黄弘纲、陈九川、薛蕙、胡直、唐鹤征、李材、耿定理、邓豁渠、高攀龙等人为学的次第和衍变情况均有详尽的叙述。
黄宗羲通过学术史史料的丰富、类型的多样以及收录传主的多元化体现其重“万殊”的史料思想;通过“序”“传”“录”的多元结构和宏观、中观、微观的多维层次在体例上体现其重“万殊”的编纂思想;通过“别派”“转手”“次第”与“衍变”体现其重“万殊”的书写方法。史料、史例、史法虽“万殊”,黄宗羲却能够使其深度融合,在充分发挥各部分特有功能的基础上紧密相连,立体地、动态地记录了明代学术的流变。学术史史料、学术史编纂体例、学术史叙述方法是黄宗羲“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在《明儒学案》中展开的思路与纲目。
四、结论
“一本万殊”是《明儒学案》的学术史观。其根本指向是儒学道体的存在方式问题。儒学范围内,道体“一本”,体道“万殊”。前人的“和会学术异同”说、“一本而万殊,会众以合一”说、“一本万殊,万派归宗”说、“殊途百虑”说、“一本万殊,万殊总归一致”说均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指向——“一本万殊”。“一本万殊”思想源于《易》,在宋明理学思想体系中与“理一分殊”关系密切,根源于黄宗羲重视“心之万殊”的哲学倾向,具体落实在《明儒学案》的史料、史例、史法中。理解“一本万殊”的关键既不在“一本”,也不在“万殊”,而在于“一本”和“万殊”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传统学术史编纂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