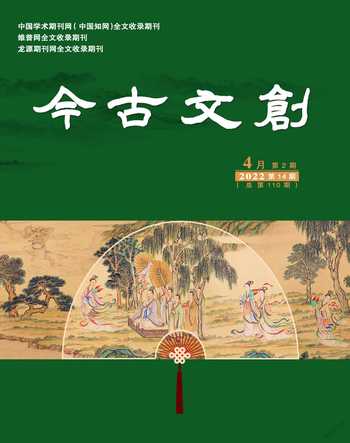异域想象遮盖本土叙事 :唐诗中的南诏形象研究
【摘要】 唐诗是一种饱含情绪的历史资料,它独特的史料价值能够帮助人们重新塑造历史时期人们心目中的“观念”。就唐诗中的南诏形象而言,遥遥万里是唐朝时人对南诏的最初印象,炎热荒芜是接踵而来的又一深刻记忆。天宝战争使得唐朝与南诏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唐人开始塑造一种“地恶人丑”的南诏形象以抒发自身对南诏的厌弃之情。但贞元会盟又将双方的关系缓和,唐朝开始憧憬着以王道使南诏臣服。最终,唐诗中构建了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南诏形象。
【关键词】 唐诗;异域想象;南诏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4-002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4.008
基金项目: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系《唐朝对南诏的认知偏差与治理误区研究》(YJSJJ21-B20)阶段性成果。
诗歌视野是一种多角度、多方位、情绪化的视野,因为诗人们的身份是多样的、变化的,他们创作诗歌时的感情是十分饱满、丰富的,他们在诗歌中反映出来的对待南诏的态度也是十分明确的。在唐代,唐诗无疑是最具传播性和影响力的文化媒介。就唐诗视野下的南诏形象而言,它所具有的独特的史料价值便在于其能够清楚、客观地反映出唐朝时人对南诏的主观印象,并生动地勾勒出一幅人们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想象图景。[1]这种诗歌中透露出的主观印象和想象,正可以清晰地反映唐朝士子文人对南诏的真实态度,对唐朝治理南诏的政策及其变化、唐朝与南诏的关系及其改变等问题的深入研究颇有裨益,并以此形塑一种唐朝时人心目中的南诏形象来弥补目前历史研究中“观念”缺位的状况。
在中原中心观的影响下,唐代诗歌的创作具有较强的空间局限性与地域象征性,唐诗的空间关注重心一直放在关中、中原、山东、河北、江南、巴蜀等中原王朝经营日久、农业较为发达、商业较为繁茂、文化较为昌盛的地区,对于中原四周边疆民族地区不甚关注,尤其是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关注远远不够。《全唐诗》中共收录唐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其中边塞诗仅有两千多首,涉及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唐诗数量更是只有百余首,仅从数量而言,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受到的忽视已十分明显。而唐诗中提到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炎”“荒”“瘴烟”等词屡见不鲜,这样就造成了唐朝时人对边疆民族地区产生了一些固定的形象认知,而且由于诗歌的传播性在唐代较其他文化媒介强了不止一筹,使得这种固定形象愈发加深且难以撼动。
此外,由于唐代南诏地区汉学尚不发达,掌握丰富汉学知识并且能够吟诗作对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所以,唐诗中关于南诏的诗歌绝大多数都是中原诗人创作的,南诏诗人的作品本就不多,涉及南诏的就更少了。因此,在唐诗这个唐代最具传播性和影响力的文化舞台上,南诏的本位认知遭到了中原汉文化权利语言的压制,处于一种被人忽视的局面。最终,南诏陷入了“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①的尴尬境地。虽然一些唐朝严肃文献和南诏本土文献陈述了较为真实的南诏事实状况,但这些文献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难以与唐诗相提并论的。这样的结果导致了中原时人对南诏形象的认知脱离了其本土叙事的真性,为异域想象的任性所构建。
一、遥遥万里:对南诏地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双重印象
遥远是一个双重概念,即地理空间上真实的遥远和心理空间上认知的遥远。所以,“它既是一个基本的空间认知,也是一个文化概念” ②。“天圆地方”的空间文化观很早就已形成并被华夏人民普遍接受,通俗的解释就是: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方形的中心就是华夏人所居的中原,方的四条边就是东、南、西、北四边,方的四个角就是东南、西北、东北、西南四陲,方与圆之间的四个月牙就是四边之外的四海,方与圆相交的点就是海角天涯。所以,大一统中原王朝统治的地方是全“天下”,即中原与四海八荒的全部地方,称为“宇内”,也可称“海内”。四陲之地靠近天涯海角,也就是说从很早以前,在华夏人的心里空间上就已经将西南边陲构建为极遥远的地方。
随着唐朝在西南地区统治的不断延伸,苍山洱海地区逐步纳入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多的中原人士开始了解西南边疆地区,了解南诏的风土人情,这种对西南边疆的“遥远”印象,在唐朝时便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对南诏的印象。并且从中原到南诏的距离本就比较遥远,途中又要经过许多山脉,地理空间上的路远难行,限制人们脚步的同时也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旧有的心理空间上的印象重新发挥了作用,并且不断加深。
南诏真的很遥远吗?仅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是的。据《蛮书》记载,“从安南府城至蛮王见坐苴咩城水陆五十二日程”,而“自西川成都府至云南蛮王府、州、县、馆、驿、江、岭开塞,并里数计二千七百二十里”,若是从中原地区出发去往南诏王城羊苴咩,三四千里的路程可见是有的。[2]也就是说从四川到南诏羊苴咩城以当时的脚程而言要走约两个月,如果是從中原地区出发,无论过四川还是经广西非三四个月不可。但是从长安出发到江南的扬州、山东的登州等地,如果是陆路也需要两三个月才能到达。也就是说,从绝对距离来说,南诏其实并没有那么遥远。南诏的“遥远”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遥远,它超越了准确的空间距离,成为一种对心理距离上“疏远”的表达。
地理空间距离上的遥远增加了信息沟通的难度,造成了沟通次数的减少、信息表达失准性的增加以及沟通双方不信任感的提高,这就造成了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王朝之间不能快速高效地建立互信和交流渠道,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政权之间自然不断爆发冲突,南诏与唐王朝也不例外。战争又加深了双方的不信任、甚至是厌恶敌对的情绪,这种情绪反映到诗歌的字里行间中,又表现出了心理距离上的“遥远感”不断加重。具体地说,反应战争或者战争时期流传下来的涉及南诏的唐诗中,具有“遥远”属性的词汇明显增多,比如刘湾的《云南曲》“百蛮乱南方,群盗如猬起。骚然疲中原,征战从此始。白门太和城,来往一万里。去者无全生,十人九人死”[3],表达了对南诏叛乱的痛恨和对普通将士战死异乡的哀痛。这固然有双方敌对立场的因素发挥了作用,但就算是敌对的双方,这种轻视与贬低仍然超出了正常意义的范畴,几成一种定式的地域歧视。
二、炎荒馀丑:对南诏“地恶人丑”的厌弃
唐诗里,中原时人对南诏的厌弃还表现在诗歌里,充满了对南诏炎热的天气、无处不在的瘴气、荒凉而无所产出的土地印象深刻,这种印象既有对南诏事实情况的反映,也有中原时人在中原中心观的思想下对南诏气候、环境、自然物产以及南诏人民的轻视与厌弃。本来南诏瘴气丛生、天干地热、物产匮乏只是自然环境作用下的自然状态,但显示在唐诗中更多地将自然环境与南诏人民联系在一起,仿佛南诏自然环境的恶劣与南诏人民的道德品行挂上了钩,“地恶人丑”成了中原时人对南诏根深蒂固的偏见。
在描绘南诏自然环境风景图像的唐代诗歌中,只有极少数的诗歌对南诏的自然环境发出了由衷的赞美。比如,唐代诗人赵叔达的《星回节避风台骠信命赋》中有一句“河润冰难合,地暖梅先开”,描绘了南诏温暖的天气,冬天河水不上冻,梅花也比中原地区抢先绽放。但赵叔达是南诏人,更是南诏的清平官,所以他对南诏环境的赞颂无法代表唐代绝大多数人对南诏环境的印象。
绝大多数唐诗对南诏的自然环境表达了嫌弃、厌恶的感情,尤其是一些深受中原中心观、大汉族主义等思想影响的唐朝诗人,对南诏不时背反以及劫掠边地的行为十分厌弃,由此开始对南诏整个地域都感到厌恶,其诗中开始有意无意地把南诏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南诏人民的本性联系在一起,开始运用自身的权利话语来构建南诏“地恶人丑”的形象。比如,高适的《李云南征蛮诗》“梯巘近高鸟,穿林经毒虫。鬼门无归客,北户多南风”,生动描写了南诏山高林密,毒虫较多,建房习俗“门户朝北”与中原之地“坐北朝南”不同而与南越之地的习俗相同,这两句基本是写实的,是对南诏自然环境的真实描写,但接下来的几句就开始构建南诏“地恶人丑”的形象;“蜂虿隔万里,云雷随九攻”,将南诏的将士描绘成“蜂虿”,其轻视、厌弃之情跃然纸上,意思是说南诏人连禽兽都算不上,只是蜜蜂、蝎子之类的毒虫而已,与前文描写南诏自然环境的“穿林经毒虫”形成了呼应。[3]仅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讲,其写作手法是相当精妙的,但其诗中反映出来的对南诏人民的轻视与厌弃无疑是一次汉文化强权下的语言暴力,是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歧视与抹黑。
储光羲《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的第一句就是“昆明滨滇池,蠢尔敢逆常”,上来就戴着有色眼镜,秉持着极端的偏见,将南诏人民说成是蠢贼、叛逆;之后“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把南诏定义成“炎荒”,炎热还可以说是写实的,而荒芜偏远则是站在中原中心观的角度对南诏的一种“安排”,也是对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中西南边陲又荒又远想象的继承;然后“玄武扫孤蜮,蛟龙除方良”大唐的士兵比作“玄武”“蛟龙”一类的神兽,而南诏的士兵则被比作“孤蜮”“ 方良”之类的山精、鬼怪;紧接着“斩伐若草木,系缧同犬羊”,南诏的士兵更是成了“草木”“犬羊”;以上都还是比喻的手法来暗示,更加直白还是其后一句“馀丑隐弭河,啁啾乱行藏”,直接将南诏人说成“小丑”。[3]自此,南诏“地恶人丑”的形象逐步在高适、储光羲这样的诗人笔下成型。
因何会形成南诏“地恶人丑”的偏见呢?战争带来的仇恨是其中最大的因素。唐代诗人雍陶是蜀人,其有数首描写南诏劫掠蜀地的史诗,悲愤伤痛之情饱含其中。其中一首《蜀中战后感事》有这样一句“已谓无妖土,那知有祸胎”[4],前一句的“妖土”是对南诏地理环境与风俗习惯的厌弃,后一句的“祸胎”更是对南诏人民及南诏政权的痛恨,“地恶人丑”的观念蕴含其中。可以参考一下唐朝诗人许裳在其诗中给出的答案。在其诗《送徐侍御充南诏判官》中有一句“地偏风自杂,天漏月稀明”[4], 为什么南诏人的风俗不好呢?因为“地偏”,这就是唐朝诗人对南诏“人地”关联的直接表达。南诏的自然环境在客观上确实不如中原地区那么良好,但從唐诗的字里行间中,可以体会出中原时人对南诏的印象更多来自主观臆想而不是客观认知。因为南诏的环境恶劣,所以想象出在这样环境中孕育的人也十分丑陋、低劣;又因为对南诏的人怀有敌视心态,故而觉得南诏人生活的环境也和南诏人一样恶劣,由此形成一个闭环。再加之传统印象的影响与唐、诏双方时有发生的龃龉,中原时人不自觉地开始在诗歌中构建南诏“地恶人丑”的形象。
三、万方同感化:对南诏顺服中原王朝的期许
虽然以上列举的诗歌中反映了唐朝时人对南诏的鄙夷与厌弃,但这并不代表唐朝对南诏没有期许,恰恰相反,唐朝对南诏抱有强烈且持久的期许,这种期许中既包含了让南诏服从王化、臣服唐朝的政治与外交期许,也包含了对南诏进行汉文化改造的文化期许以及与南诏进行商贸往来的经济期许。
尤其是当南诏与唐朝结好的时候,这时候的唐诗中最易表达出中原时人欲图南诏顺服王化的愿望。比如郑洪业《诏放云南子弟还国》“瘴岭蚕丛盛,巴江越巂垠。万方同感化,岂独自南蕃”[4],便是希望这些被放还的南诏子弟能够受到感化,从此臣服中原王朝,并且成为诸蕃的楷模。南诏与唐朝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往来也十分频繁。比如骠国是南诏的属国,其经过南诏向唐朝献乐,表达了自己对唐朝的臣服。白居易的诗《骠国乐·欲王化之先迩后远也》便说道“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正朔”[4],表示骠国王子舒难陀来献乐是奉行“正朔”。
与此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南诏能同意骠国的献乐便是对唐朝的一种恭敬与顺服,同时也是对双方文化往来的期许。实则,早在皮逻阁时期,南诏就曾与唐朝进行过音乐方面的交流,唐朝向南诏赠送胡乐和龟兹乐,在《蛮书》中有记载:“牟寻指之曰:‘先人归蕃来国,开元皇帝赐胡部及龟兹音声各两部。今死亡零落尽,只余此二人在国。’”[2]
另外,南诏的红藤杖畅销唐朝,许多唐朝人都经常使用或者当成礼物赠送出去,包括白居易、韩愈、张籍在内的多位诗人都作诗记之,其中张籍所作的两首诗最能反映这一现象。《赠太常王建藤杖笋鞋》中说:“蛮藤剪为杖,楚笋结成鞋。称与诗人用,堪随礼寺斋。寻花入幽径,步日下寒阶。以此持相赠,君应惬素怀。” [5] 《酬藤杖》中则写道:“病里出门行步迟,喜君相赠古藤枝。倚来自觉身生力,每向傍人说得时。”[5]可见南诏的红藤杖十分受欢迎,送礼的人觉得有分量,收到的人也十分欣喜。
唐朝汉化南诏的举措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南诏自阁罗凤时便请被俘虏的唐朝西泸县令郑回给自己的子孙当老师,郑回日后更是凭借帝师的身份成为南诏的清平官,在南诏政治生态中地位超然。至中晚唐时期,南诏上层政治人物便已经逐步汉化,南诏的诗人所作的诗歌已有不俗的质量,比如寻阁劝《星回节游避风台与清平官赋》、段义宗《题大慈寺芍药》《思乡》等等。而这些文化与经济上的往来使得唐朝让南诏臣服的愿望愈加强烈,贞元年间南诏能够背蕃归唐便不乏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等人的努力。这也为云南地区从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逐步融入内地,让云南之地由“异域”变成“旧疆”打下了基础。
四、结语
唐朝时人从心里认为南诏十分“遥远”,认为南诏“地恶人丑”,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唐诗这种当时最为流行、传播范围最为广泛的新闻媒介中,没有南诏自己的“声音”,南诏诗人创作的诗歌体量太少、质量也参差不齐,因此南诏的“本土表达”受到了唐朝中原诗人“异域想象”的遮盖。但随着双方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双方的了解逐步加深,唐朝时人对南诏的印象也逐步发生改变,与南诏结好或者说使南诏臣服的愿望逐渐占据上风,晚唐时甚至几度讨论与南诏和亲之事,南诏在唐诗中的形象迎来了巨大的转变,一个儒家文化初兴、物产颇丰、音乐繁荣的南诏形象开始建立起来。
注释:
①此语为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的书前题词,见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②张轲风:《异样的目光:明清小说中的云南镜像》,《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4期,第18页。
参考文献:
[1]张轲风.异样的目光:明清小说中的云南镜像[J].明清小说研究,2012,(4).
[2](唐)樊绰.蛮书[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2.
[3]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4]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5](唐)張籍著,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系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作者简介:
刘炬胜,男,汉族,山东微山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硕士在读,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