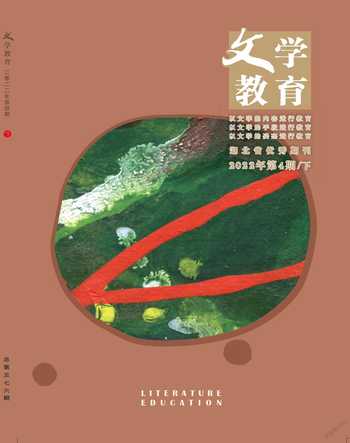《促织》与《变形记》中的生存困境焦虑
黄会兴
内容摘要:《促织》与《变形记》都表现了人类的生存困境之一,即共同焦虑。本文通过语言、题旨和想象三个角度来比较分析二者的共同点和差异性,二者在“简约与细腻”“卑微与异化”“真实与大胆”三方面各有特色,由此也能窥见两者各自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生存困境 共同焦虑 简约与细腻
卡夫卡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读他的传记《卡夫卡传》(马克斯·勃罗德著)会更细腻、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些内容背后的意味。同样,我们读蒲松龄的《聊斋自志》也有同感:“嗟呼!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这两位写人变虫的作家,在书写人类共同困境方面殊途同归,因为他们的写作都指向社会,也指向各自的内心,指向人类共同的生存焦虑。
他们的写作都貌似“闭门造车”[1]却又“洞若观火”。在写作的世界里,也许恰恰是因为“闭门造车”,才会“洞若观火”。他们如何“闭门造车”又“洞若观火”呢?期间的差异又如何呢?
一.“变形记”的中西方语言比较:简约与细腻
(一)简约疏朗、参差错落:中式语言的诗文底色
重读蒲松龄的《促织》和卡夫卡的《变形记》,第一个感觉就是《促织》语言轻盈明快。
这种语言简明精致,整散结合,张弛有序,语言与情节一起变化。如开头“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此物故非西产;有华阴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令以责之里正。市中游侠儿得佳者笼养之,昂其直,居为奇货。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短短数语,将时间、地点、社会风貌交代清楚。上行下效,争相谄媚,层层盘剥,小人得势,胥吏恶毒的丑态勾画无遗。善良的成名成为待宰的羔羊则是水到渠成了。文章另一处写失去蟋蟀,“成有子九岁,窥父不在,窃发盆。虫跃掷径出,迅不可捉。及扑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须就毙。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色灰死,大惊曰:‘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去。”语言多为散句,长短间杂,其中的情节和情感随着语言的流转而变化,与后文成名得知结果后伤心失望的惨状所用整句形成对比。此段故事推进之快,后文成名之苦尽皆形象地被描摹出来。
中国古典语言侧重简明流转的诗意,即使是小说的语言也如此,比如《世说新语》《唐摭言》“三言二拍”等都如此。简练的勾画中故事情节快速转进。也恰恰是情节的快速转进,才给读者留出了更大的想象和回味空间。
《促织》语言舒朗明快,轻盈跳跃,塑造人物方面同样让人回味無穷。这种语言的魅力在于它的简约明快,有诗一般的疏朗境界。
“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日将暮,取儿藁葬。近抚之,气息惙然。喜置榻上,半夜复苏。夫妻心稍慰,但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成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自昏达曙,目不交睫。东曦既驾,僵卧长愁。忽闻门外虫鸣,惊起觇视,虫宛然尚在。”
此段四字句居多,间杂散句,给人沉郁顿挫之感,读来如鲠在喉,有啜泣的冲动。
(二)真实准确、不疾不徐:西方语言的叙述特色
读卡夫卡的《变形记》,它细腻和真实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
“他觉得肚子上有点儿痒,就慢慢地挪动身子,靠近床头,好让自己头抬起来更容易些;他看清了发痒的地方,那儿布满着白色的小斑点,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想用一条腿去搔一搔,可是马上又缩了回来,因为这一碰使他浑身起了一阵寒颤。”
这样细致而有耐心的描写俯拾即是。西方这种细腻的描写和专注的态度还有很多,如“长途汽车的窗户关着,一只瘦小的苍蝇在里面飞来飞去,已经有一些功夫了。它无声地、疲倦地飞着,颇有些快。……每当有一阵风挟着沙子打的窗户沙沙响时,那只苍蝇就打一个哆嗦。”(加缪《流放与王国》)曹文轩说:“一个艺术家的本领并不在于他对生活的强信号的接受,而在于他能够接受到生活的微弱信号。”[2]可以设想,卡夫卡在一个静谧的午后或夜晚,一个人全神贯注地进入他的想象世界,像《盗梦空间》的造梦师一样细致地建筑他的第二生命——他给自己女友的信中说:“只有通过写作,才能维系生命。”这种语言强调真实性——生活真实、感觉真实和情感真实。
《变形记》中,作者特别在意感觉的描写。“他想,下身先下去一定可以使自己离床,可是他还没有见过自己的下身,脑子里根本没有概念,不知道要移动下身真是难上加难,挪动起来是那样的迟缓;所以到最后,他烦死了,就用尽全力鲁莽地把身子一甩,不料方向算错,重重地撞在床脚上,一阵彻骨的痛楚使他明白,如今他身上最敏感的地方也许正是他的下身。”卡夫卡的描写不仅细致,也很节制,节奏感和人物心理保持一致。在人物心理刻画上更是自然、合理、逼真。“有片刻工夫,他静静地躺着,轻轻地呼吸着,仿佛这样一养神什么都会恢复正常似的。可是接着他又对自己说:‘七点一刻前我无论如何非得离开床不可。到那时一定会有人从公司里来找我,因为不到七点公司就开门了。’于是他开始有节奏地来回晃动自己的整个身子,想把自己甩出床去。”这种写实的语言与荒诞的情节交相呼应,制造出了人物命运的梦幻感和酸楚感,仿佛要将读者的精神撕裂。
比较中西方两种语言的特点是很有意味的,因为二者的语言审美倾向迥异:前者追求简约顿挫,后者追求真实准确;前者是诗化语言,后者是叙述语言;前者简洁明快,后者细腻逼真;前者让人清醒,后者让人着迷。虽然同是人变虫,内容不同,语言审美不同,自然导致主题也会不同。
二.“变形记”的中西方题旨比较:卑微与异化
(一)《促织》:卑微的命运
蒲松龄在《促织》的结尾写下了如下的话:“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结合题目,蒲氏想说的可能是因为小小一物而可以使一个人死去活来,一会儿跌入万丈深渊,一会儿裘马扬扬高高在上,这个世界有多疯狂,人的命运就多么身不由己。
成名如此,成名的幼子、妻子亦如此,他们逃不出皇帝、华阴令、猾黠的里胥和市中游侠儿织就的天罗地网,逃不出驼背巫与神明的暗示。这里有对世态的审视,更有对小人物的悲悯。无论是君权还是神谕,都是成名的“命”,躲避掉,逃不脱。我们读到的是“卑微”,不仅是对昏聩的体系的嘲讽和无奈,更有对人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的漂泊感、无助感。当然,蒲氏不可能脱离儒家劝人向善的调子,这是他的局限,也是时代的约束。
(二)《变形记》:禁锢的生命
在《卡夫卡传·家世与童年》这一章里有这样的记载:“弗兰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卡夫卡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寒鸦’。在赫尔曼·卡夫卡商号的公函信封上,就印着这个长着漂亮尾巴的大头鸟作为标志,弗兰茨早先给我写信常常使用这个信封。”[3]
20世纪小说家中,卡夫卡的生平经历可以说是最平淡无奇的,一生都没离开过故乡。重要作品如《审判》《美国》《城堡》都未完成,且生前未出版。吴晓东的《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一书中对卡夫卡有这样的介绍:“卡夫卡的创作生涯,堪称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写作状态。他的写作不是为了在媒体发表,不是为大众。也不是为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而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个人写作。”纵观卡夫卡的一生,《变形记》其实就是这种“禁锢的生命”的艺术版本。
(三)“异化”:焦虑的生存困境
就私人写作这一点,蒲松龄和卡夫卡有相似之处。他们的著作注定与金钱和名誉无关,只与自己的爱好和心灵有关。相似的是,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也未正式出版,所以现在不同的版本篇目也略有差异。对于《变形记》,一般人认为反应的是人的“异化”。吴晓东在《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一书中说卡夫卡的《地洞》某种意义上是现代人的处境象征——在生存世界中我们都在劫难逃。读《变形记》,读到的是“焦虑”——是工作和社交带给成人(学生也一样)的压迫感、焦虑感——惊悸和惊醒。
作为社会的人,你身不由己;作为自我的人,你寂寞空虚。无论你如何挣扎,都是痛苦的。即使按照存在主义的说法,人天生是自由的,人就是他选择的自己;那这个“自己”也不见得幸福。所谓的“异化”都是外界的压迫,两篇文章的主人公都缺少由内而外的坚强自我,特别是精神层面的坚毅和超越,这是可悲的,也是普罗大众的写照。
由此看来,所谓“异化”就是在人之为人的过程中,人对自己设定的囚徒困境和由此引发的生存焦虑。哈姆雷特的名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个干净,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加高尚?”这也许是“生存困境”的最佳注脚。
那么,他们是如何实现自己的写作意图的呢?
三.“变形记”的中西方想象比较:真实与大胆
(一)从想象感觉角度看,两者都很真实而大胆
《促织》这篇文章的想象是建立在一个虚拟的一个历史背景中,也就是“宣德间”;然后由大到小,最后落到了一个普通人成名身上。他是一個秀才,为人迂讷,“操童子业,久不售”。这个名字也具有反讽的意味,因为他的名字寓意“想成名”,但实际上他的事迹是靠促织而不是科举最终得以流传下来。小说对于成名的描写维妙维肖,不管是他“早出暮归,提竹筒丝笼,于败堵丛草处,探石发穴,靡计不施,迄无济”,还是写他“惟彷徨瞻顾,寻所逐者……将献公堂,惴惴恐不当意,思试之斗以觇之”等等,这些描写都是很逼真的。这一类想象的是建立在作者对市井生活的认真地描摹和对人情的揣摩基础上的。
同样,卡夫卡的变形记也带有这样市井气息,从而给人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比如说他描写父亲对他的这种情感的细微的变化。母亲作为一个弱者,她的这种温柔以及这种无助。所以,任何的想象,它的动人之处,都是建立在对生活特别是心理真实的描摹基础上的。只有这样的细微之处,才能够打动人心。
(二)从沉思效果角度看,两者在戏剧性和焦灼感上各有侧重
《促织》之中的成名,从前面的狼狈不堪到后面的得意洋洋,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以说更具有反讽的意味。而卡夫卡的变形记则是凭空而来,又顺理成章,格里高尔的结局也是在意料之中。从阅读的感受来讲,蒲松龄的《促织》让人嬉笑怒骂后陷入沉思,读完之后卡夫卡的《变形记》后,人有一种郁闷、压抑的感觉。
同样是沉思,两者的想象方式不同,从而造成了不同的效果。蒲松龄更在于以促织作为依托来写人物的命运,他的重点是在成名身上,而不是在他的那个小孩子身上。那么卡夫卡的格里高尔重点在人变成虫子之后的表现和反应。所以呢,卡夫卡可能更关注这种焦灼感,蒲松龄更关注人变虫的这种戏剧性。
(三)从主题呈现角度看,两者都描写了人类命运的荒诞性
《促织》更有点儿热讽的意味,而《变形记》则更多地弥漫着冷潮的气息。无论是蒲松龄作品的娓娓道来,还是卡夫卡作品的劈空而来;无论是一个以喜剧结尾,一个以悲剧收场,还是众人哓哓或者一人寂寂,都表现出人性的脆弱、人生的困境:这是殊途同归。
他们的想象都非常大胆,都具有庄子“齐物论”的视角和庄周化蝶式的浪漫。只不过蒲松龄的想象是开放的,卡夫卡的想象是闭锁的。格里高尔没有走出他的家,蒲松龄的促织则有皇宫一游的经历。因此,蒲松龄的作品更轻松活泼,而卡夫卡的作品能更压抑低沉。
蒲松龄的想象是开放型的,他的境界比较阔大,涉及到县令、皇帝、女巫、村中好事者等等,牵涉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这或许和他的游历、为官僚幕府和私塾先生的经历有关。卡夫卡的《变形记》只是囿于家庭内部,映射着个人在工业社会中苦苦挣扎的无望处境,也表现了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核心的价值观对亲情和人性的侵蚀。这种侵蚀无法阻挡,无可遁逃。
(四)从写法渊源的角度看,两者古典与现代迥异且各有渊源
中国的传统小说往往将故事都是有头有尾,而西方现代小说往往是无头无尾。所以,中国的小说更具有深邃性和历史的沧桑感,而西方小说则更具有悬置性和反思内省的倾向。但是,毕竟如开头讲到的,蒲松龄和卡夫卡的思想背景完全不同,一个是儒家人本理念护持,一个受到尼采、柏格森的浸染,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
蒲松龄不是现代的,他的技法是古典的精巧,小说可作为散文来读。卡夫卡是现代的,其小说是对自己生存境况的投射。两者都在自己的世界里相当大胆地、率真地表现内心世界,都为我们描述了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人类共有的生存困境。人类对自我的焦虑从未断绝。
两篇小说故事不同,语言、题旨和艺术手法也不同,却殊途同归——关心人类的苦痛和命运,这是作家的良心所在。综上所述,帕斯卡尔说,人是能思想的苇草;可是人类一思考,命运就发笑。人因思考而高贵,人也因思考而痛苦。
注 释
[1]叶廷芳编.论卡夫卡?致菲莉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713.
[2]曹文轩.艺术感觉与艺术创造?语言的方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27.
[3]马克斯·勃罗德.卡夫卡传[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1.
(作者单位:浙江省平湖市当湖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