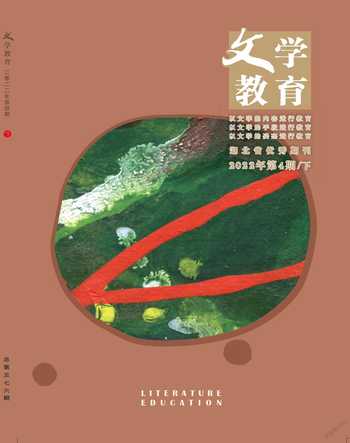李永平《吉陵春秋》中的父亲缺席探究
陈瑀
内容摘要:“父亲缺席”是李永平小说反映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在《吉陵春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对《吉陵春秋》中父亲缺席情况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吉陵春秋》中的“父亲缺席”现象是在李永平对于现实父亲的情感态度以及自身特殊生活体验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它是李永平对于文化原乡追寻与建构的入口,对其寻找自身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李永平 父亲缺席 《吉陵春秋》
“父亲缺席”现象是李永平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从处女作《婆罗洲之子》开始,李永平文本里的家庭就已经是残缺不全的。此后,“父亲缺席”的阴影持续地笼罩在李永平创造的小说世界中,“寡母—独子”成为其文本里最常见的家庭结构。
《吉陵春秋》是此现象表现得最为集中的一篇,其中存在大量“父亲缺席”的家庭。小说由十二篇相互关联的故事组成,以反乌托邦式笔法书写了吉陵镇的市井百态。作为故事发展主线,长笙受辱自杀引发了吉陵镇内集罪恶、欲望和败德为一体的狂欢,将吉陵一步步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其起因与结果均和镇中普遍存在的“父亲缺席”现象拥有紧密联系。
“父亲缺席”是华文作家们笔下的重要意象,“父亲”一词除生理意涵外也是重要文化符码,一方面指向中国传统父权文化,是社会道德秩序与伦理原则的权威象征,另一方面指向中国文化身份。因此,如何书写“父亲”既体现作者对于文化权威的态度,又关涉作者对自我文化身份的体认问题。在《吉陵春秋》中,李永平通过营造无父的世界,在文本中消解了一切秩序与道德,在一片混乱中苦苦追寻自己的精神原乡与文化身份,背后潜含复杂的文化选择与情感态度。
目前研究中,学者们对于李永平小说的关注不多,具体到“父亲缺席”这一现象的研究也相对匮乏,多是在论及其他问题时略有提及。但笔者认为,李永平小说中普遍存在的“父亲缺席”现象与他的身份认同、原乡追寻、文化选择等多个方面之间存在联系,是理解其小说内涵的突破口所在。因此,本文拟以《吉陵春秋》为例,剖析其中的“父亲缺席”现象及其造成的结果,探究这一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涵义。
一.《吉陵春秋》中“父亲缺席”现象的呈现
社会学理论认为,子辈在成长过程中会将父亲作为精神引路人,通过模仿父亲初步建立起价值观念,父亲也在此过程中实现了自我身份的文化意义。[1]因此,“父親缺席”指的是父亲缺席子辈的成长过程,没有在精神上指导子辈,没有实现自己的文化意义。
《吉陵春秋》中几乎所有家庭都是结构残缺的,并且原因均指向了父亲的缺席。他们或因不在场被直接剥夺了话语权,或因在场不作为导致家庭关系的错位与异化。在此语境下,家庭在父亲权威支柱的空缺下一步步走向崩塌,成为吉陵镇罪恶的起源。李永平以这两种缺席方式抽空了父亲的存在,营造了一个罪恶横流的吉陵镇,从侧面反映出父亲的不可或缺性。
(一)不在场的父亲
小乐、鲁保林和黑痴的父亲是《吉陵春秋》中不在场父亲的代表。父亲在现实意义上的缺失直接宣判了子辈在成长中模仿与追寻父亲的不可能,他们被迫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转向家庭外部寻找替代父亲,二是放弃找寻父亲代替者自己独自成长。但这样成长起来的子辈往往会因为缺乏父辈文化的滋养与规训失去精神依托,陷入迷茫。
黑痴便是其中的一例。作为妓女的儿子,黑痴生来就没有父亲,在母亲春红被刘老实杀害后成为了孤儿。因目睹了母亲的惨死,黑痴在巨大的精神打击之下变成了人们口中的“白痴”,丧失了寻找父亲替代者的能力,被动面对没有父亲在场的成长环境,沦为了全镇人愚弄的对象,小泼皮们口中念唱的“黑痴,黑痴,没爹没娘”[2]48的歌谣时刻提醒着他“无父”的尴尬处境。面对他人的欺侮黑痴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在苟延残喘之中恍惚度日,万福巷口被小泼皮们“搠穿了心窝的老花猫”[2]60暗示着他的下场。
不同于黑痴,小乐和鲁保林均找到了自己的替代父亲,即镇上的大泼皮孙四房。但作为强奸长笙的始作俑者,孙四房道德的败坏注定无法为他们提供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他并非一位合适的父亲替代者。这也预示了小乐和鲁保林的结局:在孙四房的带领下,他们成日流连于妓寮之中,成为长笙事件的帮凶,进一步把吉陵镇推入罪恶的漩涡深处。对猫狗等小动物冷血的残杀,都是他们成为子辈的“孙四房”的征兆。
(二)在场却不作为的父亲
《吉陵春秋》中同样存在一批在场却不作为的父亲形象。他们或被塑造成为完全沉默的父亲,在家庭中完全失语,或父亲身份被极度弱化。秦老师、萧先生和胡四均为在场的缺席者。作为父亲,他们对子辈的成长漠不关心,沉浸在满足自我的原始欲望之中,甚至将罪恶之手伸向了自己的子辈。
萧先生和胡四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蛇仇》一章中,李永平将叙事人设置为萧家小儿子萧克三,以子辈视角的讲述凸显萧先生父亲角色的失职和荒唐。萧先生沉迷嫖妓,置家中的妻儿于不顾,甚至和大儿子萧达三共同抢夺妓女罗四妈妈,父子俩反目成仇。他表面上风流潇洒,实际上却软弱无能。萧家祖父去世后,本应接管父亲权威处理家中事务的萧先生“好好一个人就全没了主意”,祖父的丧事“大大小小里里外外,都是亲家妈妈作的主”,[2]114亲家妈妈介入萧家担任了临时父亲,不仅暗示着萧先生父亲角色的失职,也暗示着萧家中伦理道德的失序——外部女性介入成为家庭父亲,而血缘父亲则弱化成为了子辈,传统父亲的权威被消解殆尽,萧先生成为了在场却失语的父亲。
而十一的父亲胡四则是一个同性恋者。十一和他并无血缘关系,是他为了传宗接代诱骗妻子和结拜哥哥生下的,这也埋下了他之后成为失职父亲的种子。胡四养育子辈的目的在于延续香火,与十一之间并无真正的父子情。这种畸形的父子观念造成了胡四父亲身份的缺席,他没有将十一作为自己的儿子看待,常常带着十一在温家与戏子寻欢作乐,对孩子的泼皮气也不加管教,最后甚至还爱上了自己的儿子。这样的结果是失去父亲管教的十一和没有父亲的小乐、鲁保林一样,将孙四房当成自己的代替父亲。他在邪行的现实父亲和残暴的父亲替代者的带领下,一步步滑向了罪恶与欲望的深渊。
与萧先生和胡四赤裸裸袒露的欲望不同,秦老师是一个在教书先生身份掩饰下的伪君子。李永平借吉陵镇众人之口勾勒出一个沉默虚伪的父亲形象:他整天躺在床上发呆,对妻儿视若无物,难得下床却是为了趁着迎神仪式前往万福巷去看女人。秦老师那“压得低低的帽檐”与心中抑制不住的欲望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一方面明白这种行为的可耻,但一方面却又无法克制自己内心的欲望,所以选择站在一旁做无声的看客。但这并不能隐藏他内心的罪恶,十一娘一针见血地揭开了秦老师罪恶的面纱,“那晚万福巷里看迎神的男人可多着哩,对门这一位秦老师,不也是一个?人家还是个读书人哟。”[2]84在看见孙四房欺辱长笙的时候秦老师选择了沉默,在本质上,他也是孙四房的帮凶之一,更是组成吉陵镇罪恶的一份子。
二.缺父的后果:罪恶横流的恶托邦
在父亲的集体缺席下,吉陵沦为了“亡父之镇”,这是李永平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弑父。黄锦树指出:“‘父亡’的必然结果是道德失序、法规荡然无存。《吉陵春秋》里充斥着色欲的罪恶,原因正在于那是一个严父己经亡故的空间。”[3]220父亲本应是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捍卫者,但在《吉陵春秋》中,父亲却成为了道德伦常破坏的始作俑者,在家庭和社会中都成为了缺席者。传统权威父亲的消亡代表着传统伦理道德的失语,子辈就此变成了自我放逐的无根的人。父亲缺席所带来的文化失落使得吉陵镇呈现出一派末日恶托邦的景象。
(一)色欲的泛滥
贯穿全文的长笙自杀事件起源于色欲的泛滥:孙四房和镇上的小泼皮们在六月十九日观音诞辰日强奸了刘老实的妻子长笙。这一事件成为揭开吉陵镇泛滥色欲的突破口,男女老少的欲望都由此牵扯而出,尽数曝光在读者面前。
几乎所有的吉陵镇人都拥有无法克制的强烈色欲。吉陵镇的男性均以狎妓为乐,万福巷中的妓寮是他们最常光顾的地方。同时,吉陵镇的女性也全无传统女性的忠贞观念,她们或如妓女春红一样,成为男性泄欲的工具并以此为傲,或如十一娘和祝家嫂子一样与他人通奸。
文本中频繁出现的“刨”字是吉陵镇里色欲泛滥的隐喻:“刨”本是刘老实打棺材时的动作“一刨一刨”,但随后却不断出现在情色对话中,“刨了你”成为吉陵镇人共有的口头禅。在此语境下,“刨”一词被赋予带有暴力和威胁意味的色欲含义,暗示着吉陵镇的最终结局——众人都與刘老实一样以实际行动为自己制造棺材,这口色欲之棺终有一天会将他们自己埋葬。
(二)道德的沦亡
父亲的缺席隐去了吉陵镇里的道德秩序,使之成为一个伦理失序、道德堕落的黑暗世界,表现为家庭伦理关系的异化和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漠。
泛滥的色欲令夫妻关系异化为特殊意义上的嫖妓:夫妻双方不对彼此负有责任意识,色欲取代情感成为维系关系的纽带。胡四虽是天阄,但其躁动不已的情欲却将十一娘“刨出了冷汗”。萧先生在狎妓的同时也不放过妻子,把她视为自己发泄性欲的道具。而吉陵镇中的妻子同样也没有坚守道德底线。祝家妇人在丈夫坐牢期间公然与他人通奸,秦老师的妻子张葆葵生下了小叔子的私生子。夫妻关系的异化也导致了父子关系的扭曲,萧达三和萧先生父子之间因争夺妓女而反目成仇,而胡四爱上了自己的儿子十一。
家庭伦理关系的异化向外延伸,呈现为吉陵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极度冷漠。朱崇科指出,李永平笔下吉陵人冷漠的“看客心态”是鲁迅对国民劣根性批判的延续。[4]长笙受辱、春红和孙四房妻子之死等事件均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但吉陵人却集体选择做沉默的看客,甚至还将它们作为娱乐,争先恐后进入现场观赏悲剧的发生。
(三)信仰的丧失
吉陵人极其重视精神信仰,一年一度观音诞辰日的酬神庆典是吉陵全年最盛大的节日。然而,本应庄严神圣的酬神庆典在吉陵却成为众人制造罪恶的渎神狂欢,其中暴露出的种种丑态撕裂了吉陵人的虚假面具,揭示出他们信仰的缺失和空心化。
李永平将酬神仪式高潮部分的地点设置在象征原始欲望的万福巷口,宗教仪式的圣洁和妓寮的污秽之间构成鲜明对比,暗示着整场仪式的荒诞。妓女们一方面将酬神仪式视为洗脱自身不洁的手段,另一方面又将其作为招揽生意的好时机,在酬神过程中四处挑逗男人。而男人们也借酬神之名从涌入万福巷狎妓,二者在神圣仪式中共同发动了淫乱的狂欢。
在渎神狂欢中,本应挺身而出维持伦理道德秩序的父亲沦为秦老师一般的看客,纵容罪恶的发生。孙四房在菩萨像下公然强奸长笙便是在此情况下发生的,
这实质上是对菩萨的亵渎,意味着神灵在吉陵镇众人的心中已经失去了威慑力。因此,失去神性的祭神仪式在为吉陵镇人洗脱罪恶的同时,也为新的罪恶的打开端口。故事从观音诞辰之日开始,又以观音诞辰之日作为结束,暗示着吉陵镇中罪恶的不断往复。
(四)罪恶的循环
理想父亲的遮蔽令吉陵镇无法建立起规训社会的道德秩序,罪恶因此难以寻得修复的途径,在不断嬗变的过程中形成了罪恶的循环。李永平在文本中设置了罪恶的三种循环模式:个人罪恶的循环,代际罪恶的循环以及整个吉陵镇罪恶的循环。个人罪恶的循环构成了代际之间罪恶的传递,最终又形成了整个城镇罪恶的循环。
孙四房与十一、小乐均为个人罪恶循环的代表。在长笙受辱事件发生后,长笙、孙四嫂和鲁保林等人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作为罪恶主体的孙四房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在出狱后依旧带领小泼皮们在妓寮中寻欢作乐。同样的,帮凶们也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惩戒。小乐将施虐的对象转移至家中的母狗,而十一则在父亲的助纣为虐之下娶妻结婚。
罪恶在个体内循环的同时,也在代际中传递。作为小泼皮们的替代父亲,孙四房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扮演了罪恶传递者的角色,带领子辈们走上精神的歧路。在此过程中,罪恶由孙四房传递给了小乐和十一,他们在孙四房的教唆下成为强奸长笙的帮凶,欺侮妇女和弱者。并且此后罪恶仍在传递,这从小说对镇上婴儿的描写里可看出端倪。小顺的儿子虽仍在襁褓之中,但已经学会狠狠掐母亲的心窝,在小乐与十一等泼皮杀害母狗时无意识地展露笑容,这是人性本恶的表现。
吉陵镇中人性之恶在横向上呈现着自我循环,在纵向上表现为代际传递,构成一张纵横交错的罪恶之网——整个吉陵镇同样处在罪恶的循环之中。故事开头孙四房的色欲的恶在结尾呈现为刘老实复仇欲望的恶,形成以惡制恶的循环,将吉陵镇变为藏污纳垢的恶托邦。
三.父亲缺席出现原因探析与文化蕴意
李永平利用父亲缺席抽去了吉陵镇中的伦理道德秩序,使之成为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小镇。这样的设置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李永平本人的经历与思想之上,背后潜含深刻文化蕴意。
(一)现实父亲的精神创伤
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李永平对于自己父亲的情感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吉陵春秋》中缺席的父亲们皆为李永平现实父亲夸张化的影子,尤其是萧先生,他与李永平父亲的形象是高度重合的。萧家的故事是李永平童年家庭的缩影,而萧先生就是李永平现实父亲在小说里的化身。李永平在回忆父亲时写道:“我那父亲!他是个天生浪子,万不该娶妻生子害惨了我母亲。”[5]59从中可窥见他对父亲的不满。他的父亲和萧先生一样是一个不务正业的读书人,移民南洋后辞去稳定教职,抛下妻小游走于婆罗洲各处经商。父亲屡次投机取巧所带来的生意失败,使得李永平童年时的家庭生活常常处于窘迫境地。《吉陵春秋》中萧先生不顾妻儿搭上妓女罗四妈妈寻欢作乐,李永平的父亲也拥有一个荷兰姘头,在公然出轨的同时又让妻子为他生下了十二个子女。不负责任的父亲为李永平童年时期的家庭氛围蒙上了一层阴影,也给李永平的内心造成了永远无法弥合的精神创伤。
此后,少年李永平又在升学问题上和父亲产生分歧:“我父亲就想把我送到英国念大学,念法律。但我对法律没有兴趣,想念文学,就偷偷申请去台湾,几乎跟我父亲闹翻了,后来就来台大念外文系,毕业后就不想回去了,不想见我父亲。”[6]可见他和父亲的隔阂之深。对现实父亲的不满反映在李永平的文学创作中呈现为父亲形象的缺席——他通过对父亲形象的隐去和遮蔽实现了精神上的弑父,借对父权的突围和叛逆完成了对于现实父亲的控诉。
(二)作者身份认同焦虑的流露
现实父亲带来的精神创伤是李永平文学创作里出现“父亲缺席”现象的直接原因,而其根本原因则来自李永平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从《婆罗洲之子》开始,李永平在小说中频繁通过书写“父亲缺席”表达对于身份认同的渴望和焦虑。
李永平出生于英属婆罗洲砂拉越邦古晋城。作为中国的第二代移民,李永平的身份是复杂且暧昧的,造成了他体认自我文化身份的困难和焦虑,这种焦虑在婆罗洲摆脱殖民统治加入马来西亚之后达到了顶峰。马来西亚在建国后采取了扶持马来人、打压华人的政策,原本在马来亚社会中就属于劣势地位的华人地位进一步下滑,成为了社会边缘人群。[7]因此,李永平始终无法对自己马来西亚公民这一全新政治身份产生认同:“我不喜欢马来西亚,那是大英帝国伙同马来半岛政客炮制出来的一个国家……我需要一个身份,才拿马来西亚护照,可是心里没法当自己是公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国家怎样冒出来的。”[6]
对马来西亚公民身份的拒绝让“华人”成为李永平唯一的身份标签,他迫切希望能够返回中国大陆寻得自己失落的中国文化身份,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却又阻挡了他回乡的脚步。李永平最终怀抱着对于中华文化的孺慕之情前往台湾,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身份认同,但台湾的生活经历并未能让他如愿。在婆罗洲时,对于马来西亚身份的拒绝令他成为社会中的他者,而在台湾,他则在他人赋予的“马华作家”标签中感受到自己仍是一个局外人。并且李永平向往的纯正中华文化认同也在“在台湾的政治语境中,在台湾的权术者手中遭‘亵渎’”,[8]令他再次陷入了“失根的焦虑”之中。
吉陵镇上父亲们的集体缺席指向李永平身份认同里的中华文化父亲的失落,道出了自己身份认同的焦虑和无奈。在“父亲缺席”的语境下,吉陵镇成为了罪恶泛滥的恶托邦,这一写作并非指向李永平的真实原乡,而是指向了李永平自己心中的失乐园——当父辈文化已经疏离,身份无处皈依之时,他永远地陷入了原乡的失落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没有父亲的吉陵镇就是无法寻得文化父亲的李永平,吉陵镇因为父法的缺失陷入罪恶的循环,而因缺失文化父亲所造成的身份认同失落,则成为了李永平永远无法摆脱的命运之网。
(三)构筑文化原乡的执着追寻
长期的流寓经历造成了李永平边缘多重的身份处境,令他困惑于对乡的体认。作为一个“迌者”,李永平注定无法在现实中寻得自己的“根源文化父亲”,即纯正的中华文化身份认同。因此,中国大陆对李永平来说不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转变为文化图腾般的存在。[9]他走上了追寻文化原乡的道路,通过作品构筑自己所魂牵梦绕的中华原乡,以此作为获得身份认同的途径。其中,李永平最为痴迷的是文字,“中国的方块字是很特殊的。对我而言, 它不单是语言符号,而是图腾。”[5]139他坚持“纯正中文”的主张并将它和民族认同相关联,在纯化中文的实践中铸造自己的理想原乡。
《吉陵春秋》便是这一实践的起点。李永平曾在采访中谈起《吉陵春秋》的写作过程:“八年间,断断续续,苦心经营,为的就是要冶炼出一种清纯的中国文字。借净化中文以净化自己,从外来的庶子一跃而成为血系嫡子。”[10]从中可见其对于文字苦心经营程度之深。在马华文学写作中,汉字和父亲一样,具有特殊的意涵。黄锦树指出,马华文学作家在运用中国文字进行创作时,“他们必须去除异质环境中的异质因素,一如他们重新中国化,中国文字在他们的手上也必须纯化,进行一种貌似还原的再创造,向一个被认为是属于中国的逝去的时代投射。”[3]243
“父亲缺席”在李永平的文字修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李永平极度崇拜与迷恋中国文字,并将其上升到民族良心的高度,使其文学实践与身份认同拥有了紧密联系,从中可见他对于中华文化血统的极度渴望。在《吉陵春秋》的文字实践中,对“纯正中文”的执着追求驱使李永平以缺席的方式,将其中他认为不够纯正的中国文化“父亲”全部清除,他通过父亲的缺席抽空了现实中身份和原乡的纠葛,以书写罪恶颠覆原乡,清除了一切的杂质,以此构筑自己心中的理想原乡。
对现实父亲的复杂情感态度和自身流寓多乡的经验相结合,凝聚为李永平笔下普遍存在的“父亲缺席”现象,体现出“迌者”李永平身份认同的失落和焦虑。故乡(婆罗洲)、他乡(台湾)、原乡(中国大陆)之间的复杂纠葛宣判了李永平追寻现实原乡的不可能,驱使李永平转向文学追寻与构筑自己心中的理想文化原乡。因此,“父亲缺席”成为了李永平用以构筑文化原乡的手段与途径,他通过“父亲缺席”的设置,在文学创作中打开了对于文化原乡的追寻与建构的入口,在其中寻求和建立文化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1]桑标,唐剑:《父母意识的结构与内涵初探》,《心理科学》2000年第3期,第279-284页。
[2]李永平:《吉陵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麦田出版家庭传媒城邦分公司2012年版。
[4]朱崇科:《旅行本土:游移的“恶”托邦——以李永平〈吉陵春秋〉为中心》,《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99-106页。
[5]李永平:《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纪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
[6]伍燕翎、施慧敏:《人生浪游找到了目的地——李永平访谈录》,载2009年3月14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7]庄国土:《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东南学术》2003年第2期,第59-67页。
[8]王列耀:《隔海之望:东南亚华人文学的“望”与“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2页。
[9]王德威:《原罪与原乡——李永平〈雨雪霏霏〉》,《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5期,第5-7页。
[10]封德屏:《李永平答编者五问》,《文讯》1987年第29期,第125-126页。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