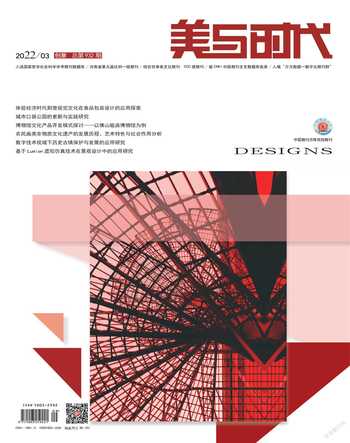探寻乔迅对中国明清装饰品的研究
摘 要:中国艺术有着自身独特的品性和历史文化底蕴,同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但随着艺术史学这门学科研究和发展,中国艺术研究的推进难免会遇到瓶颈,而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多元化的社会,信息分享便利,这有利于本土与海外进行中国艺术的学术研究交流。乔迅对中国明清时期装饰品有独特的思考方式及研究角度,在《魅感的表面:明清的玩好之物》有充分的表现。
关键词:明清;装饰品;愉悦感;感性的关联
在读《魅感的表面:明清的玩好之物》(Sensuous Surfaces:The Decorative Object in Early Modern China)之前,笔者一直带有这样的疑惑:乔迅是一位西方的艺术研究学者,中西方的社会环境、文化底蕴以及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都有着很大差异,笔者认为还是中国本土的学者研究本土的艺术和文化会更具说服力。乔迅如果不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思想观念有一个深刻的了解,那么笔者认为他会很难把握和研究中国明清的艺术装饰品。乔迅是否对中国的社会环境、哲学思想有着深入的把握,能否把中国明清时期艺术装饰品的来龙去脉论述清楚?如果他没有从这些方面入手研究,那么他又会从什么维度入手来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装饰品?
一、乔迅研究角度的独特性
——“愉悦感(pleasure)”
(一)从愉悦感(pleasure)的角度切入
在“序言”中,乔迅说道:“刚刚关于设计概念的简要叙述已为读者梳理了欧美近百年来关于中国文房雅玩研究的一系列专著的研究理念……我希望冒昧地指出,这一伟大的学术努力因为将现代西方对于装饰的假设强加于中国装饰品之上,已经扭曲了明清奢侈物品的图景。”[1]12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乔迅对于西方学者用西方艺术理论来研究中国明清的装饰品感到不满,这种研究方式存在着一些弊端。如果西方学者用西方的艺术理论来解读中国艺术,那显然和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不在一个路径上,因此他们用这样的研究体系来研究是为了在西方艺术研究语境中,和西方学者共同交流研究的。如果放在中国艺术研究语境中,则不会成立。因为西方对于装饰品的看法以及研究与中国关于装饰品的解读截然不同,中国艺术有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魅力,西方的研究方法虽然科学系统,但是用来研究中国艺术难免僵硬以至于很难推进研究。
“‘愉悦感(pleasure)在现代艺术史的知识体系下是另一个研究的盲点。在现代的艺术史知识体系中,学者们只有悬置‘愉悦感(pleasure)才能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体系里(主体—客体、中央—边缘、真品—赝品等等)书写艺术史,而这种二元对立仍然左右着现代艺术史这一学科。如果不能跳出这些二元对立,我们是无法考查愉悦感在艺术鉴赏中的重要性的。”[1]15从这一部分可以看出,乔迅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装饰品,是从“愉悦感(pleasure)”这一角度切入的,这是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角度,因为海外美术史研究大多都把“愉悦感(pleasure)”悬置起来了,而乔迅则主张将二元对立的体系悬置起来,这样才可以在艺术鉴赏中品味“愉悦感(pleasure)”。西方学者研究学术问题逻辑思维比较理性周密,研究体系系统化,所以涉及情感方面就会比较少,大多时候以理性为主。
乔迅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明清时期的装饰品,并且是可移动的小件器物(portable objects),同时从“愉悦感(pleasure)”的角度来切入,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魅感的表面》中,乔迅多次引用《红楼梦》《闲情偶寄》《长物志》等文本,从这些文本中可以看出,在明清时期玩物盛行,人们注重对器物的欣赏、把玩。特别是在《闲情偶寄》中,在“器玩部”“饮馔部”“颐养部”中,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人们特别讲究吃喝玩乐,所以在这一时期玩物盛行,研究明清时期的装饰品有便于从“愉悦感(pleasure)”的角度入手。“乔迅对曹雪芹小说的反复征引也有助我们来视觉想象这些摆设品所营造的物表景观和氛围。”[2]这里提到了乔迅引用曹雪芹小说中的关于摆设品(display objects)的内容来唤取我们的视觉想象。笔者一直认为乔迅之所以多次引用,目的是可以更好地论述“愉悦感(pleasure)”,通过小说里出现的引人“愉悦感(pleasure)”的摆设品,来显示出明清时期人们对装饰品的大量需求。但是再看一遍书中引用的关于摆设品(display objects)的部分,是可以感受得到通过视觉想象来感受装饰品在这样的氛围中,从而调动起其他感官的感知。
在学术研究中,“愉悦感(pleasure)”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无可逃避地被看似谜题似的画面所吸引,对于意义明确、解法明显的东西无法解释地提不起兴趣。这个学科的繁荣基于解决问题的愉悦,而在面对好、普通、朴素的真、熟巧、私人,以及一切拒绝将自身呈现为谜题的图像,则无能为力。”[3]我们可以看出“愉悦感”对艺术学学科的推进起着很大的作用,就像这段话说的一样,面对一个谜题,一个无法下准确定义的谜题,研究者进行自己的解读,这个解读有着研究者后天训练的思维和后天学到的知识以及自己先天的感知力,这个解读不仅会让学者感到愉悦,并且这个愉悦感也可以传递给能与学者解读产生共鸣的读者。这样看来,“愉悦感(pleasure)”不管是对于学者进行研究,还是对于观众去接收研究者的解读都是非常重要的。笔者认为能带给人们新的思考或者新的思考路径,都能带来“愉悦感(pleasure)”,这种愉悦感是精神上的,能引领人类不断前进。在“愉悦感(pleasure)”的获取中,人类会更加了解自己,精神世界会更加丰富。
(二)装饰品的“感性的关联性”
“装饰与其他的视觉艺术略有不同的一点是,它的全部调解功能就是营造这种感性的关联。”[1]13装饰品与其它视觉艺术不同的一点是,它是立体的,有质感的,通过观看并且触摸,我们可以把握它的质地、颜色、纹饰(ornament)。装饰品上的纹饰(ornament)都有着自己的隐喻(metaphoric)空间,可以让观者产生共鸣。例如,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饰(ornament),“即为成功地反映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诗·商颂》)那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4]。饕餮在中國象征着原始神秘的神权,它是神秘的、未知的,所以人们看到会产生敬畏、崇高之情,观者之所以可以产生这样的情感与所了解的中华文化是有关系的。所以乔迅所提到的装饰品的“感性的关联性”,笔者认为不只是可以研究中国的装饰品而对于西方的装饰品同样适用。
“视觉可以唤起其他感官、情感和智力的愉悦,因此感知可以移情。”[5]人对物品的感知或是对于世界的感知,视觉起着很大作用,尤其是在今天视觉文本对于我们的生活影响很大。通过视觉的愉悦调动起其他感官的愉悦,特别是情感、精神上的愉悦。《老子》第十二章中有言:“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6]在道家传统思想中,关注到物本身,就要摒弃感官的外在感知,讲究“虚静”“恬淡”“无为”,认为这样与物一体才能感知事物的内在。而乔迅认为,应该充分调动起身体的感官来感受事物。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这两种思考路径笔者都认同。这两种思考路径的感受不同,道家讲究对于物的态度是物与我相融,去除外在感官的感知,做到内心的涤静这样才能去感知物;而乔迅的方法是通过视觉唤起其他感官的愉悦,从而唤起观者情感上的愉悦,但产生的愉悦不仅是感官上的,最终还要达到情感上的愉悦。情感上产生愉悦的前提是不但能被装饰物的表面引起愉悦感(pleasure),而且还要理解物的内在隐喻(metaphoric)。
(三)器物物质的思考(thinking materially)能力
在《魅感的表面:明清的玩好之物》中,大量的高清图片十分有质感,就仿佛器物真实地呈现在眼前一样。单看这些器物,就能让人心旷神怡并产生愉悦感(pleasure)。乔迅在“‘器物—身体和表域”这一小节中,以“双手执酒杯”为例,描述了我们在欣赏把玩这个器物时,这个器物是如何对人发号施令并引导人进行欣赏的。这一部分给笔者的启发是:原来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解读器物,这样冰冷的器物,本是没有生命的器物有了自己独特的性灵,并且有了温度,这样让观者有了想与这件器物进行更深一步的交流。乔迅还阐释了装饰品具有与人的身体有关的隐喻(metaphoric)。在《魅感的表面》中,乔迅也提到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与工艺品融为一体”[1]20。笔者不是特别理解乔迅所说的这个“融为一体”具体是指什么,它是否与道家的“天人合一”有异曲同工之处,但笔者认为,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二者的语境不同,但是乔迅这样的思考路径和西方其他的研究学者相比已经是有非常大的改进。
乔迅在《魅感的表面》中提到:“如同其他强调装饰(decoration)的社会性的阐释一样,这种阐释,无论对了解社会现象多有启发,最终还是不足的,因为他们无法解释装饰(decoration)是如何运作,才可以有这么大的力量去左右社会进程。将装饰品只视为奢侈物品低估了装饰品的作用。我们需要审视装饰(decoration)的内在资源,才能对装饰(decoration)的力量有全面的理解。”[1]61乔迅开始注意到装饰品的内在资源,而不是简单地用社会学方法去研究分析装饰品,因为他发现只是简单地从社会学角度去看装饰品太浅显,无法进行深入地了解装饰品,也就无法研究中国艺术史。乔迅虽然没有从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和阐释,但是他有着着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思考,他的研究和阐释与其他研究中国艺术史从社会学角度切入的研究学者不一样,乔迅开始真正地注意到器物本身同时也更加注重主体本身,注重主体体验。用这种器物质地(thinking materially)的思考方式去思考装饰品,在观看和把玩装饰品时,就会产生表面的“愉悦感(pleasure)”。
二、反思乔迅的研究方法
中西方的文化思想和学术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西方国家研究中国艺术史难免会存在一些错误的认知,这些认知或者研究方法如果放在中国艺术研究语境下,有很多都是错误的,但是西方学者可能并不认为是错误的,他们就是要按自己的理解和研究方法去归纳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去认识中国艺术。虽然我们对待西方的研究理论不能削足适履,但是却可以开拓一些新的思考方式和研究路径,对研究中国艺术史有启发的思考路径,我们应去认真思考。从乔迅对中国明清时期装饰品的研究可以看出,乔迅从“愉悦感(pleasure)”的角度切入,并且赋予物思考能力。乔迅的研究方法非常具有原创性,敢于突破西方的二元体系研究,突破二元体系进行“愉悦感”(pleasure)的探究,笔者认为对于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艺术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二元体系太具有西方研究方法论的印记。
乔迅的《魅感的表面:明清的玩好之物》不是让中国人更加了解明清时期的装饰品、从中国本土的语境去阐释,也不是向西方人解释中国明清时期的装饰品,而是写给那些理解他的思维方式,能与他思维契合的研究学者。虽然其研究角度非常独特并且逻辑思维缜密,但是在这本书中,他回避了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思考,没有把研究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只是从“愉悦感(pleasure)”的角度切入,还有分析视觉引起的感官关联性、器物与人的同思,仅凭这样三点想把中国明清时期的装饰品研究透彻,并且可以以小见大,是远远不够的。研究中国艺术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研究一定要回归到中国艺术之根,回到中国艺术的根基上去,才能把中国艺术研究透彻,如果不深入中国哲学来思考中国艺术,那就感觉不到中国艺术文化魅力的独特性。
三、结语
从乔迅的《魅感的表面:明清的玩好之物》(Sensuous Surfaces:The Decorative Object in Early Modern China)中,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乔迅研究中国艺术的独特性,因为他跳出了西方原有的二元对立的研究体系,笔者认为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他出奇的思考路径不管是对西方的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有着很大的启发,让笔者感到对于艺术史的研究是没有穷尽的,对于文本信息的捕捉,要有敏感的感知力,但是有效的感知力需要长期的训练。虽然乔迅的研究角度新颖,并且研究方法十分有突破性,但是归根结底也存在着弊端,存在着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不能不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哲学思想的方面去深挖。纵然角度新奇,但是不结合中国艺术精神、中国艺术之本去研究,终究还是研究不到根上,感受不到中国艺术独有的魅力。
参考文献:
[1]乔迅.魅感的表面:明清的玩好之物[J].刘芝华,方慧,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2]洪再新,杨多.展示明清时期艺术消费的多重空间[J].美术学报,2013(2):77-82.
[3]James Elkins.Why Are Our Pictures Puzzles? On the Modern Origins of Pictorial Complexity[M].London: Routledge,1999:258.
[4]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38.
[5]裴珍妮, 趙毅平.中国明清时期艺术的观照方式[J].装饰,2018(1):27-31.
[6]老子.老子[M].方勇,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14:45.
作者简介:孙继超,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