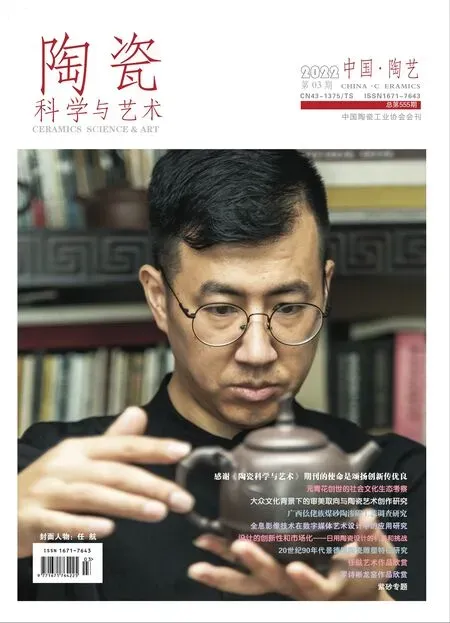陶刻山水书画之韵味
——浅析作品《四方双色鱼尾瓶》的创作
季 赟
紫砂陶刻所塑造的画面,带有典型的中国传统美术风格,无论是刻字还是刻画,都蕴含着浓郁的传统书画艺术风采,陶刻山水便很好地继承了传统书画艺术的精髓,并在其原本的基础上继续阐发衍化,最终形成了独特的陶刻艺术语言。在当代紫砂陶刻的创作中,有关于山水的书画刻绘屡见不鲜,此类作品并非是对传统书画作品的复制,而是根据紫砂器载体本身的条件重新设计规划后进行的再次创作,传统书画艺术的精神在紫砂器上重现光彩,这不仅增添了紫砂作品的艺术底蕴,也延伸了陶刻本身的创作界限,极大地丰富了陶刻的艺术语言。
作品《四方双色鱼尾瓶》上的陶刻创作采用了经典的书画结合的形式,在其中一个瓶面上刻下了宋代王禹偁的《村行》,另一面则刻画山水,诗中所描绘的意境与山水所塑造的画面相得益彰,让人在观赏之后再产生联想,在意韵上沉浸其中,其所表现出来的韵味充满了传统书画艺术的特点。中国的山水画历来强调写意,讲究“计白当黑”、“虚实相合”,在整体的画面表达中,黑白两色对应着实景与虚景,是相互对立的色彩。从现代美术的思维角度来看,这两种色彩分别代表了色彩的两极,能够产生非常强烈的对比差异。在紫砂陶刻的刻画中,通常也采用这两种色彩进行表达,紫砂器本身的颜色即是底色,由于紫砂器并非黑白色,所以眼前这件作品选择了黄色作为对比色,紫黄两色共同构筑起作品的对比感,其画面运作的原理与传统书画的黑白色是相通的。
作品《四方双色鱼尾瓶》一面所刻画的《村行》描绘的是一幅迷人的山野风光,其中包含了情真意切的乡土之情。很多艺术家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乡土之情,这一方面是联系艺术创作者的文化上的“根”,另一方面也是真实的情感表达,而真实的情感是感动其他人的必要因素。迷人的山野风光和真切的乡土之情,其画面必然是令人舒适和温馨的,所以在作品另一侧所刻画的画面以清淡刻为主,虽是山水,却无浓墨重彩,没有刻画大片浓重的阴影,而是以短促的刀法,将山野间的阳光凸显了出来,整幅画面呈现出一幅淡雅之姿,山峦依旧叠嶂,流水依旧倾泻,但不会使人感到有压力,相反画面逐级而上,如同冶游一般的景色使人轻松而愉悦。

传统山水书画艺术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意韵,创作者的思绪会影响书画的表达,或抒情或旷达,或伟岸或沉郁,情绪波动都在山水之间,山水的变化衍生出各种情感表达的方法,意韵自然也就蕴含其间。传统书画山水往往都向往“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的艺术境界,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来阐释意境。紫砂陶刻要想获得同样的表现力,必须思考如何用陶刻的艺术语言来加以转化,传统的山水笔墨能够通过晕染创造隐藏的景色,以短刀法进行刻绘的陶刻无法具有晕染的效果,所以要反其道而行之,利用传统美术中的留白留空技巧,将光影未尽之意纳入空白之中,用山水细节部分的刻画来完善整体的画面轮廓,让人可以通过这些细节推断出全体,让留空变为留实,同时也创造了独属于陶刻的画面韵味。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说:“山峰本来是不能语而‘无语’的,王禹偁说它们‘无语’或如龚自珍《己亥杂诗》说‘送我摇鞭竟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这些看似违和的说法实质上点出了山水画的本质,画面“无语”,但只要塑造好其间韵味,山水之间就能自然的道出语言。”作品《四方双色鱼尾瓶》一面刻画了一幅紧凑的山水画,另一面则是用完整的《村行》将画面内涵完整补充,书画相互结合,正反韵味的叠加,最终在观赏者的脑海中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富有诗情画意的山村情境图,映衬了“以画入诗”、“由诗入画”的过程,传神地反映出创作者的内心空间,那股悠然和怅然,拓宽了作品整体的艺术气韵。
从整体而言,作品《四方双色鱼尾瓶》的创作采用书画结合的形式来布局和构图,借由对传统艺术文化的进一步解读,衍生出自身独有的意韵表达,用实际的创造来对自我的理解进行重新演绎,技巧性地运用陶刻技法,重塑了对书画山水的理解。
结语:紫砂陶刻本就是传统书画的衍生,想要创作出优秀的陶刻作品,就必须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的书画艺术。当能够熟练地理解传统文学的艺术性,那么就能够通过画面的刻画来加以表达,从而创造出独树一帜的艺术韵味及趣味,让刻画的内容相互映衬,彼此互补,从而塑造出更多的文化内涵,这样作品的意韵得到加深,其艺术吸引力也自然获得加强,紫砂陶刻的魅力便由此发散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