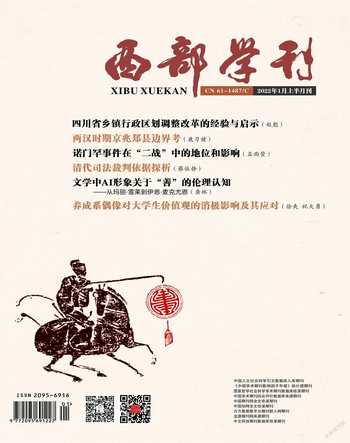清代司法裁判依据探析
蔡依静
摘要:在面对司法裁判时,清代司法官员有时会依据情理作出裁判,有时又会依据律例作出裁判,其既不能完全归属于依法裁判类型,也不能单纯归属于情理裁判。清代的司法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其制度有审级、循环簿、审转以及上控等,儒家思想主导的文化氛围影响着官员的心理偏好。国家法在清代司法活动中得到了广泛的适用,情理也是审判的重要依据,二者常常会结合起来适用。清代的司法裁判是一种情法两尽的类型,展现出中华法系不同于其他法系的司法追求。
关键词:清代;司法裁判;国家法;情理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1-0080-05
关于清代的司法审判活动是情理裁判还是依法裁判这个问题,学界有着广泛的争论。以滋贺秀三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清代的司法裁判活动多是适用情理作为裁判依据,其司法裁判具有不确定性,可归类于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卡迪司法”类型。以黄宗智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清代的司法裁判属于依法裁判,判决的作出仍是主要援引了当时的法律条文。以徐忠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清代的司法裁判实际是一种情法两尽的裁判,这种类型的裁判极力维持着法律与情理之间的平衡。从这些学者的不同观点可以看出,由于援引的依据具有特殊性,从而导致清代司法裁判类型难以被明确归类。因此,研究清代的司法裁判依据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中华法系自唐代正式确立以来,对于周边国家影响至深。科学评价传统中国司法活动,认定传统中国司法裁判的性質,对于认识中华法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传统中国司法活动,推动当代中国法治的发展。
一、清代司法的制度、文化背景
(一)清代的司法制度
基于行政兼理司法的原则,清代司法活动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一方面清代的司法制度为司法活动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这种司法制度又与行政挂钩。换而言之,清代的司法官无论是为了顺利进行司法活动,还是为了体现其政绩,都必须遵循司法制度。可以说,清代的司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官员的司法行为。
首先,关于清代的司法审级向来有多种观点,主要有三级说、四级说和五级说。三级说将清代的审级划分为州县、府和省,这是因为该观点认为“道”是“司”的分出机构,而“司”又是归属于“省的”;四级说则是将其分为州县、府、司和省;而五级说更进一步划分为州县、府、道、臬司和督抚。之所以存在不同的观点,主要是对“道”和“司”两级的司法职能存在争议。实际上,“道”与“府”的司法职能相当,按察司对各类案件享有独立的司法审判权,因此清代的司法审判级别包含着州县、府、司和省等四级[1]。其次,州县作为清代司法审判活动的第一审级,州县官的职责包括“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励风俗,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阙职而勤理之”[2]。由此可知,州县所辖范围内的司法纠纷是必须交由州县官处理的。清代的司法纠纷类型并不以刑事和民事作为划分,而是以刑罚的执行为标准进行划分的。所谓刑罚的执行包含了笞、杖、徒、流、死,以徒刑为标准分为拟判决徒刑以下案件和拟判决徒刑以上案件。拟判决徒刑以下的案件一般是那些户婚、田土类型的案件,而拟判决徒刑以上的案件则是那些命盗重案,但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案件州县官都必须审理,并且受到监督。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州县自行审理一切户婚、田土等项,照在京衙门按月注销之例,设立循环簿,将一月内事填注簿内,开明已未结缘由,其有应行展限及覆审者,亦即于册内注明,于每月底送该管知府、直隶州知州查核,循环轮流注销,其有迟延不结、蒙混遗漏者,详报督抚咨参,各照例分别议处。”[3]换而言之,拟判决徒刑以下的案件虽为州县官全权审理作出最终判决,但需要为此制作“循环簿”交给上级查核,以监督州县官的司法活动。对于拟判决徒刑以上的案件,州县官的审判权受到审转制度的限制。所谓审转制度,就是指州县官在对拟判处徒刑以上的案件进行初审后,需要将该案逐级向上详报,最后由有权对该案作出判决的审级作出终审判决。由此,所有案件的审理都要受到相应的监督。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上两种官方主动的监督方式外,还有一种被动的监督方式,即上控制度。当案件当事人或其近亲属对州县官的判决不服时,他们可以向上级官府逐级控告,此为上控制度。上控制度不同于前两种监督方式,它并非由上级官府主动监督,而是一种由民间提起的被动监督方式。虽然提起上控的条件较为严苛,但是仍对州县官的司法行为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综上,影响清代司法官的主要司法制度包括审级制度、循环簿制度、审转制度以及上控制度。这些制度看似是独立的司法制度,其实深受清代行政体制的影响。作为行政兼理司法的州县官,其司法活动不仅不是独立于行政,甚至还与政绩和升迁紧紧联系在一起。基于此,州县官在进行审判活动时,一方面受制于司法监督制度,另一方面还需迎合上级官府。这就使得清代的司法官员在作出裁判的时候,特别是对那些需要进入审转程序的案件时,一般都会选择作出保守的裁判,即司法官会更多地考虑适用国家法,从而最大程度避免承担司法责任和行政责任。可以说,清代的司法审判不仅仅是司法活动,还同时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
(二)思想文化氛围与官员的心理偏好
除了司法审级等制度的影响外,清王朝的思想文化氛围和官员的心理偏好也极大地影响着司法行为。制度性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代司法官的司法行为选择,而思想文化因素则强化了他们的司法思维和行为选择。因此,研究清代的司法活动不仅需要分析客观的司法制度,还要深入探讨思想文化氛围和司法官的心里偏好。
儒家思想作为清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深刻影响着当时的统治阶级的统治行为和百姓的心理认同。首先,统治阶级在选拔官员的时候,必然会要求被选拔者具有与其相同的思想。基于此,科举考试作为选拔清代官员的重要途径,它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核心考查所有学子,由此清代的学校教育也必然以儒家经典为主。清代的学子入仕必须经过学校的教育,而清代的学校分为官学、私学和书院三类,都以科举考试为目的[4]。这就使得清代的官员在入仕之前接受的教育皆以儒家经典为主,他们在深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普遍构建了一种儒家化的知识结构和心理认同。在入仕之后,一方面社会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另一方面清代百姓的思想和心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司法官在进行司法活动的时候必然将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为了使司法行为得到统治阶级和百姓的认同和服从,司法官在作出司法行为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运用儒家的思维方式。
儒家向来重视礼法和伦理道德,在法律问题上倾向于以情理服人,同时坚持息讼、无讼等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清代的司法官们一方面是不愿意处理纷繁的诉讼案件,另一方面则是在司法活动中会运用儒家的思想和原则来处理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官的心理偏好必然是其作出司法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由此可以见得,在这种司法审级制度和儒家思想的监督和渲染下,国家法与社会思想文化共同对清代司法官的司法行为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清代司法裁判的依据
(一)清代司法裁判活动中的国家法
在清代司法审级等制度的严格监控以及儒家思想的强大影响下,清代的司法官既要严格遵循国家法,也要把情理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学者黄宗智根据巴县、宝坻和淡水等地的民事案件,分析得出清代的法律制度是由背离和矛盾的表达和实践组成的[5]。也就是说,清代的法律制度用高度道德化的语言表达,但在审判操作中呈现出实际化的现象。实际上,法律条文和情理的考量比重在不同的案件中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许多案件的判词并未引用诸如《大清律例》等法律条文,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清代的国家法在司法活动中仅起到了象征性作用。应该肯定的是,清代的判词具有一定的诗性和人文气质,但是从清代中期开始,判词逐渐把文学表达和法律实用性结合起来,到清代后期,判词越来越注重法律适用性,并且逐渐呈现出一种规范化的表现[6]。换而言之,清代的判词并非皆以情理论事,它仍然以其法律性为特征。事实上,由于刑事案件或是拟判决徒刑以上的案件会进入审转程序,这就意味着这种类型的案件需要经过逐级的审查和裁判,一旦下级衙门审理不当就需要承担责任。因此,清代的司法官在面对这类案件时会选择作出更为保守的司法行为。换句话说,在这类案件中,他们更加注重对法律的适用,通常会把法律条文作为审判的依据。在乾隆年间发生的一起命案中判决就如是写道:
“该臣等会同督察院、大理寺,会看得威宁州倮民阿得刀伤雨濯身死一案。据此,应如该抚所题,阿得合依良人殴他人奴婢死者绞律,应拟绞监候,秋后处决。该抚既称:沙氏主使背杀起□,合依不应重律,杖八十。系妇人,照律收赎。老四、者補、者则听从背杀,致酿人命,均合依不应轻律,笞四十,各折责十五板。时逢热审,照例宽免。”[7]
可以看出,在这份判决中案件当事人的处罚都是以法律条文作为依据作出的。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条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清代作为一个封建朝代,皇帝掌握着生杀大权,只有皇帝才能超出法律之外定生死,而官吏是不具有这种权力的。司法官只能根据法律的规定进行审判,否则就会触及皇权的根本,这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事。
因此,清代的国家法在司法活动中得到了实际且广泛的适用。国家法在清代司法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二:一是刑事案件或拟判决徒刑以上案件必须以国家法作为判决的依据;二国家法起到了规范司法官审判权的作用,以防止官员随意滥用权力。因此,可以说国家法在清代的司法审判活动中起着实质性的作用,而非仅具有象征性意义。
(二)情理在清代司法裁判活动中的作用
在儒家思想的极大影响下,“情理”成为清代司法审判活动的重要依据。甚至在立法的层面上,“情理”也是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将情理运用到司法活动中是中华法系独有的特点,是中华法系与其他法系最为不同的地方。在清代,尽管情理本身是一种非形式的、感性的东西,但却在理性的司法活动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情理是一种修辞,并非具有明确定义的术语[8]36。苏亦工教授认为,“情”既是指实情又是指感情,“理”則是基于一定价值观念所形成的道理[9]。可以看出,情理并非是一种完全抽象化的存在,相反,它具有一定的标准。只是相较于实定法而言,情理更类似于一种法律原则,这种法律原则既指导着清代的立法活动,也指导着审判活动。在现代,一般而言,法官在进行审判活动的时候都会避免直接适用法律原则。然而清代的司法官们却频繁地将“情理”这一法律原则运用到实际的司法活动中,必然有其一定的深意。
正如滋贺秀三教授所言,清代的审判是一种教谕式的调处活动。之所以将审判当作一种教谕式的调处,首先是因为儒家思想提倡息讼、无讼;由于百姓过于健讼,令司法官员苦于大量庞杂的案件;诉讼纠纷的妥善解决也是考量各级官员政绩的条件之一。因此,审判的目的,一是妥善解决纠纷,二是教育百姓减少诉讼。把情理写进判决中,甚至作为审判的依据,这比引用国家法更能使百姓得到共情,从而起到教育百姓的作用,也能更好地实现审判的目的。其次是由于清代社会的发展,法律难以解决越来越多复杂的纠纷。因此,在立法空缺的情况下,情理作为一种法律原则,能够为司法官的审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依据。最后是由于清代的官员不允许在其故乡任职,他们必须去往不熟悉的地方任职,对于初来乍到的官员来说,他们难以一下子弄清当地的风俗习惯,并且强硬地适用法律也难以让百姓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更好地行政,以及维护当地的稳定,将情理运用到审判中,更能使当地的百姓从心理上认同、执行判决,从而避免激活上控程序。值得注意的是,把情理作为审判依据的案件大多是户婚、田土类案件。一般而言,这一类型的案件不会进入审转程序,司法官员也就不会被强制要求运用国家法来进行审理,而是可以直接将情理作为审判依据。在这个层面上,宽泛的审判权给司法官的司法行为选择留下了一定的自由空间。
不同于生硬的法律条文,情理基于其独特的性质和作用成为清代司法审判活动中的重要依据。只是要看到,情理作为一种审判依据,并非能够运用到所有的案件中,特别是在涉及重大命案的时候,情理就无法单独成为审判的依据。作为一种具有补充性质的审判依据,情理更多被运用到民事案件判决中。实际上,情理的运用并非会与国家法的援引产生冲突,作为一种裁判依据,情理的作用主要是用来弥补国家法的不足。因为这种特殊的作用,清代的司法官喜欢运用情理来使判决更具说服力。所以,虽然国家法和情理都是清代司法裁判的重要依据,但是相较于国家法而言,情理实际上是一种辅助性质或者说补充性质的司法裁判依据。
(三)国家法与情理的内在联系
清代的司法裁判并非完全是依法裁判,也非仅仅是依情理裁判。实际上,清代的司法裁判活动在其特殊的司法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将国家法和情理共同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只是二者在不同的案件中具有不同的地位。换而言之,户婚、田土类的案件会更多地适用情理,而严重的拟判决徒刑以上的案件则会更注重对国家法的适用。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法和情理并非是两种毫不相干的裁判依据,事实上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一个国家的法律文化必然是深受着社会及其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统治者制定法律的目的无非两种:一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二是为了维系社会秩序,而儒家思想恰好迎合统治阶层的目的。以儒家文化为其主导的清代社会,其国家法必然是在儒家精神的指导下构建起来的。可以说,法使情理得以明确化,并赋予情理以强制力[8]39。因此,法与情理并非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次,在一份判词中很少会有只适用法律或只适用情理的情况。一般来说,判词由陈述事实、辨明是非和判定责任利益三部分构成,其中辨明是非是其核心[10]。辨明是非实际就是说理,司法官一般会把法律和情理结合起来为其判决提供论据。所以,国家法和情理并非是完全独立适用的,特别是在民事案件上,二者常常会结合起来适用。
在讨论清代司法裁判活动的时候,不能孤立地看待法律和情理,而是要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否则就会得出片面的结论。实际上,正如徐忠明教授所言,清代司法裁判属于一种情法两尽的裁判,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方面,情理和律例一直互动,从而构成一个开放的循环体系[11]。司法裁判在运用国家法和情理这两种裁判依据时候,也就意味着司法活动并非仅追求形式上的正义或实质上的正义,其实更多的是在追求合法性和合理性之间的平衡。
三、情法两尽的清代司法裁判
关于清代司法裁判的类型,向来有许多学者在讨论。一些学者认为清代司法裁判由于过分追求实质正义而缺少了形式正义,进而得出清代的司法裁判具有“不确定性”,并且是属于一种由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卡迪司法”的裁判。实际上,“卡迪司法”只不过是一种用来作为研究方法的概念工具,而不是一种研究目的[11]。我们不能直接将清代的司法裁判等同于“卡迪司法”,也不能因为清代的司法裁判援引情理,而将其视作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司法裁判。清代的司法裁判并非完全依靠情理,也非纯粹引用法律条文,而是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适用的。这种“情法两尽”式的司法裁判既是受到社会条件的影响,也是司法官员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
在行政統筹司法的清朝,司法更多的是服务于行政,或者说司法活动实际上是被涵盖在行政活动当中的。基于此,官员对法律也就没有那么强烈地重视,从而清代的法制也就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清代难以产生出诸如“司法独立”“形式正义”“实质正义”等理念,司法官员自然也不会去追求这些理念。但是,这并不是说清代的司法官员并不把合法性作为其判决的目的,相反,在他们看来,案件的判决首先是要符合法律规定,其次是要合情合理。检验官员是否具有优秀的行政能力,主要看其所在的地方社会秩序是否和谐,而一个地方社会是否和谐,又要看当地的司法情况。有序的司法活动,需要司法官员作出令诉讼当事人和民众信服的判决。在法治不健全且不被重视的清代,仅依靠法律不能作出公正的判决,生硬地援引法律容易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这就需要情理来弥补这种不足。因此,符合法律规定是首要的条件,但为了使判决更具有信服力和执行力,还需要让判决能够达到合情合理的程度。
清代的司法审判活动极具本土特性,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属于某种司法类型,也不能说清代的司法审判活动由于缺少对法律条文的引用而不具有形式正义。诚然,比起形式正义,清代的司法审判活动更加追求实质正义,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法条和情理作为达致判决目的的工具,二者是紧密联系且相互补充的关系,司法官员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清代法治的不足。可以说,“情法两尽”的清代司法裁判展现出了中华法系不同于其他法系的司法追求。
四、结语
在研究清代的司法审判活动的时候,要认识到法律并非仅有一种标准。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会孕育出不同的法律文化,不能用同一种公式去套用不同本质的法律文化,这其实是一种粗暴的分类方式。与其他国家的法律文化不同,清代的司法并不过分强调形式正义,但在追求实质正义的时候也没有忽略形式正义,无论是适用法律还是情理作为依据,都不能抹灭清代的司法审判在很大程度上是满足了当时社会的普遍正义观。因此,不能孤立地研究清代的司法裁判活动,而要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要求来看待当时的司法裁判活动。
参考文献:
[1]李灿.清代地方司法的实证研究——以刑名幕友为视角[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8.
[2]清朝通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45.
[3]大清律例[M].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80.
[4]王静.清代州县官的民事审判——一个法律文化视角的考察[D].长春:吉林大学,2005.
[5]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4.
[6]苗丽.清代判词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2.
[7]清代地租剥削形态[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5.
[8]王亚新,梁治平.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9]苏亦工.清代“情理”听讼的文化意蕴——兼评滋贺秀三的中西诉讼观[J].法商研究,2019(3).
[10]俞江.明清州县细故案件审理的法律史重构[J].历史研究,2014(2).
[11]徐忠明.清代中国司法类型的再思与重构——以韦伯“卡迪司法”为进路[J].政法论坛,2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