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灭风吹初见时
——吴伯藩的留德十年与壮志未酬
叶 隽
同济大学文学院
吴伯藩 (1900 —1937),又名吴屏,湖北广济人。幼年随父到北京生活读书。1920年,吴伯藩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1921年夏季学期短期在柏林工业大学,后转基尔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氨基吡啶的结构式探讨》。吴伯藩的经历和季羡林颇像,留德也是几乎十年,六年读博,之后留校任教。其父吴道南(1875—1930),曾留日学习法政,是同盟会会员,后任湖北军政府司法部副部长,迁任北洋政府司法部佥事等,熊希龄内阁发布其为司法部常务次长未就职。吴伯藩之留德当与家世有关,因父亲之故,他自然也就得机会游历南北,譬如幼年即随父赴京,并在北京大学预科就读。北大的传统,自然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吴伯藩的求学时代也正是蔡元培长校的时期,可以说是尽得风气之先,选择留学德国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所谓“但开风气不为师”,乃是一个春风化雨的过程,使得学生能在此环境中悠游涵养、逐步成长。冯至曾说:“在北大独特的风格与民主气氛的熏陶下,我的思想渐渐有了雏形,并且从那里起始了我一生所走的道路。雏形也许是不健全的,道路也许是错误的,但我却从来没有后悔过,只要提起北大的彼时彼地,便好像感到种回味无穷的‘乡愁’。”这个说法应是有代表性的,放置在差不多同期的朱偰、吴伯藩等人身上都应是有效的。
正是因为这种前期求学的人文熏陶和修养形成,吴伯藩在留德时代介入到文化交流事业中去也就是情理之中了。早先在法兰克福的时候,他和王光祈、魏时珍、郑寿麟都住在郊外,彼此相邻,甚至都在王光祈的房东处包餐,可见他们的关系相当密切,而且王光祈确实是一个中心。其实这批人在一起一定也颇为有趣,因为他们所治专业不同,王光祈、郑寿麟都是人文学科,而魏时珍习数学、吴伯藩习化学,这种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相互交融,落实在具体个人的身上应是颇为有趣的。当然需要承认的是,那代人的传统文化根基都不错,这恐怕才是他们能够彼此欣赏、合作无间、有所作为的原因。譬如中德文化研究会的建立,他们都是发起人,无论学科如何、偏向如何,乃共同宣示:“我们是生长在东方文化的中国,现在又来到在西方文化的德国,便引起一种重大的责任。这个责任便是力谋中德两民族的了解和同情,并且产生第三种文化,以实现我们人类共同合作的生活,一洗人类历史的污点。”这应是王光祈的主笔,但也能反映出他们这批留德学人的共同想法。
1930年,吴伯藩归国,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北平大学、辅仁大学、陆军大学等。在武汉大学化学系期间,同事有陈鼎铭、熊强、刘云浦等。吴伯藩归国的时代,正值国难当头,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成为十四年抗战的开端。吴伯藩在北平大学化学系任教授期间,编纂、翻译了相关作品,也是与这个大背景密切相关的,譬如由北大化学系印制的《国难中民众对于化学战应有之认识》,即是颇为重要的一个贡献。作为化学界前辈的刘树杞(1890 —1935)作序称:“军用化学一科,自欧战以后,始渐发达,我国化学工业尚在萌芽时期,故对于军用化学之各种制造,自属毫无基础,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倭寇猖獗,国祸日亟,一般有志之士,始知国际条约原不足恃,非积极备战不足以自存,于是朝野上下始渐觉军用化学一科,于国防上甚为重要,友人吴伯藩先生于沈阳事变发生之冬,曾撰《国难中民众对于化学战应有之认识》一篇,刊诸平津各报,对于军用化学发达之历史,毒瓦斯之种类及其攻击与防御方法,言之颇为详明,诚国难中一不可多得之作也。”从这个介绍来看,吴伯藩是相当敏感的,一旦意识到国难已至,即起而行之,以自身所长参与到报国抗战的洪流中去,可谓以笔为枪之典范。吴伯藩绝非简单待在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他的大局观很敏锐,一方面认定“中日不并立,尽人皆知”,另一方面明确自身的反应:“世界上有强权始有公理,有武力始能维持和平,处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国人应打破列强均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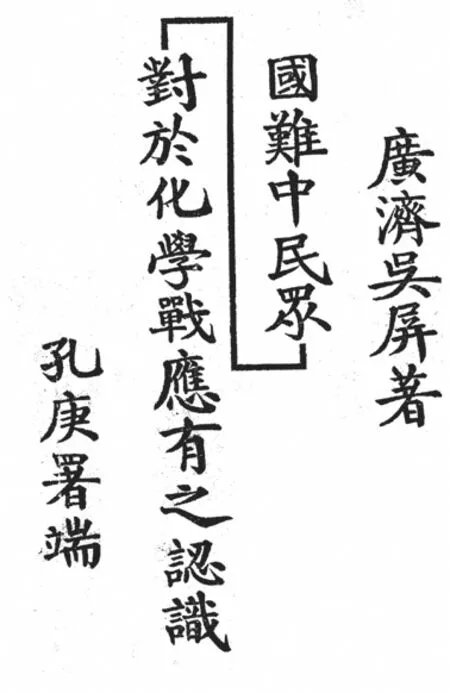
吴伯藩:《国难中民众对于化学战应有之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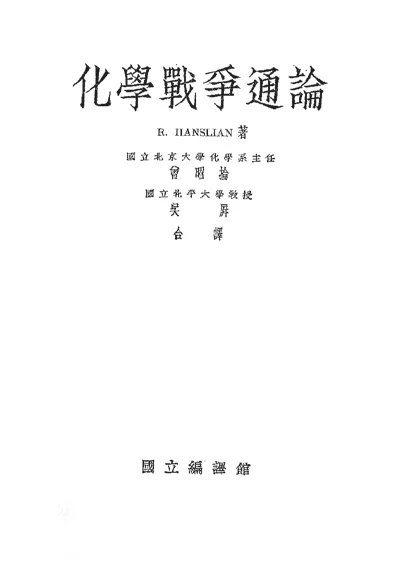
吴伯藩、曾昭抡合译:《化学战争通论》
吴伯藩还与时任北京大学化学系系主任曾昭抡(1899—1967)合译了德国学者韩斯联(Rudolf Hanslian,1883—1954)所著《化学战争通论》()一书,译者如此交代译事背景与过程:“韩斯联所著《化学战争》为西文书籍中关于此方面最有价值者之一。其讨论化学战争之历史,所用化合物,及其使用方法,至为详尽;而尤偏重于气体战争及烟雾在战争上之价值,殊为他书所不及。二十一年冬,我国受东邻之侵略,已逾一周,国人乃深知非自强无以图存。斯时国立编译馆成立未久,因鉴于目前急切之需要,乃励志多译关于军事科学之专门书籍,爰以此书之翻译属之于译者二人。译者承此,深以为幸!惟受命后不久,榆关事发。继而热河失陷,滦东不守,平津垂危。译者身处北平,无日不在危险之中。加以课务繁重,余暇不多,以致迁延至二十二年五月底始得完成一半。正在继续进行之中,而日军已迫北平城下,平市学校,暂时无形停顿。乃南走首都,费时三月而后成之。”所以,我们可以想见那代人的艰难与持守,在那样一种“国破山河在”的背景下,不但要面对国土沦丧、生命受胁的挑战,而且更需以笔为旗,在书桌上对强寇进行奋战。所谓“惊见江山满胡尘”,说的就是这种悲凉境地吧,旦夕国破,身为奴隶,是所不愿,乃南行避祸,不甘苟延,以译书而为战事!
此书译事是有更大的历史和学术背景的。时任国立编译馆自然组主任、留美归来的化学家陈可忠(1898—1992)称:“二十一年夏,教育部召开化学讨论会,特设国防化学一组,意在广征众见,共筹良策,以树国防化学之基础。与会诸公乃有请教育部设立国防化学讲座及请国立编译馆编译国防化学书籍等议案。本馆也鉴于国防情形之迫切,暨军事教育方面之需要,爰请国内对此问题夙有特殊研究之专家担任翻译。”他提到了几部著作,其中两部译著、两部专著,前者除《化学战争通论》外,还有德国学者Dr.Hugo Stoltzenberg的,即《毒气制备实验法》,由张郁岚翻译,他当时是军政部兵工研究委员会专任委员。另外两种是关于实验法,即曾昭抡的《炸药制备实验法》、韩祖康(1894—1968)的《烟幕发火剂及爆炸实验》,后者是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要知道,“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无论在哪个层次,哪个环节,哪个领域,哪些方面,哪些时空,都是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主导力量”。这固然是化学学科的基本情况,其实也反映出留学生在中国现代学术体制里的普遍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化学学科的学者因其所治专业关系往往能学以致用,所以对国家的建设发展大计也极为重要,从曾昭抡、吴伯藩、陈可忠等人的行动即可看出,这其中曾昭抡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此处不赘。
如果说当抗战之际,作文译书,以防备化学武器、准备化学战争为己责,是相对消极的防御,那么进行有效的建设性发明,则是积极的创造性工作。吴伯藩同样也致力于发明,曾研究出一项成果,即以酒精代汽油当作汽车动力燃料。“他曾租用一部汽车,实验以酒精为能源,在行驶途中,详细观察,记载其功能数据,终于成功地发明了以酒精代汽油,部份解决了当时国内能源短缺的困难。”这自然引起轰动,于是就有了多省开花、筹建酒厂乃至最终殒身的结局:
自此声誉鹊起,冀、晋、陕、桂诸省纷纷电邀,敦请吴往各该省筹建酒精厂。两三年内,全国共建七厂,均以伯藩为厂长或名誉厂长。伯藩亦为此南北奔波,绝少休息。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聘伯藩为省政府顾问,由彼经手从德国进口酒精设备。西安事变时,伯藩恰在西安筹建新厂。蒋介石被囚后,杨虎城将军曾亲赴该厂,恳请吴博士继续留陕主持厂务。设备收到后,德国厂方给他一笔回扣,伯藩分文不收,如数交给新建酒精厂。当时有人讥其为“书呆子”,正直人士则称他为真正之爱国科学家。
吴伯藩在陕西建立的咸阳酒精厂,这是中国现代工业史上一件值得记录的大事业。我们可以看到吴伯藩非为牟利,在有利可图甚至是“回扣外来”的情况下仍坚持分文不取,表现出一个科学家的应有品格,也表现出他对咸阳酒精厂的“爱厂如家”。1936年11月16日,李书华(1889 —1979)称其游陕时 “在该所(陕西化验所——笔者注)遇吴伯藩先生与谈余等欲游唐太宗昭陵之意,吴谓如往游时,可在咸阳酒精厂寄宿”。从这句话的信息里,我们可以看到吴伯藩在咸阳酒精厂还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安排朋友的食宿不在话下。这其中也有吴伯藩的留德背景在起作用。陕西筹办酒精厂时,是通过上海的礼和、禅臣两家洋行订购机械,这些都是德国公司。而伴随机械运达,礼和洋行派Manwald 与 Krotz两名德国工程师负责建筑厂房,1937年底竣工,1938年2月出产。
吴伯藩因为与陕西的这种合作渊源,所以也被陕西人当作“自家人”,譬如“西安事变”后就被陕西列为实业界代表之一安排在陕西绅商界和平请愿团之中。而且,吴伯藩在“西安事变”中颇有奇遇,有人作如此叙述:“按吴氏当‘西安之变’,尚留酒精厂中。值汉中保安司令张笃伦以谒蒋来陕,借寓厂内。乱作,溃兵有期得张而甘心者,入厂索张,时张已化装遁去。乱兵乃执吴以询,吴急誓之曰:如知张之踪迹者,当为杨虎城之儿子。乱兵不信,以枪胁之。吴益惧,再发誓曰:如知张之藏匿处者,当为张学良之孙子。乱兵为之发笑,乃释之。”这个幽默加传奇的故事,可以让我们窥见吴伯藩风格之一斑,不但机智善变,而且能及时低头,甚至不惜贬损自己,但在这种乱兵凶险的情况下能够以急智自救,则确属聪明之人。事实上并非每个科学家都善于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更不用说是做出实业,甚至“多点开花”,布局全国了。能做到这一点,当然与吴伯藩本人的科技长才之外的生性、眼光和格局是有关系的。范长江(1909—1970)指出:“建设厅创办,由吴伯藩先生主持之咸阳酒精厂,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为非常重要之企业,而对于日常生活品之‘自我供给’,仍有其有限的范围。”以范氏著名记者人的新闻眼光,自然是颇为挑剔的,但总体来说对吴伯藩的建设事业仍是予以了充分肯定。
吴伯藩是有大局观的。譬如,他曾应邀在开发西北协会的会议上作报告:“西北数省,地广土肥,矿产丰富,实一最好的国民经济资源地,东北失后,西北一变而为吾国国防线最前之一部,且为吾国民族复兴之重心。”很能见出全局性的眼光和以国家战略为考量的那种宏大视域,他接着说:“开发西北首重交通,总理遗教上已明白昭以我们,无待赘述,西北交通当示铁路为最要,公路次之,但铁路建设需款多而费时,且难普及,公路则反是,西北之地形地质,筑路较易,且可利用兵工及民众服役,帮助筑路,这样如在有决心有组织之领导下,短期内当可完成西北之公路网,我们看看一年来陕西全省公路网之渐次完成,即知顷述者,为绝对可办到之事,西北公路网完成后,交通便利,其他建设,自易随之而生,所谓一举百举是也。”吴伯藩要谈的核心问题,当然是他的拿手好戏和本色当行,即液体燃料,但却很有论述的技巧,当然关键还是大局观,从孙中山的遗训开始说起,一步步铺垫而至,一点不觉突兀,让人很容易接受。
当时各省的关系,大致是以拥权自治的成分居多,所以自谋发展也是常态,一旦看到有利可图的发展项目,自然不会坐视错过。在陕厂就绪之后,广东省的儒将香翰屏(1890 —1978)又急电发给吴伯藩,敦请其赴粤办厂,其结果是:
粤厂初竣,伯藩急回北京省母。复接广西李宗仁敦请赴桂,伯藩以母病重,婉言谢绝,旋三接急电,且云:“博士何厚于粤而薄于桂?”伯藩不得已,遂乘西南民航长庾(庚)号专机赴桂,飞至广东三水上空,天适大雾,飞机触山,坠毁于三水青旗河,与驾驶员詹道宁同时遇难。次日以专轮拽起,机首入泥三丈,伯藩与驾驶员仍端座(坐)机舱,机舱未进水,盖系窒息而死,时为一九三七年二月,伯藩年仅三十七岁。
李宗仁的三次电邀,可谓是“催命电”,以吴伯藩的正当英年,本可徐图施展、以济壮志,可惜却是天不假年、折戟沉沙。这次赴桂之旅,却是死亡之约,专机的大雾触山,与此前徐志摩乘机失事竟如此相像。吴伯藩自然不会料到专机也会失事,他的生命竟然止步于在这辗转旅途、振兴工业的行程之中!
在笔者看来,吴伯藩之死,其实也是“殉节”,他是殉给了自己所致力的化学工业,也算得是科学事业与国家振兴。他的初衷,或许正如当初在“中德文化研究会”发起时所表达的那样,是希望“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幸福,要建筑在各民族的了解和同情上面”,而他的勠力于科技、发明、实业的工作,也正是这个大愿景的一部分。这一点也从官方所给予的身后哀荣可以见出,两广政府联合出面收殓其遗体,以专车运往其家乡武汉,并在广州举行追悼大会,余汉谋、香翰屏、李宗仁、白崇禧等出席,同时发表《追悼吴伯藩博士公启》。说来也可算是“国殇”了,因为吴伯藩所作的事业,绝非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聚焦于国家民族的实业的兴盛,甚至更有全局性的战略考量,应当说他不但是尽心竭力了,也是殒身不恤的。吴伯藩在学术和战略上的见解是受到重视的,他曾撰文《中国液体燃料之代替问题》,发表于《学术汇刊》的创刊号上,此刊由委员长行营学术研究总会编辑,发刊词由顾祝同署名,刊名为贺国光题写,可见其明显是一个官方的高层刊物,吴伯藩此文条分缕析、资料详实又简明易懂,最后得出结论说:“我国液体燃料之来源,实以自极物油中提炼较为得计,川黔康等省对外交通不便,舶来油料价格奇昂,而年产桐油柴油数量甚巨,如能就近设厂炼制,短期内可谋自供自给,其影响国防资源民生经济、当不仅挽利权塞漏卮已也。”这里显然考量的不仅是学术上的论证,而更是作为实用政策的便利可行。
其实,吴伯藩本来有更大的计划和抱负,这从川籍实业家宁芷邨(1895—1984)的回忆中或许可看出端倪:“在北京碰到北大教授吴屏,他以专门研究实业的发明家自居。旧中国是个‘贫油’国家,所需汽油全靠进口。吴屏告诉我他发明了种代汽油,主要成分是无水酒精。他说现在急切需要这种东西,如果能办一个代汽油厂,不仅发展前途可观,而且还可对国家作出贡献。他还告诉我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也想搞一个代汽油厂,准备以洋芋为原料。吴说,四川有一种漏子糖,可作为我们在四川试验的大宗好材料。吴屏又约傅作义来京与我一起商谈办厂之事,并亲自开着汽车在京郊跑了三天,用以试验他发明的代汽油,看来效果很好。于是我们决定:傅作义在缓远办,我在重庆办。正在研究时,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也派人由西安到北京来找吴屏,准备开办代汽油厂。当时不仅各省想办代汽油厂,蒋介石政府也想把吴屏抓在手中,聘吴为国防委员,并派他到广东去将几家酒精厂改为代汽油厂。吴屏在前往广东时告诉我,重庆办厂等他从广东回来再说,叫我先回四川做好准备,并同机偕行。在西安机场休息时,我们又与邵力子谈了几小时,说好吴由广东回来时先到西安,然后来四川。我回成都时,刘航琛亲自来接我并支持我的计划,路上还停车参观了糖厂。几天后我前往内江搞原料,做准备工作。可是不久,接到西安方面电报,说是由广东回京时因飞机失事遇难了。”这段叙述内涵颇丰,值得细加揣摩,首先是吴伯藩的能量很大,与各方面的关系都相当不错;其次是吴伯藩的眼光和策略兼具,一方面在陕西等地陆续开拓疆域、打下根基,另一方面看中了四川作为原料和实验地,即天府之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地理意义,所以他选择和宁芷邨合作;而且他的这个计划其实是得到了很好的回应的,即不但有宁芷邨作为合作伙伴,还进一步找到了四川的重要人物刘航琛(1896 —1975),后者是大商人,有刘湘的“财神爷”之称,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等职。若吴伯藩健在,这项事业在四川生根发芽当可预期。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像此类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发明,显然并非仅是一人关注或成就的事业,有论者就这样记述道:“此外尚有一椿涉及目前大众所关心解决能源问题的轶事,值得叙述。为解决船用燃料问题,那时虽有用无水酒精、木炭、焦炭(租借法案内曾购买数以千计的比国发明制造的焦炭发气炉Gasogene)等替代汽油装在长途汽车上使用,同时还有工程家向德、汤仲明、吴伯藩、沈宜甲、李葆和等也在各处研究制造上述替代汽油的各种设备……”所以关于当时的燃料替代问题,多位科学家都聚焦此上,那代人的家国情怀由此可见一斑。
1937年3月28日,在北平举行了吴伯藩教授追悼会,时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的许寿裳(1883—1948)题赠了挽联:“奇肱驭飞车方期万里长风讵料翻身眠海底,杜康通化理太息众人皆醉未遑谋国遽仙游。”可以说是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吴伯藩如“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一生,可惜终究是人生长途行路难,长风破浪会无时!学化学的人,终究免不了和实际的工作相联系,所以学以致用是常态,遇到危险也是常态,吴经熊当初就是因化学实验遇险而另学法律的,吴伯藩没有因险而退,也没有遇火生危,但却另遭坠机之难,或许也就是命有所许吧。既然所治为化学这样经世致用的学问,投身实业与殒身许国,都也是意料中事。或许这就是那个时代索取于知识精英分子的吧。可以说,中德文化研究会命运多舛:1927年,孙少荆遭强权暗杀;1932年,金井羊病逝沪上;1936年,王光祈殇于波恩;1937年,吴伯藩遇坠机之祸。十年之间,四杰同去,真是天妒英才而英灵不灭,他们在中国现代史上所留下的痕迹,将永久地书写在历史的绢帛之上,而且必将是浓墨重彩!
注释:
[1]关于吴伯藩的一个简要介绍,参见陈从阳、肖建章:《“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发起人生平略考》,《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6年第9 期。《吴伯藩》,武穴市地方志办公室1989年编:《广济历代名人传记》,第46—47 页。关于“以王光祈为中心的法兰克福群体”(Die Frankfurter Gruppe um Wang Guangqi),参见Harnisch, Thomas:(《中国留德学生——1860 至1945年间留学的历史和影响》).Hamburg: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Asienkunde, 1999.S.213-226。
[2]董品:《吴伯藩》,湖北省志·人物编辑室1984年编:《湖北人物传记》第3 辑(试写本),第157 页。黄冈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4年编:《鄂东人物志·现代人物卷》,第290 页。
[3]《“但开风气不为师”——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冯姚平选编:《冯至美诗美文》,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 页。
[4]王光祈致幼椿、太玄、劼人、鲁之信,《少年中国》1920年第2 卷第2 期,此处转引自周月峰编:《〈少年中国〉通信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 页。
[5][26]《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少年中国》1921年第3 卷第2 期。
[6]经顺祥:《刘云浦教授传略》,姜堰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姜堰文史》第14 辑,第139 页。
[7]刘树杞:《序一》,吴屏:《国难中民众对于化学战应有之认识》,国立北京大学化学系刊本1932年。
[8][9]吴屏:《国难中民众对于化学战应有之认识》,国立北京大学化学系刊本1932年,第1 页,第2 页。
[10]曾昭抡、吴伯藩:《译者序》,[德]韩斯联(R.Hanslian):《化学战争通论》第iii 页,曾昭抡、吴屏译述,国立编译馆1935年版。
[11]《七七事变困北京》,陈士骅:《陈士骅诗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69 页。
[12]陈可忠: 《弁言》,[德]韩斯联(R.Hanslian)著,曾昭抡、吴屏译述:《化学战争通论》,国立编译馆1935年版,第i 页。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陈可忠在此处称吴屏为北平大学教授,而曾昭抡是北京大学教授。
[13][德]H.Stoltzenberg 著,张郁岚译:《毒气制备实验法》,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
[14]张培富:《海归学子演绎化学之路——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史考》,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 页。
[15]戴美政:《曾昭抡评传》,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6][17][25]董品:《吴伯藩》,湖北省志·人物编辑室1984年编:《湖北人物传记》第3 辑(试写本)第157 页,第157 页,第157—158 页。
[18]《陕游日记》,李书华:《李书华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 页。
[19]陆实愈:《三十年来中国之酒精工业》,吴承洛总编,中国工程师学会编辑:《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中国工程师学会三十周年纪念刊),京华印书馆南京厂1948年版,第4—5 页。
[20]《樊嵩甫关于陕西绅商界和平请愿团赴潼请愿情形致孔祥熙电》(1937年1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 页。
[21]雨:《吴伯藩之生平》,《北洋画报》1937年第31卷第1529 期。
[22]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上海大公报馆1937年版,第98 页。
[23][24]吴伯藩:《液体燃料与西北之关系:在开发西北协会第三届年会讲》(附表),《西北刍议》1936年第2 卷第9 期。
[27]湖北省武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广济县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版,第856 页。《粵桂绥署決追悼吴伯藩》,《新闻报》1937年2月27日第7 版。
[28]顾祝同:《学术汇刊发刊词》,《学术汇刊》1937年创刊号,第1 页。
[29]吴伯藩:《中国液体燃料之代替问题》(附表),《学术汇刊》1937年创刊号。
[30]宁芷邨:《我所经历的三个不同时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乐山文史选辑》第4 辑,第43 页。
[31]关于宁芷邨的简历,参见《重庆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重庆百科全书》,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659 页。宁芷邨写过多篇回忆录,如《回忆四川水泥厂》《大华生丝公司的创立与结局》《华西实业公司的演变》《中国兴业公司始末记》《成都学生两次罢课亲历》《犍为光复与胡谭》《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述略》《刘航琛其人》等。
[32]《抗战来华研究水道的美航业家——伯恩哈》,胡光麃:《大世纪观变集》第4 册《影响中国现代化的一百洋客》,中国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版,第364 页。
[33]蔼人先生(代撰):《三月二十八日吴伯藩教授追悼会,许院长挽联如下》,《新苗(北平)》1937年第16 期。蔼人先生当是王承吉(1882—1944),他字蔼人,作画世家,其父王毓辰(1832—1890)、其子王羽仪(1902—1996)皆为画家。洪瑞:《国画家王梦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衢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衢州文史资料》第3 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 页。许寿裳是鲁迅好友,应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之邀于1934年出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朱慧、娄国忠:《德艺双馨 风范长存——许寿裳先生生平事略》,绍兴鲁迅纪念馆、绍兴市鲁迅研究中心编:《绍兴鲁迅研究2008》,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 页。而《新苗(北平)》 的出版方正是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出版委员会编辑。所以这里的许院长当指许寿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