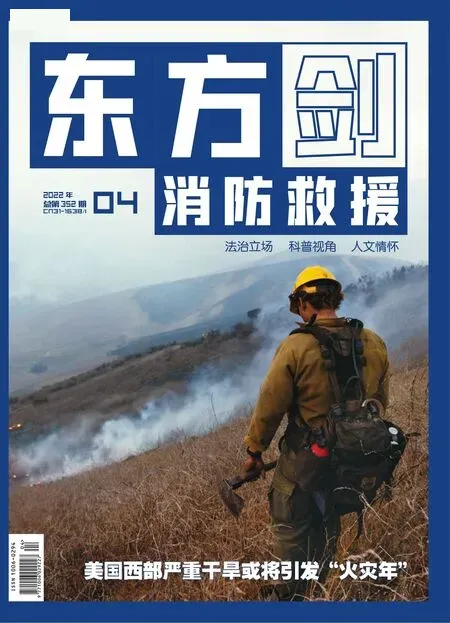隋苑繁华迹易磨
何振华/文

嵩山路北起金陵路,南至太仓路。长356 米,宽18.2~21.3 米,车行道宽10.5 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筑,以河南嵩山命名。1914年以曾任法国驻华公使名命名葛罗路。1943年复名嵩山路。沿路为住宅。
之前我讲到了嵩山消防队,就不能不讲讲嵩山路。嵩山消防队是在淮海中路上,近嵩山路。过去我父亲那一辈老人都习惯了把淮海中路叫霞飞路,其实在叫霞飞路之前,它以法国公董局的总董宝昌的名字命名叫宝昌路。嵩山消防队那个时候就叫宝昌路救火站,救火站设在嵩山路巡捕房,是当年法租界的救火会中心。有史料显示,近代史上的宝昌救火站参与扑救的火灾有多起,影响大的有朱葆三路(今溪口路)上的晋泰纸行火灾、中正南二路(曾名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上的立德布厂纱布间火灾、打浦桥棚户区大火。中国近代史上的消防始于民国,民国的消防始于上海,上海的消防始于租界,这也是不争的史实。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老上海人都注意到了地铁1 号线、10 号线、13 号线的黄陂南路站和新天地站的站名前都加冠了一个“一大会址”的新名。从嵩山消防救援站往西沿淮海中路步行没几步路,就到黄陂南路口了。此地原来四通八达的宝康里,早就被夷为平地,拔地而起的太平洋百货中心,今天已经叫新天地广场了。
沪上闻名遐迩的宝康里,如果尚存,距今也有百多年“可阅读”的历史了。它有两条南北直弄和三条东西横弄,贯通淮海路与兴安路、黄陂路与马当路。120 幢石库门建筑,外观气派。宝康里是在晚清沪上丝业巨子宋书荪的幼子宋永康捐赠给天主教会的地皮上建造起来的里弄。宋永康16 岁就病亡,遵其临终遗嘱,天主教会在此建造了这一大块住宅区,宋家以“宝康”之名纪念宋永康。
宝康里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上是留有浓墨重彩的。1913 年二次革命失败翌年,孙中山不为挫折所击倒,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并自任总理。廖仲恺、胡汉民等人任各部主任。中华革命党把推翻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作为党的纲领,先后在湖南、广东、江苏等地发动四十多次起义。被蔡元培誉为“民国第一豪侠”的陈其美,当时是实行部主任,也是上海总部负责人。实行部就设在宝康里33 号和34 号。辛亥革命时期,陈其美在沪成功发动武装起义,被推为沪军都督。他与黄兴可谓孙中山的股肱卿佐,当时他就在宝康里组织策划革命党人刺杀了袁世凯的得力助手郑汝成,打响了反袁斗争第一枪。宝康里住过不少革命党人,有被捕牺牲的尹神武,有坚定追随孙中山、大革命时期任湖北省财政厅长、后在1927 年七一五政变中牺牲的辛亥元老詹大悲。
五四运动爆发后,时任中华女子美术学校校长的唐家伟,率先在宝康里60 号发起成立了中华女子救国会,师生全都成为该会成员。当年6月5日,上海市民声援学生,发动罢工、罢课、罢市斗争的第一天,唐就率领师生走上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居住在宝康里35 号的郑家璧,也是五四运动的妇女活跃分子,多次组织上海女界联合会举行宣讲会。她作的《亡国铁路》的报告,有力推动了五四运动在上海的影响及深入。
1910 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日本吞并韩国后,大批韩国爱国志士来到了上海,黄浦江畔成为了他们争取复国独立的基地和重要战场。宽松的租界环境,自然而然使宝康里形成了韩侨社区,不少韩国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及知名人士都在此寓居。宝康里15 号是韩国东学党总部;23 号是韩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曾任临时政府总理的李东辉寓所;27 号韩国国父金九住过;44 号是中共韩国支部所在地。1932年4月29日,侵华日军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大会,日本陆军大将、领事及其他军政界要员被炸身亡。事件主角壮士尹奉吉,也住在宝康里,他就是在宝康里安恭根家里的太极旗下宣了誓之后携带炸弹化装入场。虹口公园的壮举,震惊世界。尹奉吉牺牲时年仅24 岁,他是中、韩、朝三国唯一公认的烈士。“淋漓痛饮汉城月,慷慨悲歌沪市秋”,他就义前的豪言壮语,至今仍让人低吟长叹。
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住过宝康里54 号,这里是向警予、杨之华组建的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所在地。杨之华与瞿秋白在此相遇、相识、相爱,结合为一对革命伉俪。1930 年代,打入日伪内部的女诗人关露,也住过宝康里……

尚贤坊位于淮海中路(原霞飞路)358 弄,属石库门里弄住宅,于1924年建成
过去宝康里的居民多为高级职员、中等企业主、军政人员、教授、医生及文化人,弄内及沿街也开设了商店、医院和学校。现在毗邻宝康里旧址的嵩山消防队,除了它自身原有的那幢醒目的红色老建筑之外,周边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之间,分明还有几处同样也很是醒目的红色老建筑:一是当年霞飞路法租界巡捕房旧址,曾经是卢湾区东风中学;一是咫尺之遥的新鸿基“中环广场”,当年是法国公董局及其创设的法国公学旧址,抗战胜利之后,黄炎培、江问渔、孙起孟在此创办比乐中学。它的对面,是今天全球首个融艺术、人文、自然三大核心元素于一体的豪华购物中心K11 大厦。大厦旁边那一片人去楼空已多年、不知修旧如旧至何时的红砖石库门新式旧里,就是发生过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郁王之恋”的尚贤坊。余生也晚,我虽不可能得见高吟“我比前贤路已宽”的郁达夫,但在1980 年代,经孔敏中先生介绍,有缘与王映霞女士访谈过两次。1935 年6月,出席遵义会议后的陈云,在长征途中奉中央之命秘密抵沪,向上海的党组织传达会议精神,并与共产国际重建联系。经章乃器介绍,当时陈云就住进了尚贤坊21 号他的三弟章郁庵家里。章郁庵是陈云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他不仅掩护陈云,还设法帮陈云联系上了潘汉年,在上海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形之下,得以尽快赴苏联。
而今,有人念念不忘“荣社”,嘴上老挂着“杜公馆”。而我每经此地,不免总会想到吴湖帆的“梅景书屋”,想到冯超然的“嵩山草堂”,格外想念我的恩师张双勤先生。书香门第出身的先生,在天津大学读书,好好的洋行饭不想吃,父亲一去世,旋即肄业南下唱滑稽。先生说自己吃了一辈子开口饭无怨无悔,却怎么都不允许我涉足滑稽界半步。先生是天主教徒,先生的德艺双馨,文艺界有口皆碑。小辰光,我每个星期要去宝康里他二层楼的客厅兼书房兼卧室报到。一日拜师,幼承庭训。现在,宝康里不复存在。今年是先生九十冥寿,我是连凭吊也无凭。不能说是伤心地,隋苑从来让繁华。繁华过眼,过眼即拥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