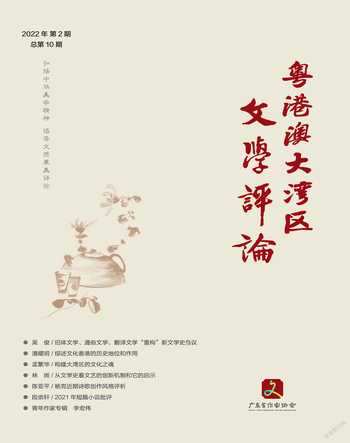创作谈:二相采访装置
李宏伟
摘要:一个谜语:A出一个谜语给B,B的谜底必须是另一个谜语,抛回给A,A再以作为谜底的谜语还B……如是往复。理论上,谜语可以无休止拆解;实际上,当然会在某一刻停止。那一刻,或许是双方默契致一,一笑而止。或许是越猜越小越猜越窄,了无意趣,讪讪作罢。也有一种可能,一方拆错,游戏告停。有些猜谜与拆解是必须,有些则未必。作者与所写的猜谜是必须,猜测人物的动机、行为、语言,人物给出反馈,猜对才能继续。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左右互搏的游戏,“我”与“我”的互看。作者与读者或评论者的猜谜不是必须,后者可以随时退出。不过,偶尔对作者与人物的猜想进行猜想,不失为一种乐趣。另一个谜语:C如何知道,其新加入的游戏中,A与B早已猜过他(她)的猜想?
关键词:相;装置
第一相:指定
对司徒绿的采访
1.愿意介绍一下你的基本情况吗?被记录的、没被记录的,都可以。
司徒绿:连我的梦境、沉默你都捕捉了,还有没被记录的?(点上烟,抽一口)司徒绿,24岁,生存部的勘察员。通常根据部里的安排,检测指定地区辐射、水源、气候等系列数据,提交报告,判断该地区当前是否宜居、未来演变趋势;不定期前往检测地区复查,核对、调整前述趋势判断;根据个人判断或直觉,偶尔前往非指定区域检测。
2.作为“团契”的一员,是否意味着“勘察员”仅仅是你的身份掩护?
司徒绿:勘察员是我的工作,在任何方面,对我的意味都绝非“仅仅”。它首先意味着如此险恶环境下,个人对他人的义务,是依据个人能力与他人肩并肩。这是我的选择,是我力所能及。生存日益局促,前景日益暗淡,我们这些幸存者,无论生活在丰裕社会、匮乏社会,难道不应该携手面对吗?当然,你不了解。作为恶之源头的男人,你始终是“团契”致力于推翻的。
3.“使者计划”这一趟行刺之旅下来,你仍旧认为“男人皆恶”吗?
司徒绿:这一路上,陈聿飞引导了我,让我明白男人中还有人和女人肩并肩。赵一最后更是教育了我,有超越于区分男女的更开阔的视野。可即使排除你问话中的不怀好意,“男人皆恶”仍旧没错,它与我的体会与陈聿飞、赵一让我看到的并不矛盾。免得你继续在这方面啰嗦,我愿意修正一下。那种以先天权力役使万物、以成团成块欺凌独立颗粒的意识,由你们这些偏狭的男人体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它导致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无尽野蛮,导致人类今天面临毁灭的局面。这种意识难道不应该称之为“男人意识”,由此难道还不能推导出“男人皆恶”?陈聿飞、赵一和任何与女人肩并肩的男人,反对的不正是这样的“男人意识”?
4.哦哦,请你放轻松。我本来想问的是,“使者计划”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转变。
司徒绿:得了吧,我请你放轻松。有话直说就行,用不着夹枪带棒,意图激怒我。(沉默中抽完烟,又拿出一支,然后放下)陈聿飞说得对,“得习惯这个味道”。你看,我放下匕首,拒绝割下赵一的人头,回到治安部,继续我的勘察、我的生活,仍旧等待“团契”安排新的任务。似乎和以前一样,但这就是我的转变——我更明白“有力量的颗粒,是我们的团契”的意思,更努力做一个有力量的颗粒。
5.有些晦涩,解释一下?
司徒绿:没什么可解释的。词语都在这里,力量、颗粒、我们、团契,明白的人会在事中明白。至少,赵一给出的狗屁选择,我现在完全不用去想。
对赵一平的采访
1.愿意介绍一下你的基本情况吗?外在的、内心的,都可以。
赵一平:没必要。
2.你是从什么时候计划好的?对徐粒说那番话时,还是去参加独立日时,甚至早在决定去做污染区处理工时?
赵一平:没什么计划。“人可以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只要他愿意也能承受全部的后果。”我确实对徐粒说过这话,可我并没有据此制定什么步骤缜密的计划,这句话显然也不能作为行动指南。它只是临时的撤退指南,标识最终的撤退边界,再积极一点,最多不过是选择的指南。一直以来,必须选择时,我以此为依据。我唯一担忧的,是影响赵匀后面的学习、生活,但依据《原则》和情势,基本能判断我最终选择的结果。
3.没错。你主动走进辐射区,以决绝的方式,免除了整个家庭受你无法婚配的影响。甚至,他们的生活还提了一级。但你想到了,赵匀因此而更名赵一,并且终生都在消化你的选择的影响吗?你想到了,你会因此被树立为典范,用以鼓动其他人采取同样“自绝”的方式吗?
赵一平:(沉默良久)推动一块石头,必然碰撞另一块石头。
4.不止碰撞了另一块石头。徐粒因为你这个决定,和她的爱人穆雪成立了“團契”,以“有力量的颗粒,是我们的团契”为号召。本来是个女性互助组织,发展到现在,声称“男人皆恶”,以推翻男性统治为宗旨。你对此有何感想?
赵一平:真的吗?(摇摇头,笑起来)有力量的颗粒、有力量的颗粒……徐粒,你真是有力量的粒子。你知道吗?我们讨论过,她的名字是不是应该由粒子的“粒”改成力量的“力”。现在……(回过神)对不起。没什么不好,就算徐粒她们成立“团契”的初始目的没那么极端,几十年下来,因应情势变化,总会有所调整。男性统治不应该推翻吗?不认可这一点的人总得说出理由,做出行动。
5.那么,你认可自己与月球隐士具有重合度吗?毕竟,现有资料中,你是第一个月球隐士故事的创作者。
赵一平:我的确为赵匀讲过一个月球隐士的故事,它可能代入了我的处境和感受,但绝非我本人任何层面的投射。后来衍生的故事中,他已经成为超级英雄,有超能力,有拯救心,更与我天差地别。不过,我很喜欢后来这些故事,也羡慕能写出这些故事的人。
对赵一的采访
1.愿意介绍一下你的基本情况吗?全部的、部分的,都可以。
赵一:(放下司徒绿、赵一平两人的采访记录)叔叔还是这样洒脱。我是在座唯一横跨三部分的人,就多啰嗦两句吧。我十二岁时还名赵匀,叔叔三十五岁,他生日前不能和人结婚的话,就得被流放至匮乏社会,我和爸爸妈妈会从丰裕社会的三等社区被赶去五等社区。最终……叔叔在生日前夜,自己走进辐射区,我们进了一等生活区,我成了赵一。二十二岁那年,我作为实习生,进入匮乏社会,为江教授传递了一个消息。几十年后,我知道了相应的处罚:“为赵一设定新身份,让其留在丰裕社会,过正常生活。在不同阶段,为赵一安排不同层次与角度的爱情经历,必须刻骨铭心。俟赵一年满三十五岁,流放至匮乏社会。”不知道仍是处罚的一部分,或者仅仅是其结果,我六十五岁时成为东方文明延续协会会长。并且,七十一岁时,我必须制订“使者计划”,通过司徒绿传递一个消息。
2.所以,你认为一切都是设计好的,协会早就给你指定了道路?
赵一:当然不是。一定有如此精密设定之事之物,但绝非协会、人类,可以窥望。否则,我们何至于百数十年仍旧陷在同一个泥潭里,且越陷越深?但消息如风,路上有人,一举一动、草摇木落,无一不是歧路上的标识,月光下的指引。叔叔以他的干净引我一段路,江教授以他的谜语引我一段路,我以一个选择为司徒绿为众人引一段路。如此而已,如此足矣。
3.如果不能设计好,你通过司徒绿给出的那个选择还有什么意义?
赵一:左手或者右手,黑暗或者安慰,重生或者绝唱。选择最重要的不是痛下决心那一下,否则,所有的占卜者甚至幼童,都可以随机决定。必须列出所有选项,穷尽每一个选项背后的骨牌。用叔叔的话说,知道推动一块石头后,连环碰撞下去,最后一块石头在哪里,才可能决定要不要推动第一块石头。所有的引路人,都是喊亮一条路,提醒别人仍有一个选择等待发现。捉住他人去推进的,那是完全置身事外的观棋的人。
4.那在你设想的未来图景中,西线有着什么样的位置?
赵一:我没有设想,你的意思,用“我理解的”更准确。在我理解的未来图景中,西线是脆弱的除不尽的余数,一如它现在。当年解散国家,成立人类文明延续协会时,社会图景是丰裕、匮乏的二元式。显然,这太过单调,因此西线作为余数出现。它脆弱,无论哪一边都能轻易将其摧毁,但摧毁并不能消灭,没了西线,余数总会以别的形式,再次出现。因此,我不愿意过多谈论西线,投射更多光线于其上,不是轻视它,而是更想保留它的混沌。谁知道,混沌会在未来孕育出什么来呢?
5.现在,你能给的指引已做出,你想喊亮的路已显明。还有什么是你想做的吗?
赵一:作为引路人,我的工作已结束,怎么选择、怎么演进,一切与我无关。我想找到十二岁那个晚上目送叔叔离开的那条路,找一个月光同样如水的夜晚,一个人往前走走。看看月光再一次洗下来时,我究竟能不能走到叔叔最后一个脚印里去。
第二相:随机
1.对迎面而来的人,说点什么吧?什么都行。
江振华:作为第十任会长,我履行了这一位置要求的所有职责,但我至今仍旧难以根除内疚。职责是一回事,感受是另一回事。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对当时的决定有悔意。哪怕以今日眼光,“净化”仍是当时唯一的最佳的方案。但清理一部分人来保障另一部分人,总归让人无法将之视作理所当然。
陈聿飞:你好,司徒绿。没想到,阴差阳错,这样认识。更没想到,随后会有这一趟旅程。你改变了我,谢谢你。要不是你,我还陷在种种纠结,挣扎于究竟该如何选择。其实,重要的从来就不是选择,对吧?要行动起来。能做一分是一分。现在,我致力于让两个东一区回归为一个。不妨说,这是一种试验,如果成功,丰裕社会、匮乏社会也就有可能复合为一。
桥洞里的女人:如果我说什么都无法避免有人在一旁窥探,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有闲的人才能够靠不停说为生,我不行,行我也不要。
小允:昨天晚上,妈妈烤了一个蛋糕,为我的生日。我知道,这个生日哥哥一定会在身边,会和我一起给妈妈喂下一块蛋糕。他俩也会一起,给我唱那首歌。可真的实现了,还是有些难以置信。许愿时,我没敢把眼睛全部闭上,总是留一条缝,盯着妈妈,盯着哥哥。保不齐,真正闭上再睁开时,发现是一场梦呢?结果,吹蜡烛时,刚吹熄两支,我就笑起来,根本收不住,妈妈被我逗得也笑个不停。我还看见她笑着转过头,抹了两下眼睛。然后,我就特别想姐姐。画像早画好了,你什么时候来取?
常青田:拿到骨灰,我反而一下子轻松不少。就这么小的罐子,任谁都装得下。颜色嘛,不过是平常那些不起眼的颜色。气味嘛,好像闻不出什么特别的。味道嘛……对不起,我走神了。反正,还是那句话,谁都逃不了最终变成,这么一捧、一罐。走出来,我就想,拿它怎么办呢?放在家里显然没有什么意思,将来还不是会被处理掉。要是处理的人不知道它是什么,他是我的什么人,过于随意,虽然说到底不过是一把灰,总还是让人不舒服。就撒了吧,或者埋了。要不是那棵苹果树站在院内,埋在下面倒不错。当然,得把他从罐子里倒出来。
蔡哥:我没啥呀,没得啥可说呀。就还是在西线待着呗,还能去哪儿?在哪儿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往下过?
小钱:那部电影我看过两遍。两遍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开始,镜头对着那杯咖啡;两次结束前后相差不过两三分钟,第一次是他提起裤子,第二次他提起裤子还掏出了手机。两遍看了这么些内容,照样搞不清在讲什么。我有次问江教授,让他们准备这部片子,究竟要干吗。江教授只是笑着看我两眼,什么都不说。
杏子: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憧憬那美好的丰裕理想/啊,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携手前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徐粒:我不是抱著拯救心态去的。我知道,一平不需要这个。我就想看看,他会对我说些什么,他又会做些什么。他最终真的会像以往留给我的印象那样,绝不做不愿意做的事吗?第一眼看见赵匀,我就知道,一平这下麻烦了。无论什么决定,首先涉及的都不是他,而是赵匀。赵匀才多大呀,心里就装了那么多的事,谁看了不想帮他一把?
行脚僧:往下走。继续走。对于行走的人来说,时间是不可能真正封闭的,只看他能不能走得进去。
甜甜阿姨:我是从他那儿听到一平的事的。他不知道,他怎么会操心这些事呢?他其实,怎么说呢,肯定比一平更适合在一起生活。心大,踏实,对我好,对孩子好。他只是不懂,当个新闻似的,说什么主动走进辐射区,说本人条件特别好那种。我当时心里一跳,没什么理由,就猜到了是一平。果然,没几天一平的名字和他那事就……就到处都在说了。行吧,按自己的想法做了选择。但是,我得说,到现在我还是理解不了,一平也……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江教授:你有没有觉得我“有些面熟”,甚至已经问过我一遍了?虽然我可以保证,这是咱俩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见面。
衍生:附加问题
假设你们可以突破三部分的阻隔,知道彼此;甚至突破小说维度的限制,来到我面前。给你们各提一个问题的机会,问彼此、问我都可以,你最想问什么?
司徒绿:我想问赵一平。你当时放弃婚姻,是因为找不到(遇不上)你心仪的爱情,还是出于对这种带着强制性的婚姻本身的厌弃?
陈聿飞:假如有机会弄清楚来龙去脉。我想问问赵一,这么做是不是太刻意,反而把有活力的选项事先排除了?
赵一平:我不想问什么。
杏子:不管是谁,可以的话,都帮我给一平带个好。希望他,不管在哪儿,都好吧。至少,我希望他临终之前少遭点罪。
赵一:我想问司徒绿。你从匮乏社会出来,为什么还是回到原来的生活?一方面没选择与陈聿飞在一起生活,另一方面你们又并没断了联系?
桥洞里的女人:你到底是谁?
作者单位: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