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冬二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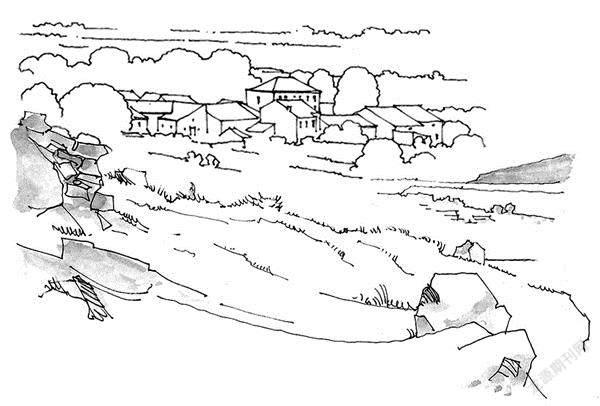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胡天翔,河南新蔡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在《百花园》《小小说选刊》《安徽文学》《四川文学》等期刊发表。出版长篇小说《避雷针》,曾获《百花园》《小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
口 琴
麦忙不算忙,就怕豆叶黄。
秋天的田野色彩斑斓。红的高粱穗,绿的玉米叶、红薯秧,黄的豆秧、花生秧,黑的芝麻秆,还有盛开的白棉花。收秋都是慢活,得按顺序一样一样地干。芝麻、黄豆先熟,拿镰刀把它们一棵棵割倒,芝麻秆用绳子束成捆立在晒场上,黄豆秧在晒场上摊开、铺平,让日头烤它,让热风吹它。高粱穗、玉米棒、红薯熟得晚,让它们再晒点阳光,吸收点水分。秋庄稼缠人,要耐着性子,忍着劳累,想着给老人看病,给儿子盖楼房,给孙子买奶粉,弯着腰、蹲着腿甚至坐着跪着,也要用手、用镰刀“擦掉”一块块的“色彩”。
二亩地的芝麻割了,二亩地的黄豆割了,花生秧子黄了,他跟着父母去东地里薅花生。半天薅个地头,还没个屁大的地方。晒场里还有芝麻要打,豆秧也要拢起来,父亲和母亲去了晒场。他站起来扭扭身子,捶捶腰,揉揉腿,赌气似的拽着一墩墩花生秧子拔出花生果,抖抖泥土,在地上摆成一溜。
天黑了,他才回晒场。母亲已回家做饭,父亲头上戴着矿灯,在灯光里垛芝麻秆。芝麻已打过了,粗布毯子上落满了芝麻和梭子,他和父亲抬着毯子放进麦秸垛后的小棚子里。芝麻秆垛好,豆秧也拢成堆,晒场里的活不多了,他先回家吃饭。
吃过晚饭,他从套房的书桌上拿起一个小盒子装进裤兜,抱著被子去了晒场。交代他夜里睡警醒些,父亲就回去了。摁灭矿灯,他斜躺在豆秧堆上,看天上的星星。夜空高远,星星像芝麻粒一样从天幕里挤出来,越闪越密。大地寂然,近处草棵子里有几只蛐蛐低吟,远处红薯地里有蝈蝈高歌。他掏出裤兜里的小盒子,掀开盒盖,拿出一把口琴。他轻轻地噙住琴孔,缓缓地吹起来。躺着吹累了,他就坐起来吹、站起来吹、来回走着吹。口琴声吓得蛐蛐静了音,他还循着蝈蝈的叫声,到红薯地里去吹,吹得蝈蝈闭了嘴,吹得露水湿了头发,他才钻进棚子里。把口琴塞进盒子里,他脱掉外衣,用被子裹着自己,沉沉睡去……
九月的夜晚,只要不落雨,他就来看晒场。
收罢秋,耩下麦,父亲闲了,乡亲们也闲了,他们来找父亲剃头。来早的坐在高条凳上剃头,来晚的坐在小椅子上等着,再来的抓把花生秧子垫着坐在地上。乡亲们来了,剃头的剃头,吸烟的吸烟,不吸烟的聊天,剃头的和吸烟的也插话,院子里很热闹。
吱——他拉开套房的门出来了。院子里安静了。大家都盯着他,没人说话,连正刮脸的人也扭头看,要不是父亲收刀快,这个人的脸上就划个刀口。来剃头的人,和父亲年龄差不多,大多数不认识,他就对着认识的人喊:邢老师、白爷爷、曹大爷——您来剃头啊!打过招呼,他奔向屋后的厕所。放完水,他回到屋里,听见他们和父亲的对话:
一民,亮子大学毕业了吗?
唉,毕业啦。
一民,亮子找工作了吗?
唉,不好找啊!
一民,村小学不是缺教师吗?让亮子先去代课嘛。
唉,不听话啊,小学缺老师时不愿意回来。
……
父亲叹一声,他的心揪一下。邢老师是他读小学的老师,教他两年语文课;曹大爷是村委的老会计,教他下过象棋;白爷爷是会算命的盲人,握一根竹竿走遍十里八村,给他摸过手相,说他能考上大学。1998年的秋天,他收到大学通知书,父亲还放电影庆贺,请他们来喝喜酒。他们夸他聪明好学,羡慕父亲供养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实习,父亲打电话让他回家,去村小学代课。那时,他想当记者,选择Y城晚报实习,不愿回家。三个月的实习期过了,报社领导明确对他说不招人,带他的石平老师鼓励他考公务员。准备了一个月,他考过笔试,背着被子回了杨楼。
他不愿见村里人。他不想听父亲的叹息,他想躲到没人的地方。
白天,走过干枯的池塘,他躲进村后的树林里看书。树林后面有菜园,有人来菜园里摘菜看到他,也问毕业了吗?找到工作了吗?他胡乱搪塞。小孩子也问,大城市的楼真有大树高吗?火车真像电视里的那么长吗?他不知道孩子们的名字,也不知道谁是他们的父母。他鼓励他们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就能进城了。考上大学也不分配工作,俺爹说净浪费钱,还不如打工哩!一个读初中的孩子说。他竟无言以对。
夜晚,拿着公务员面试书翻了几页,他拿着口琴出了门。他先是在自家屋后吹。口琴一响,杨小镰家的黄狗汪汪地叫起来。乡村的夜晚,狗叫声是会传染的。一条狗叫,一个村子的狗都叫。此起彼伏的狗叫声,他吹不下去了。走过干枯的池塘,走过一小片竹林,他来到村后的树林里。口琴声被树林一挡就散了,被风吹到竹林就消失了,不干扰狗耳朵了。他握着那把二十四孔的敦煌牌口琴,轻轻地吹起来。吹一种种旋律,忧伤的低沉的激越的;吹一首首歌,《梁祝》《大海》《新鸳鸯蝴蝶梦》……
吹口琴真好。哆咪唆是吹气、来发拉西是吸气。一吹一吸,吹吸之间,他的忧伤、他的烦闷、他的迷惑,都随琴声流淌而去。吹累了,他靠着高大的白杨树,什么也不想,仰望着天上的月亮发呆……
没人来剃头,父亲有时会去杨小镰家打牌。杨小镰开个小卖部,村里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只有老人们会去小卖部打扑克、打麻将。输赢不大,一元两元,熬个时间。一天下午,邢大国、杨大响和父亲等人哩,邢豁子叼着烟卷来了。邢豁子嚷着打麻将。邢豁子嘴不豁,嘴碎,爱吹爱谝,嘴不把门。连和了两把,邢豁子吐出一口口烟雾,又吹开了。
一民,别让你儿子晚上在树林里吹口琴啦。
嗯,咋啦?
昨晚俺去菜园掐菜,以为女鬼在哭哩,吓死人啦。
他心情不好,你个大男人怕啥。
一民,你给儿子找份工作嘛!要不你给俺买两条好烟,俺给你介绍个门路?
中!中!你操心啦,改天请你喝两杯。
邢豁子快五十了,光棍一条,整天混吃混喝的,父亲才不信他。不过,邢豁子的闲话,挠拨得父亲心烦。见有人来了,父亲把位子让给人家,甩着两只手,气呼呼地走了。去庄稼地里转一圈,父亲回家进了套房。他坐在书桌边看书。他看看父亲,父亲看看他。父亲盯着桌子上的口琴说:“夜里别去树林里吹了,人家说闲话。”
他看着父亲,父亲黑着脸看着口琴。放下书,他拿起桌子上的口琴塞进抽屉。
明天或者后天,笔试成绩该出来了吧?
象 棋
过了腊八,打工的人陆续回家了,杨小镰的院子里也日渐热闹起来。
杨小镰开个小卖部,卖油盐酱醋糖果,也卖鞭炮烟酒礼品。一到年底,村里人来玩扑克打麻将推牌九,赌钱赌烟赌瓜子。打牌的人围着桌子坐一圈,看牌的人挨着打牌的人又站一圈,从杨小镰家的二楼向下看,院子里就像长了四五个大蘑菇。打牌的人爱吸烟,看牌的人爱起哄,蒸腾的烟雾和热闹的欢笑声在院子里飘荡。
他知道杨小镰家很热闹。半个村子的人都能听见一阵高过一阵的哄笑声。腊月二十二上午十点,他掂着一塑料杯开水出门了。他不去杨小镰家凑热闹,是去找老曹下象棋。天空雾蒙蒙的,脸冷手冷,风还像蛇一样从领口、裤脚往身上钻。走过干枯的池塘,穿过竹林,向西走五十米,就到了老曹家。
杨树已经来了,正在堂屋里和老曹下棋。两人脚边烤着一个枯树根,红红的火焰噼噼啪啪地响着,屋子里挺暖和,有烟但不呛人。看了一眼,他知道杨树要输了。老曹执黑,一车领着两个过河卒在进攻,杨树只有一马一炮一士在防守。老曹下棋善用小卒,过河卒横排前拱,如车般威猛。果然,走了三四步棋,黑车站底线,双卒破士又逼宫,杨树收棋认输,让他和老曹较量。
杨楼有五个人会下象棋,曹永军、杨树、杨小石和他。他们的象棋都是跟老曹学的。曹永军是老曹的儿子,杨小石后来成了老曹的女婿。杨树和曹永军是童年的伙伴,老曹夸他比儿子聪明。初中没读完,杨树因家贫辍学,从掂泥兜子到掂瓦刀到杨楼建筑队的工头。曹永军高中没考上大学,去陕西当兵考军校,会开坦克呢。两年前,曹永军转业到县武装部,现在是古吕镇武装部部长。
老曹叫曹红志,今年七十了,不爱串门不去打牌,爱看报纸杂志听收音机,没事在庄稼地里转转,逢集就到陈店街上看看。十四年前,老曹是王庙村委的会计,戴副老花镜,胳膊弯夹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常常一个人走在王寨和杨楼间的小路上。
老曹不爱和大人说话,喜欢爱学习爱动脑的孩子。发新书了,他去村委找老曹要报纸包书皮,老曹放下手中的钢笔,拿刚看过的报纸给他。村委有个小食堂,老曹中午有时不回家。中午去校早了,校门没开,他去村委跟老曹学下棋。小学学了三年,老曹让他车马炮。初中,老曹让他一个车。高中,老曹让他个炮。老曹还教他下残棋。九宫格里,老帅位中间,对手对角两个车、两匹马,步步都要将军,一直将死老帅。老曹教他的这个残棋,中文系的象棋冠军范洪峰演练半夜才破解。
“亮子,邢豁子在牌场说面试人家问你树上有七只鸟,一枪打死了三只鸟,问你树上还有几只鸟?你回答说还有四只。是真的吗?”杨树问。
“面试不考脑筋急转弯,邢豁子不懂瞎说。”他说。
“邢豁子嘴里能跑火车,他是谝自己能哩。”老曹说。
“找工作恁难啊,等俺大福毕业后找工作不是更难?”杨树说。
“车到山前必有路,楊树你别担心,大福总比你掂瓦刀强哩!”老曹说。
“亮子也别灰心,第一次考公务员能进面试,不错嘛!”老曹说。
嘟——老曹话音刚落,院子外面传来汽车喇叭响。院门打开,曹永军回来了。曹部长回来了,咋没带司机哩!杨树笑着说。曹永军从兜里掏出帝豪烟,抽一根递给杨树说,树哥好,明天就是小年啦,接俺大进城哩。曹永军给他递烟,他没有接,摇头说不会吸。
曹永军来接老曹了。看看棋面,老曹是一车一马两小卒、士象双全,他是一炮双马,仕相各一。他收棋认输。棋没有下完,算是和局吧!老曹淡淡地说。收好棋子,老曹进西间收拾东西。树根还没烧完,他搬到院子里,杨树浇上一瓢瓢井水,升起一股股烟雾。
“亮子,你的事俺大给我说了,你在报社干过,镇里也缺个写稿子的人,镇长说一个月五百块钱,你回家和一民叔说说,中的话,过了年去县城找我吧。”曹永军说。
“有啥商量的,有活先干着,骑驴找马嘛!”杨树用脚踢他。
“谢谢永军哥,俺爹正发愁哩,俺就怕干不好。”他说。
“亮子,现在都是逢进必考,学习不能丢啊!”曹永军说。
“亮子,要有小卒一步步往前走的韧劲,接着考嘛。”老曹说。
他和杨树频频点头。老曹的衣物收拾好了,曹永军掂着一个大包袱装进了车里。老曹拿起桌子上的象棋说:“象棋也带上吧,过了年,你娘不会让我回来了。”
“俺娘不放心啊,您去了,俺娘也有伴说话啊!”曹永军说。
“曹叔,您去正好教孙子下棋,您的棋艺得往下传啊!”杨树说。
“人家打牌咱下棋,都是玩的。杨树、亮子,进城去看我,咱还下棋!”老曹说。
站在堂屋门口,老曹看了看院子,出去了。锁上院门,曹永军发动了车子。老曹拿着象棋坐进车里,对他和杨树摆摆手。他和杨树静静地站着,看着车子缓缓地驶出村子……
2002年的冬天,杨楼最后一个知青回城了。
责任编辑/何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