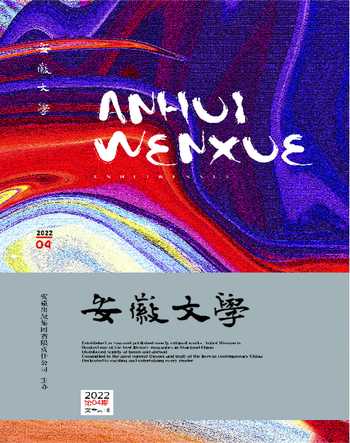老茧
响雷
被窝掀开的一刹那,女人睡得正迷糊,让突然涌入的寒气一激,哆嗦着醒了,眼一睁便箍住赵大块头的腰说,你不能出去。
赵大块头扒开她的臂说,我思量了一宿没睡着,还是得去,你莫拦着。说着下了床,摸黑穿上棉衣棉裤。女人慌忙点灯,屋里亮堂起来,却见他拔了木闩出去了。女人便在屋里骂,店又不能开,就算开了也没人敢来吃你的面,你非要死出去做什么!他在门外压着嗓子说,废什么话,撒泡尿的工夫就回来了,赶紧下来把门闩紧。
赵大块头要去巷尾的米面店扛一袋面粉回来,面馆的面粉袋子快见底了,他相信,就算暂时不能开门营业,总会有开门的一天,就算真不营业了,自家人活着也得要吃。这形势下去,面粉的价格铁定得涨。赵大块头不单是个大块头,他还颇有些经营头脑。他最拿手的就是擀面,这是他的绝活。一根三尺长的擀面杖在他手底来来回回,八仙桌面闷闷地响,四条桌腿颤颤地抖,他臂上肌肉也在一迎一送中一鼓一鼓的。等面的吃客都呆呆地看他,仿佛看一场表演。面饼擀大,折叠,再擀大再折叠,几经反复,擀成八仙桌面大的面皮。经他手擀的面,讲究的吃客能嚼出不一样的筋道。他这人向来闲不住,从不辜负这一身力气。七八天不擀面,他难过呀,感到手上的老茧有无数只蚂蚁在撕咬。
赵大块头的面馆开在夫子庙南边,堂子巷的顶头,门前横挂一面旗,旗上一个字:面。旗旧且破,时有风起,把旗卷到杆子上,像一团抹布。赵大块头擀面时瞥见了,再忙也要擦了手把它理下来。他憧憬着过些时日,请人刻一块木匾,脑子里都盘算好了,四个烫金大字:赵氏面馆。这会儿,北风从巷子里穿过,把他头顶的旗扯得哗啦啦乱响。
巷子里黑漆漆一片,除了石板路在疏朗的星星下闪着幽光,不见半点灯火。冷风直往脖子里灌,赵大块头把棉衣裹了裹,往巷尾走。石板路有点滑,前些天的积雨结成冰,冻而未化。冬至未至,天便这么冷了,这恐怕是他遇见的最冷的一个冬天。
赵大块头的面馆不大,前店后宅,店面只有一小间,能容四张方桌。客人坐满了,屁股靠屁股,后背贴后背,冬天挤着倒是暖和,夏天背上汗湿一片。来吃面的不介意,只图个填饱肚皮,一碗面囫囵下肚抹嘴走人。这闭门七八日里,擀不成面,赵大块头有闲工夫谋划起他的面馆来。他的面馆是在他爷爷的爷爷手上开起来的,一晃八九十年了,到他手上算是第五代。本来店面有两间,在他爷爷手上,因为抽大烟背了债,败掉一间。一间小店面维持生计勉强度日就算不错了,他却凭手艺,硬生生攒了些积蓄。他盘算着这两年把隔壁的茶叶店吃下来,两间打通,再添四张桌子,到那时把“赵氏面馆”的匾额挂上去,就齐全了。赵大块头沿着石板路小心地走,两只大手相互搓着,老茧磨着老茧,他算了一下,再过十来年,这店可就是百年老店了,那时正好儿子也得力了,自己也可以歇歇劲了。脑子里想着赵氏面馆,便不那么冷了。
巷子不长,果然撒泡尿的工夫就到了。他轻轻敲门,良久没人应声。他又压着嗓子说,是我,弄一袋小麦面。打了几十年交道了,熟得不能再熟,他都不需要自我介绍。
过了一会儿,门支开了一道缝,里面推出一袋面粉。
再称两斤糯米面,过冬搓汤圆儿咧。赵大块头说。
里面很快塞出一只鼓鼓的小布袋子,里面人说,不称了,快拎走吧。
赵大块头把钞票塞进去。门很快闩上。里面说,快回吧,赵大块头,你不要命了。
赵大块头扛起面粉袋子往回走。一袋面粉对他来说轻飘飘的,扛在肩上气都不喘。走到巷中,忽然一道手电筒的光从身后射过来。他浑身一激灵,拔腿就跑,他看到自己长长的影子在石板路上左摇右晃。快到家了,耳后“啪”的一声响,刺穿黎明,也刺穿他的大腿。他摔倒在地,面粉袋子滚落一旁。手电筒的光越追越近,照得他睁不开眼,也看不清灯后是谁,只看见灯下寒光闪闪的两杆子刺刀指过来。一把刺刀划破了面粉袋子,一只脚在面粉袋子上踢了两下,面粉像蚊虫似的飞舞起来。
赵大块头捂着腿上的窟窿说,太君,这是面粉,面粉……说着抓了一把捂在嘴里,示意这是可以吃的。
手电筒后面叽里咕噜不知在说什么,只见刺刀又往前挺了一下。赵大块头不敢再做动作了,本能地摊开两只手掌举过头顶,一个劲儿地说饶命,面粉呛得他咳嗽不止。
手电筒照过来,聚光到他手掌心。这么厚的老茧,一定是拿枪的手。
赵大块头只听到叽里咕噜一阵,一句也听不懂,他只知道说饶命。
饶……
话还没说圆全,刺刀穿过胸膛,赵大块头仰面倒下去。他白眼朝上翻的時候看见灯光晃过他家檐头,那面破旗又卷在杆子上了,他手指够了够,再也翻不着了,真该早些更换成木匾的。
一九三七年冬至前夕,赵大块头死在自家门前,当然,他到死也不知道他死于手上的老茧。
琢 磨
揭方晓
寒气一阵紧似一阵,将小城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可逼仄的酱巷深处,李八爷并无压抑之感。他如往常一般,悠然自得地烤着火、呷着茶。手中的茶杯,茶水浅了又续,续了又浅;炉中的炭火,暗了又明,明了又暗。眼看得续水三五回了,添炭七八次了,顾客却仍旧没有上门。
没人上门就没人上门呗,李八爷不急,亦不恼,始终悠然自得。和他一样悠然自得的,还有杯中温润的茶水,还有炉中热烈的炭火,还有这条逼仄的酱巷。
酱巷从来无酱。不管是生抽、老抽这样传统的酱油,还是芝麻酱、甜面酱、豆瓣酱这样层出不穷的鲜美调味品,统统没有。无酱,却有名,在这座小城,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这条小巷的人端的都是“金饭碗”“银钵钵”,家家户户都是金银匠,熔、敲、压、拉、剪、刻、磨,一通神出鬼没的操作,像变戏法般,金灿灿的戒指、沉甸甸的手镯、银闪闪的项圈横空出世,给美丽的女人以精致,给康健的男人以华贵,给悠长的日子以精琢细磨。
而李八爷琢金磨银的手艺承自祖辈,最是精湛。他常骄傲地吹嘘,说自家祖辈曾给王府打过金银器,某某王妃,又或是某某公主,她们戴的头簪、凤冠、项链、戒指、手镯、手链、耳环、耳钉等一众金银饰品,全是自家祖辈精琢细磨出来的呢。这话,半真半假吧。可酱巷一半的金银匠是他的徒弟,另一半是他的晚辈后生,这可是实打实的,不虚,不假。可以说,在这条巷子里,李八爷就是手艺出神入化的神一般的存在,是他人都得仰其鼻息、拾其牙慧讨碗饭吃的神一般的存在。
不过,那是过去了。
现在这条巷子冷清多了。敲打声,淬火声,焊接声,仿佛只是一转身,就突然没入了泥瓦间,没入了堂榭里,再也找不回来。时代在发展,女人们、男人们越来越喜欢成品金银饰,嫌手工打制的金银饰粗陋,不时髦。顺天应地,李八爷的徒弟们、晚辈后生们,一个个都闯出了酱巷,在小城繁华大街、热闹卖场,开了一家又一家金银珠宝店,专卖黄金珠宝成品,生意火得一塌糊涂。
李八爷对此极为不屑:“手艺人,哪能不靠手艺吃饭?”
“手艺人,怎都成了买卖人?”
“手艺人,不能都这样没出息呀!”
李八爷一口一个“手艺人”,显然,他对自己“手艺人”的身份极为看重,觉得这是他一生最闪亮、最完美的标签。
“真不靠手艺吃饭了!”
“手艺人也得养家糊口哇!”
“金银匠卖成品金银饰,怎就没出息?”
徒弟家旺心中不服,经常这样嘀咕着反击。
家旺惦记着师父咧,多次上门要李八爷去他店里“坐堂”,啥事都不用管,只要坐在那里就行。他知道,师父李八爷的名字,就是小城独一无二的金字招牌,是一等一的手艺,是一等一的信誉,是一等一的分量。只要他在,店里生意一定会更加红火。
李八爷直接拒绝:“我是手艺人,不当门神。”
家旺气恼,暗自嘟囔:“都啥时代了,机器化大生产不比你那敲敲打打强?真是老顽固,老固执,老守旧,老执拗,老拘泥,老榆木疙瘩,老秤砣子。”
李八爷耳朵贼精,好似听见,回首怒斥:“说啥嘞?”
家旺一脑门的汗,支支吾吾,撒丫子逃远了。
眼见没客人上门,李八爷索性搬出小天平、拉丝板、拉丝钳、嵌槽、焊枪、印泥、喷枪、坩埚这些“老伙计”,打细微如1克的项链,拉粗壮如120克的手链。棱角分明的金块,经过李八爷一通琢磨,真个是“揉破黄金万点轻”,真个是“蛾儿雪柳黄金缕”,真个是“梅蕊重重何俗甚”。总之,精美绝伦。
面对自己的杰作,李八爷心中无喜,亦无悲。只打量片刻,便将这样巧夺天工的艺术品,付之一炬,熔为红彤彤的汁水。待其冷却成金块,再费尽心机琢磨成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又打量片刻,又付之一炬,又认真琢磨;又打量片刻,又付之一炬,又认真琢磨……循环往复,乐在其中。
邻居罗寿来无聊,一直在旁边看着,笑得跌倒,李八爷亦笑得灿烂。两个七老八十的人,孩子般快乐,哪里还有什么寒气哟。
“休道黄金贵,安乐最值钱。”李八爷心中的唱词,磅礴而出。隔着好几里远的家旺,没来由的,心中倏地一紧。
指 路
阎秀丽
“那就是一道铜墙铁壁,一道无法突破的铜墙铁壁……”老人喃喃地说。
这是一个瘦削而又矮小的老人,满脸沟壑纵横,坐在院子里那把大大的圈椅上,身板挺得笔直,这应该是一位军人标准的坐姿。我尝试着从他眼睛里看到一些什么,可那双眼睛是沉静的,我什么也看不到。
我忽然觉得,那下沉的夕阳不是落向西山,而是落在老人的眼睛里。
作为报社的记者,领导让我去挖掘一些革命老战士的英雄事迹。经多方打听,才找到这位老人,听说他曾经参加过一场著名的阻击战,不过他不愿和任何人提起那段岁月。
谁也没想到,他会住在极普通的筒子楼里。因为我们的到来,特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军装,一顶军帽放在旁边的石桌上,那上面似乎沉淀着老人的峥嵘岁月。这让我不禁肃然起敬,更想从老人的身上挖掘出一些东西。
我提起了那场阻击战,老人沉默了很久,阳光从侧面照着他,让他的脸有一半笼罩在暗影里。
“您能亲历那场阻击战,一定有很多记忆深刻的人和事。”我说。
老人的身子瑟瑟地抖动一下,腰板瞬间佝偻起来,那宽大的圈椅,竟然让他显得有些羸弱不堪。
“那是一道无法突破的铜墙铁壁……”老人喃喃地说着,“我的耳边都是爆炸的声音,鼻子里全是烧焦的味道……”
这是真正经过战火考验的老英雄!我身子正了正,手中的笔在采访本上飞速地记录着。
“当我醒来的时候,周围很静,眼前一片漆黑,我以為我死了……还好我的腿还能动……
“我很害怕,怎么只剩下我自己?都死了吗?我不敢喊,但是我能感觉到风刮过我的脸……一股血腥味,是我的血,从我的脸上一直流,流到我的嘴里。”老人的身体在抖,声音也跟着抖起来,“我趴在地上,能闻到土里也有血腥的味道,我不知道是谁的血。但是我知道,我还没死,只是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我想活着,我不想死,香兰还等我回去娶她……”老人在我的安抚下平静下来,喃喃地说着,“她很漂亮,两根大辫子在身后甩来甩去……”
老人的脸上似乎泛起一抹红晕。
“我又听到了枪炮声,整个大地都在震动,我甚至听到很多人的呐喊声。”老人挪动一下身子,靠在椅背上,好像很疲惫,“我听到有人喊‘给我上’,我很高兴,我得救了,因为我知道这是谁喊的话。
“我大声地喊着,嗓子都哑了,除了爆炸声和喊杀声,还有那越来越浓烈的烧焦的味道……”老人想睁大双眼,那里似乎藏着深深的恐惧,“那天是阴天,我能感觉到空气里全是湿漉漉的,就连喊杀声也是湿漉漉的、黏黏的……我又听到有人喊‘跟我上’,随即……一发炮弹在我身旁爆炸……
“当我醒来的时候,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只有那种难闻的味道。”老人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像是地狱的味道……”
“没有人救您回去?”我停下笔,惊愕地看着老人。
“我以为我会死在战场上……我却碰到了他……他向我爬来,他的声音很虚弱,问我的眼睛是不是看不到了……我忍不住哭了,我想,我再也看不到我的香兰了……”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我问他是谁,他告诉了我……他的两条腿都负了重伤,不能走路了……他说他想活着,要不然他的狗剩子就没爹了。”
我的鼻头一酸,看着老人的眼睛,我以为那里也会有泪水流出来,可是什么也没有,依旧很沉静。
“我不得不跟他走,因为我也想活着。我背着他,他给我指路……他的两条腿晃荡着,一下一下地敲打着我的大腿。”老人的脸上闪现出一丝儿捉摸不透的神情,继续说道,“他没有叫,甚至连呻吟的声音都没有,我隐隐感觉到他竟然有些兴奋。他说这里就是一道铜墙铁壁,没有谁能够突破……后来,他哭了,我没想到他也会哭,他的哭声太难听了,说整整一个连的战友就剩下他,连长是第一个牺牲的……”
我不由得站了起来,我无法想象一个眼睛受伤看不见路的人,背着一个负了重伤的战士走下战场的壮烈。
“我让他闭嘴,他身上的血一直在流……我真想扔下他……他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胜利吗?因为我们军队的口号是‘跟我上’,而他们,只会喊‘给我上’……”老人的身体抖得更加厉害,声音也跟着抖得变了调,“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还是不停地说……”
“那你扔下他了?”我问。
“我没有,虽然我很想扔下他,但扔下他我寸步难行……我知道他说的都是对的,我的眼睛受伤看不见了,但是我的心不瞎……”老人从圈椅上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说道。
我看到他的眼睛有眼泪流出来,“我想让他活下去,可是他死了……我顺着他指给我的路往前摸索着爬,因为他说过,只有走这条路才是正确的……后来,军医治好了我的眼睛,我加入了他所在的军队。”
“啊?那您是?”
“那之前,我是‘国军’士兵……”老人低下头,声音轻得像风。
空气中揉搓出干燥的摩擦声,是老人拿起桌上的军帽,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那鲜红的五角星,在阳光下变得更加鲜红。
老人的眼睛里,被西落的阳光印满了温暖:“不过,他给我指了一条最光明的路。”
紫砂壶
贾鸿彬
阿翁阿婆每日总要上街逛逛。退休十几年了,他们一直这样。
小城不大,有新旧两个城区。阿翁阿婆住旧城,三个儿子成家后都住新城。不逢周末,他们是很少回来的。
街这几年变化快,新闻与新色彩日日皆有。阿翁阿婆置身其中,听听看看聊聊问问,时光就生出许多乐趣,日子过得闲适而充实。
“不是盲盒”是不久前才在老城开始销售的,刚开始极少有人问津。不过亲眼看见有人用十块钱买个彩色方盒,当着众人面拆开,找出其中的硬纸片刮开涂层,竟刮出一辆闪闪放光的电动QQ汽车,带着大红花在隆隆的电子炮声中开走,聚拢的人就多了。阿翁阿婆对这样的热闹场面从不愿放过,好几日,他们都兴致盎然地看。
拆開“不是盲盒”的人极少刮到电动QQ汽车之类的大商品,电饭锅、微波炉间而有之,大多刮到的是牙膏香皂洗衣粉之类。好在一只“不是盲盒”只要十块钱,倒也没有多少人介意,最多是叹口气:“手气不太好!”
阿翁阿婆每日回到家都很兴奋。
阿翁说:“手气好去买还是顶值得的。”
阿婆说:“手气不好也能刮到牙膏香皂洗衣粉,都是用得着的。”
阿翁又说:“反正就十块钱。”
阿婆又说:“不要说十块钱,现在就是二十块钱,对我们也无所谓。”
于是,他们从家中拿了十块钱。
阿翁说:“我来买。”
阿婆说:“一辈子没赚过大钱,你那手行?”
于是,他们又回家取了十块钱。
两只“不是盲盒”是一起买的。阿翁在前,阿婆在后,他们在货架前花花绿绿、层层叠叠的方盒间选来选去,阿翁终于选定了一只,阿婆终于也选定了一只。
阿翁先拆开,拿出硬纸片刮开:“紫砂壶!”
阿婆后拆开,拿出硬纸片刮开:“紫砂壶!”
销售员说:“恭喜二老了。你们刮到的是制壶大师时大杉的名壶。古有时大彬,今有时大杉,一只壶要一万块,算你们运气。这是岁寒三友系列,一共只有三只,你们刮到的是竹壶和梅壶。另外还有一只松壶,不知藏在哪里。”两只紫砂壶都是装在黄色锦缎匣子里的,捧在胸前,金灿灿的。
星期六最先回来的是老三,桌上两只紫砂壶的来历他很快明白。
“爸,妈,你们反正也用不着两个,我拿一个去。”他挑走了梅壶。
老三在门口遇见了老二,他们两人是双胞胎,很像。在孕育他们前,他们的大哥已经三岁。做医生的阿婆很羞涩,跟做教师的阿翁说还想要一个女儿,结果阿翁一下又给了她两个儿子。两个小家伙出生时不足月,小老鼠似的,阿婆的同事把他们放在保温箱里,呵护半个多月才拿出来让阿婆喂奶。所以,这对兄弟后来一直就受阿翁阿婆别样疼爱,生怕他们有闪失。
老二也很快明白了紫砂壶的来历。
“爸,妈,这紫砂壶是艺术品,随便用就是暴殄天物了。我收藏了!”他拿走了竹壶。
到了星期天,老大知道阿翁阿婆曾经刮到过两只紫砂壶,可已经晚了。大媳妇到老二老三家一遍又一遍抚摸紫砂壶,爱却只能释手。接下来,她天天从新城到旧城,和阿翁阿婆谈艺术。“真正的艺术品哟,我竟然闻到了梅花的清香!”“什么叫灵动呢?竹壶就叫灵动,没有风,那竹叶也沙沙响啊!”
阿翁说:“你别说了。我和你妈手气都好。我们再去摸,保证给你家也摸一只。”
阿翁阿婆又取二十块钱,阿翁在前,阿婆在后,他们在货架前花花绿绿、层层叠叠的方盒间选来选去,阿翁终于选定了一只,阿婆终于也选定了一只。
阿翁先拆开,拿出硬纸片刮开:“牙膏!”
阿婆后拆开,拿出硬纸片刮开:“香皂!”
后来他们又先后说,“香皂。”“牙膏。”“洗衣粉。”“洗手液。”
大媳妇又天天来谈艺术了。
望着成堆的香皂等日用品,阿翁在一天夜里说:“要不然,给老大家一万块钱吧。”
阿婆说:“给就给吧!”
阿翁和阿婆来到街上,买了一只黄色锦盒,将一万元红包放进其中。大媳妇见了,说:“艺术品可遇不可求。爸,妈,我不强求,你们就不要为难了。”说着拿着锦盒走了。
到了晚上,老二媳妇捧着竹壶,老三媳妇捧着梅壶,两人一起回来了。
老二媳妇说:“爸、妈,这紫砂壶让你们为难了。真是对不住!我们两个商量了,忍痛割爱,还是由你们自己收藏!”
老三媳妇说:“爸、妈,竹壶、梅壶完璧归赵。我们还是和大嫂一样吧,不能让你们为难。”
两个媳妇说完就走了。阿翁拿出一罐太平猴魁,这是他的一个学生春天时寄给他的,他一直没有舍得喝。“暴殄一回天物吧!”阿婆把竹壶洗了。阿翁说:“梅壶也洗掉吧。”阿婆把梅壶也洗了。
阿翁在竹壶里放上一撮猴魁,又在梅壶里放上一撮猴魁,阿婆把新开的水倒进两只壶。
时大杉是谁,阿翁不清楚,阿婆更不清楚,但他制的壶应该不错,很快茶香就从壶嘴飘出来了。阿翁捧着竹壶,阿婆捧着梅壶,两人没有用茶杯,各自对着壶嘴,慢慢啜。
“到底是名壶,喝茶就是不一样!”阿翁说。
“要不怎么说是时大杉壶呢。以后,我就用这个壶喝茶。”
一人啜完一壶茶,躺到床上,却都睡不着。
阿翁说:“明天取钱,给老二家一万。”
阿婆说:“取两万,也给老三家一万。反正迟早都是他们的。”
阿翁叹息一声,“也好。不然我们怎会用上这么好的紫砂壶。”
阿婆笑出了声,“幸亏松壶我们没有刮到。”
责任编辑 张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