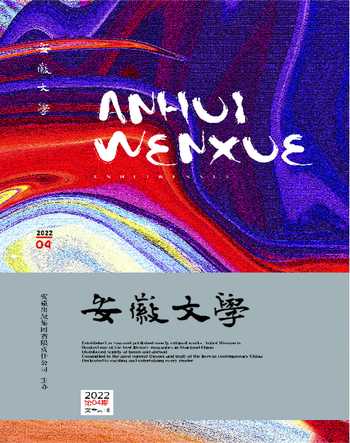黛妹
明月
一
黛妹高小毕业了,毕业也就下学了,本想往前再走一步,无奈一把手父亲说,还上个啥呀,能认识自家姓名和工分不就行了。
一把手赴朝参战时,被美国鬼子的炮弹借去半条胳膊,诨号一把手,是功臣,被生产队养了起来,属于半养。不能负重,队长就派一把手去看青,每天记十分。那时,一个分值八分钱,八毛钱够买一支铜锅铝嘴旱烟袋,两只牛窑夜壶,五斤粗盐,外搭半封火柴。
立冬后,小麦全部卧地,不用再去看青了,队长又派一把手赶辆牛车,到二百里外的怀远茨淮工地拾粪馒头,一天同样记十分。于是,突击准备了三张秫秸箔,十二根木桩,三只尿桶,一把铁锹,两把平头锨,一对粪箕子,以及他和女儿黛妹的一应生活用品。自驾牛车,带上黛妹,一路鞭花,吱吱扭扭远去了。
黛妹豆蔻年华,丢在家里不放心,带她去工地长见识。在路上晃荡了两天半,才顺利到达工地。晚间,一把手跟民工挤大铺,黛妹找厨娘打通腿。
次日,一把手围了三个露天茅厕,一个留给大队指挥部,一个给生产队,再一个专供喜欢屙跑屎的滑蛋。一把手负责另外俩坑,黛妹负责看野坑。
队长背着手走过来,跟黛妹说,如果你看的这只野坑,能拾到与另外俩坑同样多的粪馒头,就给你每天记半个劳力分。
黛妹就问父亲,给半个劳力分是多,还是少?
一把手说,够买一把半老烟叶了,不少!
瓦主任为方便民工,让黛妹身兼二职,以集体的名义到附近集镇进了一批针线、手套、毛巾、棉帽、香煙、火柴、蛤蜊油,臭肥皂、草纸等日用品,在野坑附近摆个日杂摊,官称代销点。
瓦主任交代队长说,给黛妹再加三分,凑够一个女劳力分。
黛妹为了招揽顾客,便把招牌“大”在胸前。有人光顾,就笑脸相迎招呼客人;没人时,就扯着嗓门瞎唱。黛妹天生一副好嗓子,喜欢唱歌,有革命歌曲,也有样板戏选段,间杂民间小调。黛妹长相甜,歌声也甜,留一条油亮亮的大辫子,走一步三晃悠,扮演李铁梅不用化装。这一唱,便勾来不少屙跑屎的滑蛋,真屙或假屙,真买或假买,远远地跑过来,只为剜她几眼,或听她一曲美妙的歌声。一天下来,一把手把三个粪坑挖出来堆成两丘粪馒头,估估堆儿,黛妹的收获居然与他俩坑的粪馒头基本持平,就到队长那里为她请功。
队长一高兴,又给黛妹长两分。
这样一来,黛妹就与父亲的报酬拉平了。
顾此失彼,黛妹把邻队的滑蛋吸引过来屙跑屎,惹恼了相邻大队的拾粪老头,就找到队长告黑状,说黛妹这人不地道,抢了他的粪馒头。
队长歪头笑笑说,黛妹一个小姑娘,咋会去抢你的粪馒头呢?
她用唱歌抢。
队长又笑笑,黛妹天生会唱歌,我管民工的吃喝拉撒,却无权管她别唱歌呀。
拾粪老头歪头想想也是,气得哼了一声,扭头走了。夜里,黛妹的粪馒头不知被谁偷咬一口。那年头化肥金贵,人们便向家畜家禽的腚眼儿掏粮食。一把手背着手,歪着头围着粪馒头转了一圈,毛估一下,至少丢两担,心疼得直吸溜嘴。晚饭后,借马灯照明,在距离粪馒头十米开外的地方挖个卧牛坑,坑底填满麦草,伪装起来,开始蹲坑。连蹲两天没见动静,到了第四天鸡鸣三更时,一个小黑点爬进他的视界,黑乎乎一大团,拉进一看,头戴大耳朵军帽,帽舌儿耷拉着,挡住半张脸,上穿泥青布大襟袄,腰际的大带子爬过膝盖,分不清是啥人。赶巧,这刻儿嗓子眼儿痒痒,遂捏一撮泥土送进嘴里压一压。那黑点东张西望,瞻前顾后,蹑手蹑脚猫近粪馒头,刚装好一担,正想抬腿走,一把手便悄然飘到他腚后。
一把手当过侦察兵,拳脚不俗,趁其不备,一别子把他放倒,上前拿住,扭送到大队指挥部。刚巧瓦主任带着宣传队来工地进行慰问演出,遂扭亮马灯,那偷粪贼立马原形毕露,原来是相邻大队的拾粪老头。
一把手问瓦主任,打算咋办他?
瓦主任说,夜不行更事,先把他绳起来,天明才说。
冻坏了咋办?
把他关进厨房钻草窝。
天刚模糊亮,一把手就摇响指挥部的门环,问瓦主任,到底咋办他?
主任说,我来联系一下。
当下便拧通了相邻大队指挥部的电话,接电话的是邱主任,彼此认识,瓦主任就把拾粪老头的偷盗行为上纲上线说了。
邱主任说,拔得有点高了,一个老天爷管着,都不外,看着办吧。
瓦主任说,看着办是咋办?
邱主任还是那句话,都不外,看着办吧。
瓦主任就明确指出三条路:一、重罚;二、游工地;三、开批斗会。
邱主任沉吟片刻儿,回复道,是本门堂叔,就重罚吧。
罚四担优质粪馒头。
邱主任一愣怔,这粪馒头咋分优劣呀?
不掺土兑假。
瓦主任就问一把手,叔,对这个处理结果可满意?
一把手说,再加一条,让他白纸黑字咬个牙印。
瓦主任放走了拾粪老头。翌日夜半时分,一把手的粪馒头奇迹般复原了,尚余两担。
二
瓦主任把黛妹招呼到指挥部,他要亲自验证一下她的唱功到底如何。担心吃不准,又临时叫上宣传队的头把弦王瞎子,二把弦二哥和台柱子南雪,四人一同见证,现点几曲让黛妹清唱。黛妹不怯场,往人前一站,大辫子一甩,声情并茂一一唱来。
瓦主任问王瞎子,师傅,您看这水平,能不能进宣传队呀?
王瞎子翻翻眼说,再长二年骨头吧。
黛妹灵机一动,回头请了一只牛窑香炉,三炷香,头顶香炉,一路青烟袅袅拜倒在王瞎子面前,请求学吃开口饭。王瞎子把身子摆在一把太师椅上,晃几晃端正一下,抱着二胡,翻翻左眼,大概一眼黛妹,翻翻右眼,又大概一眼黛妹,哑默了片刻儿,再度大概一眼说,芳龄几许了?
黛妹一愣神,几许是啥意思呀?眉头一皱瞎蒙道,俺软软乎乎十五了。
啥文凭?
高小毕业。
为啥不再往上念了?
爹说,女孩家是外人,能认识自家姓名和工分就行了。
戏子在旧社会属于下九流,是贱民。
俺知道,眼下是新社会。
爱啥乐器?
洞箫。
王瞎子再次翻翻眼说,老话讲,十年的笛子百年的箫,一把二胡拉断腰。这份苦你能受得了吗?
俺愿把这辈子光阴都搭进去。
搭上熬死三头牛的工夫,够了,那就把香炉留下吧。
黛妹跟父亲商量,拜师礼拿啥好。商量来商量去,决定给王瞎子置办一副墨镜,一顶马虎帽,一套泥青布便装,一双千层底黑直贡呢窄脸布鞋。一包装了,掂掂分量,去见王瞎子。
王瞎子说,见面礼就免了,抽空陪我爬爬昙城的古城墙吧。
临走,送黛妹一支前五后一的六孔洞箫。
黛妹说,师傅,给俺示范一曲吧。
王瞎子遂气沉丹田,吹了一曲青海花儿《下四川》。
民工二十天一轮休,每轮中间宣传队过来一次,蹲一周,一天演一场。黛妹就天天缠着王瞎子给她校正音准和吐字。黛妹字正腔圆,如珠落玉盘。瓦主任便夸她是个人才,前途远大。
轮休期间,黛妹天天留心天气预报,瞅准连续两天没有雨,就跟父亲商量,俺想陪师傅去一趟昙城,爬爬古城墙,了却他的一桩心愿。从南村到昙城三十六华里,二人坐公共汽车很快就到昙城。王瞎子喜欢昙城的石板路和条石巷,说是用明杖能敲出唐诗宋词。住下后,先敲大街,再杖小巷。不巧,黄昏时多云转阴,云层铺得比古城墙还厚,压得小南山矮下半头。一群暮鸦围着塔尖打踅儿,迟迟不肯归林……东北风号了一夜,临近天明时,楚楚谡谡降下一场雪,雪花儿如同棉絮一般大,飘个不停。
黛妹问王瞎子,师傅,这天气,咋爬古城墙啊?
王瞎子大概一眼满窗的白鹅毛,说,越是雪天越能找到感觉。黛妹不明白,师傅为啥偏爱选在大雪天找感觉呀。
王瞎子三分通路,看世界一派浑沌,黛妹扯着王瞎子从北门一级一级爬上古城墙,城墙下是脉小南河,河那边是绵亘千里的小南山,山上有梅花。二人沿着城垛走,王瞎子大一杖小一杖,杖杖点在白梅上。王瞎子大概一眼小南山说,黛妹,师傅考考你,是南山高,还是城墙高?
黛妹眨巴眨巴眼,说,站在城墙上看南山,是城墙高;若是站在南山顶上看城墙,是南山高。
王瞎子说,还不憨呢。
小南山苍黛一抹,浑浑茫茫,一群远征的乌鸦驮着棉絮大的雪花儿,累得呜哇怪叫。东北风鬼哭狼嚎,比锻打的菜刀还老,一刀一刀地割。
黛妹说,师傅,咱到前边的瓮城避一避吧。
王瞎子说,到了瓮城,我教你吹一曲《梅花三弄》。
黛妹说,师傅,不如先拉一遍我听听。
到了瓮城,王瞎子遂操起二胡,边拉边哼……
黛妹目啄南山,思接万里,沉浸在《梅花三弄》婉约缠绵的曲调里。
一曲终了,王瞎子突然冒出一句,黛妹,开口饭不好吃呀,若想打退堂鼓,还来得及。
黛妹说,师傅,俺命里喜欢它。
东北风一刀比一刀割得疼,棉絮大的雪花儿这一朵咬着那一朵,一咬一嘴血,南山的朱砂梅开了。
这时,一串低沉的哼哧声徐徐攀上瓮城,爬进王瞎子耳朵里。王瞎子对哼哧声特别敏感,猛地一愣,黛妹,这是骆驼的叫声,快下去找找在哪里。
不禁疑惑,这大雪天,昙城咋会有骆驼呢?
骆驼的一声哼哧,蓦然勾起王瞎子三十年前的一段辛酸往事。
王瞎子是甘肃人,天生半瞎,十八岁那年,心中装着梦中的远山,背一把胡琴,一支洞箫,牵一峰骆驼,一路跋涉寻到内地,不料那骆驼病死途中,他也大病一场,好不容易摸到菊镇,被一个老大娘救下,从此在这边落地生根。
黛妹在瓮城门洞里发现一峰卧驼,正昂首哼哧;一个怀抱冬不拉的老人,病得奄奄一息。王瞎子把他大概几眼,从面相、衣着、神态看,不像是个哈萨克人,断定是甘肃老乡。
老人终究没有扛过一场大雪。翌日黄昏,南山坡坟起一丘雪包,坟头插枝朱砂梅。
王瞎子说,苦寒之地不养艺人,老乡走了,咱也回吧。
老人撇下的骆驼是峰雌驼,黛妹管它叫阿甘。当王瞎子骑着阿甘,黛妹牵着缰绳,一路披着一身雪花儿回到南村时,弄出了不大不小的动静。村人没见过这等会吃草的庞然大物,纷纷跑来瞧稀罕,有那泼皮顽童,团团围着阿甘伸头缩脑,想摸却又不敢摸,久久不肯散去。
王瞎子郑重提醒说,阿甘欺生,小心咬人!
瓦主任闻讯赶来,他虽然见过大世面,但也同样没见过骆驼,顶着光头小孙子走上前,也想摸摸。
王瞎子再次提醒,小心咬人!
瓦主任眨巴眨巴眼,弄不清阿甘到底咬不咬人,怕吓着小孙子,便识趣地退到人后,依然高人一头。
晚炊一罢,队长披着油布雨衣,托着旱烟袋,一路青烟袅袅摸到一把手家,掏心掏肺地说,生产队愿用两千斤黄豆换你的阿甘。
一把手托着烟袋,踌躇满志,哑默片刻儿说,你去问问黛妹吧。
黛妹说,瓦主任都骑上大链盒自行车了,俺家买不起,就权当它是一辆大链盒了,不换!
隊长吧嗒吧嗒嘴,背着手,颇为失望地走进风雪里。
三
轮休的日子很快过去。太平车、独轮车和板车,七个毂辘一起转,把养足精神的民工一路咿呀拉向二百里外的茨淮工地。一把手和黛妹不想给生产队添麻烦,决定骑着阿甘去。黛妹让父亲骑,她步行;走了一段时间,一把手怕累着女儿,便让黛妹骑。
黛妹心疼父亲说,走不大脚。
一条油亮亮的大辫子左摆一下,右摆一下,大步流星随后跟。
蓝天高远,征鸟伴飞;乡原千里,路通天涯。
队长戴顶大耳朵破军帽,帽舌一半连着,一半耷拉着,遮住半只眼,倒坐在太平车栏板架上,一只脚放在车厢里,另一只搭在外边,不停地晃荡着,一手夹着旱烟卷儿,一手拍打着内栏板,瞅着一把手一副悠哉游哉的样子,颇为羡慕。
叔哇,能不能也让侄儿潇洒几步哇?
一把手品他一眼,强调说,这家伙欺生,咬人!
队长弄不清这家伙到底是不是真咬人,颇为遗憾地吧嗒吧嗒嘴。沉默了半袋烟工夫,依旧不死心,叔哇,咬死了噎熊(方言,意为拉倒),俺也得体验一把。
一把手再次强调说,咬人!
队长这才勉强死了心,头摇着,依旧不停地吧嗒嘴。
车队咿呀了两天半时间,终于晃悠到淮远茨淮工地。一把手在两个茅厕中间栽根木桩,把阿甘拴上去。
阿甘无疑是道风景。好奇的民工便趁工休时间纷纷跑过来瞅几眼,有屎的就把屎留下,有尿的就把尿留下,没屎也没尿的就把脚步丢下,顺便剜几眼黛妹,再剜一眼阿甘,这才心满意足地走开。如此一来,一把手每天的收获便比先前明显多出三成。队长一高兴,把父女俩的工分一下提到十二分,与一线民工同工同酬。
周边几个大队的拾粪老头怨声一片,骂一把手父女俩不择手段。反应最大的当数相邻大队的邱主任,晚炊时,揣一瓶濉溪大曲,一包油炸花生米,油罐子脸笑成一朵向日葵,一路左高右低摸过来,跟瓦主任大一杯小一盏对吹了半夜,临走道出此行目的,想把黛妹挖走,说是大队宣传队缺个能镇场子的角儿。
瓦主任说,黛妹是瓦庄大队的宝贝,正跟王瞎子学戏呢。
邱主任误以为他拿糖,就慷慨许诺说,包吃包住,月工资四十五元,抵上一个国家干部的待遇了,请您帮我神通一下。
瓦主任说,不急,再过几天,王瞎子就来工地演出了,先问问他再说吧。
一周后,宣传队果真来了。
王瞎子听闻瓦主任说到邱主任要挖走黛妹这事儿,翻翻眼说,黛妹还没学上路呢,再长二年骨头吧。
次日,《茨淮战报》的记者下点采访,无意间发现黛妹这个新闻眼,让她摆拍两张照片,一帧是生活照,一帧是骑着阿甘的放歌照,配上文字说明,在《茨淮战报》头条隆重推出。一夜之间,黛妹成为工地名人,前来一睹芳容的年轻民工络绎不绝,黛妹的日杂摊收入和粪馒头日增量明显翻番。
瓦主任说,茨淮新河把黛妹捧红了!
邱主任的一颗求才心越发痒痒不止,再次请托瓦主任,一瓶濉溪大曲吹亮底,报出两大愿望:一愿跟瓦主任结为儿女亲家;二愿出重金挖走黛妹。
瓦主任说,儿子在部队服役,要求进步,有话在先,五年内不提亲。
邱主任吧嗒吧嗒嘴,顿了片刻儿说,那,聘请黛妹总该没问题吧?
这个,王瞎子不吐口,我也不便硬当家呀。
邱主任撇撇嘴,嘁了一声,说,瞧你这个主任当得够稀松的,在我治下的一亩三分地,随便跺跺脚,那就是三级地震,想办啥事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
邱主任再一再二地高薪挖黛妹,提醒了瓦主任,与其被别人挖走,倒不如及早把她招进宣传队,为我所用。就把自己的想法跟王瞎子说了,王瞎子还是那句话,再长二年骨头吧。
黛妹心情愉快,就唱得越发卖力,唱累了就改吹洞箫。确切些说,黛妹的吹功远没唱功好,主要表现在气力跟不上,声线飘忽不定,行话叫托不稳。于是,王瞎子就教她练习吹铁豌豆,夯实基本功。黛妹日日抱着一只黑陶碗,碗底卧粒铁豌豆,噙着竹筒频频发功。不到仨月工夫,便把铁豌豆吹得瞎驴拉磨,黑转圈儿了。
王瞎子说,快上路了,继续用功,三年后,我听你吹一曲《梅花三弄》,那时才决定你能否进宣传队。
四
隆冬多雾,一觉醒来,一把手发现阿甘不知啥时不见了,一时吓傻了,不知如何是好,蹲在一丘粪馒头上,一袋接一袋地吧嗒旱烟袋。
天被冻僵了,溜河风沉得走不动,青烟也不再袅袅。
一把手三袋烟吧嗒完,这才愣过神来,一拍大腿,报警去。
边走边琢磨,是跑了,还是被盗了呢?
黛妹听说阿甘丢了,一下瘫在床上,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好一会儿才爬起来,只要一闭眼,面前便会闪现一幅画面,阿甘御风而起,驾一朵白云,悠向远方……
瓦主任遂给派出所拧去一个电话,派出所敌情观念重,初步定性为阶级敌人搞破坏。除留下一人值班外,全体出警。
一把手和黛妹也作了具体分工,一把手留在原地找,黛妹四处盲找。黛妹乘车找到周边的涡阳、阜阳、蒙城、怀远、蚌埠、凤台、淮南、寿县,均无所获,最后在昙城南山坡找到那峰跑丢的阿甘。阿甘卧在老人坟怀里,旁边伴卧一峰高大雄驼。
南山坡的蜡梅花儿笑得一团糟。
一时恍然大悟,阿甘想做妈妈了。
阿甘把头举上天,眼泪吧喳,发出一串低沉的哼哧声。黛妹抱着它的脖子,流下一串热泪。当下,采来一枝蜡梅花儿敬献老人坟前,然后深深三鞠躬。没有急着返回,骑着阿甘绕着古城墙转悠一圈,缓一下情绪,这才踏上回程的路。回头看看,那峰雄驼一直不远不近地随后跟着,轰也轰不走,这是谁家的驼呢?是不慎走失的家驼,还是流浪驼?
不禁纳闷,这皖西北平原哪来恁些流浪驼呀?
黛妹担心失主来找,决定不走了,又返回城里住了一宿,依然不见失主來找,就写了几张认领启事,留下详细地址,贴在四座城门旁。黛妹惦记着粪馒头,就不想再等了,次日天刚模糊亮就动身启程。阿甘闹情绪,不想迈腿,黛妹会意,款款来到老人坟前绕了一圈儿,折枝蜡梅花儿绑在它的前腿上,这才走出城门,回头看看,那峰雄驼依旧不远不近地随后跟着。就想,先带回工地再说吧,给它取名阿铎。
黛妹找回阿甘,又顺带拐来一峰流浪驼,再次引起轰动。队长第一时间赶来,弓着腰跟一把手商量,愿意托养阿铎,使役权归生产队,所有权归一把手。
一拍即合。
阿铎体型大,耐力强,拉单套步犁每天可耕五亩地,双套双铧犁每天可耕七亩地。队长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一把手让阿甘和阿铎各把一个茅厕,他负责来回跑,收拾粪馒头。这样一来,粪馒头的数量明显增多,队长派来拉粪馒头的太平车就由原来六天一次,改为四天一次。
二十天的轮休时间很快又到了,黛妹不想丢下日杂摊,每日多掙三分虽是蝇头小利,但吃着无味咂着香,就怂恿父亲出面跟队长通融一下,愿意义务照看代销点。
队长不表态,蹲在地上用烟锅不停地划圈儿,划着划着忽地站起说,叔哇,老话讲,朝廷佬不使白人,留下可以,不过,得把野坑围在百米开外的地方,不然,别人会有意见,所得粪馒头一半归公,一半归己,不记工分,队里管吃管住,您看咋样?
一把手说,够意思。
这是多么大的照顾哇!一把手为了表示谢意,决定给队长送两丘粪馒头。粪馒头是一等优质肥,可以换工分,工分就是一抖哗哗响的“工农兵”啊!特地请人定制一对火荆驮篮,一边装一丘粪馒头,约有二百来斤。从凌晨两点上路,一路晃荡,二百里路风和尘,荒鸡刚叫两遍便平平安安晃到家。卸下粪馒头,吃块剩馍垫一下,揣半把老烟叶,几枚红辣椒,又连夜往回赶。
队长得知后批评一把手,老革命呀,在部队大熔炉里锻炼了多年,就整出这觉悟?您这不是故意让侄儿犯错误吗?下不为例呀。
说归说,做归做,一把手依然隔三差五送一回。阿铎记路,一个冬天跑下来,不用带路,也能摸到队长家。
黛妹认为,是开挖茨淮新河让阿甘和阿铎有了用武之地,同时也成就了她。在家时,只要一开口,左邻右舍就撇大了嘴,诟辱她是鸡嘎鹅叫;如今上了工地就不一样了,可以放开嗓门唱,还被一众民工当个“人物”捧着。
宣传队来工地慰问演出,每次都是蹲一周,黛妹就利用这段时间,跟王瞎子学唱花儿。王瞎子夸她膛音厚,音域宽,声线拖得长,走调儿稳,夹杂几分烟嗓,唱花儿别具韵味。
黛妹仰慕吃开口饭的梨园子弟,可以天天把烟火日子唱着过;更艳羡像师傅这样的流浪艺人,背一把胡琴,一支洞箫,就可走遍全国,见识大世面。有了这动力,黛妹唱得越发卖力,希望将来有一天也能走出南村,闯出一片新天地。
宣传队每天夜晚都演出,黛妹就让父亲把活动茅厕搬到距离舞台十丈开外的地方,将两盏马灯分别吊在拴阿甘和阿铎的两根木桩上,一峰看一个茅厕,黛妹照顾日杂摊,一把手负责收拾粪馒头。有那心花腿野的年轻民工并不把心思完全放在观看演出上,而是鬼鬼祟祟猫过来,借买日杂为名跟黛妹套近乎,这其中便包括邱主任的二公子,骚眉辣眼,撺掇她唱几曲青海花儿解解闷儿。
青海花儿多与爱情有关,年轻人爱听,宣传队不唱与爱情有关的歌曲,也不演与爱情有关的表演唱,而是主打革命歌曲,兼及样板戏经典选段等。年轻人生活枯燥,劳累了一天,很想听黛妹唱一曲花儿解解闷儿,从中品味一下爱情的甜美滋味,做个好梦。这样一来,就无形中形成一个小中心。二十岁左右的一帮小伙儿多是围着黛妹这个小中心,而四十岁左右的一众中年人多是围着舞台大中心。明察秋毫的瓦主任立马警惕起来,颇不高兴,黛妹这孩子太没大没小了,便勒令她立马把嘴扎住。
黛妹愣怔片刻,说,俺带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为啥?
自己琢磨去!瓦主任手一背,走了。
次日,相邻大队为了赶进度,决定挑灯夜战。邱主任揣着两包“春秋”烟,笑眯嘻嘻地摸过来跟瓦主任商量,想把黛妹请过去爆炸精神原子弹,并许诺五元包夜。
瓦主任说,再加一元,凑够六六大顺。
成交。
没搭舞台,把平台清出来一片平地,摆放两张八仙桌,权作大舞台,请黛妹站在大舞台上自由放歌。
邱主任说,荤素不限,只要能鼓舞士气就行。
黛妹说,俺只唱素拼。
舞台背后栽两根大木桩,一根挂盏汽灯,挨着汽灯一排溜儿插八块标语牌,白底红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每块牌子吊一盏马灯,站一面红旗。夜晚的工地,虽不能像白天那样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但也同样号子声声,热火朝天。
黛妹是南雪的堂妹,南雪不放心,就把二哥使过来义务助唱。
黛妹登台首秀,改头换面,收拾成一个活脱脱的李铁梅,面对黑鸦鸦的夜战工地,心里没底,不免忐忑,就请教二哥唱啥好?
二哥壮劲说,锅底下扒红芋,拣熟的尅(方言,即吃)。
二哥拉,黛妹唱,赶到对唱选段,二哥就边拉边唱。歌声轻一鞭重一鞭地抽,把夜战的民工抽得如同打了鸡血,个个生龙活虎,号子声声。苦战到子夜,民工累得嗷嗷叫,都咋呼扛不住了。邱主任便宣布卷旗收兵,吃加班饭。猪肉炖粉条,杂面馒头,随便吃。黛妹和二哥随邱主任在大队部吃小伙,小伙有濉溪大曲,有净面馒头,还有两荤两素四碟下酒菜。黛妹不胜酒力,两个花朵厨娘一边一个文武夹杂地劝,第一轮就把她轻轻松松放倒了,邱主任遂使个眼色,两个厨娘会意,把黛妹架到厨房醒酒。二哥是一盅歪,草草吃了几口,感觉不对劲儿,就到厨房看黛妹,不在,但见两个厨娘正躲在屋角吃吃偷笑。二哥心头忽地一紧,不好!遂四处寻找,很快就在坝坡阴影里找到黛妹,邱主任的二公子正一句一个尕妹子给黛妹送温暖,二哥上前一步把她抢了出来,拉着就跑,丢了句,不是玩意儿!
五
天赶地催,阿甘怀孕了。经过十三个月的孕育,于次年暮春产下一对双胞胎,一雌一雄,雌的取名兰花花,雄的取名信天游。刚满月,队长就跑来预订托养,待成年后配成一犋。
当黛妹一条油亮亮的大辫子爬过肩头,溜过小蛮腰,触摸到腚垂时,烟熏火燎的三年一晃过去了,芳龄刚好十八。王瞎子就把瓦主任约来,一起试听黛妹吹奏《梅花三弄》。一曲终了,王瞎子征求瓦主任的意见,主任,您看这水平咋样?
瓦主任对样板戏情有独钟,提议说,再试听一段样板戏吧。
黛妹默想片刻儿,唱啥能拿人呢?挑来挑去,攒劲儿唱了一段女生版的《打虎上山》。
王瞎子再次征求瓦主任的意见,主任,您看咋样?
瓦主任一左一右歪歪头说,有板有眼,透着威势,够味儿,昙城文工团的台柱子也不过如此!您是师傅,嘴大压腮,您说咋样就咋样。
王瞎子正正腰板,翻翻眼,大概一眼黛妹說,我看可以进宣传队了。
黛妹替下B角,每天记十分。每到茨淮工地慰问演出,南雪就托故身体不爽,把她推到前台唱主角,与南雪同工同酬,记十二分。黛妹是个人来疯,极尽所能,着实风光了一把。瓦庄大队年年都能捧回一块“治淮先进集体”大奖牌,瓦主任就夸黛妹功不可没!
南雪的女儿上学了,每天两送两接太缠腿,便渐渐退为B角,黛妹遂成台柱子。这样一来,为队里拾粪馒头的担子就全压在一把手身上。
队长说,把三个茅厕并为两个,让阿甘和阿铎各看一个,每坑见天记八分。
原先拉粪馒头的那犋耕牛病死一头,队长便让阿铎代劳,独往独来。一把手就腾出手来,每隔四天往回驮一趟。阿铎是个急性子,驮着二百来斤的粪馒头,平均时速依然保持在六七公里,两头见星星,二百余里一天跑个来回,负重去,放空回,有时也顺便为生产队驮运粮草。村里一帮老娘儿们颇为称羡一把手,老革命都半百年纪的人了,咋还这么英雄啊!
一把手调侃说,天天吃白馒头撑的。
古历十二月,阿甘和阿铎步入发情期,开始出现口吐白沫、磨牙、彼此咬腿、咬尾、爬胯等明显特征,狂躁不安,夜不归宿。
距离指挥部三里外有片浩茫的芦苇荡,是水鸟的天堂,子夜时分,阿甘和阿铎闯入冬捕猎人的视界,月光如瀑,蜃气迷蒙,看不分明,闹不清如此庞然大物究竟为何物,不禁悚然一惊,以为遇见鬼了,就悄悄靠近几步,凭经验,一枪打在那鬼脑袋上。
那一夜,满荡的芦苇开红花。
次日,一把手在芦苇荡找到那峰死不暝目的阿铎,蹲倒就哭。
队长痛惜不已,问一把手,打算咋处理?
杀了,皮留下,肉给民工加餐。
一把手不吃不喝,蹲在粪馒头上吧嗒了三天旱烟袋;黛妹称病不适,休唱三天。
事后,一把手请皮匠把驼皮鞣熟了,做成一床皮褥子。将阿铎前腿埋在茨淮新河大坝上,后腿埋在老家后宅。
小南河山一程,水一程,八千里路云和月,悠到公元一九七八年,开挖茨淮新河改成机械化作业,阿甘从此结束了看茅厕、驮粪馒头的光荣使命。宣传队被推下历史舞台,秋冬之季,再也不用去茨淮工地慰问演出了。想吃开口饭的黛妹心口窝把揪似的疼,纠纠结结小半年,不想出门,也不想见人。跟王瞎子说,师傅,俺还没有唱过瘾呢!
王瞎子说,闺女呀,想开点儿,人随潮流草随风,社会进步总比退步好。
时令走至岁暮,南山的蜡梅花开了,接着朱砂梅也开了,阿甘又到了发情期。
季冬多雾,一天,黛妹带上洞箫,摇动驼铃,再度来到埋葬阿铎前腿的茨淮工地,驻足大坝,透过雾纱,但见红旗招展,轰轰隆隆的大机器作业取代了昔日百万民工大会战,她的阿甘已经不再是风景,珠圆玉润的歌声也不再是精神原子弹,一时百感交集。
轰鸣声里,洞箫无语,歌喉哽咽。
太阳越爬越高,化不开的梅香将薄雾一页一页抟起来,丢进山坳里,天地渐渐明白起来。
路在脚下,水向东流。
责任编辑 张 琳
——浅析《阿甘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