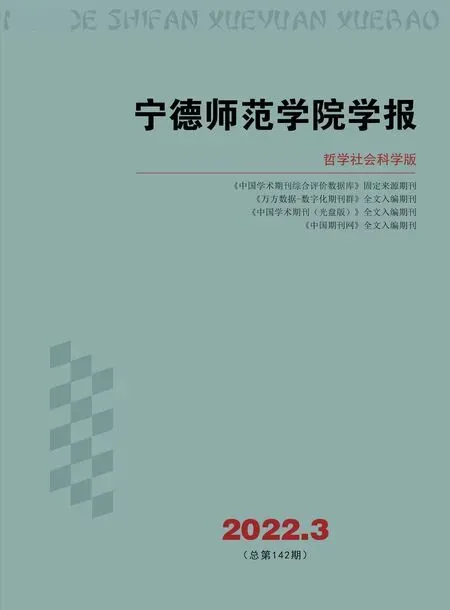对芜湖租界租地交涉的考察
黄良俊
芜湖“在春秋曰鸠兹,盖吴楚必争之地”“濒大江,据要冲,聚舟车之辐、货贝之富,达官贵人往来悉倍他邑”。[1]芜湖地理条件优越,商业繁荣,物产丰饶,商贾云集,早就为列强所觊觎。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被迫新增芜湖为通商口岸并开办租界,揭开了芜湖租地交涉的序幕。“查约开商埠中,由专管租界而变成公共通商场,又界内行政权完全归中国所有者,惟一芜湖租界耳。”[2]所谓专管租界,是指租界内的行政自治权归租借国所有,租让国在该区域不享有行政权,而公共通商场的行政权则归租让国所有。芜湖租界实际上是外国洋行的租赁地,清政府拥有行政管理权,这就是芜湖租界不同于其他租界的地方。然而,不论是何种租界,帝国主义都从中攫取了不平等权利。帝国主义对中国单一制的政治体系形成冲击,从事实上削弱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也剥夺了中国政府在特定地区的治权。
一、划定租界范围的交涉
“马嘉理案”让清廷在外交上陷于被动,清廷一心想着息事宁人。英国正是利用清廷的这种心理,不断以撤使、断交甚至以武力要挟,进行多方讹诈,以满足其侵略欲望。1876年9月13日中英签订《烟台条约》,虽然未最终获得英国政府的批准,但是英国驻华使馆便迫不及待地催促清政府立即开办各新增口岸。1877年3月初,英国人赫德与总理衙门商定,以1877年4月1日为各增开口岸开办日期,并指派各关税务司。据《申报》记载,1877年3月,英国驻烟台领事达文波到芜湖等地进行了细致的考察。[3]1877年4月1日芜湖增辟为通商口岸,由徽宁池太广道监督芜湖海关。[4]英国领事以外商和侨民只能寄住芜湖城中或货船上显然极为不便为由,援引上海租界之例,提出划定地区设立租界的要求。同年4月,达文波与芜湖关道刘传祺签订《租界约》,规定将芜湖西门外沿江一块面积为119亩的滩地划为租界。《皖政辑要》载曰:“勘定县治西门外沿江宿(松)、太(湖)木商滩地,南自陶家沟起,北抵弋矶山脚止,东自普同塔山脚起,西抵大江边止,作为各国公共租界,任各国洋商在界内指段划租。”[5]
然而,由于木商及民众的强烈抵制,不愿让出滩地,使英人企图于光绪三年在芜湖设立专管租界的计划落空。又由于《烟台条约》有关“鸦片税厘办法”和“洋货免厘的范围仅限于租界”的条款,引起英印殖民当局、鸦片商和其他列强的不满,英国政府迟迟不予批准。[6]1885年7月18日,清政府驻英公使曾纪泽与英国外务大臣萨道义于伦敦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10条,简称“烟台续约”。至此,英国政府才正式予以批准,并于1886 年5 月6 日换约。在此之前,英国领事无权要求芜湖地方官员商订租界章程和开办租界,英商只能在芜湖关道刘传祺秉准划定的租界范围内和承租对象自行议办。[7]清政府也以此为由,一直推托延宕。直到《辛丑和约》之后,英公使再行要挟,清廷迫不得已商请不开专管租界,而开为各国公共通商场。英使只好“以芜湖情形特别,又各国商人之在芜湖者惟英商为多,故承认之。”[8]芜湖开埠初期很少有洋商前来投资。1878 年芜湖只有一家英商公司,1891 年芜湖也只有4 家经营长江航运业的英商公司,以及两家日本杂货店。[9]由此可见,即使芜湖由专管租界改设为公共通商场,芜湖洋商以英商居多,英人也足以垄断芜湖贸易。
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任人宰割。英商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急欲得到租地,借机通过英国驻芜湖领事柯韪良,告知英国驻京公使窦纳乐,并向清政府施压。清政府迫于英国等列强的压力,敦促芜湖关道吴景祺尽早解决洋商租地问题。吴景祺遂与柯韪良会商,提出要明立章程,才能动员木商搬迁,并于1902年6月10日将拟定的《芜湖通商租界章程草稿》交予柯韪良领事商酌。柯韪良认为,该章程草案有两处欠妥:一为“英国不得租逾江滩之地三分之一”,二为“每商在租界只能租六亩为止”,应全部删除。[10]此时,正值英国派遣修约专使马凯前来上海,与清政府代表盛宣怀就商订《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进行谈判。柯韪良将此事向马凯汇报,马凯便向清外务部施压,提出只有中方将上述两点删去,他才同意柯韪良与吴关道继续商谈。清政府作出了让步,外务部在给马凯的复照中表示,已将“不得逾通界江滩之地三分之一”,改为“逾通界江滩之地之半”,又将每商租地的限额增至十亩,“倘有租至十亩以上,必须设立公司,或其事业非大地方不可者,应先具情禀由领事官照会地方官核明办理”,并将经皖抚聂缉规修改的芜湖租界章程附在复照后。[11]但是,马凯和柯韪良并没有同意聂缉规的修改方案,他们的目的是将这两处限制全部删除。[12]这就为将来拓展界址和扩大租地埋下伏笔。
柯韪良又与新任芜湖关道童德璋进行了多次谈判和磋商,并无进展。于是,柯韪良照会皖抚诚勋,“力诋芜湖关道童观察办事不善,闻一因铜官山矿约事,观察一再坚执废约;一因米厘加捐事,该领事谓与英商有碍,而观察卒未少徇其请;一因芜湖租界割地事,观察力争不肯让地,故该领事有此照会并请奏简他员与该道员互调”。[13]诚勋试图从中斡旋,协调柯韪良与童德璋之间的分歧。然而,清廷还是迫于压力,几番修改章程以满足英方要求,于1904 年正式签订《芜湖各国公共租界章程》。[14]1905 年5 月16日,经清廷外务部核定批准,正式生效。1905年6月28日,芜湖租界正式开辟。《芜湖各国公共租界章程》最终确定的界址范围指:“西门外南自陶家沟起,北抵弋矶山脚止,东自普潼山(又名桐家山)脚新安普潼塔起,西抵大江水边止。”[15]“改定租界章程十条尚属妥协”,经过多年谈判,租界范围逐渐扩大。[16]据民国八年《芜湖县志》记载:“租界,在陶家沟北,弋矶山南,计地七百十九亩四分四厘八毫一丝四忽。”[17]难怪时人评论:租界即外人占有之地,主权利其,范围渐广矣,奈何。[18]
二、华洋租地的纠葛及交涉
租地是列强殖民侵略的支点,租地交涉各方利益错综复杂,为了抢占先机而绞尽脑汁。芜湖开埠后不久,英人就在范罗、磨盘两山租地建筑领事署、税务司署,此外洋人还将租地用来设立教堂、医院、教会学校等。虽然租界在光绪三年就已勘定,但因未能满足英人的侵略要求,以及各方利益冲突,迟迟未能划定租地。1905 年,安徽铁路公司与怡和洋行争租界内滩地,又致其再次延宕。直至1906 年,英商怡和、太古洋行和德商瑞记洋行等才相继划段,照章缴价成租。租地交涉过程纷繁复杂,不仅反映了侵略者傲慢的强盗逻辑,也体现了清政府处理对外事务和地方事务的能力庸碌。
(一)原鸿安认租滩地的争夺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瑞记北面滩地最早被英领事代鸿安公司所认租,然而日商大阪公司也想租用此地。[19]芜湖关道冯妆灿没有赞成日方提议,随即建议日方租用鸿安以北滩地。日商不甘心,甚至不顾中国法律,竟乘黑夜在界外陶家沟以上滩地树立插标,又借助华人张子川擅自将泰和堂土地抵押给日商,企图以此占地。[20]安徽巡抚、芜湖关道与英日公使、领事进行多次谈判,终于在1907年达成协议,将瑞记洋行以北滩地根据立案请租先后,由英商鸿记公司先租三百尺,日尚大阪公司接租五百尺,日商遂放弃对张子川押地和陶家沟以上插标土地的要求。然而,日商迟迟不办理承租手续,对拟租地区进行丈量和缴款。日本副领事船津辰一郎声称“查阅地势不宜,非推广租界不可”。[21]芜湖关道冯妆灿请示皖抚,应让鸿安公司先行缴价领契,以免“两面牵制”。[22]1908年,英国鸿安公司率先缴价成租,日商节外生枝,转而谋求在陶家沟以南临近木帮滩地的区域“另租形胜之地”。[23]大阪商行与泰和堂抵押交易是在章程订立之后,日商本应共同遵守租地章程,不能以个人买卖契约而破坏租界章程,“惟欠债追偿系华官保护洋商应尽之责任”。[24]芜湖关道认为:“芜湖租界内如有地可租,该公司本可照章办理,如欲于界外展拓地段,实属碍难办到。”[25]
日本人企图界外租地的阴谋没有得逞,英国领事葛福随即提出,既然日本放弃这一滩地,就应该转给英国和记公司承租,多次催促清政府同意和记公司对该地段进行丈量。清政府担心,一旦将此地段交给英商,日本决不肯善罢甘休,仅同意将弋矶山脚的一块土地租给英商和记公司。“日领意在籍口展拓,即以弋矶山之地论,英商既以可用而议租,何独不合于日商,一允和记则日商起而坚要,芜湖租地范围势必因之而溃,鄙意所以坚持者在此。”[26]清政府自然不会答应英领事的请求,便通过外务部对英方的无理请求进行抗议,“英日两商议租同是一地,岂能分为各办,日商议租在先,现尚未与斩断葛藤,岂能一物两许,硬占办法岂是和好,舆国所应出此该领,出言无理”,“芜湖租界所存鸿安北首之地,或归日商或归英商,尽可彼此和衷商酌,乃英领谒见南洋大臣措词失当,殊非办理交涉之道”。[27]清政府告知英方,只有日本领事明确答复,同意将鸿安租地转归英商和记租用,并不再以租界无地可租为借口谋求其他租地,才可以考虑英商请求。然而,日方并不是真正放弃鸿安租地,日商只是不满租地的位置,并以此为由拓展租地。时至1911年,英国一再施压,清政府最终同意英国要求,将租界内“紧连鸿安以下滩地五百尺租给和记公司”。[28]
在争夺瑞记下江滩地的过程中,英日的强盗本性尽显。首先,日本利用外交讹诈、武力威胁,企图使清政府屈服。其一,派遣军舰前来示威,以利于商谈租地事宜;其二,利用张子川押地一事讹诈,企图非法占用土地。其三,英国与日本既有利益之争,又实乃一丘之貉。当日本派遣伏见、隅田号军舰来芜时,“英舰亦至,隐示抵制之意”。[29]同时,英领事意欲借日商租用陶家沟以南之地,拓展租界。芜关道认为,英人欲破我租界范围,歹心叵测,“兹领事以租界各地应以先指租者为准,至谓江滩之地少,不敷租用,则推广陶家沟以南亦属最好最便,不妨给日商承租”。[30]但一旦开此先例,便一发不可收拾。清政府深知英人的野心,并没有放松警惕,这使得英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二)英商筹建驳岸码头
按约章规定,本应由清政府自筹经费修筑码头、纤路,无奈财力拮据,无力筹办。英领事认为江边水势涨落无定,如果没有驳岸码头让英商装卸货物,确实极为方便。芜湖地方官也认为,如果租界一时难臻繁盛,地方又无力筹捐筑路,也断然不能妨碍英商船货的正常出入。暂时准许英商自筑码头,是临时通融办法。英领事与芜湖关道磋商修改芜湖租界章程十条,增加“驳岸码头暂准英商自筑”“如界内一时未臻繁盛,难于筹捐,地方官无力举办,应将沿江应留五丈纤路之地,准英商照界内租价、迁费暂租,听其自筑驳岸码头,日后地方官有力举办各项工程之时,将该英商原出暂租纤路租价及驳岸码头费用归还,由地方官收回”,在修筑码头时,应“会同华官公估费用定数,先行立案,以便日后照案归费收回,不致临时争论”。[31]暂租纤路之地“不另征收码头捐费”,并“免按年输纳税钱”“由地方官收回一律自办,该英商一律照章认出捐费,其码头仍永远归该英商自用”。[32]可以看出,由于清政府无力承建码头和纤路,给予英商很大的通融和优惠,英商不仅可以自行修建,还免缴输纳税钱。当由地方官收回自办时,如果英商愿意照章认缴之前的捐费,该码头的使用权仍永归该英商,这就等同于英商获得了该码头的永久租用权。
此时皖抚虽有筹款自办的想法,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财力有限,将码头暂租英商作为权宜之计。“惟目下财力支绌,各省皆同,安徽尤甚。要务尚多,安有余力及此。暂租无碍公用,尚系实在。该纤路五丈,而英商租作码头不过一隅,余地必宽可想而见,即或所租较广亦不能不留公路。矧契须我给,届时应会同勘估则权,亦我操。”[33]清政府只好同意英方筹建驳岸码头的请求,并要求英方预留土地用以今后修筑公路,届时芜湖地方归还英方相关修筑费用后,便可收回自办。
(三)安徽商办铁路公司修建铁路车站
二十世纪初,全国各地爆发了收回铁路利权运动,清政府鼓励各省修筑商办铁路,以抵制帝国主义对铁路主权的侵占。1905 年7 月,安徽商办铁路公司成立,先行筹建芜湖到南京段铁路,拟租芜湖租界内紧靠陶家沟以北的滩地建立铁路车站。
铁路车站原本拟设在租界之外,“就陶家沟南划留五十丈”,而后又改在界内陶家沟至翟家沟之间。[34]此地本是怡和洋商与招商局争留之地,怡和洋行以其指租在先,不肯让出。江督授意芜关道童德璋,只要没有划归洋商的土地,优先留作铁路车站之用。童德璋与铁路公司总办李经方会晤驻芜英领事孙德雅,经磋商辩论多时,“即以租界头段江滩一百二十丈车站与怡和各半分用为言”,孙德雅称还须禀明驻京英使定夺。[35]柯领事曾提出,如果华商想要挤入租界之内,只有将租界扩充才行。芜关道担心柯领事重施故伎,以此为由拓展租界。之后,经与怡和洋行多次协商,最终于1906年3月商定,将租界内原划归怡和洋行滩地一分为二,各得60 丈,紧靠陶家沟的南部一段“留作芜广铁路建造车站之用”[36],怡和洋行租用北段,“即系陶家沟头段之地”。[37]
为了减免租地地价,铁路公司总办李经方以“铁路为安徽全省要政,以本省之官地营本省之公益事”为由,官地则“免其缴价”。[38]芜湖关道则认为铁路公司的要求与租界章程不符,“芜湖租界定有专章,无论中外官商均应遵守,安徽铁路设立在租界地内,自应按照租界章程办理”“与图用界外官地情事不同”,但是,芜湖关道提议了一个两全之策,以此兼顾铁路公司和洋人各方利益,有主民地应“照租界章程缴价存官,由官查明的业将价给领”,而无主地“应作官地,此项官地铁路车站所用若干,照租界章程一律缴价存官,拟即由官拨入铁路公司,领执股票作为官股,于铁路车站尚属无甚出入”。[39]“租界既与外人议定章程办法,势难两歧,免致贻人口实。”[40]这种变通办法既满足了铁路公司的要求,又不违背遵守租界章程的原则,避免授以洋人废章改约的借口。
李经方回复芜湖关道,“新开租界南边第一条马路,本系沿靠陶家沟之北岸”“铁路公司浚宽陶家沟面,以便驳船停泊,其紧靠沟旁沿北岸之马路,本系照式留出,与原图并无歧异,不过沟面既经改宽十丈”“动工之先,业将图式由本公司总工程师,交与芜湖新关税务司,转寄上海新关理船厅,核准照办在案”。[41]外务部、邮传部担心英领事会借口此事,制造交涉废章的事端。“中国绅商自行集股开办,事关公益,原与洋商租建情事不同,且此北项路工一切兴作,更非他项工程可比,尤不能以为籍口,惟外人狡词争执,诚不可不防”“李京堂参照各国铁路章程另议专章,照会英领事,切实声明,以免嗣后洋商籍端牵引,以为侵占之渐至,铁路需用地亩则应丈量缴价,分别给主具领”。[42]显然,安徽铁路公司要求减免租价和私自占地的行为会引起英人的不满,芜湖地方政府惧怕英人会以租价不公和未按章用地为借口,要求修改租界章程和拓宽租界范围,故而没有同意安徽铁路公司的请求,但又采用了变通方法安抚安徽铁路公司,将官地缴价存官作为官股拨入铁路公司。
(四)修建轮船招商局码头
芜湖是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港口,是中国的粮食集散中心,也是列强向中国中部渗透的咽喉要地。英商太古、鸿安、和记、德商瑞记等洋行企图垄断芜湖的河运海运业务,对轮船招商局在芜湖租界设立码头百般阻挠。南北洋大臣发文芜关道童徳璋,要求“以招商轮船公司应于租界留一基地,以备建造局所”,童德璋当即与英领事商办,并“据上海比例谓招商码头亦在租界之中”,招商轮船公司在芜湖的用地可以以此作为参照,柯韪良则以芜湖章程并未比照上海,不得援以为例,章程已定无可更移,但是“招商码头若立于租界外,则势成孤悬,恐将来商务前途必不能与诸轮船公司竞争也。事贵机先,交涉者颟顸若是。”[43]
轮船招商局码头在芜湖租界的位置尚未确定,芜关道童德璋与英领事柯韪良一再商议,柯韪良“坚决不通融,以致屡次龋龉,未识将来作何办法也”。[44]芜关道试图通过德使葛尔士说服英领事,德使认为,芜湖租界“除弋矶山北相连之地不能作为轮船码头外”,沿江之地“可用者不过四千尺无余,有六洋行公司应彼此分用其中”,租界内“沿江地段仅仅足敷分用”,租界“其中利益亦应尽先归各洋商公司享受”,其他公司“自应置之租界之外,不能使同享租界利益”。[45]葛尔士“以拥挤为言,地段仅敷各国之用,商局不得租地”,并借口称“须请示英使,屡催未复”。[46]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排挤,招商局在芜湖的航运业务发展艰难。
三、租界租地的公共管理交涉
虽然依照《芜湖各国公共租界章程》,洋商分别在芜湖租界划租特定地域,但是并没有设立外国的立法、警察、市政管理机构和征租机构等,芜湖地方政府仍然是地方主权的主体。清政府为了维护管辖权,加强了行政事务管理和市政设施建设。首先,设立丈量局和工程局负责租界的丈量与施工,并派遣租界工程委员加强对公共工程施工的监管在开办租界时。其次,随着租界经商和人员往来日益兴盛,增设巡警所,加强警政,维护租界公共秩序。芜湖地方政府初步筹办租界水陆巡警,这与其他租界有着明显区别。[47]最后,为便于处理华洋纠纷,成立审判厅、洋务局。
(一)协调解决租地拆迁事宜
早在1882年,英国怡和洋行就认租了陶家沟北面滩地,而在此地经营的木商迟迟不肯退让。[48]芜湖关道刘传祺认为木商毕竟在此从业已久,贸然采取强硬措施,恐会民怨沸腾。“在芜湖地方屡代经营木业,自前明购地该处江滩为经商场所,至今二百余年,所费以亿万计。每年纳税款尤多”,忽然声称“木簰停近通商场,与商船及新筑码头均有危碍”,应该让木商迁离该滩地,“无异驱之就死,沿滩居户仰食于木业者,殆将万人,方事之殷”,芜湖关道文焕请求派兵弹压,结果差点酿成暴动,后来因为大冶木帮的木簰撞伤趸船,英使要求木滩迁移,外务部认为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设法从容开导”,而后建议将“木簰丈尺改小,总期无损邦交,自安营业”。[49]清政府虽然想出了变通的办法,但也只是暂时缓和了矛盾。在此后数年中,英国驻华公使和芜湖领事一再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虽总理衙门、两江总督、安徽巡抚和芜湖关道均出面劝说与调解,但均无济于事。
随后,英商据此与木商多次交涉,木商仍坚持不迁让。木商联名上书外务部,请求外务部主持公道,严拒外人无理干涉。木商在上书中陈述弊端:“外国人在中国开辟租界,其种种权力已与各国居留地大不相同,然尚幸划有定界,藉清权限,断无干预界外营业之理,若因其一言要请,而令界外大宗商业随即迁避,任其驱除芜湖一埠办通,则我国通商三十余口,何处不可效尤,提防一决将无底止,且外交之事求进无厌,今日勒我迁徙商场,姑为尝试,他日即议推广租界,更蓄野心。近日上海闸北地方,钧部正筹抵制对付方艰,倘芜案今日稍存迁就,异时闸北即是前车。公举全体代表订一改良办法遵守章程,俾外交即可保全,商业亦不至败坏。”[50]
1908 年,英商又以木簰碰伤英商趸船为由要求索赔并迁移码头木簰。英使照会称:“据该处领事禀六月二十五日有趸船一只被木簰撞断缆索,比有轮船往拖,适值木簰驳往沙滩,将该处趸船六只碰伤,就英商被损而论应索赔偿约值三千两之谱,又据英商某船主禀,该船停泊一日三次被木簰碰撞缆索等情。”[51]原来芜湖关道只允许划滩地五十丈建筑新关,税务司梅尔士则要求在“陶沟以上招商局间辟滩地六十丈建筑新关,以便各公司趸船早日迁移租界”,双方难以达成一致意见。[52]由于木商迟迟未迁出租地,芜湖新关基地迄今尚未勘定。“芜湖租界成立多年,怡和、太古、瑞记等码头已次第建筑,因新关基址丈尺未定,未能尅期开工,致各国趸船不得迁往租界码头。”[53]英商借故施压,禀告驻京英使因新关未迁之故,英商损失甚巨,请照会外务部咨商。“英领事近已询催,而木商尚在倔强,不肯迁滩让地,恃簰夫之蛮野,籍嚣风以逞横,其中自有主唆之人”,“竟敢散布揭帖,屡张虚声,嫉洋惑众,均经严密镇压”,“现多方设法密查主名,严加惩儆”。[54]迫于英方压力,清政府只有妥协退让,而至于失地农民及木商的长久生计,清政府未予体恤。
(二)完善租界公共工程建设
《芜湖各国公共租界章程》第五条载明:界内地段酌留马路数条,辟为东西街道,沿江五丈地面须留为往来船只纤路,但允各国商民任便行走、上下货物、系舶船只;第六条载明:界内日后兴旺,租居人多,所有巡捕房事宜由地方官设立管理,至公共道路、沟渠、桥梁等项工程并由地方官自办,建造修理费用地方官与领事官会商章程筹捐,无论何国商民一体照章征收,毋得抗违。[55]清廷试图通过自主修筑芜湖租界道路、码头等公共工程以示主权自保,然而租界工程的修筑并不顺利,主要受经费缺乏的困扰。
租界工程耗费巨大,需要近十万两经费,而地方政府财力却捉襟见肘。虽然章程载明工程道路建筑、修理费,与领事会商章程筹捐,然而当时仅有英国领事在芜湖,在短时间内很难与各国领事共商筹捐事宜。“待设有码头,有货上下,方可援章开议一切应用之款,不得不先由官垫,乃属事理当然。”[56]芜湖关道童德璋便向皖抚诚勋请求经费事项,“拟于芜湖新关洋税项下拨提银两,以为开办经费,现已禀明皖抚诚中丞,以便定期开办矣”。[57]可是未过多久,诚勋便调任江宁将军,经费申请之事便不了了之。继任的皖抚恩铭对此事也是一再推托:“皖江地瘠民贫,度支匮乏,苟关储可挪,尚当先其所急,岂能拨修码头,此层窒碍难行。”[58]他认为芜湖不能参照南京,南京地大物博、筹款较易,奏拨十万两修筑租界工程不是难事,而皖江地区地瘠民贫、财力匮乏,况且修筑码头也不是当务之急。
后因工程形势急迫,皖抚上书外务部,试图说明租界工程修筑之迫切、需款之巨、筹款之难,请求在洋药税厘项下预拨援款。“伏查画辟各国通商公共租界一切公用、道路、桥梁、沟渠工程,议明由我自修,本为自保主权起见。惟是经费既巨无可腾挪,悉准援案于芜湖关洋药税厘项下先行动拨银五万两。”[59]“不敷之款或俟洋税旺收续行请拨,或与各国领事磋商筹捐应用,设芜地租界铁路先后告成,便捷交通,收捐自旺,公款可期归还,尚不同于虚掷。”[60]最终,外务部同意预拨五万两援款,其余由芜关道设法在租界内筹集。在芜湖租界纵横马路、明暗水渠工料所浩费用中,“除据该抚奏拨药厘银五万两,其四万四千六百九十一两五钱以及此后无论何项不敷等款,应令该关道于租界内设法筹捐以资应用,不得再行请拨正款,所有此次动用药厘银五万两俟将来收捐畅旺,应即照数归还,以重税款相应。所拨银两核实动用,撙节开支,不得稍涉浮冒”。[61]当时,鸦片贸易占芜湖贸易的比重较大,“洋药税厘”成为海关收入的重要来源。芜湖地方财政紧张,难以承建租界内公共工程,竟以“药厘”作为工程拨款,实际上默认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地位。
结语
虽然清政府对芜湖租界拥有独立主权,但是因为清政府受制于不平等条约,在对外关系中处于弱势,而且又因为财力有限,不能自行建设芜湖租界道路、码头等公共设施,却不得不让渡部分治权和利权。列强表面上尊重满清政府,实际上租界租地换契转租归立约国商民享有,不经领事官盖印则无效,中国政府无权干预。[62]英国在芜湖租界享有“治外法权”,据咸丰八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英国民人有犯罪者,皆由英国惩办”[63]。纵有“品行不端,形同无赖”,作奸犯案,触犯了中国刑律,也只是“由监督照会领事官惩办”。[64]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列强将芜湖租界作为对华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的据点,进而沿江而上将魔爪伸向内地。与此同时,芜湖开埠客观上加速了芜湖城市的近代化进程,促进了芜湖近代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成为近代芜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机。时人记载:“外商纷至,轮舶云集,内外转输沪、汉之间,此为巨擘,新机日辟,文化遂于郁郁彬彬,人才蔚起。”[65]
注释:
[1]陈春华纂、梁启让修:嘉庆《芜湖县志》卷十九·艺文志·记上,安徽师范大学古籍馆藏室,第9页。
[2]刘彦:《被侵害之中国(即中国最低限度应取消之不平等条约)》,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174页。
[3]《芜湖情形》,《申报》1877年3月31日。
[4]赵尔巽:《清史稿》卷125·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689页。
[5]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8页。达文波当时是英国驻烟台领事,曾参与“滇案”的调查。此处“普同塔”的“同”应改为“潼”,两者为音近字,当时常有误用。
[6]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编委会常务组编:《世界外交大辞典M~Z》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7页。
[7]谢青、罗超:《芜湖租界史事考实》,《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8]刘彦:《被侵害之中国(即中国最低限度应取消之不平等条约)》,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173页。
[9]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17 外事侨务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64页。
[10]《英使马凯致外部商改芜湖租界章程照会》,王彦威纂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九,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2页。
[11]《外务部致英使芜湖章程两处欠妥已删改请照拟办》,王彦威纂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九,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3-36页。
[12]安徽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编:《安徽外事志稿》,合肥:安徽文化厅机关印刷厂,1988年,第9页。
[13]《芜湖英领事请撤关道之异闻》,《广益丛报》1906年第99期。
[14]《芜湖租界租地章程》,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国际条约大全(民国十四年增订)》下编·卷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617-619页。
[15]《芜湖各国公共租界章程》,《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12期。
[16]《外部咨安徽巡抚诚芜湖新关租界文》,外交报馆编:《外交报汇编·第24册·外交报文牍》,北京: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503页。
[17]鲍实:民国《芜湖县志》卷五·地理志·市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18]《英人又扩芜湖租界》,《振华五日大事记》1907年第39期。
[19]《日商在芜湖租地之纠葛》,《申报》1906年11月1日。
[20]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17 外事侨务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21]《日人要求扩广芜湖租界》,《振华五日大事记》1907年第14期。
[22]《鸿安公司租地已准》,《申报》1907年1月15日。
[23]《发两江总督张人骏安徽巡抚朱家宝电》,沈雲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18)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台湾地区: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42页。
[24]《大阪船会质押租界滩地之纠葛》,《申报》1909年12月10日。
[25]《大阪公司租地之纠葛》,《申报》1910年1月24日。
[26]《江督张人骏致外部芜湖租界事当商皖抚妥筹电》,王彦威编:《清宣统外交史料》卷13,黄岩王氏1933年版,第71页。
[27]《芜湖租界鸿安北首之地英领饬英商硬占请饬和平商议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2-11-001-03-008。
[28]安徽通志馆编:《安徽通志稿·外交考》,台湾地区:成文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29]《山东官报》1906年第138期,第2版。
[30][34]《芜湖关道为英商争执租界上皖抚禀》,《南洋官报》1905年第32期。
[31]《芜湖租界章程应准照行惟驳岸码头费用应先估定立案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2-11-001-02-003。
[32]《芜湖租界中准英商自筑驳岸码头照会》,《申报》1905年1月12日。
[33]《芜湖关道童详院公文(为核议修筑驳岸码头事)(附皖批)》,《南洋官报》1905年第13期。
[35]《芜湖关道上抚宪禀(为英法两国领事催丈租界事)》,《申报》1905年12月30日。
[36]《北洋官报》1906年第944期,第8版。
[37]《芜湖关道禀铁路公司安设车站应按照租界遵守办理请核明见复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2-11-003-09-001。
[38]《芜湖关道禀安徽铁路车站在租界内应照租界定章办理据情咨商应否照办候酌复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2-11-003-09-005。
[39]《安徽铁路公司在芜湖租界内设立车站应照租界办理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2-11-003-09-007。
[40]《芜湖关道文观察禀院抚文(为安徽铁路在租界内设立车站事)》,《申报》1907年8月6日。
[41]《查复芜湖铁路公司浚宽陶家沟面与原图并无歧异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2-11-001-02-017。
[42]《安徽铁路在芜湖租界设立车站办理情形请核复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2-11-001-02-009。
[43]《芜湖招商码头不能争回》,《申报》1905年6月23日。
[44]《磋商租界建设招商码头》,《申报》1905年7月3日。
[45]《芜湖租界请将招商局请拨地段驳回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3-16-044-01-003。
[46]《皖抚陈芜湖招商局租地情形》,《申报》1905年9月12日。
[47]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外事侨务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48]安徽通志馆编:《安徽通志稿·外交考》,台湾地区:成文出版社,1985年影印版,第4-5页。
[49]《芜湖木商呈恳勿令迁滩一事希饬妥筹办理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2-11-001-03-005。
[50]《恳请拒绝外人免令迁滩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2-11-001-03-004。
[51]《又札饬芜湖关道迅将芜湖新关码头木牌应饬设法迁移妥筹详办文》,《安徽官报》1908年第24期。
[52]《委员筹商迁让新关基地》,《申报》1910年3月8日。
[53]《芜湖新关迁移之交涉》,《申报》1911年2月21日。
[54]《芜湖租界订章侯复开办并设法密查倔强木商严惩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2-11-001-02-007。
[55]《芜湖各国公共租界章程》,《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12期。
[56]《芜湖租界修筑马路拟照拨洋税五万应用事请核复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2-11-001-02-017。
[57]《北洋官报》1905年第849期。
[58]《芜湖关道童详院公文(为核议修筑驳岸码头事)(附皖批)》,《南洋官报》1905年第13期。
[59]《度支部奏查明芜湖画辟租界折》,《东方杂志》1907年第4卷第9期。
[60]《芜湖租界修筑马路拟照拨洋税五万应用事请核复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2-11-001-02-017。
[61]《芜湖租界道路桥梁沟渠拨款援案》,颜世清、杨毓辉、胡獻琳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291-300)光绪丁未(三十三)年交涉要览》,台湾地区: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2689-2690页。
[62]芜湖市文化局编:《芜湖古今》,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7页。
[6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55页。
[64]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65页。
[65]查钟泰:《芜湖新修县志序》,鲍实:民国《芜湖县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