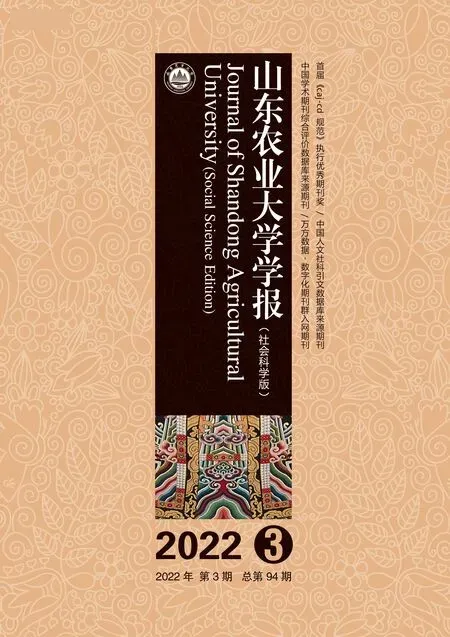迟子建VS莫里森:转型焦虑及其文化启示
胡作友 朱 晗
[内容提要]迟子建和莫里森的自然书写都有一条渐变的发展脉络,即从自然乡野到城市的空间转变、人物自然品性的淡化和传统文化的式微。这种变化可以归结为两位作家面对社会转型而产生的深切焦虑。转型焦虑在揭示作家悲天悯人的文化忧思的同时,也说明回归自然与传统是中西共同的文化心理,文化守成主义创作具有逆全球化的韧性与张力。迟子建的创作书写着传统之思、故土之怀,为我们建构了一个诗意辽阔的精神世界,给我们提供了心灵的慰籍;而莫里森的创作彰显一种更加开放、更加兼容的文化心态,使其能够在文化融合中重新建构黑人的文化身份。自然书写有助于人们在文学创作中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进行自我的反思与重构,实现从回望传统到重塑现实的转变。
自然书写在迟子建和莫里森的作品中举足轻重,因而分别得到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对于前者,以往论述往往聚焦乡土书写,如梁爱民[1]、张懿红[2],或者生态视角,如张东丽[3],将自然作为人类的精神原乡,却没有看到迟子建创作历程中自然书写的转变及其文化内因、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对于后者,前期研究往往聚焦自然书写的意义,如Christian[4]75,或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如熊文[5]。学界不乏专门研究迟子建或莫里森的成果,但是关于她们之间的比较研究尚未见到。我们发现,迟子建与莫里森的自然书写都有一条渐变的发展脉络,体现为叙事时空从自然乡野到城市丛林的转变、人物自然品性的淡化、传统文化的式微。有鉴于此,我们拟对迟子建与莫里森自然书写的转型焦虑进行对比研究,以期开拓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
在现代化转型中,自然经济让位于市场经济,以传统和血缘维系的社会关系让位于合乎理性的社会关系。在中国,随着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变,自发的经验型文化模式被自觉的理性文化模式所取代。在美国,黑人群体历经两次转型,一是从非洲故土到美国乡土的迁徙,其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模式被美国主流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所取代;一是从美国乡土迁入城市,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面对这种共同的现代化转型,迟子建和莫里森的小说表现出了一种普遍性的转型焦虑,具体体现在生态、伦理和文化三个方面。
一、城乡空间转变引发的生态焦虑
自然书写的转变首先表现为从自然到都市的空间转变。两位作家在由自然生态到现实人生的书写转变中,对自然乡野的回顾日益减少,都市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空间。现代化转型、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对自然的改造和开发、都市空间的扩大为显著标志,在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都市斩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这种空间转变的书写体现了两位作家面对现代化转型的生态焦虑。
迟子建的早期作品大多以故乡自然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生命运为书写对象,从《北极村童话》中的白云飘荡、花鸟繁盛,到《北国一片苍茫》中的蜿蜒山峦、茫茫白雪、北国密林,自然始终是其早期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从《原始风景》开始,迟子建的自然书写产生了变化,作者逐渐转向旅居城市、回望故土的视角,来书写身处城市的焦虑感和失落感。在《踏着月光的行板》《门镜外的楼道》中,迟子建开始直接将城市作为叙事空间,小说中城市底层人民艰难的生存状态,与前期小说中清新的乡村景象、温馨的乡村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城市这一叙事空间悄然崛起,替代了原先的森林空间。
从大自然中寻求生存并没有错,但现代化进程中那种攫取式的寻求,持续的开发,却使森林走向了衰老,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生活在山林中的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6]263。从《鱼骨》中生态破坏导致鱼讯如期不至,到《群山之巅》中连年采伐导致森林树种单一,虫灾频仍,再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森林不再是宁静美好的乐园,生态环境遭到彻底破坏。随着开发向森林的日益延伸,人们被迫走出山林,走向城市,在这种城乡空间的转变中,一种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忧虑呼之欲出。
莫里森在前期同样较多地书写乡野自然这一叙事空间,刻画了人与自然的相互融合:从《所罗门之歌》中的“林肯天堂”,到《秀拉》中的林阴大道,自然空间总是能帮助黑人实现自我的成长;从《宠儿》中的林间空地到《天堂》里的旷野,自然空间为黑人提供了一种宗教的力量。然而,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将目光转向了大城市;《爵士乐》以纽约为发生地,以美籍非洲人从南方农村迁移到北方城市为历史背景;《家》以城市为中心,讲述了从战场归来的弗兰克奋力拯救妹妹的故事,城市成为空间叙事的主要方式。
这种空间转变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对生态的破坏:从《柏油娃》中在白人无序开发下断流的河水、倒下的兰树、发狂的溪水,到《秀拉》中被拔掉的龙葵和黑莓、消失的梨树、烟尘喧嚣的街道;从《所罗门之歌》中被侵占的“林肯天堂”,到《慈悲》中生态恶化、疫情蔓延,这些景象都书写了白人入侵者对大自然的掠夺及其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在白人入侵者看来,自然与荒野是上帝所赐的乐土,他们是来征服和主宰自然的[7]231。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了,自然成了被征服、被损害的他者,在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日渐消失的自然空间的书写中,一种生态焦虑呈现在读者眼前。
迟子建书写了她对现代化进程的冷静观察。在迟子建看来,城市是在地球上最大的罪孽:混沌的烟云、狭窄的街道、无情的背弃、无尽的争吵,这些都是城市的景观。高楼大厦林立,阻断了人与自然的联系,人心也在焦虑、混乱的城市文明中变得冷漠与紧张。通过对现代化进程的客观审视和对城市文明的批判,一种由现代都市文明而产生的生态忧虑溢出纸面。
莫里森始终以黑人群体和自然的“他者”地位为表达的重点,她的生态忧虑中包含有针对种族主义的批判色彩。黑人民族与自然之间一直有着亲密的联系,两者之间互为依存,但这种亲密关系却被奴隶制割裂了,黑人失去了自己的历史与语言,与自然一道成为被奴役的对象,异化为一种“他者”的存在。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白人来说,黑人是自然旷野中的生物,黑人的人性特征被蔑视,被去人性化的黑人与自然都被视为一种客体存在,一种被征服的“他者”。自然与黑人的地位是大致相同的,白人对自然的破坏和侵略等同于对黑人的奴役和侵略,两者都是白人社会中被侵略、被迫害的“他者”。因此,托妮·莫里森认为,对自然的感知不是一种简单的本能反应,而是一种潜在的种族政治的反应[8]211-233。
简言之,面对现代化转型,两位作家都通过自然书写的转变表达了一种生态忧虑,但是这种生态忧虑却有着细微的差别:迟子建主要以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合理开发为主要批判对象,对于现代文明的辩证观点贯穿了她的创作路径;而莫里森则以白人殖民者的肆意开发、生态破坏为主要批判对象,她的生态忧虑中包含有更浓重的种族色彩,她始终以黑人群体和自然的“他者”地位为表达的重点。
二、自然品性淡化引发的伦理焦虑
自然书写的转变也体现在自然品性的淡化中,这种转变体现了迟子建和莫里森面对现代化转型的伦理焦虑。古代中国与传统非洲都形成了稳定的自然主义文化模式,形成了一种以人情关系和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机制。社会转型改变了这种文化模式,工业文明将理性、法制、契约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取代了以往的血缘、人情关系。一方面,高扬技术理性主义使人类的物质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另一方面,理性文化的发展也导致了事关人类生存的伦理困境,机械化发展使人的感受力丧失,情感体验变得僵化[9],人被迫走向了物化与异化,在普遍异化的世界中相互竞争,失去了原本珍贵的自然品性,形成了价值混乱、道德滑坡的失控局面。在迟子建和莫里森的笔下,人物自然品性在城市文明与自然人性的相互冲突、技术理性主义与伦理道德的相互矛盾中走向了淡化,并形成了一种伦理焦虑,这是一种由于生活方式畸变而导致的焦虑[10]。
在迟子建的笔下,自然是女性的诉说者和代言人,是女性最契合的象征。在迟子建的前期作品中,《沉睡的大固其固》中的温高娘、《逝川》中的吉喜、《树下》中的七斗等将自然作为精神家园,在困境中顽强挣扎,体现了一种可贵的自然品性。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伊莲娜热爱森林,与驯鹿为伍,与山林为伴,她从森林走进城市,最终仍旧回到森林,却葬身于河流中。如果说迟子建在伊莲娜身上寄托了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理想,那么伊莲娜的最终结局则宣告了这一理想的折翼,以及诗性性格在现代社会中的破碎。在这之后,迟子建转而描绘女性在城市空间中的失落,从《零作坊》中抛弃家庭的翁史美,到《第三地晚餐》中疑心重重的陈青,再到《晚安玫瑰》中沉迷物欲的赵小娥,这些女性的爱情与生命都是悲怆的,她们陷于精神的困境,失去了珍贵的自然品性。通过这种自然品性的淡化可以看出,作为传统伦理关系中心的情感与爱心逐渐走向衰微,技术理性主义浸透人们的精神层面,理智与金钱取代了传统的伦理价值,人性被异化,价值取向面临转型,从而形成了一种伦理焦虑,而在其底层,潜藏了一种深深的呼唤,呼唤人们回归情感与传统伦理。
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与自然亲密接触[11]。莫里森的前期作品,塑造了与自然互为象征的女性,如《秀拉》中的秀拉、《宠儿》中的塞丝、《所罗门之歌》中的派拉特[12]62。然而,在其后期作品中,这种鲜明形象却逐渐淡化。《爱》中的梅,沉迷于物欲的追求;而克里斯汀和留心的争权夺利说明,诗性性格在勾心斗角中被湮没,取而代之的是妒忌与争夺。这种自然品性的转化写出了在白人主流文化与非洲传统文化的两相碰撞中产生的伦理焦虑,具体体现为技术理性主义对人们精神层面的深刻影响,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情感体验变得僵化而机械,自然品性和生命活力在城市文明中走向淡化。当莫里森笔下的人们进入城市,旧有部落的价值观与城市文明的价值观相互冲突,人们便逐渐被这种冲突吞没了[13]120-121。非洲文化影响下的伦理道德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崇尚自然,远离都市,鄙视物质追求,也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处处受挫,于是旧有的诗性品格就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慢慢淡化了,乃至渐渐没落,人们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与抉择中形成了一种伦理焦虑。
在人物自然品性淡化的背后,莫里森与迟子建通过书写城市文明对人的异化作用,表达了一种伦理焦虑,然而其背后的缘由却是不同的。迟子建笔下的伦理焦虑来源于现代都市文明对人的异化与束缚,体现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都市以其快速发展的物质文明唤起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与渴望,如《群山之巅》中为了挣钱而抛弃爱情、出卖自己的林大花,痴迷钱财、将女儿作为挣钱砝码的烟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那些拿着怃恤金另觅他人的年轻女人们,这些人物形象被金钱所腐蚀,忽略了传统的伦理价值。另一方面,在以金钱为主要价值取向的都市文明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淡,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因此这些人的精神是失落的,她们找不到心灵的家园。个体精神的空虚,灵魂的无处安放,使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丧失了爱与信任的能力。从《第三地晚餐》中终日陷入猜疑泥沼的陈青,到《晚安玫瑰》中疲惫忧伤的赵小娥,她们在两性关系中的猜疑与博弈,其爱情的苍白与浅薄,都体现了现代都市文明的异化作用。传统伦理关系的核心在于情感与爱心,人们在博取物质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自我主体性,情感逐渐枯萎、人性趋于沉沦。情感与爱心枯萎了,以前潜伏的伦理焦虑也就昭然若揭了。
莫里森笔下的伦理焦虑来源于黑人群体在新旧文化冲突中民族身份的丧失。在几部以城市为发生地点的作品中,城市作为自然的对立面,是一种无法提供归属感的存在,黑人在城市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冲突中无法确立正确的伦理价值。《所罗门之歌》的主人公,被放置在北方工业城市中,却仍然遭受种族歧视的暴力,黑人社区在迁移过程中进一步流散[14]164,远离了原本的传统伦理道德。而《爵士乐》中的城市作为主人公乔寻找与建构自我身份的背景[15],进一步凸显了黑人在当代社会的伦理失落。在向城市文明的过渡中,莫里森通过书写黑人群体的品性和心灵转变,来说明伦理焦虑的深层原因。文化价值失落,超功利性的传统伦理价值逐渐被白人主流文化中的世俗化、功利性伦理价值所取代,从而导致了伦理危机。立足于黑人的文化土壤,正确借鉴白人主流文化,使两种伦理价值观相互促进,使黑人群体既能保存原有的伦理道德,又能完全融入当代社会,这是莫里森面对伦理焦虑而提出的核心思想。
三、传统文化式微引发的文化焦虑
现代化转型催生了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理性的、契约的文化模式,大工业社会时代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对传统社会中自然的文化模式构成了根本性的冲击与挑战[16],导致了金钱至上、权力至上等社会思潮的流行。面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迟子建和莫里森通过书写传统文化的式微,抒发了对文化转型过程中文化失范现象的忧虑。
传统文化孕育于自然,也脱胎于自然,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文化意识,自然书写的转变体现在传统文化的式微和生态文化理想的失落中。迟子建的作品书写了天人合一、融入自然的传统文化精神,这种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工业的冲击下遭遇了重大危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森林为鄂温克人的驯鹿提供了食物,人们将森林视为栖息地,在森林的怀抱中寻找依靠,森林、河流、驯鹿和鄂温克人形成一个互相依存、紧密联系的共同体。然而,森林开发使鄂温克人不得不离开森林,开始他们难以适应的山下定居生活,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伊莲娜。伊莲娜从森林走向城市,随后返回森林,最终在内心世界的颠簸中葬身河流。伊莲娜的身上体现了天人合一、融入自然的传统文化,她的悲惨结局诠释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溃败,体现了作者面对传统文化式微而产生的文化焦虑。
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现代化转型,但对黑人群体来说,如何在心理层面完成从民族传统文化向西方现代文化的转型,仍然任重而道远。莫里森的前期作品体现了非洲传统文化对自然的崇尚,而在中后期作品中,这种以崇尚自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精神逐渐丧失了。在非洲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有着紧密的情感依存关系,人类的生命依赖于自然的庇护,两者之间和谐相处。森林被视为生命之源,人是渺小的生灵,和其他生物共享地球[17]8。《所罗门之歌》中的奶娃,通过树木与世界对话,与自然和谐相处,将自己扎根于大地、自然与传统。然而,传统文化的式微在《所罗门之歌》中也已经有了苗头。黑人传统文化的体现者派拉特崇尚自然,博爱宽厚,可她对白人文化一概排斥,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最终走向了死亡,这一形象表达了莫里森对传统文化的客观审视。《柏油娃》继续书写传统文化的式微。森是非洲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他将黑人社区视为理想社会,但是,森跨不出黑人社区,始终徘徊在白人主流文化之外。通过描写森在现代社会的两难处境,莫里森书写了黑人传统文化的衰败,以及转型迫切性,表达出一种深切的文化忧虑。
在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历程中,迟子建和莫里森笔下的主人公都经历这样一种文化焦虑,而这种中西方共同的文化焦虑实际上共同诠释了“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18]。在悉尼和澳洲土著人聚集的达尔文市里,迟子建遇见了一些土著人,他们进城后无法融入灯红酒绿的城市,遭遇了“生活中本不该出现的冲突”,在城市里处处碰壁[6]265。后来,迟子建来到古老的爱尔兰,这座声色喧嚣的城市同样让她感到陌生,显示出上述尴尬、悲哀与无奈的普遍性和全球性。
从鄂温克人,到澳洲的土著人,爱尔兰人,再到莫里森笔下的黑人,乃至所有经历文化转型的人们,文化焦虑是一种在传统的断裂中失去精神故居的焦虑,也是一种在现代化来袭中寻找文化前景的迷茫。他们原本都来自自然,却都被丢进现代文明的滚滚浪潮中,他们是“现代世界的边缘人”[6]266,在传统价值意向的断裂中面临理想失落的困境,在价值的重新定位中面临精神悬置的危机[19]。从中国到世界各地,人类文明进程在传统文化的式微中,展现出一种共通的文化焦虑。面对这种焦虑,迟子建和莫里森展现出不同的希望。迟子建寄希望于融入自然和回归传统,为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的文化焦虑提供有益的启示,以医治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病;莫里森寄希望于回归自然与传统文化,建构黑人社区,同时强调对现代社会主流文化的借鉴与融合。
首先,迟子建寄希望于自然,期待以人与自然的融合来化解文化焦虑。迟子建以“半个月亮”来命名《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尾声,“半个月亮”以自然意象为隐喻,象征着迟子建理想中“真正的文明之境”,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18]。在迟子建的笔下,自然是诗意的,如《花瓣饭》,人们通过回归自然,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精神上的升华与安慰,摆脱眼前的精神困境。自然还有净化心灵的作用,与自然对话能使人超越功利性的现实生活,获得灵魂的安放与休憩。《原野上的羊群》中,那对夫妻通过领略乡土风光来医治现代文明灾难,缓解精神创伤。其次,迟子建主张通过回归传统文化来回归本真人性。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浸染下,这种本真人性在现代都市的繁弦急管中被湮没了。实际上,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精神资源,无论是儒家思想的性善论,禅宗的顺从自然的本性,还是佛家哲学强调的以自在心境化解欲望,道家思想追求的顺从自然,天人合一,都是回归本真人性的主张。因此,只有从中国本土文化大地挖掘自己的文化之“根”,发掘其永恒价值,才能挽救失落的人心,解决现代社会中信仰缺乏、道德失范的难题,化解文化焦虑。
面对文化焦虑,除了回归自然与传统,莫里森也寄希望于黑人社区的建构。首先,自然承载民族文化,是连接民族文化与自我身份的纽带。个人通过融入自然,获得心灵的慰籍,汲取生存的力量,从而融入传统文化,回归生命源头。面对着从自然乡野到城市空间的转变,促使小说人物在城市中留下来的是那些具有文化同质性的社区[20]2-3。黑人社区是美国黑人群体生存的重要空间,黑人社区中的歌唱、叙说故事等活动,都是对形成并维持黑人集体的一种寻求[14]164。黑人社区始终滋养着黑人群体的生命,传承着悠久的非裔传统文化,化解着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文化焦虑。
其次,莫里森也强调对现代社会主流文化的借鉴与融合。黑人音乐和宗教中的黑人传统观念始终与其小说艺术相伴随,而黑人文化之根能给黑人群体带来成为自己的自由,和作为部落成员的归属感[21]43-44。黑人传统文化是黑人确立自我的重要根基,只有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土壤,黑人民族才能确立自我存在,扎牢精神支柱,摆脱边缘化地位与文化认同危机。与此同时,莫里森也强调主动汲取白人主流文化,将现代文化和黑人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黑人性和美国性共生共存,解决现代化转型所带来的文化焦虑。
四、转型焦虑的时代书写与文化启示
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理性主义的盛行、大众传媒的泛滥,都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造成了极大冲击,物质主义甚嚣尘上,商业化、市场化的社会潮流席卷而来,人与自然相对立、人体与他人相疏离、情感与理性相割裂等问题层出不穷[22],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转型焦虑。在现代性文化语境下,迟子建将个体生命放置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剧烈冲突中,从而提出了个体在文化转型期如何实现自由发展的问题。她将乡土社会所代表的传统精神文化作为缓解焦虑的一种精神弥合,来对抗严峻现实带来的心灵重压,拯救在现代荒原中流浪的城市人,这种将传统精神与现代文明相交融的文化理想,为中国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文学层面的参考。如果说在创作前期,迟子建用诗意的想象、清丽的文字、亲切的故乡意象为我们建造了一个乡土世界,那么在创作中后期,她通过描绘城市对自然的挤压、物质对精神的异化、现代对传统的侵蚀,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在转型中满是焦灼与无奈的都市空间,而贯穿其小说世界的,是她对人性之美的执着追求。
以美国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黑人移民潮”现象为总体背景,针对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各种现实问题,莫里森书写了黑人群体的生存境遇及其身份焦虑,对转型期的美国社会制度给予批判,彰显了作家的社会担当[23]。独立战争后,南方日益窘迫的农场经济,持续的自然灾害,导致了经济萧条,加上南方社会的高压政策导致了黑人的认同危机,于是黑人前往城市,形成了“黑人移民潮”,这是美国城市化进程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之一[24]。第二次工业革命给美国带来了城市转型焦虑[25],更给黑人群体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击,即传统部落价值观与新型城市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困惑[26]。这种困惑是一种从南方农业社会进入北方工业社会的困惑,使莫里森笔下的人物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深切的焦虑与痛苦。莫里森从现实层面出发,书写黑人身份建构之难,让文学的光辉照进现代社会的生态困境、伦理困境、文化困境,为黑人群体的文化身份建构提供有效途径,表达自己的种族和政治思考。莫里森始终关心黑人命运的发展,表达对民族生存境遇的关注,这是其小说自然转变与焦虑书写的核心所在,也是其小说不同于其他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的小说的鲜明特征。
以迟子建为代表的文化守成主义乡土小说一直贯穿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历程。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即中国现代化转型初期,以沈从文、废名等为代表的京派作家通过小说建构起了田园牧歌式的边城世界、黄梅故乡;到四十年代的汪曾祺,继续描绘着诗意静谧的乡土世界;到九十年代的贾平凹、张炜等,书写着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重负和乡村野地形象的失落;再到迟子建,她的写作是乡土小说传统的延续,她继续书写乡土人情的淳朴和城市文明的腐化。乡土小说的方兴未艾,表明了即使面对现代化转型,中国现当代文学对文化守成主义始终有难以割舍之情。这一小说传统书写着传统之思、故土之怀,为我们建构了一个诗意辽阔的精神世界,给我们提供了心灵的慰籍。面对现代化的都市世界,用诗意自然、淳朴人情、传统文化建构起的文化田园无疑能为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慰籍,但若将更多笔力投入现代化进程的描写,揭示这个伟大时代波澜壮阔的大潮,会推动人们以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热情去解决摆在面前的困难问题。
比较之下,莫里森的文化主张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启发。莫里森立足黑人传统文化,兼受白人文化教育,双重文化的熏陶使她培养了一种跨种族跨传统的兼容并包的心态,使她超越了种族身份和文化立场的藩篱,对人类共同的文明遗产进行整合,书写着两种文化互相融合的期盼,并在文化融合中给黑人文化身份以重新定位。因此,莫里森的文化兼容呈现一个从文化固守到文化批判再到文化融合的开放性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体现了一种博大宽广的文化胸怀。守护黑人文化传统是民族的立身根本,然而拒绝变通会使人们受到思想上的束缚,徘徊在现代化社会的边缘,无法确立真正的自我文化身份认同。只有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去接受西方文化,不断地以世界文明成果充实黑人文化的内涵,黑人民族才能打破自身的文化封闭性,走向文化融合,从而更快地向现代化社会迈进。
无论是迟子建作品中对传统文化的回归,还是莫里森作品中对黑人民族传统的固守,都表明了当城市文化逼近乡村时,回归自然与传统是中西共通的文化心理,文化守成主义创作具有逆全球化的韧性与张力。不同的是,莫里森发展了一种更加开放、更加兼容的文化心态,使其在学习与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发展民族文化,积极主动地与现代文明接轨,这一点足以给当今的中国文坛提供借鉴。美好的田园牧歌时代毕竟回不去了,既然现代化的浪潮扑面而来,为何不勇敢地冲进去弄潮呢?我们不能拒绝,只能跃进未来,努力寻求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新的和谐,建构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兼容并蓄、共存共荣的新状态,向一种新的、寄予着更高希望的文化迈进。在借鉴外国文学的基础上,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汲取他者文化的经验,走出民族主义的拘囿,走出传统文化的困境,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语境相结合,建构新的文化语境,实现自我的反思与重构,实现从回望到重构的转化,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书写新时代的文学家园,或许会有新的气象。当然,以迟子建为代表的这一脉文化守成主义乡土小说无论如何都是我们永远的“桃花源”,它始终书写着美好的乡土诗意与自然向往,寄予了深厚的人文情怀,表达着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沉关怀。
五、结语
从自由自在的日常生活世界走向物化的、消费型的现代社会世界,从安静的、充盈着自然气息的乡土丛林走向技术理性主义高扬、商品经济发展的工业社会,转型焦虑是一种在自然和都市的流转中寻觅安身之所、在人性宽厚与凉薄的转变中追求心灵救赎、在民族与现代文化的熔铸中寻找精神依托的怅惘和忧思。从自然乡野到城市丛林的时空变化、人物自然品性的淡化、传统文化式微等自然转变的背后,迟子建和莫里森书写着社会转型带来的种种焦虑,描绘着人类所共同的生存困境,体现出对精神家园和心灵救赎的共同追求。
不同的是,在生态忧虑的书写中,迟子建主要针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合理开发,而莫里森则以黑人群体和自然的“他者”地位为表达的重点;在伦理焦虑的书写中,前者的焦虑来源于现代都市文明对人的异化与束缚,后者则来源于黑人群体在新旧文化冲突中民族身份的丧失。面对中西方共同的文化焦虑,迟子建寄希望于融入自然和回归传统,而莫里森寄希望于对自然与传统文化的回归、对黑人社区的建构、对现代社会主流文化的借鉴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