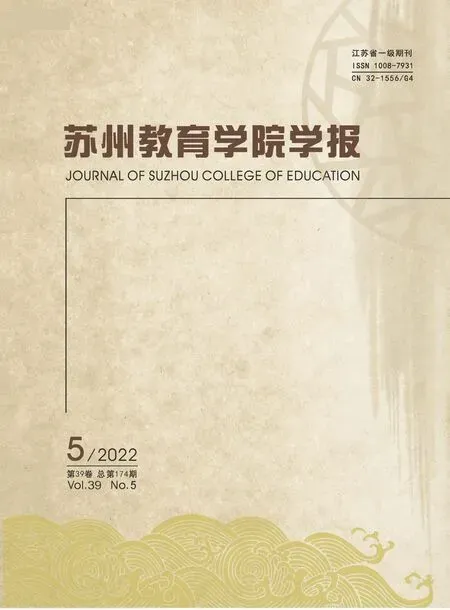中世纪早期小说与史传中的甄后之死*
高德耀(Robert Joe Cutter) 著,吕辛福 译
(1.内华达大学雷诺分校 世界语言与文学系,美国 雷诺 89557;2.青岛科技大学 传媒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一
让我们先从《文选》中曹植《洛神赋》的李善注说起,李善注《洛神赋》时引用了一篇无名氏的《记》,内容如下:
《记》曰: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①《世说新语》注引《魏略》称甄后之父为甄会。见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第489页;Richard B.Mather(马瑞志),trans.:Shih-shuo Hsin-yu: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Minneapolis: Univ.of Minnesota Press, 1976),第484页。然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引《魏略》却没有出现甄逸又名甄会这句话,见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第11a页。《世说新语》注引的《魏略》文本可能有所窜改。,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②《记》的作者对封号引用不当,当此事件发生时,无论甄氏还是郭氏,还都没有封“后”。。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懽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③这样做或许是为了防止人的魂魄逃出。在更正统的贵族葬礼中,一个玉制的塞子也有此作用。参见Michael Loewe(鲁惟一):Ways to Paradise: The Chinese Quest for Immortality(London: Allen & Unwin, 1979),第 9 页。,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④萧统撰、李善注:《文选》卷十九,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出版,第11b——12a页。
今天很少有人会相信这个材料的真实性①至于《记》是否是李善原注,相当令人生疑,这则材料可能是尤袤在1181年《文选》刻本中加入的。参见胡克家:《文选考异》,见萧统:《文选》卷四,第4b页。,确实没有依据表明《洛神赋》是写给甄后的诗,也没有理由假定曹植会跟她产生一段没有希望的热恋②Paul W.Kroll(柯睿):“Seven Rhapsodies of Ts’ao Chih”,in Festschrift J.I.Crump(Stanford: Stanford Univ.Press, forthcoming);Robert Joe Cutter(高德耀):“Cao Zhi(192-232) and His Poetry”(Ph.D.diss., Univ.of Washington, 1983),第 287——289 页。。不仅如此,这段很有新意的阐释材料很像是一则受到《洛神赋》启发而创作的轶事小说,并且利用了美丽的贵妇、威严的皇帝和皇帝的浪漫弟弟之间可能存在的一种三角恋关系③Cutter(高德耀):“Cao Zhi(192-232) and His Poetry”,第287页。。由于这段文字中涉及凡人与神灵的遭遇,可以看出受到了从曹植到李善这段时期志怪小说传统的显著影响。④有关志怪故事中的鬼神,参看Anthony C.Yu(余国藩):“‘Rest, Rest, Perturbed Spirit!’ Ghos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rose Fiction”,HJAS 47(1987):第397——434页;以及Robert F.Campany(康儒博):“Ghosts Matter: The Culture of Ghosts in Six Dynasties Zhiguai”,CLEAR 13(December 1991):第15——34页。作为一个鬼神故事,《记》是余国藩与康儒博文章中提到的鬼神故事类型的合体。甄后灵魂的现身,不仅是因为生前遭受的不公,还因为她对葬礼的不满。此外,她还是一个多情的鬼魂,她的现身是回来享受生前不能得到的情爱。值得注意的是,几个世纪后,清代的蒲松龄创作了一个以甄后鬼魂为同名女主人公的故事——《甄后》,然而这个故事却不再聚焦于甄后之死。见蒲松龄:《聊斋志异》,香港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第437——438页。
《记》中一些相似的情节在别处也出现过,首先就是曹植爱上甄后以及不同追求者之间围绕甄后出现的竞争。另外,还有一种极不可能且有点让人蒙羞的说法在《世说新语》中被精心杜撰了出来,内容如下: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将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⑤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第489页。英文版见Cf.Mather(马瑞志):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第484页。Mather把“奴”译为曹丕,但实际上这里的“奴”很可能指的是未来的甄后。参见张可礼:《三曹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第87页。
这里的记载显示,曹操对甄后有觊觎之心。三国时期相同的人与事,有时会在现存史书文献中存在广泛的叙述差异,鉴于当时文人对曹操形成的刻板印象,曹操无疑更易受到这些矛盾叙述的影响。⑥见 Paul W.Kroll( 柯 睿 ):“Portraits of Ts’ao Ts’ao: Literary Studies on the Man and the Myth”(Ph.D.Diss., Univ.of Michigan,1976),第 118——138 页。就我们刚刚引用到的这段材料来讲,刘义庆(403——444)或其他任何可能是《世说新语》作者或编者的人,在这段文字中清晰地反映出了他们当时对曹操本人的负面评价。实际上,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其他有关曹操的内容,更为不敬。⑦Kroll(柯睿):“Portraits of Ts’ao Ts’ao,”,第 129——131 页。尽管曹植爱上甄后的传说在后代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可,但出于对《世说新语》的信任,清代学者梁章钜⑧译者按,原文误为“刘章钜”。(1775——1849)在《三国志旁证》中还是对曹操追求甄后给予了热情的赞同⑨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七,台北艺文书局1955年出版,第3a页。。不过幸运的是,张可礼在《三曹年谱》中对此进行了纠正。⑩张可礼:《三曹年谱》,第87页。
事实上,有足够多的材料可看出甄夫人是如何变成曹丕的妻子的。《三国志》中甄夫人的传记中这样写道:
建安中,袁绍为中子熙纳之。熙出为幽州,后留养姑。及冀州平,文帝纳后于邺。⑪⑪陈寿:《三国志》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第160页。按,邺是冀州首府也是袁绍、袁尚政权的基础,曹操204年占领邺城,旧址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三台村。
裴松之的注把关于曹丕与甄夫人初次见面的细节以原样保留了下来“,裴注”引《魏略》曰:
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邺城破,绍妻及后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绍舍,见绍妻及后,后怖,以头伏姑膝上,绍妻两手自搏。文帝谓曰:“刘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妇举头!”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太祖闻其义,遂为迎取。①陈寿:《三国志》卷五,第160页。这段文字被方志彤和马瑞志分别翻译过,见Achilles Fang(方志彤),trans.: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220-265): Chapters 69-78 from the Tzu chih t’ung chien of Ssu-ma Kuang(1019-1086), ed.Glen W.Baxter, 2 vol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Press, 1965),第一册:第69页;Mather(马瑞志):Shih-shuo Hsin-yu,第484页。按,如前注所提,《世说新语》刘峻注引《魏略》文字与此处裴注文字略有不同。
裴松之还引用了《魏晋世语》中的材料:
太祖下邺,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妇人被发垢面,垂涕立绍妻刘后,文帝闻之,刘答“是熙妻”,顾揽发髻,以巾拭面,姿貌绝伦。既过,刘谓后“不忧死矣”!遂见纳,有宠。②陈寿:《三国志》卷五,第160页。英译本见方志彤:The Chronicles of the Three Kingdoms,第69——70页,以及Mather(马瑞志):Shih-shuo Hsin-yu,第484——485页。
尽管上述材料有些不同,但此处所引的这些文本在一些主要观点上大同小异,这些材料某种程度上也被曹丕本人间接予以证实。曹丕名作《典论》今天已大部分亡佚,但《群书治要》据称是保存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在有关段落中,曹丕谈到了他在袁绍府上停留(这件事):
上定冀州屯邺,舍绍之第。余亲涉其庭,登其堂,游其阁,寝其房。栋宇未堕,陛除自若。③魏徵(580——643)等编:《群书治要》卷四十六,第30b页,四部丛刊本。又见于张可礼:《三曹年谱》,第86页。英译本可见 Howard J.Wechsler:Mirror to the Son of Heaven: Wei Cheng at the Court of T’ang T’ai-tsung(New Haven: Yale Univ.,Press, 1974),第113页。
二
就曹操、曹丕对甄后的态度方面看,假设李善注所引的《记》和《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叙述传统是不可信的,但就甄后之死这件事情本身来讲,至少《记》中的内容比较接近历史真实。让我们回忆一下,《记》中提到甄后之死与郭后的谗言有关,也就是说郭后要为甄后之死担责,《三国志》甄后传中对她的死有如下叙述:
黄初元年十月,帝践阼。践阼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④李贵人生曹协,赞哀王,幼年去世。见陈寿:《三国志》卷二十,第590页。,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⑤陈寿:《三国志》卷五,第160页。
甄后是曹睿的母亲,曹睿在226年继承帝位,即明帝。甄后去世时,曹睿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非常想念自己的母亲。由于某些不言自明的原因,人们一定会对明帝写给郭后的悼词内容感到怀疑,这篇悼词见于王沈《魏书》,裴松之引述如下:
维青龙三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宫启殡,将葬于首阳之西陵。哀子皇帝睿亲奉册祖载,遂亲遣奠⑥见J.J.M.De Groot(高延):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its Ancient Forms, Evolution, History and Present Aspect: Manners,Custom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Connected Therewith(1892-1910; rpt., Taibei: Literature House, 1964),第一册:151——152页。,叩心擗踊,号啕仰诉,痛灵魂之迁幸,悲容车之向路,背三光以潜翳⑦“三光”指太阳、月亮与星星。,就黄垆而安厝。呜呼哀哉!昔二女妃虞⑧“虞”指“虞舜”,相传尧帝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为妻。见Bernhard Karlgren(高本汉), trans.:“The Book of Documents,”BMFEA 22(1950):第4页;Bernhard Karlgren:“Gloss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BMFEA 20(1948):第69——71页。有关尧帝两位女儿的更多材料可见司马迁:《史记》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第248页;David Hawkes(霍克思):“The Quest of the Goddess,” in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 ed.Cyril Birch(Berkeley: Univ.of California Press, 1974),第 56 页;Bernhard Karlgren(高本汉):“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BMFEA 18(1946):第296页;以及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149页。,帝道以彰,三母嫔周⑨“三母”指太姜、太任、太姒,分别是后稷、文王、武王的母亲。,圣善弥光,既多受祉,享国延长。哀哀慈妣,兴化闺房,龙飞紫极①“紫极”指帝王身份。,作合圣皇,不虞中年,暴罹灾殃。愍予小子,茕茕摧伤,魂虽永逝,定省曷望?呜呼哀哉!②陈寿:《三国志》卷五,第167页。
明帝展现对他生母尽孝的一个做法是,给予了母后家族成员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封赏,朝廷官员无疑也从明帝这种行为中得到启示,不断建议给甄氏追加一些死后的荣誉③陈寿:《三国志》卷五,第161——163页。。明帝即位后,郭后变成了皇太后,但明帝对甄后的善行并未延及郭后身上。如“裴注”引《魏略》所述:
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忧暴崩。甄后临没,以帝属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说甄后见谮之祸,不获大殓,被发覆面④这里是指她被匆忙下葬而没有举行适当的仪式。不仅她的尸体没有穿上合适的衣服放入棺椁,而且她的头发也没有进行适当地梳理。有关一般葬礼的准备,可以参看de Groot(高延):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volume 1。“大殓”指死者的入棺,包括给死者的穿衣阶段,见de Groot(高延):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volume 1:第6、331——342页。,帝哀恨流涕,命殡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⑤陈寿:《三国志》卷五,第166——167页。
相似的叙述内容还出现在“裴注”所引的《汉晋春秋》中:
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常怀忿,数泣问甄后死状。郭后曰:“先帝自杀,何以责问我?且汝为人子,可追仇死父,为前母枉杀后母邪?”明帝怒,遂逼杀之,敕殡者使如甄后故事。⑥陈寿:《三国志》卷五,第167页。
这两段文字跟《记》的内容显然有很多共同点:如《记》与《魏略》都提到,谗言与甄后之死有某种关联。又如,在《记》中现身与曹植见面的甄后之魂魄说过“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同样的叙述语言出现在《魏略》与《汉晋春秋》中,用来描述这种施加在甄后身上的非常规葬礼,《魏略》提到她在棺椁中“被发覆面”,《汉晋春秋》不仅提到她的散发,而且还用了跟《记》中一样的词断定被郭后“以糠塞口”。因此我们倾向于把《记》看作是直接或间接取材于这些历史传记小说中的一部分。
三
此外,关于甄后之死还有第四种版本,这个版本提供给了我们有关陈寿、裴松之史书撰写中的某些内情。相关内容见于王沈《魏书》,裴松之引述如下:
有司奏建长秋宫⑦长秋宫是一些皇后拥有的封号。见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第12b页;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第409页注。长秋是西汉时期处理皇后事务的官职名称,见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第734页。长秋宫建于后汉时期并成为皇后居所,见徐天麟编:《东汉会要》卷三十八,台北世界书局1971年出版,第405页。对“长秋”至少有两种解释,《后汉书》注认为,之所以用“秋”是因为这是指万物开始成熟的季节;另一种说法认为,之所以用“秋”,是因为皇后属“阴”,秋是阴之兴盛时节,见杨晨编:《三国会要》卷九,台北世界书局1975年出版,第163页。,帝玺书迎后,诣行在所,后上表曰:“妾闻先代之兴,所以飨国久长,垂祚后嗣,无不由后妃焉。故必审选其人,以兴内教。今践阼之初,诚宜登进贤淑,统理六宫。妾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寝疾,敢守微志。”玺书三至而后三让,言甚恳切。时盛暑,帝欲须秋凉乃更迎后。会后疾遂笃,夏六月丁卯,崩于邺。帝哀痛咨嗟,策赠皇后玺绶。⑧陈寿:《三国志》卷五,第161页。
与其他有关甄后之死的版本相比,这个版本在内容上显得尤为离奇,从中可以看出曹丕在他挚爱的甄夫人去世后显得非常悲痛,并在她死后很快追认其为皇后。针对同一事件存在不同甚至是矛盾的演绎(较早之前提到过的现象),《魏书》此处可谓是提供了一个相当完美的例证。
后代史学家一直对甄后之死的各种叙述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感到困惑。举例来讲,卢弼认为明帝对他生母的去世和葬礼似乎并不像《魏略》所述的那样一无所知,明帝生于建安十一年(206),到黄初二年(221)甄后去世,他应该是十六七岁的样子,不是懵懂无知的少年。①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第21a页。卢弼由此认为《汉晋春秋》的叙述较为合理且更容易接受,因为其中提到了明帝对郭后的憎恨。
不过,在一定程度上明显成为问题的是,陈寿在甄后之死事件中对郭后的某种叙事沉默。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发现这个问题的某些端倪。陈寿的写作受到了某种限制,我们或许不能读懂他当时的心思,但我们可以知道哪类事情是不受限的,即使他想摆脱它们。陈寿遇到的这个棘手问题在后代学者那里常被提到,现代史学家通常对陈寿表现出了某种同情,②例如,缪钺:《三国志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出版,第5——11页;缪钺:《陈寿与三国志》,载吴泽、袁英光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316——320页;Rafe de Crespigny(张磊夫):The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Centre of Oriental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no.9(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Centre of Oriental Studies, 1970),第 7——14页;Carl Leban :“Ts’ao Ts’ao and the Rise of Wei: The Early Years”(Ph.D.diss., Columbia Univ., 1971),第 19——29 页。《四库全书总目》对陈寿的《三国志》书目摘要中也作了部分回应:
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③《合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未收书目禁毁书目》第5册第10卷,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第17页;又见Leban:“Ts’ao Ts’ao and the Rise of Wei,”,第 24 页。译者按,作者此处引文出自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合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未收书目禁毁书目》,因译者手头并未有此书,无法核对原文,故此段引文译者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245页)中引出。
在甄后之死这件事上,陈寿没有提供合法性的质疑,或许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影响了他。例如何焯(1661——1722)曾指出,陈寿没有展开记录这些事情的细节,是因为郭太后的亲属在当时仍然具有影响力。④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注引,第21a页。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王沈《魏书》中的这段文字,《魏书》中的忠魏倾向(pro-Wei bias)或许是其对甄后之死与葬礼采取了不同于他处叙述的主要原因。⑤按,大多数学者认为《魏书》不可信,见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卷一,第16b页,载《古书目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缪钺:《三国志导读》,第3页;以及Leban:“Ts’ao Ts’ao and the Rise of Wei: The Early Years,”第11页;Kroll(柯睿):“Portraits of Ts’ao Ts’ao,”,第 120——121 页。裴松之征引《魏书》这段文字的原因是清晰的,他为《三国志》作注的目的之一就是准确地提供任何有关某个历史事件的不同叙述材料,这样读者可以自己作出判断。确实,裴注中出现的这些材料没有隐含他的态度。但实际上,裴松之有时也会批判地看待他从别处征引的材料,⑥见缪钺:《三国志导读》,第22——23页。在征引王沈《魏书》这段文字之后,裴松之加上了一条比较长的评论:
臣松之以为,《春秋》之义,内大恶讳,小恶不书。①《春秋》,儒家经典之一,据说是孔子亲自编定。是叙事极其简洁的编年史,但由于孔子、孟子等人对它的重视,《春秋》常被认为在一些历史事件的叙述上具有微言大义的特点。然而,近年来,《春秋》文本中“褒贬”信息的存在引起了学者的质疑。见 Stephen Durrant(杜润德):“Ching,”in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ed.William H.Nienhauser,Jr.(倪豪士), et al., 2nd rev.ed.(Taib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986),第 313 页。译者按,倪豪士(Nienhauser)这本著作的台湾版未亲见,译者手头有该书的美国版(Bloomington: Indiana Univ.Press,1986),经查找比对,杜润德(Stephen Durrant)对“经(Ching)”的解释位于第309——316页,其中涉及《春秋》的文字是在第313——314页。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史②译者按,作者原文中此处注曰:“魏史”意为“魏国史官”,但也提到也可理解为“《魏史》”。若以为大恶邪,则宜隐而不言,若谓为小恶邪,则不应假为之辞,而崇饰虚文乃至于是,异乎所闻于旧史。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陈氏删落,良有以也。③译者按,作者原文中此处没有注明引文出处,现补之,见陈寿:《三国志》卷五,第161页。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清楚看出,裴松之对甄后受曹丕和郭后迫害致死而且从未被册封为后是持有积极(认可)的态度,他对《魏书》的谴责之义相当明显。他更倾向于理解陈寿沉默不语的苦衷,当时机与场合都导致陈寿不能说出事情的真相时,陈寿只能自我克制不去创造出一个虚假的历史故事。
历史上甄后之死的故事,已成为了时间帷幕上的一个细小的褶皱,其中一些真相被隐藏了起来。但透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瞥见中世纪早期的两类史学家,他们出于自己的良知,在当时历史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尽他们所能地为后代留下了相对较为准确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