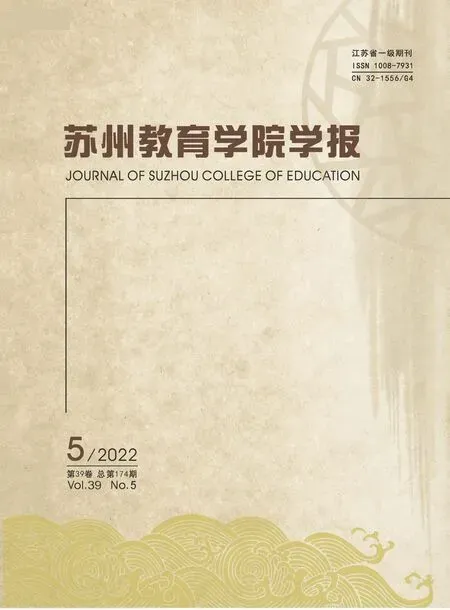1917年苏州新、旧剧团演出纠纷之考察
艾立中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清末民初,被称为“新剧”的西方话剧进入中国,对中国旧剧产生了重大冲击,新、旧剧之间的价值观冲突随即产生。《新青年》在1917——1918年开展了“旧剧评议”,当时北京大学的思想家们就新剧和旧剧的价值展开了讨论,他们对旧剧以及旧剧拥护者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提倡改良旧剧,鼓吹创造新剧,但当时人们对新剧的认识非常粗浅,因此,傅斯年认为“应当有个鼓吹新剧主义的机关”,“把新剧的组织,新剧的思想,新剧的精神,张旗擂鼓的道来,使得社会知道新剧是个什么东西,可就便于发展了”。[1]新、旧剧的理论论争的史料多见于报刊,今天的学者对此有充分的研究,但新、旧剧在演出市场上的竞争,乃至二者之间发生的纠纷,留下的史料却很少。苏州市档案馆珍藏的民国商会档案,展现了1917年11月苏州发生的一次新、旧剧团之间的演出纠纷。最终苏州总商会经过沟通协商,解决了此次纠纷。笔者梳理了这些档案和相关资料,对此次演出纠纷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并探寻纠纷背后的原因。
一、新、旧剧团演出纠纷的起因
苏州阊门地区自古就是繁华之地,但在经历了晚清民初各种兵祸之后,各业陷于萧条,1916年8月,商家向苏州总商会致函,提议在阊门开设剧场,以纾商困:
谨具略节事王瑞南等以阊门外马路向称繁华之地,如商云集,向有剧场原有三家之多,自从停歇之后,各业萧条。现当时局略定,地方安泰,各地剧场重见复活,商民等习此戏业,靠此糊口,现下聚资组织,欲思兴立剧场,重振市面,以苏民困,各业亦可望其转。……贵商会怜念商困,俯赐恩准,叩求玉函上达,务使各业复有气色,则商民等深感栽培之德矣,谨此上略。①《查复开设剧场》,苏州档案馆藏,档案号:I14-002-0013-001。
值得注意的是,提议开设剧场的都是经营茶酒、客栈的商人,而非戏剧界人士,这说明商人深知戏剧等娱乐业对拉动商业的重要作用。经过苏州总商会的沟通和争取,警察厅批准三家剧场在阊门开业,即民兴新剧社、春仙第一台和凤舞台。民兴新剧社于1917年4月成立,其前身是振市新剧社,专演新剧;春仙第一台演京剧;凤舞台专演髦儿戏①髦儿戏,即由女艺人组成的昆曲或京剧班社演出的戏。。起初,各剧团之间相安无事,虽然演出中也时有插曲,如民兴新剧社为了招徕生意,排演了新剧《玉蜻蜓》,此剧本源自苏州弹词,内容影射了申氏,故苏州的申氏后裔很早便向警察厅提起申诉,警察厅将《玉蜻蜓》列为禁演剧目,传令民兴新剧社停演。[2]但不久之后,就出现了剧团演出纠纷。
剧团演出纠纷产生的背景是当时新剧在苏州的上座率要好于旧剧,这不是偶然现象,全国很多地区也大致如此。新剧因贴近生活,传播新思想,表演样式活泼,故广受观众喜爱。在新剧的进攻下,旧剧颇显颓势。纠纷产生的直接起因是春仙第一台在演出中加入时装新剧,这种新、旧剧混演的形式直接冲击了苏州民兴新剧社的演出市场,影响了民兴新剧社的经济利益。因此,民兴新剧社于1917年9月14日致函苏州总商会,请求总商会协调解决:
民兴新剧社为限制春仙台等新旧剧混演事致苏州总商会函
谨肃者:窃商等前以振兴市面发展商业,集资合办民兴新剧社,呈经贵会核转警厅给照开演在案。伏查敝社所排各剧于社会风化可收默移潜化之功,故自开幕以来,深荷各界欢迎。乃有陈尧禄等复就阊门外开办春仙第一台演唱京戏,又有凤舞台专演髦儿戏,于呈厅领照之时曾经声明各不相犯,营业虽同,性质互异。讵第一台现已生意清淡,忽于京戏中加演时装新剧,敝社因其侵犯营业,即经向其交涉,双方订立合同,议定新旧剧限止办法。至凤舞台近更赴沪邀请民新社女子新剧来苏,夹杂于髦儿戏中,此种无谓之竞争,含有同行嫉妒之心,殊非振兴商业之道。况女子新剧,即沪上英租界尚且严禁,万一在苏演戏,殊与风俗有关。况苏州一隅三园林立,营业已勉为其难,若再同演新戏,必致均遭失败,不但于事[实]上有抵触之处,转失贵会维持提倡之初衷。素仰贵会主持公理,谨将敝社所蒙影响之损失情形沥陈钧鉴,应如何设法取缔、限止,新旧戏剧各不相犯之处,伏候核转警厅严行禁限,以维营业。无任屏息待命之至。谨上苏州总商会会长。
民兴新剧社经理张梯云、协理胡绣章谨启[3]
根据函文我们基本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苏州阊门地区的三家剧团最初都声称要保留各自的特色,在经营上互不侵犯。然而,为了维持生计,延揽顾客,春仙第一台在演出京剧的时候加入新剧,这引发了民兴新剧社的不满。民兴新剧社经过交涉,与春仙第一台议定演出新、旧剧的限止办法。但当凤舞台也去上海邀请民新社女艺人来苏演出,混演于京剧中时,问题变得更复杂了。民兴社认为三个剧团都演新戏乃“无谓之竞争”,“必致均遭失败”,并希望苏州总商会出来主持公理,保证“新旧戏剧各不相犯”。这些意见都是合乎实际的,也是亟待解决的。
民兴新剧社在函文中认为新剧女艺人来苏演出有伤“风俗”,显然是沿袭了封建意识。民国初年,风气日趋开明,女子新剧团在上海陆续成立,但新、旧思想交锋激烈,女子新剧团依然面临一定的阻力。1914年,“江苏省教育会前因女子新剧团有伤风俗,函请沪道尹查禁。杨道尹以开通女界知识,无登台演剧之必要,人数既多,流品必杂,确于地方善良风俗有碍,昨已分饬英法两廨查禁,解散以肃风纪云”[4],民兴新剧社函文所说的“沪上英租界尚且严禁”即与此有关。虽有禁令,但上海的女子新剧社并未消失,而是仍在演出,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作为一个接触、宣传新思想的剧团,苏州民兴新剧社所持的男女观念并没有真正跟上新时代,反映了民国初年文艺界处于新、旧思想杂陈的状态。
苏州总商会在当时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1904年,为了抵制列强资本的扩张,振兴民族工商业,清政府商部要求各地组织商会。商会在政府与商界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可以上达民情,下传政策,调和政府、商界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之间的矛盾。1905年10月苏州商会成立。由于苏州商业一直很发达,1916年苏州商会更名为苏州总商会。苏州总商会除了在商业领域发挥着主导作用,还协助政府管理社会文化领域,在苏州的消防、禁毒、卫生、赈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时随着新剧的兴盛、旧剧的改良,旧式的梨园行会的组织管理功能已不能适应新的演出环境,苏州原有的梨园行会——老郎庙——完全衰落,无法解决戏曲界新的诉求,而新的戏曲同业组织又尚未成立。因此,从1905年到1920年代,苏州总商会承担了戏曲同业组织的职责,包括管理戏剧演出市场,调解演出纠纷,沟通戏曲界、政府部门以及报界之间的关系,表达戏曲界的诉求,等等。加之,苏州总商会在1915年实现了各商家在阊门重开剧场的愿望,获得了剧团的信任。所以,调解苏州民兴新剧社与其他剧团的纠纷的任务自然落在了苏州总商会身上。
民兴新剧社除了致函苏州总商会,还向苏州警察厅呈文。按民国初年的法令,各地开设戏园要经警察厅批准,警察厅负责管理戏园的治安、消防、卫生、剧目审查。比如1916年10月31日《申报》登载苏州警察厅“取缔章程中有禁演淫戏,不准男女杂座,限晚间九时散场,桌椅排定不准多添一凳,并多开太平门,新剧底本须送厅审查各条,违则分别罚惩”[5]。
苏州警察厅厅长崔凤舞收到民兴新剧社的呈文后,又于1917年11月23日致函苏州总商会,请求其负责调解此纠纷:
迳启者:据民兴新剧社张梯云、胡锦文呈称,窃商筹集股开设民兴新剧社,遵章纳捐领照营业。惟阊门马路共有戏园三家,当由商会核议不能同一性质,禀蒙批准在案,足征维持商场并免冲突。阴历本月初三日阊区马路春仙第一台京戏馆停演,今日忽见门前悬挂化装游戏团改良新剧于初八日夜开演之牌,此即文明新戏巧立名目,同商等新剧社同一性质,与商会原案大相违背,理合据实禀明,伏乞恩准即行禁止,以维商业。等情。据此,除批示外,相应函达贵会,究竟有无此项议决成案,希即见复,以凭核办为盼。此致苏州总商会。①《江苏苏州警察厅公函》,苏州档案馆藏,档案号:I14-001-0583-075。
然而,从这份函文来看,崔凤舞厅长对如何处理新、旧剧演出的纠纷并无良策。警察厅只负责审查剧目是否涉及淫秽,以及剧场的治安等,新、旧剧混演纠纷涉及新剧和旧剧之间的表演差异问题,超出了警察的管理权限和能力。而且,崔凤舞也不清楚各剧团先前是否达成过演出协议,为慎重起见,他希望商会出面解决。苏州总商会在先后收到民兴新剧社和警察厅的函文后,开始着手处理三个剧团之间的纠纷。
二、新、旧剧团演出纠纷的解决与深层原因
在苏州总商会的调解下,民兴新剧社和春仙第一台、凤舞台达成了协议,副会长许祖藩、刘敬禳在1917年12月21日向商会报告了处理经过:
谨肃者:前由贵会所示警厅公函,因民兴新剧社与春仙第一台为新旧戏剧禀控纠葛,嘱为调和。当即邀同三家园主公同讨论,佥谓春仙当日虽有化妆游戏《琵琶记》戏单发出,而实未开演,姑不置论,惟戏剧一门,同类之戏新旧均皆演唱,何止数十出,如《红蝴蝶》、《新茶花》等比比皆是,对于戏名实在无从分别,故新旧界限惟有将剧员出身之新旧为区别,嗣后新剧社中不得用旧剧员,而旧剧班中亦不得用新剧员,照此解决,尚属简易平允,民兴新剧社与春仙第一台暨凤舞台三家亦均意见相同,各无异议,愿共遵守。与官厅批定成案不得同一性质,亦属相符。窃惟苏地表面虽称商场,寔则市面衰颓,迥非昔比,即照定案三家戏园,已觉亟亟难支,新旧争执未始非营业各不发达之原因。现在惟有遵照成案,准开三家,不得同一性质,区别分明;以后无论何人,均不准再为添设,亦为根本解决之一法,庶于浮华场中略加限制。是否有当,请转咨警厅备案,俾使永远遵守,以息争执。谨复总商会正会长鉴核。①《许祖藩等为报告调处民兴新剧社与春仙台纠纷情形复苏州总商会函,查复新旧剧争执由》,苏州档案馆藏,档案号:I14-001-0583-077。
细读上述函文,我们可以感受到苏州总商会为解决此纠纷是颇费心思的。首先,从剧名的新旧来解决纠纷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很多热门题材被新剧团和旧剧团竞相采用,《红蝴蝶》本来是一出文武齐全的新编连台旧剧,学习话剧的布景,内有真刀真枪、真火烧屋的表演,有较好的票房,《申报》曾报道苏州1916年12月16日振市新剧社编演《红蝴蝶》。《新茶花》本为新剧,也被旧剧家所改编。其次,通过限制新、旧戏班的演员出身来解决纠纷的办法为大家所接受。“新剧社中不得用旧剧员,而旧剧班中亦不得用新剧员”属于一种简易可行的处理方法,艺人是剧社的关键因素,管住了艺人,很大程度上就保证了各戏园的性质,并强调“以后无论何人,均不准再为添设,亦为根本解决之一法”。
苏州总商会完成了本次演出纠纷的调解之后,于1917年12月27日给苏州警察厅复函:
迳复者: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接准贵厅公函内开:全叙云云等因。遇会。准此,查阊门马路前于上年禀请开设戏院者有一二十人之多,当奉镇守使、道尹批交本会查核情形妥协复夺,是经本会查明向有剧场三处,复奉核准,应即以此为限。并以男女混合演剧内地风化攸关,函请一并取缔。各在案。此外并无不能同一性质之议决成案。准案前因,即嘱本会会董调查理处去后。兹据许董、刘董复称,云云等情。前来。察核所议尚属平允,既据声称该三家愿共遵守息争,相应函复查照,备案为荷。此致苏州警察厅。②《复警察厅公函,查复新旧剧争执由》,苏州档案馆藏,档案号:I14-001-0583-077。
自此,苏州总商会的调解终告完成,函文所谓“并无不能同一性质之议决成案”回答了警察厅致商会的疑问,说明当时总商会并没有规定各剧团演出的性质,至于民兴新剧社所说的“于呈厅领照之时曾经声明各不相犯,营业虽同,性质互异”,可能是剧团之间的口头约定,并未落实到具体文字,民兴新剧社也没有预料到会出现新、旧剧混演的情况。至于总商会以风化为理由要求取消男女合演,反映了当时苏州地界还存在浓厚的保守气氛。苏州新剧的演出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当时有报纸反映,一些无良男子自称是新剧中人,在游艺场所哄骗良家妇女,导致苏州民兴新剧社名誉扫地,经营日益困难。[6]
苏州新、旧剧混演纠纷的深层次原因是值得探讨的。前面副会长许祖藩、刘敬禳在给苏州总商会的调解报告函中指出,此次新、旧剧混演纠纷的实质是“市面衰颓,迥非昔比”,“未始非营业各不发达之原因”,这一结论是比较客观的。如果我们将同时期的苏州和上海的演出市场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当时苏州演出市场确实不发达,观众数量有限,有竞争力的戏园不多。这与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苏州自古繁华,很长时期内是全国戏曲重镇,职业剧团和家班分布于全城,很多昆剧艺人从苏州走向全国各地。近代以降,苏州和上海两座城市的经济、文化地位发生了巨大改变,产生了巨大差异,上海跃升为晚清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吸引了全国大批艺人;而苏州本地,无论是旧剧还是新剧,都缺乏全国当红艺人。苏州虽为昆剧故乡,但当时很多昆剧艺人纷纷前往上海发展,本地的昆剧演出已经衰落。苏州的京剧也不发达,戏园为了增强竞争力就从上海聘请名角,这自然也增加了戏园的成本。为了保障各戏园的利益,规范各戏园的演出性质,避免不当竞争是唯一的办法。
从戏剧艺术的本身来看,新、旧剧混演是因为当时不少戏剧界人士对新剧和旧剧的艺术本质都缺乏深刻的体察,对戏曲的改良缺乏一个系统完整的计划,要么制造对立,要么简单拼接。一些戏园主和艺人为了追求票房,吸引新老观众,将新、旧剧简单拼接,造成了新旧杂陈、不中不西的状况,忽视了不同戏剧之间的特点。当时很多文明新戏的一个明显弊端就是“话剧加唱”,是戏曲和话剧的杂烩,这段时间也是中国话剧发展、戏曲改革历程中一个不成熟的时期,是艺术发展过程中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演剧市场中活跃着一批新、旧剧兼擅的艺人。1912年9月23日上海新剧促进团演出《江皖革命史》,声称“除本(团)合体演员登台外并请新旧剧大家合演”[7]。这实际上也是新、旧剧混演。各戏园对这些新、旧剧兼擅的艺人非常欢迎,一是可演剧目多,二是可减少演员成本。从《申报》当时刊登的广告来看,上海在民国初年出现了“著名文武小生新旧剧花旦青衣赵君玉”[8],“新旧剧生夏月珊,新旧剧旦周凤文、邱治云、邱沁如七本《三笑姻缘》,八本《三笑姻缘》”[9],“丹桂第一台敦聘南北著名文学大家新旧青衣花旦欧阳予倩”[10]——欧阳予倩学过京剧,也会演新剧,又懂理论,颇受观众欢迎。
新、旧剧混演与新、旧剧兼擅艺人的出现是新、旧时代转变的特殊现象。清末民初各戏园之间的激烈竞争需要戏园主有创新思维。戏园主聘请通晓新、旧剧的艺人,可以借此作为招揽观众的广告,势必增强戏园竞争力。包括苏州在内的各地戏园主对新剧和旧剧混合表演并无成见,他们只追求演出利润,哪种表演赚钱,他们就欢迎、支持哪种表演,常常会带来一些新鲜的表演形式。苏州凤舞台聘请上海新剧艺人来苏州演出,这对苏州的本地艺术有促进作用。不少艺人和观众开始顺应时代,打破新、旧剧之间的壁垒,对新、旧剧的认识逐步从对立转向融通。新、旧剧兼擅的艺人也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但当时很多学者对这一现象缺乏认识,落后于实际。只有少数戏评家持一种相对平和、公允的态度来看待新、旧剧之间的竞争:“夫新旧剧之魔力入于社会人心之深浅,其资格各有不同,兹姑置弗论。即就戏论戏,各举其足以号召座客之优点言之,旧剧亦有其天然自存不可消灭之处”[11],“苟新剧日兴,旧剧不但不至消灭,且因受此激刺而愈益进步”[12]。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些认识极富眼光,旧剧在话剧的刺激下不断改良,话剧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一些旧剧的创作和表演之优点。我们过去夸大了新、旧剧之间的冲突,而真实的情况是,新、旧剧在演出过程中既有冲突,又有融合,戏剧实践远比戏剧理论丰富得多。至于实践中如何更加符合艺术规律,一代代戏剧人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申报》在20世纪30年代初到抗战前还在宣传“新旧剧家”,比如汪优游(汪仲贤)和张国斌等,但汪氏此时年龄偏大,已成明日黄花,被演出市场冷落。新、旧剧兼擅、拥有很好叫座能力的艺人已基本消失。从戏剧的发展演进过程来看这是必然的。“五四”以后,随着话剧剧目日渐丰富,表演趋于职业化,话剧艺术开始成熟,话剧对演员的文化素养、表演技巧的要求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旧剧尤其是京剧流派艺术日臻完备,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旧剧对艺人各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新、旧剧兼擅的艺人不再出现,新、旧剧混演的现象也就消失了。新、旧剧开始了各自的艺术探索,但在艺术上并没有对立,而是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新、旧剧兼擅的欧阳予倩日后为戏曲现代化、话剧民族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苏州的新、旧剧团演出纠纷的解决让我们看到了苏州总商会的重要作用。虽然这次剧团纠纷在当时全国的剧坛上没有产生影响,但却是现代戏剧演出史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我们通过此案例既可以管窥民国初年苏州剧坛的生态,又可以考察民国之初新、旧剧之间的对立、混演与新、旧剧理论之争的关系,从而使戏剧史的叙述更加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