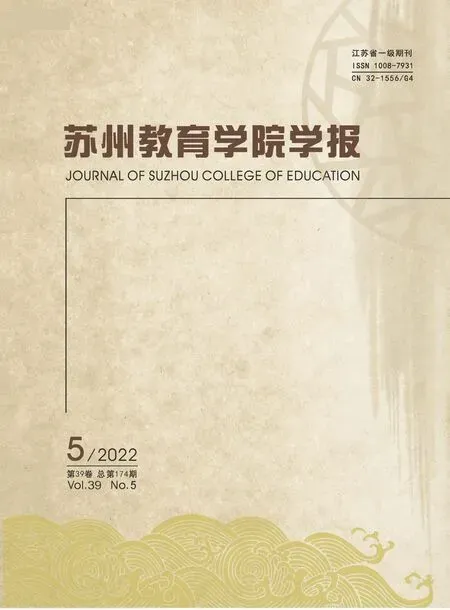为大众而写:文学史的另一种可能
——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略》
石 娟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2020年12月,由范伯群先生领衔,徐斯年先生、刘祥安教授共同参与完成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25]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18万字左右的体量,回答了如上问题:文学史还有另一种可能——为大众而写。
一、“崇尚浅薄”:为普通人而写的小说史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牵头,在大型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编撰工作中,苏州大学①时名江苏师范学院。现代文学教研室承接了《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卷的编撰任务。自此,范伯群先生开始走上了他本人乃至苏州大学文学研究的转型之路。至2017年12月去世,近四十年,范伯群先生带领苏州大学研究团队从史料开掘和文本细读入手,从作品、作家到社团流派,再到文学史书写、文化研究,分别于2000年、2007年、2017年完成了通俗文学研究“三书”②徐斯年先生认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卷)、《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上、下册)是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三个标志性事件”,“《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出版,历经二十年辛苦;《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的出版是巍然巅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上、下)的出版为通俗文学研究的未来开辟了新局,也体现着他对第三代弟子无微不至的关爱”。参见徐斯年:《怀念范伯群先生——兼谈范伯群先生的中国通俗文学研究》,《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34——41页。:《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卷,江苏教育出版社)③该书于2010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再版,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新版)》(上、下卷)。、《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上、下册,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这些不同时期分阶段、系统性的研究实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史观重构和研究空间的拓展。
作为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三个标志性事件”[26],范伯群先生及其团队在写作过程中陆续提出以“摒弃雅俗,崇尚经典”为思想方法,构建多元文学史观。从新文学转向通俗文学研究,继而为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正名[27],并确立《海上花列传》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28];从“双翼齐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29]到“多元共生”的文学史[30],再到“冯梦龙——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小说”的中国古今市民大众文学链[31]的提出;从“鸳鸯蝴蝶——礼拜六”派[32]、“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33]到“市民大众文学”[34]等概念的确立,再到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的互文研究[35]……在研究的不同阶段,针对研究界的关切问题,对于理论界的棘手问题,范先生总是勇于接受挑战,并以新颖丰富的史料和别具匠心的论证结构,得出令人耳目一新、逻辑谨严的开拓性结论。同时,与海外汉学研究特别是北美的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对话,这样的意识,在范先生的第一部通俗文学史研究专著《礼拜六的蝴蝶梦》中,已有极为直接的表达。在治学中,范先生时时处处流露出其学术研究的“才华”[36],而这一“才华”,自1962年他与曾华鹏先生合作的《蒋光赤论》[37]问世,历经半个多世纪,至《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略》体例的设计及写作,一以贯之。这既是范伯群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追求,亦是其研究的特色。在2013年《填平雅俗鸿沟——范伯群学术论著自选集》出版时,严家炎先生称赞范先生“知道鸳鸯蝴蝶派名声不好,受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去着手研究,这是要真正有点勇气、有点眼光的,不仅要有科学的头脑,而且要有坚毅的精神才能做到”[36]。
相较于通俗文学研究“三书”的厚重,《史略》显得轻盈、小巧了许多,根本原因在于该书最初是为“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而准备的。正如策划者章俊弟先生的回忆,范先生首先考虑的是“外译”的接受策略,即怎样使国外的普通读者关注《史略》。经与编辑沟通,范伯群先生确立了文学史书写的“通俗化”方向,为此他做了三方面工作:
一是确立文体,以小说体裁为中心。范先生认为,“通俗文学的最大成就还是小说。抓住小说,也就抓住了通俗文学的主体,抓住了通俗文学的核心”①见章俊弟:《以通俗文学的名义——范伯群先生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略〉的选题诞生和外译立项》,参见本期。。由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的研究专著十分缺乏,因此,《史略》以小说为主体,不仅抓住了通俗文学的核心,从文学史坐标来看,亦弥补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书写的空白。
二是强调“浅显”,甚至要“浅薄”。在《史略》的书写过程中,范先生选择以通俗小说的趣味生动消弭国外普通读者的陌生感。因此,在与编辑和合作者沟通的信件中,他多次强调《史略》的书写要“浅显生动”②同①。、“崇尚浅薄”③见笔者对徐斯年先生、刘祥安教授的采访整理稿:《徐斯年、刘祥安:范伯群先生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略〉》,参见本期。,期冀外国读者能够对中国通俗小说产生兴趣,促使他们进一步阅读和研究。④据章俊弟先生回忆,谈及《史略》的书写要“浅显生动”的理由时,范先生说:“这是给外国普通读者看的,如果他由此对中国通俗小说产生兴趣了,他可能就要回去学中文了,然后找中文著作来研读了。我们这里有的是大部头中文书等着他们呢!”见章俊弟:《以通俗文学的名义——范伯群先生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略〉的选题诞生和外译立项》。当然,范先生强调的“浅显”“浅薄”并非无深度无章法的铺陈,而是融入了既有学术研究成果的“浅出”。
三是严格控制字数。学术著作原本不必考虑字数问题,资料越翔实、论述越严谨、阐释越丰富,越能造就一部理想的著作。范先生主编或撰写的通俗文学研究“三书”均体量庞大,但如果将全书翻译成外文,难以实现。同时,对于普通的外国读者而言,译著的厚度亦会直接影响他们的阅读感受。注意到这一问题,考虑到范先生的年龄和身体状况,编辑章俊弟先生建议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删节,然而为了保证全书体例的完整,范先生果断决定重新写作,同时希望尽力控制著作的篇幅。可是,学者写“大书”容易,写“小书”难。对于“小书”而言,能否以精巧的结构、精练的文字处理好内容和学术观点,能否“小中见大”,对学者是极大的考验。《史略》在有限的文字里,不仅要讲清楚小说的故事情节,还要深入浅出地阐述有价值的学术见解,对撰写者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对时年已87岁高龄的范先生来说,亦是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考验。为了保障全书字数不失控,在项目组最初分配写作任务时,范先生即已拟定好各章的字数,⑤范伯群先生2017年4月15日致章俊弟、周敬芝两位编辑的邮件。见《徐斯年、刘祥安:范伯群先生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略〉》。并计划将全书总字数控制在理想的15万~18万字之间。他以身作则,对字数的控制近乎精确⑥范伯群先生2017年5月16日连续两次致信徐斯年先生和刘祥安教授:“……我再三约束。记得我们原定6千字,现在却超了4百多字。真是没有办法。一是你们看看这样写内容是否可以;二是是否还有压缩的余地。”“出版社规定的15万——18万字是不大可能完成全书的。现在想请你们看看,一是内容这样写老外是否能看得出这是一部杰作;二是从此内容中还能删去那(哪)些情节。现在是超了400多字。”见《徐斯年、刘祥安:范伯群先生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略〉》。,却又能从翻译接受的客观情况出发,对徐斯年先生撰写的《蜀山剑侠传》“网开一面”⑦据徐斯年先生回忆:“《蜀山》这篇字数超过许多,我向范老师作了说明并致歉,他说:这样的作品,评介文字少了不行,可以超的。”见《徐斯年、刘祥安:范伯群先生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略〉》。。范先生宽人严己的学术品格、严谨认真的学术作风、变通豁达的学术智慧,点点滴滴,都镌刻在这些细节里。
二、“讲故事”:由“史”向“文”的调整与回溯
作为一种小说叙事传统和文学研究体例,无论是书会才人、作家的创作,还是学者的历史叙事,“讲故事”都是一种基本的方法,亦有其不可忽略的功能。在中国小说创作中,无论长篇还是短制,故事情节一直是基本的叙事要素。至晚清报刊出现,“连载”彰显了“故事”的叙事功能,虽遭遇所谓“五难”的批评①《〈新小说〉第一号》载:“……名为小说,实则当以藏山之文、经世之笔行之。其难一也。……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往往不能相容。其难二也。……今依报章体例,月出一回,无从颠倒损益,艰于出色。其难三也。……此编既按月续出,虽一回不能苟简,稍有弱点,即全书皆为减色。其难四也。……不得不于发端处,刻意求工。其难五也。”载《新民丛报》第二十号(1902年)。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56——57页。,却也令长篇章回体小说的面目为之一新。张蕾将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定义为“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38]并予以系统考察,即是对“故事”在现代章回体小说中的叙事功能的进一步确认。从“讲故事”到“写小说”,“自觉把写作对象定为‘读者’而不是‘听众’”,是晚清以来“写故事的人”实验各种叙事可能的根由、基础和背景,更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发生转变的历史契机。[39]用文字“讲故事”者,一般多为“文士”,旨在创作,用以娱人或自娱;而文学史学者多为“专门家”,他们对小说的分析阐释、整理源流,很少以“讲故事”作为著述的核心,这主要与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学史写作观念有关。林传甲所开辟的百余年的文学史传统,重在科学主义的“史学”训练,强调史实,讲求客观、持正、公允,文、史两分。而长久以来的史学训练,使得文学史书写侧重于考证史实、阐释理论和建构史观,在此过程中,“史”的分量越来越重,“文”的要求却有所忽略,文学史特有的“文”的艺术感觉日渐消弭。正如李剑鸣先生所言,像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那样的“文史交融”的经典著作,已多年未见,这其实是百年文学史不断学术化、科学化进程中付出的代价之一[40]28。至于对史学书写中“文”与“史”的关系和功能的调整,李剑鸣先生指出:
目前的家装建材配送市场秩序很不规范,普遍存在配送时效差以及货损率高的情况,配送成本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家装企业必须规范其配送模式,加强对与配送相关的供应商以及承运商专业配送人员的管理,与对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且不断地进行优化,提高效率和效益,在降低配送成本的同时,努力实现供应商、企业、消费者三者共赢。
就史家的修养而言,“文史不分”则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策略。良好的文学修养和高超的文字技巧,有助于提升史学著述的质量。……不同层次的史学著述,对文字的要求并不一样:通史性、综合性和通俗性的史学作品,应当在遵循专业标准和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讲究文采和故事性;而专题论著则以材料和论证为重,必须大量引证和分析,在内容方面通常缺少故事性,也不便过于讲究辞章。[40]28-29
事实上,中国小说批评长期以来遵循着“话体文学”的传统,其中的一种即以“小说话”的形式进行文学批评。“小说话”中的“话,即故事”,遵循黄霖教授在《历代小说话》中的界定,小说话的“基本特点是以笔记体、随笔型、漫谈式为主要表现形态,或录事,或论理,或品人,或志传,或说法,或评书,或考索,或摘句,品格各异,丰富多彩”[41]。受限于学术传播的“读者期待视野”,学者如何在文学史叙事中向普通读者“讲好故事”,特别是厘清当下读者已经十分陌生、但又体量庞大的近代以来长篇小说的故事内核,处理好表达学术观点与叙述小说故事之间的分寸感,无疑十分考验学者的学术智慧,亦有着相当的挑战。考虑到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数量众多、篇幅普遍较长,动辄几十万字,研究者的阅读工作量巨大,如果仍然延续学界的科学主义历史书写惯性,恐怕很难引发一般读者的兴趣。
作为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的“启蒙”读本,《史略》遵循了“少讲理论,多‘讲故事’”的原则,采用“夹叙夹议”的笔法,合作者徐斯年先生和刘祥安教授亦将“讲故事”的原则贯穿始终(这也是本书在三人合作的方式下写作风格相对统一的保证②见《徐斯年、刘祥安:范伯群先生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略〉》。)。文学史家化身为纸上“说书人”,笔法与“小说话”十分相似,但具体的写作事实上并不容易。在撰写《李寿民和〈蜀山剑侠传〉》时,徐先生的初稿写得比较学术化,他依据会议论文《修仙者的爱——〈蜀山剑侠传〉里的“情孽”》一文撰写了《蜀山剑侠传》一节,提交给范先生审读,并为字数超过计划致歉。读后,范先生对《蜀山剑侠传》字数超出并不以为意,还非常体谅地指出“这样的作品,评介文字少了不行”①见《徐斯年、刘祥安:范伯群先生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略〉》。,但感觉徐先生行文学术性太强,建议他“以‘讲故事’的方法写”,同时在回信中将自己完成的《海上花列传》供徐先生参考。如何用“讲故事”的方法做好《蜀山剑侠传》的文本叙事,令徐斯年先生感到为难②在2018年4月17日给笔者的回信中,徐斯年先生称:“现在在憋范老师留下的一份作业——以‘讲故事’的方法写《李寿民和〈蜀山剑侠传〉》,很难写,我在考虑是不是放一放……”,直到范先生离世半年多后,经过长时间的揣摩,徐先生方才动笔。他考虑到《蜀山剑侠传》作品中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正是‘中国特色’,也是国外读者感兴趣的东西。所以对于有些内容(例如‘元神’‘情孽’)没取回避策略,而是在‘讲故事’中加以解释”③同①。。不难看出,“讲故事”是范伯群先生构筑《史略》的核心方法,亦是本书不可让步的原则,但对这一方法的选择,除了对学术传播中“读者期待视野”的考量,亦其来有自。
陈平原先生指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之所以备受肯定,多由其“辑佚稽考方面功力深厚成绩突出”[42]18而来,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难以逾越”,却是“在其史识及其艺术感觉”。[42]30这份“史家的精细准确的艺术感觉”[42]36,即表现在《中国小说史略》每一章各类小说的讲述及赏析中。如叙完《金瓶梅》全书故事时,鲁迅不禁赞叹: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43]187
区区百余字,无论是“洞达”“条畅”“曲折”,还是“刻露而尽相”“幽伏而含讥”,不动声色间,字字动人。鲁迅在序中称,《中国小说史略》因“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43]4。史家的“文采与意想”使其在“讲故事”时并未因文言而受限,反而因其炼字功夫,尽数传递出“敏锐”的“艺术感觉”[42]48。
早在1987年,范伯群先生曾专门谈及文学鉴赏的技艺,强调“文学鉴赏是在‘有法无法’之间”,从“点滴心得起步,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44]其中的“点滴心得”,即在讲述小说的故事内容时,亦关注读者的情感体验,这在《史略》一书中有很明显的体现。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一节中,范先生对王莲生的遭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
王莲生的一声长啸般的叹息比张惠珍的干号更为震撼人心。他一而再地要将自己真诚的爱施于这两个女子,但得到的回报却是一次次的心碎。我们觉得他既“窝囊”又“真诚”,更“可怜”。他离开了不堪回首的上海,去江西找寻他的新生活。当他离开这万家灯火的上海时,他带走的只是一腔“垂泪的凄清”。[25]10-11
王莲生的“长啸般的叹息”,在范先生的笔下,成为“故事之外的故事”。“讲故事”的历史叙事,统摄全书的“艺术感觉”,有生动的口语,有对世情的关切,亦有对角色的体贴,这就与“科学主义”“零度情感”的文学史书写发生了显著的差异。《史略》以“讲故事”为写作原则,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着重分析了“文”的情感体验,注意文本分析的艺术感觉,实现了从“史”到“文”的回溯,其初衷虽然仅仅是便于海外读者的阅读,却在无意中向《史记》所开启的历史书写传统致敬。从这个意义上说,《史略》首先从笔法上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实现了接榫。
三、“独立的准备”:接续与发展《中国小说史略》
每一部产生影响的文学史,都有其内在的学术谱系,更有责任者独立的价值选择和评判。当年陈西滢曾质疑《中国小说史略》“剽窃”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著作,鲁迅先生坦然直面①鲁迅在发表于1926年2月8日《语丝》周刊第65期的《不是信》一文中,回应陈西滢对其“整大本的摽窃”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指责时称:“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此处借用其说。:“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45]陈平原先生认为,鲁迅先生的“独立的准备”是“一种相当严谨的著述态度”[42]26,他的著作由于“从理论设计到史料钩沉”的“独立的准备”,“远比盐谷书精彩”[46]。而范伯群先生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从史料的搜集到小说文本的分析,从作家和流派的考辨,到史观的建构和文学史书写,亦始终有着“独立的准备”。
如前所述,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至2017年去世,范伯群先生都在为通俗文学撰史。可贵的是,如同金庸15部小说的创作从不重复已有套式,范先生所编、所撰的每一部文学史亦各具慧心。《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以类型小说为体例,《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以读者为中心分期,《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则侧重于文化研究转向。体例关系到文学史写作的成败,而史观则是体例的内核。范先生的文学史体例展现了他的自觉意识——不人云亦云,不重复自己,因形就势,决不盲从,虽然各有丰姿,却都被统摄在“多元共生”的文学史框架之内。因此,尽管《史略》的目标读者是非中国文化语境的国外普通读者,尽管写作过程中不断强调“浅薄”,但事实上该书另有“巧思”:它承续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时代为经”[47]、以小说类型为纬的写作原则,发展出“时代与类型互为经纬”的小说史体例——“从宏观上看,由‘开山之作’到‘新市民小说’是一个继时程序;从微观看,每一类别内部又有一个继时顺序”②见《徐斯年、刘祥安:范伯群先生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略〉》。。从书名到体例,均不难看出《史略》与《中国小说史略》的承继关系,但在时间上将小说史书写下延至1949年。因此,本书完全可以视为致敬《中国小说史略》之作,亦是根据时代特征的发展之作。③范伯群先生在2017年4月15日致章俊弟、周敬芝两位编辑的邮件中,专门解释了《史略》与《中国小说史略》的关系:“先是讨论这部书的书名。有两个书名可以选用。一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简史》,二是《清末民国通俗小说史略》。讨论后,一致同意用《清末民初……》为好。只写到1949年,‘现代’这个词汇似乎只有中国专用,因为中国多了一个‘当代’,而在世界上并不通行。这部‘史略’实际上是接着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写下去。”从全书章节、体例乃至字数的设计,均可以看出本书“独立的准备”之充分:
我们初步计划分如下类型与章节:一、绪论(约七千字),二、《海上花列传》要独立成为一节,因为它是现代通俗小说的标志性的开端(约八千字),三、社会小说类型,选了三部作品: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和上海春秋④按:应为“《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和《上海春秋》”,此处为范伯群先生致刘祥安教授邮件原文,尊重史料的原始性起见,标点符号错误不作改动。以下邮件引文同。,(二万字),四、哀情小说、社会言情小说、新狭邪小说类型相近,连着写。哀情只选玉梨魂、社会言情选恨海(不选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个重要作家就选恨海,因为也有论者认为此书是社会言情小说的开端)、李涵秋、张恨水、刘云若、秦瘦鸥(共三万五千字),新狭邪小说选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和何海鸣的倡门红泪包括何海鸣的优秀短篇小说,(约二万字),五、武侠小说选向恺然、姚民哀、李寿民和王度庐(三万字),六、历史宫闱选孽海花、蔡东藩和杨尘因的新华春梦记(二万字),七、幽默滑稽选徐卓呆、程瞻庐、耿小的(二万字),八、侦探小说选程小青与孙了红(一万五千字),九、幻想小说选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传、吴趼人的新石头记,这两部都是清末民初的,再要选一部民国中后期的,待定(一万五千字),十、雅俗融汇的新市民小说,选张爱玲、北极风情画和风萧萧(二万字)。这样相加约二十一万字。如果再有必要的膨胀,至多控制在二十三万字以内。这是最高限度了。我们从2017年5月1日算起,一年内完成,即2018年4月底。中间还要请译者与我们碰一次头,因为李寿民的玄幻武侠较难译,要特别关照一下。①范伯群先生2017年4月15日致章俊弟、周敬芝两位编辑的邮件。见《徐斯年、刘祥安:范伯群先生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略〉》。
全书的终稿,除了幻想小说部分由民国中后期小说改为民初支明的《生生袋》之外,最后出版的书稿目次,几乎与范先生的设想和布局完全一致,不难看出《史略》的缜密与科学——篇章布局,乃至每一章的字数,都得到近乎精确的设计。成竹在胸的文学史谱系,是《史略》得以如约完成的坚实保障。
事实上,所有精心结撰的文学史,都有其独特的体例创制,在史料和史观方面均会有“独立的准备”,但如前文所述,这些文学史著作习惯于以论代述,在形式上均十分“严肃”,功用也殊途同归——供学术研究和高等院校专业教学使用。那么,在书写形式上,文学史是否可以跃出门墙,探索更多可能?
2022年2月,王德威先生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文版问世,以其“方法论实验”色彩[48]在学界迅速引发关注,其体例与学院派文学史著作有着十分显著的差异。在设计之初,编写者首先考虑的也是读者的接受——“原本设定的对象为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化怀抱兴趣的读者”[49]序ⅲ,亦同样遭遇了《史略》所预想的困境——“在不同语境下,许多中国文学论述里视为当然的人、事和文本必须‘从头说起’,而西方汉学界所关心的话题和诠释方法往往又可能在中国学界意料之外”[49]序ⅲ。为了“自觉地凸显文学史的‘文学’性,以期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历史书写”,《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全书以单篇文章构成,风格包括议论、报道、抒情甚至虚构,题材则从文本文类到人事因缘、生产结构、器物媒介,不一而足。……出版体例每篇文章以2500字(中文译为4000字)为限,篇首以某一时间作为起发点,标题语则点明该一时间的意义,继之以文章的正题”。[49]序ⅱ全书的出发点和对字数的自觉约束,与《史略》十分相似。引人注目的是《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设定的文学史起始时间别出心裁:起点为1635年——杨廷筠《代疑续编》以“文学”二字“指称诗文、史书、论说,包括古代圣贤格言等文字艺术”之时[49]41,终点则为2066年——韩松的科幻小说《火星照耀美国:2066年之西行漫记》中的虚拟时间。这样一种设计无疑相当大胆,亦别开生面。但《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初衷毕竟是为了“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化怀抱兴趣的读者”,也就是说,这些读者对中国文化已有初步的了解,因此,全书以文本研究为体、以所涉事件发生时间为脉络的书写体例,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深化认知。相比之下,《史略》则是为对中国可能几无了解的西方读者书写的“中国故事”,因而特别强调要“浅薄”。
四、结语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为“普通人”而写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略》与《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相继出现,事实上共同昭告了一个基本事实——文学史书写可以也应该具有更多的“可能性”。文学史不再是少数人的“权力”,它可以很“学术”、很“严谨”、很“刻板”地高居于学术庙堂之上,亦可以很“文学”、很“故事”地走向民间,成为每个普通人走向文学的“圣经”,使更多普通人找到进入中国文化的“门径”。同时,呼啸而来的“碎片化阅读”亦使文学史面对更艰巨的挑战,其书写亦受到深刻影响——文学史不仅可以很“个人”,更可以从“建构”走向“解构”,从严肃走向“好看”,它是开放的、流动的,有着更多的可能和面向。因为,它本就来自“街谈巷议”,是记载“引车卖浆者流”的故事的历史,亦是“我们进入中国历史、文明、文化的一种方式”[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