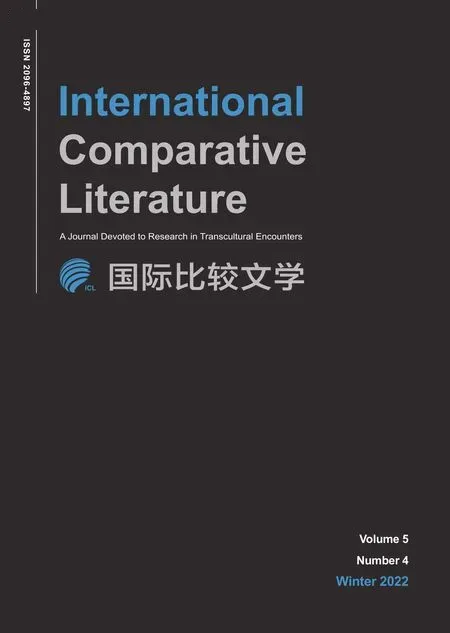惊鸿一瞥四十年
——李永平专访文学人类学创会会长萧兵先生*#
李永平 陕西师范大学
萧兵 淮阴师范学院
一、文学人类学的起航与路径
李永平(下文简称“李”):萧先生,您好!文学人类学已经走过了近40年历程,该学派立足本土,在跨文化、跨学科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围绕文学人类学理论或直接受文学人类学理论支撑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达11 项。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先后筹办文学人类学研究刊物。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从教40年以来,您的研究成果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创会会长,您见证了文学人类学近40年的学术历程,首先请您谈谈自己的学术历程和生命体验。
萧兵(下文简称“萧”):我的学术之路与人生最大的变故紧密相关。在此之前,我已经在《文艺报》和《上海文艺》发表《宋江论》《贾政》《电影剧本的银幕体现》《论电影〈宋景诗〉》等数十篇有影响的论文,还在《解放日报》开专栏撰写《唐诗采句》。可惜我被打成右派后,连最基本的学术研究条件都没有了。更为不幸的是在劳动中,我不慎失去四个手指,但即便如此,我依然没有停止过学习。1977年,淮阴师专复校,招纳贤才,提出要把我调来。当时,还在运输队跑供销的我开出了一个“天价”:一要学校出钱让我办一个刊物,二要给我一套房子。当时的学校领导还是力排众议,拨款一万元让我办一个刊物,以给刊物编辑部办公室为名给我这个单身汉一套房子。从此,萧兵主编的《活页文史丛刊》诞生了。它团结了国内一大批文史专家学者,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文章,成为当时一个学术品牌。
可以说,从我被定为右派到得以平反间的20 多年是自己默默学习的沉潜期。当我被聘为淮阴师专教师之后,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同时也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出版著作。这才终于让自己的知识积累、学识才能得以发挥。
自1978年以来,我连续发表论文300 多篇。因此,学术界当时流行“世上有签皆沫若,天下无刊不萧兵”的说法,甚至学界将我的学术文章惊呼为“萧兵现象”。我的著作有《楚辞研究》系列七种,《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四种,《中国小说的人类学趣读》系列四种,《中国文化的精英》《傩蜡之风》《神话学引论》等总计近40种;其中论文集《黑马》等五种由台湾时报文化公司出版。我也曾应邀赴中国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地安纳大学、加洲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国内外30多所高校和学术机构讲学、访问。
我的履职经历也能为我的人生体验提供注脚:自己历任上海海军预备学校教员、淮阴县农民、淮阴市文联编剧、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华中师大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社会调查所人类学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分会会长、江苏省淮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李:谢谢萧先生的分享。我知道您主要研究《楚辞》,出版了《楚辞与神话》(江苏古藉出版社,1987年版)、《楚辞新探》(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楚辞的文化破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王子今、李时人先生都撰文评价,您是因为《楚辞》才走上文学人类学研究道路的吗?
萧:我起初不是研究《楚辞》,而是研究上古神话,主要研究神话传说。不过,正是因为对传说批判性的研究基础上,对《楚辞》产生了兴趣。《楚辞》就是文学人类学的一个典型范例,我后来就是用文学人类学研究《楚辞》。我研究了屈原的生日“摄提”与太阳神帝舜重华的关系,揭示出了屈原作品中潜藏的光明祟拜系统,又对于“《离骚》结构的症结”,即所谓3 次飞行、4 次对话的文化意义进行了成功的释读。《离骚》主人公与太阳圣地及天体诸神的关系于是得以说明。
对于《九歌》诸文化层次的探掘,也有新的创见。通过多层面的文化分析,确认《九歌》的原始面目与祈求甘雨和丰年的仪礼有关,并且与高禖、社祭和万舞有密切的关联。继而又发掘了《九歌》的深层结构、主题思想以及与巫术性歌舞、民间狂欢庆典、人神恋爱幻想、人牺祭神仪式的复杂联系。
虽然我的研究“难免烦琐冗赘之讥”,因此而曾经招致“重复堆砌和不恰当引用材料”的批评。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学术坏境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在跨学科、跨地域的开阔视野中阐释,别开生面,创见很多,有一定的引领作用。我搞这个东西是非常早,我是自学出身,又是军人出身,15岁就当兵了。我当兵以后,在部队里得到学习锻炼,中间对文艺发生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也通过搞一些部队里基本的文艺工作学习了一些东西。我那时候对写作很有兴趣。因为有这些因缘,所以我现在搞《孙子兵法》研究。
李:早期部队的学习生活,对您的科研道路有哪些帮助?
萧:要两条腿走路,采取双轨会好一些。一条腿搞一点创作,我过去是搞戏曲的,因为我有戏曲情结,写过十几个剧本,写过旧体诗。另一方面,过去我们必须写文言文,要有一点基础的中国文化的知识,学一点文艺批评,做一些学问,两条腿走路,所以我从十五六岁就开始发表文章了。我后来到了上海,受到了闻一多的《神话与诗》和郭沫若的《神话的世界》等一些著作的影响,我发现了能够发挥自己特长的东西。
除此之外,我的研究之路也与主编《活页文史丛刊》密切相关。我们办《活页文史丛刊》的时候不要刊号。除国内的朱光潜、钱钟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我还发表了一些美国学者、华裔学者的一些文章。凭借这个平台,我们为文学人类学的早期萌芽提供了土壤。随之,我就正式地转入文学人类学的研究了。那时候,我发现叶舒宪在《民间文学论坛》上发表了《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2参见叶舒宪:《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1期,第33~43页。[YE Shuxian,“yingxiong yu taiyang—〈jierjiameishi shishi〉 de yuanxingjiegou yu xiangzhengsiwei”(The Hero and the Sun:the Archetypal Structure and Symbolic Thinking of The Epic of Gilgamesh),Minjianwenxueluntan (Folk Culture Forum)1(1986):33-43.],论文结合“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学”和“文学人类学”等文学批评理论认为,《吉尔伽美什史诗》在表层的叙述之外还有一个深层的象征层面,吉尔伽美什的命运和太阳的起落、运行合而为一。史诗之所以写在十二块泥板上是与巴比伦历法中一年分为十二个月、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相对应的。吉尔伽美什的命运在第六块泥版开始由盛转衰,这与太阳每天午后由高转低的运行曲线相对应,史诗作者自觉地以自然现象解释社会生活,以太阳的运行规律来象征人类的命运。那篇文章得到了学术界的赞赏。后来,我与叶舒宪开始合作,我们决心要用文学人类学研究思想史。我写了《中庸的文化省察:一个字的思想史》3萧兵:《中庸的文化省察:一个字的思想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XIAO Bing,Zhongyong de wenhua xingcha:yige zi de sixiang shi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Wuhan:Hubei People’s Press,1997.]。在这本100 多万字的书里,其实我就写一个字“中”。再到后来,我就陆续写成了《楚辞的文化破译》和《老子的文化解读》。就这样,我慢慢地进到文学人类学的研究阵营中去了。
李:您对文学人类学确实有垦拓之功。您能用几个关键词概括您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吗?
萧:我一贯坚持“跨学科”与“跨文化”研究,多重证据法。我曾说过:“人类学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工作方式,也是生存方式”。作为“新兴”的学科——人类学,特别是其核心民俗学、神话学研究在中国长期被边缘化,我的研究长期被恪守学科的学者称为“野狐禅”“旁门左道”。我把台湾出版的论文集题为《黑马:中国民俗神话学文集》,原来的副标题就是《民间文艺学向哲学挑战》。长期的沉潜学术研究,让我也深信,交叉学科、辅助学科正是学术创新的增长点,在成熟的土壤里开垦,固然需要,更重要的是开拓研究领域,升级研究范式。
李:萧先生的研究视野开阔,很早进行跨学科研究,在治学理念上不自觉地走在时代前列,对文学研究走向纵深做出了有力的探索,这必然给后辈学人们很多启发。您83岁高龄,还出版了《玄鸟之声——艺术发生学史论》,请问,您认为艺术起源于什么?
萧:过去人们常说艺术起源于劳动,实际上有一部分艺术根本不起源于劳动。我个人的观点是艺术发生于学习或者展演。我提出的这个观点跟我们日常讲的不大一样,跟孔夫子讲的学习有点联系。我讲的主要是心理上的学习,创造性的学习。比如,英语学习就是研究型的学习。人具有能动性的思维,在学习的过程中能不断地把他们的种属文化基因解放出来。
我认为科学也要通过人的学习不断推进。但是,科学是通过创造的形式进行,而艺术是通过形象的展演形成。这是一个过程哲学。过程哲学认为艺术在人的学习过程中间自然而然就出现了。简单的艺术发生于学习,它们会跟过去对抗。对于这个观点,我常常采用很多心理学上的概念去做假设。
李:谢谢您的高见。我想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您近期的研究对象。那么,请您围绕自己的兴趣爱好,谈谈手头上正在做的工作。
萧:我现在实际上在搞军事人类学,正在研究《孙子兵法》,尽可能多用人类学的材料,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如果研究战争的起源和所谓的原住民,或者是原始居民集团战争的时候,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可以用军事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这里头要研究人类的心理、生理机制。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也很难。
李:现在看来,从大历史来看,2000 多年前发生的战争,孙子兵法是有人类学基础的。为什么?我们看看历史,先是炎黄之间的战争,接着是与蚩尤的战争,人类的战争行为是集体基因所决定的。
萧:这不奇怪,人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研究兵法,而且不断地产生新的兵法。
李:刚才您说到,目前您正在叶舒宪教授主持的“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 中,准备出版除《神话学引论》以外的另外七种著作,都包括哪七种呢?
萧:我目前是四个出版计划。第一个出版计划就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合作,在“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中,出版除《神话学引论》以外的《四方风神话》《中国古代神圣建筑》《宇宙的划分与中国神秘构型》《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汉字与美学》《玄鸟之声——艺术发生学史论》《中国政治伦理的黄金律》七种。
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的精英》,改成《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这是一本修改的书,压缩了很多篇幅,又补充了一部分,还有60万,补充的主要是“弃子英雄”母题这部分,因为我认为现在国内研究弃子英雄的还没有像我这样的比较全面,从各个维度展开的研究。你看我这本书里,弃子英雄,你看过没看过里面的文章?
李:看过一些。您的这本书里的这些文章发表的比较早。
萧:弃子英雄我收集了将近100个,把它分成几类,这个分类到现在海内外基本能接受了。弃子英雄分为两大类型:一、漂流型或河海型,二、物异型或山野型。我外语水平有限,勉强能看得懂工具书,但是我很注意收集资料。这是第二本书,这是中国第一本比较神话学著作,但是我不敢打比较神话学的旗号。
这本书当时获得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一等奖,到美国也是讲这个题目。其他的还有四种,一个是中国宇宙的划分,讲古人对宇宙,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划分办法。比如说划分成东西两向,划分成四个方向。以后又划分为八个方向,四面八方,古代的这种划分方法,是分类管理,这是一本。
还有一本,我写了甲骨文四方风神话,在一片牛肩胛骨上刻有24 个甲骨文,记载了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神与对应的四位风神。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宋镇豪先生对我的研究有保留意见,胡厚宣对我非常鼓励,我当时写了这篇论文。
李:四方风代表四个方向的神与四位风神。著名甲骨学家、史学家胡厚宣先生对这片牛肩胛骨进行了考证。他在1944年发表了《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他对这片牛肩胛骨的释文是“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夹,风曰微;西方曰夷,风曰彝;北方曰宛,风曰隩”4胡厚宣先生于1944年发表《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后将其收录在《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中。本文的引用参见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5~276 页。[HU Houxuan,Jiaguxue shangshi luncong chuji shangc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Names of the Four Wind Directions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vol.1,Shijiazhuang: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2,265-76.],他们是殷朝人发明的独立标准四季体系,与四方神和四季对应,是确定日历与闰月的重要依据,与《山海经》中的记载可以互证。
萧:我这个论文就是与胡厚宣商榷的。胡厚宣先生看完以后非常高兴,这篇论文当时准备发表在《甲骨文与殷商史》第四辑上,以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搬家,把这个书稿弄丢了,一直也没出。胡厚宣很了不起,他发现《山海经》里头也有四方风,先秦其他的典籍里也有。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发现。
但是有一个重要东西他忽略掉了,那就是什么叫四方风呢?胡厚宣没有讲清楚四方风为什么这样称呼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证的。
李:您做了考证吗?
萧:对,我做了考证。这要从夏代的历史讲起,夏的祖先是传说中的五帝。它的原型是一种大型的鹰雕,一种大鸟。实际上,它就是大鹏鸟。大鹏就是“大凤”,“凤”过去就念“鹏”。最后我认为,四方凤是八种鸟。我写了一本书《甲骨文四方凤鸣考析》,专门研究这八种鸟。而且这八个鸟跟先公先皇都有对应的关系,殷人祭四方风神。对于这一点,最初是有人反对的。因为这个推翻了他们的许多理论,人们现在以鸟为图腾。每一个先公先皇都会变成鸟。我考证出来了六种鸟。而且我发现了《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神话中也有四方风,古代印度、印第安人都有四方风,它跟中国极为相似。
李:萧先生,我们这会儿从您最近研究的军事人类学出发谈了很多上古文化。您曾经就战国楚墓帛画的主题发表过重要观点,您能否介绍一下?
萧:战国楚帛画中的女性墓主人合掌祈求、希望飞腾的神龙、神凤引导或驾御她的幽灵早日登天升仙。参考另一幅由湖南博物馆于1973年5月从有《十二月神帛书》的长沙子弹库楚墓里发掘清理出来的《人物御龙帛画》,那“墓主人”站立在一艘龙形的“魂舟”之上。两幅帛画都出土于楚国腹地,时代相去不远,它们与《楚辞》文化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个墓主人都站立在舟船之上由龙和鸟呵护、导引“升天”。“魂舟”观念的起源很古老,几乎遍及亚非近海各地,现代所谓“环太平洋文化区”都有这一风俗。古埃及人认为地府之内,川流交错,故太阳神经行是间;死者的灵魂,要是能够搭乘太阳的大舟,便可以避免妖魔的侵害,神明的盘阻,顺序抵达乐土。
二、文学人类学的发展与突破
李:萧先生,我知道包括您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认为文学人类学近些年取得了显著成绩,那么,您认为文学人类学这些年主要成绩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萧:我在《文学人类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回忆文章《四十年,惊鸿一瞥》5详见萧兵:《四十年,惊鸿一瞥》,徐新建主编:《文学人类学研究》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9 页。[XIAO Bing,“Sishinian,jinghongyipie”(Forty Years at a Glance),in Wen xue renleixue yanjiu (Literary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vol.1,ed.XU Xinjian,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18,5-9.]的文章,其中表达了我对文学人类学40年发展的看法。
我认为40年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的贡献体现在三套丛书里。
一是人类学运用于思想史研究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这一套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如对《老子》《论语》《庄子》《中庸》《诗经》《楚辞》《孔子诗论》《史记》《山海经》等的人类学阐释。这些传统国学中的文化经典在跨文化的比较分析和透视下,借人类学的普遍模式的演绎功能使传统考据学所不能彻底认知的远古文化密码得到破解。这其中,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争议与影响最大,至今未息。人们认为 “不可能”用人类学来研究的《老子》,我跟叶舒宪却大胆“实验”,合作完成了《老子的文化解读》,这本书在“汉字文化圈”里有些反响,海外朋友说“引用率”颇高。
二是由叶舒宪教授团队撰写“神话历史”丛书。学术界关于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关联的探讨,主要有两种学术传统。一是20世纪初叶兴起的以顾颉刚、杨宽、童书业等为主的古史辨派,二是以美国学者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n H.McNeill)、唐纳德·R.凯利(Donald R.Kelley),以及以色列学者约瑟夫·马里(Joseph Mali)为主的神话历史(Mythistory)学派。较之于古史辨派,西方神话历史学派则强调神话如何进入历史,即从虚构如何建构真实这一论题出发,进而探讨神话对历史的塑造性作用。该团队的研究试图由此切入中国古史传说与民俗—口头文化的研究,再现比“书面文本”更高的“诗歌真实”和古史本相。他们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三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型“神话学文库”共38种。其中多数是翻译海外神话研究的前沿著作。他们包括《〈旧约〉中的民间传说——宗教、神话和律法的比较研究》《凯尔特神话传说》《苏美尔神话》《洪水神话》《日本神话的考古学》《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一个近东的共同体》《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头》《薄伽梵往世书》《神话动物园:神话、传说与文学中的动物》《巴比伦与亚述神话》《韩国神话研究》《众神之战:印欧神话的社会编码》《神圣的创造:神话的生物学踪迹》《熔炉与坩埚:炼金术的起源和结构》《萨满之声:梦幻叙事概览》《神话的哲学思考》《从前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的神话和哲学》《希腊神话与美索不达米亚:荷马颂歌与赫西俄德诗作中的类同和影响》《心理学与神话》等,因为种类较多,我就不再一一列举。
在对这三套书反映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思想转型评述以后,我也提出了自己的期待,认为“神话历史”丛书暂且停留在理论或一般的认识批判上,对具体的“转换仪式”或礼俗,如诞生礼、冠礼、葬礼、婚礼,以及大量的“祭典”(如祼礼、衅祓)等的微观研究,还较少且不深入。另外,我还撰写了《龙凤龟麟:中国四大灵物探究》。另外,为了“图像证史”,我们的书有大量插图,还有好几种科学普及性的读物问世。
李:好的,谢谢萧先生对文学人类学四十年发展情况的高度概括。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您和叶舒宪教授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刚才您主要谈了您的工作,请问您如何评价叶舒宪教授的学术贡献?
萧:叶舒宪最大的特点是他懂得要从国学基本元典出发,做中国学问,所以他努力学习甲骨文、金文和诸子经典。这很不容易,这是他第一条过人之处。第二,叶舒宪爱读书,阅读量非常大,掌握了文史哲中大部分的基本概念。第三,他英语水平非常好,能够直接读原著。第四,他思辨能力强,这是一种天赋。所以,凭借这种天赋,他的理论水平高,常常能提出有创造性的看法。当然,他最大的特点在于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比如把文本《山海经》中有关玉的叙述与西部上古玉矿的调查结合起来,把神话、考古与中国文明探源问题结合起来,同时在理论上又善于东西贯通,因此总结提出了文学人类学七大理论。
近年,文学人类学、神话学拓展的一大特征,就是认识到我们的研究,如果不想空泛、重复、浅狭的话,就要寻求考古文物的基础,以古文字为切入点,用田野调查资料或民族志为参照系。与此同时,考古学界也开始重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协同。资深考古学家王仁湘等一批学者自觉运用神话学、民俗学研究彩陶,出版巨著。王仁湘推出《中国史前考古论集》及其续集两大册。
叶舒宪提出前丝绸之路“玉石之路”和中国玉文化在上古史、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意义,撰著《玉石之路踏查记》及其续篇和《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等论著。我在《山海经的文化寻踪》里对《穆天子传》、希罗多德《历史》等文献与文物所反映的前丝绸之路的种群、文化做了一些探索,除此之外,我还写了《中国早期艺术的文化释读——审美人类学微观研究》6参见萧兵:《中国早期艺术的文化释读——审美人类学微观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XIAO Bing,Zhongguo zaoqiyishu de wenhua shidu—shenmeirenleixueweiguanyanjiu(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Chinese Art:A Microscopic Study of Aesthetic Anthropology),Wuhan:Hubei People’s Press,2014.]等“艺术考古”著作,对上古和远古的某些玉石器、青铜器和陶器等的形制、母题、内涵和用途提出与考古学界、与主流学术完全不同的新见解。特别是《中国上古图饰的文化判读——建构饕餮的多面相》7参见萧兵:《中国上古图饰的文化判读——建构饕餮的多面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XIAO Bing,Zhongguo shanggutushi de wenhua pandu—jiangoutaotie de duomianxiang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Illustrated Decorations:Constructing the Multifaceted Aspects of Taotie),Wuhan:Hubei People’s Press,2011.],以饕餮纹为重心,力排众议,希望在新的层面上回归它的本意或“古义”,反思张光直先生的“泛萨满”通天理论。
李:从您刚才的表述中,我们又对叶舒宪教授有了更多了解。谢谢您。叶舒宪教授这些年在做“神话学”研究,比如他提出的“神话观念决定论”“神话中国”“神话历史”论等等。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神话历史”观。而且,您在上面的答复中也提到了“神话历史”观,的确,这一观念更新了人们对中国文化传统乃至人类文明进程的看法。这里有一个具体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您。我注意到“高庙文化”在“神话历史”观落地生根的过程中影响了学界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认识。对此,请问您怎么看?
萧:高庙文化起源于湖南。我十分重视高庙文化,因为高庙文化和仰韶文化不同,而且它非常先进,它有凤凰。高庙文化出现了凤凰,和现在的凤凰差不多,这个令人惊讶。湖南的一个学者发表了好几篇有关“高庙文化”的论文。他发现了最早的饕餮,最早的凤凰鸟,他的这个发现很有价值,值得注意。所以他这个假设很对,至于后面的假设则并不准确。苗瑶,当时连苗瑶这种影子都没有,哪有这种呢?所以,根本不叫苗瑶。中间有一支红山文化,是从东方来的。山苗是从南方来的,然后他们在湖北、湖南那一代相逢,这就是蚩尤的祖先。因为蚩尤族北上,那边的黄帝南下。
李:不仅仅是一个传播,而是一个文化带来了一种源流。如果我们从人类起源的角度就会发现外来的文化也会与当地的文化相结合。为什么现在叶舒宪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我不知道您近期有没有关注过,他非常认同这种观点。在一次文学人类学会上,叶老师演讲中提到,人类走出非洲,受到神话天文观念中最重要的极星——北斗星的影响,您看他从非洲,从南面拼命地往北走,一直追那个北斗追到北方。受到复旦大学分子人类学中心李辉教授研究的影响,李辉认为在南方中国,一场重要的战争就发生在高庙这个地方,这个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然后到了5600年左右,也就是黄帝在北方这个地方出现了,然后到了5300年的时候,也就是黄帝炎帝联手,就在中原与蚩尤发生了涿鹿之战,这个他认为是最关键的一个年头。
现在李辉的观点就是用三个时间点标示出不同的文化类型。第一个是6800年的高庙文化,第二个是5600~5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第三个是5300年的崧泽文化。最关键的是第三个时间点所标示的文化。
萧:分子人类学我不能做任何的批评。人类以小群的形式走出非洲以后,从各个地方分散地走。他们一股一股地走,目的地是走到南欧,走到巴尔干那边。他们从南欧过来以后到中欧,再从中欧进入东欧,最后从东欧转到西亚。
李:对的,欧亚大陆里面有一支队伍。
萧:不过,他们到中亚就转到东亚了,就是从北方来的。
李:另外,他们这个理论后来关注基因的变化。
萧:简单讲就基因和环境的互动。它这个里头还有一个理论,因为他为什么讲两个阶段呢?这里头有一个尼安德特人,我那个书里面专门写了一章,尼安德特人南徙。
李:现在他提出这样的观点了。尼安德特人,对我们现在智人基因很重要,只有一点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智人不是尼安德特人。而是跟尼安德特人有一种基因的交构,男人和女人之间保留了一点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萧:他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了,分子人类学家不承认现在人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以后逐渐开始承认。以前的划分比较混乱。智人分两种,前期智人和后期智人。克罗马农人是前期智人。伴随着考古上基因研究上的新发现,分子人类学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因为现在尼安德特人有些遗骨已经发现了。西伯利亚发现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并未完全灭绝,它走出西伯利亚。还有一种说法山顶洞人是尼安德特人的直接后代,他们的文化跟尼安德特人是一样的,它并没有完全灭绝,我是赞成没有完全灭绝的,这个问题争论很大。
李:好的,谢谢萧先生对文学人类学四十年发展情况和拓展方向的介绍。
三、文学人类学的影响与启示
李:您是文学人类学的奠基者之一。请您谈一谈文学人类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
萧:我认为文学人类学的最大影响就是唤醒人们对文学功能的重新认知。今天学界呼吁跨学科提倡“新文科”,大文学,要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即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我们以前习惯于将文学的功能局限于认知、教育、审美等层面,可是唯独忘记了文学最初的功能就是“治疗”。叶舒宪曾在《文学与治疗》8详见叶舒宪:《文学与治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YE Shuxian,Wenxue yu zhiliao(Literature and Therapy),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1999.]中强调文学的精神医学功能,重申了人类生存的精神生态状况与文学治疗密切相关。语言艺术可以治病,确是古已有之。最早在部落社会里行使语言艺术的是巫,而那时的“巫”和“医”实为一体。在我国,像《七发》中就有“杜诗疗虐”以救太子之类的典故,文人们对此津津乐道。更重要的是,文学治疗这个理论命题的提出,不仅有助于从源头和功能上反思文学的本性和特质,也让关注生态批评的人意识到,生态批评不只是倡导保护环境和绿色写作,其实人本身就是一个微妙复杂的生态系统。作为人类的文学,从创作到阅读,在根本上都蕴涵着精微的生态原理。
李:的确,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性越来越显著了。萧先生您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而且拥有丰富的文学人类学的阐释经验,基于此,您能否给我们后辈学人在文学人类学的探究方向和理论构建方面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呢?
萧:第一条,必须选准题。如果打算以中国的资料为研究对象,那么就选择一个具体的问题去研究,比如说你选中国俗文学中的宝卷为研究对象就很好。再比如说你想研究创始神话,那么你就要把中国所有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以及西方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关联起来,照此来看,“创始神话”这个题目就太小了,需要选上一个稍微大一些,但也不能太大。第二条,要学习现在各种各样的理论,最好能够综合一下它们。比如,叶舒宪就有综合使用各种理论的本事。如果一个人在综合使用各种理论之后,那么他极有可能提出新的高见。不过,这些新的高见可能离不开对具体材料的梳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学习理论要善于综合。学习理论最好的方法是把理论学习运用到研究里头去,而且有所发挥,有所创造。可是,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啊!
李:是啊!这就要求现在的年轻博士做学术一定要有抱负。
萧:对于年轻博士而言,他们做研究一定要首先选好研究方向。这个被选定的研究方向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持续探究才能渐入佳境。学术研究忌讳“东一锄头西一榔头”。我这些年的研究就紧紧围绕一个领域,那就是上古文化,主要围绕古史传说、神话展开。除此之外,我的研究就再多涉猎了一个《孙子兵法》。这个多出来的研究领域与我的经历密切相关,因为我是军人出身,所以懂一些军事术语,掌握了一些军事知识。
李:谢谢萧先生对青年学人的指点。在此,还想就文学人类学以后的拓展方向听听您的看法。
萧:近年来,神话学研究是文学人类学拓展的一个主脉。2017年底,上海交通大学成立神话研究院,还召开了“中华创世神话”研讨会,建议将来重建中国“神话历史”,从中发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与文化心理,与出土材料互参,修正中国上古史,开辟中国神话研究新局面。
也就说,我们的研究如果不想空泛、重复的话,就要寻求神话与古史、考古文物材料的支撑。比如以古文字为切入点,用田野调查或民族志材料为参照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人类学试图拓展——“文字人类学”与审美关系试探》,其主要想法是在人类学视域下,通过对汉字的“象意”和“音响形象”的探讨,厘清汉字与审美的关系,从而对建构“文字人类学”做出新的尝试。文学人类学近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既要有集中的研究阵地,又要立足现实,解决实际问题。近20年,从神话原型批评开始,文学人类学在中国上古典籍的人类学破译、上古神话的学理、神话历史问题的探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玉教理论、文化文本等,大大拓展了文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文化符号学理论。
李:萧先生,我们的后学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神话学研究感兴趣。您能根据您这些年对神话的研究经验,给后辈学人一些启示吗?
萧:做神话研究的人最起码要有四方面的素质:一是要有一点想像力;二是要有一点创作力;三是要有一点灵性;四是要有一点悟性。我讲话不客气,我们许多神话学家,很多搞文化史的,学问都好得不得了,但是缺乏一点灵性,缺乏一点悟性,所以创造性的东西很少。我举个例子,最明显的就是王以欣,他是我很佩服的人,他研究希腊神话,在中国懂希腊语的并不多,他过去比较谨慎,他是历史学出身。与文学人类学接触以后,他的研究开始有灵性。搞神话研究的人必须一“出场”就要有灵性。你也有一点灵性,我讲一句实在话,你提的这些问题很好!
李:谢谢您,萧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您作为创会的会长,对文学人类学的发展有哪些期望?还有哪些寄语?
萧:现在我认为人类学的发展,非常重要的是培养人才,因为比较活跃一点的,年龄一个个都大了,大部分都超过60岁了,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我希望你们年轻人都能一个个跟上来。但是这里头还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我和叶舒宪这一代人比不过比我们老的那一代人。老专家那一代人,比如钱钟书、朱光潜、饶宗颐他们,虽然年轻学者有时候见解比他们新颖,但是学问的根基比不过老一辈学者。那些老先生们对于“经、史、子、集”滚瓜烂熟,甚至都会背诵十三经。我们这一代人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也有我们这一代人的优点。一是外语水平普遍较好;二是能见到丰富的资料,尤其是出土资料;三是在我们的研究基础上展开,起点要高一些。换句话说,年轻学者可以踩着我们的肩膀前进。
在此,我要不客气地指出当下年轻学者们所普遍具有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年轻学者虽然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也不乏独到见解,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不够深广,甚至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不怎么全面。所以,年轻学者不能仅仅关注那些热点,比如人工智能、世界主义和动漫、电影等等。人工智能、世界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就真的如“游戏”般简单吗?这些实际上很难懂的。一个年轻学者去研究这些看似新潮的事物其实是需要深厚的国学修养底子的。我希望文学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年轻学者能够在国学的承继中吸纳中外优秀文化,不断拓宽文化文本的研究路子,创造出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学术辉煌。
李:好的,访谈就进行到这里,谢谢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