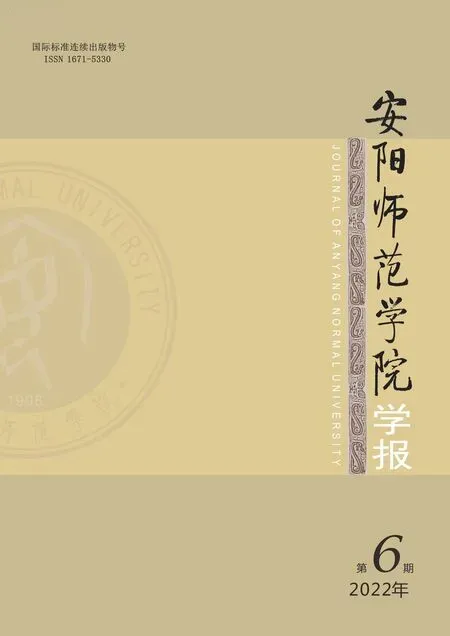论《观卦》仪礼的身体性感通
——基于人类学的展演与解释
王沁雨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古代易学研究有“两派六宗”[1](P3)之说,各家以不同重心(如占卜、造化等)或不同方法(如义理、相数等)解读《周易》。但是,《周易》卦辞本身是时人针对各类活动进行占卜后总结而成的规律,在解读《周易》时不能忽视卦辞本身针对的活动及其存在的时代背景。
《观卦》卦辞“《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2](P75)蕴含“盥而不荐”的取舍关系,涉及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2](P76)的宏大主旨。已有研究对此卦所述仪礼的行为考察并不多见,基本没能发掘其中的“感通”机制,对理解所谓的“神道设教”或存缺憾。文章从人类学视域下的身体行动出发,采用文献考察与互证的方法,展演与解释《观卦》仪礼,试图阐明其“神道”之意。
一、展演“盥”“荐”仪礼的必要性
理解《观卦》的重点在于“盥”“荐”及其关系。“盥”为“灌祭”[3](P2753);“荐”读为上声,表“进献”[3](P3524)。
《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2](P75-76)
“盥”是一种盛大的仪式或时刻,触发神圣空间中的临在状态,而不仅仅是《周易本义》所谓的“将祭而洁手”[4](P120)。《观卦》所述乃是“大观”(弘大的场面),圣人以“神道”推行教化,教化的关键是使天下人“观仰感召”。《周易集解》引马融的说法,将“盥”解为“祼”或“灌”,强调的是以香酒灌地而降神的仪式[4](P120),历代不少注疏家都认为这种理解较为合理(1)远至孔颖达、朱熹、郑玄,近至顾颉刚、刘起釪等都基本认同“盥”同“灌”“祼”的说法。。
《观卦》卦辞涉及宗庙盛大祭祀仪礼中紧密相连的“盥”与“荐”两个仪式环节。古代文献对“盥而不荐”原因的分析,较好地佐证了这种取舍关系。例如《论语·八佾》有“褅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也”[4](P120)之言,《周易注》有“王道之可观者,莫盛乎宗庙;宗庙之可观者,莫盛乎‘盥’也。至‘荐’,简略不足复观。故观‘盥’而不观‘荐’也”[4](P120)之说。
人类学的视域或可弥补现有研究中对《观卦》解释有余而展演不足的遗憾。仪式是人类学关切的核心问题之一,自从泰勒、弗雷泽等民族志学者构建了最初的人类学研究,仪式就与人类学紧密相连。还原到个体层面,仪式是一系列身体行为,用以开启或进入一个神圣空间,身体作为诱因,也作为载体,是仪式展演的基础,这使得任何仪式的研究都不应跳过从“仪式实践者和宗教信徒的第一人称的视角出发,强调仪式的切身性和委身性”[5](P210-213)的过程。其中,对“身体性”的强调可以借助伊利亚德的“共情/同情”理论[6](P69),感同身受地把对“神道”的挖掘从单纯依托文献经典的解释,提升到理解仪式中实践者的心灵感受到的神圣临在感的层面。
在展演相关仪礼前,还有必要澄明“临在”“感通”及“神圣空间”的概念。“临在”是超越对象或特质的当下呈现,在时人的祭祀仪礼中,指“神灵”的感格或在场。“感通”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2](P245),神灵感格是祭祀仪礼的目的,唯有诚敬的心灵状态才能让处于上天的神灵感应到并降临在场,达到这种状态又需要身体虔诚地执行仪式。此外,在伊利亚德的理论中,有一种时空模式与日常生活(世俗)的秩序有所差异[7](P368),在此模式中,仪式实践能使参与者感受超越性的神圣感召,其空间便是“神圣空间”。人总是在世俗空间中进行活动,实践仪式的意义就在于把一个区域从世俗中隔离出来,使在场者感知显圣,只有当身体经历特定的仪式或心灵体验特定的叙事时,“神圣空间”才会被构建。
进一步讲,引入“神圣空间”的人类学理论,有助于更好地发掘《观卦》仪礼的“临在”与“感通”。按照上述理论,祭祀者在《观卦》所叙仪礼的行进过程中,以身体上的仪礼实践(包括言说、肢体动作、乐舞、静默等活动),打开通往“神圣空间”(在此卦中或为“上天”)的通道。若其在心灵上同时保持诚敬,上天“神灵”就能感应,从而“临在”这个被构建的神圣空间。于是,圣人以此使民“观天之神道”,在每个人切身的神圣体验基础上推行道德教化。
二、“盥”与“荐”的身体行动
(一)诚敬的坍缩:从“盥”到“荐”
“盥”是重要的仪礼,“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祼。”[8](P636)《礼记》称“祼”,《周礼》称“灌”,《周易》称“盥”,下文从仪礼的角度称为“祼”。
“以圭瓒酌郁鬯灌地以将神,谓之祼。”[9](P845)“祼”指祭祀时以酒灌地请神的仪式,“(凡祭)周人先求诸阴也。”[8](P325)“求诸阴”在“祼”中即以酒灌地,酒气下涉,沟通地下的阴气,与焚烧馨香的阳气汇合,阴阳之气一同感通,切割世俗世界。典籍对“祼”礼仪式的记载以“三礼”为主。
郁人掌祼器。凡祭祀、宾客之祼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凡祼玉,濯之,陈之,以赞祼事,诏祼将之仪与其节。凡祼事沃盥[8](P296)。
大祭祀,逆粢盛,送逆尸,沃尸盥,赞隋,赞彻,赞奠[8](P366)。
“祼玉”指圭瓒、璋瓒等酒器,“祼将”指协助灌酒的将士。“祼事”又名“沃盥”“沃酒”,是指以酒浇地而祭;“沃尸盥”指面对装扮神灵的“尸”(2)古代祭祀时代表示死者(神灵)受祭的活人。进行灌酒的仪式。在具体仪式操演中,肆师指导王使用圭瓒把“郁鬯”(3)古代祭祀、宴饮用的香酒,用郁金草和黑黍酿成。盛出授予“尸”,而“尸”扮演的是一个可上身的“容器”,是整个仪式象征意义的中心,人和“神”依靠他才能相交感通。
此处的仪式有较为明显的巫术特征,是“身体性”感通的一个显性标志物。弗雷泽指出,交感巫术有“相似律”与“接触律”两大原则,相似律指在法术的实施中仅仅是相似或模仿就能够对所模拟的那个目标对象实现效用[10](P19)。基于“相似律”的顺势巫术在尸祭礼仪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尸”的身体隐喻祖先,如果完成了“祼”礼就意味着祖先上身。此时的神圣临在已经不是心灵意义上的感通,而是现实世界象征出的切实神显了。
“尸”庄重地将郁鬯浇灌于地,郁鬯以其“臭阴”达于黄泉,“所达之深,而足以感于死者之体魄。”[10](P713)此时不需要将酒全部灌地,仅做象征行为即可,剩下的郁鬯会先被“尸”喝下一口以象征祖先的享用,尔后将余下的酒液放置在祭台供桌上,一祼告毕。然后,由内宰指导“后”(帝王的妻子)重复王所行之礼,“尸”亦重复其在一祼中的行动,二祼礼成。
两祼皆成后,降神之机已至。随后,乐舞立即依礼而作,歌《九德》舞《大韶》,往返九遍,降神祭祖的重要环节至此告终。此刻,可被视为上天之神正式降格,神圣临在达到至极。
进一步讲,在歌舞所营造的神圣氛围中,主祭者与“尸”一同身心严肃地实践典仪。这种忠实的行动试图重演、重复过往时空中的原型行为,即古人认为一切神圣的东西都是典范性的原型,非原型的就是世俗的,仪式的意义之一就是使人不断回溯最初的神圣范式。
更重要的是,从仪礼中还能发现从“祼”到“荐”的过程,面临着一个显著的转折——诚敬的坍缩。祼礼在虔敬上达到顶峰,此前的斋戒洒扫和一系列极为庄重的仪式及其器皿酒液都是为了辅助达成此时最重要的目的——试图请神上“尸”。为了达到这种感通,所有参祭者无不至诚至敬,其虔敬的程度在等待降神的过程中逐步累积,直到 “神”上“尸”,那时便是在场者诚敬的极致时刻。也就是说,时人认为祼礼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沟通阴阳,制造“感通”,以达到神灵降格的神圣临在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主体性被神圣压覆,达到《观卦·彖传》所谓的“天下服”的效果。
“既灌然后迎牲”[8](P325),王杀牲,将不同部位分别依不同方式献于“尸”前,整个过程即为“荐”。不过,“荐”时的诚敬程度不及“祼”,原因主要有:首先,当众杀牲是一种具有强烈原始色彩的祭祀仪式,其中蕴含的血腥意味无可避免地把在场者从极端诚敬的状态拉向野蛮迷狂的状态;其次,荐礼仪式过程单一且重复,难免使人心生倦怠,不利于人们长时间保持诚敬顺服;最后,当在场者认为祖神已经附于“尸”后,精神状态自然松懈,余下的只是依照规制完成剩下的仪式罢了。此外,乐舞显然会助推人们进入迷狂的心理状态,此刻“神圣空间”的性质已然改变,故而出现“诚敬的坍缩”。
(二)禘礼中的“祼”与“荐”
“祼”与“荐”是禘礼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考察承载“祼”“荐”的整体礼仪,有利于进一步认识其中的身体行动。
“禘”乃祭名,可细分为宗庙时禘(宗庙四时祭之一)、殷禘(宗庙五年一次的大祭)、大禘(郊祭祭天)[3](P2574)。在禘祭的准备、实施过程中苦心营造的庄严肃穆状态,令参与禘祭的所有人物切身感受到神圣氛围,使其在“祼”等重要环节更好地实现感通。
实施禘祭的记载散见于“三礼”等相关文献,这为展演其中的身体行动提供了可能。
在准备方面,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帅执事以卜日”[8](P282)。首先,王在肆师的帮助下,通过卜筮确定行礼日期,然后清洁宗庙以示对祖神的虔敬,祭祀场所、祭祀用具、祭祀用牲、各诸侯与参祭人员等都需要提前精心安排。随后,王、助祭者以及全体族人斋戒十日,“散齐七日以定之,致齐三日以齐之”[8](P634),达到“齐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交于神明也”[8](P634)的临近出神的状态。当致祭者开始三日“致斋”时,还需要通过卜筮从有爵位的嫡孙中,选出代表祖神接受祭祀的“尸”。其在被确认为“尸”的一天后,需要接受王的“宿尸”(被告知祭日将要到来),同时还要庄重地准备以达到能与“神”相交的精神状态。
祭祀当日清晨,专人再次检视一切是否妥当,参祭者各安其位。典仪开始时需要“阴厌”,即设馔(饭食)于室之奥(室内西南隅)[9](P781),“阴厌”后仪式继续进行,最后向神行礼致辞。礼毕,由王带领所有致祭者前往宗庙的东阶上等候,“祝迎尸于门外”[8](P429),直到“尸”踏入宗庙则开始“九献”之祭(禘礼主要仪式的汇称),又落实为“九酌”的身体行动。在此,“九谓王及后祼各一,朝践各一,馈献各一,酳尸各一,是各四也。诸臣酳尸一,并前八为九”,是为“祭之正也”。[12](P518)
可见,“九献”“九酌”并非一蹴而就,祼献、朝践、馈献、酳尸等四个流程依次由王、后二人各执行一次(共八次行为),诸臣在“尸”食毕后“再次酌酒献尸”[9](P1027)一次。与《观卦》“盥而不荐”相关的就是“祼献”“朝践”,展演如下。
执礼者在宗庙外把“尸”迎入室内,脚步稳而缓,到规定位置站定,然后通过一系列神圣空间的展开(整个仪式的准备创造了浓厚的神圣临在感),进行灌酒仪式——王与后二人到“尸”的面前,向其献酒,二人须用圭瓒、璋瓒各酌两次。献酒交付到“尸”手中后,“尸”虔诚肃穆地手执玉器,灌酒于地,以郁鬯之芬芳吸引祖先神灵前来享受祭祀。献酒前后两次,是为裸献,“谓始献求神时也”[8](P276),其终极目标在于“降神”。
此后,“感通”仪式进入第二环节“朝践”。朝践是“谓荐血腥、酌醴,始行祭事”[12](P516),“既灌然后迎牲”[8](P325)。裸献之礼结束后,王出庙门迎牲,亲自牵祭牲入内,将其绑在庙柱上杀死。然后“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13](P1073),王取祭牲之脂,混以萧草、黍稷一同焚烧。所生馨香以气之形充盈神圣空间,使人处于恍惚之状,起到打通人神相通之效。
火燔升香后,王接着将牲体肢解为七块,后以豆、笾盛之。王将牲肺以郁清洗,献于“尸”前,是为荐腥。荐腥之后,“王以玉爵酌醴齐以献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齐以献”[12](P518),是为朝践二献。
虽然禘礼的主旋律是诚敬,但是不同流程的诚敬状态也有差别——既有肃穆摄人的仪式,壮观动魄的音声,也有血腥荐食的癫狂,焚烧油香的气味。此时对神秘的畏惧、道德的感召、庄重的仪式、迷狂的状态都在神圣空间的场域中混为一体。禘祭礼节繁琐复杂,致祭者皆需心思澄明、至诚至敬。这种感召,无论是在道德教化、尊卑制度或是神圣体验层面都极为震撼人心。
就意义而言,“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8](P699),西周涉及祖宗祭祀的礼制强调大小宗的差序,不断肯定、维护大宗统治者的绝对权威。春秋之后,礼制僭越、继承紊乱、昭穆失序,禘祭的预期功效逐渐转向辨明血缘和厘清继承权力。进一步讲,作为包含《观卦》所言“祼”“荐”仪礼的整体大礼,禘祭具有追终慎远、震慑诸侯、重新凝聚及确认王权绝对性的群体功能。
三、结语:身体感通的力量来源
《观卦》所言仪礼,建立在以天人感通为核心目标的祭祀祖先神灵的活动上,蕴含了时人“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8](P325)的魂魄观。《周易》论“气”不多,主要集中于《易传》,把“气”视为阴阳之体、化生之本。如《咸》之《彖》言“二气感应以相与”[2](P111)、《系辞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2](P233)以及《说卦》“山泽通气”[2](P282)等。
在义理上,“感通”可以源于“气”。一方面,《周易》的“气”是异气相击,其化生感应万物,使宇宙变化无穷。所谓“气”的感应属于宇宙的自然变化,包括所描述的阴阳、男女等类之间的感应,是顺遂自然的非人为造作。另一方面,人作为世间受造,其阴阳二气同属宇宙大气,可以观照感应,动乎天地,故“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4](P182)。圣人影响天地的依据并不是圣人的“力”,而是切身感受了仪式展演时的神圣临在状态。这种感通可以“观民设教”[2](P76)、推行教化,这种超越性的感受,对于时人来说由阴阳之气与天地之气相接而来。
通过“气”的连接,天地、自我身心以及神灵之间确立了感通的基础,使仪式行为和身体行动有了观念基础。从仪式行为的意义上讲,自我首先是身体性的,因而身体的经验与行动和意识的关系无比重要,这正是文章选择把理解《观卦》的视角放置在仪式角度的重要原因,它较之纯粹的义理注疏和观念或信仰的理性确证具有更强的实在感。
仪式中的身体行动往往又可以转化为象征性的神圣经验,甚至进入宇宙进程之中[14](P35)。唱诵、舞蹈、对仪式的忠实实践和对神圣原型的模仿等身体行为,使宇宙过程及时人心中的神圣创世神话真实重现,瞬间的神圣感会在香气、氛围、环境等条件下激发人的迷狂状态。
在仪式中,身体被纳入到与超越性合一的叙事想象中,其行动严格按照某种程序和规则展开,而这些程序和规则恰是超越性过程的启示所规定了的。因此,个体的任何一个行动可以超越自身限制,成为宇宙过程的一部分。那么,当参祭者在自我的消解与重构过程中,以身体为中介较好地执行禘礼时,“感通”得以实现。
沿着行为实践的视角进一步分析,这样的“感通”不仅是自我与宇宙的融合,还蕴含了万事万物各安其位的和谐状态。祭礼的基本功效是程式化秩序感的确立——秩序感并不仅仅是社会意义上的秩序感和等级层次,而是面向人神关系的秩序感,其中包含对日常生活及信仰实践的时空、程式的规定。秩序感一方面严格地规定了“盥”“荐”及禘礼等仪式仪礼的实践程式,另一方面又依赖于以行动不断重复的严格程式来完成天人感通。这种对仪礼的一丝不苟,或可称为祭礼的实践工夫,既体现在对祭祀对象的尊重,也通过显性行为的实践不断展现、考验、叩问参祭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