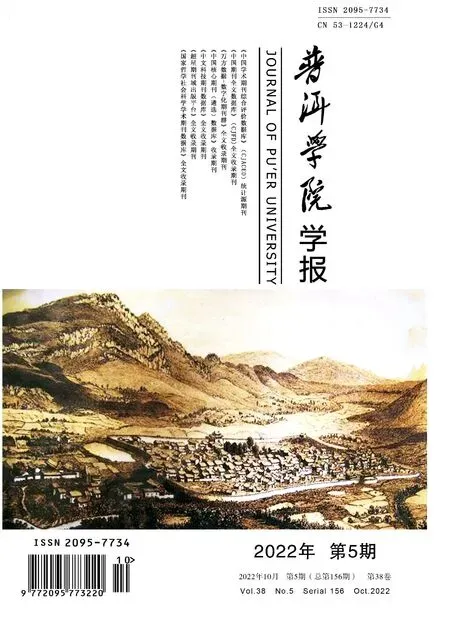再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写作初衷及其被建构的历史影响
杨阎文
普洱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普洱 665000
卢卡奇(György Lukács,1885.4.13~1971.6.4)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其标志性的“物化理论”也经常被用来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比较。他在未读过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观点提出自己的物化理论,足见其理论的深邃性。然而部分学者[1][2]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认为卢卡奇物化理论是对马克思异化学说的创造性发展,或者认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微进化”。笔者认为,从卢卡奇提出“物化”概念的初衷出发,类似提法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本文从探寻卢卡奇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初衷出发,明确卢卡奇提出“物化”概念的最初想法及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发表之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随后通过梳理后世思想界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建构作用,反思思想史研究中应当坚持的方法原则。
一、卢卡奇的早年经历及匈牙利革命对其个人的影响
卢卡奇于1885 年4 月13 日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银行家家庭,然而他在宗教信仰上却非犹太教徒,其在自传中也明确表示:“犹太民族的意识形态对我的精神发展没有任何影响”[3]。
早年的卢卡奇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02 年6 月高中毕业后,他先在1906 年10 月在科罗茨瓦皇家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于1909 年11 月在布达佩斯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17 年他在一份为谋求海德堡大学哲学讲席而拟的简历中提到,“狄尔泰的影响主要在于激起对文化史联系的兴趣,西美尔的影响则在于表明了社会方法和文化具体化的可能性。此外,麦克斯·韦伯的方法论著作对我起了澄清问题和开拓思路的作用”[3]。
1909 年秋到1911 年春,卢卡奇在柏林期间,兴趣集中在德意志古典哲学上,但对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哲学的学习也促使其把关注的重心转到现代德国哲学,包括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拉斯克的哲学中。其后他曾在佛罗伦萨短暂居住过1 年,之后便迁居海德堡,期间于1914 年春与海德堡同赫尔松地方自治局书记安德烈·米海伊洛维奇·格拉本科的女儿叶莲娜·格拉本科结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后国际和匈牙利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使其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1915 年他返回布达佩斯,但因为精神衰弱症而没有服兵役,之后他在布达佩斯与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组织了星期日社论(Sunday Circle)的沙龙。这个由知识分子组织的文化沙龙由于成员严重分裂的政治倾向而最终在1918 年解散,期间沙龙的部分成员介绍卢卡奇加入刚刚成立的匈牙利共产党。
此时是卢卡奇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时期,自传中他将这一段经历命名为“走向命运的转折点”。对战争的激烈反对促使其兴趣中心从美学转向伦理学,并留下类似这样的自传提纲:“1917-1918 是决定性的一年;对俄国革命的反应。我自己的道路:充满矛盾、且带有反复的迷恋:1918 年加入共产党”[3]。期间波尔什梯贝·盖尔特鲁德(卢卡奇第二任妻子)对卢卡奇的影响尤其巨大。卢卡奇在自传中表示,“我的路线总是坚定的;关系——甚至爱情——总是在既定的发展路线中,现在,每一个决定都有盖尔特鲁德强有力的参与;特别是那些最富有人性和有关个人的决定。她的反应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3]。
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之后,卢卡奇曾短暂的担任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主管文化和教育的人民委员及匈牙利红军第五师的政委。然而这段时间无论是卢卡奇个人、匈牙利共产党还是整个匈牙利苏维埃革命在思想层面都是极端混乱的。卢卡奇在自传中坦言自己入党时是完全没有理论准备的,匈牙利共产党对如何进行革命也没有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和行动方案,只是焦急地等待来自莫斯科的经验和指导,然而结果就如卢卡奇所言:“从莫斯科来的人告诉我们的东西都很不高明”[3]。
正是在这样仓促而混乱的背景下,匈牙利苏维埃革命只坚持了130 余天便失败了,包括卢卡奇在内的一大批流亡者逃往维也纳。随后卢卡奇在维也纳生活到1929 年末。此时,卢卡奇才真正开始对马克思进行系统的研究,这段时期也被他称作“生活和思想的学徒期”。
二、《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写作初衷及核心观点
从卢卡奇早年的经历来看,即使在其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并出任党的重要领导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仍然是不够深入的,甚至于到集结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之时,也没有到达思想的成熟阶段。他本人也一再强调《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部过渡时期的作品,具有“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特征”。
那么卢卡奇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初衷到底是什么?这本书的核心又是什么?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先从他的自传中窥见一二。
“即使作为军队中的政委,我曾多次看到农民由于我们未能分配土地而不信任我们”[3];“当捷克和罗马尼亚的进攻在4 月份开始时,人民委员会决定,半数的人民委员应该到大的军事单位去当政治领导人……蒂萨费勒德的保卫战弄得很糟,因为布达佩斯的红军战士不放一枪就逃跑了”[3];“在军事上,我自然只能在明显的情况下进行干预。我为此找到了一种很好的方法。我们的特别反革命的参谋长一但我使用这个方法就要发火。我往往对他说:“瞧,你是当兵的。你有你士兵的语言,我有我哲学家的语言。但是军事问题我一窍不通。如果你要告诉我这个或那个营需要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你不必详细谈这样集结或那样集中以及诸如此类只有专家才懂的东西。对这些东西我毫无概念,所以你必须以那种使我这个外行人也能懂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或那样做的方式来进行解释”[3]。从以上三段话中我们可以窥见,在匈牙利革命这个短暂而混乱的时间里,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匈牙利共产党人与广大工农士兵的割裂和自身在思想、理论和组织上的不成熟。
我们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就可以发现匈牙利共产党成立的时间远远晚于布尔什维克党,其创始人库恩·贝拉等人早年大多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的角色存在,其后更长期在国外开展革命工作。可见,匈牙利共产党在匈牙利革命期间的群众基础极为薄弱,加之整个领导层对革命缺乏起码的准备,因此革命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失败也不足为怪了。
至此,我们可以探讨一个问题,革命期间匈牙利广大的工农群众在思想意识层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知道,匈牙利自1867 年起便与奥地利组成了一种特殊的二元帝国政体,奥地利承认匈牙利“历史领土”的统一和完整,匈牙利则承认皇帝对于二元帝国的外交与国防权力,两者均设立自己的国会、两院和行政机构,同时各由一个首相领导。艾伦·帕尔默认为从技术性来说,“奥匈协议”所创造的是奥地利——匈牙利二元君主国,但马扎尔人所得的好处极大,因此不如说“匈牙利——奥地利帝国”更为恰当一些[4]。之后的匈牙利在萨蒂·卡尔曼家族领导的政府治理下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铁路网宣告完成,主要干线都由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通过匈牙利的唯一海港——阜姆的贸易值,15 年内增长了12 倍,甚至开辟了横跨大西洋直达纽约的航线[4]。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无产阶级群体的发展与壮大,然而必须要明确的是,一个阶级群体的发展与壮大并不直接意味着其相应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和成熟,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真正觉醒和最终成熟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引,需要无产阶级政党持续的组织、宣传和动员,然而这些条件在1918 年前的匈牙利都不具备。中东欧特殊的自然与历史条件形塑了区域内极端复杂的民族关系结构,各民族间的矛盾常常将阶级矛盾掩盖。同时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又是欧洲民族主义全胜的时期,它总是带着两幅面孔:一面是群众起义,力求爱国愿望得到普遍承认;另一面则是内心以某些美德的化身自居,似乎是要把一种传统的继承者同他们不甚幸运的邻居截然分开[4]。许多蛊惑人心的政客谈论着各式“大民族主义”,它也构成了欧洲19 世纪80 至90 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成长的基本舆论背景,而这些人在后来的人类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历史的指针拨动到1918 年,随着同盟国的崩溃,匈牙利面临的是极端残酷的历史现实。且不论持续4 年的战争对匈牙利造成的直接影响,仅以战胜国强迫匈牙利签订的《布里亚农条约》而言,就意味着匈牙利失去了1867 年“奥匈协议”签订时所承认的2/3 的领土,割让给罗马尼亚的领土面积甚至大于条约签订后匈牙利所剩的领土面积,可以想象这样的结果是对一个民族何等巨大的打击。故此,在1918 年的匈牙利革命中民族革命的色彩远远浓于阶级革命,同时在这场革命的中后期作为革命的领导者的匈牙利共产党,由于自身的巨大缺陷,未能有效领导匈牙利人民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
面对如此惨淡的现实,当时的卢卡奇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革命的敏感的资产阶级学者,不可能不对革命的种种进行反思,加之他移居维也纳后日渐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最终将其引向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阶级斗争分析路径。然而作为一个刚刚从非马克思主义的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学者,其自身所带有的种种思想印记是不可能迅速消除的,加之客观历史环境的影响使其又滑向了过分强调主观意识的唯心主义怪圈内。
首先,卢卡奇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初衷,应当说随着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不断提高,面对匈牙利革命的具体现实,促使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问题。匈牙利革命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兴起又被反动势力扑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族意识压倒了阶级意识,最终导致最富革命性和战斗力的工人阶级未被有效的组织动员起来。也正因为其政治觉悟和历史主动性的缺乏,使得他们不能采取持续有力的革命行动。同时,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匈牙利共产党又未能提出实际的土地革命方案,致使农民没有支持革命。卢卡奇面对匈牙利革命具体的历史条件,断定要想获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就必须呼唤阶级意识的觉醒。所以《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基调就是破除资本主义“自然永恒”的魔咒,为无产阶级革命提高理论根据[4]。
其次,则如他本人在1922 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明确的:因为我们的任务——而这是本书的基本信念——就是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方法的本质,并正确地加以运用。我们决不求在任何意义上“改进”它。因此,我们坚持马克思的学说,决不想偏离它、改进或改正它。这些论述的目的是按马克思的意思来解释、阐明马克思的学说[4]。所以,从卢卡奇写作的初衷而言,他绝没有打算对马克思异化学说进行“创造性发展”,其“物化”概念也不是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微进化”。
反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实际上它是一本论文集,是卢卡奇1919 年至1922 年在维也纳期间,对于党的理论及组织进行反思之后撰写的8篇文章的集结。专门为本书撰写的文章实际上只有2 篇,一是“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二是“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就“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这篇文章而言,卢卡奇先在第一部分对物化现象进行了讨论,而后在第二部分明确了古典哲学存在“二律背反”的局限性以及无产阶级通过“把辩证的方法当作历史的方法”来超越古典哲学局限性的历史使命。随后卢卡奇便开始了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讨论。故此,我们可以认为卢卡奇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讨论才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而“物化”概念仅是构成这一核心的结构性论点。
三、后世对“物化”概念的持续建构
综前所述,笔者认为卢卡奇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5]的初衷是其个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面对匈牙利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低潮的具体历史现实,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意图通过呼唤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其中,关于物化的讨论仅是构成此核心理论的结构性论点。
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何部分学者会认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对马克思异化学说的创造性发展,或者认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微进化”,甚至在行文中将两者等同起来?
类似不恰当的提法促使我们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构建问题。在确切的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特定历史叙事支持下的建构。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为起点来定义一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与其他思想史研究一样,都已经是一种事先追溯。这种追溯旨在揭示一种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发展的轨迹,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张力,从而为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多样性发展提供一种历史前提。这不仅要求我们的研究有更大的理论自觉,而且实际上会带来历史认识的深化[6]。我们知道,对于一个既存的理论体系而言,其在后世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会不断受到“建构”的影响。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一般民众都会参与到这个“建构”的过程当中,因为后世对于某个既存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必然经过对其进行“个性化把握”的过程。“个性化把握”的过程意味着作为把握主体的个人会根据现实及个人的需求对被把握的对象进行一定的“解释—阐释”。
上述过程落实到《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现实经历中,我们可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历史现实逼迫一大批知识分子反思资本主义社会,恰巧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物化现象的分析成为其反思及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现状的有力武器。因此,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就在知识分子的书斋和沙龙中,在“五月风暴”的学生手中逐渐脱离原作者撰写本书的初衷,产生出超出作者想象的历史效果。从这个分析框架出发,可以认为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中的异化理论也遭遇了同样的经历
四、结语
通过分析卢卡奇的早年经历,明确其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初衷是个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面对匈牙利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低潮的具体历史现实,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意图通过呼唤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其中关于物化的讨论仅是构成此核心理论的结构性论点。可见,对于思想家的作品而言必先明确其写作的初衷,同时在作品的初始语境下对其中反映出的理论体系进行还原的理解。之后则是把握它被建构的具体过程,理清它与其他理论体系的历史关系,才能避免作出不恰当的解释。
——回望孙伯鍨教授的《卢卡奇与马克思》
——读《卢卡奇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