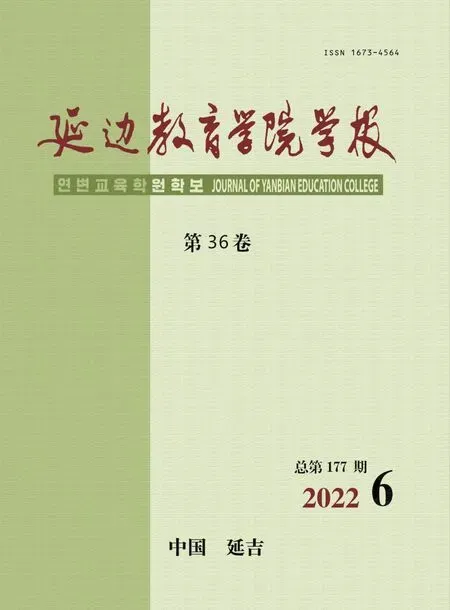中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三个维度
朴英梅
中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三个维度
朴英梅
(延边大学师范分院 政史地教研室,吉林 延吉 133000)
中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主要包括生活地域上的加入、国籍身份上的加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国家认同上的加入三个维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中国朝鲜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显示出以下变化:一是大规模人口流动下的中国朝鲜族共同生活地域趋于分散化;二是从朝鲜半岛迁入后经过几代人的发展,其国籍身份更明确;三是在跨国流动与异文化的碰撞中其国家认同更加趋于鲜明和巩固。
中国朝鲜族;中华民族大家庭;加入维度;生活地域;国籍身份;国家认同
习近平同志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1]“‘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中华民族是中国国族,包括拥有中国国籍的全体公民,指代国家整体。广义中华民族则是文化民族,包括拥有中国国籍之全体公民及海外所有对中国国家或中华文明有着认同感的人,指代的是更宽泛的中华文明共同体。”[2]基于以上定义,中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主要包括共同生活地域上的加入、国籍身份上的加入和国家认同上的加入三个维度。
一、中国朝鲜族从生活地域上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维度
目前学界研究中国朝鲜族的成果比较丰富,其观点普遍认为,“我国朝鲜族不是土著民族,而是从朝鲜半岛迁移而来的跨境民族”[3]生活地域上加入中国意味着迁入以后在同一个地区生活较长时间,形成一个共同体。据此,首先是“明末清初”[4]的观点可以作为朝鲜族在中国形成生活地域和共同体的开始。其次是19世纪后半期朝鲜北部发生三次天灾后朝鲜人的“犯禁潜入”。后来清政府出于维护边疆安全和增加财政税收的目的,开始默认在东边道垦荒定居的朝鲜人,到1881年取消“封禁”,转而实施“移民实边”政策。特别是1885年,清政府将延边地区定为朝鲜人的专垦区,吸纳朝鲜灾民垦荒定居,设管理机构,颁布垦荒优惠政策。朝鲜垦荒农户可以享受5年免租,可得房屋、口粮、种子和资金等援助。[5]据1894年统计,当时图们江北岸的4个堡共住有5990户朝鲜移民。[6]这说明,此时的迁入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且奠定了日后形成朝鲜民族聚居区的基础。再次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强制吞并朝鲜以后,国破家亡、失去土地的朝鲜农民大规模涌入中国东北地区。此时涌入的朝鲜移民有45.94万人之多[7]。“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移民达到70万人。[8]1937年-1945年期间,日本对东北地区朝鲜移民采取的措施带有浓厚的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主义政治色彩,与之前朝鲜移民的迁入有着本质区别。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朝鲜移民又重新回到了朝鲜半岛,但仍很多人留在中国东北地区继续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来守卫其生活地域安全和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权利。因此,到1953年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留在中国的朝鲜族人口仍多达112万人。[9]而共同生活地域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其积极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维护其各项权利的重要前提。
二、中国朝鲜族从国籍身份上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维度
从身份上看,我国境内的朝鲜族是拥有国籍的中国公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的重要成员。”[10]在中国朝鲜族移民史上,对于迁居东北地区的朝鲜移民,清政府曾实施“薙发易服”“领照纳租”等政策,可以说这是朝鲜族作为中华民族之一员获得公民身份,其权利得到保障,编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起点。[11]但清政府的“薙发易服”在发型和服饰上有着明显的变化,很多朝鲜移民不接受,所以到1890年代前期,归化者不到朝鲜移民总数的两成。后来清政府官方出于戍边和税收的目的,以去留相要挟,归化者方增至50%-60% 。[12]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为了抵制日本势力渗透,鼓励朝鲜移民归化入籍。而朝鲜移民也为摆脱日本人的企图、得到中国政府的庇护而主动向民国北洋政府申请“归化入籍”。此时归化入籍者为数不少。但期间,因日本人的蓄意破坏,以及中国北洋政府无法为朝鲜移民提供合法保护等原因,无奈很多朝鲜移民放弃朝鲜国籍,也放弃中国国籍,成为无国籍者。据统计,1930年代初东北大约100多万的朝鲜移民中,无国籍者占50万-70万左右[13]。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国共两党对峙的环境下,东北的朝鲜移民分散在两个不同的区域内,但从人数上,绝大多数的东北朝鲜移民生活在中国共产党保护的“解放区”,[14]他们生活在离中、大型城市较远的乡村偏远地区,背井离乡而来的朝鲜移民也是无产阶级。土地革命时,周保中强调过“东北地区朝鲜族的社会地位问题,除参加华北抗战的朝鲜义勇军,在东北的朝鲜居民一般的是视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15]1948年刘俊秀也曾强调,“确定居住在延边境内的朝鲜人民,承认为中国境内之朝鲜少数民族,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一部分。”[16]据此可知,在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新中国建设等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完全承认了朝鲜族作为中国公民的身份,并使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当家作主。
新中国成立以后,朝鲜族的公民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先是延边地委和专员公署第一书记、专员都由朝鲜族干部担任,其参政议政权利得到了充分保证;后是《共同纲领》的通过意味着朝鲜族在新中国的公民地位从法律的角度得到了保障。[17]在新中国成立时,朱德海同志代表中国朝鲜族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后在朝鲜族聚居地区成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等民族自治地方并行使民族自治权利;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其作为中国公民的身份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障。
三、中国朝鲜族从国家认同上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维度
“‘国家认同’的概念主要体现民族的政治认同与归属,其核心是国籍认可。”[18]“作为一个跨界民族,中国朝鲜族形成和增强国家认同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选择”[19]“中国朝鲜族在东北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浴血奋战,他们的命运已经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中国早已成为了他们割舍不掉的热土。”[20]
在抗日战争时期,“朝鲜同志和朝鲜群众所建立的强大的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了东北抗日联军”[21];解放战争期间,“朝鲜族组建的武装部队编入第四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为解放东北各大城市而奋勇杀敌,之后又参加平津战役,甚至一直打到重庆、广西、海南岛等地”[22];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朝鲜族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踊跃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中国与美帝国主义浴血奋战。由此可知,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中国朝鲜族的国家认同逐渐形成和发展。正如贺敬之的那句“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朝鲜族在中华民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与重要贡献,也与这片热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将中国东北视作“新家乡”。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下,国家认同的纽带也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中国朝鲜族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与信仰的力量使朝鲜族形成了一种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国朝鲜族的中华民族国族意识和文化民族意识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中国朝鲜族的新变化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后,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中国朝鲜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其发展变迁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中国朝鲜族生活地域趋于分散化
在经济全球化与城镇化的趋势中,朝鲜族人口大规模流动到韩国、日本、美国等其他国家和国内各大发达城市,在这些地区又形成了分散化的小规模的朝鲜族社区,比如北京望京、广东东莞、韩国的大林洞、加里峰洞等地都聚集着很多朝鲜族。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原来地理上共同生活地域的意义发生变化,延伸到了网络上的“共同生活圈”,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的后疫情时代,彼此之间交流的渠道更多的是在微信、微博、抖音等网络社交平台上,学习、工作、消费、娱乐等生活越来越依赖于网络平台。因此,对于中国朝鲜族而言,他们已经超越了地理意义上的生活地域,分散居住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另外,朝鲜族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使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和其他朝鲜族散居地区都出现了村屯空洞化、土地荒废、人口老龄化等现象,原来共同生活的地域也因为人口减少,村屯萎缩,发展动力迟缓等原因而出现相对分散化的情况。
2.中国朝鲜族的国籍身份更明确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朝鲜族作为中国公民的身份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此时,老一辈中国朝鲜族还仍然保留着情感上的双重性,甚至部分朝鲜族老一辈还向往着拥有双重国籍。进入21世纪,朝鲜族的老一辈中“20后”“30”后老人在世者不多,“40后”“50后”“60后”老人居多,此年龄段的老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生活在中国,尤其是和平年代生活安逸,在中国的生活幸福美满,对朝鲜半岛故土的感情渐渐淡去,反而对中国东北的感情却日渐加深,因此现在的中国朝鲜族中再无人提及“双重国籍”。而且在中国出生的朝鲜族二代、三代、四代逐渐增多,加上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日渐完善,基于享受养老金、高龄津贴等各项社会保障福利政策的需要,其国籍身份更明确。
3.国家认同更加鲜明和巩固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朝鲜族的跨国、跨地域流动更加活跃,流动人口迅猛增长。在经济全球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朝鲜族的跨国流动是以就业与经济收入为目的的流动,主要的流入地是韩国,他们的“韩国梦”是“经济梦”。这种“经济梦”的驱使下,大多数朝鲜族在韩国只能从事相对脏乱差的行业,感受到了来自韩国人的歧视与偏见,对韩国社会和文化产生排斥心理,从而加深了其对国籍祖国的归属[23]。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迅速提高,让在韩朝鲜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和自信心。[24]在面对韩国人的歧视和排斥时,祖国的强大成为他们内心最坚强的后盾,其国家认同感也更加趋于鲜明和牢固。在新冠疫情肆虐时,在韩朝鲜族宁愿放弃“经济梦”也要纷纷回到祖国的怀抱,政府也为归国人员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安置和服务。这充分说明,在他们的心目中,国籍祖国才是真正的心灵归属。
综上所述,中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主要包括生活地域上的加入、国籍身份上的加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国家认同上的加入三个维度。从生活地域的维度上,共同生活地域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其积极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前提;从国籍身份的维度上,新中国成立以后朝鲜族中国公民的身份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障;从国家认同的维度上,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中国朝鲜族形成了对中国的情感纽带,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与信仰的力量形成了一种凝聚力,使其国家认同更加趋于鲜明和巩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中国朝鲜族也发生了新变化,在大规模人口流动、在网络时代、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其生活地域更趋于分散化;在岁月的流逝中,其国籍身份更明确;在跨国流动与异文化的碰撞中,其国家认同更加趋于鲜明和牢固。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朝鲜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员的归属感进一步增强。
[1]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2).
[2]钱雪梅.论“中华民族”:概念内涵及其与国家和各民族的关系[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2):90-105.
[3]孙春日,沈英淑.我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J].东疆学刊,2006(4):54.
[4]朴昌昱.试论中国朝鲜族的迁入及其历史上限问题[A].朝鲜族研究论丛[C].延边大学出版社.1989.
[5]舒展.中国朝鲜族的形成与贡献[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5-11.
[6]摘自延吉厅同知呈所管各事宜选具清册.延边地区历史档案史料选编之一:11.“朝鲜移民”的称谓强调的是从朝鲜半岛迁移到中国东北地区的国界地理位置的变化,即孙春日说指的“国际迁移”。
[7]崔昌来等.延边人口研究[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6.
[8]朴昌昱.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30.
[9]金炳镐.中国朝鲜族人口简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63.有的学者主张,日本败亡之前,在东北居住的朝鲜人达到200万人,甚至已超过200万。但据普遍的观点,光复之前在满(东北)的朝鲜人就170万人左右(也出自本书)。
[10]金元石.关于中国朝鲜族的含义[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4):42.
[11]孙春日,沈英淑.我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J].东疆学刊,2006(4):54.
[12]孙春日认为此数据有过高估计之嫌,但因此类统计在至今的官方史料中无发现,故在此转引自孙春日,沈英淑.我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J].东疆学刊,2006(4):55.
[13]全满朝鲜人民会联合会.全满朝鲜人民会联合会会报(第三卷)[M].开明书院,1935,5(5):7.
[14]李虎.中朝日三国早期西学对应及其比较[J].东疆学刊,2004(1):22.
[15]周保中.延边朝鲜民族问题[A].中共延边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C](1945年11月至1949年1月).延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1985:359.
[16]刘俊秀.关于民族政策中的几个问题(草案)[A].中共延边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C](1945年11月至1949年1月).延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1985:392.
[17]舒展.中国朝鲜族的形成与贡献[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8.
[18]李梅花.中国朝鲜族国家认同研究综述[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2,14(02):97.
[19]朴婷姬.试论跨国民族的多重认同——以对中国朝鲜族认同研究为中心[J].东疆学刊,2008(3):37-43.
[20]李梅花.中国朝鲜族国家认同研究综述[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2,14(02):99.
[21]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丛书编委会.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丛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704.
[22]李梅花.中国朝鲜族国家认同研究综述[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2,14(02):100.
[23]金烨.祖国有多远?[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 96.
[24]朴光星.赴韩朝鲜族劳工群体的国家、民族、族群认同[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7 (03):46.
C951
A
1673-4564(2022)06-0064-03
2022—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