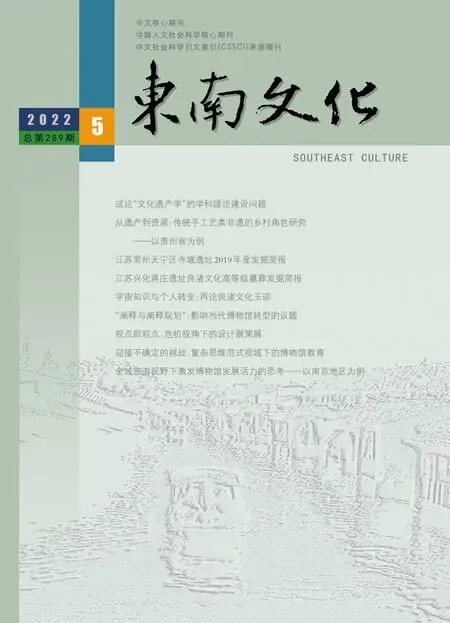再论“新博物馆学”
汪 彬尹 凯
(1.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2.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山东青岛 266237)
内容提要:“新博物馆学”是20世纪下半叶博物馆世界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但国内学界对其基本内涵的理解却长期存在着混淆、误解和偏差。“新博物馆学”在法语世界和英语世界拥有两种不同的内涵,有着各自独立的理念主张和演变脉络:在法语世界,“新博物馆学”一词在1980年由安德烈·德瓦雷提出,并随着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发展而在国际博物馆界流行起来;英语世界中的“新博物馆学”则因1989年彼得·弗格主编的《新博物馆学》一书而得名,在之后广泛使用的过程中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虽然这两个概念因其“新”的诉求而共享一些共识性主张,但是彼此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别,对它们进行清晰的区分与说明对于当代博物馆学研究来说极为必要。
作为20世纪下半叶博物馆世界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新博物馆学”(new museologies)[1]在被广泛使用与讨论的同时,也存在滥用与误用的现象。在国内学界,新博物馆学要么作为一种话语语境而出现,要么作为一种分析视角而出现,而鲜有真正直面该术语基本内涵的研究。从目前的文献成果来看,甄朔南先生(以下省略敬称)和尹凯是为数不多的试图界定、梳理和阐释新博物馆学的学者,但前者较少关注新博物馆学法语传统和英语传统的差异[2],后者则以单线进化的方式勾勒了新博物馆学的演变轨迹[3]。虽然这些研究对理解新博物馆学的基本内涵有所帮助,但它们均未能清晰准确地认识到法语新博物馆学与英语新博物馆学之间的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博物馆学在使用过程中被不断阐释,形成了多元内涵,然而,对新博物馆学复数性质的重新发现却并未触及其得以可能的两大传统。
立足于上述研究现状,笔者首先回溯新博物馆学在中国博物馆学界的传播与误解过程,考察国内学界在新博物馆学的基本内涵上长期存在的认知偏差;其次,经由原始文献的阅读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具体分析法语新博物馆学和英语新博物馆学各自相对独立的问题意识、理念主张和演变脉络。在笔者看来,对新博物馆学的再探讨不仅能澄清国内学界长期以来对新博物馆学概念的混淆,而且对于理解当代国际博物馆世界的多元脉络和思想差异也至关重要。
一、从新博物馆学在国内的传播与误解谈起
新博物馆学最早被我国(大陆地区)学者关注是在1986年。在谈到当时国际博物馆学界的新动态时,孙葆芬关注到了在加拿大、法国等国家正在兴起的“新概念博物馆学”运动以及一些新型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社会博物馆、整合博物馆——的实践经验,并简单介绍了新概念博物馆学的基本理念[4]。这里提及的“新概念博物馆学”运动,其实就是指1984年兴起的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
由于当时英语新博物馆学并未出现,这一时期中文文献所提到的新博物馆学都是指法语新博物馆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1991年,冯承柏在介绍欧美博物馆学理论时,关注到了两本理论性较强且同为“新博物馆学”之名的著作,即1988年出版的安德瑞·赫恩施莱德(Andrea Hauenschild)的《新博物馆学》(NeueMuseologie)[5]和1989年出版的彼得·弗格(Peter Vergo)的《新博物馆学》(The New Museology)[6]。前者属于法语新博物馆学的范畴,后者则是英语新博物馆学的代表之作。冯文简单介绍了两本著作的基本内容,强调其共同的革新性质,但并未关注到两者之间的差别。
或许是由于在最初引介时就未能对法语新博物馆学和英语新博物馆学进行有意识的区分,以至于这两种传统在之后的使用中逐渐被理解成为同一种思想。在1998年出版的《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严建强在介绍新博物馆学理念时,先引用了赫恩施莱德的观点,认为新博物馆学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变革运动中,接着又说,在此背景下,一些激进的博物馆学家开始批评“传统的博物馆学对技术和方法讨论太多,而对博物馆的目的和理论的研究太少”[7]。实际上,赫恩施莱德论述的是法语新博物馆学产生的背景,而对传统博物馆学的批评则是弗格在《新博物馆学》一书中的著名阐述。这一段论述将新博物馆学的两种传统前后放置在一起进行理解,而未对其加以区分,成为之后国内学界理解新博物馆学的基本模式。
甄朔南在2001年发表的《什么是新博物馆学》作为国内学者理解新博物馆学内涵与主张的基本参考文献之一,被广泛引用,但此文是将法国的生态博物馆和新博物馆学运动与英国弗格《新博物馆学》的主张整合在一起,归纳概括出新博物馆学的6条主要内容,分别是:第1条“以人为本”;第2条“强调博物馆在终生教育中的独特作用”;第3条“关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倡环境教育”;第4条“主张博物馆陈列应该有贯彻博物馆功能的非常明确的主题”,“要尽可能地利用高科技的传播手段”(原文有两个第4条);第5条“反对单元文化,强调宣扬文化的多样性,保护原住民文化”;第6条“主张博物馆的博大精深……博物馆学的内涵将与更多的学科交叉”[8]。由于文中缺少引文注释,所以笔者只能大致辨析出第1条、第3条、第6条属于法语新博物馆学的范畴;第5条属于英语新博物馆学的主张;而第2条以及两个第4条虽然代表了当时博物馆界的一些新理念,但并不是新博物馆学的核心内容,因此无法归类。同样,同年出版的《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在第一章第三节的《生态博物馆和新博物馆学运动继续在探索中前进》中,也将弗格的《新博物馆学》及其理念置于此标题之下而未加以区分[9]。上述两篇文献在国内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其对新博物馆学的理解也影响了国内很多学者的认识。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学界逐渐意识到新博物馆学的复杂性。2019年出版的《博物馆学概论》一书指出,“在博物馆学文献中,‘新博物馆学’并非单一的指称,至少可以区分为来自法文和英文两种”[10]。尹凯也意识到当代博物馆理念内部的两股力量——重置与转向,分别对应的是英国新博物馆学和拉丁美洲新博物馆学[11],不过在涉及新博物馆学和批判博物馆学的区别时,他将英语新博物馆学和批判博物馆学割裂开来,进而将其归入到法语新博物馆学的发展脉络中[12],尚未清晰地认识到英语新博物馆学、法语新博物馆学、批判博物馆学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王思渝最近在对新博物馆学在中国引入与发展过程的回顾性梳理中[13],虽然发现了新博物馆学在国内引入的两条脉络,但是未能认识到这两条不同的脉络对应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新博物馆学理念。
自20世纪90年代新博物馆学的两种传统被引介到国内,它们之间的混淆就一直存在。尽管最近几年有所好转,但是尚未被学界普遍接受。要想纠正这种概念混淆的状况,就需要借助原始文献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中,从根本上理解二者的内涵与特征,彻底厘清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新博物馆学的两种传统:情境、内涵与差异
(一)法语世界的新博物馆学
从根本上来说,新博物馆学两种不同的传统源于20世纪后半叶法国与英国面临的社会状况的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新博物馆学的理念自然也就存在差异。因此,了解新博物馆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是理解新博物馆学传统之别的前提。
法语新博物馆学萌芽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中。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北美和拉丁美洲的民权运动、1968年欧洲的学生运动、学界对地方社会的“部落”文化和社会价值的重新发现以及对传统博物馆精英主义的不满共同构成了新博物馆学运动的背景因素[14]。作为对上述变革的回应,博物馆界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变化与调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72年智利“圣地亚哥圆桌会议”(Round Table of Santiago)的召开。会议聚集了来自博物馆、教育、乡村建设和城市规划等方面的专家,探讨了博物馆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主张将博物馆作为一种直接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工具。之后这些观点被归纳并发表成为《圣地亚哥宣言》(Declaration of Santiago de Chile),对新博物馆学理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圣地亚哥圆桌会议”和《圣地亚哥宣言》也被认为是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的起点[15]。
虽然新博物馆学的社会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但其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被博物馆学界提出和关注则是在80年代。1980年,法国学者安德烈·德瓦雷(André Desvallées)在一部百科全书的《附录》中首次使用了法语形式的“新博物馆学”(muséologie nouvelle)[16]。这篇文章一般被作为法语“新博物馆学”一词的诞生处,德瓦雷也被认为是这一术语的创造者[17]。新博物馆学的首先使用可以说是德瓦雷的无意之举,因为他只是在文章里更新了“博物馆学”的早期条目,而并不是想要创造一个新的术语或思想流派[18]。因此,法语新博物馆学一词的发明和使用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并不如后来想象的那样具有特定的目的性。没有预料到的是,该术语甫一出现就被法国一批年轻的研究员(curator)接受,借此批判法国博物馆僵化的组织结构[19]。在此过程中,它逐渐被赋予了后来认为的那种批判与革新的内涵。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新博物馆学概念被正式提出、生态博物馆实践也获得快速发展时,法国学者便开始计划凝聚新博物馆学支持者的力量,并谋求其在国际博物馆界的正式地位。1982年,新博物馆学与社会实验协会(Muséologie Nouvelle et Experimentation Sociale,MNES)在法国成立。雨果·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在表述该组织的哲学使命时认为,“作为一项运动,该协会清楚地表明了它对当代社会的承诺。作为一种集会,它质疑的不是博物馆的技术,而是它的基本使命。要么通过澄清博物馆的意义来证明它们,要么通过提出替代方案来挑战它们”[20]。这清楚地表明了新博物馆学的革新和实验性质,而且这一组织的成立也为1985年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组织(Movement Internationale pour la Nouvelle Muséologie,MINOM)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之后在1983年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ology,ICOFOM)的年会上,加拿大学者皮埃尔·梅朗德(Pierre Mayrand)首次提议在委员会内部设立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以致力于“社区博物馆学”(community museology)的研究[21]。但这项提议并没有得到认可。出于对委员会消极回应的失望和不满,加拿大博物馆学界于1984年在加拿大魁北克组织了第一届“‘生态博物馆和新博物馆学’国际工作坊”(Le colloque International“Écomusées et nouvelle muséologie”),并将他们关于新博物馆学的主张发布在《魁北克宣言》(Declaration of Quebec)中[22]。随后,1985年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工作坊中,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组织正式成立,并成为国际博物馆协会的一个附属机构。作为这场理念与实践革新运动的代称,新博物馆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国际博物馆学界的普遍认可。
从《魁北克宣言》可以看出,法语新博物馆学和生态博物馆、社区发展、社会进步等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社区博物馆学”、“大众博物馆学”(popular museology)、“生态博物馆学”(ecomuseology)等概念也与其具有密切的关系[23]。彼得·冯·门施(Peter van Mensch)根据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组织的章程,将新博物馆学的内涵归纳为四个特征: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生存状况;通过跨学科的方法,在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考虑人类,环境(milieu)和情境(context)的概念至关重要;其方法和实践被用来促进居民参与;具有灵活性和去中心化的结构[24]。对社区参与和整体环境的强调以及跨学科的方法、去中心化的结构,成为新博物馆学的主要特征和关注所在。
1992和1994年,德瓦雷等人将新博物馆学领域的重要论文结集为两卷本的《浪潮:新博物馆学论文集》(Vagues:Une 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Muséologie)[25]出版,这被认为是公开宣称新博物馆学诞生的关键时刻。此书汇集了为新博物馆学的发展与反思奠定重要基础的文献,集中表述了新博物馆学的诉求和主张。但是由于此书是法语出版物,且一直没有英译本,因此它虽然在法语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在英语世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多数英语学者对法语新博物馆学的诉求和主张也并不了解。
但法语学者却关注到了法语新博物馆学和英语新博物馆学的不同。例如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组织的成员对弗格《新博物馆学》一书并未参考新博物馆学的法语“词源”表达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弗格错误地使用和“翻译”了这一术语[26]。实际上,新博物馆学一词在1958年的英文文献中就已出现[27],并不存在法语词源一说,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弗格使用的新博物馆学借鉴自1980年的法语术语。因此这一批评反而体现出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组织的成员忽视了新博物馆学在英语语境中的独立词源和特定内涵。
新博物馆学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发展高潮,但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与主流博物馆学的融合与对话,新博物馆学也失去了其先锋和革新气质。而且,法语新博物馆学的“浪潮”并没有波及大洋彼岸的英国。但是从80年代末开始,英语世界也经历了一场博物馆思想的范式转换。巧合的是,这种新的博物馆范式同样以“新博物馆学”命名。
(二)英语世界的新博物馆学
20世纪下半叶的英国虽然面临着和法国相似的世界背景,但是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国内环境。例如法国在二战后由政府主导建设了新型博物馆,20世纪60年代中央政府为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资助成立的“地方自然公园”是第一代生态博物馆的雏形[28];而英国则发展出由政府外组织主导赞助的模式,慈善信托在博物馆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更促进了博物馆运营的市场化。因此,新博物馆学在法国主要涉及去中心化和地方化,在英国则表现为对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关注;法国学者主要讨论国家和政治在文化中的作用,而英国学者强调文化市场的角色;在法国,博物馆面向的是“公民”,在英国则是“消费者”[29]。同样,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源于欧洲大陆地区及北美地区的批判理论在80年代也影响至英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八九十年代英国博物馆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30]。正是在英国这一系列独特的经济、文化和思想背景下,作为一种新理念的新博物馆学诞生了。
1989年,“新博物馆学”一词出现在英文文献中,弗格用它来命名自己主编的论文集。在《序言》中,弗格认为新博物馆学:
……来自博物馆专业和外界对“旧”或传统博物馆学的普遍不满……“旧”博物馆学过多关注博物馆方法而较少关注博物馆目的;博物馆学在过去也很少被视为一门理论或人文学科;一直以来,上述一系列问题几乎未被提及,更不用说被深入讨论了……除非彻底地对博物馆在社会中的角色进行重新审视,即不仅仅用更多的收入或更多的观众等标准来衡量博物馆的“成功”,否则,英国或其他地区的博物馆可能会被贴上“活化石”的标签。[31]
相较于德瓦雷的无意之举,弗格笔下的“新博物馆学”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目的性:一方面表达了对“旧博物馆学”的不满,另一方面传递出想要创造出一种新型博物馆理念的意图。
如果说弗格在《序言》中只对新博物馆学的特征作了基本的描绘,那么书中所收录的论文则具体体现了新博物馆学的基本主张。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曾从中识别出了新博物馆学的三个重要内涵,即新博物馆学认为博物馆物件的意义不是固定的,而是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重新关注那些早期被认为是在博物馆学领域之外的事项,例如商业主义和娱乐;理解博物馆和展览如何被观众感知和联系,从观众/公众的角度理解博物馆参观[32]。它们构成了新博物馆学的基本内涵。
除了《新博物馆学》一书的具体主张,“新博物馆学”一词所代表的对传统博物馆的批判态度也很快被其他学者接受,并被用来概括20世纪90年代新出现的博物馆理念。例如,美国学者茱莉亚·哈里森(Julia D.Harrison)就使用新博物馆学指称20世纪90年代巴纳姆(Barnum)幽灵的重现——博物馆的商业经营模式和迪士尼化[33]。这其实与《新博物馆学》对商业和娱乐的关注不谋而合,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和美国都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府大量削减公共资金,迫使博物馆不得不依靠自身收入和社会支持维持运营[34]。因此,商业经营和娱乐化就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下博物馆的一种新运营模式。而1997年英国新工党的执政及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政策的实施也赋予了新博物馆学新的内涵:博物馆和图书馆、档案馆被共同纳入到政府的文化政策之中,成为执行社会包容政策的工具[35]。对少数和弱势群体的表征和对多元文化的呈现成为博物馆的重要关注。新博物馆学也开始寻求更加包容、更加民主和更能代表多元化社区的方式,强调博物馆与社区的合作、多元声音的重要性,以及承认人们在展示和保存其遗产方面的权利[36]。
随着新博物馆学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它有时也成为一种新的博物馆思想范式的代称,更宽泛地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博物馆在理念、思想或哲学层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37]。这种新博物馆学的内涵似乎可以容纳上述英语新博物馆学的所有内容。在这一层面上,“批判博物馆学”(criti-cal museology)、“反身性博物馆学”(reflexive museology)等概念也经常被不加区别地纳入到新博物馆学范式中[38]。
1989年以来,英语新博物馆学至少发展出六种不同的内涵:对博物馆社会角色给予重新检视的理论化的人文学科,博物馆藏品意义阐释的情境化转向,博物馆对商业主义和娱乐的重新关注,博物馆对观众参与及体验的关注,寻求更加民主、包容和多元表征的博物馆政治工作,一种新的博物馆哲学范式。但是在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新博物馆学也面临着一系列批评:它被认为“没有那么新了”;它对博物馆理论和政治工作给予过度的关注,从而造成与实践的分离。因此,如何弥补理论与实践的裂隙成为当前英语博物馆学界的重要关注内容[39]。
(三)差异与对比
二战后法国和英国面临不同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使得新博物馆学在法语世界和英语世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理念主张,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根本性差别。在集中表述法语博物馆学思想的《博物馆学关键概念》一书中,德瓦雷和方斯瓦·梅黑斯(François Mairesse)就对这两种不同的新博物馆学理念作了区别:
新博物馆学……自1980年代初期起网罗一群法国博物馆理论家,自1984年起更扩大至国际间的博物馆学讨论。此一思想运动强调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以及博物馆学的跨领域特质,同时也强调更新的表达与沟通方式,其兴趣特别朝向与传统博物馆将收藏品置于核心相对所构想岀的新型态博物馆方向发展:有如生态博物馆、社会博物馆、科学技术文化中心以及一般大多数试图将文化遗产运用于地方发展的新尝试。英文的“新博物馆学”出现于1980年代末期,且以一种对博物馆的社会与政治角色的批判论述的姿态呈现。这对法文的“新博物馆学”词语的普及造成了一定的混淆(英语系民众极不了解法文的说法)。[40]
而威尔克·海宁(Wilke Heijnen)认为,弗格的新博物馆学理论是基于机构的,希望博物馆可以向更多的观众开放,吸引、包容更多元的观众,因此可及(access)、参与和社会包容是其关注的重点,自上而下的方式更常见;法语新博物馆学则更多地涉及发展的理念,并且表达了一种对进步的内在渴望,其基本方法是自下而上的[41]。这意味着在博物馆的本体论层面,英语新博物馆学希望传统博物馆机构能够革新自身的理念和实践,从而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而法语新博物馆学则放弃了传统博物馆机构,试图通过一些新的博物馆形式——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整体博物馆——实践自身的理念。
也有一些学者出于新博物馆学的法语和英语形式容易引起混淆的原因,倾向于使用“批判博物馆学”代替英语新博物馆学,例如杰西-佩德罗·劳伦特(Jesús-Pedro Lorente)就对法语新博物馆学和英语批判博物馆学作了区分:新博物馆学起源于法国,参与者大多是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通过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组织发挥了很强的领导力,主要关注生态博物馆以及将代表着乡村和工业过去的人类地域和栖息地“博物馆化”(musealizing)的过程;而批判博物馆学发展自后现代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即英语世界),参与者主要是艺术史学者和人类学家,他们主要在大学里工作,联系相对松散,主要关注博物馆的表征与阶级、性别、多元文化、原住民和非西方文化的问题[42]。从劳伦特对批判博物馆学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一理念和英语新博物馆学有很大的相似性。
三、结语
自20世纪90年代新博物馆学的两种传统被引介到国内,它们之间的混淆与误解就一直存在。在笔者看来,共同使用“新博物馆学”这一术语应该是造成误解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国内学者习惯于强调“西方”内部的一致性而疏于对其差异性的关切,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新博物馆学的英语与法语传统之别。本文借助原始文献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一方面呈现了这两种理念在中国传播与误解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具体分析了二者在法语和英语传统中不同的产生背景、基本内涵及特征。
法语新博物馆学萌芽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中,但这一术语直至1980年才被德瓦雷提出,并随着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英语新博物馆学则是因1989年弗格主编的《新博物馆学》一书而得名,并在之后广泛的使用中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法语新博物馆学和英语新博物馆学并不是一条前后相继的思想脉络,而是法国和英国的博物馆在20世纪后半期对其面临的特殊社会状况的回应,它们在基本内涵、理念主张等方面都存在着根本性差异。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语新博物馆学和英语新博物馆学内部也不是同质的,它们既有时间上的内涵演变,也有地域上的概念分化。在历史层面,虽然冯·门施将“新博物馆学”的最早用法追溯至1958年,但笔者发现,这一术语在1908年就已经被使用,指的是博物馆建筑空间中研究系列与展览系列的分离[43],以同时满足大众和专业人士的兴趣[44]。卡斯帕·博登·克拉克爵士(Sir Caspar Purdon Clark,1904—1910年担任馆长)领导下的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更新与1909年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新馆的建设是其代表[45]。但这种用法还未得到博物馆学界的关注,如何理解其内涵及其与之后术语的关系,仍值得学界思考。
在地域层面,法语新博物馆学在法国等欧洲国家与在拉丁美洲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是发达的前殖民国家,后者则是相对落后的前殖民地国家;法国的新博物馆学已经融入主流博物馆学之中,拉丁美洲的新博物馆学则演化成为新型的社会博物馆学(sociomuseology)[46]。在英语国家,英国和美国、加拿大虽然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北美地区原住民的历史与文化等特殊的社会背景,也使北美学者所理解的新博物馆学不完全等同于英国学者所说的新博物馆学[47]。限于篇幅,本文未能对这些内容加以阐释,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能对新博物馆学在不同语境中的具体内涵和特征进行更进一步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