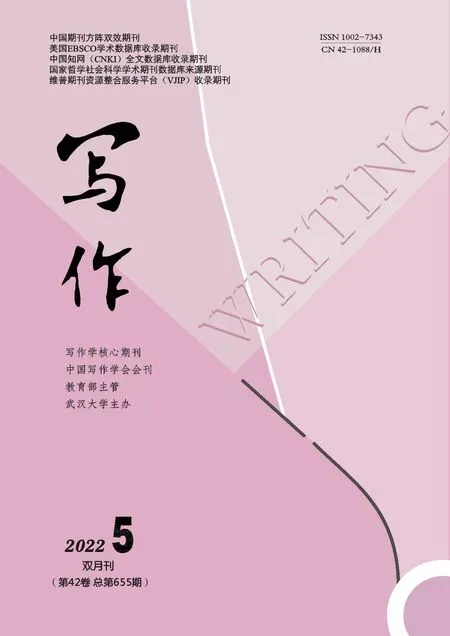被“围观”的写作
——论莫言小说集《晚熟的人》
蒋成浩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使得边缘化数十年的中国文学再次成为社会焦点。“诺奖”不只是莫言的个人荣誉,在网络媒介推波助澜的宣传下,它已成为复杂的象征符号。“诺奖效应”在莫言周围集聚了数量庞大的“围观”群体,他们把与莫言有关的文学事件营造成娱乐化的全民狂欢。在“被围观”的目光中,“诺奖魔咒”的争议一直存在,2020年《晚熟的人》新书发布会上,莫言也坦言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2012年至今,莫言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公众的密切关注,他的言行成为全民围观的娱乐中心,他迟迟未有新的长篇面世,也让“好事者”感叹“诺奖魔咒”的应验,莫言真的“无言”了吗?
《晚熟的人》是莫言获得诺奖后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共12篇,除《澡堂与红床》是他获诺奖前的作品,其余11篇皆是他获诺奖后的创作。一如既往,高密东北乡依旧是莫言苦心经营的文学空间,是属于莫言的文学“品牌”。在这部小说集中,几乎有一套固定不变的模式——以“我”的返乡见闻作为小说叙事的主要线索。鲁迅是乡土小说返乡叙事模式的集大成者,莫言也在作品中有明显致敬鲁迅的细节。因此在阅读这部小说集的过程中,很难不跟鲁迅的“返乡作品”进行比较。以莫言创作史观之,又很难不跟他获诺奖前的作品进行对比。两相对照中,能够更全面地窥见莫言获“诺奖”后写作的“进”与“退”。
一、主体之“我”:从洞见到盲视
《晚熟的人》中的每一篇小说,都有着相对一致的叙述视点。小说视点决定了叙事的基本架构,站在不同的观察位置,自然会看到不同的风景。莫言这部小说集将“小说之我”与“现实之我”熔铸为一体,有“自叙传小说”的色彩。在《晚熟的人》新书发布会上,莫言坦言“这部小说,我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同时作为作品里的一个人物,深入的介入到这本书了”①黄蓥:《莫言线上分享新书150万人“围观”》,搜狐网,网址:https://cul.sohu.com/a/512459855_120099877,发表日期:2020年8月1日。。于是我们看到,在小说中,“我”反复出现,“我”的名字叫“莫言”,是一位获得国际大奖的著名作家,小说中“我”的返乡之旅为作品增添了很强的现实维度,真实的“莫言”与小说中的“莫言”交错存在,使得作者随心所欲地处理现实经验与文学构思的关系,但同样也模糊了“现实之我”与“小说之我”的界限,以至于频频出现叙事上的断裂感、错位感与生硬感。
“返乡”是文学的母题之一,乡土“给失意者提供一种温和的宽宥和庇护;它是倦旅者温暖的泊留地、诗意想象的源泉”②叶君:《感伤的行旅——论侨寓者返乡》,《中州学刊》2005年第5期。。中国新文学作品里不乏经典的返乡叙事,鲁迅、沈从文、师陀等,他们将自我经验与想象创造融为一炉,借助叙述者的“返乡”,呈现其对乡土世界的思考。文学作品不单具有审美的特性,更要负载深刻的思想内涵。鲁迅借助“我”的返乡,书写有关启蒙与反抗、希望与绝望,以及国民性的命题,在新旧交错的时空里,他笔下的鲁镇,逼仄、阴沉、压抑,饱含作者对凝滞的现实中的启蒙忧思,“反抗绝望”诞生于一次次的返乡旅途。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记录了返乡见闻,沅河两岸百年颓败的街镇引发了他有关历史“常”与“变”的思考,故乡始终是他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
回到莫言,《晚熟的人》不再有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反思的退化”表征在叙述者“我”的盲视。小说集中的12个故事正如高密东北乡的人物志,莫言则是以“我”为视点的“讲故事的人”。小说的故事很精彩,作为现实与虚构维度的“我”,却越来越空洞无力。莫言在长篇小说《蛙》中,“我”的返乡揭示出乡土的伦理世界在“计划生育”国策下的崩坏,反思着政治暴力中人性的扭曲与沉沦,作为叙述主体的“我”保持着知识分子清醒的批判意识。到了《晚熟的人》小说集里,“我”返乡的最终的目的只是“猎奇”,“我”完全沦为无“主体性”的叙述机器,高密东北乡人事的哀乐与“我”若即若离,它们是作家与材料的关系、是看与被看的关系、是“我”鉴赏苦难与乡民苦难表演的关系。
通过文本的细读,我们可以看到莫言小说中“我”是如何从一个“反思叙事者”退化成“无主体性”的“叙事机器”的。在《等待摩西》这篇小说里,面对生命的苦难,莫言给出了一个“玄学”的结尾。小说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我”数次返乡,村民“柳摩西”的故事让我念念不忘。在“我”印象中,摩西头脑精明,敢为人先,改革开放后率先经商,成为村里最早的万元户,建起了小洋楼。然而,在摩西事业蒸蒸日上之际,却离奇地失踪了;第二条线索是“摩西”与“马秀美”回肠荡气的爱情,年轻时,一穷二白的摩西与马秀美突破世俗层层的阻力,结合在一起。但天不遂人愿,摩西离奇出走,成为一桩悬案,马秀美的生活也一落千丈,她对摩西的爱近乎癫狂,数十年彷徨于希望与绝望之间,过着“祥林嫂”般的生活;第三条线索,当失踪了多年的摩西再度出现时,却做起了诈骗的行当,“我”四处打听摩西出走的真实原因,想要解开摩西出走的谜团。当“我”来到摩西家的庭院时,发现一直因摩西出走而受尽折磨的马秀美面色红润,沉浸在幸福的家庭氛围中。小说如此结尾:
我看到院子里影壁墙后那一丛翠竹枝繁叶茂,我看到压水井旁那颗石榴树上硕果累累,我看到房檐下燕子窝里有燕子飞进飞出,我看到湛蓝的天上有白云飘过······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于是,我转身走出了摩西的家门。①莫言:《等待摩西》,《晚熟的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33、132、119页。
小说的这一结尾不可谓不精彩,充满“玄学”的气息,辛苦寻找,一朝顿悟。“我”煞费苦心想要解开谜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当“我”踏进摩西家门,看到摩西出走后形销骨立的马秀美再度精神起来,意识到自己无非是“好事者”,一切都不那么重要,原因亦不必再究。单就结尾而言,莫言显示出他对人生世相的思考,但也正是结尾对“我”苦苦追寻的“解构”宣告了“我”好事者的实质。在整篇小说中,“我”是被故事推着走,始终被动、始终空洞、始终失语,只是小说叙事的机器。有意思的是,在这篇小说里,莫言有意识的借鉴鲁迅《祝福》中的细节,在结尾处“我”也明言由“马秀美”联想到“祥林嫂”,“我想象中她应该腰背佝偻、骨瘦如柴,像祥林嫂那样木讷,但眼前的这个人,身体发福、面色红润,新染过的头发黑的有点妖气,眼睛里闪烁着的是幸福女人的光芒。我知道我什么都不要问了”②莫言:《等待摩西》,《晚熟的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33、132、119页。。由此可见,莫言在塑造马秀美这一人物形象时,有意无意地参照了鲁迅的《祝福》。当摩西无故消失,马秀美过着步履维艰的生活,活在精神的惶恐之中,价值的虚无感使她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我”与马秀美相遇,作者模仿了鲁迅《祝福》里“我”与祥林嫂相遇的场景。
我在集市上遇到了马秀美,她擓着一个竹篮,里边盛着十几个鸡蛋。从她灰白的头发和破烂的衣服上,我知道她的日子又过得很艰难了。
她眼里噙着泪花问我:“兄弟,你说,这个王八羔子怎么这么狠呢?难道就因为我第二胎又生了个女儿,他就撇下我们不管了吗?”
我说:“大嫂,卫东不是那样的人。”
“那你说他能跑到哪里去了呢?是死是活总要给我们个信儿吧?”
“也许,他在外边做了大买卖······也许,他很快就会回来······”③莫言:《等待摩西》,《晚熟的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33、132、119页。
不难看出,这几段“我”与“马秀美”的对话像极了《祝福》里“祥林嫂”在大雪天对“我”的发问。不同的是,在《祝福》中,祥林嫂遇见“我”时已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祥林嫂追问人死之后有没有灵魂,是为了得到精神的告慰,这一细节笼罩着宗教的崇高感。马秀美提问的是“摩西为什么这么狠,抛下妻女而不顾”。通过这两篇小说中“相遇时刻”的描写,能看到两位作者的高妙与笨拙之处。祥林嫂、马秀妹的问题,都令小说中的“我”局促不安,不知所措。同样是没有答案的问题,祥林嫂的发问使作为返乡知识分子的“我”感到震颤,引发“我”对旧礼教与新道德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的思考。“灵魂”的有无问题,对于书斋里的“我”,自然不成问题,然而直面濒临精神困境中的祥林嫂,启蒙竟有可能成为压垮祥林嫂的最后一根稻草,由此,“我”也深刻洞察了知识分子启蒙者身份的尴尬处境。莫言的《寻找摩西》中,马秀美的提问令我无言以对,语言失去了效力,变得空洞,这番缺少心理描写的对话只写出了现实中无所劝慰的“尴尬”,没有任何深层的指向,远没有《祝福》中祥林嫂与“我”相遇时的那种心灵震颤。而“我”亦只能作为“失语”的存在,造成我“失语”的原因,是“我”与现实处境之间的隔阂。莫言在小说里塑造的“我”,时时陷于世俗与超拔的两难,随着叙事的推进,反而逐渐取消了“我”作为主体的自我反思的精神,沦为叙事的机器。
《晚熟的人》里的诸多小说中,“我”总是不停地追着故事走,“我”以功成名就的返乡者身份,观察到的是乡间五花八门的故事,作者急于通过“我”为读者讲述这乡间的传奇,而看不见故事背后对人性、人情、人伦的批判性思考。莫言笔下的“我”过分钟情于故事的讲述,无形中消弭了“我”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反思,以至于小说笼罩在乡村传奇故事的氛围中,“我”最后则沦为“不用问”“不用管”的“好事者”。莫言使“现实之我”过度的操纵着“小说之我”,甚至出现以“小说之我”为“现实之我”辩护的情形。莫言似乎无力于对人物进行细致且深刻的心理刻画,对人性的洞察也浅尝辄止,或许,正由于“现实之我”的过度介入,阻止了莫言对“自我”的剖析,因为任何的心灵探索都必将触及主体的阴暗面。在《等待摩西》的故事里,“我”早已卷入到摩西、马秀美的生活中去,“我”看着马秀美家徒四壁、生活艰难,无人肯伸出援手,冷静超然得如同木偶。“我”在酒楼里与战友叙旧,推杯换盏,畅谈往事,摩西的故事不过是我与朋友酒桌上的谈资,“我”深深地参与到故事中去,却淡淡地沦为故事的叙述者而已,丝毫看不到“我”的主体性批判之所在。
二、匠气兴起与灵韵消逝
所谓“匠气”与“灵韵”,是审美接受中的两种美学体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如果雕琢过度,作品就常失却自然之美,流于匠气。李裕德《文章论》中就明言“琢刻藻绘,弥不足贵”①李裕德:《文章论》,张文治主编:《国学治要集部》,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6页。。王夫之《薑斋诗话》借齐梁诗批评道:“咏物诗齐梁始多有之。其标格之高下,犹画之有匠作,有士气。征故实,写色泽,广比譬,虽极镂绘之工,皆匠气也。”②王夫之:《薑斋诗话》,陈伯海主编:《唐诗论评类编》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65页。中国传统文论中,尚自然天成,反对过于刻意。与“匠气”相对的,是“灵气”“灵韵”,亦即谢眺所言“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黄庭坚则以“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为文章优劣的标准。西方的文论系统中,1939年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指出了大规模机械生产时代艺术品“灵韵”消逝的现象。灵韵,是艺术作品所传递出的精微的审美心理体验,与传统的“仪式崇拜”相连。
具体而言,经典的小说作品无论在情节的安排上,还是人物的塑造上,往往都形成自足的逻辑与美学系统,使思想的深度通过不悖于“心灵真实”的叙述呈现出来。在这样的作品中,作者隐匿起来,小说的舞台由作者塑造的人物掌控着,情节也由他们推动,人物在他们的世界里歌唱与悲恸,沿着他们的生活逻辑展开命运的演出。而蹩脚的小说则能明显感受到作者的苦心安排,作家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常常介入到小说情节中,于是小说人物成了作者的提线木偶,作者不停地制造矛盾,补救情节漏洞,模糊了“导演”与“演员”的生活界限。
《晚熟的人》里,莫言早期小说中“汪洋恣肆”的神思与充满质感的语言修辞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过度的节制与刻意的经营。情节密度提高了,一个情节推着另一个情节前进,以故事性掩盖小说思想与艺术上的缺陷。“诺奖”归来后的莫言,在处理“小说之我”与“现实之我”中裹足不前,莫言试图将自身的真实经历植入小说中去,现实的强力介入使他无法抛弃知识分子对乡民的俯视。文本中“我”的身份也是国际著名作家,也叫“莫言”,“现实之我”的盛名反而给“小说之我”带来负累。小说中经常能看到现实与虚构维度的自我意识的搏斗,这种搏斗简而言之就是小说之“我”想要挣脱作者的操控,有自我发展的意愿,但作者却摆脱不了现实身份对小说人物的介入,以至于要时时权衡现实身份与小说中“我”的关系。甚至于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现实的“莫言”与小说中的“我”互相掣肘,因为小说中叙事者“我”是以莫言为原型,导致莫言在叙事中生怕对“虚构之我”的过度着墨会有损现实形象,从而在塑造“小说之我”时笔法拘谨,想象力也趋于干涸。
艺术虚构与现实经验之间产生了拉锯战,这两者对作家而言本不成问题,但或是由于“诺奖”的原因,莫言在创作时无形中感受到“被围观”的压力,最终少了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大开大合的笔法,而多了谨慎与匠气。《晚熟的人》中最失败的角色就是“我”,“我”缺少心理深度,温温吞吞、欲说还休、欲行又止,沉迷于对乡间故事的开采、挖掘,但毫无反思的能力,只是故事的讲述者。莫言在小说里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故而试图以解构的形式自我开脱,《火把与口哨》里,情节碾压着情节,以至于莫言在小说中说:“情况大概如此,大家看,我这哪里像是写小说啊?简直是写交代材料或是记流水账。”①莫言:《火把与口哨》,《晚熟的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25页。这句话既是小说叙事的自我解构,也是莫言对其写作状态的自况。
此外,这部小说集的匠气还体现为莫言时常在“小说之我”中掺杂“现实之我”的困惑,借“小说之我”浇莫言胸中块垒,但却没能开掘出“我”的性格深度。具体表现在莫言通过小说中“我”的自述,来为现实中的自己进行维护与辩解,以塑造“现实之我”的正面形象。《晚熟的人》里描写了大量性格有缺点、相对饱满的圆形人物,而唯一毫无缺点、缺乏立体感的人物就是“我”。小说中的“我”以正面的知识分子返乡者的形象出现,“我”是懵懂无知、充满好奇、饱含同情却耽于行动的旁观者。在《红唇绿嘴》一文中,莫言巧妙地借助“小说之我”抒写了“现实之我”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借助主人公“高参”之口,道出了“我”的现实愤懑。
“我看到‘公知’骂你‘奴才’,‘极左’骂你‘汉奸’,你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受气。这两伙人其实是一伙的,他们都是嫉妒你。我那个急啊!恨不得赤膊上阵帮你去打架,但后来我明白了,在这个时代里,必须利用网络,这个道理我前几天对你说过,千言万语一句话,得网络者得天下。”
“表哥,听说你得奖后才赚了几千万?你太笨了,如果我帮你经营,一年我可以让你赚一个亿。”②莫言:《红唇绿嘴》,《晚熟的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8页。
莫言借助小说人物之口,对自己遭受的不公表达了愤怒。于是我们看到,莫言现实身份在小说中的过度介入有着强烈的目的性,对“现实之我”的辩解有之,美化有之,独独缺少自我反思,更没有触及对“我”人性幽暗面的解剖,以至于“我”的形象的弱化。莫言把现实的自我“化”为小说的叙事者,却“化”得很生硬,似乎处处要依据现实身份来做与之相匹配的描写。在作者苦心经营之下,小说的主线叙事显得扭扭捏捏,瞻前顾后。《晚熟的人》里,莫言早期小说中性格饱满、敢爱敢恨、敢于剜心自食的反思性叙事主体消失不见了,转而变成了处处顾及作家现实形象的提线木偶。在现实与虚构互相掣肘的纠缠中,匠气兴起,灵韵消逝。
莫言在小说《红高粱》《檀香刑》《生死疲劳》《丰乳肥臀》中将叙事才能发挥到近乎“狂欢”的境地,笔触所指、机锋所向,往往自然流泻,情绪如狂涛漫卷,笔势如天马行空,语言与思维并没有太多阻塞。此外,“他对色彩与气味有着良好的感受,并刻意追求对它们的感觉以及用上好的文字将它呈现于人”①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页。。谢眺诗论所言“好诗完美流转如弹丸”大抵如此。谈及小说的人物塑造,沈从文曰“贴着人物写”②汪曾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晚翠文谈新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5页。,一“贴”字成为不二法门。小说中的人物应当获得它自身的独立性,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如其所是,而不必如作者所是。莫言《晚熟的人》中的“我”,被虚构与现实中的两个“主体”所操控,两个“我”互相利用,互相掣肘,最终成为没有个性的叙事机器。
三、故事为王:传奇化与空洞化的乡间
早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莫言就做了《讲故事的人》为主题的发言,他自觉地将自己定位成“讲故事的人”。诚然,身为小说家,讲故事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但小说家如果仅仅沦为故事的叙述者,追求故事性,终将成为“故事”的奴隶。汪曾祺曾言:“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太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不大真实。”③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集〉自序》,《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如何处理作为材料的“故事”,如何“讲故事”,是作家必须直面的问题,最终达成故事性与思想性的融合,则是经典小说的特征。“诺奖”归来后的莫言,“讲故事”的技法越来越娴熟,但内蕴在故事中的思想深度却逐渐退隐。
《火把与口哨》颇有代表性,整篇小说依旧以“我”为叙事线索,但故事的讲述犹如放电影,人物的出场,情节的推进,都被固定在模式化的位置上,“摄影师”的镜头对准了先后出场的人物,依次展开故事的叙述。小说开篇,讲述的是村里教书先生宋老师的故事。村里的小学设在一个被历史遗弃的教堂里,教堂的二楼墙上,画着巨大的“狼画”,宋老师终日住在教堂,与妻子分居两处,后来一场大火焚毁了教堂,也烧死了宋老师和他的儿子。紧接着由宋老师的死引出“我三叔”迎娶镇上瘸腿姑娘顾双红的故事,“我三叔”会吹口哨,技艺超群,引得调戏过顾双红的三个流氓青年都仰慕不已。“我”“三个流氓青年”连同村里的“笔杆子”杨结巴,因顾双红而结为兄弟。三叔在采煤时发生瓦斯爆炸而殒命,接着又引出“我”三婶顾双红的传奇经历。三叔死后,三婶顾双红接连遭到命运的打击,三婶育有清泉、清灵一儿一女,先是儿子清泉被狼叼走,尸骨无寻,以至于村里流言四起,认为是清灵受到人贩子的蛊惑,出于对弟弟的嫉妒,眼睁睁看着人贩子带走了清泉。清灵不堪村里的流言与母亲顾双红的盘问,喝下“敌敌畏”自杀了。三婶顾双红沦为了当代版的“祥林嫂”,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找到儿子的尸骨,终于,在一个月夜,“我”与三婶顾双红举着火把,找到了林中的狼窝,三婶在愤怒与绝望之中砍死狼群,为儿子报得大仇,不久后卧床而终。
这篇小说故事情节密度之大令读者屏气凝神,无法分神,在莫言出色文笔的加持下更是精彩异常,“我”与三婶顾双红“月夜屠狼”是整个故事的高潮部分,莫言将其安排在小说的结尾,可谓煞费苦心。然而细心品读就会发现,整篇小说的故事一环扣一环,三个故事分别以死亡告终,死亡成为叙述的起点,亦是终点。这篇小说在《晚熟的人》中最为传奇,莫言再次借鉴了《祝福》中祥林嫂的故事。不同的是,《祝福》在情节密度上比《火把与口哨》简单得多,但“简单”的《祝福》却留下了深刻的思想与余韵,情节“复杂”的《火把与口哨》则除了阅读时“传奇故事”的吸引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余韵可言。莫言在这篇小说里究竟想要表达什么?爱的质朴、现实的魔幻、命运的不公、谣言的杀人、乡村伦理的伪善,好像什么都有涉及,又好像什么都浅尝辄止。小说中也有引人深思的地方,尤其当三婶顾双红的儿子清泉被狼叼走后,女儿清灵作为唯一的见证者,她的“实话”却因为村中人找不到狼的蛛丝马迹而变成“假话”,各种卑劣的流言四起,都指向清灵撒谎,认为是因为清灵的疏忽才导致清泉失踪。更令人意味深长的是,身为母亲的顾双红沉浸在丧子之痛中,也丝毫不顾因流言而惴惴不安的女儿,对清灵百般怀疑、质问。最终清灵不堪精神的重负,喝农药自杀。这段情节在小说中极具批判价值,它道出了乡村社会某些难以移除的痼疾,人与人之间打着邻里相好的温情旗号,实则情感冷漠、疏离,凸显了这种伦理道德的脆弱与虚伪,“爱”沦为了精神屠戮的工具。可惜的是,莫言急于讲述“精彩的故事”,无意于在故事的细枝末节处做更深入的开掘,这一情节很快被故事中的“月夜屠狼”高潮所淹没。
莫言显然钟情于鲁迅的《祝福》,《火把与口哨》中三婶的儿子被狼给叼走的情节,无疑是对《祝福》笨拙的模仿。祥林嫂失去了儿子,她认不出自己的敌人是谁,只能归结于命运,变得疯疯癫癫。三婶顾双红失去了儿子,却坚定的以“狼”为敌人,向“狼”复仇,这成为她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大仇得报后,才安然死去,这样的情节安排使故事完全沦为乡间传奇。《晚熟的人》中,除了《天下太平》在节奏上稍显舒缓,其余诸篇“我”都在急不可耐地讲故事,偶有思想的火花,也很快被情节的潮水吞噬,星星之火,终未燎原。
谈及这部小说集的创作,莫言说“我的年龄变大了,我的视野可能变广阔了,但是我的思想是不是变深刻了?很难说,但是变复杂是肯定的”①莫言:《晚熟代表了求新求变——从〈晚熟的人〉开始的漫谈》,文汇网,网址:https://wenhui.whb.cn/third/baidu/202009/22/371876.html,发表日期:2020年9月22日。。莫言获奖之后,成为媒体捕捉的焦点,每次的返乡之旅也都受到特别的关注,乡间故事四面八方向他涌来,起码在写作素材上,他比其他作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也正如其所言,他的视野变广阔了,“思想是不是随之变深刻了,很难说”。读《晚熟的人》,会让人感到“过瘾”,不过在获得阅读快感之余,总觉得缺少些思想的洞见。这部小说集的12篇作品,体量不一,故事情节的密度极大,《晚熟的人》《火把与口哨》《红唇绿嘴》故事一波三折,小说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遭际密雨般倾泻而出。作为故事叙述者的“我”,失却了思考的能力,“我”被故事牵引,“我”四处打听乡野故事,最终消失在故事的大潮中。
《晚熟的人》收获了市场销量,一方面固然是“诺奖”带来的象征资本,另一方面这部小说集的故事的确足够“精彩”,能引起阅读的快感。但对于莫言研究者而言,《晚熟的人》是一道难题,它在艺术上似好非好、似坏非坏。批评它,有哗众取宠之嫌;肯定它,又觉违背自己的心意。讲故事的人,口若悬河,修辞譬喻,精彩非凡,然而却处处流露着浓重的匠气,批判性与反思性也不知遁于何处。《晚熟的人》里再也找不到莫言早先作品中所隐含的价值批判的锋芒,故事取代了一切,那些精美的修辞语言在脱离了思想支撑之后,显得空空洞洞,如奇幻的空中楼阁。
结语
《晚熟的人》首印40万册,两个多月间,已经第五次印刷,由此可见“莫言归来”强大的魅力攻势。书的腰封上赫然写着只有莫言堪当的宣传语“诺奖后首部作品”“十年蕴积,人事全新;一言置地,壁立千仞”。腰封后面则附上大江健三郎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艾斯普马克的评语,分别是“如果在世界上给短篇小说排出前五名的话,莫言的应该进去”,“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市场运作的商业手段很能搔到读者的“痒处”,吊足了莫言“围观读者”的胃口。
《晚熟的人》已然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莫言“讲故事”的功力丝毫未减,但在故事精彩、可读性强的背后,却是精神向度批判性反思的失落。具体表现在小说叙述者“我”的主体性反思的缺失,莫言似乎难以摆脱自我形象的现实影响,将“现实之我”强烈的介入到小说叙事中去,使得“小说之我”成为无主体性的提线木偶,“我”成了小说中最扁平的人物形象。其次,莫言沉湎于对乡间故事的打捞,高密度的故事情节损害了小说思想意蕴的表达,使得许多灵光一现的有待深入挖掘的细节淹没在情节的海洋中,莫言真正成为“讲故事的人”。最后,《晚熟的人》或多或少照见了莫言写作中灵韵的消逝,没有了汪洋肆意的文风,没有狂涛漫卷的情绪,也无力深入人性的幽暗明昧处,有的是充满匠气的营构与空洞乏味的抒情。在“被围观”的状态下写作,实属不易,莫言要想打破“诺奖魔咒”,还有待更有力的作品予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