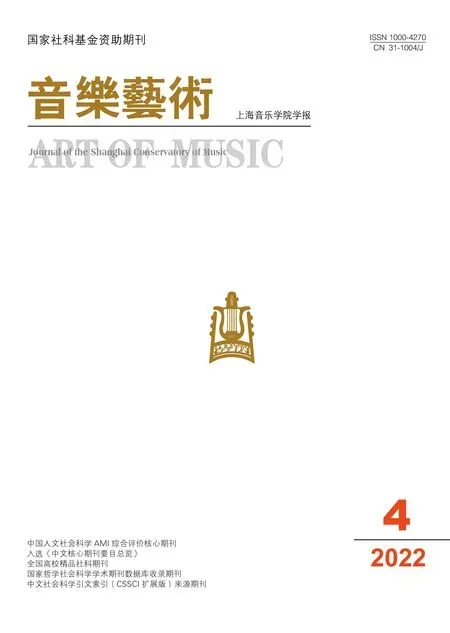一带一路上的梨形琵琶
吴慧娟 宋婉忻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上的梨形弹拨乐器,起源于史前美索不达米亚的一种叫“乌德”也称“巴尔伯特”的弹拨乐器。在中国演变成被称为“琵琶”的乐器。不仅乐器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演奏姿势由横抱、斜抱转为竖抱,演奏方法由指肉或加内指甲触弦,转为以指甲面触弦的奏法,这是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审美观念的转变。一带一路促成了沿途各种梨形式弹拨乐器的产生,其间主要是西洋的琉特琴属和中国的琵琶属。这一切都是一带一路带来的开放、包容、接受、变化的结果,对今人有着极大的启示。
引言
“梨形琵琶”,顾名思义,就是那种乐器共鸣箱体下宽上窄、似梨子形状的琵琶乐器。这种名称显然就是为了与圆形共鸣箱体的弹拨乐器相区分。早在魏晋时傅玄(公元217—278)的《琵琶赋·序》中就已经讲到那时的琵琶:“今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之象也;盘圆柄直,阴阳之叙也;柱有十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①这里先要分辨两点:一是所谓“盘圆柄直”的乐器,其实就是后来被称为的“阮”或“阮咸”等弹拨乐器,它们的乐器形状不是梨形而是圆形的,但是,在那时却是最先被称为“琵琶”的。之后,又有的将此器称为“直项琵琶”,这似乎更为恰切些,至少加了“直项”两字与后来的“曲项琵琶”已有了区分。二是当“曲项琵琶”流入中国后,“琵琶”名称实际上就用来专指“曲项琵琶”,“直项琵琶”名称由此就逐渐消失。当然,到了唐宋时期有时还偶被提及,那只是因为引用典故时的一种习惯,且容易使人产生出误会来。其次,“曲项琵琶”被称为“屈茨琵琶”即“龟兹琵琶”,这是那时翻译用词上的差异。唐杜佑《通典》(766—801成书)卷一四二“历代沿革”载:“自宣武以后,始爱胡声。屈茨(龟兹)琵琶、五弦、箜篌 ……胡舞铿锵镗鎝、洪心骇耳。”②这大概是屈茨(龟兹)琵琶最早的文字记载。另外,据《旧唐书》载:“《梁史》称侯景之将害简文也,使太乐令彭雋赍曲项琵琶就帝饮,则南朝似无。”③这是曲项琵琶最早的文字记载,也是琵琶流入中国后的大致情形。以现代音乐学家沈知白的认为:“在汉代,从西域传入我国的是波斯的长颈琵琶(笔者注:或称直项琵琶);在南北朝时代传入的是波斯的短颈琵琶(笔者注:或称曲项琵琶)。”④而今天的琵琶就是由曲项琵琶演变而来的,它与丝绸之路上的外族、外国乐器均有着直接的、极为密切的联系。
一、美索不达米亚梨形乐器的起源
世界最早的人类文明是古美索不达米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其两河城邦文明从公元前6500—6000年始;那时的苏美尔人楔形文字(公元前5200年)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另外,从世界音乐发展史来看,两河流域也是世界上弦乐器最早的产生地,而“苏美尔里拉”和“长颈鲁特琴”是两种史前最早的弹奏乐器。前者琴身呈梯形,是一种小型怀抱弹拨的乐器;后者的形制是由一个娇小的椭圆形共鸣箱和细长的指板所组成。稍后的古希伯来人(“希伯来”意思就是“渡过河而来的人”),也就是今天的犹太人,在其族长亚伯拉罕率领下,从两河流域的乌尔城渡过幼发拉底河和约旦河来到当时被称为“迦南”的巴勒斯坦。在那时已经出现很多的乐器,其中有一种叫“乌德”(Oud,之前称为“巴尔伯特”Barbat)的弹拨乐器,就是以梨形共鸣箱体著称,是那时的“乐器之王”。这种乐器后来不断扩展它的溢出效应,不仅几乎传遍整个阿拉伯地区,而且通过阿拉伯伊斯兰势力的扩张,传到了更西方向的欧洲。在欧洲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发展成为“琉特”琴,一度被认为是最为完善、最为浪漫的乐器⑤。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在公元初的数百年间,我国汉、唐时期的西域文化,主要是来自天竺(今印度)的佛教艺术和波斯(今伊朗)文化,以及希腊文化和草原文化,形成了一种混合型的艺术种类。这种混合文化的代表就是历史上被称为的“犍陀罗”艺术。犍陀罗国是公元前6世纪已经存在于南亚次大陆的国家,为列国时代十六大国之一。其范围相当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现今阿富汗被破坏的巴比扬大佛,就是遗存的著名古代佛教象征之一。该地区曾经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前四世纪又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印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曾派僧人来这里传布佛教。其后,它又归属于希腊人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因此,该地盛行吸取古希腊后期雕塑手法的佛教雕塑,史称犍陀罗式雕塑。同样,一些马上或驼背上演奏的弹拨乐器,也通过犍陀罗地区大量流入到我国中原腹地,像敦煌壁画中的琵琶伎飞天形象,就深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而位于天山之麓的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地区),作为中国丝绸之路通向外国的重要交通节点,反过来也是中亚、西亚地区进入我国新疆地区的前沿重镇,其艺术同样深受外来“犍陀罗”混合艺术风格的影响。龟兹地区不仅本身具有较为发达的音乐,而且在历史上不断受到波斯、天竺以及阿拉伯各国音乐文化的洗礼;又受到我国中原汉族音乐文化的熏陶,而成为当时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汇之地。如果说犍陀罗艺术是那时印度和波斯艺术、希腊艺术的混合集大成者,那么,龟兹艺术可以说主要是中国与西域外族外国艺术混合的产物。据《大唐西域记》“屈支(即龟兹)条”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这就使我们联想到,今天新疆地区歌舞之发达,其实早在千年之前已就是这样了,可见它有着极其悠久的传统。
二、波斯梨形弹拨乐器的流入
据《隋书》中记载说:“今曲项琵琶、竖箜篌之徒,皆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⑥从这个记载至少可以说明像今天我国新疆地区众多的弹拨乐器,基本上和那里的国家及地区的弹拨乐器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例如,“弹拨尔”(Tambur),梨形共鸣箱,琴把细长张五弦用指弹,是由古龟兹的“五弦”演变而来的。这种乐器在阿拉伯也使用,其四弦的称为“弹布尔·夏尔吉”(Tambur-shardī);六弦的称为“弹布尔·布孜尔库”(Tamburbuzurk);土耳其称为“弹布拉”(Tambura),四弦;阿富汗称为“弹布尔”(Tambur),有众多共鸣弦;印度称为“弹布拉”(Tambum),无品四弦。“热瓦甫”(Rawapu),在清代称为“喇巴卜”,与阿拉伯的“拉巴卜”(Rabap)、“列巴卜”(Rabab)同音,但后二者是拉弦乐器。阿富汗有一种弹拨乐器叫“鲁巴卜”(Rabāb),形制不一样。巴基斯坦的一种称为“拉巴布”(Rabab),与印度的“瑟路达”(Saroda)相似。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甫”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是“多朗热瓦甫”,这种曲项的乐器和古代龟兹的“曲项琵琶”有着一定的联系。还有“喀什热瓦甫”和印度的“维那”“坦坎穆里热瓦甫”及“羊倌热瓦甫”。“都塔尔”(Dutar),在伊斯兰国家和印度都有使用。“塔尔”(Tar),印度称“西塔尔”(Sitar);伊朗称“塞他尔”(Sentar);阿富汗称“多塔尔”(Dotar),都是用手指弹奏的,但形制和弦数并不相同。只有中亚的乌孜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突厥语系民族中的较为一致。此外,还有我国哈萨克族的“冬不拉”,塔吉克族的“赛依吐尔”“热布卜”“库木日依”和“巴朗孜阔木”,柯尔克孜族的“考姆兹”,塔塔尔族的“曼多林”,以及藏族的札木聂,等等,它们和西欧的属同类,但大小不一。而琵琶的称谓就是古波斯Barbat的音译,且随着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称谓的语音也有所转变。例如,西藏流传的类似琵琶长颈的叫pi-wang;蒙古叫bi-ba;东北地区叫Fi-fan;流传至日本叫ビワ(bi-wa),等等。
而且,在《简明牛津音乐史》⑦中,开篇第一章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史前”,说明它们已经被纳入到了西方音乐史中,成为世界音乐早期的主要发源之地。在今天若是来研究中国弹拨乐器琵琶,其发源地也就在这一地区。
三、中国的梨形琵琶
“梨形琵琶”被称为“琵琶”,那是进入中国后的称谓。从汉魏时流入的直项长颈类琵琶,并不是我们今天琵琶的祖先,而南北朝时流入的曲项短颈类的波斯“乌德”乐器,这才是今天我国琵琶的前身。上面“引言”提到的(晋)傅玄《琵琶赋·序》中的琵琶,属于直项长颈类琵琶。还有(晋)孙该《琵琶赋》、(晋)成公绥《琵琶赋》、(唐)虞世南《琵琶赋》、(唐)薛收《琵琶赋》等,⑧凡是作《琵琶赋》的几乎都是属于歌咏直项长颈类琵琶,还有一些在诗词中也不乏有这样的描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献记载中,如(东汉)应劭《风俗通·批把条》有“以手批把”,以及在刘熙《释名·释乐器》中有“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的说法,都未明确说明用拨子弹奏乐器,也都是指的直项长颈类琵琶。真正描写曲项短颈类琵琶大概是从唐诗中开始的,这与曲项短颈类琵琶演奏特点,用拨(子)弹拨有关。
“乌德”原就是一直用拨子弹奏的乐器,因此,中国出现琵琶的“弹”与“拨”字,首先是和“乌德”的演奏方法联系起一起的。汉代许慎(约58年—约147年)《说文解字》中,还没有出现“琵琶”这两个字,虽有“弹”字但无“弹弦、弹琴”的解释;有“拨”字,也无“拨弦”的解释。《辞源》中“弹”的解释是“弹奏、弹击”,《辞源》中“拨”的解释是“弹拨弦乐器。也指拨弦之具”。这显然已是指的曲项短颈类琵琶乐器。在唐宋大量的诗词中,“弹”或“拨”字都用,如(唐)白居易《琵琶行》的:“寻声暗问者谁……转轴弦三两声”等。而且,似乎用“拨”字还比用“弹”字要多些,尤其是唐后期至宋,出现“拨”字的频率更要高一些。那么,直项长颈类琵琶用手指奏法,一般就是用“鼓”或“摘”字,另还有用“搊”字。在《辞源》中的解释是“用手指拨弄筝或琵琶等弦索乐器”。其“搊琵琶”的解释是“即手弹琵琶”;“搊弹家”的解释是“弹奏管弦乐器的乐人”。由于用拨子弹奏手法比较单一,实际上它只有“拨”与“反拨”两种基本手法,这在日本的文献⑨记载中最为明确,出现了“返(反)拨”一词,在中国没有这一词,而是以“弹、拨”相对的。因此,可以说现今的弹拨乐器,首先就来指用拨子弹奏的乐器,后来才引申为包括用手指弹拨的乐器。
曲项短颈类的梨形琵琶,早期实际上就是波斯的乌德,不仅乐器本身几乎是乌德的原型,演奏方法也是用拨子演奏的。后来渐渐在乐器结构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敦煌石窟中所画的琵琶乐器是诸乐器中最多的,不仅说明这种乐器在那时的影响力,而且在形制上也是各有千秋,但大都仍以保持着梨形音箱为主。从制作上而言,乌德的梨形音箱都是用几块弧形的条木块黏合而成的,自进入我国后就改成用独块的檀木挖槽,故那时称为“檀槽”,甚至以“檀槽”来替代琵琶这一名称。早期的乌德,梨形音箱内空而大,底部较圆些,因此出音也就较宏大声隆,显然偏于中、低音区的发音。后来制作的共鸣音箱逐渐趋于扁平,出音就向中、高音区发展,这大概是乌德演变成为今日琵琶的开始。从面板材料上看,乌德是用楸木或松木制做的,木质较坚硬些,进入我国后开始改用中国的泡桐木制做,这也为后来琵琶音量、音色的改变奠定了基础。
另外,在演奏姿势上,梨形琵琶是善于怀抱在身与胸前演奏。因此,乌德乐器就以横抱为主,乐器常倾向于水平方向或上水平方向,但也有下水平方向倒抱的。这主要是因为这种乐器是外国游牧民族,骑在马上或驼上弹奏(我们统称为是一种便携式弹拨乐器)。这与我国早期的弹奏乐器,如琴、筝、瑟等放在“几”等桌面上弹奏的乐器显然不同,故而它们会出现那种倒抱演奏的姿势。如果改为坐在席上或矮凳上演奏,就不可能出现那种倒抱演奏姿势。可见,演奏姿势的改变是造成后来乌德华丽转身为中国琵琶的关键一步。
梨形琵琶大致从宋代起,由乌德的横向演奏姿势,转为斜向演奏姿势。虽然关于横向或横弹一词,在文献及诗词中很少记载,故无法细举例子,或许也有可能这种姿势从国外流入时早已普遍成风,没有必要再来加以强调。但是,我们从大量的壁画中可以发现,当时的乌德乐器大都用的是横弹的姿势。例如,比较典型的如“天水麦积山第78龛壁画残片琵琶飞天图”中,这种用肘与下臂夹琴靠胸,用拨子弹奏的横抱式姿势即是。而后来改用斜弹且将琴身放在右腿上,则是演奏姿势的一种典型转变。而且,乐器的形状也已不同于乌德的原样,面阔而大,只是用较大的拨子弹奏仍保留着。例如,著名的(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中,那个女弹琵琶者的姿势就是一种典型的斜抱姿势。在唐宋大量的诗词中,斜抱的诗句或词句出现得很多。例如,(宋)曾觌《踏莎行》:“四弦斜抱拢纤指”;晁端礼《绿头鸭》:“美人斜抱当筵”等。也有作闲抱的如陈亚《生查子》:“琵琶闲抱理相思”;晏几道《清平乐》:“小琼闲抱琵琶”等。
至明代,特别是明代中期,梨形琵琶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一是梨形制式变得较为窄长,尤其是腹部更趋于扁平。一方面出音向着中、高音方向发展,与刚流入时乌德的宏大声隆有了明显的区别,故而有的琴面板上的出音孔也被取消。另一方面,乐器整体较为修长,为下面增加品位(音位)提供了可能,因而出现了相位与品位的区别,大致已发展到四相七品及以上。例如,明代宋濂《元史·志第二十二·礼乐五》载:“琵琶,制以木,曲首,长颈,四轸,颈有品,阔面,面饰杂花。”⑩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载:“琵琶其制……大小斑竹品十二,乌木拨一,用牙嵌。近引面板施描金盘龙文。”11另王圻《三才图会》12中的十三柱(四相九品),已与今天琵琶的形制相当接近了。二是演奏姿势逐渐由斜抱转为竖抱,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但是,在史料中却很难找到这方面的记载。三是由于演奏姿势的转变,促成了右手手法的重大改变,其中真正实现和确立了历史上废拨(子)用(手)指弹的演奏法。最主要的是,这种指弹不是通常横弹乐器上那种大指由里向外、食指或其他指由外向里的、以指肉触弦的所谓“勾弹”;而是一种反向而行之,由大指由外向里、食指或其他指由里向外、以指甲面触弦的正弹法,这是一种最具革命性的转变。这种演奏法及其丰富的表现力,即使在世界弹拨乐器中也是鹤立鸡群、独一无二的,从而使中国琵琶在世界弹拨乐器中独树一帜,同时也成为我国最具特色的乐器之一。
四、一带一路上的梨形琵琶
今天,“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早在汉代,张骞就凿空丝绸之路,加强了我国与西域地区以及中亚、西亚的互通,自然也包括音乐上的联系,使得像波斯的“乌德”能流入中国。之后,海上的丝绸之路也开通了起来。例如,唐代的琵琶能手康昆仑,在那时的首都长安与段善本和尚赛琵琶的盛事,与那时著名的“旗亭画壁赌唱”一样,成为流传千年的文化艺坛佳话。那么,康昆仑是如何进京的呢?据载他进京是走海上丝绸之路。康昆仑是康国人,康国即今中亚细亚萨马尔罕地,在周武帝娉突厥女时,康国乐和龟兹乐同时传入了我国,成为唐代十部乐中的两部乐。据(唐)张固《幽闲鼓吹》载:“元载子伯和,势倾中外。福建观察使寄乐妓数十人,既至,半载不得送。使者窥伺门下,出入频者有琵琶康昆仑最熟,厚遗求通,即送妓。伯和一试奏,尽以遗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凉州》,昆仑求之不与。至是以乐之半赠之,乃传焉,道调《梁州》是也。”13可见,康昆仑入京走的正是海上丝绸之路,他先期到达福建,以擅长琵琶而成为元载长子伯和的门下客。后由于元载和其子伯和同被赐死,他便成为宫廷中的一名乐工,在长安素有“琵琶第一手”的美誉。当然,康昆仑如何流落海外无记载不得而知,但进京是走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记载中是明确的,说明那时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早已开通。我们今天福建南音中的琵琶(南琶),仍保留了唐宋横抱或斜抱的演奏姿势,演奏曲目亦很古老,说不定那时流入福建的琵琶,很可能就是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
显然,正是一带一路使得最古老的“乌德”,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世界上主要的梨形弹拨乐器也就如珍珠般的串连了起来。例如,我国的梨形琵琶于唐以后,在东北亚地区得到了很大的传播。日本大概是一带一路在东方的终点站,在其奈良正仓院中仍存有传自唐代的五弦琵琶一面,以及四弦琵琶多面。日本从中国传入琵琶因用于日本雅乐而得名“雅乐琵琶”(其实琵琶在我国唐代是属于俗乐乐器)。日本后来又有了盲僧琵琶,其中有平家琵琶,比雅乐琵琶小一些,也因盲人用琵琶伴唱而得名。另还有萨摩琵琶,且衍生出筑前琵琶、锦琵琶等。日本至今仍保留着我国唐代琵琶横抱或斜抱的演奏姿势,用偌大的拨子演奏。
在朝鲜,其著名的《乐学轨范》一书中,有“唐琵琶”条记载了韩国唐琵琶的图形、散形及解说。在整个韩国音乐史中,“唐琵琶”在朝鲜前期宫廷音乐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一种重要的弦乐器。在《高丽史·乐志》中所记载的多种乐器中,也包含有“琵琶”,其中用于唐乐演奏的是四弦琵琶,用于俗乐演奏的是五弦琵琶。在《世宗实录·五礼》的文献史料就记载有“唐琵琶”和“乡琵琶”两种名称,这种情况与日本有所相似。这种分类方法是在朝鲜时代(1392—1910)以后才出现。在《乐学轨范》以及《世宗实录·五礼》《国朝五礼仪序礼》中的唐琵琶图,已出现了除四相外的很多品位14。而且,中国式梨形琵琶对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是很有影响力。总之,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同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今天“一带一路”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与提升,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正如上面谈到的,除了原波斯、阿拉伯的乌德向东发展以外,也很早就进入了欧洲腹地,演变出多种琉特琴族的乐器,就是以面平背驼、半梨形音箱为特征的。琉特琴主要指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在欧洲使用的一类古乐器的总称,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为风靡的家庭独奏乐器。于是,在广义的乐器分类中,把类似的乐器统称为琉特属,包括曼多拉、曼多林、西奥博、奥法里昂、西塔隆等乐器,而曼多林和维奥尔琴正是当时的世俗音乐,即游吟诗人的音乐中运用最广的乐器。更甚至把中国琵琶也纳入其属内,这大概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乐器祖先之故。
结语
综上所述,一种乐器的传播与地区人员及文化的交流密切相关。往往由于随着人口的迁移,带来文化等方面的流动,这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我国东南方向上,由于自晋代后人口的大迁移,尤其是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大量流入闽、粤等地,这是如今福建南音与广东潮州弦丝乐、汉乐等乐种形成的主要原因。其间,交通的便利与否则是关键的关键。正是由于交通的阻隔,而使一旦流入进来的音乐,很难再进一步受到外界的变化而变化,这样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当初流入时的形态。因此,像这些乐种所使用的梨形琵琶,就保留了唐宋时的演奏姿势、定弦法、手法等。而在西北方向上,新疆歌舞音乐的发达,也是与历史上的音乐文化的交流直接相关。在东南方向上是从赣南进入的,致使随着苏浙明代昆曲的强盛,影响到闽粤之地。总之,中亚、西亚与我国的新疆地区,都是十分流行这种半梨形的乐器。只是在流入我国中原地区以后,由于我国汉族的社会生活、民族习性、欣赏习惯、审美观念等等方面的原因,致使这种乐器被竖立起来演奏。正由于这一大奇观,也就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技巧奏法。但是,同样在我国的福建南音等乐种,以及受我国影响的日本、朝鲜等国中,却仍然基本保留了唐宋时期的姿势与奏法等。因此,如果着眼于一带一路上的梨形琵琶与其他弹拨乐器,正犹如一串项链上的颗颗璀璨的珍珠。当然,它不是大小质地完全相同的颗粒,但却是有着共同祖先的各各不同的结晶,组成了丰富多彩的弹拨乐器世界。这一切都是一带一路带来的开放、包容、接受、变化的结果,对今人具有极大的启示。
注释:
①庄永平:《中国琵琶文化类编》,三联书店出版社,2018,第413页。
② 杜佑:《通典》,长泽规矩也、尾崎康校订,韩昇译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③刘昫等撰:《旧唐书》,第四册卷28至卷37(志),中华书局,1957,第1076页。
④ 沈知白:《中国音乐史纲要》,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第43页。
⑤ 同④。
⑥ 魏徵等撰:《隋书》,第二册卷13至卷21(志),中华书局,1973,第348页。
⑦ 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简明牛津音乐史》,顾犇译,钱仁康、杨燕迪校订,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⑧ 同①,第298—300页。
⑨ 日本《三五要录谱》,上海音乐学院藏影印本。
⑩ 刘迎胜编:《二十五史新编·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1 王圻:《续文献通考》,现代出版社,1986。
12 王圻、王思义编集:《三才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3 丁如明、阳羡生、李宗为、李学颖编辑,张固:《幽闲鼓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4 张师勋:《韩国音乐史(增补)》,朴春妮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