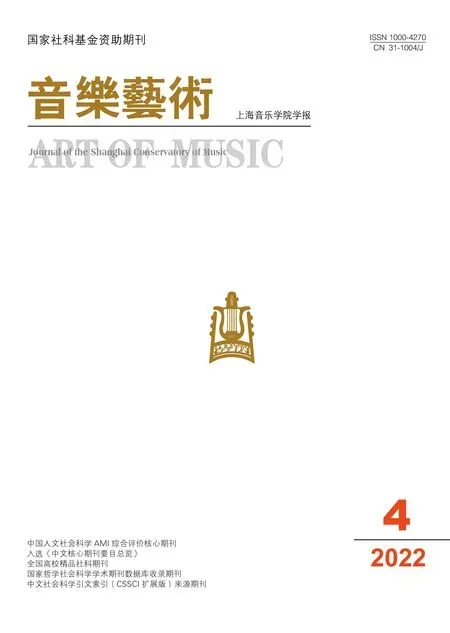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对民歌的利用
陈 星
内容提要: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谣”充分利用了中国民歌,于是便有了根据传统民歌音调重新填词的新民歌。“革命歌谣”对民歌的利用,体现出循着军事斗争进程、在何地打仗就运用何地民歌的特点;不仅利用革命根据地民歌而且还启用革命根据地民歌手的特点;一曲多用和在音调选择上不拘一格的特点。这种作为“革命歌谣”的新民歌还展露出传统民歌重词轻曲的价值取向,并延续了传统民歌的“救星崇拜意识”和批判精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对民歌的利用体现出一切都旨在满足军事斗争需要的实用理性精神。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对民歌的利用,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在近2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的新民歌一直备受关注。但其关注点却一直都是“革命话语”对“民间话语”的利用或“革命叙事”对“民间叙事”的改造。这在一定程度上赓续了“五四”时期“歌谣运动”中的某些研究选项,故而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忽视了对红军各战斗序列及其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语境的了解,未能关注军事斗争对新民歌的影响;二是仅关注歌词而忽视了新民歌的音调特点。同样,在20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
谣”的新民歌也炙手可热。但问题仍是缺乏军事斗争语境,以致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利用传统民歌生成新民歌,仅仅看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事情,而对其他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闽浙赣、湘赣、湘鄂西、湘鄂川黔、滇川黔、鄂豫皖、川陕、鄂豫陕、东江、琼崖)的新民歌则缺乏关注,以致一些结论还值得商榷。本文在克服上述研究弊端和缺陷的前提下,力图就新民歌如何兴起、为何利用根据地传统民歌、如何利用传统民歌,以及这些利用民歌重新填词的新民歌到底起到了哪些作用,进行简要阐释。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新民歌及其历史语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为何存在这种作为“革命歌谣”的新民歌?这得从“革命歌谣”说起。早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共产主义小组的革命活动中就运用了“革命歌谣”①。比如,王尽美(1898—1925)在山东的革命活动中就运用了“革命歌谣”②。在李大钊直接领导的北京长辛店工人运动中也有“革命歌谣”。这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上北方代表的报告中就有提及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兵士运动中,“革命歌谣”也唱得十分响亮。尤其是在海陆丰、左右江、湘鄂赣的农民运动和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开滦煤矿工人运动中,当地的一些传统民歌就被填词为“革命歌谣”成为新民歌,在工运、农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值得一提的是,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在其家乡湖南韶山冲开展农民运动时就充分利用了“革命歌谣”;在执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也曾带领学员到粤北韶关收集“歌谣”,要求学员重视“革命歌谣”④。当时的教员中有彭湃,利用“革命歌谣”在海陆丰地区开展农民运动的领袖(“农民运动大王”);学员中则有韦拔群和方志敏,两人也均是利用“革命歌谣”开展农民运动的。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革命歌谣”大多就是运用传统民歌音调重新填词的新民歌(如湘鄂赣、左右江、海陆丰新民歌)。这些都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利用“革命歌谣”开展革命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韦拔群作为重要领导人的红七、红八军及其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及其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革命歌谣”更为响亮,便是见证。尤其是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韦拔群等人利用壮族“勒脚歌”发展出的“革命歌谣”,在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还不难发现,1927年至1929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发动系列武装起义并创建根据地的高级将领和重要领导人,大多都经受了大革命的锻炼和考验,故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利用“革命歌谣”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利用“革命歌谣”(尤其是新民歌)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利用根据地民歌重新填词发展“革命歌谣”进而使其成为革命斗争武器提供了直接和宝贵的经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在起义之前、之中、之后都有“革命歌谣”助阵;在其后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中,“革命歌谣”更是大有可为。这些“革命歌谣”大多都是用传统民歌音调重新填词的新民歌。
1927年9月底,秋收起义部队攻打长沙不利便向井冈山地区转移。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起义部队)一部抵达井冈的茨坪,并在此设立军政机关,开始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为了发动群众,工农革命军中的宣传工作者就用当地民歌音调重新填词,编创了《雇农苦》《倒苦水》《诉苦情》《新十杯酒》《五恨心》《土地革命歌》《还我地来还我田》《劳苦工农庆翻身》《分田歌》等“革命歌谣”⑤。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新民歌得以兴起的重要标志。在其后几个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中,“革命歌谣”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利用井冈山地区的民歌编创的“革命歌谣”在发动群众和工农革命军开展军事斗争(武装割据)、政权建设(工农兵政权建设)、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破除迷信、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28年1月,秋收起义部队攻占遂川后,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第9连(特务连)党代表罗荣桓(1902—1963)就是举着写有“宣传队”字样的红布旗子、唱着“革命歌谣”到草林圩一带进行宣传和发动群众的⑥。由此可见,只有这种土生土长的民间文艺形式才能为当地民众所喜闻乐见,进而才能发动群众参加革命。这也说明,利用根据地传统民歌音调重新填词编创“革命歌谣”,是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的需要。伴随着茶陵(1927年11月18日)、遂川(1928年1月24日)、宁冈(1928年2月21日)工农兵政权的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利用根据地民歌编创“革命歌谣”并将其用于根据地的武装割据、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已成为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一种重要的宣传手段和形式。1928年4月底、5月初,朱德带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军上井冈,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井冈山会师),5月初合编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使得井冈山根据地更为稳固,并在1928年6月底的龙源口大捷后进入全盛时期。但在“八月失败”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渐进入艰难时期,直至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撤出井冈山,奔向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在14个月(1927年10月至1929年1月)的井冈山斗争时期,“革命歌谣”在红四军及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宣传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初步形成利用“革命歌谣”开展宣传教育的传统,并成为“井冈山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湘鄂西、鄂豫皖、琼崖、陕甘边、湘鄂赣、闽浙赣、左右江的武装起义及其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利用各地传统民歌音调重新填词的新民歌,如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黄麻起义歌》(1927)、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要当红军不怕杀》(1928)、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刘景桂主席到我家》(1927)等,也成为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手段,并像红四军及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谣”一样,在武装割据、政权建设、土地革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1929年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革命歌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赣南、闽西的客家山歌成为发展“革命歌谣”的重要文化资源。比如,1929年4月,毛泽东带领红四军第3纵队到江西省兴国县开展土地革命,颁布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以来第一部土地法规—《兴国土地法》,于是便有《日头一出红彤彤》(“哎呀嘞,日头一出红彤彤。来了朱德、毛泽东,千年铁树开新花。同志哥,工农做了主人翁。”⑦)这首根据当地民歌音调重新填词的新民歌。在红军入闽后,闽西客家山歌更被充分利用,其中邓子恢、阮山等闽西革命根据地重要领导人对利用客家山歌发展“革命歌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他们早在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就已成为编歌能手),于是便产生了一大批根据闽西客家山歌发展出来的新民歌,最重要的一首就是《韭菜开花一管心》。总之,新民歌已在赣南、闽西唱得十分红火。但毛泽东对“革命歌谣”运动却有更高的期待,故在古田会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批评—“革命歌谣简直没有”⑧,于是将“音乐”作为士兵政治训练的一个科目。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十分强调红军宣传队的建设,极大提高了红军中宣传队的地位。这些都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案》),故在红四军及后来的第一军团(1930年6月组建)、红一方面军(1930年8月组建)的宣传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革命歌谣简直没有”的批评,极大促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革命歌谣”的发展,尤其是其中新民歌的发展。
1930年后,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革命歌谣”得到极大的发展。伴随着1931年1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小布)成立,上海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文艺工作者,如李伯钊等)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这使红军各战斗序列及其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谣”运动得到新的发展。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1931年11月7日),赣南、闽西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这使得苏区文艺得以极大发展,其中的“革命歌谣”运动也更为高涨。但尽管如此,利用根据地传统民歌音调重新填词的新民歌仍是“革命歌谣”的主体。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如此,在湘鄂赣、闽浙赣、湘鄂西、湘赣、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如此。1934年2月5日,瞿秋白从上海到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有文献记载,瞿秋白在观看庆祝“二苏大”召开的文艺演出中瑞金云集区演唱的“革命山歌”后,十分兴奋,便对李伯钊等中央苏区的文艺工作者说,这些“革命山歌”平易通俗,浅近易懂的歌词便于开展民众教育,民众喜欢,又好听,又好唱,容易传播,胜过专门创作的曲调。⑨不久,瞿秋白还将“向山歌、民歌学习”写进了《苏区文化教育计划》(1934)中⑩。瞿秋白鼓励苏区文艺工作者“搜集民歌来填词”、发展“革命歌谣”,还亲自动手利用民间山歌编创“革命歌谣”。这就使得民歌对“革命歌谣”的意义进一步体现出来。但十分可惜的是,还未等到这种利用传统民歌音调重新填词的新民歌进一步发挥其功用时,中央红军主力就撤出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路。
从1930年至1934年10月战略转移(长征)之前,新民歌都是红军各战斗序列及其革命根据地“革命歌谣”的主体,并在武装割据、政权建设、土地革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1934年秋以后的战略转移中,这种新民歌在红军各战斗序列都发挥了重要的鼓动作用;在战略转移中,红军还利用长征沿途的民歌音调填词,发展“革命歌谣”,以争取群众支持红军、参加红军。
综上所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对传统民歌的利用,即利用根据地传统民歌音调重新填词形成新民歌、发展“革命歌谣”,进而将其用于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的宣传工作,旨在满足红军及其根据地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的现实需要,从根本上说是“井冈山道路”的一部分,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体现。这就在于,这种作为“革命歌谣”的新民歌,是根据地广大军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故而才能吸引他们去关注其歌词,理解其思想内涵,进而鼓舞他们参加革命并具有旺盛的革命斗志。这似乎就是一位论者说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只有“民族化”才能“群众化”进而才能“革命化”11。这也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何依托革命根据地传统民歌音调重新填词发展新民歌、发展“革命歌谣”的根本原因。
二、“革命歌谣”对传统民歌利用的几个特点
土地革命战争十年间,红军各战斗序列及其革命根据地“革命歌谣”对民歌的利用呈现出了以下特点。
(一)循着战争进程选择不同地区的民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对传统民歌的利用,与土地革命战争进程密切相关,并以满足军事斗争的现实需要为目的。总体而言,土地革命战争可分为四个时期:武装起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期(1927年夏秋至1930年夏)、反“围剿”斗争(1930年夏秋到1934年秋)、战略转移时期(1934年秋到1936年秋)、立足陕甘宁/建立西北大本营(1935年秋至1937年夏秋)。“革命歌谣”对传统民歌的利用就展露出不同时期利用不同地域民歌的特点,即不同时期红军在不同地区创建根据地、展开军事斗争,进而选择了不同地区的民歌发展“革命歌谣”。
从宏观上看,在武装起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期和反“围剿”斗争时期,“革命歌谣”的发展主要利用南方各省(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川、浙江、广西、广东)的民歌;长征时期主要利用沿途的民歌;会师西北后则主要利用陕甘宁民歌。土地革命战争是从南昌起义开始的,在接着的1927年9月至1929年11月两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湘赣边、鄂中、鄂西、海南、黄麻、清涧、万安、广州、湘南、石首、赣西南、弋横、桑植、渭华、平江、霍六、左右江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创建红军;接着在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湘鄂西、黔东、湘鄂川黔、鄂豫皖、川陕、鄂豫陕、陕甘边、陕北等地区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随后,红军则在这些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因此,除西北红军及其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谣”外,红军其他各战斗序列及其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谣”则主要利用南方民歌。1934年秋,反“围剿”失利后,红军主力放弃原有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长征)。于是“革命歌谣”则得益于长征沿途各地的民歌。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并开始扩展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在原来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成)。于是,其“革命歌谣”便利用了陕北民歌“信天游”。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西北后,立足陕甘宁,建立西北大本营。于是,红军及其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谣”就依托陕甘宁民歌,故不仅利用“信天游”,而且还利用“花儿”。可见,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主要利用南方民歌和陕甘宁民歌。
从微观上看,在哪里开展军事斗争就利用哪里的民歌的特点也显而易见。正如前面所说的,红四军割据井冈山时就利用井冈山地区的民歌;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后,就利用赣南、闽西的客家山歌。再如,第二军团(贺龙部)1932年9月在洪湖失利,于是转战湘鄂边,至1934年5月到达黔东,同年9月与红六军团(萧克部)会师木黄,最终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于是,其“革命歌谣”所利用的民歌,就从原来的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民歌变成了湘鄂川黔地区的民歌。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转战川陕,其“革命歌谣”所依赖的民歌也从鄂豫皖边的民歌变成了川陕地区的民歌。伴随着红七、八军失利,奔赴中央苏区归建红一方面军和韦拔群的牺牲,原左右江以壮族“勒脚歌”为主的“革命歌谣”也逐渐淡出。总之,红军各战斗序列及其革命根据地“革命歌谣”对民歌的利用,随着部队驻地(根据地)的变化而变化。这一特点在1934年10月后的整体战略转移阶段体现得更为突出。比如,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遵义地区的民歌就被重新填词为“革命歌谣”12;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创建川滇黔革命根据地,故其“革命歌谣”就利用了川滇黔边的民歌。13再如,1936年9月初,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南洮泯地区,于是便有了作为“革命歌谣”的“洮泯花儿”。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路军)进攻河西走廊,于是甘肃民歌音调也被重新填词为“革命歌谣”。1934年11月红25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到达鄂豫陕边并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于是此时红25军及其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谣”就主要利用了鄂豫陕边的民歌。14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对民歌的利用,循着战争进程,体现在哪里打仗就利用哪里的民歌的特点。
(二)因地制宜:当地民歌、当地歌手
为何会呈现出这种在哪里打仗就利用哪里的民歌的特点?这主要是因为红军的军事斗争(无论是武装割据还是战略转移)从根本上说是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才能赢得战争。但要依靠人民群众,首先就要发动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做群众工作,开展社会动员,就少不了利用根据地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歌音调重新填词的“革命歌谣”。另一方面,红军中相当一部分官兵也都来自根据地(尤其是在反“围剿”时期),故用根据地民歌音调填词的“革命歌谣”就更能为他们所喜欢,故而就更具有教育作用,更能鼓舞士气。由此可见,在哪里打仗就利用哪里的民歌,作为一种“实用理性”,既是土地革命进程所决定的,又是满足军事斗争需要的结果。正因为如此,革命根据地的民歌得到了充分挖掘,尤其那些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歌形式被广泛地利用。比如,第一方面军及其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歌谣”对赣南、闽西客家山歌的利用;红五、红八军及其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革命歌谣”对“五句子”民歌的利用;西北红军及其陕甘革命根据地“革命歌谣”对“信天游”和“花儿”的利用;红二军团及其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革命歌谣”对长阳土家族民歌、“五句子”民歌的利用;广西红军及其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革命歌谣”对壮族“勒脚歌”的运用15,红四方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革命歌谣”对巴渠民歌的利用。这种因地制宜的做法也可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革命斗争的总的方法或路径。
因地制宜还体现在对革命根据地民歌手的启用。比如,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就启用了永新西乡汤溪的民歌手李右莲,并让她参加了红四军的宣传工作。正是这位歌手,在1928年“八月失败”后曾用一首民歌(“工农和红军原是一家人,打倒土豪和劣绅。反水农民莫受骗,回家割禾受欢迎。哎呀嘞,快快回家受欢迎!”)规劝宁岗反水农民(受谣言蛊惑的农民)不要跟着反动派去永新。161929年1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后,则大量启用赣南、闽西的民歌手;尤其在1931年秋冬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之后,启用的赣南、闽西民歌手就更多,尽管此时已有李伯钊、危拱之、崔音波、沙可夫等一批从上海来的知识分子。这些民歌手包括赣南的客家山歌手刘秀章、陈亭秀、曾子贞、谢水莲、刘承达,17闽西的客家山歌手王秋连、张锦辉等。在1933年扩大红军的宣传中,民歌手起了巨大的作用,曾创造了“一首山歌三个师”的佳话。18山歌手不仅能鼓舞红军士气、扩大红军规模,也能瓦解敌军。据曾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彭加伦回忆,在1931年9月7日的兴国高兴圩战斗中,一位山歌手唱道:“哎呀嘞,白匪到了兴国城,今天又到了高兴圩,哎呀,他们一心要消灭我根据地,红军哥呀!快快杀敌莫迟疑!”敌军听到山歌后,战斗力涣散,于是就缴枪投降了。19正因为如此,当时国民党军中也曾有这样一首歌谣:“一怕红军刀枪镇,二怕兴国山歌声,刀枪镇来头落地,山歌声来勾掉魂。”20所以,国民党军就疯狂屠杀民歌手,仅在江西兴国牛坑一次就杀害了十几名山歌手。21闽西著名山歌手张锦辉(1915—1930)也是被敌人杀害的。上述这些事例也间接说明了因地制宜启用民歌手的重要意义。同样,在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等其他革命根据地,当地民歌手也大量被吸收到红军的宣传队伍之中,如湘鄂赣的晏友清、湘鄂西的“姚氏三姐妹”(姚玉兰、姚玉蓉、姚玉莲)和“张氏三兄弟”(张启康、张启春、张启伦),以及鄂豫皖的王霁初、徐光友、徐光华、梁定商等。著名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最早的编歌、填词者王霁初(1890—1932)22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名民间戏班班主,能写戏、能作歌,也会唱歌。除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之外,他还编写了《打商城》《穷人调》《反动派与白军吵嘴》(又称《反动派与白色士兵吵嘴歌》23)等歌曲。可惜的是,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川陕途中,他为了找回一个装满宣传材料的口袋而不幸中弹牺牲。再如,中央红军到遵义时,当地的民歌手也被吸收为红军的宣传员。总之,因地制宜启用根据地民歌手,使其进入革命队伍,并使他们根据传统民歌音调直接编创“革命歌谣”进而为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的宣传工作服务,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利用民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实用原则:一曲多用,不拘一格
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用原则。这就是利用民歌音调时往往是一曲多用,不拘一格。众所周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对民歌的利用也不限于根据地民歌,常常也选择了一些在中国各地都广泛传唱的歌曲,比如《孟姜女》《无锡景》《四川调》等。且不难发现,这些民歌的音调在红军各战斗序列及其根据地都被使用,成为“革命歌谣”中的公共音调。于是便出现了一曲多用的情况。如“仿孟姜女调”的“革命歌谣”就比较多,在红军各战斗序列及其革命根据地都有。如中央红军的《长征歌》、直罗镇战役中的《瓦解敌军歌》、红25军的《红二十五军长征歌》都用的是民歌《孟姜女》的音调。《四川调》(或“泗州调”)的音调也被用来填写了多首“革命歌谣”,如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的《第二次反“围剿”胜利歌》《妇女慰劳红色歌》24等歌曲就运用了《四川调》;红二、六军团历时35天(1935年6月23日至7月27日)的龙山困敌战役中的《包围龙山城》也用了《四川调》。有时,同一首民歌音调在红军同一个战斗序列及其革命根据地,也被反复使用,以至呈现出一曲多用的情况。比如,在红一方面军及其中央革命根据地,“仿无锡景”的“革命歌谣”就有多首,如《白军受苦》《春耕运动歌》《唱起革命歌》等。这种就是一位论者所说的“同曲异词”情况25。为什么会有这样“同曲异词”情况?也如其所说的:“尽管可作为苏区用来填词编歌的曲调浩如烟海,但真正被传歌者所掌握、所熟悉的曲调并不多,为苏区军民所熟悉、所喜欢的曲调更不多。这就要求传歌者将目光投向一些较流行的曲调。更重要的是,基于宣传工作的实用理性和认为旧曲更能奏效的经验理性,也要求传歌者尽量选择一些为苏区军民所熟悉、所喜欢的曲调。于是那些曾被广泛使用的曲调(如《苏武牧羊》《工农兵联合起来》)和广为传唱的曲调(如《孟姜女》《可怜的秋香》)成为编歌者的首选,因为他们深知,只有用这种曲调填词编写的歌谣,才能有事半功倍之功效。接着,这些为苏区军民熟悉、喜欢的曲调就成为一种通用的曲调,在各苏区填入不同的歌词,进而便有‘同曲异词’现象。故归根结底,一曲多用特征仍是以实用理性为着眼点的。当然,一曲多用特征或‘同曲异词’现象的出现,正是以民歌式口头传播方式为前提的。”26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对民歌音调的选用是不拘一格的,唯一的条件是民众熟悉和喜爱。即使是一些歌词格调明显不高的民歌(如《打牙牌》),但因为它的音调民众很熟悉,也被重新填词为“革命歌谣”。这一特点也是追求实用性的结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对民歌的利用,之所以呈现出以上三个特点,都是为了满足军事斗争的需要。
三、“革命歌谣”对传统民歌文化特征的继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虽然具有新的内容,但呈现出对传统民歌的继承。这不仅是音调的照搬,保持原歌词的句式结构、表述风格乃至歌词中衬词的一致性,而且还在于作为“革命歌谣”的新民歌在一定程度上还呈现出传统民歌的文化特征。
第一,继承了传统民歌重词轻曲的特点。中国民歌的音调虽然具有较强的形式感,其音乐形态也十分复杂,但与民歌的歌词相比还显得较为单薄。中国民歌的歌词,不仅具有强烈的形式感,当然这种形式感与音调相关,而且其思想内容也更为丰富。总体而言,中国民歌具有重词轻曲的价值取向。这一特点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声乐艺术(包括戏曲、说唱艺术)整体上重词轻曲特征在民歌中的彰显。但从根本上看,这种重词轻曲的特征无疑是中国儒家音乐思想在中国传统声乐艺术中的体现。就儒家音乐观点而言,音乐要遵从“礼”的秩序。这种秩序既反映在音乐形式上,也反映在音乐内容上。但是,儒家强调音乐必须符合“礼”的秩序,更强调音乐对人的感化和教育作用。于是,中国传统声乐中的歌词(唱词)就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这也就是中国传统声乐为何在演唱上更“重字”的原因。27其实,这种“重字”的背后却是对歌词(唱词)的强调。中国民歌“一曲多用”“分节歌”居多的特点,就是这种重词轻曲价值取向的反映。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展“革命歌谣”的目的在于教育红军广大官兵和革命根据地民众,故在利用民歌的过程中,也继承了传统民歌重词轻曲的特点。这不仅是前面已谈及的“一曲多用”,而且还在于多段歌词共用一个音调的“分节歌”居多的事实。可以看到,作为新民歌的“革命歌谣”,大部分都是“分节歌”,多段歌词共用同一曲调,甚至还增加了原传统民歌的歌词段数。比如,利用《孟姜女》填词的“革命歌谣”,如前述的《长征歌》《红二十五军长征歌》《瓦解敌军歌》,已不再是“四季歌”,而是“十二月歌”。与此同时,传统民歌的“四时歌”“五更歌”“十送歌”“十二月歌”等常见的“分节歌”形式的民歌,也得到了更多的利用。上述均是对传统民歌重词轻曲特点的继承。
第二,显露出传统民歌中的“救星崇拜意识”28。这种“救星崇拜意识”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特征,在传统民歌中也用一定的形式表露出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歌谣”在对传统民歌的利用中继承了这种“救星崇拜意识”。比如说,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不久,江西南昌地区就传出了一首“革命歌谣”—《八一起义歌》:
七月三十一,半夜闹嚷嚷,
手榴弹、机关枪其格格其格格响啊,
闹到大天亮;
莫不是国民党又在闹兵变,
莫不是伤兵老爷又在闹城?
啊噢嘿!噢嘿!噢嘿!
我想到就害怕。
八一大天亮,百姓早起床,
昨夜晚机关枪,其格格其格格响啊,
它是为哪桩?
原来是共产党武装起义,
原来是红带兵解决国民党,
啊嘻哈!嘻哈!嘻哈!
我快活笑嘻哈!29
不难发现,这首歌词中传奇式的笔调就流露出一种“救星崇拜意识”。如果说这首“革命歌谣”中的“救星崇拜意识”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三湾后产生的《三湾降了北斗星》就更明确地展露出了这种“救星崇拜意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宁冈时则有《宁冈来了毛泽东》。在武装起义、创建根据地时期,这种具有“救星崇拜意识”的“革命歌谣”在红军各战斗序列及其根据地都普遍存在。比如,邓小平等人在广西发动百色起义之后就有《邓斌就是大金龙》(邓斌即邓小平);刘志丹等人在陕甘边发展起义后就有《刘景桂主席到我家》(刘景桂即刘志丹);在湘鄂赣则有《湖南来了彭德怀》;在湘鄂西有《来了贺龙军》;在闽浙赣有《江西有个方志敏》等。尤其是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许多关于刘志丹的“革命歌谣”30都在不同程度上显露出这种“救星崇拜意识”,传递出革命根据地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的一种原始、朴素的情感。
第三,继承了传统民歌的批判精神。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民歌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即对封建统治的批判和讽刺,如《诗经·魏风》中的《伐檀》《硕鼠》就具有这种批判精神。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对民歌的利用中也赓续了这种批判精神。比如,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新民歌《骂蒋介石》《抗日反帝歌》《十骂反革命》(均用民间《十送调》的音调填词)、湘鄂赣的新民歌《骂国民党歌》《十骂国民党歌》、鄂豫皖的新民歌《豪绅地主太狠心》《反国民党歌》、陕甘的新民歌《地主坐下吃》等,就可以说是延续了传统民歌的批判意识。这与这些新民歌作为“革命歌谣”的特质也是相吻合的。
结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在发展“革命歌谣”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中国民歌,尤其是各根据地的传统民歌,于是便有了采用传统民歌音调重新填词,旨在宣传革命、发动群众、鼓舞士气的新民歌。这种作为“革命歌谣”的新民歌,其编创体现出循着军事斗争进程、在何地打仗就运用何地民歌的特点。这种“革命歌谣”的编创,不仅充分利用了革命根据地(属地)的民歌,而且还大量启用革命根据地(属地)的民歌手,具有因地制宜的特点。此外,一曲多用和在音调选择上的不拘一格,也是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革命歌谣”编创利用民歌的重要特点。这种作为“革命歌谣”的“新民歌”不仅体现出传统民歌的音调和形式特点,而且还展露出传统民歌重词轻曲的价值取向,并延续了传统民歌的“救星崇拜意识”和批判精神。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对传统民歌的利用体现出一切都旨在满足军事斗争需要的实用理性精神。也正因为如此,这种作为“新民歌”的“革命歌谣”在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割据、政权建设、土地革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释:
①李诗原:《歌曲中的百年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21,第6页。
② 1919年夏,济南学联代表王尽美回乡开展革命活动时就“用《长江歌》调子创作歌曲,教群众演唱,宣传反帝爱国”;“为农民创作歌谣,以唤醒农民”。《王尽美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第91页。
③中国共产党一大上北方代表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说:“我们在长辛店播下了宣传工作的第一批种子,去年五月一日,那里举行了示威游行。应该称赞同志们举行的这次示威游行,这一天召开了有千百个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工人亲自在会上发表了鼓动性演说,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可是仍有一些工人来不及发言。群众大会以后,开始游行,由一千五百名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高举着写有重要标语的旗帜,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增加工作、缩短工时’的口号沿街行进。”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18页。
④ 黄景春:《当代红色歌谣及其社会记忆——以湘鄂西地区红色歌谣为主线》,载《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31 — 37页。
⑤ 刘云主编:《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第221 — 222页。
⑥ 潘振武:《战歌春秋》,解放军出版社,1984,第5页。
⑦ 谢济堂:《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集》,鹭江出版社,1990,第84页。
⑧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第350页。
⑨ 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1950年6月18日),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6,第72页。
⑩ 苏剑:《从客家山歌到革命情诗—闽西苏区的新民歌运动评述》,载《福建党史月刊》,1992年第3期,第17页。
11 李诗原:《红色音乐研究的学科理论与问题框架—音乐学术研究的反思与探讨(四)》,载《音乐研究》,2020年第2期,第94页。
12 遵义县政协文史委员会、遵义县文化馆、遵义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壮歌行》(内部印刷),遵义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编印,1992。
13 王一晋:《红色音乐在川滇黔的传播与发展》,载《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第34 — 41页。
14 中共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歌谣三百首》(内部印刷),中共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印,1985。
15 陈鱼帆:《壮族“歌会”—壮民族文化的“雏凤”》,载《民族研究》,1982年第2期,第59 — 66页。
16 叶福林:《井冈山时期革命歌曲的创作及传唱》,载《党史文汇》,2013年第6期,第64页。
17 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江西苏区文化研究》(内部印刷),2001,第441 — 453页。
18 曹成竹:《从“歌谣运动”到“红色歌谣”:歌谣的现代文学之旅》,载《文艺争鸣》,2014年第6期,第90页。
1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奉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彭加伦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南昌),第95 — 96页。
20 胡建军、邓伟民、傅利民:《江西苏区音乐文化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第31页。
21 同⑤,第243页。
22 华庄:《〈八月桂花遍地开〉的作者王霁初》,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6,第344 — 347页。
23 解放军歌曲选集编辑部编:《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内部印刷),解放军歌曲选集编辑部,1954,第115 — 116页。
24 燕录音、许玉明、汤光华编:《中央根据地红色歌曲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201页。
25 李诗原:《苏区歌谣民歌式传播中的差异及其解读—音乐学术研究的反思和探讨(五)》,载《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176 — 190页。
26 同25,第178页。
27 侯莲娜:《“字正腔圆”三题》,载《音乐研究》,2005年第1期,第104 — 108页。
28 关于这种“救星崇拜意识”,参见姚莉苹《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所蕴含的民间思想》,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56 — 158页。
29 同23,第2页。
30 关于刘志丹的“革命歌谣”,可参见邱桂香:《音乐学分析的跨学科研究效度探讨—以刘志丹题材革命历史民歌为例》,载《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第26 — 31页。